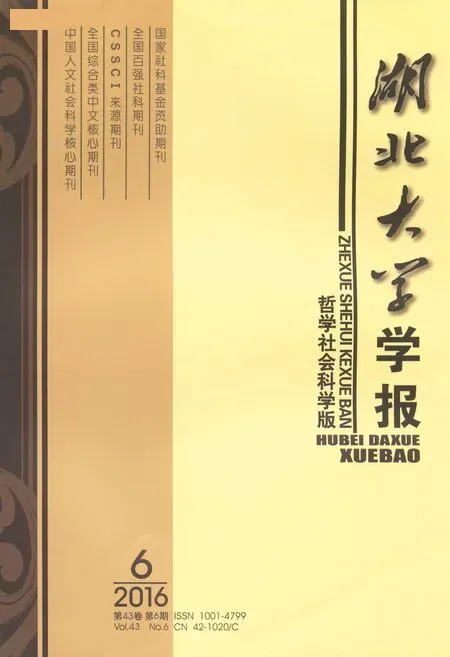主导与推广:晚明士人阶层对传奇传播之贡献
2016-03-11胡丽娜
胡丽娜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主导与推广:晚明士人阶层对传奇传播之贡献
胡丽娜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在晚明传奇的传播系统中,士人阶层发挥主导功能,身兼多重角色。一方面,晚明士人以文本作者、评点者、编辑、刻书家、出版商等身份进入传奇的文本传播渠道,另一方面以传奇排演的指导者、演出中的“串客”以及家班班主等身份参与传奇的演出传播。作为创作者、参与者、推广者和接受者,士人阶层对晚明传奇文本传播的内容、渠道及演出传播的形式、场所都有着重大影响。
晚明传奇;士人阶层;文本传播;演出传播
晚明时期,传奇作为南曲的代表,成就极高、传播极广。吕天成道:“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1]211晚明传奇文本成为人们争相阅读传诵之作,传奇观赏则成为艺术大餐,令人大快朵颐。无论是阅读案头文本,还是欣赏场上演剧,无论以哪种形式,传奇都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传奇如此风靡,士人功不可没。晚明士人阶层将传奇揽入麾下,不遗余力对其进行改造打磨,使其体制愈见完备,内容丰富繁杂。他们将天然的求雅倾向植入传奇文本创作、评点以及演剧环境之中,将晚明传奇的传播过程打上了士人阶层特有的印记。考察晚明士人在传奇传播中的地位、功能、作用等,不仅可以发掘士人阶层对传奇大兴局面的贡献,同时可以审视士人阶层在晚明时期的文化活动,具有一定的文化史价值。
一
戏曲作为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传播途径比偏重文学性的诗、词、文等更为多样。在没有影音记录设备的古代,戏曲的传播方式按媒介主要分为文本传播、演出传播两种。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种方式在戏曲传播系统中所占的比例各有消长。
在元代,以杂剧为代表的戏曲其传播虽然十分兴盛,但因知识分子数量不多,士人阶层尚未形成,社会上对文本有阅读接受能力的文化群体规模并不壮大,加之刊刻与印刷技术不发达,故而当时戏曲的传播与接受多见于观赏过程中,戏曲文本传播的方式并不普遍。直至明代中叶传奇最初成熟之时,演出传播仍然是最有代表性、最广泛的戏曲传播方式。晚明时期,戏曲的演出传播仍然以蓬勃之势向前发展,但独占鳌头的局面已经被打破。随着刊刻技术的提高及传奇案头化倾向的增强,戏曲文本传播开始普及。在晚明,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者都参与到戏曲文本传播与接受中来,传奇的阅读价值得到了正视,文本传播开始在戏曲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
晚明传奇文本传播和演出传播有着各自的传播渠道。文本传播主要倚仗刊刻业的完备,通过书坊发行、文人私刻等渠道进行,而演出传播则依靠演出团体如士大夫家班、民间班社的演出来进行。此外,士人、狎客玩票性质的登台扮演以及路岐艺人行走江湖时的演出也是重要补充。晚明传奇文本传播与演出传播的受众构成也不尽相同。文本传播使传奇文本走入文人墨客、闺阁女性甚至商贾百姓的案头,人们在收藏、品读传奇文本之时获得审美愉悦,产生对于观剧的期待;而经典传奇在演出传播过程中虽体现的是士人趣味,却为更广泛的受众所熟悉、接受和喜爱,上至身份尊贵的皇亲贵族,下至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均可在欣赏传奇演出时获得审美享受。在晚明,传奇的阅读、观赏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娱乐活动,而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晚明之前,在进行戏曲文本创作时,士人作家们并非对自己的作品没有消费期待,盖因戏曲体卑不为正统文人所重视,加之其传播者和受众多为未掌握文化权柄的下层民众,故而在广泛的社会群体中,戏曲文本的阅读需求并不大,戏曲消费大多拘囿于观演的形式,戏曲文化消费的产业链并不完备。在戏曲文化消费勃兴的晚明社会背景下,探讨传奇的传播模式则可沿戏曲的生产、消费全过程进行。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传播的5W模式,即“谁说了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2]35~36。如将晚明传奇置于5W模式之中,“谁说了什么”(Who Says What)作为传奇传播的开端显得尤为重要。“谁”(Who)直接决定了戏曲创作的立场和视角,这在传奇的传播链条中是比较明晰的,即士人阶层。士人们对传统文学观念中传奇的卑下地位毫不计较,纷纷加入创作行列,诸多被列入典章制度的士大夫观戏禁忌在此时期被人为地忽视。无论是创作、阅读传奇还是观剧,在当时社会都成为了雅事。《万历野获编》载:“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吴中缙绅,则留意声律”[3]627,“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4]303。
在戏曲史上,有“场上之曲”与“案头之曲”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实质是戏曲是应注重文学性还是演出性的问题,体现了戏曲创作中的两种不同倾向。晚明经典传奇如《牡丹亭》等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不仅适合案头阅读,也适合场上演出,是案头、场上的双美之作。而少量士人作家执著于使气逞才,片面追求曲词的骈俪艰深和幽雅冷僻,将曲词创作与音律的规范完全脱离开来,使部分传奇失去了演出性,成为纯案头赏玩之作,此类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必不久长。“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的分野,结合传奇传播模式,可以判断为是由“谁说什么”(Who Says)中的“谁”(Who)来把握。简单来说,是由“谁”(Who)的创作倾向所决定的。在晚明时期把握并贯彻这两种倾向的就是士人作家群,他们作为传播链条中的第一个“谁”(Who),地位至关重要。
当士人以作者身份参与到传奇传播中,他们的兴趣爱好、个人经历、创作理念、文学主张等均会影响其文本创作,会在传播的源头对整个传播过程造成先导性的影响。无论是在曲谱的校正、声腔的改造还是在题材的选择上,士人都当仁不让地占据主导地位,具有话语权。首先,传奇在演出传播中虽需要调动各种戏曲元素并依靠演员的表演来传达信息给受众,但曲词、曲谱却需要恪守曲家编排的曲律规范。如沈璟以蒋孝《南九宫谱》为蓝本作《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被称为“词林指南车”[5]235,成为诸多传奇作家作曲的准绳,并被评价为“法门大启,实始于沈铨部《九宫谱》之一修”[6]1。其次,在传奇的结构上,士人作家们逐渐将悲欢离合与天下兴亡的双线结构固定成为标准模式,使金戈铁马之气和才子佳人之思成为传奇的主要内容。这种形式,便是“士人阶层”在说本阶层的故事,这便是“说什么”(Says What)的主要内容。
“对谁说”(To Whom)引出了与受众相关的问题。晚明传奇文本的接受群体以士人为主,另有具有文化水平的商贾、知识女性及寻常百姓。在晚明时期的戏曲演出实践中,伶人艺人的身段虽然是梨园行当代代相传的,角色行头也是有一定之规的,但其曲词、宾白等则受文本所限。在实际演出中,为了追求更好的演出效果,伶人、导演虽可能对演出的细节进行小幅修正,但却不能够任意篡改曲词和音律。盖因在文本传播也很兴盛的情况下,在演出中任意改动曲词恐不为受众所认可,断不能图花样翻新、夺人眼球而失了音律标准。沈德符云:“如太仓张工部(新)、吴江沈吏部(璟)、无锡吴进士(澄时),俱工度曲。每广坐命技,则老优名倡,惧皇遽失措,真不减江东公瑾。”[3]627可见,演出传播虽然能直接调动受众的感官,但仍脱不开士人作家和曲家通过文本固化和曲谱规范所造成的潜在约束力。同时,具有艺术素养的士人阶层作为晚明传奇的主要受众群体,在观剧时对传奇有着较高的审美期待——要求既美目又美听。这种标准,既是士人阶层作为第一个“谁”(Who)而制定的标准,同时也需遵循第二个“谁”(Whom)的审美要求。
戏曲的传播带有双向循环的特点,既有传播,也有传播的反馈。但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比较强调传播的后续延展,并未在传播效果的反馈方面进行回溯。在晚明传奇传播中,接受者可将接受效果、评价反馈至传播者,这种反馈将影响文本作者对脚本的修正以及戏曲后续的演出实践。如张岱家班为刘半舫演出《冰山记》时,张岱就曾根据刘半舫的建议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加戏七出,又再度搬演,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刘半舫极为惊讶。这种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互动体现出传奇传播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则与士人阶层兼具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有关。
综上,晚明传奇的传播模式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述为:掌握了文学权柄的士人作家按照本阶层的审美标准,展开艺术思维,进行曲律制定和传奇创作,借助文本传播和演出传播的双重渠道,向士人、伶人、商贾、出版商、戏班主人、闺阁女性、普通百姓等传达他们对于社会、伦理、情感、道德的认知,使受众包括士人阶层自身,在进行文本阅读和演出观赏的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享受审美愉悦。
二
在晚明传奇的传播链条中,士人阶层身兼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除了编排曲谱、创作文本之外,还积极参与传奇编排及演出并揣摩演唱及表演技巧,时而在幕后对伶人作出指导,时而走到台前客串演员,可以说,士人阶层参与了对传奇进行创作、排演、推广、观赏的全过程。
首先,在晚明传奇的文本传播方面,士人阶层参与了传奇从生产到流通的全环节且发挥了主导作用。
一是士人作家创作了诸多精品传奇,促成了晚明传奇文本的大肆流行。传奇创作是士人作家浇心中块垒的一种方式,起初的目的是为了自我赏玩或借此一吐胸中之气,表达别样寄托,但在传播过程中高水平的传奇为大众所认可和推崇。随着戏曲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刊刻水平的提高,士人们案头阅读的爱好与刊刻业和出版业形成了良性互动,晚明经典传奇大量刊行,人们争相购买。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梅鼎祚《玉合记》“士林争购之,纸为之贵”;张凤翼《红拂记》、周朝俊《红梅记》均炙手可热,在习南音之地广为流传。晚明刊刻业发达,官刻、私刻都很兴盛,万卷楼、大业堂、建阳书局、富春堂等书坊均十分有名。有些书坊为了提高销量、赚取声誉,在传奇刻本中加入插图,在传奇剧名之前冠名“绘像”、“绣像”、“全像”等,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引人眼球,受到读者追捧,销量更大。
二是士人阶层对传奇文本传播的参与延伸到编辑、出版、策划、批评等各个领域,以评点者、编辑、出版商等身份对传奇文本进行推广。陈继儒等名士应书商之邀对时下风靡传奇进行评点,将评点与传奇合并刊行,使得传奇名声更胜,文本更为畅销。谢天佑曾作《靖虏记》、《泾庭记》,又应富春堂之邀校订《白兔记》、《玉玦记》。纪振伦(秦淮墨客)作《三桂记》交由书坊出版。朱少斋作《金钗记》、《英台记》,又校《白蛇记》。一些士人作家如冯梦龙身兼刻书家、编辑、批评家,汪廷讷曾自设印书局发行家刻本。一些著名藏书家同时也是刻书家,如苏州的黃鲁曾、黄省曾兄弟以及王延喆、顾元庆等人,以家中藏书作“家刻本”,除自我赏玩之外,也送亲朋好友等有同好之人雅玩。这些藏书、刻书家们不仅与士人作家交好,而且本人也是士人身份。他们在对传奇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对传奇进行着推广,其刻书的首要目的虽不在牟取利益,但也获取了一定物质收益,从而成为传奇文化消费链条上的从业者,直接推动了传奇文本的流通。
其次,在晚明传奇的演出传播方面,士人直接参与传奇的编排与演出,不遗余力对传奇进行推广。
一是士人以身示范对于传奇的喜爱,登台搬演传奇。随着晚明时期戏禁政策的疲软,士人们公开表现出对传奇的兴趣和热爱,将票玩戏曲当做风雅趣事。“明代传奇竞作,士大夫自许通脱,不复以形迹为嫌。或则粉墨登场,或则持板按拍”[7]14。屠隆常登台串演,其“能新声,颇以自炫,每剧场则阑入群优中作技[3]645。祁彪佳堂兄祁豸佳蓄有家班,除创作和排演传奇之外,其对演鬼戏有癖好。祁彪佳在其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日记“观止祥兄小优演剧”中言其兄于灯下演鬼戏,“眉面生动,亦一奇也”。彭天锡“曾五至绍兴,到余(张岱)家串戏五、六十场,而穷其技不尽”[8]52,最擅长扮演奸雄佞幸之类的人物。“沈光禄金张世裔,王谢家风,生长三吴歌舞之乡,沈酣胜国管弦之籍。妙解音律,兄妹每共登场;雅好词章,僧妓时招佐酒”[1]212。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李蓘归田之后,纵情声伎,放诞不羁,女优登场,至杂伶人中持板按拍。有些士人的传奇演技已颇为高超,不仅能自娱还能感染观众。“颜容,字可观,镇江丹徒人,(周)全之同时也,乃良家子,性好为戏,每登场,务备极情态;喉音响亮,又足以助之。尝与众扮《赵氏孤儿》戏文,容为公孙杵臼,见听者无戚容,归即左手捋须,右手打其两颊尽赤,取一穿衣镜,抱一木雕孤儿,说一番,唱一番,哭一番,其孤苦感怆,真有可怜之色,难已之情。异日复为此戏,千百人哭皆失声”[9]353。薛瑄《读书录》记方以智“吹箫挝鼓,优徘平话之技,无不极其精妙”。《明诗综》记“胡白叔幼而颖异,以狐旦登场,四座叫绝”。黄宗羲《思旧录》记黄梨洲之友谭九子(宗初)与群少年登场演戏,九子扮《绣孺》乐道德,摹写帮闲,情态逼肖。冯家祯长于度曲,丧乱之际,结为歌社,登场宾白,讥慈人陈谟云云。汤显祖虽不曾粉墨登场,但在离开官场之后,也曾“自掐檀痕教小伶”[10]791,“自踏新词教歌舞”[10]567,并且不避讳将这种经历写入其诗中。这些有仕宦经历之人以身演曲或指导演出的行为,在士人们眼中堪为传奇推广之典范。尤其是屠隆等特立独行的话题人物,其粉墨登场敷衍传奇的文化效应,在传奇的传播中具有特别的推广作用。
二是士大夫们组建家班排演传奇,促进了传奇编排艺术的成熟,加强了士人之间关于戏曲的交流,为传奇的演出传播推波助澜。陈龙正《政书》云晚明士大夫们“居家无事,搜买儿童,鼓习讴歌,称为家乐”。士大夫家班主要集中在今上海、江苏南部、浙江东部,正是当时最为富庶、仕进人数最多、文人士大夫最为集中的“江左”之地,士大夫豢养家班的风气一旦兴起,便极易在风俗相近的江南之地蔓延,一时间家乐蔚然成风。上自内阁辅臣申时行、王锡爵始,士大夫甚至市井商人,家中蓄声伎、教小童、建班社、演戏曲,均是平常现象。礼部尚书董份甚至将“青童都雅者五十余人,分为三班,各攻鼓吹戏剧”。一些知名士人如屠隆、沈璟、张岱、冒辟疆、阮大铖、查继佐、李渔、尤侗等都蓄有水平较高的家乐,他们“妙解音律,自按红牙度曲,今松陵多畜声伎,其遗风也”[11]486。士大夫家班常在园林、坐舟、厅堂中进行演出,除了少部分家班仅供主人自己赏玩之外,大部分家班都是能为主人的亲朋好友进行演出的,名气大的家班甚至受邀至外地进行演出。周亮工《读画记》云祁豸佳“常自为新剧,按红牙,教诸童子。或自度曲,或令客度曲,自倚箫和之”,他对家班更是严格调教,“精音律,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8]39。张岱在其《祁奕远鲜云小伶歌》中自言“昔日余曾教小伶,有其工致无其精”。阮大铖给家班“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且其家班搬演剧本,多出自其本人之手,“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8]73。徐锡允亦是对“家畜优童,亲自按乐句指授,演剧之妙,遂冠一邑”[12]23。叶宪祖“花晨月夕,征歌按拍,一词脱稿,即令伶人习之,刻日呈伎”[13]109。对于这些士人作家来说,传奇的创作和表演本就是相通的,并没有将其作为割裂的两端,创作传奇、蓄养家班的目的是为了搬演,体现了“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创作理念。
三
在对晚明传奇传播模式进行分析、对晚明士人参与传奇传播的方式进行梳理之后,可以发现,在晚明传奇的传播系统中,士人阶层把控着传奇传播的内容、形式、渠道,当仁不让占据传奇传播的主导地位。首先,晚明士人对传奇文本进行创作、改编、规范、雅化,催生了诸多富有阅读审美价值的传奇文本产生,使晚明传奇文本大肆流播。其次,晚明士人将阅读传奇文本、观赏传奇演出当做必不可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明确表现出对传奇阅读和观演的喜爱,还通过粉墨登场、执拍按板、指导伶人等以身示范的方式参与到传奇的演出实践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明士人对传奇传播链条的掌控是全方位的。
结合晚明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士人生活状况进行分析,士人阶层之所以能在晚明传奇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士人在晚明时期数量极速增长,规模不断壮大,作为主流阶层,他们对传奇的爱好和推崇对其他阶层具有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有明一朝,广宣文教。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后,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与全国上下对科举的热情两相叠加,使读书入仕成为了广大士人心中的必由之路。当时规定参加科举须具有学校教育经历。一时间国民对教育的热情空前高涨,各地教育机构齐全,生员激增。生员制度本自汉朝创始,历朝历代有之,唯在明代达到其巅峰,中央有国子监监生,地方各州府县有诸生,全国生员数量之巨达历史之最,最多时达到五十万之众。数量之众是士人阶层主导传奇传播之必要条件,地位的提升却是促使士人阶层掌握文化权柄的关键因素。考察中国传统戏曲的发展之路,可以发现历代戏曲的文本创作主体即传播模式中的“谁”(Who)在社会层级方面有上移的趋势。在宋代,参与南曲创作的多是下层文人,他们将村坊小曲进行一定修饰,促成了俚俗南戏的产生。在元代,民族压迫政策之下,诸多不入官场的书会才人在红尘俗世中翻滚,于勾栏瓦舍间流连,既没有侍弄花草、吟诗作赋、游历山水的闲趣,亦没有条件在吃穿用度上追求精巧雅致的格调。为求生计,他们为人润笔或参与戏曲创作,促使杂剧蓬勃发展,一时蔚为大观。至晚明,传奇从文体上来说虽仍跻身于“体卑”的戏曲之列,但其文本创作主体在身份和地位上与前代相较有较大提升,已从混迹勾栏的“郎君领袖”、“浪子班头”转换为居于社会主流阶层的士人群体。士人作家们的倚声填词迎合了时下流行之趋势,更重要的,他们的示范与推崇使观戏听曲成为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他们中不少人生于书香之家、官宦门楣,很多人都有出仕经历,即便并不是位高权重的几品大员,但毕竟身在官场之中,其号召力和影响力更大,对于传奇传播所起到的推广作用更大。
戏曲作者的文化程度和阶层属性对传统戏曲的风格也有影响。宋元时期,戏曲作者多为书会才人,其笔下的戏曲文本往往以俚俗见长,似《西厢记》“花间美人”般曲词风格的杂剧和类似《琵琶记》反映文人趣味的南戏为数较少。而在明代,士人作家按照本阶层的审美趣味,将民间南戏中惯见俚俗粗鄙的成分剔除,使南戏的曲词得到雅化,格调得到提升。至晚明,士人作家通过改造传奇声腔、规范传奇曲律、选择传奇题材、固定传奇结构等方式使传奇成为本阶层所追捧的高雅艺术,并按照本阶层的审美标准对传奇的传播进行了明确的引导。虽然晚明传奇自创作之初就已经打上了士人情趣的标签,但可贵的是,晚明士人并非将传奇独揽为一己阶层赏玩之专好,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不遗余力地将本阶层的审美趣味向大众进行推广,从演出团体的培养组建到传播场地的挑选建造,都体现出由士人阶层主倡且能适应晚明时期大众文化品位的求精、求雅等标准,使得传奇成为既合乎士人要求又能突破文化阶层界限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即便传奇在文本传播过程中会有些文化程度的门槛,却仍能面向各阶层包括最普通的百姓演出而博得满堂喝彩。
第二,结合晚明时期士人阶层的生活史来考察,士人阶层的交游聚会为传奇的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晚明士人的交往并不拘泥于好友圈子,甚至突破了文人集团的范围。除了单纯的迎来送往之外,士人们参加各种社集、雅集、民俗聚会等,在其间举行的堂会之上,传奇演出司空见惯。晚明士人雅集之时,颇多士大夫携家班出演,也有士人于其中客串。如万历三十年(1602)八月十五日的西湖大会,屠隆携其家乐出演。“十五大晴,屠长卿、曹能始作主倡西湖大会,饭于湖舟。席设金沙滩陈氏别业。长卿苍头演《昙花记》宿桂舟,四歌姬从。羡长、东生、允兆诸君小聚始散,而薛素君从沈景倩自李至”。十六日,“诸君子再举西湖之会,以答长卿、能始,作伎于舟中”[14]179。万历三十一年(1603)八月十五日,福州乌石山邻霄台大会,“名士宴集者七十余人,而长卿为祭酒,梨园数部,观者如堵。酒阑乐罢,长卿幅巾白衲,奋袖作《渔阳挝》,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11]445。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朔日,“赴项楚东别驾之招,与王稚方孝廉联席。楚东命家乐演玉阳给谏所撰蔡琰《胡笳十八拍》与王嫱《琵琶出塞》”[15]350。再则,晚明曲宴的兴盛也为传奇传播提供了路径。一些戏剧理论家和活动家如阮大铖、潘之恒等多次举办、主持大型“曲宴”,其间传奇演出成为约定俗成的必备项目。
士人交往中的士妓交谊对晚明传奇的传播亦具有推动作用。明初,高祖制严,对官员狎妓有严厉惩治措施。晚明时期,士大夫重声色、纵情欲,性爱风气日盛,禁止官员狎妓的禁令也不太有管制力,于是狎妓饮酒、携妓冶游等行为在士人群体中比比皆是。一些名士如袁宏道、张岱等从不隐藏自己狎妓的嗜好,李贽甚至挟妓同浴,惊世骇俗。当时妓女多善工词曲乐器,尤其金陵秦淮之畔,能演出传奇的妓女不少,比较有名的有杨元、杨能、顾横波、李十、董白等。晚明传奇作家与妓女交好者也不在少数。叶宪祖宠爱一名妓女,王骥德为其作《南吕·懒画眉·赠燕市胡姬》。王骥德本人常流连妓院,与青楼女子交往甚密。史槃也与众妓女交好,其《南宫词纪》、《吴骚合编》中约有十首套曲为赠妓之作。大规模的雅集、宴会等为士人与妓女的交往提供了社交机会与场所。如齐王孙承彩“万历三十一年中秋开诗社于秦淮,会名士张幼于(张献翼)辈百二十人,名妓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至今艳之”(清光绪甲辰瑞华馆刊本)。一些名士与名妓相恋或纠缠之事在为人们提供谈资的同时也成为了传奇素材。名士王稚登与名妓马湘兰事、屠隆与名妓寇四儿事便被余翘和吴兆改编为《白练裙》传奇,引起轰动。在士人光顾较多的知名青楼之中,也常上演妓女和狎客共同表演的传奇曲目。丁继之、张燕筑、朱维章、沈公宪、王式之、王恒之等常常客串登场。龚芝麓曾挈顾横波重游金陵,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恒之,与酒客丁继之、张燕筑,共串《王母瑶池宴》[16]65。这些串客的演出,虽然以在青楼院中为主,但在狎妓之风兴盛的晚明时期,看客也并不在少数,传播范围有限但影响却也不小。
第三,晚明士人具备的财富、实力与对格调、品位的要求促使传奇演出场所发生重要变化——从勾栏瓦舍、村坊社火、神庙戏台转向厅堂、园林。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出士人阶层的审美意趣,同时也顺应了晚明物质文化发展的趋势。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了消费水平的提升,人们不再以朴素无华为美,而开始崇尚繁复和奢靡。服饰趋向华贵富丽,用品追求精美高档,在精神文化生活上则偏好风雅,讲求格调。品茗、制曲、观戏、游园、搜奇、玩古等,既为士人们的共同爱好又颇有流行文化的趋势。士人有意识地对传奇传播场所进行规划、改造和修建,使观剧场所极尽风雅,正体现出与晚明普适性的文化生活要求相一致的特点。
晚明士大夫之中修筑园林之风鼎盛,士人常于园林中游宴聚会,赏湖光山色,听传奇新声。祁彪佳请造园名家张南垣的儿子张轶凡到绍兴布置寓山别业。汪廷讷在松萝山开湖修建坐隐园和环翠堂,庄园规模之大、景点之多,令人咋舌。修筑园林的原因虽则源于主人之爱好,客观上也为晚明士人的社集、雅集以及传奇欣赏提供了绝佳的场所。园林建起之后,园林主人常搜买童子或伶人,延师教习并修筑戏台,开辟专门场地用于传奇演出。在园林中与三四好友相聚时欣赏传奇为当时士人聚会时常见的项目。晚明名士常聚会赏曲的园林主要有:祁彪佳“寓山园”、潘允端“豫园”、吴昌时“勺园”、祁彪佳“柯园”、顾大典“谐赏园”、冒辟疆“水绘园”等。这些园林往往风景怡人,亭台楼阁相连,石景水色相接,衬得士人们的集会及观剧活动无限风雅。邹迪光所作《五月二日载酒要屠长卿暨俞羡长、钱叔达、宋明之、盛季常诸君入慧山寺,饮秦氏园亭。时长卿命侍儿演其所制〈昙花戏〉,予亦令双童挟瑟唱歌,为欢竟日,赋诗四首》[17]385便是抒发园中观曲的感受。崇祯七年(1634)进士、“鸳湖主人”吴昌时与江南文人张溥、张采、吴伟业等人交好,这一批“复社”同人时常在鸳湖勺园中聚会、听戏、饮酒、作诗,其间家班曾演出《牡丹亭》等传奇助兴。厅堂之上,水榭之边,乃是绝佳赏曲之处。用于演剧的祁彪佳“四负堂”、冒襄“寒碧堂”等均是临水而建,这不仅是因为士人独爱山水以附庸风雅,而是他们深谙听曲之道,认为“竹肉之音,实与山水相发”,于水榭边听昆曲,定能更贴切地品味水磨调的精髓与妙处。对士人们来说,在有水榭楼台、花草掩映的园林中观戏听曲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此时,能让士人们心旷神怡、神思荡漾的除了婉转的昆曲所带给人的感官及精神享受之外,还有外部整体环境和氛围所带来的雅韵。
[1]吕天成.曲品[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2]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M].展江,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顾起元.客座赘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徐复祚.曲论[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6]冯梦龙.太霞新奏·自序[M]//续修四库全书:一七四四·集部·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庞石帚.养晴室笔记[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8]张岱.陶庵梦忆:卷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李开先.词谑[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0]汤显祖.汤显祖全集[M].徐朔方,校笺.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1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五[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0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14]冯梦桢.快雪堂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15]李日华.味水轩日记[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16]余怀.板桥杂记.[M].李金堂,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7]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熊显长]
I206.2
A
1001-4799(2016)06-0078-06
2016-01-08
胡丽娜(1980-),女,湖北京山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暨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暨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化产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