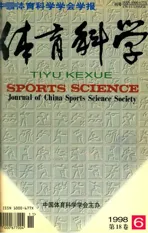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体育治理
2016-03-11赵毅
赵 毅
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体育治理
赵 毅1,2
拜占庭帝国早期始于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统一帝国,终于公元565年优士丁尼逝世。这是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过渡时期,体育治理在对传统的承继中回应着新的时代要求。对原始文献的考察显示,这一时期的体育法制以鼓励体育活动、保障赛事经费、缩减赛事开支、反对贪污挪用为目的。对于战车竞赛、斗兽和角斗等“马戏”活动,法律也给予了不同评价。受基督教影响,与异教相关的竞技活动不复存在,体育立法和竞赛仪式也进行了基督教化的改造,但整体上,基督教对体育治理的影响是改良性质的。帝国整体政治环境的转型也导致了竞技党和体育骚乱的政治化。这是一个体育史上具有承上启下重要地位的时代。拜占庭帝国早期体育治理的经验证明,体育治理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法治则是发挥体育治理积极作用的主要路径。
体育治理;体育法;拜占庭帝国;基督教
1 论题说明
1.1 研究之旨趣所在
历史研究的旨趣,在于人类的好奇心永远指向未知的世界,而对先人的崇敬总是推动人们在面临现实困境时到祖先智慧中去寻找出路。在18世纪,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问,在那个思想变革风起云涌的启蒙时代,充满睿智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理论上卓有创见,而且在知识的各个领域都产生出许多流传后世的杰作[5]。“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他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8]
拜占庭是欧亚大陆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下来,从古典时代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一[22]。现今,拜占庭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除了通史性的整体叙述外①叙述拜占庭通史的经典包括G Ostrogorsky.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Joan Hussey Trans[M].Oxford:Basil Blackwell,1956;A A 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324-1453[M].Madison:Univ of Wisconsin Press,1958;Waren 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英]西里尔·曼戈.牛津拜占庭史[M].陈志强,武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晚近的学者们对拜占庭文史资料展开了更广泛的搜集和更精确的注释,尤其注意从专题史上切入,以填补研究的薄弱环节。在我国学界,受“广义文化观”影响[6],拜占庭研究历经转型,研究视野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展到包含了社会物质生活各个维度的更为广阔的空间①高志民.拜占庭音乐对后世东方教会音乐的影响[J].当代音乐,2015,(15):32-35;郭云艳.再论中国发现的六枚拜占庭中期金币[J].中国钱币,2015,(1):53-59.。然而,颇为遗憾的是,除了高强、董超的一篇论文[10],拜占庭体育文明——包括体育法制文明,仍然处于研究的薄弱环节,这对我们全面认识并系统梳理体育治理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留下了盲区。
暨有研究已经证明,在古代社会(古希腊、罗马[37]以及古代中国[11]),存在着发达的体育文明和法律文明。两种文明之碰撞,产生出了辉煌璀璨的古代体育法制文明。这是一块古典文明的自留地,而拜占庭体育治理之研究旨趣,同样在于证成这一文明的理论框架、方法论基础和之于当代世界的价值。
1.2 研究之现实关怀
东欧那个早已逝去的中古帝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拜占庭学的发展反映出这样一个现象: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人们在物质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对未知世界的求知欲也逐步增强,而当他们观察事物的眼界不断扩大时,人类文明遗产的所有领域都将纳入其视野,这种追求也最终汇聚为对世界文明走向的认识,并回馈现实本身。
由此,本研究之现实关怀表现在:第一,为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第二,丰富体育史和体育法的认识视野;第三,深化对体育法治价值、定位与功用的认识,挖掘其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的独特角色。
1.3 研究之史料来源
我国学界已经日益重视史料在体育史研究中的运用②王邵励.女性参与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问题再研究——基于原典史料的考辨[J].体育科学,2015,(10):74-81;赵毅,[意]萨拉·朱茉莉.体育史和罗马法:文献与方法——约勒·法略莉教授学术访谈录[J].体育与科学,2014,(1):17-21.。就拜占庭帝国体育治理研究而言,史料既有第一手的,也有第二手的;既有现代作家的,也有同时代或稍晚时代作家的;既有法学原始文献,也有文学原始文献。显然,对史料的梳理应当秉持第一手文献优先,同时代作家优先,法学原始文献优先的原则。史料之搜集还需回答如下前提问题:拜占庭帝国从何时开始?如何分期?为何本研究仅局限于帝国早期?
尽管备受争议③比如Bury认为,“拜占庭帝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罗马帝国直到1453年才灭亡。”J B Bury.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Arcadius to Irene(365 A.D.to 800 A.D.)[M].London:Macmillan,1889,preface,V。相关综述参见,陈志强.拜占庭史研究入门[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0-134.,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是从君士坦丁皇帝重新统一罗马帝国的公元324年[31],或者其都城——君士坦丁堡正式启用的公元330年[5]开始的,并以这个首都最终于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克且长期占领为结束。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段,横亘古代与中世纪两大历史分期。本研究只选取拜占庭早期(始于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统一帝国,终于公元565年优士丁尼④史学界之“查士丁尼”在罗马法学界则译为“优士丁尼”,前者按英文Justinian译出,后者按拉丁文Iustinianus (Justinianus)译出,本文在非直接引用时,取后一种译法。逝世)作为分析对象⑤此处采用专事早期拜占庭研究的我国历史学家徐家玲的划分方法。徐家玲.拜占庭的历史分期与早期拜占庭[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30-36.,这是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过渡时期,“为此后1 000余年内拜占庭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32],具有独立且独特的研究价值。研究对象的限缩有助于更为深入、有效地探讨这一时期的体育治理政策与立法。
这一时期重要的史料包括公元438年狄奥多西二世组织编纂的《狄奥多西法典》,优士丁尼皇帝于公元528年至533年颁布的《法典》、《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公元约500—565年)所著《战史》、《秘史》,另外还有大量编年史、人物传记、碑铭、纸莎草、考古实物、建筑景观等。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专题史,故下文将抛弃通史写作惯行的时代切割法,而是基于研究之侧重,分4个部分进行论述。在第2和第3部分,本文将在梳理帝国颁布的第一手法律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考察体育赛事和承袭古罗马传统之“马戏”的法律治理状况。在第4和第5部分,本文将视野进一步扩大,通过揭示帝国早期在宗教与政治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考察这一时期重要意识形态转型对体育治理带来的深刻影响。
2 体育赛事的法律治理
东、西罗马帝国在分治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意识形态都出现了较大差异,特别是几乎所有拜占庭帝国所占据的东地中海区域都在历史上经历过希腊人的统治[51],“正是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在罗马帝国框架内的融合,才引出了我们所知道的拜占庭帝国这一历史现象”[45]。尽管如此,拜占庭人仍然渴望自称为罗马人(Romaioi),“宣称他们自己的传统是罗马的传统”[17]。罗马的体育活动显然是拜占庭人冀望保留的“传统”的一部分。体育治理亦在对传统的承继中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这从原始文献保留下来的体育立法史料中可窥一斑。
2.1 鼓励体育活动,保障赛事经费的立法
当君士坦丁皇帝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建立其都城时,他就打算建立一个第二罗马,“他鼓励意大利贵族家族在新都建立豪宅,同时向新都民众发放面包和竞技比赛票”[17]。然而,谁为免费发放的“竞技比赛票”买单?一种说法认为,竞技活动花销的亏空部分由国库来补助[1,18]。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君士坦丁皇帝专门颁布了法律,规定竞技比赛由城市长官举办,费用也由城市长官筹措,这其中,既包括了征税而来的收入,也有城市长官自掏腰包所作的捐献[38]。后一种说法可能更具说服力,因为在优士丁尼《法典》(CodexJustinianus,在标注中简示为C.J.)中,君士坦丁皇帝颁发的这一以鼓励体育活动为目的的敕令被完整记录下来:
C.J.11,40,1。朕虽然不鼓励公共消遣,但还是提倡市民们在竞技场上重建与力量和技巧相关的赛事。另外,由于城市长官希望通过迎合人们的口味与欢愉以获得人民的支持,朕允许他们主办这类赛事,只要他们能够承担费用[48]。
在拜占庭帝国早期,实行城市自治制度,“城市并不支付长官们的薪俸”[16]。所以,能够担任这一职位的,往往都是富人。通过民选产生的城市长官还必须向帝国缴纳任职费用,根据《狄奥多西法典》(CodexTheodosianus,在标注中简示为C.Th.)记录的公元384年10月23日由格拉蒂安、瓦伦丁尼安和狄奥多西一世联合颁给元老院的一个敕令(C.Th.6,4,25),4种城市长官职位各需花费250磅到1 000磅白银不等[50]。这可能是向国家证明自身经济实力的一种表现,城市长官担子不轻,必须筹措城市的经费,“城市举办的各种庆典,包括祭祀、竞技,以及灾荒年份救济灾民,都需要城市里的富裕市民捐钱,城市长官也必须带头捐献”[18]。显然,上有国家政策推动,下有“经费”来源保障,体育在帝国早期的发展是顺利的。君士坦丁堡建成了一座能容纳5万人的竞技场,其不但用来举办体育赛会,也用作国家的公共活动[12]。
国家对赛事活动经费的保障还可见于优士丁尼《法典》收录的,颁布于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皇帝执政时期的一个敕令:
C.J.11,41。如果按你所说,行省总督将公共赛会的经费用于修缮城墙,该行为将不可撤销,因为这是出于对大众福祉之考量。但是,在城墙修缮完工以后,竞技场所需之正常花费应一如古代惯例予以保证。这样,一方面,通过完成修缮城墙这一公共安全上的大事,城市的防卫获得了保证;另一方面,在城墙完工后,运动会也将得以举行[48]。
这些立法整体上奠定了拜占庭帝国早期体育治理的基础。C.J.11,40,1点明了竞技活动的价值,它是力量和技巧的表现,是人民欢愉之源泉,也是帝国和官员获得人民支持的重要媒介。C.J.11,41则将竞技赛会与修缮城墙相提并论,其隐藏的含义是:除非将赛会经费用于后者,即除非出于公共安全之需,其他一切挪用行为皆为违法。这说明,帝国统治者高度重视体育赛事的作用,体育治理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2 缩减赛事开支,反对贪污挪用的立法
《狄奥多西法典》中出现了大量赛事组织立法,这些立法又以缩减赛事开支,保障赛事秩序为核心。比如:
C.Th.15,9,1。瓦伦丁尼安、狄奥多西和阿卡狄流斯皇帝致元老院:不允许任何私人在运动会上将丝质礼服作为礼物分配。通过这一敕令,朕也再次告诫,除了执政官外,不允许任何人将金牌或者象牙奖牌作为礼物颁发。在举办公开比赛时,礼物应该是银币,奖牌应由象牙材料之外的其他材料制成。银币的规格不能超过惯例,1磅银要制成60个硬币。朕鼓励将此等奖励规格降得更低的行为,并认为此等行为值得尊重。公元384年7月25日于赫拉克勒斯,里克摩尔和克莱尔库斯担任执政官[50]。
这一敕令详细限定了赛会奖品制作规格和颁发程序,昂贵的黄金、象牙制品和丝质衣物被禁止作为奖品颁发,例外则是经执政官允许。在两年以后,格拉蒂安、瓦伦丁尼安和狄奥多西皇帝致禁军长官路福努斯的一个敕令中,黄金制品的使用例外受到了进一步限制(C.Th.15,5,2):“所有的裁判官和市民都应知晓,这些表演不会颁发任何以黄金制成的奖品,唯一的例外是执政官下令,且颁发的对象是朕认同已经作出了丰功伟绩的人”[50]。到了公元409年,奖励的标准被进一步降低,霍诺留和狄奥多西二世致城市禁军长官安忒米乌斯的敕令规定,“每份礼物或者奖品不得超过2罗马币”[50](C.Th.15,9,2)。
如何解释这些缩减赛事奖励标准的立法?因为表面上看,这与古罗马传统似乎并不相符。根据塔西佗在《历史》中的记载;“但是只知道花钱的皇帝却一直给赛马师修造马厩,在比赛场上接连不断地举行剑奴比赛和斗兽比赛,并且一直在浪费金钱,就好像他的财库里的钱已经多得放不下似的。”[25]吉本更是形象地描绘道:“罗马皇帝为装饰豪华场面,不惜工本大手笔投资。很多记载提到大竞技场的摆设都是用黄金、白银和琥珀制成。”[2]这是因为罗马帝国晚期多年战乱、商道中断、经济衰退,导致了国库空虚,无法支持基本的奖励开销吗?但事实上,与政局动荡的西罗马相比,东部的拜占庭帝国无论政治还是经济状况都相对稳定,“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了东罗马帝国商业贸易的兴起,……晚期罗马帝国社会中上层分子特别是富有的商人纷纷迁居到帝国东部”[4],帝国境内的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和安提阿更是成为商贸兴盛的国际大都市。因此,仅从拜占庭帝国的经济状况不及罗马帝国盛期来解释赛事开支的减缩,似乎不具有太大的说服力。而且,即使4、5世纪在整体上比2世纪的五贤帝时期衰败,但国库并不需要为赛事开支买单,因为前已述及,这主要归城市长官和城市财政负担。
更可能的一种解释,是这些立法意在通过反奢侈腐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当然,遵循罗马人遗留下来的法律传统,这样的政治考量是通过法制手段实现的。罗马人早有先例通过法律规制奢侈行为。在罗马共和时期,有大量专门立法不分公私地规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方面的过度开支[30],目的在于控制经济,纯洁风气,并最终利于统治者政治目的的实现。在体育活动方面,针对从非洲进口动物在竞技场举办斗兽比赛的风气,公元前103年出台的《奥菲丢斯法》要求对此进行适量限制[41]。在比C.Th.15,9,1更早出台的一个敕令中,我们能清楚地感受拜占庭皇帝反对奢侈举办赛会,限制城市长官以此捞取政治资本的考量:
C.Th.15,5,1。瓦伦丁尼安、瓦伦斯和格拉蒂安皇帝致禁军长官普罗布斯:无论是市政官员还是民间牧师发起的赛会活动,只要是基于城市管理和古代习俗需要的,都不应由城市长官管理,如果城市长官高额花费金钱举办赛会,以挣得市民的喝彩,应将其调至赛会能够正常、合适且勤勉地举行的其他城市。如果有人能提供赛事的开支和花费,赛事可以由其举办。公元372年4月25日于特雷尔,莫得斯图斯和阿里特乌斯担任执政官[50]。
这一敕令显示,一般的赛会如果能由更低级别的市政官员或者民间牧师发起,城市长官就没有必要为此负责。显然,这样可以节约城市长官大量开支。如果私人能够自行举办赛会,则因不用耗费市民和城市的钱财而予以优先鼓励。敕令还显示,赛会举办应以“正常”、“合适”和“勤勉”举行为标准,高额花费金钱举办赛会则有悖于这些标准,城市长官由此将受调职处分。在C.Th.15,9,2中,霍诺留和狄奥多西二世更明确地规定:“城市长官不能因对喝彩的渴求而丧失谨慎与理智,由此既带走各城市元老院的财力,又对官员的宅邸和市民的财富造成威胁。”[50]这些反对奢侈办赛的立法,可以有效预防腐败,维护赛事秩序,更重要的是,可以使运动会的举办与民生不发生冲突。
既然国家极为重视节俭办会,自然不能容忍任何贪污挪用行为。首先是针对体育赛会负责人,即城市长官的反贪污挪用立法:
C.Th.15,5,3。霍诺留和狄奥多西二世致禁军长官安忒米乌斯:在从城市或行省调入另一个城市和行省时,任何城市长官不得带走任何用于战车竞赛的马匹或者赛车手。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城市长官无节制地追求民众崇拜,耗尽城市的资源,干涉各城自有的节庆活动。如果任何人有违此令,皆将受到专门法律的处罚。公元409年8月6日于君士坦丁堡,霍诺留第8次担任执政官,狄奥多西二世第3次担任执政官[50]。
这一立法后为优士丁尼《法典》完全沿袭(C.J.11,40,1),暗示私占战车竞赛马匹与赛车手的现象是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一种“潜规则”。作为帝国最流行的竞技表演项目,拥有好的赛车手和马匹,就能赢得市民更多的支持,由此更易获取“政绩”。这可能是城市长官希望私占优秀车手与马匹的原因。但是,这一敕令仍然留下疑点:第一,赛会既然主要由城市长官捐资或者筹款举办,城市长官为何不得拥有用于赛会的马匹?马匹之所有权为何人?第二,“专门法律的处罚”为何?对体育领域的违法行为,处罚将是民事性质的(返还原物)、行政性质的(罚款、调职)还是刑事性质的(自由刑)?第三,贪污挪用立法只适用于城市长官吗?城市长官之外的主体如有这些行为,是否会被处罚?
优士丁尼《法典》记录的公元381年的一个敕令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
C.J.11,40,3。格拉蒂安、瓦伦丁尼安和狄奥多西皇帝致城市禁军长官瓦伦里乌斯。任何基于其私人方便或利益使用朕或执政官用于公开战车竞赛马匹的人,将被罚款黄金1磅[48]。
这是一份珍贵的古代晚期体育行政法原始文献,目的在于对体育领域内的贪污挪用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敕令详细规定了处罚适用的主体(除皇帝与执政官外的“任何人”)、处罚的构成要件(“基于私人方便或利益”使用用于公开战车竞赛的马匹)和处罚的内容(罚款黄金1磅)。可以发现,战车竞赛马匹似乎属于珍贵的国家财产,只能由皇帝或执政官支配,即使城市长官也无权挪用。对赛马的保护和合理使用有利于赛事顺利进行,并保障竞技的精彩程度。
2.3 小结
形式上看,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体育法制具有鼓励体育活动、保障赛事经费、缩减赛事开支、反对贪污挪用的功能。可以发现,拜占庭的统治者将支持体育活动作为赢取民意的重要手段,对体育活动的鼓励和赛事经费的保障有巩固政权合法性的目的。去除时代的局限性,通过法律形式确定的反奢侈办赛和要求体育主管官员廉洁自律的规定在今天仍然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3 “马戏”的法律治理
C.Th.15,5,3 和C.J.11,40,3已经显示,拜占庭帝国早期存在专门的法律保障战车竞赛顺利进行。始于古罗马传统,包括了战车竞赛、斗兽和角斗的娱乐性质的“马戏”在体育治理中扮演着特殊角色。然而,三者在拜占庭时代的命运并不相同。《狄奥多西法典》第15卷专门在第10、11、12三题分别收录了与战车竞赛、斗兽和角斗相关的立法。因此,本部分将首先揭示历史语境下“马戏”作为体育范畴的客观性,再按照《狄奥多西法典》的顺序,讨论战车竞赛、斗兽和角斗在拜占庭帝国早期的法律治理状况。
3.1 作为体育范畴的“马戏”
“面包与马戏”语出公元1~2世纪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Iuvenalis),讽刺的是当时贵族用免费的粮食和流行的娱乐(斗兽场的演出)来安抚、拉拢平民的政策,也寓有平民胸无大志,安心充当食客和低级娱乐之意。马戏属于体育范畴吗?如果是,它显然与希腊传统和现今我们对体育的认知存在差异。在古希腊,体育是通达神灵的手段,是德性的象征,是体现美的竞戏,然而,“古罗马人不像希腊人那样崇尚贵族生活,体育运动与休闲娱乐二者缺一不可”[27]。从古罗马开始,体育从身体享受变成了视觉冲击,体育运动变成了野蛮的、暴力的和流血的运动,性质正在发生着改变,先前主动的参与变成如今被动的观赏,游戏的主体正在发生着角色的互换[13]。事实上,“体育”的范畴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下讨论才有意义,正如斯坎伦想要厘清的那样:
“由于体育活动在不同的社会重现并且可以从历史上追本溯源,因此人民可能会误认为类似体育活动在本质上都具有相同的功能。……只有当我们认为一个社会里被称为‘体育’的活动是由另外一个社会的该类活动演变进化而来或者受到了另外一个社会活动的影响时,对这些活动的‘历史’的讨论才具有意义”[26]。
所以,当古罗马人将希腊人的竞技项目与自己的某些公共比赛相结合时,他们也将希腊人的竞技项目彻底转变成了一种娱乐表演,其意义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但是,这仍然不妨碍我们用“体育”称之,它所包含的活动范围事实上是一种社会的构建,“几乎每一个社会都沿用或创造了大量的休闲活动、娱乐性的竞赛,也即我们现在普遍指定的‘体育’这一名称所代表的内容”[26]。所以,在体育史家看来,希腊与罗马的节庆尽管不同,但都是体育节庆,只是在前者,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体育场并参加比赛,在后者,则演变成为专业的角斗士为感兴趣的观众表演[29]。
角斗史研究者也专门讨论过角斗是否为体育竞技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体育竞技由两个要素构成,一为人们出于本意进行肢体对抗,一为受一定规则约束,角斗就正好符合这两点[14]。与现代观念不同处在于,角斗中的死亡是比赛的一部分,且往往是蓄意而为的,现代的体育竞技有专门规则避免伤亡事故。正如顾拜旦男爵在《体育》中写道,“任何一个机构不可能持续千年而不走样,不变形”,“体育”的内涵与外延也是如此。所以,在历史的语境下,“马戏”作为体育范畴是客观的,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体育治理也包括了对各类承袭古罗马传统之“马戏”的治理。
3.2 战车竞赛的法律治理
战车竞赛也称马车竞赛,是古罗马历史悠久的运动项目,出现时间甚至早于角斗。菲克·梅杰说道:“角斗士游戏在公元前4世纪末5世纪初进入罗马人生活之时,两种大众娱乐形式已经成熟:双轮马车竞赛和舞台戏剧表演。”[9]罗马时代战车竞赛的固定场所一般是马克西默斯竞技场(Circus Maximus)。战车竞赛的赛程一般为:主办者举旗发令后,分属不同车队的四马双轮车——有时是两马双轮车或三马双轮车——立刻从起跑位置出发。赛车手必须驾车围着竞技场中344 m的障碍物跑4圈。赛车手有摔死摔伤的风险,但也很受民众欢迎,经常在比赛中一举成名,名利双收[9]。
然而,社会上的知名度高,不等于法律地位就高。优士丁尼《法典》收录的公元396年的一条敕令规定:
C.11,40,4。如果城市里的公共门廊或者任何可放置雕像之处挂有穿着短衣的小丑、皮肤起皱的战车手或者恶俗演员的画像,皆应立即被移除。对于这等堕落之人,将他们的画像在任何圣洁之处展出皆为违法。但是,朕并不禁止他们在戏院或者竞技场的入口处摆放[48]。
对优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Digesta,在标注中简示为D.)的整体考察显示,赛车手的法律地位介于演员与运动员之间。作为“马戏”表演者,赛车手并无混斗、角力、拳击等传统竞技项目的运动员可以享受的免税(C.10,63)、免监护义务(D.27,1,6,13)等法律上之特别优待。但赛车手也与被视为“贱业”的演员不同。D.3,2,4pr.显示,赛车手和运动员皆不受社会唾弃。
《狄奥多西法典》收录的敕令显示,战车竞赛享受国家福利,一些赛马可以获得国库财政供养:
C.Th.15,10,1。瓦伦丁尼安、瓦伦斯和格拉蒂安致城市禁军长官阿莫皮流斯:朕规定,在帕尔玛蒂安马和厄尔谟吉尼安马因为战车竞赛的不确定风险或者经年累月的劳累或者其他原因,已经失去了继续参加战车竞赛的能力时,国库中的粮草仍然可以供应给它们。但朕并不阻止竞技党的负责人按照惯例,售卖西班牙血统的赛马。朕还要求大家遵守下列规则,从这里的希腊赛马一经售出,名字就不能再更改。公元371年1月1日,格拉蒂安第2次担任执政官,普罗布斯同任执政官[50]。
帕尔玛蒂安马和厄尔谟吉尼安马是拜占庭帝国当时最优良的赛马,西班牙血统的赛马与前两者相比,在品质上要稍逊一筹[50]。前两种赛马被法律赋予了专门的由公共财政供养的优待:即使它们不再能在竞技场中出赛,也不会被卖出。从马的角度看,这里有一定的动物保护主义因素;从人的角度看,这个规定主要在于照顾与赛马朝夕相处的战车运动员的感情,利于后者发挥出更佳的竞技状态。希腊赛马不能改名之规定作何解释?可能是出于保证交易安全和维护竞赛秩序之考量。希腊赛马品质比上述几种赛马又要差些,禁止它们在售出后改名,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以次充好的情况[50],最终影响战车竞赛秩序。
3.3 斗兽的法律治理
斗兽即把野生动物送上角斗场,既包括了动物之间的对抗,也包括人兽对抗。据说,第一次斗兽比赛发生在公元前186年罗比里奥尔举办的庆祝朱比特的路迪节上[9]。法律对斗兽比赛的规制也随之出现,在公元前170年,罗马元老院通过了一个立法,禁止从非洲运回野生动物[9]。在《狄奥多西法典》中,与斗兽立法相关的敕令主要有两个,一为 C.Th.15,11,1,这是在公元414年由霍诺留和狄奥多西二世颁布的敕令,规定出于安全因素考虑,任何人杀死野兽的行为皆不需承担法律责任,但须由皇帝专门授权。这类似现代法上的行政许可。敕令衡量了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第一,公共安全高于体育娱乐活动,由此,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下,杀死野兽的行为合法;第二,对杀死野兽之授权并不会阻碍斗兽活动的开展。这一敕令仅授权杀死危害公共安全的野兽,而此类情况并不多见。但敕令明确规定,人民无权进行捕猎和售卖野兽行为。言外之意在于,一旦野兽的捕猎权和售卖权放开,国家的野兽资源将减少,无法支持斗兽竞技顺利开展[50]。第二个敕令为C.Th.15,11,2,这是一个有关野兽运输程序的行政命令。该敕令在公元417年由霍诺留和狄奥多西二世颁布,规定边境的王公在向皇帝运送野兽时,出于节约花费目的,在任何城市皆不得停留超过7天,违者罚款黄金5磅,缴入国库[50]。优士丁尼《法典》沿袭了这一规定(C.J.11,44,1)。
在优士丁尼时代,《学说汇纂》中记录的两条与斗兽相关的立法颇值注意:
D.48,8,11,1。莫德斯丁:《规则集》第6卷:如果一个奴隶未经判决即用于斗兽比赛,奴隶的出卖人和买受人皆有责任承担处罚[49]。
D.48,8,11,2。莫德斯丁:《规则集》第6卷:根据《佩特罗纽斯法》和与之相关的元老院决议,主人无权裁决将自己的奴隶用于斗兽。但在主人理由充分且将其送至长官处接受审判后,奴隶可被判处该项刑罚[49]。
这两个法言深刻体现了处于转型时代的拜占庭帝国早期法律的特点:既有深厚的罗马法渊源,又融入了基督教兴起后在法律中体现的人道主义特征。D.48,8,11,2中提到的《佩特罗纽斯法》(LexPetronia)全称为《关于奴隶的佩特罗纽斯法》(LexPetroniadeservis),经史家考证,可能颁布于公元61年[21],是尼禄皇帝的统治时期。让人斗兽事实上是一种死刑刑罚。《罗马十二帝王传》(DeVitaCaesarum)中的《克劳狄转》记载,如果有人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克劳狄皇帝会从重处罚,判决犯人与猛兽搏斗[23]。随着罗马疆域扩张和经济发展,奴隶(主要是战俘)的来源变少,特别是伴随着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之普及,奴隶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在公元2世纪哈德良皇帝执政时期,主人被废除了随意杀害奴隶和把奴隶卖给角斗场的权力[3]。及至拜占庭帝国初创,君士坦丁大帝专门颁布敕令,宣布故意杀死奴隶与杀人同罪(C.9,14)[48]。优士丁尼皇帝此处的两条规定,同样意在保障奴隶的公正审判权,禁止奴隶主滥用私刑。
合法投入赛场的“人”的减少,也预示着斗兽活动走向末路。史载,公元6世纪初,斗兽遭到官方取缔[9]。如果这一说法为真,被取缔的最多是人与兽之间的对抗,而让野兽互相争斗的比赛方式不会消亡。有历史学家指出,无论是在拜占庭帝国,还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各封建诸侯国,斗兽仍然在有组织地延续。为了观众的兴趣,人们甚至从未间断努力发明新奇的斗兽方式。直到1689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当局才迫于压力,颁布法令,严禁“在阿姆斯特丹市及其行政辖区内斗熊、斗牛、斗狗等一切斗兽行为”。而且,出台这项法令的目的,不是政府同情可怜的动物,而是出于公共安全考量[9]。
3.4 角斗的法律治理
与传统观点认为角斗起源于埃特鲁斯坎人(Etruscans)不同,最新的考古研究证明,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代罗马人就从意大利半岛的南方人那里,引入了角斗表演[14]。在优士丁尼《法典》的英译本中,美国罗马法学家斯科特写下了这样一段评注:
“罗马的角斗比赛既血腥又残忍,它们是贵族与平民最喜欢的运动,是国家颓废和堕落的证据。……庆祝这一仪式变成了一个消遣,被认为展示了男子的强壮、往日的荣光和家庭的守护神,对血的渴求是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有钱人经常花费巨资出于这个目的进行角斗表演。……逐渐,角斗从私人仪式变成了公共演出和政府活动。在葬礼,祭坛和竞技场频繁发生。”[48]
整体上,拜占庭帝国的立法对角斗持否定态度。比如,《狄奥多西法典》收录的公元357年君士坦提乌斯和尤里安致城市禁军长官奥菲图斯的一个敕令规定,士兵和王公贵族皆不得参与角斗表演,如有违抗,角斗的组织者将被罚款黄金6磅,士兵则依军法处置(C.Th.15,12,2)[50]。优士丁尼《法典》收录的公元381年格拉蒂安、瓦伦丁尼安和狄奥多西皇帝致伊里利亚行省禁军长官瓦伦里乌斯的敕令则显示,角斗同斗兽一样,被用于刑罚处罚,承受者为参与骚乱之人(C.J.11,40,2)[48]。
与斗兽相同,角斗也在拜占庭帝国走向了消亡。公元325年,即君士坦丁皇帝统一帝国的第2年,他就颁布了一个致禁军长官马克西穆斯的敕令,决定废除角斗。这一事件是体育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将采纳李小均先生的精彩翻译,还原这一收录于《狄奥多西法典》第15卷第12题第1段(C.Th.15,12,1)和优士丁尼《法典》第11卷第43题第1段(C.J.11,43,1)的体育法制史上的重要文献:
“天下方定,内乱初平,血腥游戏,难以悦心。故应根除角斗士之土壤;判罪为角斗士之人,速送至矿山。不流血而减其孽,两全之策也”[9]。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份对角斗这一“竞技场上的酷刑”进行负面评价并明令禁止的法律文献。当然,也有后世史家认为,到底这道敕令是否真的拉开了向角斗开战的浪潮,很难说清,因为这可能只是君士坦丁皇帝的权宜之计,旨在解决采石场劳动力的短缺[9]。而且,就在3年以后,即公元328年,角斗表演照样在安提阿举行,君士坦丁皇帝也未表示异议。他的继任者们也没有反对在拜占庭帝国的城市内继续举办这项运动。只是这些城市的主教决定,基督徒不能参加任何与角斗表演相关的工作,同时剥夺了所有角斗士受洗的权利[9]。
然而,从4世纪后半叶开始,角斗的确衰落了。公元399年,狄奥多西一世的儿子霍诺留皇帝关闭了角斗士学校,间接导致了主要角斗士选手水准的下降。在公元404年,一个来自小亚细亚的僧侣冲入罗马的角斗赛场,对比赛进行抗议,愤怒的观众抓住他五马分尸,霍诺留皇帝拒绝容忍这个暴行,下令永久取缔在罗马的角斗士表演[9]。但角斗在拜占庭帝国之末路并非出于官方的明令禁止,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趋消亡过程。在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后,作为异教失败的象征,大竞技场和角斗表演成为被打击的重点。公元440年以后,角斗就再也没有出现过[14]。与之对比,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优士丁尼时代,战车竞赛和斗兽仍然保留在节目单上。
3.5 小结
与古罗马的马戏传统不同,在拜占庭帝国早期,统治者通过立法,对战车竞赛、斗兽和角斗等不同的马戏活动给予了迥异的法律评价。法律对战车竞赛持支持、鼓励态度,甚至通过国库供养比赛用马;对角斗和斗兽则持否定态度,导致两者在帝国早期先后消亡,“马戏”由此独剩战车竞赛一家。在对这些马戏活动的法律治理中,一些动物保护主义和人道主义因素初露端倪,显示了一定的进步意义。
4 宗教转型对体育治理的影响
可以发现,角斗、斗兽等罗马传统体育活动在拜占庭时代之衰微,基督教扮演了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拜占庭帝国是考察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意识形态转型如何影响体育治理的独一无二的范例。作为一个基督教帝国,开国大帝君士坦丁曾在公元313年一手缔造了《米兰敕令》,由此使基督教合法化;在狄奥多西一世治下,按照圣安布罗斯所言,“他遮蔽了部落之神,也用自己的信仰遮蔽了所有其他的偶像崇拜,抹去了所有异教庆祝活动”(St.Ambrose,De obtiu Theodosii)[42]。基督徒对竞技运动充满敌视,那么,宗教转型会对拜占庭帝国早期之体育治理带来何种影响?拜占庭帝国的体育如何在此环境下走向涅槃重生?
4.1 异教竞技传统的最后余晖
公元392年11月8日,狄奥多西一世与阿卡狄奥斯和霍诺留皇帝在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颁布了一条极为著名的敕令,规定帝国境内所有人,无论处于何种社会条件,皆无一例外不得参拜异教,任何城市不能举行异教活动(C.Th.16,10,12)。这条敕令史称君士坦丁堡敕令,它意味着狄奥多西一世在帝国全境最终废除了异教崇拜。此时,距离君士坦丁皇帝一统帝国已有68年。这一期间,异教竞技传统散发了最后一丝余晖,为体育治理史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
基督教对竞技运动的态度,神学家们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北非教士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论表演》(Despectaculis,约写于公元200年)中,无论是跑马场中的赛马和战车竞赛,还是露天竞技场上的角斗、斗兽,亦或体育场中田径选手们的跑、跳、投比赛,都属邪神崇拜,因为这些起源于希腊和罗马的竞技游戏都出自敬拜异教神明的节日或举行异教的死亡祭礼[29]。最初,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只占少数,神学家们的观点也少有影响。随着基督教影响力日增,基督教神学家们的反对逐渐发生成效。君士坦丁皇帝是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他认为战车竞赛好过角斗,因为它不那么强烈地让人想起异教祭礼[29]。4世纪的圣徒希拉容(Hilarion)利用一切机会反对竞技比赛,他写道:“来自加沙的马车手在战车竞赛中被恶魔击中,陷入完全的麻痹……他被带向希拉容……并被告知除非他放弃以前的职业并笃信基督,否则永远无法痊愈。”[52]然而,在本质上,竞技场不过是基督徒战胜异教徒的另一个舞台而已。在一场基督徒伊塔里库斯和玛拿教(Marnas)徒的比赛中,希拉容毫不犹豫地选择帮助后者:把圣水撒在马背上、赛车手身上和战车门上,伴随着教徒的欢呼,“玛拿教徒被基督徒打败了”[52]。
君士坦丁逝世后,他统治帝国西部的三子君士坦斯皇帝在公元341年率先颁布过一个禁止异教仪式的敕令,但在次年即342年,他又对首都罗马的居民发布了禁止破坏神殿的命令:
“一切迷信确实应当遭到排斥,但在城墙外的神殿应以现状保存。战车竞赛与田径竞赛固然起源于献给诸神的仪式,然而若破坏举办仪式所需之竞技场与附属神殿,将剥夺平民常年来享有的娱乐。”[34]
剑客决斗、四轮、双轮马车竞赛、田径等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献给希腊、罗马诸神。因此,选手在参加比赛之前,照例要先到附属的神殿参拜。从这层意义上说,并非竞技场附设神殿,而是神殿附设竞技场。所以,破坏神殿的行为,容易连带造成竞技场受损。君士坦斯皇帝并非想要保存神殿,只是不希望为了破坏娱乐设施而得罪民众[34]。
公元361年,“叛教者”朱利亚努斯掌权,力求恢复希腊、罗马宗教传统,由此对抗基督教,这是异教竞技传统最后的黄金时期。但是,朱利亚努斯下令要求祭司阶层过严格的生活,要求神袛官和祭司不得前往剧场,也禁止观看战车竞赛与剑客决斗,禁止狩猎。另外,还禁止祭司与演员、赛车手、剑客等当时受群众欢迎的人物往来。历史学家指出,这种方案注定失败,因为“在现实的罗马人眼中,这根本不是人的生活”[34]。随着朱利亚努斯在公元363年与波斯军队的一场战役中英年早逝,基督徒约维安继位,前任皇帝的政策被全盘推翻,基督教重新控制了帝国,并再也没有将权力旁落。
公元390年,即在君士坦丁堡敕令颁布前2年,一场叛乱席卷了位于帝国要冲的帖撒罗尼迦城(Tessalonica)。一位名叫布托里克(Butheric)的战车运动员被伊利里亚行省军事长官逮捕,愤怒的民众发生暴动,布托里克被杀,狄奥多西一世“为了镇压该城的叛乱,一气之下,将人们尽戮于城内的竞技场”[42]。此事导致7 000余人被杀害,也使得皇帝与米兰大主教圣安布罗斯(St.Ambrose)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是君士坦丁堡敕令出台的重要原因,因为皇帝为了取得大主教的宽恕,决定下令废除一切异教活动,以表现出皇权对教权的臣服[40]。所以,从狄奥多西一世开始,尤其是在公元392年以后,拜占庭帝国的体育治理揭开了新的篇章:体育面对的是一个异教传统被彻底抹去痕迹的时代。
4.2 基督教对体育立法的影响
基督教合法化后,一大批上层阶级、富人和名利之徒涌入教会,使基督教会从一个由穷人和中层阶级组成的宗教团体演变成阶层式和官僚式组织的世俗化团体。在拜占庭帝国早期,教权与皇权的斗争贯穿始终。狄奥多西一世向米兰主教的臣服只让教会获得了短暂的独立和自由,但很快,特别是优士丁尼即位后,教会再次沦为皇帝的附庸[28]。这表明,尽管基督教在成为人们新的精神支柱后,自然而然地渗透到罗马法中,给传统罗马法的各项制度提供了新的精神导向[30],但这种影响“不可能是一种革新,而是一种适度兼顾罗马传统的前提条件下的局部性的改良。换言之,倘若这种改良与罗马传统严重脱节,导致法律瘫痪,那么,一切将恢复常态”[28]。这一史观也可用于考察基督教对体育立法的影响。
原始文献的考察证明,基督教因素渗入到了一些体育行政法中,改变了体育活动的组织模式。《狄奥多西法典》记录道:
C.Th.15,5,2,2。格拉蒂安、瓦伦丁尼安和狄奥多西皇帝致禁军长官路福努斯:此外,朕再次警告,任何人不得违反朕此前颁布过的敕令,即禁止在星期日举办赛会或者庆祝活动干涉对上帝的崇拜。公元386年5月20日于赫拉克勒斯,霍诺留和最尊荣的埃沃狄乌斯担任执政官[50]。
狄奥多西二世和瓦伦丁尼安在公元425年1月1日于君士坦丁堡颁布的敕令进一步补充道,下列时间也不能举办竞技比赛,即耶稣生日、主显日、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因为这些时间需要开展宗教性质的纪念活动(C.Th.15,5,5)[50]。优士丁尼皇帝在其《法典》中也借用了瓦伦丁尼安、狄奥多西和阿卡狄乌斯皇帝发给禁军长官阿尔比努斯的敕令,禁止在特定的基督教节日举办公共演出活动(C.J.3,7,7)[48]。这些立法对后人影响极大。在17世纪,清教徒们曾经烧毁了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体育之书》,原因就是他把星期日用于开展体育活动,而这是蔑视上帝的行为[29]。
当然,基督教对体育立法的影响是有限的,在体育行政法领域外,特别是在体育私法领域,罗马人沿袭下来的法律观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优士丁尼《学说汇纂》大量采纳了罗马古典时期法学家们的观点,规定体育侵权案件的处理需以是否存在过错为标准(D.9,2,9,4;D.9,2,11pr.);伤害如果发生在赛场上,则属意外而非过错(D.9,2,52,4)。在D.47,10,1,5中,优士丁尼沿袭了罗马法学家提出的“自愿之人不发生侵辱”(quia nulla iniuria est,quae in volentem fiat)原则,该原则在中世纪发展为“同意不生损害”(volenti non fit injuria)格言,作为大陆法系处理体育伤害的基本原则,一直延用至今[44]。
4.3 基督教对体育赛事的影响
拜占庭时代早期也是古代奥林匹克文明末期。最后一位古代奥运会冠军是谁,历史学家的说法不一①一说为Varazdates,他是来自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在公元385年举行的第291届奥运会上获得了拳击冠军。参见[德]沃尔夫冈·贝林格.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M].丁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2.但斯坎伦认为,Varazdates赢得的是公元369年的拳击比赛冠军,公元385年的最后一位奥运冠军是来自雅典的拳击手Zopyros。参见[美]托马斯·F·斯坎伦.爱欲与古希腊竞技[M].肖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07.支持后一种说法的学者还可见于:王以欣.神话与竞技: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79。。奥运会是否为狄奥多西一世的一个专门敕令所取缔,历史学家们也存在争议[36]。但在君士坦丁堡敕令颁布后,奥运会确实已经无法在全面废除异教的宗教环境下生存。
自奥古斯都时代就有的安提阿运动会继续照以前模式举行,并逐渐成为帝国“最重要的运动会”[41]。安提阿建立于公元前3世纪,历史远比君士坦丁堡悠久,在拜占庭帝国早期是与君士坦丁堡和罗马齐名的三大都市之一,是帝国与东方贸易通商的中心[34]。安提阿运动会的正式名称为“安提阿奥运会”(Giochi olimpici di Antiochia),始于公元45年。是年,克劳狄皇帝授权给安提阿居民“举办奥运会”的权利,在当时的风气下,各地都想得到这种授权。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等同于奥运会”的运动会,虽然与在奥林匹亚举办的奥运会同样庄严,但却徒有奥运会之名而无奥运会之实[53]。此“实”即奥运会通过仪式宣扬的异教崇拜,如运动员在赛前被要求到宙斯神庙前宣誓。安提阿运动会没有这些要求,避免了在基督教时代被贴上异教标签。随着城市的国际化和在帝国地位的上升,安提阿运动会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运动会,而是吸引了来自整个希腊——拉丁世界的参赛者[41]。《狄奥多西法典》收录的公元409年由霍诺留和狄奥多西二世颁布的敕令(C.Th.15,9,2)显示,安提阿运动会的组织者不受法律规定的赛事开支和奖励限制[50]。安提阿运动会的繁荣持续到了优士丁尼时代,一直到公元521年,才被一项规定天主教基本原则的法律所废除[41]。再隔一个世纪,在公元638年阿拉伯人入侵后,安提阿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34]。
体育史学家注意到的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是狄奥多西一世在公元390年曾经耗费巨资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方尖碑运到君士坦丁堡,“他想藉此继承君士坦丁皇帝的传统,让战车比赛成为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支持的事,从而使这项运动不怕教会的攻击”[29]。对狄奥多西二世而言,他尽管被认为在公元426年关闭了奥林匹亚宙斯神庙,颁布了毁掉所有圣殿的命令,但“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都没有受到迫害,只要体育锻炼与异教神明崇拜无关,就不受干扰。皇帝本人死于一次骑马意外事故,摔断了脊椎”[29]。可以发现,尽管奥运会和其他与异教祭礼相关的体育活动消失了,但以战车竞赛为代表的“面包与马戏”在拜占庭帝国仍然火热地持续着。直至首都在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攻陷,赛马场在整个中世纪都扮演着君士坦丁堡社会中心的角色[39]。这里既是帝国最受欢迎的战车竞赛举办之处,也是新皇登基接受欢呼之处、民众庆祝军队凯旋之处、执行公开刑罚之处[47]。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宗教,赛马场增加了新的功能,战车竞赛的仪式则渗入了诸多基督教元素。
赛马场增加的新功能是庆祝基督教节日。作为异教节日牧神节的替代,狂欢节在大斋节前一天举行,人们在赛马场举行战车比赛并载歌载舞赞颂上帝。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建城节,皇帝和元老在赛马场分配食物给穷苦百姓,这是早期罗马“政治面包”惯例的替代,此时反映的却是基督教慈善传统[47]。
基督教对竞赛仪式的改造可能并不情愿。基督教领袖们对这些起源于罗马异教的世俗娱乐有着深刻的反感,他们希望这些活动远离拜占庭人的生活。但是,战车竞赛对于拜占庭人实在太重要了。拜占庭体育史学者卡梅隆解释了基督教介入体育赛事的目的:“宗教涉入赛马场仪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教会的团结,并培养这样一种重要观点:上帝指定的君主是信仰的保护人,也是正教的捍卫者。”[39]这样,战车竞赛在从希腊模式过渡到罗马模式后,在历史的洪流中再次过渡到拜占庭模式。
在罗马帝国早期还依然保留的希腊模式中,是战车所有人而非赛车手获得战车竞赛的优胜奖励[39]。罗马模式的特征则是高度的仪式化,处处体现对皇帝的崇拜[39]。拜占庭模式在继承罗马模式的基础上,将基督教元素植入仪式,表现为:首先,战车比赛通过皇帝划十字架开幕;随后,人群簇拥着皇帝,唱赞美诗向这位上帝的代表致敬;赛后,优胜者赴最近的教堂致谢[47]。在拜占庭帝国的意识形态中,任何赛车手的胜利也是皇帝的胜利,而皇帝是被上帝挑选的在尘世的代表,上帝、皇帝和战车竞赛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关联,一如冠军在从皇帝手中接过奖牌后,他所在派系支持者所吟唱的那样:“我们祈求分享您源于上帝的胜利,平等的分享您的胜利,主啊,对王的忠诚矢志不渝。”[47]
4.4 小结
在君士坦丁皇帝一统帝国后最初的68年时间内,异教竞技传统散发了最后一丝余晖,直至公元392年君士坦丁堡敕令颁发,体育治理开始面对一个异教传统被彻底抹去痕迹的时代。在有关体育活动组织的体育行政法、战车竞赛仪式以及赛马场的功能定位上,都出现了基督教化的改造,表征异教传统的古代奥运会也在这一时期消亡。但是,整体上看,基督教对体育治理的影响是改良性质的,与异教传统无关的体育活动仍在继续,安提阿运动会在帝国早期持续繁荣,罗马人沿袭下来的体育私法也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基督教与体育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都在这个转型的时代做出了调整、妥协,以更好地适应对方。
5 政治转型对体育治理的影响
与宗教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相对应,拜占庭帝国在政治制度上也日益远离古罗马传统,“新帝国建立了由皇帝任免、对皇帝效忠并领取薪俸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在拜占庭社会中,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与罗马帝国时期作为公民代表和‘公仆’的官员有本质区别”[4]。虽然不及宗教转型对体育治理之影响剧烈,但政治转型对体育治理的影响亦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由此使得竞技党日趋政治化,带有政治目的的体育骚乱频发,体育比赛成为反对派表达不满的工具。
5.1 竞技党的政治化
在古罗马,拥有马匹是身份显赫的象征。无论是饲养马匹、训练赛车手还是吸引观众都需要花费大量金钱与劳力,三教九流由此在竞技场汇集,竞技党之组织成为可能。有组织的竞技党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就已出现,他们最初的功能是服务比赛并保障公平。来自图密善时代的一份碑铭文献显示,竞技党类似一个体育俱乐部,有紧凑的内部组织结构,无论赛马、赛车手的助手还是医生、信息员,甚至协助起跑的操作手,都被安排得紧紧有条,学者将之誉为自助的职业组织[43]。最晚在公元1世纪之前,蓝党、绿党、红党、白党支配了战车比赛的竞技场。
从罗马共和后期开始,随着政治的独裁化,竞技活动被统治者用来表达政治姿态的作用日趋明显。皇帝公开宣布自己支持某个派系,以获取一定的政治支持。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党出现于4世纪晚期,即大竞技场完工之际[43]。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拜占庭新都建成后,君士坦丁皇帝就让“从老罗马迁移来的竞技党组成新都的城防部队”[17]。无论如何,在拜占庭早期,竞技党的政治化达到了巅峰。这与其他传统体育项目衰落而战车竞赛地位提高有关:“对于普通拜占庭人而言,战车竞赛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作为某个竞技党的支持者,拜占庭人不惜用自己的尊严给比赛下赌注,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在一个日趋权威化的社会获得斗争、对抗和冒险的机会。”[47]竞技党失去了古罗马传统的独立性,转变为国家控制、国家资助的由表演者和粉丝组成的团体,即“一个国有化的俱乐部”。当帝国将竞技党纳入拜占庭公共生活的行政组织结构中时,他们就成为帝国秩序承认且不可分割的一份子,他们有皇帝的认可与支持,教会尽管有所保留,但也接受了他们[47]。
《狄奥多西法典》收录的一些相关敕令显示,竞技党承担协助皇帝和城市长官管理、组织比赛的职能。比如,C.Th.15,10,1显示,战车比赛赛马之售卖归竞技党负责;C.Th.15,10,2则指出,坎帕尼亚人不能将赛马用于任何娱乐活动,除非他们通过任何一个竞技党上缴2 000莫迪的大豆[50]。后一敕令似乎是一种比赛的准入要求,竞技党扮演了类似现在体育协会或职业联盟收取赛事参加者“准入金”的角色。在君士坦丁堡,绿党和蓝党成为势力最大的两个派别,白党和红党变成了他们的附庸。前两者政治地位的获得,主要源于他们在皇帝加冕典礼上的重要角色:新皇只有在赛马场上接受了绿党和蓝党领导下的民众的欢呼后,才能顺利就职。有时出于政治原因,竞技党拒绝欢呼,但这只是极端情形,必须要靠政治手段解决。所以,尽管竞技党有权阻止新皇登基,但这种权力极少被使用过[39]。5.2 体育骚乱的政治化
体育骚乱在古代社会并不鲜见。塔西佗在《编年史》中记载过,公元59年庞培城的一场角斗比赛演化为两个城市支持者间的流血冲突[24]。在我国宋代,龙舟竞渡引发骚乱,造成13人死亡[15]。政治化体育骚乱之出现和普遍化,则肇始于拜占庭时代。体育骚乱的政治化是竞技党政治化的产物,一如普罗柯比在《战史》中所述:“当时,拜占庭帝国各主要城市都出现了蓝党和绿党这两个党派,他们争锋相对,经常在竞技场因争抢座位而发生殴斗,他们买凶将敌人致伤致死,也毫不在意自己的生命。”[20]竞技党为何要“争抢座位”?因为座位离皇帝更近,就更能接近他,并能更便利地表达自己派系的政治观点。皇帝出于政治利益,往往更偏爱其中某个竞技党,这种偏爱有时成为体育骚乱的根源。整体上,帝国当权者对竞技党的暴力倾向持容忍态度,由此造成拜占庭帝国早期体育骚乱频繁。优士丁尼皇帝是蓝党的支持者,但在他执政后,试图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而不支持任何一方。马拉拉什(Malalas)在其《编年史》中记录了皇帝在公元527年对竞技党政策的转变:
“他在罗马帝国的每个城市建立了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他向各个城市发出神圣的敕令,要求暴徒或者谋杀犯,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竞技党,都要受到惩罚;因此,未来无人胆敢引发任何混乱,他已经成功地让所有行省惊惮。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安提阿的竞技党保持着友善的关系”[54]。
但是,这样的中立政策可能适得其反。正如普罗柯比在《秘史》中所述,整个社会充斥着对优士丁尼皇帝、提奥多拉皇后以及一些高级官员的抱怨,人们不满高额的税收和混乱的司法体制[19]。最终,君士坦丁堡的蓝、绿两党密谋休战,联合起来反抗政府,这就是发生在公元532年1月的尼卡骚乱。优士丁尼最终控制了骚乱,在赛马场内,“蓝绿两党已溃不成军,民众更是伤亡惨重,死亡人数达3万人”[40]。一些反对派元老院议员被流放,“城市陷入安静之中,很长时间内,都再也没有举办过战车竞赛”[40]。
5.3 小结
体育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专制集权社会中尤其如此。“和古代几乎所有的皇帝一样,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也是大权在握,进行独裁统治,个人的决定往往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7]与罗马的开明传统日益背离,拜占庭政治体现了浓厚的东方式宫廷政治色彩,竞技党由此失去了古罗马传统中的独立性,变成统治者社会治理的工具。然而,统治者与竞技党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后者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对前者也存在着反作用,由此导致了政治化体育骚乱的出现。所以,在拜占庭帝国早期政治转型的背景下,体育秩序成为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与政治形成了互相影响、互为制约的关系。
6 结论
拜占庭帝国在体育史上居承上启下之重要位置,然而,“历史观中的因果律观念和西方中心论导致了拜占庭体育在体育史研究中‘失落’”,由此,使学者发出“使拜占庭体育重获在体育史中的地位”之思[10]。原始文献的考察显示,就体育治理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在《狄奥多西法典》和优士丁尼立法中,体育法承继了古典罗马法的荣光,又回应了新的时代要求。整体而言,本文对拜占庭帝国早期体育治理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就体育的法律治理而言,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体育法制有形式上的进步性。统治者重视体育赛事的作用,通过立法鼓励体育活动、保障赛事经费、缩减赛事开支、反对贪污挪用。对于斗兽和角斗等血腥的“马戏”活动,法律持否定态度,导致两者在帝国早期先后消亡。在这一系列法律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主义、反奢侈浪费等多种进步思潮,展示了拜占庭体育内在的文明基因。
第二,拜占庭体育法制形式上的进步性实质上服务于统治者的专制性。无论君士坦丁皇帝和狄奥多西皇帝确立基督教的统治地位,还是优士丁尼皇帝整顿律法,目的都在于强化君主集权制度。立基于这一背景,才能理解原始文献中限制城市长官追求民众崇拜以及相关反奢侈腐败立法服务于统治者巩固政权的本质。即使基督教对竞赛仪式的改造具有宗教目的,但核心仍然在于通过加大个人崇拜来强化皇权统治。
第三,就意识形态与体育治理的关系而言,拜占庭帝国早期宗教与政治转型对体育的影响并非彻底的和绝对的,只具有相对性与改良性。在拜占庭帝国早期,尽管与异教相关的竞技活动不复存在,体育立法和竞赛仪式也进行了基督教化的改造,但置身于时代之具体情境,基督教对体育治理的影响是改良性质的,两者也有相互调整、适应和妥协的一面。竞技党和体育骚乱的政治化只是帝国整体政治环境转型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拜占庭体育治理走向了异化。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战车竞赛的车轮还在激荡,直至城市在13世纪经过欧洲军队掠夺,赛马场变得荒芜[29]。地中海世界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繁盛后,虽然许多体育活动在这片土地上最终消亡了,但也孕育出新的希望。这片土地上积淀的深厚的希腊罗马体育传统,成为近代体育运动在复兴过程中取之不竭的源泉。
拜占庭帝国早期体育治理的经验证明,体育治理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法治则是发挥体育治理积极作用的主要路径。需要认识到,古代的法治与现代的法治还有很大距离[35]。拜占庭的体育法治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与宫廷密切联系。现代的体育法治则通过分权与制衡机制,重在保障体育参与者的基本权利。当然,拜占庭帝国早期反对奢侈办会、缩减赛事开支、制裁贪污挪用的措施,在今天仍然有着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应以史为鉴,大力推进依法治体工程,发挥好体育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角色。
[1][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M].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90.
[2][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M].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283.
[3][德]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M].姜瑞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02.
[4]陈志强.拜占庭帝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28-42.
[5]陈志强.拜占庭史研究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135.
[6]陈志强.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的新动向[J].世界历史,2007,(6):122-129.
[7]崔艳红.普罗柯比的世界: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11.
[8][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44-445.
[9][荷]菲克·梅杰.角斗士:历史上最致命的游戏[M].李小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161.
[10]高强,董超.拜占庭体育史的重现——基于文化逻辑的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39(5):6-11.
[11]郭文庭.唐代诏敕与体育[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35(12):41-44.
[12][美]汉斯·A·波尔桑德尔.君士坦丁大帝[M].许绶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9.
[13]刘欣然,李亮.游戏的体育:胡伊青加文化游戏论的体育哲学线索[J].体育科学,2010,30(4):69-76.
[14][德]马尔库斯·荣克勒曼.角斗士史话[M].王勋华,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6-47.
[15][美]马伯良.宋代竞渡骚乱罪——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法律案件的解决[C]//戴建国,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6-137.
[16][美]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M].马雍,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09.
[17][英]N.H.拜尼斯,主编.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M].陈志强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2-181.
[18]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12-419.
[19][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M].吴舒屏,吕丽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60-78.
[20][东罗马]普罗柯比.战史(上)[M].崔艳红,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49-53.
[21]齐云,徐国栋.罗马的法律和元老院决议大全[M]//徐国栋.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八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218.
[2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上册)[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9.
[23][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M].田丽娟,邹恺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194.
[24][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下册)[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67-468.
[25][古罗马]塔西佗.历史[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58.
[26][美]托马斯·F·斯坎伦.爱欲与古希腊竞技[M].肖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7-9.
[27][法]瓦诺耶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及古希腊罗马的体育运动[M].徐家顺,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52.
[28]汪琴.基督教与罗马私法——以人法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9-41.
[29][德]沃尔夫冈·贝林格.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M].丁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7-76.
[30]向东,陈荣文.奢侈行为的法律规制:从古罗马到现代[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181-182.
[31]徐家玲.拜占庭的历史分期与早期拜占庭[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30-36.
[32]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2.
[33]杨代雄.《优士丁尼法典》中关于基督教的敕令初探——兼论基督教对晚期罗马法的影响[M]//何勤华.多元的法律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63.
[34][日]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XIV:基督的胜利[M].郑维欣,译.台北:三民书局,2007:162-175.
[35]张中秋,杨春福,陈金钊.法理学——法的历史、理论与运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67.
[36]赵毅.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被废除的吗?——意大利学界的争论和基于《狄奥多西法典》的考察[J].体育科学,2014,34(6):83-89.
[37]赵毅.古希腊罗马:体育法制文明的先驱[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4,29(3):209-214.
[38][东罗马]佐西莫斯.罗马新史[M].谢品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73.
[39]CAMERON ALAN.Circus Factions.Blues and Greens at Rome and Byzantium[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153-308.
[40]DE BERNARDI MATTEO.Atti di violenza in occasione di manifestazioni sportive:alcuni “precedent” nell'epoca dell'Impero romano[J].Rivista di Diritto Romano,2011:1-15.
[41]DELL’ORO ALDO.Giustiniano:Manifestazioni Sportive e Tifosi[C]//Atti Dell’Accademia Romanistica Costantiniana,VIII Convegno Internazionale.Napoli: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1990:624.
[42]FARGNOLI IOLE.Sulla 《caduta senza rumore》 delle Olimpiadi classiche[J].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2003:140-151.
[43]HAROLD ARTHUR HARRIS.Sport in Greece and Rome[M].NY:Cornell UP,1972:185.
[44]INGMAN TERENCE.A History of the Defence of Volenti Non Fit Injuria[J].Jurid Rev,1981:1-8.
[45]OSTROGORSKY G.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M].HUSSEY JOAN,trans,Oxford:Basil Blackwell,1956:25.
[46]SALIO EMANUELA.Intorno alle Leggi Suntuarie Romane[J].Aevum,1940,(1):174-194.
[47]SCHRODT BARBARA.Sport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J].Jouranl of Sports History,1981,(3):44-47.
[48]SCOTT S P.The Civil Law including The Twelve Tables,The Institutes of Gaius,The Rules of Ulpian,The Opinions of Paulus,The Enactments of Justinian,and The Constitutions of Leo,Vol.XV [Z].Cincinati:The General Trust Company,1932:27-277.
[49]The Digest of Justinian,Latin Text Edited by Theodor Mommsen with the aid of Paul Krueger,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Alan Watson,Vol.IV [Z].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5:821.
[50]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glossary,and bibliography by Clyde Pharr[Z].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52:126-436.
[51]TREADGOLD WAREN.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3-4.
[52]WHITE CAROLINNE.Early Christian Lives[M].Harmondsworth:Penguin,1998:96-99.
[53]WIESNER J.Olympia (Kleinasien)[A].PW,XVIII.1[C].Leiden:Brill Publishing,1939:c.48.
[54]WILLIAM MAIN ROBERT.Mob Politics: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Circus Factions in the Eastern Empire from the Reign of Leo I to Heraclius (457-641)[D].University of Ottawa,2013:10-11.
Sports Governance in the Early Byzantine Empire
ZHAO Yi1,2
The period of early Byzantine Empire starts from the unification of Constantinus I Magnus in 324 AD and ends as Justinianus passes away in 565 AD.It is a transfer time from the classical to middle ages,in which sports governance has to react to the new demand as the new time comes.The observation from sources shows that sports legislations in the period have the goal of encouraging sports activities,ensuring game expenditure,decreasing unnecessary waste and objecting corruption.The legislations also give different judgment as for the race-horsing,wild beast and gladiator.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sports activities related to paganism no longer exist,and sports law and game rituals are modified by the new religion.However,the modification is not fundamental.The transfer of the overall imperial political conditions causes the politicization of circus factions and supporters violence.It is a time that connects between the proceeding and the following in sports history.The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Byzantine Empire proves that sports governance plays a vital role in nation governance,and rule of law is a main road in promot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sports governance.
sportsgovernance;sportslaw;ByzantineEmpire;Christian
1000-677X(2016)06-0061-12
10.16469/j.css.201606007
2016-02-23;
2016-06-01
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15SFB3004);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196SS15083);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TYB004);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作者简介:赵毅(1979-),男,江苏江阴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法、体育史,E-mail:xiaozhaoleon2006@163.com。
1.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6;2.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 550018 1.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06,China;2.Jiangsu Universities Coordination and Innovation Center in District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Nanjing 210023,China.
G80-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