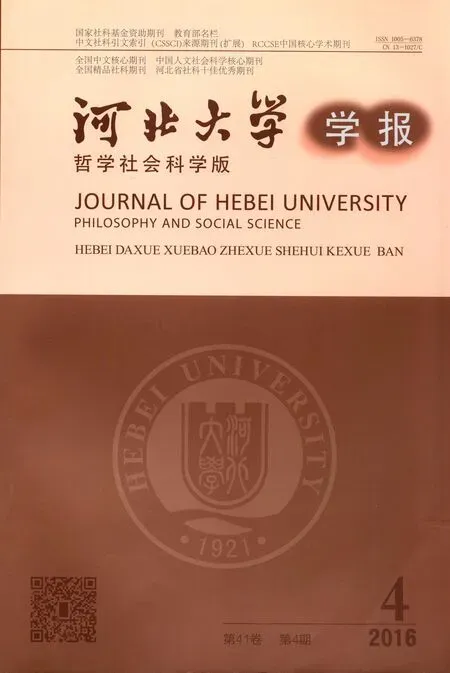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2016-03-08宋宇
宋 宇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宋 宇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曹禺1930年代剧作;表现主义;经验主义;诗化现实主义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以其对“反封建和个性解放”主题的深刻阐释和对“时代风貌与社会百态”题材的全面展现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审美范式逐渐形成并臻于成熟的标志。然而,一直以来研究者以及曹禺本人对这三部作品的美学范畴的界定却并不局限于纯粹的“现实主义”。正如严家炎指出:“他自身剧作中有那么多象征色彩,仅仅用现实主义似乎很难概括曹禺的剧作”[1]348。毋庸置疑,《雷雨》对古希腊悲剧艺术命运悲剧模式的模仿,《日出》对类似自然主义的叙事结构的学习,以及《原野》对象征主义手法的借鉴,使得其20世纪30年代剧作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中存在很多现代主义的元素。笔者将这些戏剧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元素归纳为曹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
一、素材的摄取与对“审美经验论”的借鉴
“经验本体”是曹禺的戏剧创作在意象营造和人物塑造等方面的思想源泉。杜威认为,艺术和审美的“源泉存在于人的经验之中”[2],艺术即经验。这种经验是一种审美层面的界定,不是一种感官上的简单快乐,而是一种触发审美情感的生命体验。这种“审美经验是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并非游离于其他经验之外;但它又是日常经验的集中、概括和实现,是具有完整统一性的经验”[3]550。曹禺擅长在日常的生活中发现具有可塑性的“美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是其童年记忆中宣化府的“荒原和神树”,也可以是其青年时代记忆中的“靳以和王右家”,它们可以是其童年的“伤城”在《原野》中搭建的黑色“森林”,也可以是其青年的“懵懂”在《日出》中塑造“方达生和陈白露”的人物“模特”。杜威认为美学的“任务旨在恢复经验的高度集中与经过被提炼加工的形式——艺术品——与被公认为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和痛苦经历之间的延续关系”[3]548。曹禺正是通过意象的营造和人物的塑造,完成了这种从“日常经验”到“审美经验”的转化过程。
另外,杜威将“经验”的形成解释为“有机体和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标志和报偿”[4],他说,“经验是有机体在客观世界中进行斗争、取得成果、完成使命”[3]551。杜威的这一套经验主义或生物学经验主义必然导致“审美主体”或“创作主体”对“自然过程”和“自然的材料”[5]的关注。曹禺20世纪30年代的三部话剧有一个共性,正是对“生态环境”“天气状况”的有意设置,比如《雷雨》中郁热的雷雨天气,《原野》中迷宫般的原始森林,还有《日出》中冲破黑暗的黎明。这些“自然环境”作为一种“日常经验”,通过一种情感的想象和艺术的加工,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曹禺通过“创境”的理论对剧作“诗境”的营造,搭建了一种柯林伍德所谓的“总体想象性的经验”。与此同时,曹禺也正是“通过为自己创造一种想象性经验或想象性活动以表现自己的情感,”形成柯林伍德所界定的“艺术”[6]156的范畴。观众在“郁热”氛围里承受了情感的压抑,在“迷宫”的求索中体味着生命的焦虑,在“黎明”的承诺下感受着希望的温暖等等,“审美经验”通过剧作的形式得以形成和传达,“经验主体”也在曹禺的提炼和加工过程中升华为“艺术”所表达的“情感与内涵”。诚如柯林伍德所说,“我们所具有的是这样一种眼睛,它足以看出画家希望我们看出的东西”[6]155,而这种观众的“眼睛”和曹禺剧作要表达的东西正是一种对“审美经验”创造和接受的过程——通过审美主体(观众)的艺术想象与创作主体(曹禺)的意象营造的方式,实现的一种对各自“日常经验”的提炼与加工,最终实现审美主、客体间(曹禺与观众间)“审美经验”的共鸣。
当然,曹禺并非全盘接受“审美经验论”,而是在“创作的发生学”层面对杜威的“经验主体论”和柯林伍德的“总体想象性经验论”进行有选择的借鉴。研究者曾指出,杜威的审美经验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缺陷——对“审美经验社会性”的抹杀,以及“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统一、连续性”与“审美经验的独特性、不连续性”的自相矛盾[3]552。一方面,曹禺的戏剧创作对审美经验和日常经验的关系做了妥善的处理,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审美经验源于日常生活经验,通过审美主体的艺术想象和创作主体的意象营造,完成二者的相互转化,对二者在杜威理论中的“矛盾性”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与超越。另一方面,曹禺非常重视其剧作对“审美经验社会性”的创造,强调一种普适性的艺术价值。《雷雨》和《原野》的创作都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人们生存困境的普适性思考,剧作“实际上表现和传达了一种真正的人类感觉”,也就是卡里特所肯定的“艺术的表现性特征”“一个成功艺术所创造的普遍性”[7];《日出》中第三幕的对地狱般妓女生活的揭露也体现了作者具有正视“总体性社会现实”[3]634的真诚和勇气,以及那种同情底层人民、批判社会黑暗的人道主义情怀。当然,这种剧作中存在的“审美经验社会性”也是其剧作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一种潜在因子。比如,《日出》中的《打夯歌谣》的几次响起和《雷雨》中“鲁大海”与《原野》中的“仇虎”的职业归属,既可以作为一种对人类“原始力量”的呼唤与歌颂,同时也可以实现一种对阶级情感的诉诸与阶级意识的搭建。当然这种因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反映生活、烛照现实、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而存在。同时,曹禺在剧作中对于柯林伍德以及卡里特的美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则更深刻地集中于他们在表现主义美学理论的建构中。
二、方法的实践与对“表现主义”美学的应用
曹禺在话剧创作中对“表现主义”美学的借鉴主要体现在“艺术与语言的同一性”和“艺术对情感的表现性”,以及“艺术作为一种创作活动的想象性”。就艺术、语言与情感的关系来看,“语言的哲学就是艺术的哲学”“语言与诗和艺术是一致的”[3]58,“语言在其原始或朴素状态中是想象性的或表现性的”[6]232,“包括与语言表现方式相同的任何器官的表现活动”是“情感的身体表现”[3]74。正如本文之前提到曹禺剧作中的“诗性表达”,作者在其戏剧语言中所赋予的“情感性”“故事性”“节奏性”和“动作性”,正是对“克罗齐——柯林伍德表现说”在艺术、语言与情感之间关系方面的一种有益实践。另外,“同直觉一样,艺术是一种想象活动,它的对象是个体,它所产生的是形象化了的意象”[3]47,而曹禺剧作对“诗情”的释放和“诗境”的营造,更多的就是借鉴这种以“个体”为基础的合理创造和艺术联想,而这里的“个体”就是被提炼和加工的“日常经验”本身。由此看来,“表现主义”美学是作为一种诗性特质的表现形态渗透于曹禺的剧作中的,“经验本体”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原始材料”,既是表现主义所表现的内容,又是诗性特质所体现的根本。
《雷雨》《日出》和《原野》所表现的是作者的情感与生活,《雷雨》和《原野》风格更为紧凑、激烈,是情感化的心理剧,《日出》风格较为细致、缓和,是理性化的生活剧。研究者在谈到《原野》时曾指出,“由于借鉴了表现主义艺术,曹禺才别开生面的展示了一幕农民复仇的心理悲剧”[8]268。仇虎复仇前的犹疑、压抑和复仇后的恐惧、愧疚,以及前后转变过程中每个人物的那种生存的焦虑、选择的困惑,都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其心路历程的一种反映。这与《雷雨》的创作初衷是一致的,正如曹禺自己所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9]137。从艺术与情感的关系来看,柯林伍德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3]69,正如他自己所解释,“当说起某人要表现情感时,所说的话无非是这个意思:首先他意识到有某种情感,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情感是什么;他所意识到的一切是一种烦躁不安或兴奋激动”[6]112。《雷雨》和《原野》的创作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一种反应,“兴奋激动”和“烦躁不安”既表现为“《雷雨》蒸热氛围里的两种自然基调”—— “极端”和“矛盾”[9]138,又表现为《原野》中原始森林被赋予的双重象征——原始的力与生存困境。后者也同时体现为一种对表现手法的借鉴,正如研究者指出:“第三幕仇虎在森林中逃跑的幻觉描写,则是吸收了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琼斯皇》的表现主义艺术”[8]268。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雷雨》和《原野》以情感的表现为创作的初衷,通过情感的变化控制剧情的节奏;从创作手法的角度,二者通过剧中意境的营造、冲突的搭建凸显剧中人物的心理,进而表现作者的情感。
《日出》的创作风格较《雷雨》和《原野》不同,其对表现主义的借鉴并不是体现在形式和结构层面,而是在于语言层面,在于对“艺术与语言的同一性”理论的借鉴,其对生活片段、人生百态的诠释是通过“诗性的表达”逐渐呈现的。一方面,曹禺在《日出》中是用语言来搭建结构、演绎生活的。正如曹禺自己所说:“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起《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所谓“‘结构’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观念,即第一段引文内‘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9]293。另一方面,曹禺在《日出》中是用语言来呈现情感、表现自己的。正如柯林伍德所讲,“这是一种和我们叫做语言的东西有某种关系的活动:他通过说话表现自己”[6]113。“‘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睡了’。我是先有了这样几句诗,慢慢地演化出来很多人物”[1]42。曹禺将诗的韵味凝练在语言之中,形成一种诗性的表达。情感的抒发和自我的表现自然而然的在人物对话中呈现,每一句诗意般的陈述既囊括了作者创作的初衷,又涵盖了剧作演绎的主题。
综上所述,《雷雨》《原野》和《日出》对表现主义美学理论的借鉴,由于角度的不同决定了其剧作风格、节奏的不同。前者倾向于结构和形式层面的借鉴,后者则倾向于语言和内容层面的援引;前者将“诗情”通过意象的营造融入戏剧的形式之内,后者将“诗语”通过韵味的呈现浸染于戏剧的内容之中。
具体来看,曹禺剧作中所呈现的诗性因子和诗性表达是表现主义美学得以成功借鉴的前提。曹禺在创作手法层面对“表现主义”美学的借鉴是要以“经验主体”理论为基础的,其剧作中意象的营造和艺术的联想也是以“日常经验”作为“原始材料”的。两种美学思想的融合是通过曹禺剧作中的“诗性”的渗透来实现的,“表现主义”是“诗性表达”的方法,“经验主体”是“诗性特质”的内容。曹禺话剧中的“诗性”风格作为一种溶剂,在融合两种美学元素的同时,也弥补了它们各自在方法性与材料性方面的局限,最终通过“想象”实现了从“日常经验”到“审美经验”的过渡,完成了从“生活再现”到“艺术创造”的升华。
毋庸置疑,曹禺剧作中的诗性特质在情感的表达媒介与情感的普适层面弥补了“表现主义”美学的不足。曹禺在创作初衷层面对表现主义的借鉴是以情感的表现为前提的,但这种“情感”与克里特为代表的表现主义所表现的“单纯的个人情感”[3]92不同,而是一种“诗人表达的情感”,是一种“能够普遍引起共鸣的社会性情感”[3]71。这是由曹禺自身所具有的诗人气质所赋予的“诗人使命”[3]70-71所决定的,也是前文提到曹禺对创作中的“审美经验社会性”和“普适性的艺术价值”非常重视的必然结果。另外,曹禺通过“诗”与“剧”的融合将情感蕴藉于形式之中,“在自己的媒介里创造一个他能因为满足的情感体现”[10],也就是鲍桑葵所倡导的“使情成体”,将“情感变成有形”。前文提到,曹禺的创作是“诗”与“剧”的结合,是“戏剧诗”。这种戏剧风格的形成作为“使情成体”的条件和“表情达意”的“媒介”,打破了克罗齐“表现无需物质媒介和传达”的理论局限,使得情感与形式二者的相互融合更为客观与自然。
三、风格的确立与“诗性现实主义”的形成
“表现主义”与“经验主义”是作为一种诗性特质的表现形态渗透于曹禺的剧作中的,曹禺对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为基础的。正如克罗齐所指出:“诗人的每一句话,他的幻想的每一个创造都有整个人类的命运、希望、幻想、痛苦、欢乐、荣华和悲哀,都有现实的全部场景”[11]。这与中国传统诗学中“创作本事”的说法类似。曹禺20世纪30年代的戏剧创作,在诗情的抒发、诗境的营造、诗语的表达和诗韵的呈现都是以其现实生活的情感、经历、环境与时代氛围相契合的,后者是前者创作过程中的“全部场景”和“创作本事”。从审美形态的角度来看,曹禺对表现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借鉴,也更多是基于一种创作手法的引用,整体剧作风格的搭建仍然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曹禺以人本主义立场,塑造人物、描写生活、烛照现实,“作品具有内容的深广性、形式的完整性、典型的丰富性、批判的深刻性等特点,这正是卢卡奇所推崇的现实主义作品的理想形态”[3]641。
田本相先生将曹禺剧作的美学风格界定为“诗化现实主义”,肯定曹禺“从黑暗现实中发现美好的事物,善于揭示污秽掩盖下诗意的真实”“走了一条诗与现实结合的,富有民族个性的创造的诗化现实主义创作道路”[1]4。笔者认为,曹禺20世纪30年代剧作对纯粹“现实主义”的“诗化”主要表现为对20世纪“表现主义”和“实验主义”两种美学思想的借鉴,当然这种借鉴是以曹禺自身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简单来说,是一种中西诗学和文化的碰撞使然。笔者将20世纪30年代曹禺剧作的“诗化”倾向界定为两种层面的过渡:一是在形式层面从诗到剧的过渡,二是在内容层面从表现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不是线性的、单向的,而是环状的、往复的。从《雷雨》到《日出》,再到《原野》,一方面看到一种创作形式与现实生活距离的由远及近,再及远;另一方面同时看到一种表现手法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表现风格的由近及远,再即近。除此之外,尽管诗性特质在曹禺剧作中的呈现自始至终,但也同样表现出从形式、结构到语言、内容的不同渗透方式的交替转变。因此,曹禺20世纪30年代的剧作确实存在一种诗与剧的文体互渗现象,但二者的主、客体关系并不明显,其对经验主义、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的选择也表现为一种犹疑的状态。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剧作“诗化”风格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原因,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曹禺“诗化”风格的形成是其诗人气质的自我展现,其1930年代的创作历程是一段作家心灵的独白。“以人为文学史的核心,即文学史之人本观”[12]68的角度来考虑,曹禺处在“作品—作者—时世”[12]69的思路链环的中心,因此曹禺作为“作者”的个人气质,决定作品的创作风格,也就是“时世”在作品中反映的方式。正如研究者指出,“曹禺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诗人”[1]360,“曹禺有诗人的浪漫与天真”[1]357。因此,曹禺剧作中语言的深刻与韵味、情感的奔放与普适实际上都是其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底蕴和诗人使命的一种外化。
勃兰兑斯认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3]2。这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观“文如其人”类似——“即视文学创作是人内心世界和人之品格情操的外在表现”[12]69。纵观曹禺1930年代的创作历程,从人物的塑造到故事的呈现,从情感的表达到意象的营造,均能深深地感受到其生活的影子,融入了他对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整个生命价值的普适思考。因此,从《雷雨》到《日出》,再到《原野》,不仅详实地记录了曹禺对时代与命运的思考过程,更深刻地呈现了曹禺成长和生活的心路感言。
其次,曹禺审美范式的转型深受时代氛围的影响,是在特定历史环境内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根据文化史学派的观点,“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历史有着广泛的联系,是一种社会精神现象;文学受到社会、历史的制约,而形成各自的特点”[14]。曹禺20世纪30年代剧作的表现手法、主题呈现,以及作者走入文坛的姿态和其作品在文学史地位均受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氛围和文化环境的干预。
《雷雨》(1934年)、《日出》(1935年)和《原野》(1937年)的创作时间集中于1934—1937年间,在“无产阶级戏剧”浪潮之后(1930—1931年),在“国防戏剧”运动兴起(1936)之前。特殊的历史阶段赋予该时代同时拥有左翼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和“五四”启蒙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氛围。正如“文学是社会状态的反映,而不是造成这种社会状态的原因”[13]189,“文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15],文学作品必然会体现该阶段整体的文化氛围。因此,曹禺一边是作为“具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8]196的姿态在文坛崭露头角,另一边是“带着深厚的生活积累与现实主义的艺术修养登上剧坛的”[8]197。其作品纯艺术的表现手法和现实主义题材共存的特点是特定文化环境与特定时代氛围的一种体现。与此同时,正如研究者指出:“人是‘浸染’在一个整体文化现实和文化传统之中,他被文化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文化。因而,每一位作家的文化精神在承袭传统的同时也改变着传统。”[12]415曹禺有自己的选择,这种审美范式的选择意味着一种对“诗化现实主义”文化传统的塑造。在这个层面,理解20世纪30年代曹禺剧作审美范式的含混状态,本身也是一种对不同风格选择并适应的过程,一种戏剧形式在时代浪潮的影响下融入中国文化形态的过程。
综上所述,经验主义、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20世纪30年代文化环境和时代氛围在艺术层面的精神主体,共同影响和制约着曹禺话剧的创作。经验主义是戏剧创作的原始材料,表现主义是戏剧创作的艺术手法,现实主义是戏剧创作的主要风格,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其中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是作为一种诗性的特质融入现实主义的框架之中的,也就造成了曹禺剧作“现实主义”风格的不够纯粹,或者是研究者所界定的“诗化现实主义”。一方面,“诗化”作为曹禺将现代主义元素融入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的价值是可以肯定的,与“戏剧诗”的形式确立和完善同步,意味着西方戏剧形式民族化进程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诗化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是20年代以田汉为代表的纯艺术化的表现主义话剧到40年代以夏衍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话剧的一种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1]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2] 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333.
[3] 朱立元,张德兴.二十世纪美学(上)[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2.
[5]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87.
[6]罗宾·乔治·柯林伍德.艺术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7]埃德加·卡里特.走向表现主义的美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82.
[8]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9] 曹禺.曹禺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0]鲍山葵.美学三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57.
[11]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267.
[12] 董乃赋.文学史学原理研究[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
[13]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4] 钱中文.文学原理——发展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59.
[15]昂利·拜尔.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
【责任编辑 王雅坤】
Study on the Poetic Integration in the Realism Creation of Cao Yu in the 1930s
SONG Yu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The modernism of Cao Yu’s plays created in 1930s shows his reference and learning on two kinds of western aesthetic ideology “empiricism”and “expressionism”. This is based on his poetic temperament and poetic character contained in Chinese culture. The plays present the epitome of culture type in the 1930s. Meantime, the formation of his realism of poetization is not only the internalization of western modernism in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 of poetry, but also a transitional product of Chinese modern drama from expressionism in the 1920s to realism in the 1940s, which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odern Chinese theatre.
Cao Yu’s dramatic works in the 1930s; expressionism; empiricism; realismof poetization
2015-12-11
宋宇(1987—),男,河北省保定市人,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话剧。
I246
A
1005-6378(2016)04-0077-06
10.3969/j.issn.1005-6378.2016.0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