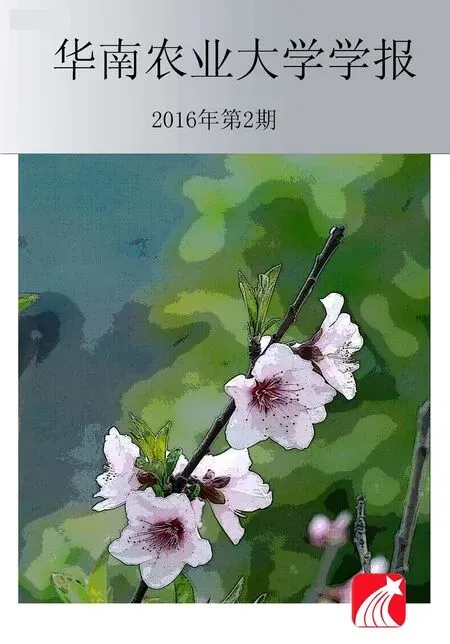从绅士到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变迁
2016-03-08马华灵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
马华灵(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
从绅士到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变迁
马华灵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绅士权威有两个来源,其知识来源是:知识正当化使绅士成为文化权威,知识等级化使绅士成为政治权威,知识公共化使绅士成为道德权威。其社会来源是,由于古代绅士跟州县官在知识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跟乡村平民在社会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并且州县官与乡村平民在知识视野与社会视野上存着着双重空集视域,所以绅士是州县官与平民之间的中介,而这为绅士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古代绅士逐步逐代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绅士权威的知识来源与社会来源都解体了,于是绅士权威也崩塌了。而绅士权威在乡村社会的崩溃,正是启蒙运动失败的根源。
关键词:绅士;知识分子;权威;启蒙;科举制度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传的自我安慰的思想挽歌[1-3]。这句话向世人昭示了启蒙的两种命运:启蒙运动业已寿终正寝,但启蒙精神永垂不朽。那么,启蒙运动何以最终走向覆灭?
要回答启蒙运动何以覆灭,首先要回答启蒙运动何以生存。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生存基础是两个根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是,西方价值是普遍价值。启蒙知识分子以传统/现代两分法以及中国/西方两分法为基本出发点,把中国与传统划上等号,把西方与现代划为等号。于是,中国的问题就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问题,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成为西方的问题[4-7]。基于此,中国启蒙运动的内在使命就是如何用西方现代的普遍价值取代中国传统的落后观念。第二个假设是,启蒙者在被启蒙者之前享有权威。启蒙者是知识分子,被启蒙者是普通民众。正是由于知识分子在普通民众之前享有权威,所以普通民众才愿意聆听知识分子的启蒙之道,并在某种程度上心甘情愿地践行这种启蒙之道。
启蒙运动的覆灭源于这两个根本假设的瓦解。第一,如果西方价值不是普遍价值,而是特殊价值,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以西方价值取代中国价值的问题。这样,以西方价值为旨归的启蒙运动就没有必要了。第二,如果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权威关系丧失了,那么,被启蒙者就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启蒙之道。这样,启蒙运动的纽带就崩裂了,启蒙之死就是它难逃的劫数。
中国学术界主要从第一个假设的瓦解出发来考察启蒙之死,而没有充分注意到第二个假设的瓦解也是启蒙之死的重要原因[3]。本文尝试从社会史角度切入思想史研究,从而探讨启蒙者的权威在乡村社会(即清代县以下地区)逐步逐代失落的过程,以此揭示权威解体与启蒙消亡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的论述以1905年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为中轴,向前追溯科举制度废除前中国绅士的权威来源,向后分析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威解体。本文的结构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古代绅士权威的知识来源及其解体,第二部分探讨古代绅士权威的社会来源及其解体。
一、绅士权威的知识来源及其解体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绅士由“绅”与“士”构成。“绅”指的是在职、退休、离职或遭贬黜的居乡官员。绅扮演着双重角色:绅在任为官时是官僚集团中的成员,而居乡闲赋时则是绅士集团里的成员。“士”指的是有功名或学衔的未入仕者,包括生员、监生、贡生、举人与进士。大部分官员亦有功名或学衔,且通常从“士”集团中的进士、举人与贡生里选拔而来,因此,“士”是潜在的官员[8-11]。绅士取得其身份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正途,即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取得,由国家授予其学品、学衔或正式的官职。另一种是异途,即通过捐纳获得,但并非所有官职与功名都可以捐买,通过捐买获得的功名只有例监生与例贡生,而通过捐买获得的官职通常都是低级官职[10]1。
绅士阶层被称为“四民之首,一乡之望”。就职业身份而言,士是士农工商之首,绅是官僚集团一员;就社会身份而言,绅士是乡村社会的领袖。清代文献中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表述: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载:“为士者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属编氓,皆尊之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庠之选。其所言所行,俱可以为乡人法则也。”[12]732
王凤生《绅士》曰:“为政不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礼,固不可以权势相加。即士为齐民之首,朝廷法纪不能尽喻于民,惟士与民亲,易于取信。”[13]
何耿绳:《绅士》曰:“绅士为一方领袖,官之毁誉多以若辈为转移。”[13]《钦颁州县事宜》云:“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10]34
绅士是官员与平民之间的中介。一方面他们代表乡村社会,向州县官提供信息与意见,表达乡村社会的诉求,维护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他们是惟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8]283另一方面则代表州县官,向平民百姓传达州县官的命令,以便于政令通达[14-15]。正是由于这种特殊身份,绅士在乡村社会中享有权威。绅士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基本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费孝通、瞿同祖、张仲礼、何炳棣、萧公权以及张静等对此都有论述[16]。相对于州县官所享有的正式权力,绅士在乡村社会享有非正式权力[8]282-284。在某种意义上,州县官与绅士共治乡村社会,官员的权力是官方法律正式授予的,而绅士的非正式权力则是民间惯例赋予的。
绅士权威的来源是知识,但是知识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权威的来源。知识成为权威的过程,就是知识成为资本的过程;而知识成为资本的过程,就是知识产生额外价值的过程。这个额外价值就是权威[17]。知识成为权威,主要经过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知识正当化,知识成为文化资本[18-19],绅士成为文化权威;第二个过程是知识等级化,知识成为政治资本,绅士成为政治权威;第三个过程是知识公共化,知识成为道德资本,绅士成为道德权威。
第一个过程是知识正当化,知识成为文化资本,绅士成为文化权威。在讨论知识正当化之前,首先要讨论绅士掌握的是何种知识?因为知识类型学可以揭示知识与权威之间的关系[20]。根据知识的不同对象,知识可以分为经验知识与观念知识。经验知识追问的是:事物实际是怎样的,怎样才是真实的,怎样才是有效的,它思考的对象是经验世界。例如,耕田怎样耕?织布如何织?关于这些问题的知识都是经验知识。而观念知识追问的是:事物应当是怎样的,怎样才是合理的,怎样才是正当的,它思考的对象是观念世界。例如,为什么要服从皇帝的统治?为什么要纳税?关于这些问题的知识都是观念知识。经验知识的功能是判断事物的真实性与有效性,而观念知识的功能是判断事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农民是“劳力者”,他们掌握的是经验知识;绅士是“劳心者”,他们掌握的是观念知识。
绅士掌握的是何种权威?权威是相对于知识的对象与知识的类型而言的。相对于绅士而言,农民是经验知识的权威,他们掌握耕织知识与苗圃知识;相对于农民而言,绅士是观念知识的权威,他们掌握政治知识与伦理知识。因此,绅士的权威指的是观念知识的权威,而不是经验知识的权威。
那么,从观念知识到权威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绅士的观念知识就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成为权威的过程就是知识正当化的过程。就政治系统而言,儒家学说是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可以解释为什么皇帝应该统治,为什么平民应该服从,而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又采用独尊儒术的策略,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因此,儒家学说确认了官方政治秩序的政治正当性,同时,官方政治秩序又反过来确认了儒家学说的文化正当性。两者之间是互相正当化的关系,儒家学说使政治秩序成为正当,政治秩序使儒家学说成为正统。就社会系统而言,儒家学说又是民间的社会伦理规范。儒家学说是民间伦理规范的理论化表达,它能够解释平民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关系、宗族关系与礼仪方式等。例如,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三从四德是正当的,为什么孝悌是必要的。这样,儒家学说确认了民间社会秩序的伦理正当性,同时,由于儒家学说在民间社会的充分解释力,民间社会秩序又反过来确认了儒家学说的文化正当性[21-22]。因此,儒家学说是一根拴起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伦理链条,整个中国传统秩序在这根链条的每一个节点上都可以找到其独特的位置,三者之间互相支援,构成了一个一体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要而言之,向上,儒家学说确立了政治秩序的政治正当性,而政治秩序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文化正当性;向下,儒家学说确立了社会秩序的伦理正当性,而社会秩序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文化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以儒家学说为媒介,绅士可以上通庙堂,下达民间,从而占据了官民枢纽的位置。因此,儒家学说成为文化资本,其额外价值是绅士成为文化权威。
第二个过程是知识等级化,知识成为政治资本,绅士成为政治权威。如果知识全民共享,人人唾手可得,那么知识就是廉价物,没有任何神秘性。作为廉价物的知识无法“购买”作为昂贵物的权威。只有知识成为稀缺产品,被少数人占有,作为稀缺产品的知识才能兑换成同样是稀缺产品的权威。知识等级化就是使知识成为稀缺产品的过程;同时,知识等级化也是知识成为政治资本的过程。绅士知识的等级化是通过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来完成的,其考察的核心内容就是绅士所掌握的儒家学说。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是过滤阀门,通过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层层过滤筛选,逐渐形成了金字塔形的阶梯性序列结构。这个金字塔从低到高依次为平民、生员、贡生、举人、进士与官员。平民处于金字塔的底端,人数最多,他们向绅士阶层流动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23]。生员、贡生、举人、进士及官员则构成了绅士阶层。越是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人数就越稀少,影响力就越大,政治权威就越高;相反,越是处于金字塔的底端,人数就越多,影响力就越小,政治权威就越低。每一层考试都是一个筛选器,筛选掉大部分,留下少部分。此外,绅士还通过知识等级化背后所隐藏着的座师、门生与同年等关系网络,跟官僚集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对州县官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他们可以越过州县官而直接跟其上司打交道[8]300。而农民通常没有能力来抵抗政府权力对乡村社会的侵扰,所以他们常常希望绅士能够在政治上保护他们[14]7-10。因此,相对于平民而言,绅士通过知识等级化而成为政治权威。
第三个过程是知识公共化,知识成为道德资本,绅士成为道德权威。倘若绅士仅仅关注私人事务,而不参与公共事务,那么,即便绅士拥有官方授予的学品、学衔或官衔,他们依旧不是地方权威。但是,如果绅士不首先具有官方授予的学位,绅士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否则,平民百姓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参与公共事务,从而形成非绅士的平民地方权威[8]285-286。因此,绅士的地方权威角色来源于官方与民间的共同非正式授权,官方授予绅士学品、学衔或官衔,使之具备一定的资格与能力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而绅士参与公共事务,从而跟乡村社会形成利益共同体,所以才成为地方权威[16]18-48。据叶镇《作吏要言》记载:“为官不接见绅衿,甚属偏见。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若槩不接见,势惟书役之言是听矣。况邑有兴建,非公正绅士不能筹办。如修治城垣学宫及各祠庙,建育婴堂,修治街道,俱赖绅士倡劝。”[24]绅士参与的公共事务主要有公共工程(例如修路筑桥),公共福利(例如赈济灾民),教育事务(例如修缮孔庙)、调解纠纷等[20-21]。绅士通过知识获得知识公共化的资格,反过来又通过知识公共化,把知识转化为道德资本,从而成为乡村社会德高望重的领袖。
然而,以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为标志,中国古代的绅士逐步逐代丧失了其政治与社会根基,他们逐步逐代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同时也逐步逐代丧失了其原来的绅士身份特征。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绅士通过从医、从军、从商等诸种途径转变职业身份,专业化与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25]。绅士阶层中的一支则逐步逐代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26]。但是,随着中国古代的绅士逐步逐代向现代的知识分子转型,他们在乡村社会所享有的地方权威在知识来源上也逐步逐代解体了。
在古代社会,中国绅士的知识是作为观念知识的儒家学说,但是,随着西学东渐的发生与中国新式学堂的建立,中国逐步逐代引进西方的现代学科建制,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从一元化逐步逐代走向多元化了。作为现代自然科学为科技知识分子所掌握,而现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则为人文知识分子所掌握。在传统中国,绅士的观念知识是一元化的儒家学说,但是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伦理知识则是多元化的现代学科知识: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知识人知识结构的变迁直接动摇了他们在乡村社会所享有的权威地位的根基,传统绅士的知识正当化、知识等级化与知识公共化随之逐步逐代解体了。
首先,绅士知识的正当化解体了,知识依旧是文化资本,但知识分子无法在乡村社会成为文化权威。在传统社会,中国绅士的知识正当化,是通过作为政治系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与作为社会系统的民间社会伦理规范来共同完成的。但是,在现代社会,按照西方学科建制设立的知识体系同时丧失了这双重正当性。一方面,哲学、政治学与法学等现代学科知识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知识系统。官方意识形态可能会涉及到某些学科的局部知识(例如马克思主义可能会涉及哲学、政治学等相关知识),但是现代学科知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不再像儒学那样,整体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它们已经无法在政治系统中找到它得以正当化的位置。另一方面,哲学、政治学与法学等现代学科知识也不是民间的社会伦理规范。民间的社会伦理规范同样可能会涉及到某些学科的部分知识(例如伦理学),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同样无法在民间的社会伦理秩序中找到其正当化的位置。现代中国民间的社会伦理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中国民间的社会伦理秩序,紧紧地焊接在传统的肢体之上,因此儒家学说对民间的社会伦理秩序依旧有充分的解释效力,即便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现代学科知识系统的挑战。反之,现代学科知识系统却无法对民间的社会伦理秩序做出充分的解释,它们与之产生了极大的疏离感与隔膜感。最近十年来这种现象逐渐为学术界所注意,例如朱苏力的法社会学研究[27-29]。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知识分子无法成为文化权威。
其次,绅士知识的等级化也解体了,知识在乡村社会无法成为政治资本,知识分子无法成为政治权威。从表面上看,现代知识体系也通过教育制度授予文凭与学位的方式完成等级化过程,但是现代知识的等级化过程不是在乡村社会完成的,而是在城市社会完成的。现代学科知识在乡村社会鲜有用处甚至毫无所用,无用的知识无法成为政治资本。正如费孝通所言:“当年轻人从学院毕业时,发现几年不在家乡,已经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在乡下,大学生无事可做。在现代大学里,学生学到了西方科学和技术(当然也包括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笔者注),而且也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体系,这是完全不同于乡下的。……如果他回去的话,他会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工作来应用在学院里所学到的知识。因为中国的大学不是为在农村工作的人准备的。他在大学里学到的是从外国输入的一般性知识。”[11]93-94并且,现代的教育制度与传统的科举制度完全不同。传统科举制度可以让绅士在政治系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从而使其在乡村社会成为政治权威。但是,现代教育制度无法让知识分子在政治系统中占有某种位置,因此知识分子无法在乡村社会成为政治权威。
最后,绅士知识的公共化也解体了,知识在乡村社会无法成为道德资本,知识分子也无法成为道德权威。中国绅士逐步逐代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的城居化,并且主要迁居北京、上海以及各省省会城市等大城市[30-31],他们不再像绅士那样与自己的家乡有着紧密的社会联系。现代知识分子离开乡村后,一般不再返回乡村,费孝通把这个过程称为乡村的社会腐蚀过程[11]95。现代知识分子离村不返村的原因之一,是现代学科知识在乡村社会没有用武之地,即所学无所用。正是由于这种与乡村社会有着极大隔膜感的现代知识体系,使得现代知识分子返回乡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样,离开乡村的现代知识分子也不大可能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因此,现代学科知识在乡村社会就无法兑换成道德资本,现代知识分子也无法在乡村社会成为道德权威。
在传统乡村社会,绅士的观念知识通过知识正当化、知识等级化与知识公共化,汲取其权威的知识来源。但是,在现代乡村社会,知识分子的现代学科知识无法在乡村社会正当化、等级化与公共化,绅士权威逐步逐代解体了。
二、绅士权威的社会来源及其解体
然而,州县官同样掌握着这种正当化、等级化与公共化的观念知识,何以他们在他们所治理的乡村社区并不享有这种权威,而仅仅是权力呢?为什么他们无法直接与乡村社会进行沟通,而必须通过绅士这个中介呢?由此可见,绅士权威的知识来源尚不能充分解释绅士在乡村社会的权威。接下去,本文将探索绅士权威的社会来源,以此来解释为什么绅士具有权威,而州县官却只有权力。
在分析绅士权威的社会来源之前,不妨先分析一个简单的事例。
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门,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么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32]
为什么乡下人不会躲汽车,而城里人不认得麦子?乡下人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知识结构、话语系统、生活习惯与处事方式等,这些构成了他之所以为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一切就是他的乡下人“视域”( horizon)。而乡村社会也有乡村社会的地域环境、生活状况、政治结构与经济水平等,这些就是乡村社会之所以为乡村社会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乡村视域。乡下人熟悉乡村社会,因为乡下人视域与乡村视域有许多交集。而正是因为乡下人视域与乡村视域之间的交集,乡下人维持了他在乡村社会的有效生活方式:他们知道什么时候麦子长熟了,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了。同样,城里人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知识结构、话语系统、生活习惯与处事方式等,这些就是城里人之所以为城里人而不是乡下人的城里人视域。也正是因为城里人视域与城市视域的交集,城里人维持了他们在城市的有效生活方式:他们知道过马路要看红绿灯,知道如何躲避汽车,知道如何去购物。而乡下人之所以不会躲汽车,是因为乡下人视域与城市视域在汽车这个方面没有充分的交集;城里人之所以不认得麦子,是因为城里人视域与乡村视域在麦子这个方面没有充分的交集。
两种视域之间没有交叉的部分,可称之为“空集视域”。两种视域之间互相交叉的部分,可称之为“交集视域”。如果一个人的视域与他所生活的社区视域有许多空集视域,那么他就会无所适从,格格不入。如果他要继续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的有效性,那么他必须重新社会化,慢慢习得这个社区的视域,从而使其视域与该社区的视域构成充分的交集视域。而如果这两种视域有充分的交集视域,那么,他就会如鱼得水,得心应手。由于城里人视域与乡村视域之间有许多空集视域,所以城里人在乡村社会不会生火,不会割稻,不会捉泥鳅;由于乡下人与城市社会有许多空集视域,所以乡下人在城市社会不会坐车,不会过马路,不会躲汽车。但是,如果城里人在乡村生活久了,慢慢熟悉乡村社会,那么,城里人视域与乡村视域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交集视域,城里人就逐渐适应了乡村生活。乡下人在城市生活亦如是,乡下人慢慢熟悉城市社会,乡下人视域与城市视域也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交集视域,乡下人也会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因此,交集视域是生活方式有效性的前提,空集视域是生活方式失效的前奏。
交集视域也是理解和沟通的前提,空集视域则是无法理解与无法沟通的条件。酒逢知己千杯少,是因为知己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共同语言就是交集视域。交集视域使知己之间默契投缘,惺惺相惜。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因为双方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就是没有交集视域,也就是空集视域。空集视域使双方之间无言以对,相交不欢。斯瑞西阿得斯无法理解苏格拉底,所以火烧苏格拉底的思想所[33];柏拉图理解苏格拉底,所以写下流传千古的《申辩篇》。
以空集视域与交集视域为基础,再回头检视这个问题:州县官为何无法在乡村社会享有绅士般的权威?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清代的政治结构中找寻答案。清代政治结构中三个特别之处:第一,根据《回避法》,官员不得在他原籍省份任职,并且也不能在距原籍不足五百里之地的邻省任职[8]292。第二,清代州县幅员辽阔,除了州县行政驻地及其周围市镇外,尚有大量村庄,最少的四川省彭水县也有26个村庄,而最多的江苏省溧阳县居然有1560个村庄[34]。第三,州县官的任期较短,据张仲礼对清代顺治朝至光绪朝的河南鹿邑与湖南常宁所做的统计,州县官的平均任期基本不超过五年,道光朝常宁知县的平均任期甚至只有1年[10]51。
正是以上三个因素的结合,使得州县官无法在短时间内熟悉他所治理的地方社会。州县官原来所有的那套视域无法与其辖区的视域构成充分的交集视域,相反,两种视域之间有许多空集视域,例如,州县官可能不熟悉当地的风土民情、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等。因此,州县官必须求助于当地人,尤其是绅士,清代州县官对之有所记载:
汪辉祖《客言簿》云:“民情土俗,四境不同,何况民之疾苦,岂能画一。好问察迩,是为政第一要著。书役之言,各为其私,不可轻信。阍人之说,往往为书役左袒。绅士虽不必尽贤,毕竟自顾颜面,故见客不可不勤。余初到官,见客即问其里居风土,再见则问其里中有无匪类盗贼讼师,如有其人,并其年貌住处皆详问之。而告以迟迟发觉,必不使闻风归怨,故绅士无不尽言者。客去,一一手记于簿,或问其地,某多平原,某多山泽,与某里连界,亦手为详记,扃之箧中,置之内室。”[24]
叶镇《作吏要言》曰:“为官不接见绅衿,甚属偏见。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24]
而即便州县官在上任之初对乡村社区的诸种独特性详加咨询,他们也仅仅获得部分的交集视域。相对于其所辖区的辽阔幅员来说,这还远远不够。要想熟悉,恐怕要许多年才行,而当他们逐渐熟悉了乡村社区的这些独特视域的时候,他们又被调走,赶赴他地走马上任了。因此,乡村社会与州县官之间始终存在着各种空集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即便州县官与绅士一样掌握了正当化、等级化与公共化的观念知识,这种观念知识还是不能有效地应用于各种具有地方性特征的乡村社会,两种视域间的各种空集视域限制了观念知识的效力范围。
而乡村社会的绅士,对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社区了如指掌,他们的视域与乡村社区的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存在着大量交集视域。因此,他们能够以自己的观念知识有效地解释乡村的伦理规范等。这样,州县官就需要通过绅士这个中介,与乡村社区进行有效地沟通。官僚发布的命令与平民横亘着一道沟壑,因此,命令不一定能够有效地执行。而绅士与平民的视域之间有许多是交集的,他们之间的沟通是有效的,所以,官方的命令透过这个中介,反而能够得到有效地执行。如果官员的视域与百姓的视域之间共享着充分的交集视域,而官员与绅士一样掌握着有效的观念知识,那么绅士的中介功能就会被架空,绅士在乡村社区的权威定然会大打折扣。正是因为中国特殊的权力结构,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力无法着陆,从而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形成了区隔,造成了官方与民间之间的诸多空集视域。这些空集视域为绅士预留了权威的缝隙。
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看,平民的视域与官僚的视域存在着双重空集视域:在社会层面,官僚不熟悉乡村的乡土民情、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等,平民也不了解官僚的生活方式等;在知识层面,平民不熟悉绅士的观念知识,绅士也不熟悉平民的经验知识,因此,平民与官僚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这样,平民与官僚之间就需要一个可以有效沟通的中介,这个中介的特殊性是既可以上达官方,又可以下至民间,而绅士就是这样一个中介。就绅士与平民的沟通而言,在知识层面,平民与绅士同样存在着诸种空集视域,因此双方无法在知识上进行有效的沟通;但是在社会层面,平民与绅士却存在着诸多交集视域,绅士同样熟悉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社会,这样,绅士就可以通过这些交集视域,把他们的观念知识传译( translate)给平民,把抽象的观念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地方性知识,使平民知晓这些观念知识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何关联,从而有效地与平民进行沟通。因此,正如王凤生《广教化》与栗毓美《义学条规》所载,州县官通常把宣讲与解说皇帝的圣谕十六条的任务交给当地绅士与长老,而不是自己亲自到现场进行宣讲[13]。就绅士与官僚的沟通而言,在社会层面,双方同样存在着诸多空集视域,官僚不熟悉绅士与平民共同生活的乡村社会;但是在知识层面,双方却存在着诸多交集视域,官僚与绅士都掌握作为观念知识的儒家学说,因此,双方可以借助知识层面的交集视域有效地进行沟通。在这个意义上,绅士在乡村社区是被双重依赖的,他们上与官僚以知识层面的交集视域进行沟通,下与百姓以社会层面的交集视域进行交往。绅士这个特殊的纽带,带动着官僚与百姓的齿轮,使乡村社会的机器得以正常运转。
因此,绅士在乡村社会所享有的权威,既与知识紧密相关,也与社会紧密勾连。州县官、绅士与平民之间的空集视域与交集视域关系是绅士获取权威地位的社会来源。
但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古代的绅士逐步逐代向现代的知识分子转型,绅士在乡村社会的社会权威地位在社会来源上也逐步逐代不复存在了。
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城居化。知识人迁居城市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古代的绅士也倾向于迁居市镇与城市,但是,古代绅士迁居市镇与城市的人数规模与迁移距离远远不及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人数规模上来说,迁居城市与市镇的主要是那些占少数的官员与高级功名持有者,一般的生员通常没有经济能力维持他本人及其家庭在市镇与城市的生活,这样,大量的低级功名持有者只能在乡村生活。但是,现代知识分子则主要生活在城市,因为现代城市里的学校、媒体与社团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空间[21],而在乡村却找不到这些机构。从迁移距离上来说,即使古代的绅士迁居市镇与城市,他们通常都迁往离其家乡不远的市镇与城市,因此,他们依旧与他们生长的乡村社会有着紧密的血脉联系,并且仍然可以保持其与乡村社会的交集视域,以及社会权威地位。但是,现代的知识分子则倾向于迁居大城市,并且大量集中于北京、上海或其他省会城市,因为这些地方集中了中国最主要的学校、媒体与社团。这样,现代知识分子与其乡村社区之间的空间距离逐渐拉远,并且逐代疏离,他们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交集视域亦逐步逐代慢慢缩小,而空集视域则逐步逐代慢慢扩大。而更要紧的是,这些空集视域不是在一代人之间突然扩大的,而是有如水的波纹层层扩散般,逐步逐代蔓延开来。
所以,在现代知识分子与乡村社会之间,逐步逐代产生了双重的诸种空集视域。一方面,在知识视野上,现代西学与平民的知识结构之间有一条鸿沟,两者之间产生了许多无法共享的空集视域。而另一方面,在社会视野上,现代知识分子与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等亦逐步逐代产生了诸多空集视域。在知识分子城居化这个背景之下,知识分子远离乡村,逐步逐代丧失了对乡村社会的熟悉感,使得知识分子把西学传译给平民在空间上发生了困难。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双重空集视域使现代知识分子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在社会来源上也不复存在了。
结论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前,中国古代绅士的权威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知识来源,古代绅士所掌握的观念知识主要是儒家学说,这种知识在乡村社会经过知识正当化、知识等级化与知识公共化,构成了绅士权威的知识基础。第二个来源是社会来源,一方面,中国古代绅士与州县官在知识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与乡村平民在社会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而另一方面,州县官与乡村平民在知识视野与社会视野上存着着双重空集视域,这样,绅士就成为州县官与乡村平民之间的中介,而这构成了绅士权威的社会来源。
但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古代绅士逐步逐代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绅士权威也逐步逐代解体了。绅士权威的解体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知识方面,现代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主要是多元化的现代学科知识,这种知识结构的变迁使得传统绅士的知识正当化、知识等级化与知识公共化都逐步逐代解体了;第二,在社会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城居化使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在知识视野上与社会视野上产生了双重空集视域。
启蒙与权威的关系到底如何呢?在权威的知识来源方面,现代学科知识在乡村社会没有用武之地,如果启蒙知识分子以这套知识体系为启蒙内容,乡村平民自然毫不理会,甚至不屑一顾,更不必说接受这套知识体系了。在权威的社会来源方面,即便这套知识体系对乡村社会价值非凡,但由于知识分子在社会视野上与乡村社会逐步逐代拉开了距离,产生了诸多空集视域,从而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难于把这套知识体系以交集视域的方式传译给乡村平民,这样,乡村平民依旧会认为这套知识体系与自己相距甚远。
赫拉克利特曾言:“驴子宁愿要草料而不要黄金。”[35]问题是驴子为何不选择能够购买更多草料的黄金,而选择吃完即无的草料呢?在人类的世界里,黄金价值连城,而草料一文不值,因为黄金可以购买更多的草料,而草料却无法兑换出更多的黄金,因此,人类宁愿要黄金而不要草料,驴子实在是“大蠢驴”!但是,在驴子的世界里,恰恰相反,黄金一文不值,因为它不能给它带来温饱,而草料却可以填饱肚子,因此,草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类实在是一头“大蠢驴”!而这就是现代的启蒙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之间的关系。换一下赫拉克利特之箴言的主语与宾语,这句话就变成“乡村民众宁愿要白花花的米饭而不要空洞的自由民主”。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看来,自由民主是民众可以每天正常吃上白花花的米饭的根本前提,如果没有自由民主,已经拥有的白花花米饭,随时可以被剥夺,因此,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民主是自由的制度保障。而民众居然对自由民主等核心价值置若罔闻,竟然不知晓自由民主所承负的价值意义。有些启蒙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民众太愚昧,太不可理喻,甚至发出一些感慨:“我终生为中国民众的自由民主而抗争,但是中国民众却毫不理会,我为如此愚昧的民众而抗争,值得吗?”而另一方面,有些民众则认为知识分子都是一群在书斋里胡思乱想的书呆子,谈什么自由民主,吃饭问题比什么自由民主重要多了,自由民主又不能当饭吃。如上所述,驴子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一个关于黄金的空集视域,而民众与知识分子之间则存在着一个关于自由民主的空集视域。在这两个空集视域之中,双方互相误解,互相无法有效沟通,互相以为对方是傻子。而这跟权威解体紧密相关,在知识层面上,民众对自由民主不以为然,因为自由民主无法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等形成充分的交集视域,;而在社会层面上,知识分子难以把自由民主传译给民众,因为知识分子逐步逐代与乡村社会形成了许多空集视域。因此,乡村民众认为自由民主抵不上米饭。
然而,自由民主与米饭之间的空集视域并非不能打破。尽管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存在着知识视野上的空集视域,但是,倘若知识分子能够以一定的方式深入乡村社会,逐步熟悉乡村的风土民情、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状况,与之形成充分的交集视域,那么,知识分子可以借助民众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等方式,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扣紧乡村社会的脉搏,阐释自由民主与米饭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自由民主与米饭之间就可以通过这个交集视域所形成的桥梁得以互相传译,从而使启蒙在乡村社会产生效力。而这或许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主义启蒙在乡村社会大获全胜,而自由主义启蒙却一败涂地的奥秘所在。
在古代乡村社会,启蒙是有效的,启蒙运动却不必要;在现代乡村社会,启蒙运动是必要的,启蒙却无效了。启蒙越是无效,越是呼唤启蒙运动,而越是呼唤启蒙运动,启蒙越是危险。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M]∥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239-271.
[2]许纪霖.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许纪霖,等.启蒙的自我瓦解[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1-26.
[4]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透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M]∥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86-106.
[5]张灏.传统与现代化——以传统批评现代化,以现代化批评传统[M]∥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19-133.
[6]LIN,YU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
[7]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8]瞿同祖.士绅与地方行政[M]∥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88-293.
[9]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49.
[10]张仲礼.中国绅士[M].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1]费孝通.中国绅士[M].惠海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2]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徐栋,辑.牧令书:卷十六[M].李炜,校刊.清道光28年刊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14]FEI,HSIAO-TUNG.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6,52( 1) : 8.
[15]HSIAO,KUNG-CH’UAN.Rural Control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J].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53,12 ( 2) : 173-181.
[16]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17]DE SOTO,HERNANDO.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lls Everywhere Else [M].London: Black Swan,2001: 41.
[18]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9]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0]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M].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1-22.
[21]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M]∥许纪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30.
[22]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M]∥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27-161.
[23]HO,PING-TI.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1368-1911[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59,1( 4) : 330-359.
[24]徐栋,辑.牧令书:卷七[M].李炜,校刊.清道光28年刊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25]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26]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J].二十一世纪,1991.
[27]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28]苏力.阅读秩序[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29]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30]邓若华.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M]∥许纪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55-193.
[31]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M].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37.
[3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
[33]阿里斯托芬.云·马蜂[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08-109.
[34]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范忠信,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
[35]HERACLEITUS.Heracleitus on the Universe[M].tran.W.H.S.Jone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 487.
From Gentry to Intellectuals: the Decline of Authority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MA Hua-ling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nd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gradual shift of author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gentry to modern intellectual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Base on the analysis,gentry's authority comes from intellectual origins and social origins.Legitimation,hierarchy and publicity make gentry's authority in cultural,political and moral area.There is“convergent horizon”in the intellectual area and social area while“divergent horizon”exists between the country magistrate and villager in the intellectual area and social area.The ancient gentry as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country magistrate and villager and forms the authority in the rural society.With the abolition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the gentry's authority was gradually undermined duo to the urbanization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with the crash of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and social origins.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gentry to modern intellectuals leads to the failure of the Enlightenment.
Key Words:gentry; intellectuals; authority; the Enlightenment;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作者简介:马华灵( 1982—),浙江临海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哲学、知识社会学、乡村社会学与当代中国政治。E-mail: 11110170004@ fudan.edu.cn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 201206100043)
收稿日期:2015-09-29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2.013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 2016) 02-01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