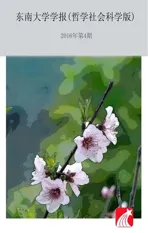传统艺术理论中的欲道观与雅俗论:去欲归雅
2016-03-07张婷婷
张婷婷
(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3)
传统艺术理论中的欲道观与雅俗论:去欲归雅
张婷婷
(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3)
在中国古代不同时代与文化语境中,传统艺术观念中“雅”与“俗”的关系极为复杂: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转换,既彼此互动又相互消长,不断规正着传统艺术发展的走向。在儒道观念影响下,传统艺术理论均尚雅抑俗、以雅为正,但其贬抑之“俗”绝非民间艺术中质朴淳厚、直白率真的“质”“野”风格,实质上乃是直接表现人的感官欲望、放纵无节制、恣肆恶俗的艺术形式。在求“雅”的追求中,传统艺术理论总是在寻求不同于世俗感官表现的艺术方式,试图突破“人欲”的束缚,达到具有超越性的雅化境界,并由此产生一套独特的艺术理论,作用于画论、琴论、曲论等各个门类艺术。①
传统艺术理论;雅俗观念;去欲归雅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艺术史演进过程中,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总是相互争夺着社会文化空间,二者在不同时代与文化语境中相互渗透与转换,虽彼此互动但又相互消长,规正着艺术的发展走向,使传统艺术大致经历着由俗返雅、由雅趋俗、雅俗兼备的过程。因而,在传统艺术观念中,“雅”与“俗”是一对重要理论范畴,是历代文人学士们品评艺术并为之分定优劣的核心标准之一,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以士大夫精英阶层为代表的精英艺术与以大众阶层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均各为畛域,双峰并峙,“雅”与“俗”的观念也根植在传统士阶层精神世界,为其最为稳定的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去俗归雅,即对艺术的归正性审美追求,这成为影响着中国艺术的进程与发展的巨大力量。事实上,无论是儒家以“和”、“古”、“中”、“正”为雅,还是道家以“清”、“奇”、“高”、“逸”为雅,各家各派对于“雅”的阐释与见解虽不尽相同,但都坚执雅俗二体的二元思维,其审美观念深深根植在艺术理论的阐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建立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与道家的生命情怀之上的雅俗观,从哲学层次到文艺理论均为中国传统艺术建构起一套尚雅抑俗、以雅为正的审美价值观。然而,儒道两家所否定的、所贬抑的艺术之“俗”,并非针对民间艺术质朴的性格而发,相反,对于民间艺术的朴实淳厚、直白率真的“质”与“野”风格创造,往往抱持肯定的态度,赞赏其直抒胸臆而毫无矫饰、率性抒发而毫无雕琢的自然而然的格调。传统之雅俗观,非但不是将“精英艺术”与“民间艺术”简单的对立,而且也非草率地否定传统艺术的质朴率真之本性,“俗”之观念乃是建立在道德层面上的,即指艺术中过度而无节制的靡靡之音,这种艺术直接表现人的感官欲望,其放纵无节制,恣肆无顾忌,以低级恶俗、颓靡淫荡的表现形式,大坏人心,损害道德,违反自然而然的天道伦理,这与中国艺术主心主情而非重物重欲、以心灵直觉展现形而上的精神相悖,这有违对宇宙自然的美的追求,桑间濮上的亡国之音,即“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1]1016之谓也,必然导致“有国必亡国,有家必败家,有身必丧身”[2]49-50的结局。所以,无论精英阶层还是草根阶层,都力求通过对雅的归正性审美文化的建构,以“雅”的文化权力去除“欲”之俗而存“正”之雅,因而在传统艺术观念中,“雅”与“俗”并非大传统精英艺术与小传统民间艺术的直接对立,而是直指道德层面的古正美德与靡靡淫侈的风格对立,通过道德层面的“去欲存雅”,保存艺术风格的“以雅归正”,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探索的归正性审美追求,并作用于各个艺术门类的理论观念之中。梳理画论、琴论和曲论中共通的艺术规律,对于我们厘清古代“雅”与“俗”的复杂关系以及古代艺术的发展走向,具有正本清源的文本意义以及指导并开创当今艺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时代意义。而这首先应该明确中国古代“雅”的归正性审美追求的本质和内容。
一、雅的归正性审美的追求:代去杂欲
一般说来,艺术中的“雅”通常指雅正、高雅、大雅、文雅等含义,代表着艺术发展的纯正方向,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内蕴在作品中的博大、崇高、深刻与先进,具有深远的意味与上层的境界,追求深层次的精神探索。与之相对,“俗”则曰通俗,被赋予不雅、非正、低劣等义,代表着艺术价值的世俗化取向,通常不追求深刻的哲思与精神的拷问,以质朴的、浅近的、单纯的、通俗的方式,满足大众的口味,显示出娱乐化的色彩。
雅俗的概念起源于先秦,此时的艺术是一种包括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观念,而尤以音乐为其代表,因此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乐”通常指综合的艺术形式,当时建立在“乐”的艺术活动中展开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认识或总结,可视为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发端。最先出现“雅”的概念为《毛诗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雅即正也,意味着一切符合规范、符合标准、符合道德的行为,均能称之为“雅”。例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雅,正也”(《玉篇·隹部》);“雅言,正言也”(魏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雅,正也”(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等等。正而有美德是儒家认知的“雅”的本质意义,也意味着“雅”的概念从产生之始就被赋予一定的政治性意味,具有儒家的伦理化色彩,并非纯粹的审美活动,它与人的道德行为密切相关,被融入人性美善、人格确立等一系列规正性的指引作用,以形而上的方式影响着人的道德行为,即儒家所说的“乐者,德之华也”(《礼记·乐记》)。因此,中国古代艺术“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是儒家主流派极力倡导而践行的艺术观念,也与其“祟礼”的礼乐文化精神不可分割。乐的实用功能的政治化、仪式化是中国文艺批评传统的开端,也是探讨雅俗观念起源及其特征的切入点。
所谓“俗”,《康熙字典·俗条》将其解释为:“不雅曰俗”,把“俗”直接放置于“雅”的对立面,这也形成了我们对“俗”的一般性理解。然而在传统观念中,“俗”乃有更为深层的指义,如东汉刘熙在《释名》中的定义:“俗,欲也,俗人之所欲也。”将“俗”诠释为“欲”,提出“俗”即是“人欲”也,作用于艺术,则其通过物质形式直接表现人的感官欲望,目的是迎合大众的流俗的喜好与品味。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欲”是俗的根本特征,或者说是“俗”的劣根性,其特点是:“欲者,性之烦浊,气之蒿蒸;故其为害,则燻心智,耗真情,伤人和,犯天性。”[3]67欲望是人性之浊气,倘若一味放任不加以节制,便会有伤天人之性。同样,嵇康用木与蝎的比喻贴切地点出过度表现“欲”的“违性”“害性”,亦即:“蝎盛则木朽,欲胜则身枯。”[4]169这种害性,常常根植在艺术表现中,以娱乐消遣的方式,使人溺情沉湎,迷恋于物,而丧失于志,如同《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对齐王沉溺于世俗之乐的生动记载: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在这一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齐王直言不好听先王之雅乐,笃爱世俗之乐,原因则是,与雅乐相比,世俗之乐更具有“享乐愉悦”的娱乐性与消遣性,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形式,直接宣泄人的内在心理,用艺术的方式刺激感官,满足人们的审美欲望,使其获得身心的享乐快感。事实上,“俗”的义涵也是丰富的,除了“欲”之外,还有风俗、习惯、大众的等等语符指义,当作“风俗”、“大众的”解释时,“俗”并不具有褒贬的倾向性,当其纯粹表现欲望,用与感官相联的艺术形式以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使之审美欲望获得即时的满足,产生享乐的快感,这种艺术违反了道德伦理与审美原则,当被贬抑与禁止。从这一层面上看,儒家“以德为雅”、“以欲为俗”的雅俗观念,是一种道德与审美的统一,二者相互构成了儒家审美追求的终极目标,因而贬抑非道德的欲望,批评淫靡的郑卫之音,将其置于“俗”的艺术,皆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观照艺术,是直接立足于现实人生、积极有为的审美方式。
在雅俗异势,雅乐与郑声二元对立的影响下,艺术如何去“俗”存“雅”,达至无功利性的澄明境界,这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试图阐释的重要问题。儒家通过礼乐等级的制定,并根据等级的原则对艺术的表现形式作出明确区分,即通过“以礼约之”的方法约束艺术的活动,强调“发乎情,止乎礼”,因而“季氏八佾舞于庭”明显违背了礼制,所以便不能不遭到孔子“是可忍,熟不可忍也”的严厉批评。然而,艺术的活动又是一种情感性的表达,其中又不能没有“欲望”表达的层面,因为人生皆有欲,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自然客观的物质欲望也是为生命所必需,它在与外物接触的活动中不断呈现,因而它也是合“理”或依据于人性的,应该给予肯定,但是如果缺少了自我的内部节制,一味被外物引诱,欲求就会过度或膨胀,甚至背离“天理”,不利于道德精神的修养。所以,儒家提出了“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观念。正因如此,《荀子·正名篇》提出了“道欲”和“节欲”两个概念,“道欲”是合理化的欲望,“节欲”是节制过度的欲望,因为在无节制的精神状态下,人往往会被私欲所蒙蔽,看不到人生与世界的真实,更无法体悟天地万物之理。要真正体验万事万物的共同之理,就必须遏止超出社会限定而有违于正当欲望的奢求,除去源于原始心理而过度放纵的私欲。从这一意义看,作为人的情感的一种表现方式,传统艺术的境界,从来不于喧嚣处激荡情感,宣泄放纵,向来追求于安静处体悟物我合一,天地同心,作到“胸中无事”便能“自和乐”,一旦超出合理的欲望而一味放纵,或“放开一路而欲其和乐”,便是违反常理的刻意追求,无论对人心涵养或对艺术意境而言,都是大有伤害而不可取的。也就是说,艺术不能用华丽复杂的形式去刺激人的欲望,让人执著于艺术的外在形式,丢失了本心本性,耽溺于纵情享乐。因此,传统艺术追求恬淡和谐,使人既不着意于艺术形式,又不受情性的拘限,并通过艺术化的赏析,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身心。因而,“从对美的主观感受来说,就是要把对味、色、声的粗野放肆的官能快感的追求同真正的美感区分开来;从客观的美的对象来说,就是要探寻那能引起真正美感的对象的构成规律。”[5]81
在道家的观念中,其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尽管不赞成儒家人为的音乐教化,但也反对用过分华丽的艺术形式愉悦感官,否定以享乐为旨归的审美方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6]7过度追求艺术形式上的炫目华美,只能以形害志,使人玩物丧志,从而体会不到艺术真正的美感。因此,在道家看来,最高的艺术境界是心无挂碍的“大音希声”,是一派圆融自然天成的境界。在老子的基础上,庄子则另求一种胸中求正、祛除杂欲的方式:“此四六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7]810这就是说,破除过多的欲望之后,才能使心胸正静,一派澄明,达到“物我两忘之地”、“仁智独得之天”的状态,超越外在形式的束缚,进入艺术的本体内涵,体会到天地间的意义,达致一心不乱,疾空烦劳,顿破无明,廓然开悟,才是艺术的至高乐境。
综上,在儒、道观念的影响下,中国艺术在求“雅”的追求中,总是在寻求不同于世俗感官表现的艺术方式,以此化解欲望的表现,试图突破“欲”的束缚,达到具有超越性的雅化境界,并由此产生一套独特的艺术理论,并作用于画、琴、曲等各个艺术门类。下文将从画、琴、曲三个艺术理论角度逐一论述中国古代去欲归雅的归正性审美追求。
二、画论中的去欲归雅论:嗜欲者,生之贼也
在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的去俗归雅论的精髓体现在在对“欲”的批判理性中达至“脱俗”而归于“雅静”“淡泊”的人生境界。历史地看,中国画论雅俗观念基本形成于魏晋时期。此时画论品评的著作,已有尚“雅”黜“俗”的评价。南朝宋画家宗炳提出“澄怀味像”,认为观山赏水,引起无限的情思,目的只不过是让精神充盈愉悦,审美主体要求以清澄纯净、无物无欲的情怀,在非功利、超理智的审美心态中,品味、体验、感悟审美对象内部深层的情趣意蕴、生命精神。五代后梁画家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欲”对艺术创作的害性:“嗜欲者,生之贼也。”[8]4影响绘画精神表现的最大障碍即在于“杂欲”,过多的欲望让使人杂念挂心,浮躁不宁,只有将欲望渐少渐无地化解,内心愈加宁静愉悦,达到减淡玄远、清逸高韵,无功利地进入艺术的创造,才是“雅”的境界,这也成为此时画论所倡导的艺术观念与风格追求,诚如宗白华所言:“他们的艺术的理想和美的条件是一味绝俗”,“晋人的美感和艺术观,就大体而言,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富于简淡、玄远的意味,因而奠定了一千五百年来中国美感——尤以表现于山水画、山水诗的基本趋向。”[9]203如何使艺术获得简淡、玄远的意味,必须从人心的根本下功夫,坐忘肢体感官的存在,祛除迷妄之心与无明幻象,以虚无之心对待万物,在内外彻明的自性中,通于宇宙,获得灵明不昧的艺术本真,诚如谢赫《古画品录》对姚昙度“真为雅郑兼善”[10]12的盛赞,又如对毛惠远“力求韵雅,超迈绝伦”[10]14的激赏,再如对陆杲“体致不凡,跨迈流俗”[10]17的褒扬,等等。均是强调以内省的方式,获得虚静空明的艺术之真。此时“雅”的审美已逐渐从儒家道德理想的评价中脱离出来,从道德教化与艺术审美的相辅相成,走向道家“游”的纯粹审美,但脱离了以正为雅的道德规约,并不意外着艺术的表现可以向世俗化方向发展,道家以其“游”的超越精神艺术贯注了灵性,点缀了超越世俗生活的意义,祛除了“欲”的世俗性表达,打开了为人性提升的向上之门。借用铃木大拙的表述,便是“艺术家作为创造者,同我们这些只在俗套范围内活动的人不同,他生活在更高的层次。禅主张独特方法论的目的,正是在于从比这更深的灵感之泉中,掘出一条自由宣泄的通路。”[11]157
在明清时期,中国画论更提出文人要自觉地去俗存雅,作画先要修身,必须化解自身的欲望,以虚静的状态进行创作,继而达到“雅”的境界,文人画家依托庄子“虚也者,心斋也”的思想,黜聪明,去知识,消弭人为物役,解除心为物累,寻找去除“俗欲”的途径与方法,从而探索超越性的审美追求。如明代的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所言:“绘事必以微茫惨淡为妙境,非性灵廓彻者,未易证入,所谓气韵必在生知,正在此虚淡中所含意多耳。”[12]278明末沈宗骞更是撰成《芥舟学画编》论“避俗”,提出“存雅去俗”的观点,批评绘画趋俗的害性:“画而俗如诗之恶,何可不急为去之耶?”他提出“俗”的五种形式:“既不喜临摹古人,又不能自出精意,平铺直叙、千篇一律者,谓之格俗。纯用水墨渲染,但见片白片黑,无从寻其笔墨之趣者,谓之韵俗。格局无异于人,而笔意窒滞,墨气昏暗,谓之气俗。狃于俗师指授,不识古人用笔之道,或燥笔如,或呆笔如刷,本自平庸无奇,而故欲出奇以骇俗,或妄生圭角,故作狂态者,谓之笔俗。非古名贤事迹及风雅名目而专取谀颂繁华,与一切不入诗料之事者,谓之图俗。能去此五俗而后可几于雅矣。”[13]61绘画之五“俗”,是形式上之“俗”,将其在作品当中摒绝抛弃绝非容易,不经过一番涵养德性的修证功夫,绝难达到。因此,文人画家不断从理论上寻找去俗的方法,例如沈宗骞认为,去俗的根本,要从平时里除去杂欲,在日日习以为常生活中的涵养习性,从人的根性上下工夫,做到无一点尘俗之染,方可达到艺术创作的“雅”,并提出“市井之人,沉浸于较量盈歉之间,固绝于雅道”;“乃有外慕雅名,内深俗虑,尤不可与作笔墨之缘”[13]63。入世较深者,精于算计,终无清气,故再有技法,终难达到艺术的脱俗之境。这些观点,可视为对绘画领域历代倡雅鄙俗思想的总结。同样的观念,在清初画家恽格《南田画跋》中也有体现:“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着笔。所谓天际真人,非鹿鹿尘埃泥滓中人所可与言也。”[14]48“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是文人画家追求的审美理想境界,是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艺术旨趣,非“鹿鹿尘埃泥滓中人”所能理解。而后,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列“远尘”、“脱俗”二章,系统的以理论形式对绘画中的雅俗进行了探讨,石涛坚持倡雅贬俗的立场,明确地提出避俗的方法,“人为物蔽,则与尘交。人为物使,则心受劳。劳心于刻画而自毁,蔽尘于笔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损无益,终不快其心也。我则物随物蔽,尘随尘交,则心不劳,心不劳则有画矣”[15]157。也就是说,人过多地执著于尘世的物欲,则身心受到拘束,为物所累,便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开启澄明的艺术境界。诚如董欣宾、郑奇对石涛雅俗观的评价:“最主要的并不是大众化、普及化的下里巴人之俗,而是指画家心地不干净,人俗而导致了画格之俗。”[16]209只有当画家忘却自身的存在,不为物累,不为心劳,达到非功利的艺术创作状态,才能一任自由精神的逍遥遨游,进而存雅去俗。
上述表明:绘画理论中的去俗论,一方面强调主体精神的修养,只有艺术家从本性上涤尘除浊,化解自身欲望的束缚,保性全真,不以物累形,或进入“虚静”、“专一”的状态,方能创造出清净绝尘、静穆和雅、圆融无碍的艺术作品;而另一方面也强调人们从根源上涤除尘俗之气,超然趋淡泊,闲逸归宁静,才是艺术人格的胸襟气象,也是去俗求雅的根本。这诚如宗白华所说:“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欧阳修说得最好:‘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17]162事实上,绘画理论中“脱俗”而归于“雅静”“淡泊”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也贯穿于中国古代琴论之中。
三、琴论中的去欲归雅论:琴者禁也
作为士阶层的“雅器”,琴论中也有大量关于雅俗之争的探讨。早在东汉,桓谭在其《新论·琴道》中,便提出了“琴者禁也”的命题,“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18]64,琴乐的根本是禁止欲望杂念,收敛身心,回归心性的本源,达到万物合一的超然状态,不像其他音乐一样,是刺激的、享受的,古琴的声音是收敛的、回归的,从而让人从禁体悟静。因此“琴者禁也”成为琴论中重要的命题,被后世理论不断诠释,一直影响了其后近两千年中国的琴论发展史。如汉代《白虎通·礼乐》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19]53,明确将“禁”作为“琴”之本性规定,认为琴乐是禁止淫邪欲望,归正人心的雅器。唐代薛易简著《琴诀》云:“盖其声正而不乱,足以禁邪止淫也”[20]555,认为琴声是雅乐之正声,绝非郑卫之乱音,是可以禁止淫邪之欲望,而归正人心的雅乐。宋代朱熹更是具体提出琴音的作用:“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21]45,在朱熹的观念中,琴乐不以华丽复杂的音声去刺激人的欲望,让人执著于音乐的外在形式,进而丢失了本心本性,耽溺于纵情享乐,琴乐以“静”、“和”的特殊美感,使人调整身心,修德养情,净化人心。由此可见,“琴者禁也”的特征,自汉代开始已然成为琴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不断被诠释发展,“禁”的内容也不断被深化发展,从禁止不平和的“烦手淫声”,到禁止琴乐的“慆堙心耳”,古琴的音乐以其特有的美感形式,成为士大夫阶层的雅器,呈现出士阶层对“希声”“虚境”的超越性追求。有如晋殷仲堪《琴赞》云:“五音不彰,孰表大音。至人善寄,畅以雅琴。声由动发,趣以虚乘。”[22]1392沈括《梦溪笔谈》提出“艺不在声,其意韵箫然,得于声外”[23]918;苏璟的“鼓琴者心超物外”[24]787;陈世骥所言“琴与书参,音与意参”[25]等等,都体现了这种艺术观。古琴音乐清微淡远,平和高远,以简淡而寡味的音声,于含蓄虚音处寻求况味,于无音停顿处寻求无限,以“虚实相生”表现,获得大音希声彻明。琴乐之“雅”也与俗乐之“俗”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筝、琵琶、三弦、胡琴、月琴之类,声调纤巧呖呖,嘈嘈切切,如莺语恰啼,珠落玉盘,俗耳听之,甚乐人心,陶醉于声色的美感体验,但与琴瑟、钟鼓这类雅乐之器比较,其雅俗之高低拙劣自现,如同明代戚继光的感受:“俗调,犹如嚥肉食饴,雅调,则如嚼玄嗽苦,滋味深长,万听不厌。”[26]257因此,文士阶层常常认为“弹琴不清,不如弹筝”[27]81,无所欲求,无所挂搭的清净与旷达,是大雅之本源,若雅音翻作俗调,以音色之美为目的,则流为肤浅,失雅鄙俗,有违琴乐的美感特征,必须摒弃。
由上述可以看到,中国文人将古琴视为“大雅之音”,“古人之于诗则曰‘风’、‘雅’,于琴则曰‘大雅’”[27]84,作为文人寄意的搭挂,弹琴听乐是以“器—乐—艺—境—道”为整体性结构的,凝聚着先贤圣哲格物致思的探求,也是其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在琴乐的审美性活动展开过程中,指法手势与音色表现既是弹琴的基础,又是最浅层的追求,不能一味追求乐音华丽的技巧繁复,过度张扬吟猱绰注、轻重缓急音色表现,造成“烦于淫声,滔堙心耳,乃忘和平,君子弗听也”[28]2025,这是弹琴所忌,也是有违大雅之音的俗法,因此徐青山在《溪山琴况》专门指出:“喜工柔媚则俗,落指重浊则俗,性好炎闹则俗,指拘局促则俗,取音粗厉则俗,入弦仓卒则俗,指法不式则俗,气质浮躁则俗,种种俗态未易枚举,但能体认得‘静’、‘远’、‘淡’、‘逸’四字,有正始风,斯俗情悉去,臻于大雅矣。”[27]84弹琴更强调声音之外的美感,以跌宕旷达,简淡平和的形式,直接作用于人心,获得“音中之意”、“弦外之音”,即“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而和乃得也。”[29]611。合于天地万物,则必须修养自己的身心道德,节制自己的过度欲望,做到自律坦荡,谨慎不苟,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其要只在慎独”[29]611,如此,才能祛除外物的蒙蔽,通达纯一的本然状态,获得超越性的美感体验,“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28]2025由此,从根本上看,古琴之雅源于自然、合于中道,通过可感可闻的音响,传达不可穷尽的意蕴,弹琴的过程,即是去掉欲望的过程,于安详陈静中获得自由,这种艺术精神与老庄哲学“主体虚静,玄览万物”的思想是想通的,于动中求静,实处求虚,于无欲处达至真如,于念中去除虚妄遮蔽,非清心不能尽古琴之美,非黜欲不能赏琴音之妙,在“空”与“静”中,体悟超越性之美感,诚如老子所言:“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复观”,在主体虚静、无挂无碍的状态中,空纳万境,以音制静,以实求虚,从而去欲绝俗,趋向雅流,最终契入自性的澄明。因此,文人雅士才将琴视为大雅之器,认为八音之中,琴德最优。
作为禁止欲望的雅器,“静”也是古琴最具代表性的审美特征。与“静”相关涉的一系列美学范畴为“清”、“淡”、“虚”、“远”、“自然”等,旨在追求恬逸、闲适、虚静、深静和幽远的意境。自《老子》提出“大音希声”后,“夫物芸芸,归根曰静”的观念以有声之乐为参照,充分肯定了“深静”之乐永恒之美,这一观念历来备受文人推崇,也深远影响着历代的古琴理论。大多琴学论著都将“深静”、“希声”作为琴音追求的至境,如嵇康的《琴赞》言:“昔在黄农,神物以臻,穆穆重华,五弦始兴,闲邪纳正,感物悟灵,宣和养气,介乃遐龄。惟彼雅器,载璞灵山;体具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温乎其仁,玉润外鲜。”[30]327-328琴乐的境界是“无尽”、“无限”、“深微”、“不竭”,“音至于远,境入希夷”,这种境界恰恰与“俗乐”的“繁声促调”相对立,琴音“体具德真,清和自然”、“温乎其仁,玉润外鲜”,单纯枯淡,乐而不过,哀而不伤,低声吟诵,无人无我,大音稀声,以清远古淡为美的特质。要做到琴音之静,必须涵养心中之静,心迹宁静,抚琴运指,发声取音,不暴不躁,才能清澈静谧,诚如徐上瀛《溪山琴况》所言:“盖静由中出,声自心生,苟心有杂扰,手指物挠,以之抚琴,安能得静?惟涵养之士,淡泊宁静,心无尘翳,指有余闲,与论希声之理,悠然可得矣。”[27]81音与心,手与意,是合一而不二的,在心体上去欲绝尘,归于宁静,归于淡泊,归于清朗,归于纯善,才能宁静至雅。诚如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所说:“‘静’的艺术作用,是把人所浮扬起来的感情,使其沉静,安静下去,这才能感发人之善心。但静的艺术性,也只有在人生修养中,得出了人欲去而天理天机活泼的时候,才能加以领受。”[31]22以“静”为美,也就是要以最少的声音物质来表现最丰富的精神内涵,以琴音之和、静、正、古,达到绝去尘嚣、遗世独立的大雅之境,从而以器入道,以技修身,所谓“自古圣帝明王,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然则,琴之妙道,岂小技也哉。而以艺视琴道者,则非矣。”[32]378这也是中国艺术精神,最高的价值求索。
四、曲论中的去欲归雅论:淫艳亵狎,不堪入耳
与画论和琴论略有不同的是,“雅”与“俗”的关系在戏曲艺术中表现得更为复杂。中国古典戏曲正式形成于宋元时期。由于最早来源于民间,其创作主体也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因此戏曲在本质上属于民间艺术的范畴,具有本色俚俗的审美风格。但是随着戏曲的不断发展,戏曲逐渐进入知识精英的视野,文人雅士、儒生士大夫主动参与到戏曲的创作与演出中,他们必然会按照文人阶层的审美情趣来“雅化”戏曲,即“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33]173。有异于民间艺人的“以曲娱人”,文人制曲的目的是“以曲言志”,或“以曲自娱”,因而他们摒弃民间戏曲本色粗鄙的表达,更不屑民间戏曲将声色欲望作为戏谑的桥段,大肆渲染,从而以此迎合大众的趣味。因此,文人的曲论中常常关注戏曲展现的滔滔文略,琢磨声律辞藻,激赏刻意求工的“雅化”之作,而鄙薄不加修饰“人欲”展现与“本色”表演。如明代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云:“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白兔》、《破窑》、《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耶?”[34]151民间戏曲的表演,往往以一个故事为主线,以俚俗的插科打诨来吸引观众,并将歌词与杂耍等技艺贯穿起来,呈现出取笑与逗乐的游戏品性,具有明显的粗俗性——即所谓“语多鄙下”、“里俗妄作”[35]239,因而遭到文人的鄙薄与不屑。
明代中叶,戏曲创作及其表演活动空前繁荣,戏曲理论批评亦获得长足发展,文人将曲作雅俗的标准,广泛运用于戏曲批评中。李开先《市井艳词序》批评【山坡羊】、【锁南枝】:“二词哗于市井,虽见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李开先认为【山坡羊】、【锁南枝】之类的曲子,有如郑卫之音,直白地表演男女之情,内容过于淫艳亵狎,是流行于市井的俗曲,何奈“市井闻之响应,真一未断俗缘”,因此“二词颇坏人心,无之则无以考见俗尚”[36]408-409,这两首词,情爱之欲,出于其间,有违传统儒家的雅正之风,不仅坏风俗,也坏人心,但出于考风俗的目的,李开先才为其作序。明清曲家尽管对民间戏曲抱持不同态度,但是对“淫艳亵狎”的粗鄙表演,大多持批评的态度。例如朱之蕃《北宫词纪小引》批评当时的曲作:“大都音节既乖,鄙俚复甚。”[37]113虎耘山人的《蓝桥玉杵记凡例》说:“科诨似详,演者慎勿牵强增入,以伤大雅。”[37]117槃薖硕人《刻西厢记定本凡例》评关本《西厢记》:“其曲多鄙陋秽芜,不整不韵。”[38]61许道承《〈缀白裘〉十一集序》评弋阳梆子鞅腔:“事不必皆有徵,人不必尽可考,有时以鄙俚之俗情,入当场之科白,一上氍毹,即堪捧腹。”[37]505实际上,戏曲作为一种通俗艺术,本来就有日常世俗的一面,必须面向观众进行表演,不得不掺入大众熟悉的方言俚语,“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故吾谓: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34]160。曲论家似乎也到这一点,认为戏曲的创作,应从当行本色入手,做到雅俗兼容,用典雅之语而不至于矫饰,用本色口语也不至于粗俗,诚如冯梦龙《太霞新奏》云:“词家有当行、本色二种。当行者,组织藻绘而不涉于诗赋;本色者,常谈口语而不涉于粗俗。”[38]129冯梦龙提出当行与本色的两种风格,也提出戏曲本色“俗”,是一种质朴的风格,而不是粗野庸俗,赤裸裸地展现人欲。
然而在戏曲艺术中,本色之俗与淫靡之俗,必须分而论之,前者运用恰当,可增戏剧之趣,后者则是低级的旨趣,曲家向来鄙夷的恶俗。因此,如何化本色为典雅,也成为曲家时常论及的问题。如王骥德《曲律》云:“故作曲者须先认其路头,然后可徐议工拙。至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34]122王骥德认为,戏曲具有通俗朴质之性格,这种通俗之“俗”是中性的,介于“文雅”之藻饰与本色之“俚腐”之间,片面堆砌文采则会使语言晦涩难懂,一味本色质直则会走向粗率鄙俚的方向,过施文采和过求本色都有弊病,戏曲之本色,在于二者之间,必须拿捏有度,做到俗而不俚、文而不晦。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也从“雅”的角度,品评郑光祖《倩女离魂》之《越调·圣药王》曲词:“‘近蓼花,缆钓槎,有折蒲衰草绿蒹葭。过水洼,傍浅沙,遥望见烟笼寒水月笼沙,我只见茅舍两三家。’清丽流便,语入本色,然殊不浓郁,宜不谐于俗耳也。”[39]456这种词语,哀而不伤,乐而不淫,适度的表达了情感,遣词造句,文质恰当,无虚浮的文辞雕琢,也无俚俗的宣泄直白,因而有清丽流便雅正之风,而无一点迎合俗耳的低下之气,才是戏曲应该追求的美感与意境。
能从日常世俗的语句中,点铁成金,化俗为雅,既无质胜于文的肤浅,又无文胜于质的雕琢,这是曲家最赞赏的雅化之道。如徐渭评《琵琶记》中《十八答》套曲:“句句是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35]243。又评《西厢记》中《佛殿奇逢》套曲:“大好大妙,可谓到八九分矣。中有俚语太凿凿、大发露者,是亦小疵”[38]40。屠隆的《昙花记凡例》声言自己对《昙花记》的校勘:“虽尚大雅,并取通俗谐□□,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37]103张凤翼的《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序》评《新刊合并董解元西厢记》:“雅俗兼收,则援古证今之姝肆也;情兴逸宕,则破拘摘挛之斤也。”[38]58李渔《闲情偶寄》也详细探讨了曲文雅与俗的关系:“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尘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不见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40]22。所以,戏曲语言与诗、词、歌、赋等文学词采不同,它是一种相对纯粹的特殊的口语化语言,须要适应戏剧本质——舞台性与表演性,直接面向观众演绎,个性化地展现人物性格,依角色而定其语。比如花面,则以粗俗之语入之,而生、旦则宜用雅语,其曰:“如在花面口中,则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其词。无论生为衣冠、仕宦,旦为小姐、夫人,出言吐词,当有隽雅春容之度;即使生为仆从,旦作梅香,亦须择言而发,不与净、丑同声。”[40]26《幽闺记》中,陀满兴福本为经历由屈而伸小生角色,在《避兵》中却曰:“遥观巡捕卒,都是棒和枪”,口吻直率粗俗,为花面语气,与生角身份不相符。“语求肖似”篇中,李渔感慨自己“无一刻舒眉”的落魄人生,欣慰自己可以借戏曲舒愠郁之情,并深刻揭示了戏曲代人立言的本体特点,又进一步强调了戏曲“说一人肖一人”的语言要求:“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籛之上。”[40]54不同人物的身份、阶层、性格、气质,在语言表达上均有较大的差别,剧中人物的语言必须有益于表现人物独特的个性。故而“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要将自己化作舞台人物,想人物之想,言人物之言,自然而然地又合符情理地将人物的语言特征表现出来。从人物语气必须符合人物身份的角度来看,戏曲难免有市井之语,粗鲁之词,站在舞台表演的真实性效果,文人不但对肖似人物之粗鲁语言风格加以肯定,而且认为这类语言具有极强的舞台性,这种浅易朴质的通俗之“俗”,呈现出表演的戏剧性、真实性与趣味性,正是戏曲艺术的魅力所在。文人鄙薄之“俗”,乃是从道德层面出发,否定戏曲之媚俗、低俗与庸俗,以大尺度的手段表现人欲之俗,以此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刺激观众的感官欲望,以至于“淫艳亵狎,不堪入耳”,损害道德,蛊惑人心,因而不得不遭到曲论的贬抑与批评。与此相对的戏曲之“雅”,即是通过平易通俗、质朴率真、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丰富大众的娱乐生活,在通俗之中承载道德教化以及审美功能,从而担负起“以雅归正”的诉求,这也构成传统曲论的理论旨趣。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戏曲的雅俗之辩,比画论和琴论有着更为复杂的意涵。在曲论中,“俗”的内涵必须加以严格区分,因为俗既有“语求肖似”之俚俗与粗俗的“本色”指义,又有“淫靡”的内容。曲家对于“本色”之俗,大多保持褒义,认为这种俗具有极强的趣味性,如果能化俗为雅,便可称为佳篇丽作。但是带有粗鄙淫靡的欲望之“俗”,文人通常鄙夷不屑,诸如民间戏曲的里俗妄作,诲淫浅俗,宣泄放纵,轻浮粗俗,是恶俗低级之趣味,与高雅精神文化相违背的,始终是士阶层所不齿之“俗”。
五、结 语
雅俗之辩,从表面上看,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但实质为两种不同的艺术精神,精英阶层总是寄寓精神的挂搭于艺术作品之中,以图以艺术的手段表达超越的精神,因此无论何种形式,或文或质、或绮或朴、或藻或简、或丽或白,均是形式上的选择,最终寄寓的是“诗以言志”、“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书以如情”,以艺求索精神的“雅”,即是根本的大雅;欲望之张扬、情趣之低级的恶俗,是有违天道自然的大俗,“欲”即是“俗”的本质。换言之,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清雅韵致并非存在于外在的形式,而是取决于内在的心态,去俗从雅即是去“欲”的艺术追求,实质上是文人阶层所持之理想价值,修德讲学,修身养性是其进退出处的根本,超越于现实的人生和世俗世界,步入人性本体的澄明与自由之中,此时无论美与丑、文与质的形式之间便可破畦执而求会通,均能达到“雅”的精神性存在。诚如叶朗所说:“一个自然物,一件艺术作品,只要有生意,只要它充分表现了宇宙一气运化的生命力,那么丑的东西也可以得到人们的欣赏和喜爱,丑也可以成为美,甚至越丑越美。”[41]126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根植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理论家在儒道观念的影响下,去欲俗从而“以雅归正”,在更高层面上将艺术引入“道”的思想内涵与表演精神,从而匡正着艺术的发展路径,避免其越来越走向纯粹讲求娱乐享受的只追求感官刺激、表现声色欲望的艺术形式,为其在理论上灌注了深邃的思想与内涵,最终形成最具中国写意特征与美感特征的艺术表现方法。
[1] 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李贽.初潭集·夫妇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颜延之.庭诰文[M]//李佳选注.颜延之诗文选注.合肥:黄山书社,2012.
[4] 嵇康.答难养生论[M]//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6] 薛蕙.老子集解(第十二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郭庆藩.庄子集释·庚桑楚[M].北京:中华书局,1961.
[8] 荆浩.笔法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9]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M]//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宗白华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10] 谢赫.古画品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
[11] 铃木大拙.禅和日本文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2] 李日华.紫桃轩杂缀[M]//彭莱.古代画论,上海:上海书店,2009.
[13] 沈宗骞.芥舟学画编·避俗[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14] 恽格.南田画跋[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15] 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16] 董欣宾,郑奇.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7] 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8] 桓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9] 班固,等撰,王云五注.白虎通(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0] 薛易简.琴诀[M]//蔡仲德注译.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21]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八十五)[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2] 严可均.全晋文(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3] 沈括.梦溪笔谈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24]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25] 陈世骥.琴学初津·制曲要篇[M].清光绪二十年抄本.
[26] 戚继光.愚愚稿(上大学经解)[M]//戚继光著.止止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27] 徐青山.溪山琴况[M]//琴曲集成(第十四册琴学正声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28] 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元年[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29] 王善.治心斋琴学练要[M]//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0.
[30] 嵇康.琴赞[M]//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1]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2] 徐祺.五知斋琴谱[M]//琴曲集成(第十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33] 虞集.中原音韵·序[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4] 王骥德.曲律[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5] 徐渭.南词叙录[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6] 李开先.市井艳词后序[M]//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
[37] 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38] 秦学人,侯作卿.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辑[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39]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
[40] 李渔.闲情偶寄[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41]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J0
A
1671-511X(2016)04-0105-09
2016-03-11
2012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表演艺术理论研究”(12YSC014)、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建构与文化创新研究”(2015ZSTD008)阶段性成果。
张婷婷(1979—),女,贵州贵阳人,文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