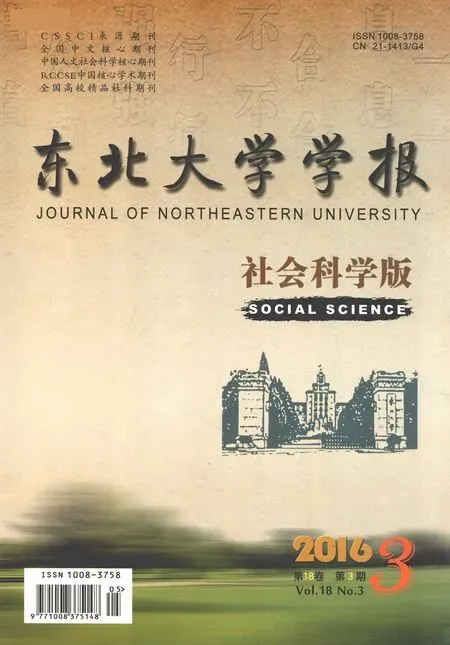第四世界建构与政治伦理书写
——《死者年鉴》中的帝国逆写策略
2016-03-07赵丽
赵 丽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2)
第四世界建构与政治伦理书写
——《死者年鉴》中的帝国逆写策略
赵丽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100872)
摘要:对美国社会的政治道德关注与批判,一直是西尔科的创作主题之一。在《死者年鉴》中,作者将美国政治话语书写的意图与特征归结为一种话语霸权模式。无论是国内的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的集体失语,亦或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下的外交策略,都折射出美国政治伦理书写所存在的问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构成西尔科建构第四世界的思考起点,她认为第四世界是消除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社会的不公正现象的理想图景,也是逆写帝国叙事的有效策略。擎举第四世界的理念,西尔科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在文本中建构一个阶级平等、各个种族趋于融合的政治空间。
关键词:莱斯利·马蒙·西尔科; 《死者年鉴》; 第四世界; 政治伦理; 融合观
美国土著女作家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的长篇小说《死者年鉴》(AlmanacoftheDead, 1991)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巨大争议。不少西方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文辞艰涩、结构复杂,批评小说中充斥过多的色情与暴力描写,认为这是西尔科在刻意丑化美国社会。然而,另一些评论家却为西尔科喝彩,认为该小说是当之无愧的杰作。美国土著评论家琳达·尼曼(Linda Niemann)就指出:“这是我读到过最精彩的一部小说,……它仿似一叶轻舟,载满故事与声音,上面还乘着许多人,这些人要在旧世界的废墟中重建一个新世界。”[1]尼曼这里提及的“旧世界”,可理解为现实中的美利坚合众国或整个美洲大陆,而“新世界”就是西尔科在小说中,以美国城市图森(Tuson)为中心而建构的第四世界。
《死者年鉴》的故事叙述横跨美洲大陆近500年的殖民历史,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作者有意将读者逐步引至对美国社会政治道德的叩问。在充分挖掘后殖民社会中民众殖民经验的基础上,西尔科不断反思美国政治话语的书写意图和特征,将对美国社会矛盾的思考指向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内在结构问题,并聚焦于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的集体生存状况,从而使伦理关怀和社会批判成为这部小说的基本向度。西尔科以建构第四世界为理念,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阶级平等、各种族趋近融合的政治空间,主动肩负起重新书写美国社会政治伦理的责任,最终实现逆写帝国叙事的意图*文中“逆写”一词的英文为“write back”,源自澳大利亚学者阿希克洛夫特等人所著的《帝国逆写》一书。就如何翻译“write back”,国内学者持有不同见解,其中,任一鸣将其译作“逆写”,而其他学者则将其译为“反击”或“回述”。但无论哪种译法,这一词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后殖民文学在书写过程中对历史或政治话语具有反思、反拨与重述的目的与特征。。
一、 第四世界与平等理念
《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即同一社会中的公民应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对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2]。然而反观当今美国社会,政治领域的不平等仍然存在,精英政治与等级政治依旧是美国政治话语的主色调。如何将平等与民主纳入美国政治伦理的书写范畴是西尔科在《死者年鉴》中致力探寻并力图解决的关键问题。
西尔科在创作《死者年鉴》之时,美国旷日持久的种族问题虽然得到缓和,但在美国政治领域,不平等现象却仍旧清晰可见,社会等级观念仍是实现政治平等的首要大敌。正如美国学者安东尼·豪尔(Anthony J. Hall)所说:“在全球历史进程中,西方世界的使命无疑等同于文明(世界)的使命。”[3]这句话折射出当下西方社会的现实政治状况: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俨然成为最基本的社会事实,它按照权利关系进行社会阶层划分,恪守社会等级制度,并使这种制度成为“构设‘优劣文化’的批评工具”[4]141。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涌现并逐渐演化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运动,以抵御主流社会对人类等级划分持有的绝对话语权。其中,目睹第三世界民权运动开展的美洲印第安人,也开始积极争取自身权利。1975年,第一次“土著民族世界大会”(World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在美国召开。“第四世界”(Fourth World)这个概念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用来指称第一世界中因经济、文化发展滞后而受压迫的群体。其实早在1974年,萨斯瓦普族首领乔治·曼纽尔(George Manuel)与迈克尔·波斯伦斯(Michael Posluns)在其合著的《第四世界:印第安人现状》(TheFourthWorld:anIndianReality)一书中,便提出了“第四世界”这个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美洲大陆上受压迫的全体少数族裔所处的生存状态与抗争状态[5]。无论是上述哪种界定,第四世界这一概念意在团结后殖民社会中被剥夺话语权的群体,共同打破阶级划分造成的欧洲中心主义,实现各民族政治地位平等的政治理想。这一理念贯穿《死者年鉴》整部小说,成为西尔科实现各个种族政治平等之夙愿的良方。
在小说中,西尔科首先将目光聚焦当下西方社会传统政治范畴中把人们分成不同等级与阶层的食物链式划分制度。作者描绘了诸多第三世界的民众,他们或是萨义德笔下的“东方民众”,或是斯皮瓦克书写的不能说话的“属下”,亦或是莫汉蒂塑造的第三世界的妇女,这些人无一不是受西方社会制度压制的食物链末端种群。作者无不讽刺地写道:
一些伟大的领导人与思想家都有着这样的顾虑。(他们)认为如果不适当保持种族基因平衡,那么人类将会灭亡。“领主享有奴隶新妇的初夜权”,一直以来其目的只为将贵族优秀的血统不断地注入到贱民的血液中,……而非他们的性欲过强,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天赋的”职责去改良那些混血与纯种印第安人的血统。[6]541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以肤色或经济状况为基准的阶层划分方式,使帝国主义势力与阶级压迫集结在一起,从而导致美国政府推崇的正义、平等与民主政策无法荫及第三世界的民众。小说中的印第安人斯特林便是这一典型代表。斯特林将白人社会当成了“救命稻草”[6]35,但当他被部族驱逐后,却不能真正地融入白人社会。斯特林成了两种不同文化与社会间的“夹缝人”(in-between)。在白人社会等级森严的阶级划分中,他只能游走于社会边缘地带,生活贫穷困苦,并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虽然他自我抚慰,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6]762,但这种“噩梦”却真实地折射出美国政治伦理书写存在的问题。
根据《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inAmerica)一书,民主政治被视为政治伦理中“无限完美的理念”。此书也赋予了平等以极高的地位,认为“平等”会给予人类以新的特质,“使人性得以提升”[7]。但西尔科在《死者年鉴》中却重新阐释了美国的“政治平等”。小说中的资本家与政治家们为确保他们的财富与地位,不惜剥削贫苦民众的财产与谋害他们的生命。例如,博费雷通过绑架孩童和流浪的瘾君子们积累财富;特里格以盗取社会底层民众的器官谋取暴利。这些角色形象地描绘出小说中西方政治的实质——恶毒与道德沦丧成为权势与地位的先决条件,平等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妄。通过小说中不同人物的遭遇,作者凸现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假象。这种依附等级而存在的人权思想与平等理念,不过是帝国主义使其霸权支配地位永久化的又一掩饰。
在批判这种社会等级架构的差异性时,西尔科并未将由此衍生的矛盾直接简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小说中也存在着邪恶势力与剥削阶级,但小说中更有一众像埃尔·费奥与莱卡、泽塔一样,虽为富人,却是抗争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在此,经济地位已无法有效区分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的身份及其在政治斗争中的立场,小说中呈现出的斗争也已不能再用简单的阶级冲突来限定。可见,《死者年鉴》中的美国社会已不再是阶级社会,在这一点上,西尔科似乎与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克劳、墨菲达成了共识:现代社会“不存在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8]。
西尔科笔下的第四世界建构,是基于她对重组美国社会阶层划分以获取平等权利的期待。在作者看来,平等是在社会不断进步中获得,而非构建在某种社会契约之上。第四世界的实现无疑加强了政治话语书写的道德性,使社会不断向着至善的方向前进。在第四世界中,不同种族与阶级的人,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以身份概念取代阶级概念,他们由于政治认同而集结在一起,从而使第四世界表现为,多种群和多文化之间的共同协商。同时,第四世界也将种族关系从阶级对立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将土著民族的抗争模式认定为没有阶级之分,其主旨即在消除美国社会中二元对立的格局。
不可否认,西尔科的第四世界建构是一种逆写帝国话语的叙事策略,是相左于第一世界的话语模式。作者可谓在后殖民文化中进行了一次最具革命性的实验,是对美国社会阶层划分的一次彻底重组。它不仅逆转了阶层秩序,更加质疑了该秩序所基于的政治伦理学假设,而这次重组的最终意图是要实现西方社会缺失已久的社会正义。
二、 第四世界与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是政治平等理念的实现基础,指在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分配责任与利益。这一观点来自于美国思想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他视正义为“社会制度中的第一美德”[9],而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则是构建正义的社会秩序。然而,一系列战争的爆发,尤其是“二战”与“冷战”相继到来,导致无论政府职能部门或社会权贵人士都各怀鬼胎,企图利用战争将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正义与平等只不过是他们各自为政的幌子,正义的社会秩序之实现更是遥遥无期。如果说,作为一名印第安人,西尔科期望的正义是土著人民享有平等的权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的美国民众,她更希望美国政府可以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
《死者年鉴》出版之际恰逢美苏两大阵营之间长达40余年的“冷战”告一段落,但这部小说在创作时却正值“冷战”的第二阶段。此时的“冷战”文化已深入美国社会,它不光加剧了美国政府的焦虑与偏执,也导致美国民众深陷由此产生的恐怖幻象。在《死者年鉴》中,作者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实施地缘战略而产生的社会动荡、民众不安,以及最终影响到社会正义的实现,描写得淋漓尽致。
然而,这并非是她的初衷。在一次访谈中,西尔科坦言,她最初只想写一部“关于商业、比较简单的短篇小说”[10]154。不可思议的是,一次梦境却改变了原初计划。在谈及这个梦时,她说道:
这是一个十分真实而可怕的梦。我家所在的阿布拉峡谷有许多小的基地,……图森的空军基地就在那里。我不敢想象使我最终动笔的灵感来自于那里,这简直就是种折磨。……在一天早上醒来之前,我做了这个梦。……在梦中,我看到这些飞机飞得十分低。这个梦让我感觉到,……某一天会有战争发生。[10]101
无论西尔科的噩梦是否会成为现实,都折射出处于“冷战”时期普通民众的焦虑心理,“冷战”情绪造成的民众恐慌也已积重难返。较之40年代末开始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这一轮“冷战”导致的冲突则更为危险、局面更为难以控制,大规模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如更加严峻的种族问题、愈演愈烈的道德沦丧,都无疑加速了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以及偏执政治文化的复苏。
在偏执政治思想的主导下,里根政府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所谓的“促进民主运动”(Democracy Promotion Campaigns)[11],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巩固在“一战”“二战”中美国取得的经济与政治的优势地位,欲将更多地区划入反共阵营中,并以此使美国推行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洪多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等等。然而,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中,民主运动的推进并未使社会正义得以实现,反而导致美国政府过于偏执地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强行划出界线,不遗余力地去除任何夹杂在“我们”中间的“他们”,使潜藏在地缘政治下的种族主义思想暴露无遗。地缘政治也因此成为种族主义的延续,是霸权思想的理论变形。
这种“冷战”背景下的地缘政治战略在《死者年鉴》中被刻画到极致。这部小说的人物角色颇多,随之而来的故事线索也颇为繁杂,但西尔科却将情节与人物命运的发展与如下两个地方密切关联:美国城市图森与墨西哥城市图斯特拉-古铁雷斯。其中,图森是边疆要塞,美国政府以此为据点,密谋实施所有反共的地缘政治活动,并将其打造成为一座“冷战”时期美国军事与情报行动的中心基地。一方面,政府秘密操控伊朗反政府组织,暗地与神秘的B先生及军火商格林利勾结,加强反共势力;另一方面,政府怂恿马克斯·布卢一干人等进行政治暗杀,密谋扩大其地缘政治的影响。这种阴谋政治最终导致图森集结了所有的恐怖势力与非法行径,城市四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使生活于此的居民时刻都处于恐慌之中。在墨西哥方面,图斯特拉-古铁雷斯则成了图森在第三世界中的一个缩影。这里的政治精英们一致接受美国“冷战”时期的化约论,将不同场域的内在逻辑统一化约为二元对立关系,反对各个阶层的政治、文化自主性,将一切可能挑战他们权威势力者,都认定是共产主义的颠覆分子。小说中,以一半印第安血统的资本家梅纳多和美国前大使J上将等为代表的墨西哥精英阶层,寄期于在政治与经济上与美国政府达成依附关系。他们相信,只要在全球共同反共的战役中取得胜利,他们便可实现对第三世界民众的霸权统治。
不得不承认,西尔科笔下的这种美国社会偏执狂的心态与阴谋论的思想,俨然已成为极权主义的一对共生体,其邪恶的形象潜伏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黑暗角落,政治道德危机与民众思想恐慌已成当下美国社会秩序的主色调。西尔科在创作《死者年鉴》时便已意识到这种地缘政治带来的后果:
……美国政府生产可卡因,因为他们要供给尼加拉瓜反抗军来对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也成为了一个美国政府想要极力地掩盖的大丑闻。[10]154
这种政府的非正义行为揭露了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贪婪的政治本性。所以,当西尔科开始提笔时,她“便意识到这部小说不会那么简单,也意识到这部小说将会写些什么”[10]154。
小说伊始处的一句“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战争从未停止过”[6]16,坚定地表明西尔科的这部小说意在颠覆地缘政治与民族身份的“冷战”范式。在“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模式下,作者以一种全球化的视角,将不同种族与不同民族联合,来共同抵抗“冷战”时期美国社会中的偏执文化现象。为了达到正义的目的,西尔科在小说中筹划了一次革命。她以图森为中心,将原本已被美国政府圈定为反共联盟战线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转变成为第四世界共同抗争的联盟。
同时,西尔科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了这次革命斗争之中。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安吉丽塔这样一个人物角色。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她不仅熟知马克思思想,也深谙其中的政治力量。她同马克思一样谴责资本主义那种“盗窃”“掠夺”“抢劫”的占有规律,并且希望通过斗争获取平等的政治权利,最终达成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正义性。在安吉丽塔眼中,只有“马克思了解部落人们的思想”[6]520,因为他把维护正义的社会秩序视为合理的社会标准。安吉丽塔在第四世界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鼓励第四世界民众反抗种族殖民压迫。她将她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汇集成了另一部“年鉴”,上面记载着从古到今土著民族一系列的起义和抗争。安吉丽塔认为,“马克思明白……,在历史中蓄藏着寻求着正义的那些无眠无休的力量”[6]316。为此,她建立了“正义与资源重分军”(Army of Justice and Redistribution),希望发动更多第四世界民众加入印第安人的反抗运动之中。
除了安吉丽塔及土著双胞胎兄弟塔科与埃尔·费奥这样的抗争领导者外,西尔科还塑造了一系列其他人物角色,来共同抵制“冷战”下的美国意识形态与政治压迫。如亚裔黑客阿瓦·吉帮助泽塔和其他一些革命份子攻击美国的电网系统;残疾退军人黑裔土著人克林顿创办了一个电台广播节目,为反抗造势;退役军人蓝博·雷在图森的周边秘密招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与退伍老兵,成立了“流浪者之军”。
这些原本属于边缘群体的第三世界民众,在西尔科的笔下成为反抗第一世界、瓦解地缘政治阴谋、寻求社会正义的第四世界斗士。此时的西尔科已意识到文化身份的重构必须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吸纳全球化下各种优秀的理念与观点。她的小说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逾越了种族、民族、性别、阶级的鸿沟,为不同社会文化现象之间创造联系。
三、 融合观的初现与政治伦理理想
一如上文所述,西尔科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冷战”格局下美国政府的政治阴谋,其最终目的是要书写以正义、平等、民主的融合观为主线的政治伦理。不难看出,《死者年鉴》中描写的世界,已逾越殖民者与受殖者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此时作者不再拘泥于将这部后殖民小说打造成一部表述土著民族身份的重要意象来源,她希望将小说中的世界变为一个第四世界的“地球村”(global community)[12]48。这里可以包容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也可以体现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同特征。正如西尔科曾经说道,这个世界上的族群“没有什么可以只是黑色,或棕色,或白色”[6]747。
因此,西尔科笔下的西半球已成一个整体,在这里没有国家、民族等政治界线的存在。作者将不同种族、不同类别的人聚集在小说的中心地点——图森。他们有非裔美国人、古巴人、危地马拉人、海地黑种印第安人、因纽特人、拉古纳人与墨西哥人等等。这些人的身份更是种类杂多,从黑手党到退役军人,再到流浪者;从企业家到毒枭,再到脱衣舞娘,等等。他们“如同杰弗里·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前往坎特伯雷大教堂去朝拜圣托马斯·贝克特圣像的人们一样”[12]48-49,最终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第四世界,不再是帝国话语延续表达的第四世界。
在破解年鉴的过程中,西尔科刻意将塞斯设定为关键角色,她也是小说中唯一一位被拯救的白人女性。印在《死者年鉴》封底上的《纽约时报》书评这样评价塞斯:“处于《死者年鉴》核心地位的是塞斯”。塞斯之所以居于整部小说的核心地位,缘于她是西尔科的融合观的见证者。塞斯还是一个幸运儿,她的幸运不仅表现为摆脱了皮条客蒂尼与毒枭博费雷,最为关键之处是通过融合观,她成功地寻得新的人生目标与真谛。在抄录与翻译年鉴的过程中,塞斯将自己经历的痛苦与不幸融入这部记录着印第安人点滴的史书中,从而使这部年鉴也成为了一部记述白人遭遇的融合的典籍。可见,作者笔下的这种联盟不仅仅是跨文化、跨宗教的联合,还包括着持有不同政治目的的人共同合作,以对抗美洲大陆上的不公正。
在西尔科看来,第四世界的构建并不是将尘封许久的土著文化习俗强加到当下的美国社会中,而是重新挖掘并革新土著文化中的优势与精神信仰。作者在小说中充分地表现出土著文化的宽容性与忍让性,她渴望用一种语言描绘文化多元性的全球交集,以土著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特质来化解全球冲突。
在小说中,西尔科将融合的土著民族性扩展到“西半球甚至是全球的范畴上”[13];但作者对于“泛部族”(pan-tribal)融合的提倡,却触动了一些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与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敏感神经。对西尔科这种跨文化的融合,土著学者保拉·古娜·艾伦(Paula Gunn Allen)的批评很是尖锐,她认为西尔科创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一个作家企求(被主流文学)接受”[14]。民族主义者库克琳(Cook-Lynn)认为西尔科与其他一些当代土著作家一样,虽在文坛获得了成绩,但却“为了获取主流读者的兴趣,而远离民族关切”。她在评价《死者年鉴》时,认为小说并没有有效地维护部族的主权[15]。这些评论家认为,西尔科小说强调的跨文化政治与精神融合并不会加强美国印第安部落的主权诉求,只不过是作者受到其成长环境的影响,将事物憧憬得过于美好而已。
不可否认,西尔科笔下的第四世界构想,是在社会现实性与历史进步性之间的张力中寻得发展动力,并不断向作者心中理想的融合观前进。作者认为,对融合观的批评是因其未能从印第安人的视角来思考。作为土著民族中的一员,西尔科与其他印第安人及他们的祖先一样,真挚地欢迎并接受新的居民与新的文化,他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刻意地筑起一道城墙、划出一道界线,因为他们的“人性……与灵魂不需要边界”[16]。正如阿希克洛夫特所言,“文化融合是所有后殖民社会最具价值与不可避免的特性,它恰恰是后殖民社会特殊的力量源泉”[4]26。当西尔科的融合观一再受到土著批评家的否定时,她并没有放弃,而是不断通过融合观寻求的普适性正义标准,使该主题在第三部小说《沙丘花园》中得到更加完美的诠释,成为西尔科界定土著身份话语的新坐标。自此,《死者年鉴》为作者融合观的确立正式拉开了帷幕。
《死者年鉴》延续了西尔科作品对土著民族身份建构一如既往的关切,但又不同于以往的作品,此刻的西尔科以第四世界为图景,更多地强调印第安文化与西方世界、其他文化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一种包容、大同的融合观。所以,第四世界无疑成为土著民族未来发展的一个走向,而这一未来正是构建在他们先辈的信仰、力量及价值观的基础上。除此之外,作者将目光移至美国政治话语书写的伦理向度,直指潜藏于西方历史进步话语之下的种族、政治与文化的问题。在西尔科的塑造下,第四世界俨然已成为帝国话语的有效“逆写”策略。虽然“第四世界”这个术语在后殖民文学批评中尚未被广泛使用,但其政治与理论涵义却十分耐人寻味。
参考文献:
[1] Linda N. New World Disorder[J]. 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1992,9(6):1-4.
[2] 德沃金. 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M]. 冯克利,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190.
[3] Hall A J.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Fourth World: The Bowl with One Spoon[M].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4]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著. 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M]. 任一鸣,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5] George M, Michael P. The Fourth World: An Indian Reality[M]. Cambridge: Collier-Macmillan Canada, 1974:40-42.
[6] Silko L M. Almanac of the Dead[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7] Alexis de T, Isaac K. Democracy in America[M]. Cambridge: Sever and Francis, 1862:514.
[8]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 尹树广,鉴长今,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95.
[9]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3.
[10] Arnold E L. Conversations with Leslie Marmon Silko[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0.
[11] Thomas C.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U.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the Reagan Year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238.
[12] Snodgrass M E. Leslie Marmon Silko: A Literary Companion[M]. Jefferson: McFarland, 2011.
[13] Sadowski-Smith C. Border Fictions: Globalization, Empire, and Writing at the Bounda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8:74.
[14] Allen P G. Special Problems in Teaching Leslie Marmon Silko’s Ceremony[J].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1990,14(4):379-386.
[15] Cook-Lynn E. Anti-Indianism in Modern America: A Voice from Tatekeya’s Earth[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80.
[16] 赵丽. 论诺斯替主义与西尔科的世界融合观——以《沙丘花园》为例[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6(2):215-220.
(责任编辑: 李新根)
Construction of the Fourth World and Writing of Political Ethics——The Write-back Tactics inAlmanacoftheDead
ZHAO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The concern and criticism about political ethics in American society have been the themes in Leslie Marmon Silko’s writings. In Almanac of the Dead, the inten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 writing are summarized as the hegemonic discourse by Silko. Both the collective aphasia of the minorities and vulnerable groups at home and the geopolitical diplomatic strategies abroad reflect the issues existing in American political ethics writings. How to solve these issues becomes the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Fourth World in Silko’s novels. In her opinion, the Fourth World is an ideal state to eliminate the problems of imparity and injustice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and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write back the imperial narrative. Based on the Fourth World concept, Silko’s ultimate goal is to construct a political space in her books where different nations enjoy an equal and syncretic relationship.
Key words:Leslie Marmon Silko; Almanac of the Dead; Fourth World; political ethics; syncretism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3.016
收稿日期:2015-11-08
作者简介:赵丽(1982- ),女,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6)03-03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