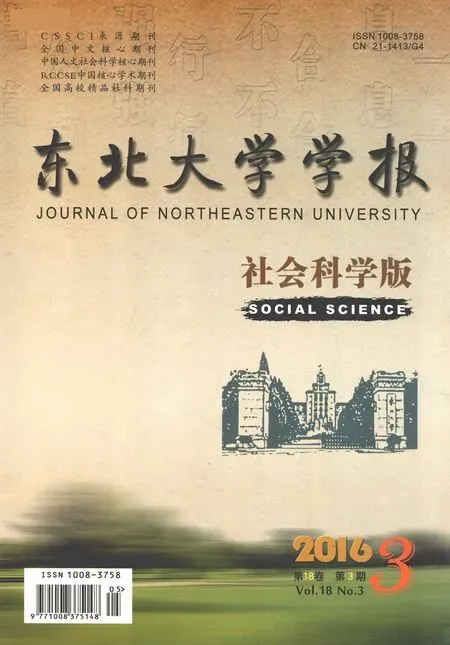国际康德科学哲学思想研究的定位、问题域及当代意义
2016-03-07代利刚安维复
代利刚, 安维复
(1.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2.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国际康德科学哲学思想研究的定位、问题域及当代意义
代利刚1, 安维复2
(1.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214122; 2.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200241)
摘要:康德科学哲学研究是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就合法性和地位而言,最新的科学哲学史研究复活了康德自然哲学并赋予其作为科学哲学的合法地位,使其成为科学哲学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就学术视野而言,康德科学哲学研究关注的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如科学和形而上学关系及更深层的方法论问题等。就当代价值而言,康德科学哲学对于当代学者探讨的科学实在论问题可以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为走出库恩和蒯因肇始的科学哲学研究的相对主义困境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进路。更为重要的是康德科学哲学可以为科学哲学本身提供新理解,为康德哲学研究和科学哲学研究开辟广阔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康德; 科学; 哲学; 实在论; 相对主义
2012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三批重大招标课题与2013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指南都将科学哲学史列为研究重点,2014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课题“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经典文献编目与研究”是对古希腊到现代科学哲学思想的文献整理,为进一步地研究科学哲学史奠定基础。以上说明国内学界已经意识到了科学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在国际学术界,从古希腊到现代的科学哲学史研究是正在兴起的思想工程。之所以要进行科学哲学史的研究,是因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特别是自然主义和科学社会学)面临难以解决的相对主义和实在论问题*参见代利刚:如何走出科学哲学研究的相对主义困境[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5):32-37。在文中,笔者详述了当今科学哲学研究面临的相对主义困境与弗里德曼的理性动力学的解题向度,而理性动力学是一种新康德主义科学哲学,继承了康德科学和哲学的平行论,这种平行论也是科学哲学史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进路(如在第一届“整合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大会上,Ernan McMullin评论Herbert Feigl的话语时指出“Feigl回到了康德主义的主题,……科学史没有科学哲学的参与是盲的,科学哲学没有科学史的参与是盲的”。因此,面临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困境,国际学界试图回到科学哲学史进行反思。,国际学界试图回到科学哲学史寻求反思和解题路径。不管我们对科学哲学史起点的态度如何,康德是承前启后的思想家并且对经典力学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反思,所以他的科学思想在科学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合法性与重要性: 作为科学哲学史重要环节的康德科学哲学
长期以来,康德关于科学的哲学思想一直被认为是不必过多关注的研究领域,之所以被遮蔽,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主流康德哲学研究认为康德的理论哲学是知识理论。其二,主流的科学哲学研究都以逻辑经验主义为科学哲学史的起点*持这一观点中最具代表性的有Sahotra Sarkar的The Emergence of Logical Empiricism: From 1900 to the Vienna Circle, 其他还有Wesley C. Salmon和Merrilee H. Salmon编辑的Logical Empiricism: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Ronald N. Giere和Alan W. Richardson编辑的Origins of Logical Rmpiricism等。,康德对于科学的反思自然也没有纳入其研究视域。
因此,对于科学哲学本身理解的单一及对康德思想的知识论解读导致了康德科学思想一直被遮蔽,但是,康德关于科学的哲学反思思想可以称之为科学哲学,论证如下:
第一,科学哲学含义本身需要重新理解,这为康德科学思想赋予科学哲学地位提供可能性。事实上,科学哲学本身的定义也具有多样性和流变性,当今科学哲学种类众多,可归结为四类: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哲学就是一种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包括受其影响的科学社会学)把科学哲学定义为探究科学实践活动本身的科学(包括实践的社会性);法兰克福学派把科学哲学理解为利用哲学理念对于科学技术社会影响的批判;自然主义则把科学哲学理解为科学家的心理活动。
以上四种对于“科学哲学”复合语词的理解,在对语词“科学”的理解上是一致的,但是对语词“哲学”的理解上有着明显的差异,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哲学”是逻辑分析,拒斥形而上学;历史主义和科学社会学认为“哲学”是科学实践的社会活动,含义极其庞杂;法兰克福学派等认为“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批判,背后的指向是一种非异化的存在理念;自然主义认为哲学是心理活动,拒斥形而上学。
以上四种对于科学哲学的理解在科学和哲学之间制造了一种割裂,导致无法全面地理解科学哲学本身,陷入理论困境。也就是说,形而上学是哲学的重要内容,科学哲学不能完全清除哲学的重要内容(形而上学),无论后现代的一些思想家如何拒斥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依然是人无法取消的思想倾向。“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联系非常紧密”[1],是“以世界本体为对象的、超越经验之上去追究世界的存在和本质的哲学”[2]。对作为一种普遍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消解和拒斥要么走向失去普遍性标准的相对主义,要么走向对于科学哲学的单一解读。
对此,我们可以展开阐明,首先,自然主义由于拒斥形而上学陷入相对主义困境,如Haldane在对自然主义评论时指出,“如果我们大脑中的原子运动完全决定了精神活动,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的信念是真的”[3]。其次,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哲学定义为逻辑分析,拒斥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只能对科学哲学进行单一的静态理解。再次,如果把科学哲学定义为形而上学或哲学对于科学的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会导致科学理论内核与哲学之间的疏离。最后,科学哲学可以关注科学实践活动本身(如历史主义和科学社会学),但是不能把形而上学和科学作为一个浑然体,无视二者的互动关系,会导致对于形而上学的简单或断裂式理解,从而使得科学实践共同体之间无法沟通,陷入相对主义,因此,“科学哲学的社会学化也由于其理论基础(库恩范式理论的‘不可比拟性’)的先天不足而走向相对主义”[4]。
因此,当今主流的科学哲学的定义忽视或割裂科学与哲学(或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其实,科学哲学就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想互动,科学哲学史就是科学与哲学观念共同体的融合形成、冲突、重建的观念史,科学哲学史研究应充分汲取宏大叙事与社会学分析的优缺点,以科学—哲学的观念史为纲领,通观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与文化等之间的思想关联及演化过程。
事实上,以上理念越来越得到当代国际学界的认同。John Losee、David Oldroyd、Edward Grant和Michael Dickson等科学哲学史研究专家的著作*主要包括: John Losee的《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David Oldroyd在1986年出版的《知识的拱门——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历史》(The Arch of Knowledge: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ce);新近的研究还有Edward Grant在2007年撰写的《从古代到19世纪的自然哲学史》(A History of Natural Philosoph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以及Mary Domski和Michael Dickson在2010年编辑出版的《关于方法的对话:重新激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整合》(Discourse on a New Method: Reinvigorating the Marriag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等。都把科学哲学的起点定位古希腊。更为重要的是,1996年4月19—21日,第一届国际科学哲学史大会(1st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在弗吉尼亚工学院举行,标志着科学哲学史研究的兴起。同年,《国际科学哲学史学会杂志》(TheJournaloftheInternationalSocietyfortheHistoryofPhilosophyofScience)正式创刊,从首刊文章中看出科学哲学史的研究已经覆盖了从古希腊到现代的科学哲学史研究*创刊内容包括以下文章: James G. Lennox的《亚里斯多德关于研究规范》(Aristotle on Norms of Inquiry)及Eric Schliesser的《牛顿对哲学的挑战》(Newton’s Challenge to Philosophy)等。。不但如此,2007年11月11日,作为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整合科学哲学史”研究大会(Integrated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在匹兹堡大学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召开,与会的人员都是当代科学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专家。该大会的主题是“关于科学史和哲学史整合的过去和将来”,以后几乎每隔一年召开一次。
第二,康德关于科学的哲学思考符合以上关于科学哲学的重新定义,赋予其科学哲学地位具有合法性。如果以笔者所在研究团队的研究理念及国际学界最近兴起的科学哲学史研究来看,康德关于科学的哲学因为是对当时牛顿力学、拉瓦锡化学和欧拉的数学等重要科学理论的推演和反思,所以称之为科学哲学具有合法性。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专门对“康德科学哲学”列出词条,以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进行了定义(这一定义也契合了笔者所在研究团队的学术理念):“(i)康德认为科学定律包含了一定的必然性,但是(ii)这个必然性不是基于宇宙万物之间普遍的关系,而是基于特定的主观的、先天形式的条件”*网址为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kant-science/。(本词条由研究康德科学哲学的专家Eric Watkins撰写)。康德科学哲学不但具有合法性,而且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Michela Massimi称赞道,“康德的批判哲学可能是科学和哲学之间长久结合的最高点”[5]。因此,他呼吁“科学哲学应当重新发现我们长久遗忘的康德认识论的灵魂”[5]。事实上,现代哲学已经普遍承认“《纯粹理性批判》是现代哲学的基石”,分析哲学也承认“《纯粹理性批判》是分析哲学的基础”,但是作为科学理论的《纯粹理性批判》在科学哲学的重要地位还没有确立*不仅如此,第一届国际科学哲学史大会的议题“科学的哲学:新康德主义与科学哲学的诞生”(Scientific Philosophy, Neo-Kantianism and the Rise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直接发源于康德思想的新康德主义与科学哲学有着紧密的关系,可见康德科学哲学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康德科学哲学会成为未来科学哲学史的重要研究领域。
总之,以上考证的命题论证逻辑是:科学哲学是科学和哲学之间的互动;康德科学思想是科学和哲学之间的互动,因此,康德科学哲学是科学哲学。一旦我们赋予其作为科学哲学的重要地位,康德思想作为科学哲学的研究会向主流科学哲学研究者敞开,当今国际学界对此的关注也正因为这一原因。
二、视野和文献:康德科学哲学的问题域
康德科学哲学研究关注的问题极其广泛,包括心理学哲学、地理哲学、生物哲学问题等,限于篇幅所限,下面重点介绍学界对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
1. 科学和形而上学关系问题
近些年的研究表明,科学和形而上学关系问题贯穿于康德思想发展的始终,是理解康德哲学的重要线索。前批判时期,康德的数学、自然科学思想和哲学观念交织在一起,很难厘清康德的致思线索,国内的康德研究更是直接把科学和哲学分开来研究,致使这一康德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一直被遮蔽。在此,Martin Schönfeld依据科学和哲学关系梳理出这一时期的发展线索:在1747—1763年,康德试图把牛顿力学、数学观点引入形而上学;但到了1763—1765年,康德思想陷入了矛盾,是继续把自然科学、数学引入形而上学,还是使二者割裂;在1765—1770年,把自然科学的领地和形而上学的领地分离——形成了划分两个世界(可感世界和理知世界)的思想。所以Schönfeld认为康德前批判时期致力于“协调了形而上学和牛顿力学的矛盾”[6]。
需要指出的是,Schönfeld所说的只是自然科学和数学所处的领地和形而上学的领地的分开,并不妨碍康德在方法论和核心理念上对自然科学核心理论的信任和推演。沉默时期,康德认识到休谟的怀疑论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破坏,所以试图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详情参见:弗雷德曼·库恩.康德传[M].黄添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233页。。批判时期,康德一方面试图用先天形式综合判断为自然科学和数学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直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推演出形而上学。具体而言:①康德根据牛顿万有引力理论论证方式(假说—证明模式)推演出先天形式范畴的假说—证明模式(先验演绎的证明方式);②根据对《作为科学的未来形而上学》《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的分析可知,康德从开普勒第三定律到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推导过程中,推演出知性的作用原理——数学原理和力学原理;③在晚年,康德一直在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拉瓦锡化学的发展使康德放弃了化学不能作为科学的观点,并且把拉瓦锡的热量学说中的“热量”范畴推演为充斥于整个世界的“以太运动力”,形成了新的世界理论——以太理论。甚至,Förster Eckart还认为,晚年的康德还关注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注意到了生物的应激性理论,并推演出自我设定理论。
2. 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康德“科学和形而上学关系问题”主要从广度上探讨科学如何推演出形而上学,那么“方法论问题”主要是从深度上对康德科学和哲学的具体关系进行反思。这是康德科学哲学的研究者争论最多的疑难问题,更是当代科学哲学可以向康德科学哲学借鉴和学习的根本问题。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纯粹理性批判》(KRV)、《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F)与牛顿物理学三者的关系问题。按照传统的解读方式(如Erich.Adickes和August.Stadler的观点),康德MF的任务只是把物质范畴置于KRV中先验的范畴和原理之下,以证明外在对象(具体自然科学)的确定性,所以,KRV的先天形式范畴和原理、MF的物质理论跟具体的自然科学之间只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然而,这种观点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并形成了三种对立的学说:“松散说”“范导对应说”和“修补说”。
Gerd Buchdahl认为康德KRV中的“科学的形而上学”与MF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间存在着一种“松散的对应”关系。知性范畴原理整合经验杂多形成特殊的物理学定律,产生的只是直觉杂多的统一性(具体在MF中完成),而“理性的范导性活动才能产生经验定律的统一性”[7]。形成具有统一性的物理学定律(主要在KRV和《判断力批判》中完成),也就是说,知性范畴和原理和理性范导性原理之间存在断裂,KRV和MF之间只是一种“松散的”对应关系。针对Buchdahl的“松散说”,Robert E. Butts认为“范导性”不仅存在于理性和经验定律之间,而且,在理性的统觉作用下,知性范畴和原理可以用范导性来统摄特殊的经验定律,所以“经验定律和先天形式原理(SC)之间具有不相似的形态,但是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亲和性,即范导性”[8]。因此,在Butts看来,先天形式范畴和原理也具有范导性来统摄MF的物质力学理论和物理学定律,理性、知性和具体的经验定律是紧密的对应关系。Friedman不同意以上两种观点,他提出了“补充说”。他认为,KRV的先天形式范畴和原理应用于具体科学(如牛顿力学)的先验演绎由于缺乏空间的图型而存在“漏洞”,物质力学理论作为空间的图型修补了漏洞,确保先天形式范畴和原理作用于具体经验科学。他指出,“纯粹知性的范畴和原理虽然本身不是数学的,但是需要在我们的纯粹直觉形式(时空)中得到实现”[9],而物质力学理论的“空间中可运动的物质”作为一种“空间图型”使范畴和原理在空间中取得实在性。
3. 物质理论
康德的物质理论即是自然科学问题,也是形而上学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主流的科学史研究很少关注,哲学史研究者也无人问津。然而,在国际学界越来越关注康德的科学哲学的情况下,这一理论由于是联结科学和哲学的中介,又是贯穿于康德哲学始终的范畴,所以便成为了康德科学哲学的核心范畴和理论,如Wolfgang Lefèvre 等编撰的康德自然哲学范畴谱系数据库*数据库的介绍:Wolfgang Lefèvre, Falk Wunderlich. The Concepts of Immanuel Kant’s Natural Philosophy(1747—1780)——A Database Rendering Their Explicit and Implicit Networks[M].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er, 2000。 数据库的网址:http:∥knb.mpiwg-berlin.mpg.de/kant/home。把物质力学范畴作为核心范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何谓物质理论?在近些年研究的基础上,Martin Carrier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康德的物质理论包括三重含义:力学论(Dynamist)、普满论(Penist)和连续论(Continualist)。力学论意思是力是比物质的广延性和不可渗透性更为基本的东西,是物质的最基本的属性;根据普满论者的观点,物质完全充满所处的空间,没有空的间隙;最后,以连续论者的立场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没有原子存在。”[10]
不仅如此,国际学界还从来源、形而上学意义和当代价值等方面对康德的物质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①康德的物质理论受到了牛顿力学和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思想的双重影响。一般认为康德物质理论完全等同于牛顿的三大定律,Eric Watkins通过对比物质理论的核心内容(MF中机械学三定律)和牛顿的三大定律,发现康德的物质理论并不是完全吸收牛顿的理论,而是做了一些修改,比如,康德增加了量的守恒定律等。修改的“原因是康德受到了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单子和物体的理论(康德超越了物体仅仅有单子组成的观点)”[11]。换言之,康德的物质理论不仅受到了牛顿力学的影响,也受到了形而上学传统的影响。②康德的物质理论是一个实在论,这种实在论的成立根据不在于我们可以认识的物自体的内在属性,而在于我们放入、具有交互属性和因果属性的力[12]。③康德的实在论是先验哲学的基础。康德《遗著》的以太演绎所证明的物质(以太)具有引力和斥力,并且是“从可能性推演出的实存”(拉丁语“a posse ad esse valet consequential”[13]),具有先天形式性,Jeffrey Edward据此反向解读康德从前批判时期到晚年的整个理论,其结论是,先验哲学不仅仅是先天形式理论,而且是先天形式质料理论,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形成知识的先天形式质料条件[14]。
以上三个问题在当代依然重要,科学和形而上学问题是科学哲学的永恒主题,科学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是科学哲学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物质问题演化为当代的物理主义,依然是当代的重要问题。因此,康德科学哲学的问题和解题方案在当代依然值得关注。
三、意义和价值:康德科学哲学与当代科学哲学的重大难题
以上研究的三个方面的核心要旨是理性和知性范畴(先验形式)与科学对象和理论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科学和形而上学关系问题处理的是科学理论如何推演出先验范畴;方法论问题探讨的是理性和知性与科学理论的构建关系;物质理论是理性和知性面对的科学世界的样态(物质形态)。思想史的意义在于对于当代问题的解释力,当代科学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是相对主义困境和实在论问题,对此,康德科学哲学都能给出教益。当然这种意义的探讨只是康德科学哲学意义的一部分,广阔和深远的意义还有待挖掘。
1. 当代科学哲学的相对主义困境
肇始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当代科学哲学经过蒯因整体论和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批判,逐步出现自然主义化和社会化等后现代思潮。两种思潮都逐步陷入了相对主义(第一部分已有论述)。如何应对相对主义危机?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绝对主义取代相对主义,以普遍观念迎回正统的科学哲学。正如贺来教授所言:“立足于绝对主义立场,必然导致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或此或彼’的外在对立, 并最终陷入‘用绝对主义取消相对主义’或‘用相对主义反叛绝对主义’的恶性循环。在此, 相对主义只是被绝对主义所消解和‘吞并’,而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有效的克服。”[15]事实上,根本的问题在于,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在事实判断(科学或知识)与价值判断(哲学或观念)等重大理性问题上已经陷入了偏向于一方的境地(如自然主义化拒斥形而上学)。进一步说,后现代主义不能容忍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科学(事实判断)与哲学(价值判断)关系上背离了康德等思想大师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忽视了二者的辩证关系*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一直主张从科学和哲学关系来反思后现代思潮。笔者吸收了课题组首席专家的这一思想。。
如果把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定位为科学和哲学关系的割裂,那么康德科学哲学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良药”。康德科学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在科学和哲学(形而上学)之间保持张力,这主要归功于康德的独特方法——追问科学事实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如何可能(先验方法),即数学如何可能?自然科学如何可能?对此,康德表示“只有关于这些表象根本不具有经验性的来源,以及何以它们还是能够先天形式地与经验对象发生关系的这种可能性的知识,才能称之为先验的”[16]。
事实上,米切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已经成功利用上述思想,发展出了解决相对主义的理性结构模型。在面对牛顿理论被相对论取代,康德哲学的基础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弗雷德曼吸收赖欣巴哈的思想,指出我们应继承康德的先天形式的构成性,摒弃先天形式的固定性*赖欣巴哈在《相对论和先天知识》中有着类似的理论,参见:Hans Reichenbach.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and A Priori Knowledg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使先天形式相对化。在此基础上,他依据科学史创立了更为完备的三层理性动力系统:“在底层是经验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原理,即所谓的自然经验定律,例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或者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这些定律通过严格经验检验过程之后,直接地精确地面对‘经验的涡旋’(tribunal of experience)。下一个或者第二个层面是具有构成性的先天形式原理,这一先天形式原理规定了基本的时空框架并且在框架内才能使得严格的公式及第一层或底层的定律能够为经验所检验。这种相对的先天形式原理就是库恩所谓的范式”[17]45。“事实上准确地说,我们的第三层是作为哲学的元框架和元范式,它的作用在于促使和引导一个范式(或范畴框架)向另一个过渡,具有激励和引导作用。”[17]46显然,弗里德曼的三层结构(经验定律、相对的先天形式和哲学元框架)中的经验定律和相对的先天形式平行于康德所理解的科学和形而上学,并适应了时代发展,把先天形式相对化,在相对的先天形式之上引入了一个沟通范式的哲学元框架(或哲学反思)。总之,弗里德曼的理性动力模型基本承袭了康德科学哲学的精髓(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辩证关系)。所以称之为“康德主义的新发展”[18]。
以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解题模型来看,自然主义要走出相对主义,就要对所依据的具体科学进行“先验分析”,追问他的普遍观念(或形而上学),而不是坠入地方性知识或信念不能自拔。科学社会化思潮要避免相对主义,也要找到沟通“范式”的哲学元框架,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科学史本身的社会维度。因此,康德科学哲学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所蕴含的科学和哲学的辩证关系或许能为走出相对主义困境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2. 科学实在论问题
一般认为,康德是经验实在论者,但是,最近几十年国际学界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康德是科学实在论者(如Margaret D. Wilson 和Kathleen Okruhlik)。康德的科学实在论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在论,而是在确定真理存在的意义上的实在论,可分为两层内容:知性的构成性确定具体科学定律的存在,理性的范导性是科学理论系统化。正如Kathleen Okruhlik在确认康德是科学实在论者时认为:“康德的理性试图为经验杂多建立一致性和统一性,以促成和确保知性的运用和经验层面上的真理的存在。”[19]康德的科学实在论对于我们当代的实在论问题依然具有批判意义,下面从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整个实在论问题有所言说。
一些学者认为普特南的实在论受到了康德的影响,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深入挖掘康德实在论思想和普特南的思想的不同,进而失去了以此批判和改进普特南实在论的契机。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的核心洞见在于:“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20]55具体而言,符合可接受性的理论是多元的,但是为了“工具性效能、融贯性、全面的和功能上简单性”[20]151的目标,多元的真理不断地“会聚”为一种理想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关键缺陷在于真理的融通性只是以一种信念契合其他的信念,并非方法论上的、人类内在认知层面上的联系,导致理论之间的联系是模糊的、非具体的,所以必然陷入真理的多元论。因此普特南只有求助于“我们人类认知能力兴盛发达”来整合多元理论,其结果只是达成理论之间名义上的统一,依然不能摆脱多元论。然而,在康德看来,理性通过一种单独的、整体的先天形式时空框架,为外感觉对象及结成的经验理论,建立了一种范导性的统一性。理性的这种自然合目的性的统一性是真正的、内在于认知的、方法论上的统一性,根本不存在多元论。对比来看,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如能汲取康德“理性的内在合理性”的精髓,或许既能克服“多元论”的困境,又能避免康德科学哲学忽视文化和历史的弊端,进而增强理论的可辩护性。
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是反实在论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理论是主体对于经验世界建构的结果,不同的建构方式产生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理论之间是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关系,都具有经验的“充足性”,所以承认不同理论的存在使得他的理论走向了反实在论。弗拉森认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在于陷入了观察和理论的解释学的循环,即“如果可观察的东西本身并非只是理论揭示的事实,而是和理论相关或依赖于理论的,那么就会导致恶循环”[21]。从否定意义上看,弗拉森瓦解了科学实在论的核心洞见(整体的理论对应整体的观察结果),但是,从肯定意义上看,弗拉森的这种反实在论假设了某一理论和观察之间的对应关系,承认特定现象可以“充足”证明某一理论的实在论。置换到康德实在论的语境下,弗拉森承认了知性(具体理论)对于经验(观察)的认知,否认了理性的范导性对于整体经验系统性的认知。对此,康德的科学实在论可以给予有力的反驳。在康德看来,理论所对应的经验的充足性不能离开理性的范导性和知性的构成性对于经验的建构,只有在理性和知性建构作用中,科学理论才是实在论的。因此,弗拉森的反驳和证明忽视了理性的范导性可以证明具有系统性的科学理论为真。如果弗拉森能注意到这一点,或许他会走向更强意义上的实在论。
此外,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在其后的发展中又出现了多种形态,如Ian Hacking的实验实在论、Richard H. Schlagel的语境实在论、Arthur Fine的非实在论、Kukla A.A.和French S.等人的结构实在论等。尽管种类繁多,但是,正如郑祥福教授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无论是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或者中间形态“都没有正确地把握理论、人、世界三者的关系。在这三者的关系中,理论与世界、人与世界两个层面的理解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哲学观: 突出人的地位就形成了反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哲学观,突出理论对世界的反映就形成了实在论的唯物主义观点”[22]。对于二者观点的对立,郑教授给出的药方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和辩证法。然而,如果我们悬置康德科学哲学的“物自体理论”限制和缺乏历史感的问题,从康德科学实在论的观点来看,或许会为实在论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认识模型。在康德看来,世界只能呈现给我们经验,经验世界在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建构下形成理论,不同的理论又在理性范导性的作用下不断地“会聚”为一个统一的体系。所以,具有建构能力的人、理论和经验世界是一体的、统一的,反实在论者都是在割裂这种统一性。
四、讨论:元科学哲学问题的反思与研究空间
对于康德科学哲学的合法性、学术史、主要问题和意义进行学术梳理并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要对科学哲学一些重要问题进行重新反思。
何谓康德科学哲学?康德科学哲学在科学哲学史研究兴起的浪潮中取得合法性并占有重要地位,学术核心是在具体科学和哲学(或形而上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学术前景是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困境和问题提供一条解题路径。
何谓科学哲学?通过康德科学哲学,我们对于科学哲学有一种新的观点:科学哲学不仅仅是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或游离于精密科学之外的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科学哲学是事实判断(科学或经验)和价值判断(哲学或超验)的统一。
康德科学哲学遗产的核心在于他提出了“先验分析方法”(这一方面后经马堡学派加工整理*马堡学派的创始人柯亨认为,康德的哲学是对“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理论”分析的结果。参见:Hermann Cohen. Das Prinzip der Infinitesimal-Methode and seine Geschichte: Ein Kapitel zur Grundlegung der Erkenntniskritik[M]. Berlin: Dümmler,1883:119-120。后来的Paul Natorp 和Ernst Cassirer等人发展和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主张追问科学知识何以可能,并用分析出的先验形式和理性构成科学知识。康德的这一“科学哲学平行”互动思想遗产为我们开辟了两条重要的研究路径:
其一是康德科学哲学本身的深度挖掘。这包括对康德哲学重要概念的深层理解。正如Robert Butts所说,“如果以科学和哲学双重维度的路径来理解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话,这本书的每个重要元素都要重新理解”[23]。这包括了康德的质、量、关系和模态与牛顿力学的具体关系等。
其二是对科学哲学史的研究路径的示范意义,康德的“科学-哲学”的方法和遗产为我们研究科学哲学史提供了“科学-哲学平行论”的新路径。正如Michela Massimi所言:“只有以康德的这种方式,我们才有希望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24]这种平行论的路径不同于分析性和诠释学的编史纲领,而是一种科学和哲学之间互动的综合史观,为科学哲学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以此路径,我们可以重新发现科学哲学史的重要理论,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数论之间的关联;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和三段论与生物学的关联等。
参考文献:
[1] Craig E. The Short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656.
[2] 辞书编委会. 东西方哲学大辞典[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3.
[3] Haldane J B S. When I Am Read[M]∥Possible World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9:209.
[4] 代利刚. 如何走出科学哲学研究的相对主义困境——以“理性动力学”的反思为求解向度[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4,35(5):32.
[5] Massimi M.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After Kant[J].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2009,65:276-277.
[6] Schönfeld M. The Philosophy of the Young Kant: The Precritical Projec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95.
[7] Buchdahl G. The Conception of Lawlikeness in Kant's Philosophy of Science[J]. Synthese, 1971,23(1):31.[8] Butts R E. The Methodological Structure of Kant’s Metaphysics of Science[C]∥Butts R E. Kant’s Philosophy of Physical Science.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170.
[9] Friedman M. Kant’s Construction of Nature: A Reading of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592.
[10] Carrier M. Kant’s Theory of Matter and His Views on Chemistry[C]∥Watkins E. Kant and the Scien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206.
[11] Watkins E. Kant’s Justification of the Laws of Mechaniscs[C]∥Watkins E. Kant and the Scien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153.
[12] Warren D. Reality and Impenetrability in Kant’s Philosophy of Nature[M]. London:Routledge, 2001.
[13] 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21[M]. Berlin: Druck Uno Derlag Don Georg Reimer, 1936:592.
[14] Edwards J. Substance, Forc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Knowledg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1-8.
[15] 贺来. “相对主义”新议[J]. 人文杂志, 2000(3):26.
[16]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55.
[17] Friedman M. Dynamics of Reason[M].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s, 2001.
[18] Suárez M. Science, Philosophy and the a Priori[J].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2,43:6.
[19] Okruhlik K. Kant on Realism and Methodology[C]∥Butts R E. Kant’s Philosophy of Physical Science.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318.
[20] 希拉里·普特南. 理性、真理与历史[M]. 童世骏,李光程,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1] 范·弗拉森. 科学的形象[M]. 郑祥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2005:74.
[22] 郑祥福. 科学实在论在当代的发展[J]. 哲学研究, 2012(10):109.
[23] Butts R E Gerd Buchdahl: A Tribute[C]∥Woolhouse R S. Metaphysics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Dordrecht: Kluwer, 1988:13.
[24] Massimi M.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After Kant[J].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2009,65:302.
(责任编辑: 李新根)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f Kan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Status, Horizons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DAI Li-gang1, AN Wei-fu2
(1.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of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Research of Kan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a heated issue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In terms of the legality and status, the latest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has resurrected Kant’s natural philosophy and given it a legal status as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king it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erms of the academic horizons, research of Kan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focuses on the eternal research theme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and the more profound problems in methodology. In terms of the contemporary value, Kan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y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scientific realism that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have been discussing.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a feasible approach to getting out of the dilemma of relativism in research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itiated by Kuhn and Quine. More importantly, Kan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can provide new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space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self.
Key words:Immanuel Kant; science; philosophy; realism; relativity
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3.002
收稿日期:2015-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4ZDB01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JUSRP116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5BKS066)。
作者简介:代利刚(1983- ),男,河南平顶山人,江南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安维复(1960- ),男,吉林九台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N 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6)03-022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