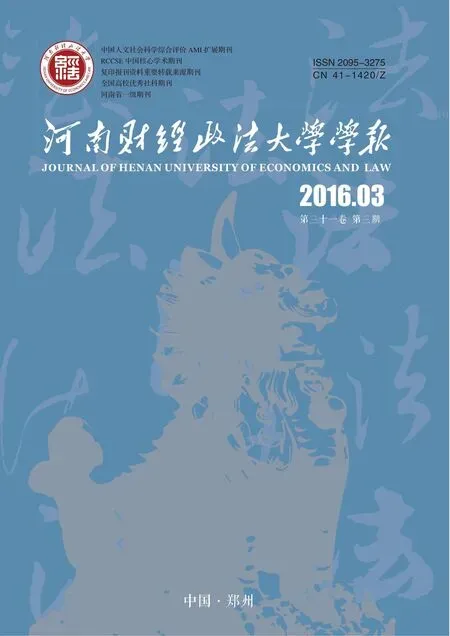论传统中国个性司法的发生及规制
——以清代为中心的考察
2016-03-06李相森任佳莹
李相森 任佳莹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解放军理工大学 训练部,江苏 南京 211101)
论传统中国个性司法的发生及规制
——以清代为中心的考察
李相森任佳莹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解放军理工大学 训练部,江苏 南京 211101)
形式理性化的现代司法排斥司法主体个性的侵入。但个性司法行为在中国传统司法中真实存在,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传统法制为司法主体个性作用的发挥留有空间,司法主体的性格、气质、能力等个性因素直接影响司法的进程及结局。但传统司法并非完全由司法者的情绪、偏见等非理性因素主导,更非个体化的恣意专断。传统法制有一套形塑和规制司法主体个性的机制,以保证司法行为的大体稳定和基本取向。以史为鉴,平衡和缓解个性影响司法与依法公正裁判之间的张力,需从塑造司法人员良好个性及完善司法制度两个方面进行。
个性司法;卡迪司法;传统司法;确定性
关于中国传统司法的性质,学界历来存有争议。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中国传统司法“依赖于一种实在的个体化与恣意专断”[1],是所罗门式的“卡迪司法”。黄宗智对清代司法档案的研究则表明,清代法律制度“不是韦伯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和理性化的,但它显然也不是卡迪法”,“不是专横武断、反复无常和非理性的”[2]。地方一级的司法活动远非随意的、取决于官吏个人清浊智愚的和难以捉摸的,相反,它们大部分是“依法判决”的*黄宗智从宝坻县、巴县及淡水新竹等司法档案中选取了628宗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其中221件经过官府的正式审判,“在221件经过庭审的案子中,有170件(占77%)皆经由知县依据大清律例,对当事双方中的一方或另一方作出明确的胜负判决”。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司法主体的行为是前后一致和可预知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合理性。
2006年以后,学界关于中国传统司法是不是“卡迪司法”、有没有“确定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争论双方分为两派,一为赞同中国传统司法为卡迪司法、不具确定性,以贺卫方、高鸿钧等为代表;另一方则反之,以张伟仁、林端等为代表。关于争论焦点及各方观点的梳理,可参见陈景良:《宋代司法传统的叙事及其意义——立足于南宋民事审判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马小红:《“确定性”与中国古代法》,《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学界还针对中国传统司法的性质问题专门召集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名为“中国传统法制与法律文化”的研讨会,张伟仁、贺卫方、高洪钧、林端、范忠信、徐忠明、张中秋、陈景良等学者与会讨论;2008年4月10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召开“中国古代法律的确定性”学术研讨会,李贵连、杨一凡、苏亦工、赵晓耕、马小红、刘广安、俞荣根、龙大轩、张仁善、王志强、李启成、俞江以及日本学者寺田浩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源盛等参与研讨。。有关此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例如陈景良关于南宋民事审判理念、制度、原则的研究表明,“宋代法官是依法判案,而不是随心所欲;宋代的司法传统是成文法传统,判决具有客观性与确定性,而不是‘卡迪司法’”[3];柳立言对南宋五位司法者所审理的28起立嗣、分产案件的研究表明,他们“作出相当一致的判决”[4]。马克斯·韦伯的论断在中国学者扎实史料及严密逻辑的反驳之下,暴露出纯理论概括及简单类型化的脆弱和片面。同时,亦有学者对以“确定性”“依法判决”来评判中国传统法制提出质疑,认为“以确定性评价中国古代法律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错位”[5];坦承中国传统司法的“不确定”,“作为一种颇具特色的法律文明,中国古代司法并不以‘确定性’为最高的追求”[6],试图跳出问题预设的概念前提,寻求突破。但如何解释有关中国传统司法恣意专断与依法判决两种论说之间的矛盾,超越“确定”与“不确定”的二元划分及对立,尚待进一步探讨。
梁治平在指出韦伯有关中国传统司法论断错误的同时,强调在认识中国传统司法时不能趋向于另一种极端,即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确定的、完全可预期的、形式理性的。“古代州县官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确实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包括援用的规则、适用法律的方式以及具体刑罚的确定等。这固然并不简单意味着恣意专断,但也不完全否认‘个性’因素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7]梁治平已注意到古代司法官员个性因素在司法中的作用。个性因素影响司法并不简单意味着司法的恣意专断,但却与传统司法的不确定性相关。张仁善则明确提出了“性情司法”的概念——“性情包括性格和情趣两个方面,性格为先天的,情趣多为后天养成,它们共同作用于司法主体的司法活动时,即为‘性情司法’”[8],并通过大量的案例、史料对性情司法进行了类型化,考察了司法主体不同性情取向对司法实际效应产生的影响;认为传统中国的专制政体、司法权机制、司法程序的瑕疵等为司法主体性情养成提供了条件,从而决定了传统法律预期的不确定性[9]。这为探讨传统司法的确定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传统司法的性质,离不开对司法主体个性与司法关系的探讨。如果说传统司法为个体化的恣意专断,那么是司法主体的个性主导或影响了司法的进程及结局,而非一套预先确定的法律规定及司法程序。司法主体的个性是否影响了司法,产生了多大影响,直接决定着对传统司法是不是“恣意专断”的论断。本文拟从司法主体个性与传统司法关系的角度,考察个性司法的发生如何导致了裁判的“恣意专断”之嫌,传统司法的一套规制机制又如何保证司法行为的大体稳定和基本取向,以及这看似矛盾的两种形态如何共存于传统司法之中,以期对中国传统司法的性质作出一种可能的解释,并为当前处理司法主体个性与司法的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一、个性司法及传统中国的个性司法
(一)个性、司法主体的个性及个性司法
个性是一个多学科共用的多义性概念。按照心理学的定义,“个性,也可称人格,指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10]。社会学援用心理学的定义,“个性是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定倾向性和稳定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11]。社会心理学将个性定义为“一个人在其生活、实践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带有一定倾向性的个体心理特征”[12]。总结这些论说,可将个性定义为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倾向性的个体心理特征的总和。
个性具有多层次结构,包括:(1)个性倾向性子系统,人积极活动的指向性,主要包括需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观等心理成分;(2)个性心理特征子系统,个体经常、稳定地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气质、性格、能力;(3)心理调节子系统,如自我评价、自我感受和自我控制等[13]。其中,个性倾向性是个性的核心,制约着人的情感性质与情绪变化,影响着认识的正确与深度,对人的行为起最高调节作用。个性心理特征则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较早,是个性结构中比较稳定的成分。心理调节则对个性倾向、个性心理特征具有整合作用。这些结构系统错综复杂、交互联系、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影响、调节、控制着个体行为。
个性带有浓烈的个人色彩,由个体的先天遗传素质、物质生活条件及教育背景所决定,并随着个体自身阅历、社会地位、外部环境等的变化而变化。但同时,个性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惯性和可预期性,而非变幻无常、难以捉摸。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多变的喜怒哀乐和无常的动静行止背后,是稳定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惯性。而经由成长经历、教育塑造、生活打磨、岁月沉淀而形成的个性更是成为一个人行为的“潜在背景”,时刻影响甚至主导着个体的思维及行为方式。
人皆具有个性,作为人的司法主体当然有其个性。法律由活生生的人来实施。司法便不可避免地要与人的喜好、情感、性格、观念等个性特征发生纠葛。在案情不变的条件下,将司法主体置换,若司法进程及方式明显变化,或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那么司法主体这一因素便影响了司法。清代樊增祥于陕西臬司任上,曾批韩城县令张瑞玑所审案件。卜刘氏夫妇没有儿女,遂抚养卜随儿为嗣,并聘定薛智之女为随儿妻。但随儿长大后不务正业,屡犯偷盗。于是,卜刘氏不欲随儿继续为嗣,逐令归宗,另立卜荆树为嗣,并让随儿与薛女离婚。卜随儿竟然剥掉荆树之衣,进行侮辱,并扬言薛女如果改嫁,定要刁抢。卜刘氏与薛智一齐控案。张瑞玑将卜随儿予以笞责,断令薛智将女另聘,所得彩礼分给随儿一半,以俾随儿小本经营。樊增祥批云:“美哉,仁人之用心!”但接着笔锋一转,“若吾断此案,岂惟不给银而已,并当久押县厅,使知法令之严与幽禁之苦”[14]。如果将司法主体置换,在同一案件条件下,卜随儿的遭遇将完全不同:一为仅受笞责,领得经营本钱;一为久被羁押、受幽禁之苦,且无钱可得。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两人对同一当事人截然不同的判罚?
决定司法主体做出相异的司法行为及裁判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比如与司法主体相关的身份、社会关系、声望等外在因素的干预和影响,除此之外即是司法主体个人的能力、气质、性格、理念等内在因素在发挥作用。司法主体在司法活动中表现出来并影响司法进程及结局,明显具有个体特征的内在因素,是司法主体的个性。司法主体的个性表现为个体的能力、气质与性格等心理特征。上案中,樊增祥并非不仁之人,他亦言万事以仁为本。但其阅历较张令为深厚,颇知人心不古,以仁恕对待恶人适足以长其恶,对恶人应行霹雳手段。樊亦自陈“本司向来惩治恶人,每施辣手”[15]。在仁恕之外,樊增祥尚多一“老成”与“严明”。由此可见,不同主体作出不同的判决,个性影响实占据重要地位。
在司法主体个性主导或影响下,司法进程及结局带有明显个体化特征的司法活动,是为个性司法。首先,司法主体个性的存在是个性司法的前提。司法主体的个性先于司法活动而存在。若司法主体为毫无情感、偏见、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的机器,则不存在所谓的个性司法。其次,司法主体的个性被允许在司法活动中到场,具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司法主体享有较大的自主裁量权,可以根据自身个性运用司法权。再次,司法主体的个性决定了司法进程及结局,而非确定的法律及司法程序。在多种影响裁判作出的主客观因素中,司法主体的个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果将司法主体的个性抽离,司法进程及结局将截然不同。但司法主体的个性主导或影响司法进程及结局并不代表个性司法就违背法律。个性司法也可以表现为依法判决。依法判决与否不是判定司法行为是否为个性司法的标准。
个性司法的发生需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一是司法主体具有个性;二是个性具备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三是特定事件、情境的激发和驱动。第一个条件不成问题,司法主体可能不是清一色的“法律人”,甚至缺少必备的法律知识,但无疑都是具有自身性格、气质、情感、偏好、观念的人。因个性是可以塑造和规制的,故该条件是可控的。第二个条件则是个性司法发生的决定性条件。如果司法制度根本没有为个性作用的发挥留有余地,则不可能有个性司法。司法制度允许或需要司法主体个性在司法活动中出场,此种司法制度下的司法实践才有可能成为个性司法。第三个条件,哪些特定事件或情境会进入司法主体的视野并引发其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事先无法预知,不可直接控制。但该条件的存在以前两个条件的存在为前提,可以通过司法主体的个性形塑、必要的制度性设置控制特定事件、情境与司法主体个性的耦合。
(二)传统中国的个性司法
揆之中国传统司法实践,司法主体个性迥异,其理讼断案的方式及结局亦有差别。例如,乾隆年间,凤翔府知府康某为人仁慈,处罚犯人时通常仅打三板而已,因此得名“康三板”[16]。而道光年间,直隶获鹿县知县甘崇敬,号称能吏,一旦捕获案犯即打八百板,被称为“甘八百”[17]。两位知县一为仁慈,一为严苛,以致犯人所受待遇有天壤之别。二人因司法行为不同而赢得诨号,可见其任个性而司法非一日一时之举。再如,光绪年间,陈豪署随州,即将离任,听说接任官长“好杀”,于是“竭数昼夜之力,凡狱情可原者,悉与判决免死”[18]。两位不同的司法官,一为宽仁“好生”,一为残刻“好杀”,同一犯人则生死殊途。可见,传统中国司法主体的个性直接决定着裁判的有无、轻重,影响着司法权的具体运用。
个性影响司法一二之例的存在并不能证明中国传统司法即为个性司法。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则必然存在个性对司法的影响。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与形式理性的现代司法在根本上排斥个性(不论其对于司法目的之达成具有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的影响不同,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是对司法主体的个性开放,为司法主体个性作用的发挥留有空间,且其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司法主体个性作用的发挥。
第一,传统司法制度赋予司法主体极大的司法自主权,为司法主体的个性主导、影响司法提供了空间。与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清代最高司法权由皇帝总揽,其行使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皇帝根据“他个人对形势的估计,对法律的解释,对案情的知悉,来决定如何运用自己手中的最高司法权”[19]。最高司法权掌诸一人时,凭个性而司法,势所必然。其他各级司法官员则享有极大的司法自主权。传统法律允许“比附援引”,允许司法者在律无明文的情况下斟酌案情量为判断。乾隆六年(1741年)颁发上谕:“律例一书原系提纲挈领,立为章程,俾刑名衙门有所遵守。至于情伪无穷,而律条有限,原有不能纤细必到,全然概括之势,惟在司刑者体察案情,随时详酌,期于无枉无纵即可。”[20]地方州县官员对于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等自理案件有权决定受理或不予受理,甚至可以超越律例进行裁断。“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州县本执法之官,情有可原却不妨原情而略法”[21]。这类案件的处理便“依法官的为人而有所不同”[22]。咸丰三年(1851年)之后,封疆大吏更是取得了“就地正法”之权,无需奏请核准即可处死案犯。就地正法本是特殊情势下的产物,但“疆吏乐其便己,相沿不改”[23]。手握绝大司法权的督抚大吏难免为“便己”而生杀予夺。司法实践中,州县官吏亦有“先斩后奏”者。同治年间,蒯德模署长洲县令,下乡访闻,有乡保拿获姚阿福、谭大兴等盗棺人犯请求处理。蒯德模亦知“官格于例而事必上详”,但还是“施速死之刑”,判令杖毙姚、谭二人,并接受乡人之请,将二犯尸首投水喂鱼鳖[24]。蒯德模并未因此种司法行为而受追究。史书反称其“执法平,不为核刻”,判案“尽惬民意”,将其列为循吏*《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九,列传二百六十六,循吏四有蒯德模传。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80页。。可见当时的司法制度并不追求所谓的程序正当,司法主体具有相当大的司法自主权,为个性作用的发挥提供了足够空间。
第二,传统司法追求具体案件的妥当解决及社会的有效治理,依赖于司法主体个性作用的发挥。与西方现代司法将客观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不同,中国传统司法是考虑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对法则进行不同的解释,甚至斟酌天理、人情,以达到具体案件的妥当解决。实现案件的妥当解决,并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程式化的逻辑推演以及是非对错的简单判断,还应考虑每个当事人不同的处境予以妥善安排,维系当事人相互间的共存关系以及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依法判决”“同案同判”、裁判的“确定性”尚无法达致这种司法目标,还需司法主体斟情酌理,妥为处置*在清末做过幕友的陈天锡曾言:“有些案件并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牵涉到许多其他因素,假如硬生生地去依法办理,有时反而不能得到情理之平”,并列举案例进行说明。宣统二年(1910年),湖南沅陵县有一贫苦妇人,拾取遗落田间的稻穗,而田主却以盗罪向沅陵县典史(捕厅)呈控。典史违例擅受,派遣差役去拘拿妇人究办。结果,妇人畏惧不已,上吊自尽。后,田主愿出钱求和。县官亦不拟深究。但此事为上司知府所知,大为震怒,要求严办,不准讲和。结果,将典史革职,田主判刑。虽是依法正办,但依靠妇人生活的亲属却没有得到经济补偿,田主控告也非恶意致人死命,但却因此背负刑罚,殊非正当。参见张伟仁访问,俞瑜珍记录:《清季地方司法——陈天锡先生访问记》,载于张伟仁:《磨镜——法学教育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这就呼唤个体的直觉、阅历、经验、能力等个性因素的出场。传统司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首先服务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允许并需要治理者的个性化司法。帝国统治者意图将所有违背统治秩序、有害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为尽可能广泛地发现违法行为,尽快地求取裁判结果、案结事了,恢复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需要司法主体各显神通,便宜行事。治理者的个性便决定了司法权的运用,或宽容以显仁爱,或威严以示震慑。乾隆年间,江西丰城知县满岱“天性长者,宽恕有容”,“尝自春迄冬,仅用杖二十”[25],而不事鞭扑,纯任自然,竟也治化一方。后因事被参而离任,百姓无论智愚,皆为之饮泣。这种仁厚司法显然与律法规定有违,但并未受到上峰指责,甚至还得到百姓称赞,被后世奉为治理法则。前文所举之“康三板”“甘八百”与此同类,也可见这种个性司法绝非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传统中国个性司法的发生机制
基于传统司法制度及理念展开的所有司法实践都有可能成为个性司法。但一项具体的司法实践是否能够现实地成为个性司法又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和条件。个性司法是由具体个性司法行为完成的。个性司法的发生即是个性司法行为的进行。以个性主导或影响司法发生机理的不同,可将个性司法行为划分为恣意型个性司法行为、无意型个性司法行为及有意型个性司法行为。不同类型的个性司法行为的具体发生条件及机制亦有所差异,表现为各个不一的形态,从而使得传统司法呈现出复杂的面相。
(一)恣意型个性司法行为的发生机制
马克斯·韦伯将社会行动划分为传统行动、情感行动、价值理性行动及目的理性行动四种类型[26]。其中,由情绪决定的行动是情感行动,是非理性的。传统中国,部分司法主体残刻无情,动辄刑罚,生杀予夺,草菅人命,如唐太宗怒杀大理丞张蕴古,以忤旨而斩交州都督卢祖尚于朝堂之上[27],是完全由情绪决定的、非理性的恣意型个性司法行为。
清代,黄六鸿任直隶东光县令时,接上令修复各村庄墙濠,责令保正庄头负责此事。完工后,黄六鸿亲自查勘。查至东乡保正赵某辖区,赵某为前导,却托故绕行,不为引视。黄六鸿径自前往查看,墙濠依旧颓塞如故,问于村民乃知赵某收受贿赂。黄六鸿“怒其欺诡,且私敛民财,命杖之”。其他保正环跪请求免除处罚。结果愈发激怒了黄六鸿,责令重杖赵某三十大板。不出一月,赵某伤重身故。日后,黄六鸿每念及此事,未尝不追悔莫及,并反思道“为民上者,凡接物处事,惟酌其理与情,而用法慎毋骋一时之躁怒,而流为残刻”[28]。因一时之躁怒而施以重刑,显系情绪主导下的司法行为。
再如,清代名幕汪辉祖在其《佐治药言》中记载:叶某在山东馆陶作幕友时,有士人告恶少调戏其妇。叶某本不欲提妇人质对,但其友谢某认为该妇应有姿色,可以寓目,遂提审之。结果该妇忿激,投缳而死。恶少因而被判死刑[29]。提审妇人这一行为的做出完全是色迷心窍,放任好色之性的结果。
恣意型个性司法行为是完全在司法主体个性驱动和主导下的一时冲动或应激反应。其发生机制为:一是司法主体手握权力(并不论其实际之大小),缺少必要的有效监督和规制,可以不计后果、为所欲为;二是特定情境下,个性中的非理性成分被完全激发,如勃然大怒而丧失理智*但司法主体故意地对诉讼当事人“慑以盛怒”不属于此类。清代刘衡曾总结理讼之经验,“于接呈时,向告状人逐细诘问,即用五听之法,或慑以盛怒,或入以游词”,以求得真实之案情。[清]刘衡:《州县须知》,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6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09页。,当然也可能是欣喜若狂等其他非理性情感。
恣意型个性司法行为是恣意地放任个性,但并不一定违背法律或超离法律。专制体制下,皇帝即可凭个人喜怒行使最高司法权。黄六鸿重惩贪贿亦在知县权限范围内。叶某作为幕友帮同审判,代理县官权限,有权决定是否提审,提审涉案妇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实际上,在恣意型个性司法行为中,司法主体的个性影响盖过对行为合法、非法,抑或适当、不适当的理性判断,司法权仅是其行动的工具和手段,而司法程序则遭遇漠视。至于是否依法裁判并未被纳入司法主体的考虑范围。
(二)无意型个性司法行为的发生机制
恣意型个性司法行为是非理性的,是理性的彻底退场。有的个性司法行为则是深思熟虑、周密思考的结果,具有价值或目的合理性。司法主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意愿和目的,对自身行为有所意识,能够进行相应的掌控和调整。但对决定其意愿及行为的“潜意识”和“不自觉”却往往无意识,无法加以掌控。个性恰在这种“潜意识”和“不自觉”中显露,主导或影响着主体的行为方式、司法进程及结局。这是司法主体在个性潜在影响和驱动下做出的无意型个性司法行为。其发生机制为:司法主体的个性作为潜在背景贯穿于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并因外部事件及情境的触动在某一点上无意识地被激发,使司法进程及结局打上司法主体个性的烙印。无意型个性司法行为完全可以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依据法律或情理等规范做出判决。但行为是否依法并不是重点,也不是决定司法进程及结局的主因。
汪辉祖就馆长洲县时,遇一案:周张氏十九岁守寡,抚育遗腹子继郎至十八岁,而继郎不幸病殇。周张氏欲为继郎立嗣,而族人以继郎未娶,仅能为张之夫继子。双方僵持不下,辗转讦讼,历十八年之久。汪辉祖览案后,代县批曰:“殇果无继,谁为之后?律所未备,可通于礼。与其绝殇而伤慈母之心,何如继殇以全贞妇之志”[30],认为不可令节妇抱憾以终,遂为继郎立嗣。历十八年之案,无人能结,可见极为棘手。即使在汪辉祖批判之后,知县郑君亦大为诧异,嘱令改判。但汪辉祖却坚持作出了有利于节妇的判决。汪辉祖自称处理此案,并无私意。但引礼断案,成全贞妇,与他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汪辉祖少年失怙,嫡母方氏与生母徐氏“励节食贫,纺织余功,兼糊楮镪自给”[31],含辛茹苦,抚育汪辉祖长大成人。正是这种成长环境及经历的影响,让汪辉祖对守节之嫠妇犹加体恤同情。由成长经历所决定的同情之心潜在地影响了其司法行为。
清代张船山任山东莱州知府时曾审得无赖李大根偷窥邻女杨二姐洗浴一案。嫉恶如仇、爱民如子的张船山一面郑重宣称“若不严惩,何以正风化而匡人心,自当照律科刑,聊以安良善而戒来者”。另一面又念其情节尚轻,怀菩萨慈悲心肠,予以宽恕,判令“李大根将杨二姐浴汤一饮而尽”[32]。张船山的判决出人意料,非律所载,又不违于律(清律规定有“不应为”之罪,裁判官可量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罚),寓庄于谐,令人忍俊不禁,可谓“任性”。这样极富个性的判决是与张船山的个性分不开的。张船山工于诗,号称“青莲再世”;喜闲情,书画俱佳;宗理学,谙于史事,为治有方。诗人情怀、艺术雅兴、理学精神共同决定了这亦庄亦谐、情法两得判决的作出。若换作他人,当无此判。
(三)有意型个性司法行为的发生机制
恣意型与无意型个性司法行为中,个性作用的发挥皆是“潜在地”“无意识”的。司法主体对于自身的个性无意识,且无法进行掌控。但亦有司法主体充分了解自身个性,有意识的地培养、固守某种品性,在司法过程中控制、约束自己的行为,特意使司法判决表现出特定趋向,达致某种目的。此时个性发挥作用的方式是“有意识的”,即理性主导下的个性司法行为,可称之为有意型个性司法行为。其发生机制为:司法主体具有或宽或严的司法自主裁量权,完全清楚自己的意愿及目的,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自身司法行为,从而达致某种目的或状态。
清代陕西朝邑县令曾某,系能吏,风采隐然,但偶有贤智之过,较为偏狭、苛刻,用刑颇重。樊增祥作为他的上司“时相规切”。结果,曾令有所改进,在上报自理词讼册内的案件“语语持平”,讯明田见龙、张择铎等无赖后,仅予薄责,以行德化[33]。曾令从严苛司法到仁恕司法的转变即是在自己的有意控制下完成的。再如,“一般认为康熙宽仁,他在位的六十一年,据《实录》统计,秋审停勾、停止秋审等就有三十年”[34]。停止秋审或勾决即意味着缓决的死刑犯人可以继续活命。这与康熙帝宽仁的个性不无关系。但其宽仁个性是在理性控制下对司法发挥作用的。可以说此种宽仁司法是刻意为之。有意型个性司法行为中,司法主体固守的个性完全可以是“公正无私”的,其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司法程序,而最终的裁判结果是依法作出。因而,有意型个性司法行为可以表现为“依法判决”。但是否依法判决仍取决于司法主体的个性。
三种个性司法行为都有个性在司法活动中的到场,裁判的进程及结局受到司法主体个性的主导或影响。当然,个性司法中法律、司法程序依然会到场,只是它们已不是司法进程及结局的决定因素,不是主要的参与者,甚至形同虚设。司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因而受到破坏。恣意型个性司法行为因完全是由非理性情绪、情感主导,故其进程及结局皆不具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无意型个性司法行为中,司法主体的个性以潜在的方式发挥作用,司法主体个人且不自知,更不易为他人所窥知,因而不具有可预期性。有意型个性司法行为是在司法主体理性支配下的自觉行为,受特定目的的指引。但不了解其个性及目的的他人,亦无法预期其行为方式及倾向。“他们在诉讼之前,无法判断当值司法主体的性情,无法了解司法主体性情,他们就无法作出应有的法律期待”[35],在这一意义上,个性司法行为不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从而使传统司法表现出“恣意专断”的面相。
三、传统中国个性司法的规制机制
个性司法的发生受多种条件及因素的影响,且这些条件和因素具有可控性,任一条件或因素的改变都可能制约个性对司法的影响。这就为通过外在或内在的规制,形塑司法主体稳定良好个性,保证司法行为的大体一致及基本取向提供了可能。中国传统司法允许个性在司法中到场的同时,还有一套形塑、制约司法主体个性的规制机制,司法主体个性作用的发挥亦受一定司法制度、目的、理念的规制。这使得传统司法表现出“依法判决”的一面。
(一)律法及制度之规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律法本即为防止君主任意司法所设。所谓“万世之法,有伦有要,无所喜怒于其间”,“先王恐后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违,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孙”[36]。人君尚不能“任喜怒”而司法,奉行“圣人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理念的最高统治者自然不愿,亦不允许属下官吏任性而为。传统中国的成文律法“从根本上讲不过就是统治机构内以官吏作为控制对象的内部规范,或者说是官吏执行职务的准则、王者治理天下的工具”[37]。在赋予司法主体以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律法又对他们的司法行为进行了规制,尤其是禁止明显偏离司法目标的个性司法行为的发生。《大清律例》明文规定“断罪皆须具引律例”(《大清律例·刑律·断狱下·断罪引律令》),反对任凭个性妄引比附,“凡问刑衙门,敢有恣任喜怒妄行引拟,或移情就例故入人罪,苛刻显著,各依故失出入律,坐罪。因其而致死人命者,除律应抵死外,其余俱问发为民”(《大清律例·名例律·断罪依新颁律》)。此条之设正为防止“拟罪者比附例条,以资游移,舍律从例,以从苛刻”[38]。
律法的规定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于司法主体头上,让其司法时不能不警惧审慎,依律为断。司法官的恣意性因而受到限制。汪辉祖曾言及自己习幕、佐幕二十余年的观感,“凡为幕者,率依律阐义,辩是非于一定,不敢丝毫假借。为吏、为上官者,据义斟酌,惟律是遵。虽颟顸如临汾中丞,刚愎若如皋观察,事关人命,犹不敢径行己见”[39]。即使个性再强的司法者,也不敢置律例于不顾,而专任自己的“颟顸”“刚愎”。而仁恕之人,欲行其宽大,也只能在律法规定的范围内斟酌权衡,所谓“仁者执律而断狱,虽罹于死,有一线生路之可求,未尝不求之。求之亦在于律耳”[40]。咸丰年间,聂亦峰知冈州,有陈梁氏之独子犯强盗案,应处死,陈梁氏呈请留养。聂亦峰在批词中称“强盗例无留养之文,氏男即系单传,亦难妄冀宽宥。本县虽具不忍之心,然止施于良民,不能施于强盗”,未予准理[41]。在不忍之心与律例的冲突中,司法官最终选择了遵从律例。
传统政治制度还建立了一套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对司法主体的个性司法行为进行规制。清代司法权的配置,自居于最高位的皇帝,其次中央司法机关,再次地方各级衙门,上级授权于下级,并进行监督;下级对上级负责,并接受监督。此一司法制度附属于整个帝国唯一合法的统治系统,依靠内部的自觉和监督来保持正常运行。上级衙门对下级官吏的操守品行和司法活动进行全面监督。“有司之贪廉,上司自有耳目,或密加访闻,或被害鸣控。仁恕者,尤先之以切责,冀其改过;严介者,遽登之以白简,顿丧身名。”[42]下级司法官的裁判要接受上级衙门的复核,州县初审之徒刑以上案件自应按审转复核程序呈请上司核批;至于自理词讼,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各省州县及有刑名之厅卫等官,将每月自理事件作何审断,与准理拘提完结之月日,逐件登记,按月造册,申送该府道司抚督査考。”(《大清律例·刑律·诉讼之一·告状不受理》)此种内部监督无疑会对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产生影响。前举陕西曾令例,也可见上司监督对下属司法个性之塑造及影响。
(二)儒家思想观念之规制
传统司法主体虽不具备充分的法律知识和专业的法律素养,但大多是儒家道德信条及政治理想的信奉者、践行者。“长期以来,帝国各级官吏由具有一定资格的读书人充任,这些读书人虽然不是技术专家,但却饱读诗书,熟知古来圣贤教诲”[43],饱受儒家经典浸润的帝国官员,践行着一套基本一致的为人处世的准则,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儒家所主张的仁爱、恕道、中庸、公正、廉明、诚信等道德品格,以及以礼为中心的有关人与人之间上下尊卑、内外群己的一套周密伦理规范,塑造了帝国官员的品性,为他们的司法行为提供了价值及规范指引。这使得大多数司法主体的个性能够大体保持在一个标准状态,保证他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恒定性和确定性。
清代官员手册中,有数量众多的立基于儒家思想观念的箴言和说教: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公门中所见,无非呼天抢地、鸠形鹄面之人,仁心尤易触发。正当随时体恤,随事矜全,以尽其不忍之心。倘无辜者则怜之,而人有罪者则以为死不足惜,犹非仁人之用心也[44]。”
“遇愚民犯法,但能反身自问,自然归于平恕……尚可以从宽者,总不妨原情而略法[45]。”
此种本于仁恕之心、行宽大之法的教说对传统司法官员产生了普遍影响。嘉庆年间的张经田曾言“近日办案家,失入者少,失出者多”,司法官多从轻量刑,皆是本于《尚书》“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轻”的千古忠厚之至论[46]。樊增祥初为官,其师问曰:“子为政何以?”对曰:“以仁。”师喜曰:“得之矣。人心不慈祥,既贼民而亦害己。”[47]为政以仁是师徒相传之知识,更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认知。仁是与惨刻、忿戾相对的,所谓“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戾,亦非仁也”[48]。在仁恕观念熏陶的政治环境下,部分司法主体欲妄行严苛、酷烈之性,亦有成为“众矢之的”的危险。从而,儒家正统思想大体上保证了司法主体个性的同一和稳定,不至过于偏离司法目的。
司法主体解释适用律条时,往往受儒家经典思想的指引,趋向某种内在统一,也避免了个性的任意发挥。传统中国法制经历了一个逐步“儒家化”的过程,西汉大儒董仲舒据经义以决狱,东汉马融、郑玄诸儒引经注律,唐律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司法官遇有难以议决之案,往往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斟情酌理,综合为判,保证了判决的大体一致*柳立言认为南宋五位司法者所审理的28起立嗣、分产案件,判决相当一致的原因之一即是审理者依照儒家的《论语》《春秋》等经义进行审判。柳立言:《南宋的民事裁判:同案同判还是异判》,《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他们靠自己的修养和对事物的理解去补足法律应用中的不足,并且依靠共同的自觉意识最终去实现中国古代法律的统一”[49],司法官的修养、知识以及共同的自觉意识则大部分来源于儒家思想文化的熏染和规训。
(三)其他非正式之规制
瞿同祖先生提醒我们,“执法官吏个人的福报观念对于司法的影响亦不可漠视,关系甚大”[50],传统司法主体的个性养成,除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之外,还受到佛教及道教因果报应、吉凶祸福观念的影响。
吉凶祸福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渊源深厚。《易》六十四卦皆言吉凶祸福。《尚书》四十八篇多言灾异祥瑞、成功失败之事。《诗经》之《雅》《颂》则推究福禄寿考之原由。善恶与吉凶福祸相关联,为善则吉,为恶则凶,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坤卦·文言》);“惠迪吉,从逆凶”(《尚书·大禹谟》),顺正道而行则吉,逆道而行则凶。传统的吉凶祸福观念被本土道教所继承、发扬,并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融合,造就了传统中国人为善去恶、积善求福、趋吉避凶的观念,并指导着人们的日常行动。
帝国的司法官员亦受果报、功过观念浸淫,并按照这些观念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积阴德、求福报。佛教不杀生及因果报应观念对传统司法主体宽仁个性的形成深有影响。源自道教的功过格,也为司法官员所借用,何种司法行为为功可受善报,何种司法行为为恶当受恶遣,每日自记自省,对司法主体向善个性的塑造不无影响。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批评道“今之法家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人罪以求福报”[51],可见当时果报思想对司法行为之影响。明清时期,为官之书中多有记功过、谈因果者。明代袁了凡的《当官功过格》,“举官司应兴应革之事,条分缕析,即其得失之轻重,以定功过之多寡”[52]。其中如“不嗔越诉”“不偏护原告”,“不徇嘱托”“耐烦受言”“不以成心怒翻案”等可算为功德应受福报之项,皆与塑造司法主体良好的心性及道德修养相关。在当时的司法官员看来,这种功过计算实有强大效力,“此阴司之纪功,较上司之纪功,效验更神”[53]。可见司法主体对功过格的重视,亦可想见此种非正式力量对司法主体个性的形塑。汪辉祖16岁时接触到劝善之书《太上感应篇》,“读之凛凛”,自此以后晨起必虔诚诵读一遍[54]。《感应篇》对汪辉祖的为人处世影响颇深,“有一不善念起,辄用以自儆”,为幕之时“日治官文书,惟恐造孽,不敢不尽心竭力”,做官之后亦然。汪辉祖终生不敢放纵,谨慎人命,宽为裁判的个性,实为受行善去恶、因果相报思想之影响,即其所自陈“得力于经义者犹鲜,而得力于《感应篇》者居多”[55]。
四、传统中国个性司法的逻辑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传统司法无疑表现出恣意专断的一面,但同时又不能否认大量的案件是依法判决的。如何解释传统司法所表现出来的完全相反的两种面相,或者说两种面相是如何并存的,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一)两种论断的偏颇
在马克斯·韦伯的类型概念和理论体系下,“卡迪司法”是脱离形式化的法律及司法程序而诉诸法外因素进行个案裁量,不具有确定性。在此一意义上,中国传统司法确实不注重严格依法裁判和程序正义,而具有恣意性。马克斯·韦伯无疑揭示了中国传统司法的部分特征*已有学者指出“韦伯关于中国传统司法属于‘卡迪司法’的判断直接针对的对象是中国的帝王”。参见高鸿钧:《无话可说与有话可说之间——评张伟仁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但有将中国传统司法简单化、类型化的嫌疑。不注重依法裁判,并不意味着“恣意专断”,更不意味着裁判的“非理性”。而且“卡迪司法”的论断无法解释传统中国大量案件是依法裁判的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
而黄宗智等人的研究亦有问题。一是其所使用的档案材料本身即是一种“表达”,是一种“建构”*学界对于传统司法档案的真实性问题亦有所认识。徐忠明通过对清代同治十三年广东罗定州发生的“梁宽杀妻案”刑科题本与本案初审官员杜凤治所写的相关日记的对比,发现刑科题本中存在比较明显的虚构,得出了“司法档案当中存在制作乃至虚构的成分”的结论,并提醒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在研究司法档案时,必须保持应有的批判态度,留意其中可能存在的制作或虚构。参见徐忠明:《台前与幕后:一起清代命案的真相》,《法学家》2013年第1期。,司法官不会将自己的恣意专断堂而皇之地书写下来,故经由官方制作的档案资料不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传统司法的面貌;二是其研究建立在韦伯的概念体系之上*对此,黄宗智并不否认,他所要做的恰是要用西方的学术术语刻画清代的司法特征,从马克斯·韦伯观点出发,引申“实体理性”这一概念对清代的法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亦有学者指出,黄宗智对韦伯的概念多有推演,而离开了韦伯概念范畴的原意。参见林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卡迪审判”或“第三领域”——韦伯与黄宗智的比较》,载于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西法律传统(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452页。,并用是否“依法判决”来衡量中国传统司法,无论其得出的统计数据如何,都难以抓住传统司法的实质。另外,邓建鹏对黄岩诉讼档案的研究则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档案表明,尽管《大清律例》对违法行为明文规定给予惩处,但这些法律在基层社会很少甚至没有得到遵照、执行”[56]。这也说明,传统司法面相之复杂,不可简单用是否“依法判决”来判定其性质。更为关键的是表面上依法作出的判决,完全有可能是恣意专断*可参阅本部分后文所列举的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中记载的吏员设计陷害吴青华一案。。
关于中国传统司法“恣意专断”及“依法判决”的两个论断都是建基于同一套概念体系和价值标准之上,即“形式理性”。但在根本上,依法判决并非传统司法的惟一和最高价值,不是判断中国传统司法正当(或公正)与否的惟一标准,甚至不是主要标准。质言之,用是否符合形式理性来评判中国传统司法是不恰当的,也是无效的。支撑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显然是另一种逻辑和理念。
(二)个性司法的逻辑
传统中国虽然建立了科层官僚体制,但它的治理仍然是“诗意”的人治。整个国家的治理依靠“在精神上尊奉一套共同价值准则的文官集团”[57]。富有文人情怀和圣人理想的帝国官员,肆意挥洒着自己的才情,实现着“为官一任,平治一方”的政治理想。世袭的专制君主高高在上垂拱而治,他的臣僚只要不违背正统意识形态和基本的统治底线,尽可各显其能、各行其是。具体到司法制度,中国传统司法追求具体案件的妥当处理和社会秩序的有序良好。它不排斥个性人物的出现,关键是个性的内容应是大公无私、嫉恶如仇等正面品质;它不拒斥个性司法行为,但应与司法的社会治理目的相合。若将个性司法行为与传统司法目标进行对接,用“手段——目的”的互动、契合关系来审视个性司法,则传统司法的目标决定了个性司法,而个性司法亦在一定的“目的”框架下进行。这使得传统司法表现出合目的性的一面,保证了司法行为的大体稳定和基本取向。
首先,传统司法所追求的个案妥当处理本身即不要求统一的形式化法制。完美司法的终极状态是“揆之天理而安,推之人情而准,比之国家律法而无毫厘之出入”*光绪丙午年(1906年)武进李氏圣译楼刊《徐雨峰中丞勘语》。参见陈全伦、毕可娟、吕晓东主编:《徐公谳词》,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689页。。律法在整个规范位阶上并不是第一位的,所谓“善折狱者,斟酌于天理人情,然后衡之以律例”[58]。律法之外尚有天理与人情。天理、人情合称为“情理”,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公众内心中的、无法形式化的一种“价值观念”或“衡平感觉”[59]。天理始终高于律法,律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天理。律法与人情出现冲突时,律法不妨稍措而全人情。司法要达致“天理、国法、人情”的完美融合,让个案的每个当事人心悦诚服,实现社会关系的妥善安排,是一门高超的艺术。艺术只能由人来完成,并且呼唤个性。它为司法主体提供了“画笔”“画布”,并规定了一些基本的“技法”。但也给司法主体个性的挥洒留有空间,将个案解决妥当与否交由司法者进行判断,允许司法主体个人良心的出场和发挥作用。在意识形态式的情感直觉、个体自具的司法经验及能力以及形式合法性的限制共同作用下,由司法者绘就了每一幅判决的最终“画面”。这些画面流淌着活生生的个人情感,蕴藏着独具一格的个人特色。理想的个性司法并不必然违法,更与恣意专断无关。
其次,作为一种治理手段的司法服务于更高的价值目标——社会的有效治理。“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如同烹菜需要掌握火候,治国同样需要拿捏好分寸,经权并用。这是一门高超的技艺,需要治理者的智慧和才能。“古典中国法律根本特点还是旨在‘平衡’社会秩序,如何实现社会管理,乃是首要任务”[60],司法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是君主授予各级管理者的权柄。如何在治理目标之下,灵活运用司法权,发挥最大功效,则取决于司法主体个人。正是在这样的授权和目标框架下,“康三板”“甘八百”式司法者的行为,不仅不是违法乱制,反而是为政有方:宽大者,以仁恕化民;苛刻者,以刑威惩恶。但他们的个性司法行为尚属低层次的,僵硬而呆板。满腹才情的张船山,不仅判词文采飞扬,裁判精妙,且正风化、匡人心,显然技高一筹。虽然他们的个性司法行为没有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司法程序,看似“恣意专断”,但都没有脱离治理目标,仍具有其妥当性、合理性。因此,也就为君上所允许,自然也为律法所默认。而普通民众更是呼唤“包青天式”司法主体的出现,对那些能够为民请命、惩恶扬善的清官循吏赞美有加。
再次,中国传统司法不仅反对司法主体的恣意妄为,而且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司法主体的个性有一套规制机制。传统司法对司法官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并极力塑造个性良好的司法主体。所谓“非佞折狱,惟良折狱”(《尚书·吕刑》),仁、公、明、廉、勤、慎等品格是“良”的内在要求。“惟温良忠厚之长者,乃能折狱也”[61],仁为政本,亲民、爱民之心是治民者的首要素质。审判不能放任一己之喜好和情绪,“任喜怒,则不能公”[62],“讯狱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63],为听讼之要道。司法官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听讼宜静,明由静生,未有不静而能明者”[64],“听讼要平心静气”[65],要“忍性气”“戒躁怒”[66]。这种塑造普遍良好个性其本身可保持司法大体上公正、妥当的常态,如果司法主体的个性司法行为所根据的信念和情感是普遍的、公理性的,那么司法裁判的结局并不可怕。
(三)个性司法之失
当然,传统中国司法也为这样的品性和追求付出了代价:一是司法运行之良窳系于司法主体之个性而不具确定性;二是规制的无力及失效所导致的任性司法;三是偏重治理目的的达成而忽视手段的正当性。
中国传统司法主体并非专业化的职业法律人。经由科举考试选拔而来的官员,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司法训练,对司法审判而言是十足的“外行”*传统中国并没有正规、专门的法学教育。科举考试虽试策论,但对应试者法律知识的要求极低。法律知识的获取途径基本依靠学徒式的私相授受及司法实践中的自学历练。具体可参见张伟仁在《清代的法学教育》一文中的讨论。参见张伟仁:《磨镜——法学教育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清代律学被视为俗学,“今人于会典、通礼、律例等书视为俗学”,可见法律之不受重视及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地位之低。参见[清]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1页。。由非专业的外行来进行复杂案件的处理,没有专业知识及职业素质的指导和保障,司法主体的个性因素就在司法活动中格外彰显,案件裁判结局就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主体的情感喜好、阅历经验、是非观念及断案能力等。个人天资聪慧、能力高超者,如清代名吏徐士林“听断精敏,无不得之情”,“及其得之心而应之手,落笔数千言。析疑疏滞,如见如绘;批隙导窾,无不迎刃而解”[67],自然胜任愉快,成为“包青天式”的断案能手。但昏庸、糊涂者亦所在多有,晚清能吏端方在判词中责备下级官员“折狱糊涂”,甚至大骂“混帐东西”[68],更有不晓律例却刚愎自用者,樊增祥即言“近来不通刑名办案,专以颟顸笼统,自诩空灵”[69],殊难求其辩驳明白、情法两平。
律法虽明令断案须援引律例,但实际上未能得到有效遵行。雍正十年(1732年),大学士张廷玉上疏称:“《律例》之文,各有本旨,而刑部引用之时,往往删去前后文词,摘中间数语,即以所断之罪承之。甚至有求其仿佛而比照定拟者”[70]。司法主体并不严格依法为判,妄引条文,避重就轻或避轻就重,自主空间很大。结果,司员藉以营私,吏书高下其手。作为中央法司的刑部尚且如此,可以想知其他司法衙门的情形。汪辉祖亦言“一二年间(乾隆四十六、四十七年,公元1781、1782年——笔者注),风气顿易,律例几不可凭”[71]。律例被弃之一旁,剩下的只能是司法主体的任性司法、恣意专断。
内部监督的约束和规制在遭遇群体性、“抱团式”的“官官相护”时,无疑遭遇失败。清代督抚俨然一方诸侯,手握地方最高统治权,蒙蔽于上,勾结于下,案件如何处断,全任其一己之意愿,个性肆行。人在下位之时,尚有友朋之规益,上司之责让。但一旦居于上位,则下位之人不敢进言,无人规劝。若更上位之人亦昏庸糊涂,甚至沆瀣一气,或者鞭长莫及,或者遭受蒙蔽,那么制度系统内部的监督也就宣告无效。制度上的约束尚告无效,思想层面的规制对于部分司法主体而言更无效力。他们或披着道德的外衣,谋一己之私利,或惑于因果之说,故为宽纵,皆与司法公正有损。
司法主体的自主司法权,因缺少必要的程序予以监督规制,往往为个性左右,导致实质上不公正的结果。甚至为求取治理目的而不惜滥用、不当行使司法权。前举黄六鸿重杖赵某案中,黄六鸿惩治贪腐的初衷并不错,但在手段上出现偏差。为追求一正当目的,却为躁怒之情绪左右,结果夺人性命,不可不谓为个性司法之失。
更有以司法权行非法事,为实现所谓的“治理目标”而不择手段者。乾隆年间,浙江乌程举人吴青华靠“吃漕饭”为生*官府征收漕粮时多有浮额,于是有狡黠者以向上级衙门告诉为要挟,官府为平息事端遂令司漕吏给要挟者以金钱,进行收买。此种人的生活费来源于漕粮,故曰“吃漕饭”。,且是众吃漕饭者之首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将开征漕粮,吏员设计陷害吴青华。先将他灌醉,再诱其进入妓院。青华甫一入,娼女即大喊“强奸”。官吏之党伙潜伏四周,佯为邻佑,一拥而上,将其扭送县衙。结果:
令素愎,且有成见,乘青华醉不省事,录供系狱。次早覆讯,青华不承,令白太守。太守尤酷烈,立提亲勘,以妓与邻佑为证,批其颊,威以三木。青华遂诬服,从重外遣[72]。
汪辉祖在乌程为幕时,县令蒋志铎即欲惩办吴青华,但因吴青华无其他可入罪之行状,被汪制止。一旦治者易人,吴青华随即遭殃。吴青华要挟官府,吃漕饭为生,殊非正当。但官府多征少报漕粮的行为亦不正当,而为处理“碍脚石”竟然不惜使诈、设圈套,可谓卑鄙无耻之极。县令固执一己之偏见,有意入罪,太守酷烈成性,将冤案办成“铁案”。司法权被不正当利用,一套司法程序充当了实现私利的工具。个性使然乎?制度使然乎?不完善的制度为不肖之人利用,传统司法难免“恣意专断”!
五、结语:个性与司法的契合之道
西方政治思想中,人天生具有“恶性”,是靠不住的。政治制度应依靠形式理性的法律来组织和运行,完全排除人的个性因素的影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73],而法律正是“免受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74],主张完全没有感情的法律之治。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则系统地排除人的因素,包括人的感情、情绪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成分,“旧式统治者常常受同情、宠爱、慈悲、感激等感情的支配,而取代他们的现代文化为维持其外在机构,则需要不受感情驱使的、绝对‘专业化’的专家”[75]。人的个性与制度是对立排斥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讲究规则之治,排斥司法主体的主观任意和反复无常,个性在其中没有存在的空间。确实,如果像法律现实主义所言的“法律规则根本不是法官判决的基础,司法判决是由情绪、直觉的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理性的因素决定的”[76],“司法裁判与法律判例之间的关系还不及这些裁决与法官的早餐更密切”[77],因早餐好坏而带来的情绪左右审判,司法裁判的结局将陷入全然的不可知。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个性与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实质上是多变的非理性的人与稳定的形式理性的法律之间的冲突。
与西方理性传统下人与制度的必然对立不同,传统中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任人”的,而非“任法”的,相信人性之善,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来实现治理目标,并通过道德观念来维系整个官僚体制的运行。具体到司法而言,司法目标的实现依靠司法主体的积极作为,允许个性司法行为的存在,并注重调和个性与司法,让司法大体呈现出较为稳定的面相,达致个案妥当解决和社会有效治理的完美司法境界。但在具体实践中,中国传统司法往往又陷入这样的悖论:一方面司法目的的达成需要司法主体个性的积极作为,另一方面个性主导司法则又背离了司法的基本价值追求。艺术化的司法追求着个案妥当处理和社会和谐有序的理想画面。但司法主体并不总是素质合格、技法纯熟、遵循套路,以致躁怒、刚愎、残刻等不良个性主导了司法进程及结局。当然,这并不是传统中国司法的全部面相。个性良好的司法者发挥自己的才情、经验、能力,作出合理、合法、合情的判决,也是传统中司法的重要一面。于是,中国传统司法呈现出或恣意专断、或依法裁判的复杂面相。
悖论的出现说明中国传统司法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其目标设定与制度架构并不匹配,较为简约粗疏的制度不能适应过高的司法追求。在司法权的配置上赋予司法主体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但相应的司法程序、监督机制却较为粗疏或宣告无效,导致司法主体个性的恣意横行。其调和个性与司法的方式——试图通过道德说教塑造稳定、良好司法主体个性,用道德说教代替制度约束,但“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相不可捉摸”[78],难免让非理性因素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从道德、理性堤防的罅隙趁虚而入,背离了最初的司法目的。这种调和的努力虽不够成功,但仍有益于我们对个性与司法关系的思考。
道德说教的力量不能代替制度性约束;但制度的良好运行也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持,甚至可以说再优良的制度也弥补不了道德的缺失。对平衡司法者个性和依法公正裁判而言,良好个性的塑造与必要的制度约束,二者不可偏废。实现司法主体个性与司法制度完美契合的可能途径是:塑造具有普遍价值认同、高素质的合格司法主体,更为重要的是创设完善的司法制度。具体而言,以法律知识和法治精神武装职业司法群体,尽可能培养具有统一法律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的司法主体,让复杂多样的个性趋同为合目的性的“法律个性”,以更好地实现公正司法的目的;对司法主体的个性司法行为进行制度化规制,设置必要的制约、监督程序,让司法尽可能地少受、不受司法主体不良个性之影响。
[1][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122.
[2]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11.
[3]陈景良.宋代司法传统的叙事及其意义——立足于南宋民事审判的考察[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4).
[4]柳立言.南宋的民事裁判:同案同判还是异判[J].中国社会科学,2012,(8).
[5]马小红.“确定性”与中国古代法[J].政法论坛,2009,(1).
[6]胡永恒.从清代视角看中国传统司法的“不确定性”[J].法治论丛,2008,(6).
[7]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77.
[8]张仁善.论传统中国的“性情司法”及其实际效应[J].法学家,2008,(6).
[9][35]张仁善.从司法主体性情取向的养成看中国古代法律预期的不确定性[A].曾宪义.法律文化研究(第4辑)[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68-79,77.
[10]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25.
[11]程继龙.社会学大辞典[Z].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392.
[12]费穗宇,张潘仕.社会心理学辞典[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19.
[13]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心理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11.
[14][15][33][47][69][清]樊增祥.樊山政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499,505,279,279-280,60.
[16][清]邱煌.府判录存[M].卷五.
[17][清]桂超万.宦游纪略[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1辑810).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192.
[18][23]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084,4202.
[19][34]郑秦.清代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9,89.
[20][清]昆冈,李鸿章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卷八五二.
[21][清]方大湜.平平言[M].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
[22][59][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A].[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王亚新,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6,34.
[24][清]蒯德模.吴中判牍[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201-202.
[25][61][63][清]袁守定.图民录[M].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209,194,197-198.
[26][美]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的结构[M].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719.
[2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39.
[28][42][66][清]黄六鸿.福惠全书[M].清光绪十九年文昌会馆刻本.50,52,50、52.
[29][清]汪辉祖.佐治药言[M].张廷骧辑.入幕须知五种.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149-151.
[30][31][39][54][71][72][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17,7,39,9,39,30.
[32][清]张船山.张船山判牍[M].襟霞阁主编.上海:中央书店,1934.1-2.
[36][38][清]薛允升.读例存疑[M].胡星桥,邓又天,点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2,95.
[37][日]寺田浩明.日本的清代司法制度研究与对“法”的理解[A].[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王亚新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20.
[40][清]蒋陈锡.大清律辑注·叙[A].[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上)[C].怀效锋,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
[41][清]聂亦峰.聂亦峰先生为宰公牍[M].聂其杰校刊.1943.60.
[43][49]梁治平.法意与人情[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2,12.
[44][清]陈宏谋.在官法戒录[M].培远堂刻汇印本,清乾隆八年(1743年).21.
[45][清]汪辉祖.学治续说[M].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298.
[46][清]张经田.励治撮要[M].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50.
[48][62][清]李容.司牧宝鉴[M].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3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198,200.
[50]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260.
[51][宋]朱熹.朱子语类[M].[清]张伯行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52.
[52][清]陈宏谋.从政遗规[M].培远堂刻汇印本,清乾隆七年(1742年).11.
[53][清]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M].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8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49.
[55][清]汪辉祖.双节堂庸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131.
[56]邓建鹏.清代州县讼案和基层的司法运作——以黄岩诉讼档案为研究中心[J].法治研究,2007,(5).
[57]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95.
[58][清]薛福成.庸盦笔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73.
[60]徐忠明.案例、故事与明清司法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48.
[64][清]汪辉祖.学治臆说[M].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276.
[65][清]翁传照.书生初见[M].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
[67][清]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M].卷五十.
[68][清]端方.端午桥判牍[M].襟霞阁主编.上海:中央书店,1937.13.
[70][清]张廷玉.请免滥禁慎引律疏[M].[清]贺长龄辑,魏源编次,曹堉校勘.皇朝经世文编.魏源全集(第18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22.
[73][7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63,169.
[75][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论文集[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60-461.
[76][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65.
[77][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M].郭星华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
[78]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77.
责任编辑:程政举
The Mechanism and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Personalized Justice of Traditional China
Li XiangsenRen Jiaying
(LawSchoolofNanjing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3;TrainingDepartment,PL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Jiansu211101)
The rational modern judicial excludes the invasion of judicial personality.But the individualistic behavior of judiciary really exist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justice,and had certain universality.The traditional legal system allowed the individuality of judiciary to play role.The legal character,temperament,ability and personality factors of judiciary directly affect the process and outcome of justice.B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justice is not the individual arbitrary,or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rational factors such as emotional bias of judiciary.The traditional legal system has a regulation mechanism to shape the individuality of judiciary,and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an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judicial behavior.We should shape individuality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justice to eas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ity and the judicial justice.
individuality of judiciary;Khadi Justice;traditional justice;certainty
2015-11-15
本文为张仁善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司法中的理性与经验研究”(11BFX016)的阶段性成果。
李相森(1984—),男,山东昌乐人,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史学;任佳莹(1982—),男,山西阳泉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训练部讲师,研究方向:法律理论、法律文化。
D929
A
2095-3275(2016)03-002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