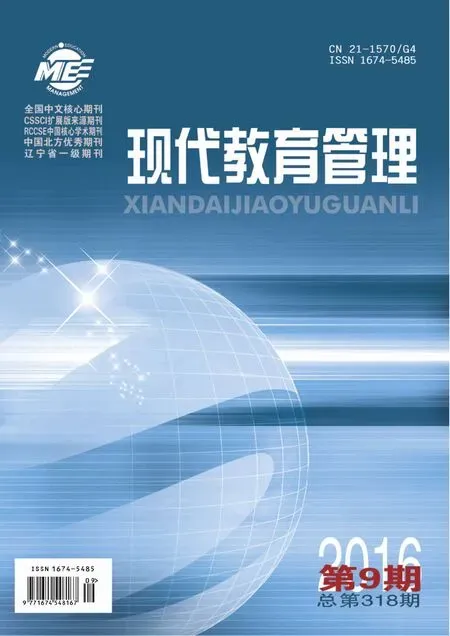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①
2016-03-05陈玥翟月
陈玥,翟月
(1.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710062;2.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陕西西安710100)
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①
陈玥1,翟月2
(1.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710062;2.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陕西西安710100)
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从事比较研究的人员多,专业研究人员少;追求短评快的多,有理论建树的少;启示借鉴的多,起实质作用的少;跟着感觉走的多,注重方法与方法论的少;有学科情结的多,解决问题的少。对此,我们需要正确面对比较教育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在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关注理论研究、夯实方法论等基础上,更好地开展跨国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促进自身研究的科学化。归根结底,着力解决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才是比较教育学科立足的根本所在。
比较教育;比较教育研究;专业化队伍;理论;方法与方法论
近年来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在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比较教育研究在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诸如研究队伍不纯、研究成果肤浅、研究重短评快等方面的问题,这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批评、质疑与争论。因此,我们既要科学地审视我国既往比较教育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也要正视比较教育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既是探究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理论与价值的诉求,同时也是关乎未来比较教育学长久有序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从事比较研究的人员多,专业研究人员少
专业化的研究队伍,不仅是学科知识的重要载体,也是学科组织发展中最能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1]可以说,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对于比较教育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一流学科的建设,甚至一流大学的创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2]当前,比较教育研究的确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其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然而,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许多人都发现,似乎比较教育的“领地”逐渐被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所“侵袭”。教育学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也都做着相关方面的努力,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更好地理解教育,更好地揭示、解释和解决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人员不断增加,但其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个“大杂烩”抑或“兴趣集合体”。
学者方文曾指出:“职业化的研究者,必然栖身于确定的研究机构如大学系科或其他研究机构中,才能开展其研究活动。”[3]近年来,由于比较教育学科常常受到学科身份认同危机的影响,许多比较教育学者并没有像其他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那样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一部分人实际上成了当代外国教育史的专家;另一部分人回到了他们原来从事的学科,不是以比较教育学家的权威而是以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的权威自居;少数人则继续研究方法论问题,埋头钻研比较研究的认识论”。[4]的确,就目前比较教育的现状来看,许多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人员几乎都不愿自诩只是“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甚至有些学者已经从比较教育学科逐渐“漂流”到其他教育学科中。
在很大程度上,这不仅冲淡了比较教育学科的专业性,也使比较教育的学科认同和专业地位受到挑战,尤其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质量产生了重大影响。诚然,我们也欢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参与到比较教育研究中,共同为促进该学科的交流与发展发挥作用。然而,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一套自身的规则和逻辑,比较教育学也不例外。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提升比较教育研究水平,有必要创建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结构合理的专业队伍,使他们能够栖身于专业的研究机构中开展专业化的研究。
二、追求短评快的多,有理论建树的少
在过去的20余年中,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在推动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以及比较教育研究水平的提升方面功不可没,他们较为完备地介绍了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并且引进了许多新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然而,随着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发展、外语水平的提升以及教育改革的推动,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往对外国教育的译介已逐渐不能有效应对教育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克服教育学本身发展所遇到的障碍,妨碍了比较教育的学科创生”。[5]
澳大利亚学者菲利普·E·琼斯(Philip E.Jones)曾指出:“记住这一点是很明智的——比较教育的任何研究重点都是随着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6]因此,对于比较教育研究人员而言,他们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探寻其他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些最新动态和趋势。也正是比较教育学这一显著特征,许多研究者,尤其是一些非专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人员,误认为比较教育研究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就是把国外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做法简单介绍并引进到国内即可,殊不知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也需进行严格的专业训练和大量的知识储备。在国内,比较教育的研究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国外颁布了某项新的教育政策,不久国内便会有诸多研究人员撰文对该项教育政策进行解读,往往都会包括该项政策出台的“背景”、“内容”、“措施”等等。不可否认,此类“研究”是与时代发展同步的,具有很强的前沿特性,对于我们及时了解国外教育改革与发展动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类“研究”能否称作“研究”?能否列入“比较教育专栏”?和其他一些编译类的稿件有何差别?如果比较教育研究纷纷停留于此,其未来发展空间何在?
对于比较教育研究而言,文化因素对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7]从本质上而言,比较教育研究是一种基于文化理解的教育活动。文化理解程度的不同,将会导致研究水平的不同,进而导致研究成果价值的不同。为了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需要研究者深入研究影响该国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以此探寻比较教育领域中那些隐晦的、藏匿于表面之下的因素和力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时应该认识到“跨文化比较教育研究不仅仅是关于两种或更多文化的研究,而且本质上就是跨文化的,因为研究结论不但来自被研究的文化,而且来自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观点”[8]。
就目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现状而言,有理论建树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绝大多数比较教育的研究成果既没有深刻把握国外教育的状况,更没有对本国教育状况有所体认,导致“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事实的呈现或是一种材料的集合或是研究者个人经验层面的一种理解,甚至只是文本翻译,而没有凸显出研究者本人对于事实或材料背后的根源、实质和隐含意义的深度观察和剖析,因而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均受到严重局限”。[9]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三:早期旅行者见闻的角色并没有完全转变;受研究者急功近利心态的影响,过于追求研究的“短”、“评”、“快”;研究者对比较教育的理解偏差。基于此,笔者认为,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需要分清哪些属于研究过程,哪些属于研究。上述提到的那些“背景”、“内容”、“措施”等,只是开展研究的一些资料性准备,充其量只能算作是研究的过程。不可否认,这同样也是开展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它为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重要的是,研究者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那些隐晦的、藏匿于这些资料表面之下的规律、特征、关系等,而非简单地“一译了事”或“话语平移”。
三、启示借鉴的多,起实质作用的少
纵观目前国内学术期刊所发表的一些比较教育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启示借鉴类依然占着“半壁江山”。如前所述,国内许多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人员非常热衷于对国外一些新发布的教育政策进行解读,其中不乏很多文章在最后加一个研究的“尾巴”,即“启示借鉴”。殊不知新颁布的教育政策在国外也属于探索阶段,其未来的实施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那么作为研究者,我们的研究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借鉴的“由头”到底在哪里?国外的教育政策就一定是好的吗?可以说,在纷至沓来的诸多比较教育研究成果中,解决教育改革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且起到实质性作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我们不禁要反思:比较教育研究“繁荣”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我们取得了那么多的研究成果为何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为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比较教育研究有用吗?
造成目前比较教育研究的这种状况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
首先,自比较教育创立之日起,“借鉴”便被视为比较教育研究最主要的目的,试图通过借鉴“以促进本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借鉴是贯穿于比较教育学发展史及研究全过程的重大使命”。[10]类似的许多观点也基本贯穿于各类比较教育学的教材和专著中。如此,“借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人员的一个基本思维和价值取向。尽管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在不断调适和拓展,但“借鉴”仍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其次,服务决策制定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功能,试图通过对不同文化或国家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等方面的深入比较研究,服务于本国教育决策和实践的需要。埃德蒙·金(Admund J.king)曾指出,“教育的比较研究之所以是合法且充满活力的,主要是源于教育决策的需要”。[11]第三,长期受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误认为只要是从西方引进的教育制度就是好的,换言之,西方的教育制度优于我们的教育制度。萨德勒(M.Sadler)曾指出:“认为所有其他国家都拥有比我们更好的教育制度那就大错特错了。认为或暗示一种教育制度可适用于每一个相似国家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能详尽且设身处地研究外国教育制度(详尽性和切身性是完成这项任务所必须的两个特征),我相信这种思索探究的结果一定会使我们获得意外的收获。”[12]许多研究者对国外的教育制度存有一种“顶礼膜拜”抑或“讴歌”的心态,其研究常常缺乏一定的批判与争鸣。第四,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缺乏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认为没有“启示借鉴”的比较教育研究论文是没有意义的,甚至认为没有“启示借鉴”就不能称作是比较教育研究的论文。
如前所述,比较教育是服务教育实践、服务决策制定的。服务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实践中许多研究者却放大了“服务”的内涵,试图为政府部门在教育决策的各个方面“开处方”,其中包括教育经费投入、教育法律法规建设等。需要注意的是,教育决策的制定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因素。毋庸置疑,制定教育决策不是比较教育研究人员的主要任务,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只是政府部门制定教育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作为比较教育的研究人员需要明晰“服务”的内涵,打破以往试图为政府部门“开处方”的藩篱,尽可能地挖掘教育现象背后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扎扎实实地开展一些“真研究”,在夯实自身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决策的制定、服务于教育实践,而非一味地讲求“服务”,一味地“越权”。
四、跟着感觉走的多,注重方法与方法论的少
方法与方法论的进步对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常对其反思也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方法与方法论是一种交互式作用的关系,学界对二者的关系问题也有不少讨论,有学者曾做过这样一个较为形象的比方:“方法就如同是路(road),而方法论是道(way),每走一条路(road)就能为道(way)的拓展提供帮助,而且way也须经过road的经验验证,但仅由road是生不出way的,合在一起才叫真正的道路。”[13]可以说,该比方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何为方法、何为方法论具有重要的作用。就比较教育而言,其研究方法更多的是指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的途径、方式、方法和手段,而方法论则是关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态度。
纵观比较教育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比较教育方法与方法论的问题历来是比较教育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然而,不管是对比较教育学科理论的探讨,还是对比较教育学科下定义,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现出“方法与方法论”的倾向。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学者们从方法的角度来界定比较教育这门学科。从客观上来讲,这不仅反映出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对于一门学科的重要性,而且也揭示出方法与方法论问题是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中一直存在的问题。
比较本身就应该是比较教育的方法论自觉,带着清晰的比较意识去考察教育问题,如果失去比较,比较教育则可能会被窄化成外国教育现状调查。[14]然而,从目前比较教育学所呈现和交流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并非是通过扎实可靠的方法与方法论来获得的,就其本质而言仍属于“信息提供型”的外国教育报道。马骥雄先生曾指出:“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现状看,方法问题是个关键问题。不用一定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处理,就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比较。抓住国外一点什么,翻译介绍一番,最后总说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有‘借鉴’意义,这并不是比较研究。”[15]的确,目前许多比较教育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跟着感觉走”。然而,作为比较教育学者也应该不断反思,我们常常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来不断促进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但是比较教育学科又能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哪些理论和方法呢?若仅仅停留于表面,必将对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因此,不论我们能够从其他学科学到多少,比较教育学科也应该守住自身的“精神内核”,并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在实现自身“科学化”的进程中证明其存在的价值。
五、有学科情结的多,解决问题的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比较教育是作为教育科学中的一个“工种”而非“学科”被“重新”建立起来的,它主要承担的是搜集国外教育信息和追踪国际教育改革发展动态的任务,而不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任务。[16]伴随着我国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且日渐成熟,尽管如此,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毋庸讳言,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中的问题不仅有学科自身长期未解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因社会变革所衍生出的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对“比较教育是什么”没有达成共识,仍存诸多争论。其中,争论的焦点当属比较教育究竟是一门“学科”抑或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说,这一争论自比较教育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时至今日依然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这不仅反映出比较教育学科未来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也昭示着比较教育研究的“学科情结”,学者们在不断争取和证明比较教育学科的合法性与科学性的路上努力着。龚放教授认为:“‘学科还是领域’的提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将‘学科’与‘领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相互关联、密切关联的。因为‘学科’其实就是科学研究的某一领域,就是知识系统的某一领域;科学研究一定是在某一领域或者某些领域中进行,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拓展到一定广度,成果积累到一定阶段,形成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就被人们称为‘学科’”。[17]比较教育存有学科情结是好的,可以使比较教育学者更好地找准自己的位置和归属,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人员而言,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一是借鉴他国经验,解决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二是探索和完善比较教育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增强学科知识谱系的建设。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比较教育研究在解决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有相关的理论创新和知识贡献,对于提升比较教育学科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及研究水平都不无裨益。
事实上,比较教育学科之所以会引起内外部各方面的争论,其处境绝大部分是由于比较教育学者自己造成的。他们试图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因此也在不断地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地”,不断地更换自身的称谓,从“外国教育”到“国际教育”、“比较教育”、“国际与比较教育”等等。这一系列的努力,的确反映出比较教育学科的大力发展以及比较教育学者的开拓精神,其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比较教育学科的特色渐趋丧失,学科的边界也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在教育学科领域,“通才”其实是有一定限度的,尤其步入新世纪,在知识以及信息技术不断更新的大背景下,试图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的梦想基本上是不能企及的。
顾明远先生曾指出,比较教育学者首先不是去纠缠比较教育是什么的争论,而是要从切切实实研究当代世界教育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当中,找到关于比较教育自身问题的答案。[18]由此,笔者认为,如果我们长期纠结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不仅没有抓住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而且无益于比较教育学科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作为比较教育的研究人员,应该切切实实地做一些“真研究”,真真正正地解决一些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不需要去自我证明,而是要拿出高质量的、不可替代的研究成果让这一争论“不攻自破”。因此,当下比较教育研究应该立足于“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和原则”。[19]
六、结语
透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比较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既有专业队伍方面的,又有理论、方法与方法论方面的,可以说这些都是比较教育研究中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朱利安曾经设想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性的科学”,他认为,“就解剖而作比较解剖的研究,终于促进解剖而使之成为一门科学。同样,作比较教育的研究也必然能为教育的完善而成为科学,提供一些新的手段”。[20]从此意义上来讲,在未来的发展中,比较教育也应该树立起学科的自信,为实现比较教育学科的“科学化”而不断努力。
不断强化学科的专业队伍建设,对于比较教育学科,乃至整个教育学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毋庸置疑,目前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人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外语出身的,他们利用语言优势在早期为我国引入和翻译了一大批国外的教育制度,其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随着外语的普及以及全球化、国际化的不断推动,单纯靠语言优势来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比较教育专业学者们致力于比较教育的研究,继而推动整个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以及研究水平的提升。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比较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与方法论建设,从而推动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科学化”,使比较教育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基于扎实可靠的理论和方法的,而不再具有可替代性,不再是以往外国教育信息的“改良版本”。
比较教育常常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因素对比较教育研究的重大影响是不容轻视的,因为它更多是隐晦的、藏匿于表面之下的,有待研究者去不断发觉和探究,所以其影响也是最深刻和最持久的。基于此,比较教育研究人员需在跨国、跨文化的视角下,不断深入开展比较教育研究工作,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教育实践,为我国的教育决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但在这里还需指出的是,既然比较教育要服务于决策需要,那么首先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产生大家都能利用的‘知识’”[21]上。事实上,比较教育也应该注重学科知识谱系的建设,追求知识不仅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比较教育证明和突显自身价值的理由所在。作为比较教育研究人员,怀揣着学科情结是不断推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研究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比较教育学科不断证明自身合法性与科学性的重要表征。然而,我们更要追问的是研究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归根结底,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才是比较教育研究应该考量和关注的,这也是比较教育学科立足的根本所在。
[1]马健生,陈玥.论中国比较教育的重生——基于学科制度结构的视角[J].比较教育研究,2015,(9):38-47.
[2][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23.
[3]方文.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
[4][英]霍尔斯.文化与教育:比较研究的文化主义方法[A].赵中建,顾建民.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C].顾建民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19.
[5][14]陈玥,余庆.论比较教育研究的五重路向[J].外国教育研究,2014,(2):28-35.
[6][澳]菲利普·E·琼斯.比较教育:目的与方法[M].王晓明等译.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11.
[7]Cowen,R.&Kazamias,A.M.Ⅰ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M].Netherlands:Springer,2009:124.
[8][英]贝磊,[英]鲍勃,[南非]梅森.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M].李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8.
[9]马健生,陈玥.论比较教育研究的四重境界——兼谈比较教育的危机[J].比较教育研究,2013,(7):56-61.
[10]冯增俊,陈时见,项贤明.当代比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5.
[11]Admund J.King.Comparative Studies and Educational Decision[M].London,Methuen andⅠ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8:93.
[12][英]萨德勒.我们从对外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多少有实际价值的东西?[A].赵中建,顾建民.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C].开振南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19.
[13]余庆.论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情境生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1):25-30.
[15]马骥雄.比较教育学科的重建[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8,(5):60-63.
[16]项贤明.从比较教育走向比较教育学[J].全球教育展望,2013,(9):3-10.
[17]龚放.追问研究本意纾解“学科情结”[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4):41-48.
[18]顾明远.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及出路[J].比较教育研究,2003,(7):1-4.
[19]Kandel,Ⅰ.Education Yearbook 1939[M]. New York:ⅠnternationalⅠ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1939:436.
[20][法]朱利安.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A]赵中建,顾建民.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01.
[21]P.G.Altbach&G.P.Kelly(eds.).New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323.
(责任编辑:徐治中;责任校对:赵晓梅)
An Exploration of Several Issues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CHEN Yue1,ZHAI Yue2
(1.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062;2.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100)
At present,there have some problems in our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which are mainly embodied in five aspects:more people conducting comparative research,but less belongings to the professionals;more research are eager for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but less in theoretical accomplishiment;more research focus on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but less worked;more research go with the flow,but less focus on methods and methodology;more research possess sentiments of discipline,but less to solve the problem.To this issue,we need to face th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orrectly.On the foundation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team,focusing on the theory studies,consolidating methodology basis,ect.,we can well develop trans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scientification of our research.All in all,to solve important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s the foundamental purpos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education;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professional team;theory;method and methodology
G40-059.3
A
1674-5485(2016)09-0112-06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国家青年课题“中美研究型大学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比较研究”(CDA150129)。
陈玥(1984-),男,陕西周至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翟月(1984-),女,辽宁大连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