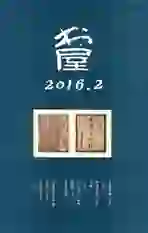风托霓裳泪沾襟(五)
2016-03-04韩秀
1997年初,夏公在纽约也极忙,甚至为郑培凯与李安的电影座谈会作总结,夏先生热爱电影,他的一番话大约和别人的意见大不相同。同时,他又在《联合文学》月刊上发表张爱玲给他的信件。这些信件真是说不得的凄惨,我看到了忍不住大哭,遂写了信到纽约去,啰啰嗦嗦说了许久。
8月下旬,夏公的信到了。
亲爱的韩秀:
看到7/15的大函,应该才七月下旬,知道您看了张爱玲的信件,“忍不住大哭”,我也极为感动。当时即想写封信给你,但还是迟至今日,望你能原谅。自从为张函作编注工作开端,每月我要花两星期的时间在project上,交出一篇后,人太累了,就不想再写信,所以这几个月,积信甚多。最近这一个月,身体似比以前好些,所以赶快多写些回信。到了九月一日,又得为张先生再编出一个书信续篇了。
爱玲来美前一无准备,吃了大亏。至少她得多有些积蓄,才能为自己作更妥善的安排。凭翻译——写稿养活自己,是最累的事。她应该迟两年来美国,先在HK凭写稿、编剧多赚些钱。她对女子服装设计最有兴趣,也有天才。如来纽约后即在Fashion Institute读一两年书,拿一个degree,从此日里凭此项工作养活自己,either在公司做事,or有野心的话,自己创业,更可成大名,赚大钱。这样身体转好,心境转好,晚上多的是写作的时间。画妇女的服装,对她来说,应该是最有趣,最relaxing的工作。这样介入了美国的生活,她可以继续不断的写作。有了自信心,也就不必专写上海那一段生活了。当然爱玲孤独惯了,在学校里要同老师、同学接触,可能也不习惯。我的朋友间,卢飞白(早死的英文学Ph.D)太太在fabric上画图,亲戚间也有来自台湾的女子作这方面的工作。Vera Wang为新娘做bridal gown,已算是纽约第一家了。
你们去希腊后,也到埃及、Austria等地方游览过,很羡慕你们的福气。写埃及之文,不知在何处发表。《联合报》航空版早已不寄给我了——自己文章实在太少,也不能怪他们。二残刚返Madison,在Wisconsin教了一学期书,大概即要退休,再回HK当Dean去……他原是HK孤儿,能有机会在港当Dean,自感心满意足。董桥在“明月”当主编的时候,我同他通信很多(他的毛笔字实在秀气),我想他跟定金庸,是不会离开香港的。胡菊人、戴天他们到哪里去了?凭写作维持生活也很不容易。
我有个邻居叫Ellen Shire,她的父母兄妹两代都是艺术家,musicians。Ellen原先跟Balarchine学ballet,未成大名,后来专为儿童写书,近十多年来则专心画画,画的是抽象画,受Rothko的影响最深。前几年每个暑假她都到德国去作画,今年夏天她在一个希腊小岛。她临走前,我打了个电话给她,说她如去Athens,可见见你们。现已暑期末梢,她如未来找你,也就算了。想起你帮了Marlene多大的忙,Ellen临走前我才想起你。但Ellen这两年的作品并无新意,在美国抽象画也已不走红,她的前途很难往好看。
Andrew在Athens,想大开眼界,很开心。Jeff工作忙碌,请代问好。
张的信件已经载了五期。《联文》反正迟早你能看到,也不另寄了。祝
俪安
志清 1997年8月21日
8月28日我收到来信的当天,便写回信给夏公,并寄上小文《尼罗河抒怀》,这篇文字1997年7月18日到24日在台北《青年日报》副刊连载了一周。1998年2月27日到3月3日又在美国《世界日报》副刊连载了五天,最后收到了散文集《风景》里。
1998年3月中旬,夏公的信来了。
韩秀:
昨天刚重看了你给我的卡片,今天桌子上只见信封,卡片却找不到了。桌面太乱永远是没有办法的事。原定是要在昨天给你写信的,但已近傍晚,人有些累了,就不写了,今天续写。香港之行,又让你见到不少文友,应该是很高兴的事。二残在他潦草的英文信上还提到你一笔,问我一声手指开刀后想一切正常。
谢谢您在卡片上提及“中副”为我出专号的事。看了你写我的那篇好文章后,有一天,王海龙来我家,顺便也把他那篇谈我的文章带来了。我原想不管事的,看了他那篇却很生气,文章里factual errors实在太多,而且他不表明他同我的关系,不负责的乱捧乱吹,看来非常embarrassing,只好叫林黛嫚不用这一篇(除非revise后我认为可用),另请白先勇写一篇讲《中国古典小说》的,因为大文已把《现代小说史》的功用讲得很透彻了。隔了两天,我觉得应叫於梨华、陈若曦这两位老友也各写一篇——自己年纪大了,她们现在不写,下一次写可能就是纪念我的文章,而我自己反看不到了。白、於都已有书信、电话来,表示要好好写一篇。Lucy在台北,我想也一定会写的。上次余光中的专号连登两期;这次我的可能要出三期。但Why not?《中央日报》一直销路不畅,这三期有你,有绍铭、先勇、若曦、梨华四位红作家、大作家,再加上一篇访问,梅新泉下有知,一定也会很高兴的。林黛嫚因此更受重视也说不定。对我自己来说,哥大有了一次退休集会之后,等于台北也举行了一次,虽然我已七八年没有回去了。
告诉你这项消息,不想把此页写满,因为还有别的信要写。我身体维持现状,不能多工作,但也无退化的迹象。你同Jeff听了应该放心。上星期王蒙夫妇从Conn州Hartford Trinity College来访纽约的朋友,我也在大上海那次宴会上见到了陈小莹,她是凌叔华、陈西滢的女儿。我初次见到她,你在北京,想一定早同她见过了。
祝
俪安 笔健
志清 1998年3月10日
孩子身壮如小牛(借用沈伯伯的笔调)
Conn是很传统的Connecticut的缩写,现在几乎没有人懂得怎样使用了。Jeff在康州长大,看夏公这样写,感觉离夏公更近了,十分高兴。
这封来信,我摊在书桌上,看了好几遍,心里却非常的不舒服。很明显,夏先生写这封信的时候,心里是极不痛快的。他努力地压制着火气,尽量地转移话题,但是王海龙带给他的不愉快,实在是太清楚了。
究竟是哪篇文章让夏公如此的不开心?
很奇怪的,在信夹里保存着的王海龙的文章只得一篇,是分为上、下两部分于1997年2月23日及3月2日刊登在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上的《谈夏志清与钱钟书》。这篇文章真的不能算好,也确实如夏先生所说,王完全没有谈及他个人与夏先生的关系,恐怕既非学生也非朋友。关于钱先生未完成的小说《百合心》一案,王说:“夏志清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百合心》中途而废的原因远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夏先生还分析给他听,为何不是那么简单,字里行间便有着两人促膝谈心、交情匪浅的意味在里面,这很可能让夏先生极不舒服,这当然是王的不知深浅造成的。这篇文章里也有许多废话、许多完全没有必要的东拉西扯,连苏小小的故事都被提到。如此非简洁,自然不是夏先生喜欢的。但是,通篇文字倒还不至于让夏先生觉得丢人,觉得错误百出地让他忿恨。更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里还嵌入了夏先生与钱先生1979年在哥大的合影以及钱先生给夏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曾经让夏公感觉非常舒服。所以,让夏公如此气恼的应该不是这篇文章。
从时间上推测,让夏公生气的大约是那篇《赤子心·老顽童·夏志清》。这样的题目本身就不太像样,而且,这篇文章早在1998年1月就已经收进了王海龙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哥大与现代中国》中。如果此一推测正确,1998年1月已经出版的文字在3月以前是不可能征求夏先生意见、善加修正的。“不想管事”、不愿意得罪人的夏先生忍无可忍,还是跟黛嫚说了王海龙的文章不能用,除非改到令他满意为止,于是“大师篇”里便没有王的文字。四位红作家、大作家也只得三位的好文章,没有见到白先生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宏文,好在罗茵芬的特稿《文学·思想·智慧——西方汉学重镇的掌舵人夏志清》非常详实地全面介绍了夏公的学术成就,《中国古典小说》这本重要的书当然也没有遗漏。郭琼森的访问记也是中肯、诚挚的好文章,不太像一般的纪实文字,郭先生个人的气质、学养、用情至深使这篇专访简洁、细腻而精彩。
其中,我有幸先睹为快的是刘绍铭先生的文章,刘先生在1998年1月20日寄了给我。此时,刘先生已经用计算机写作,文章的题目叫做《我所认识的夏志清先生》,在“大师篇”刊出时才更名为《可怜读书人》。文章盛赞夏公学术成就,“今天在美国研究中国小说的‘汉学家’,不论师出哪一名门,都不得不承认志清先生当年在这门功课上给他们立下的开天辟地功劳,至于我自己和王德威这类后辈,一直受先生的指引提携,感激之情,更是一言难尽了”。文章亦对现下文学批评之不重文本、专门钻牛角尖提出了意见,深刻而不失诙谐。
《智慧的薪传——大师篇·第三卷》这本书藏在我的书架上很多年,不知多少次,我的眼睛从书脊上看过去,我的手却没有伸出去,将这本书再一次打开来看,原因却是梨华大姐那一篇《C.T.二三事》。身为夏府的老友,身为知情人,这篇文章将夏先生与师母的锥心之痛写得十分清楚,我只读了一次,印象已然非常非常深刻,以致不忍再读。在夏公与我有限的交往中,他从未提起过他那位美丽而病弱的女儿。张爱玲给夏公的信,总是问候夏府一家三口。我的信却总是只问候夏公伉俪,虽然我早已听闻夏家的不幸。但我觉得,身为晚辈没有权利提到这件事情。这个不幸是身为父亲的夏先生最最痛心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去碰触,直到日后夏公主动告诉我Natalie的近况,我才在见面的时候,在信中问候一声。我也从来不提自己家里的事,不提我对“父亲”这样一个角色深切的渴望与强烈的感受,那是我今生今世无法规避的失落与痛楚。夏公绝对没有任何必要由此而引发联想,加深他自己已然十分痛切的忧伤。他喜欢我的儿子Andrew,常常问长问短。孩子非常好,但我知道分寸,与夏公谈到儿子总是淡淡的,谈到父子之间的趣事更是避重就轻,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
1997年“双十”,我们失去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梅新先生。在我与夏公的来往信件中,总是谈到他,谈到“中副”的朋友们。在回忆与现实生活中,梅先生总是和我们在一道,在我们的心里也总是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梅夫人张素贞教授不但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者,也是现代小说的研究者。九十年代初,在台北东大连续出版《细读现代小说》、《续读现代小说》。1998年5月,素贞大姐寄我《张爱玲世界的深度导引》,评析的是大陆作家余斌的《张爱玲传》。我把这篇文章影印,并寄给了夏公。在回信中,夏公提到大陆出版的张爱玲传记,指的就是这本书。素贞大姐的这篇文章收在2001年九歌出版的《现代小说启事》中。
关于连登三期的“大师篇”则还有下文,1998年6月17日,夏公的信抵达雅典。
亲爱的韩秀:
近信少说有三封,知道你七月即要返美,也就不写一封地道的回信了。返美度假,盼望你们全家再来一趟纽约,有时间同你多谈谈。这封信主要谢谢您寄我的两期“中副”和董桥谈我改张英文的一篇短文。此文我极喜欢,董桥当《明报月刊》主编,我同他的确通信很勤。他珍惜我的信,其实他写的毛笔信,更值得珍惜,虽然大半来信都用ball pen或钢笔写的。(大陆流行的“圆珠笔”其实是“原子笔”的改写。胜利后上海人“学重庆人”称之为“原子笔”。)耀群也已把《端木与萧红》寄我了,还来不及看。我算是端木研讨会海外发起人之一,当然不会去,也得在开会前给耀群嫂一封信。我喜欢端木一家人(包括女儿在内),希望这次大会,端木的名誉可以得到rehabilitation,耀群也给人承认是位作家,真把《曹雪芹》写完。
大陆出的《张爱玲传》我尚未看到,想哥大早已备置了。两三星期前我要同林黛嫚联络,office电话总无人接。后来灵机一动,打电话给张素贞。她虽不在,却有留话的设备。翌日黛嫚自己就打电话来了。信到时,你可能已看到了“中副”上有关我的专辑了。谢谢你特为此辑写了一篇,后来我自己请了陈、白、于三友。我给Lucy的信,信封上把“一段”写成了“两段”,结果隔了一个月她才收到,她听从林的话,写了一千字;于写了四千字;白写了一万三四千字,专讲《中国古典小说》此书。正好我要为此书出台版,故白文搁着不用,出书前再刊出。北京大学陈平原也要为该书出大陆版(安徽版把版权让给北大了),此文更可在北京刊出。我自己也要写篇新序,待张爱玲信件全部刊出之后。
Jeff一年来辛苦了,想为国家办了不少要事。Andrew有没有学古or今的希腊文?想你自己忙于写作、看书,生活很好。
祝
旅安
志清 1998年6月12日
收到信,马上再次翻开董桥先生新书《英华沉浮录——给自己的笔进补》,找到《夏志清改张爱玲的英文》这一篇,读得津津有味。
6月18日,我将完整的“中副”《大师篇——夏志清专辑》寄到香港给董桥先生,同时谈了一点读书心得。
我与董桥先生相识于1995年初。台北艺术家侯吉谅带我到埔里去看望他的老师江兆申先生,也见到了温柔娴静的江师母。江先生字、画、印都好得不得了,在埔里,对着墙上悬挂着的字,我感动得无以名之。江先生为人非常的谦和、非常的温暖,甚至准备了精美的作品集送给我做礼物,让我非常感动。在此之前,1994年6月,高雄美术馆制作了一个册页,是江先生录的《凤山县令曹瑾判沈氏兄弟辞并诗》。题跋处,江先生这样说:“此文规风励俗,大有益于人心,虽辞藻不求高骏,固自可传。”这本册子制作得不够好,用心却是极好的,更不消说,字更是极敦厚的,那是我保存的江先生最早的一本字,时时翻看,感情很深。这一天在埔里,我面对着江先生,面对着他的字,便情不自禁地想到溥雪斋先生,心里翻江倒海。因为一直感念吉谅那许多美丽的字、画带给我的温暖,那一天稍早些时候,我送给吉谅一副劫后余生的对子,是吴让之的字,小小两个滚动条套在一个布套子里。套子是外婆手缝的,上面的字是外婆写的。这会儿,吉谅拿出来给老师看,惊异着套子上字的好,竟说:“这是你外婆的字?比吴熙载的字还要好。”听了这句话,江先生微笑。我便很诚实地说,外婆总是跟我说,熙载真正好的是印。由此说开去,江先生是大行家,谈了些他对印章的研究,然后提醒吉谅,若是知道有可以托付的人到香港去,要想法子托带一笔钱给董桥先生。原来,1994年,江先生在香港古玩市场相中一盒上百方铜印,临时手上港币不够,是董先生垫的钱。江先生还把那些铜印拿出来给我看,讲了许多掌故。我这时正准备到香港去参加一个会,短短一个周末而已。于是我带走了那一笔钱,信封上写着董先生的电话号码和家居地址。1月6日抵达香港旅店,马上联系了董先生。董先生极客气地请我喝下午茶,当面交过了这一大笔钱,也带去了江先生与吉谅的热诚问候。自此,与董先生通信不止,更成为他最热诚的读者之一。在我的收藏里,江先生的信只得一封,看邮戳,这封信是1995年11月28日自埔里寄出的。信封是江先生自家的航空信封,回邮地址没有寄信人姓名,却有江先生的字:揭涉园书检,下面是印刷体地址,江先生还特别在下面用笔注明ROC。邮票三张都有意思,十五元的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百年纪念邮票;五元的是严“前总统”逝世周年纪念邮票,九元的是书籍装帧“蝴蝶装”邮票。内容却是一张江先生自家的贺年卡,印着他一幅极为俊朗的山水画,里面的印刷只有“江兆申鞠躬”五个字。江先生用红笔题写“恭祝圣诞敬贺新禧百福”,用蓝笔写信:“谢谢来信并贺卡。真是不得不回信了。接到你来信,立刻接到董桥来信,都是快乐,可佩。董桥夫妇的确也是我遇到的好人之一,我相信会更优秀。铜印只辛苦了一半,另五十方还没有开始整理,因为我兴趣又转到刻印上去了。祝阖府吉祥。内子附候。”既无抬头也无落款,更无年月日,简短、独特、情谊深长。不幸的是,江先生竟然于1996年5月12日心肌梗塞猝逝于沈阳鲁迅美院演讲席中,结束了中国文人画整整一个世代。多年来,江先生这封信被我留在台北近思书屋出版的《江兆申书画集》里,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本集子正是为了在沈阳的展事准备的,展期1995年8月22日到9月5日,主办单位是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美术家协会、鲁迅美术学院、辽宁美术馆、辽宁画院。我们尊敬的江先生没能看到这次展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