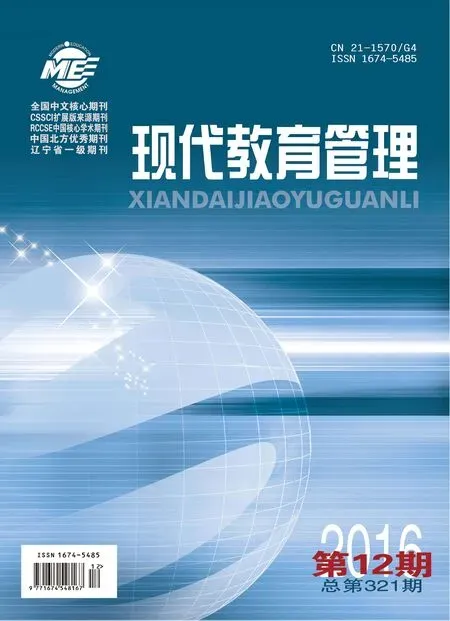美国品格教育的回潮与核心价值的寻求①
——基于政治斗争的分析视角
2016-03-04高原
高原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美国品格教育的回潮与核心价值的寻求①
——基于政治斗争的分析视角
高原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
20世纪80年代之后,品格教育在美国道德教育领域出现了“回潮”现象。这场品格教育运动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一场改革,也是美国国家文化与核心价值层面的一场政治运动。从政治斗争的角度重新考察美国的品格教育,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美国近30年德育改革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场品格教育运动背后的政治意图——对于核心价值的寻求。
品格教育;核心价值;新保守主义;政治斗争
一、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合与分
美国学者利昂乃尔·屈林(Lionel Trilling)1950年曾宣称:“自由主义不仅是美国的主导思想,而且是美国唯一的主导思想。一个简单而又明了的事实是,保守主义思想在美国现在已流传不起来。”[1]然而,他的这一断言并没有维持太久,便被卷土重来且来势汹汹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反戈一击。1964年,在新保守派的努力下,成功地使他们的代言人巴里·戈德华特(Berry Goldwater)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此之后,新保守派全力拥戴的罗纳德·里根又在1980年竞选总统成功,这标志着共和党连续12年入驻白宫,更是巩固、壮大并确立了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政坛上并驾齐驱的地位。虽然两者的内涵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文化”问题和对于“核心价值”的态度上,两者却有着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了两派二三十年以来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甚至延伸到了教育领域当中。可以说,美国“品格教育”的回潮,其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更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价值转向。而这一转向正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政治斗争的结果。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思想都是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复。新自由主义相信市场逻辑具有强大的作用,倡导全球化经济、反对国家过多干涉。这种反对政府监管的全球化经济鼓励国家之间的竞争,进而促进经济的繁荣,而强调通过竞争产生动力的逻辑给各国在全球市场立足的能力带来了危机。不仅是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也被引入了教育领域。诸如特许学校、教育券以及教育税收等相关政策都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假设,即学生之间以及学校之间的竞争将会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进而实现更高的学业成就。学业成就高的学生在之后的市场竞争中,就很可能取得更高的收益。
随着全球市场扩张的影响,国际间的交往以及通讯、技术等方面的进步开始影响到移民问题。这些变化除了造成经济实力的差异日益加大,同时也使得很多国家开始重新检视“公民”一词的含义,并且开始对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保持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问题产生担忧。此外,各国也察觉到了公共领域日益分离的现象,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公民教育改革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体关注。社会经济差异加大、政府对于社会服务的支持力度减小、人口数量的巨变以及始终饱受争议的全球化,面对这些问题,美国也开始产生焦虑并且呼吁寻求新的对策。在这种情形下,新保守主义对于核心价值的强调与新自由主义更加看重的市场经济逻辑逐渐并驾齐驱、相伴而行。
然而,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又有着一些区别。相对而言,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包含了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关怀,但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传统的道德权威。新保守主义希望回归曾经田园牧歌式的时代,在那里纯粹的真理毋庸置疑、人们具有强大的品格和道德观念并能够相互理解他人的价值观、政府对于私人生活也不做过多干涉。对于浪漫年代回归的渴望反映了人们对于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的诉求,这两方面特征能够给人们带去内心的踏实和安全。通过标准化运动和重新引入强调爱国主义、国家文化的品格教育,新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的教育产生了显著影响。
实际上,大部分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成员原本都来自于自由主义阵营,后来由于在学生运动、反越战、反文化等社会问题上与自由主义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与自由主义的决裂。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独特发展背景以及与传统保守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存有分歧,因此在传统保守阵营中也独树一帜,而被称为“新保守主义”。
在里根执政期间,一批新保守派人士在里根政府内担任负责国际关系、军控与裁军、教育、民权事务的高级官员或顾问,控制了里根政府的外交、国防和教育政策。在新保守派的影响下,里根提出了“里根主义”的对外政策纲领、“星球大战”计划、“推回”苏联扩张战略等。可以说,新保守主义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2]此后,随着冷战结束和民主党上台执政等因素的影响,新保守主义作用开始下降,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低潮。然而很快,在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中,“代表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共和党人以压倒性的胜利夺得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这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势力已经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占据主流地位。”[3]小布什执政后,更加看重新保守派,其内外政策都深深地打上新保守主义理念的烙印。
随着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文化与价值转向,以社会、国家的责任取代自由主义,以传统文化价值取代个人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渐成潮流。20世纪80年代,美国德性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他的代表作《美德之后》当中,强烈呼吁复兴自启蒙运动以来被长期排斥的美德传统。他认为,人类在共享生存中有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观是必须的,这些美德和价值观的传授能维护人的尊严、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只有重建美德才能弥补社会道德信仰的缺失。此后,美国加强了对于举国上下共同信奉的价值观的培养和寻求。因此,有学者认为小布什政府是当代美国史上最保守的一届政府,此前的里根革命是在经济、财政和外交、防务上保守,金里奇的保守革命主要是在预算方面和社会文化方面保守,而此届的小布什政府则是全面的保守。[4]
2008年,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新的,我们应对挑战的措施也许是新的,但那些长期以来指导我们成功的价值观却是古老的——勤劳、诚实、勇敢、公平竞争、宽容以及对世界保持好奇心,还有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主义——却是历久弥新,这些价值观是可靠的,它们是创造美国历史的无声力量。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回归这些古老的价值观”。[5]奥巴马总统的一席话仿佛是在对美国80年代之后,新保守主义推动之下的回归品格教育传统、寻求核心价值之趋势的总结。
二、新保守主义推动下的品格教育的回潮
(一)品格教育的再度兴起
20世纪60-70年代,用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奥尼尔的话来说,美国在各种社会运动的猛力冲击下,已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价值体系失去支撑中心,社会结构缺少凝聚力量,政治权威受到嘲弄嗤笑,文化观念出现迷茫混乱。[6]到了20世纪80年代左右,大量的研究和报告描绘了美国公立学校的状况。其中很多文献指出,公立学校的学生不仅在学术学业上情况堪忧,道德水平也是一塌糊涂。20世纪60-70年代进步主义的道德教育方法远远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就连道德认知理论的提出者和实践者科尔伯格自己也承认,宽容放任并不能产生道德,20世纪70年代应当因为其失败的教育实验而被铭记。开放的校园、缺乏组织的作息时间、免费学校解除了对于青少年的限制,但是并没有培养出他们自我引导和积极参与的意识。
由于意识到此前过分强调“价值中立”的问题,美国政府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着手进行自我调整。1980年,里根入住白宫,他的管理团队仍旧将教育问题置于重要的位置。里根政府在最初几年颁布了一系列的法案,除了众所周知的《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外,还有《学生需要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What Students Need to Know and Be Able to do,1983)和《美国中等教育报告》(A Report o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America,1983)。这些报告强调了学业成就的失败,但是实际上很多学校的失败在于道德教育出了问题:缺乏纪律、暴力行为、毒品泛滥,等等。
时任教育部长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和加利福尼亚州公立学校督导霍尼格(Bill Honig)率先提出要破除“中立”的魔咒,将“公共责任”和“相互尊重”作为必要的美德。贝内特强烈要求复兴品格塑造,霍尼格对此表示认同,并且更进一步地指出,品格塑造给更为传统的道德课程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虽然此前被价值澄清运动和认知发展理论清除出去的宗教并不一定要在课堂中得到华丽转身,但是其他的很多价值观需要被得以重新重视。此外,很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也强烈地意识到需要通过预防性的计划应对美国青少年道德品质的急剧下滑。
不久之后,右翼的支持者菲利斯·沙夫里(Phyllis Schlafly)成立了老鹰论坛(Eagle Forum)。在1984年美国教育部举行公众听证会时,作为节育运动(Pro-family Movement)的主导力量,这个论坛对公众意见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沙夫里报告(Schlafly Report)和其他右翼组织的言论,引发了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关道德责任问题的争议,并影响到了议会、联邦政府、媒体、家长以及学生的看法。右翼在这场争议中的胜出促使美国教育界不再排斥保守派的思想。从那以后,保守派组织——比如道德多数派、宗教右派、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等对很多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州和地方层面,这些组织能够直接影响到政策改革,进而影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
正是在保守派思想复归之时,一些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和政府的教育官员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对话,并很快掀起了“品格教育运动”。尽管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观点,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却是一个新的词汇,意味着重新强调“品格”的重要性,并强烈要求帮助形成青少年形成更好的道德基础。使用“品格”一词也考虑到了与此前价值澄清和道德认知发展之间的差别,这两种方法竭力与价值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划清界限。很多品格教育的支持者认为,反映在文化和传统当中必要的道德品质是存在的,随着传统的丢失,美国的文化也已经丧失。在这场运动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除了此前提到的贝内特和霍尼格,还有很多大学教授也参与到了这场运动当中。
在这段时间,社会评论者和科学家撰写了大量的书籍和论文,除了贝内特的《美国的价值滑坡》(The Devaluing of America)之外,还有布鲁姆(Alan Bloom)的《美国思想的分裂》(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艾齐奥尼(Amatai Etzioni)的《社区的精神》(The Spirit of Community:The Reinvention of American Society)、希梅尔法布(Himmelfarb)的《社会的道德滑坡》(The Demoralization of Society)、韦恩的《美国青年的品格滑落》(The Declining Character of American Youth)以及麦金泰尔(Alisdair MacIntyre)的《美德之后》(After Virtue),等等。对于学校来说,让学生变聪明已经不是唯一的任务,还要让他们具备美德。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学生获得技能、态度,以及能让美德发扬的性情。对于品格教育者来说,核心的任务是确保让下一代人具备必要的工具和美德,以此提升国家文化和传统。
(二)品格教育在全美的广泛推行
20世纪90年代,美国进一步朝向右翼政治发展,品格教育仍旧是重要的议题,但是此时的探讨有了更广泛的内涵。1992年,一个名为约翰逊美德研究所(Josephson Institute for Ethics)的私立机构组织了一批青少年和品格教育专家一起探讨美国公立学校品格教育的需要和发展方向。经过讨论,名为“品格有价值”(Character Counts)的模式成为美国品格教育运动中最流行的方法。与此同时,约翰逊基金会(Johnson Foundation)就“如何为K-12年级的学生提供有效的品格教育”这一问题组织了一场研讨会,以进一步促使国家层面的教育机构重视品格教育。不久,品格教育合作组织应运而生,并很快成为美国品格教育的领导先驱和重要的教育资源的供给。[7]同年,美国约瑟逊学院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Aspen)召开了为期4天的会议,并最终制定出“阿斯彭宣言”。“阿斯彭宣言”界定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六种核心道德价值观,并提出了将要付诸行动的品格教育计划。[8]在政府方面,1994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地采纳了支持品格教育的联合决定,指定每年的12月16日到22日为“全美品格测量周”(National Character Counts Weeks)。1994年,美国国会再次批准授权《中小学教育法案》(ESEA),对于品格教育的资助问题增加了两个经济来源。此外,白宫还分别于1994年至1996年,连续三年组织了关于公民与民主社会品格构建研讨会,并在会议上反复重申品格教育在全国优先发展的地位。[9]
在理论层面上,从品格教育重回美国公立学校的那一天开始,各州以及联邦教育机构就已经努力尝试弄清这场运动真实的内涵。内科南(Thomas Lickona)在《为品格而教》(Educating for Character)一书中提出了品格教育的理论框架以及实施策略。为何学校应当教授品格?在民主的社会中,学校传授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合法的?围绕这种价值观,学校应当发展学生的哪种品格?为了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内科南还提出了品格教育的12种方法。[10]
此外,由于国家的重视,大量的教育项目(CEP)如雨后春笋般地席卷全美。比如,长颈鹿(Giraffe)项目关注如何更大程度地鼓励学生“从内心深处按照公共的善的标准行动”。显然,品格教育在美国公立学校中得到的回潮。在经受住党派之争和意识形态的博弈之后,品格教育成为一种折衷的方案而广泛使用,影响了全国以及地方的教育实践。
(三)品格教育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联邦政府又进一步通过具体的教育政策,支持美国公立学校的品格教育。虽然美国的教育一直由各州负责的,然而自从布什2002年签署《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之后,联邦政府在促进学业成就和促成教育目标方面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众所周知,NCLB要求在全国各个学校实施严格的学业成就标准。与此同时,NCLB颁布之后,通过相关的系列法案,先后三次向品格教育提供政府拨款,总数多达2500万美元。这些拨款被用于不断普及的品格教育项目之中。
新世纪以来,由于理论体系已较为成熟、价值取向也已深入人心,因而美国公立学校实施品格教育时,在策略方法的选择上游刃有余。然而,大多方法都保持了一套核心价值体系,只是在具体的教学方式和事实策略上有所区别。一些品格教育项目结合学校的总体改革,采用了综合的方法,比如儿童发展计划(Child Development Project)和公正社区学校(Just Community School)。其他的一些教育项目则使用学校课程已有的资源,比如约翰·邓普顿基金会和赫特伍德研究所设计的生活的法则(Laws of Life)。正如伯克维茨(Marvin Berkowitz)所言,“各种项目和方法都将品格教育看作是一种综合的途径,道德推理能力的培养(道德教育)、特定价值观的教授(比如责任感)、减少不良行为(比如吸毒、暴力行为)以及学生的整体发展等目标可以同时实现。”[11]此外,在2004年,美国心理协会也出版了《品格优点和德行——手册及分类》一书,书中将美国品格教育的范畴概括为“智慧和知识”“勇气”“博爱”“公正”“自我克制”和“超越”六个方面。[12]这就使得品格教育更为系统精细,明确了其内容和目标。此外,一些学者在讨论何为品格教育当中的核心价值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操作层面的理论设想。比如,美国本世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位品格教育推动者托马斯·里克纳认为,要获得大家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核心文化,首先就是要培养学生“尊重”和“责任”的基本品格,他在《为品格而教——我们的学校如何教授尊重和责任》一书中,呼吁学校要唤起青少年的尊重和责任感,这是品格教育的基础。在相互尊重的集体氛围中,个体就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并发展为良好的品格。[13]
三、美国品格教育对于核心价值寻求的政治意义
可以看出,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对于核心价值的强调是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品格教育责无旁贷的任务,这也是新保守主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是其必须捍卫的用以安生立命的基石。施特劳斯从西方古典的视野对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自由主义宣称其目的是一视同仁地尊重所有宗教、所有种族、所有性别、所有历史文化传统,但其结果实际则是使得所有宗教、所有种族、所有性别、所有历史文化传统都失去了意义,都不重要了......”[14]与此针锋相对地,新保守主义强调的是传统价值信仰、共同的价值观,矛头直指新自由主义对于市场逻辑的呼吁。
阿普尔曾提到,新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具有良好品格的个人在市场竞争中会取得成功。这一假设表明,通过努力奋斗并且具有良好品格的个人赢得物质利益是理所应当的,而那些失败者是因为他们缺乏获得成功必备的良好品格。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来看,美国此前平民主义对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当下社群主义对于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且不必过多阐释的普遍认可的假设,包括习俗、风俗、偏见以及习惯,都强调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然而,这种普遍认同的观念现在却饱受普遍怀疑,人们也不再对所谓的超越阶级、民族、宗教和种族的价值体系抱有太大希望。“全球市场没有创造出对共同利益和趋势的新理解,却似乎强化了人们对种族和民族差异的意识。市场的统一与文化崩溃成了一对孪生兄弟。”[15]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市场的壮大与文化的分裂如影随形,并每况愈下。因此,布什总统于2001年签订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之时,美国实际上恰好正处于普遍的道德滑坡时期,联邦政府希望通过实施品格教育项目以改变当时的状况,从文化品格的角度赋予青年人更大的成功筹码。
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就业的目的,品格教育在当今全球化的文化、价值多元的背景中,还肩负着更加艰巨的使命。在多元文化当中寻找一个统一的价值核心,对于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美国9·11恐怖袭击已经提醒人们对于多元文化的思考。无独有偶,2003年西班牙马德里地铁爆炸案造成了190人丧生、1500多人受伤,也被定性为一起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此外,2005年英国遭遇伦敦地铁骚乱事件,再一次提醒人们多元文化主义走向极端危险。这一起起惨案似乎在一次次地发出警告,在这样价值多元的时代,巩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统一核心价值的必要性。伦敦地铁骚乱事件之后,时任工党政府首相布莱尔在讲话中指出:“迁居英伦不只是一种权利,定居于此更带有一份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分享和支持那些支撑英国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16]布莱尔的继任者工党前首相布朗也多次强调了“英国国民性”(Britishness)的概念,认为应该以共同价值观来增强国家凝聚力。而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则说:“英国的教育政策没能向少数民族描绘出那种他们愿意归属的社会前景,英国社会甚至对那些行为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封闭群体进行容忍,而所有这些原因导致一些有不满倾向的少数族裔青年缺乏归属感,在寻找归属和信仰的过程中,少数族裔青年可能会落入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怀抱之中。”[17]
无论是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来说,还是这个社会当中本来就存在的多元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信仰的大众来说,寻找一种共同的、大家都能够认可的文化价值标准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美国当前的品格教育也正是为了这样的一种文化价值诉求而努力。即便是在自由主义者那里,他们对于共同的道德准则和个人品格不屑一顾,声称“一个适当的立宪制度甚至让坏人都更有机会为公共事务出力”,美德的基础是“政府的原则”,而非“渐渐消失的个人品质”,但是他们也认为公民美德与个人基本的品格特质是必要的。弗里德曼自己也承认,一个自由社会不仅需要“最起码的识字和知识水平”,以及“对某种共同的价值体系的普遍接受”。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写到,“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根本就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理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是不构成社会[18]。”可见,新保守主义呼吁核心价值并非仅仅是某一个政党为了独立而标新立异的政治宣言,更不是为了迎合民众的无病呻吟,而是依仗于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美国的“品格教育”运动强调培养学生核心价值也绝不是对于20世纪前后品格教育的简单重复,而是面对当下社会背景以及政治的现实状况,从教育层面进行的思考和采取的实践,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价值多元的一种深刻的文化关怀。同时,美国品格教育的回潮也体现了政治运动对于教育改革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如今,当我们再次体味美国保守派政治家亨廷顿发问“我们是谁?”的时候,应当够透视出品格教育对于核心价值寻求的深刻内涵,也能够体会到美国政治斗争与教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Lione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M]. New York:Viking,1950:ix.
[2]吴雪.美国“新保守主义”研究状况评述[J].外交评论,2006,(10):81.
[3]孙逊.论新保守主义思潮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10):59.
[4]张立平.论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J].太平洋学报,2002,(4):59-60.
[5]奥巴马就职演说[EB/OL].http://news.sina. com.cn/w/2009-01-21/042417085569.shtml,2009-06-10.
[6]William O’Neill.Coming Apart[M].New York:Quadrangle Books,1971:98.
[7][11]Marvin Berkowitz,Esther F.Schaeffer,Melinda C.Bier.Charact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Education in the North,2001,(9):53.
[8][9]王学风.美国现代品格教育运动及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3,(8):27.
[10]ThomasLickona.EducatingforCharacter[M].New York:Bantam Books,1991:23.
[12]Christopher Peterson,Martin E.P.Seligma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2.
[13]易莉.论美国道德教育的转向[J].教育评论,2011,(1):168.
[14][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51.
[15][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M].李丹莉,刘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69.
[16]任梦格.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困境与反思[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
[17]Oliver Wright,Jerome Taylor.Cameron:My war on Multiculturalism[EB/OL].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cameron-my-war-on-multiculturalism-2205074.html,2011-02-05.
[1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04.
(责任编辑:赵晓梅;责任校对:李作章)
The Resurgence of Character Education in America and the Persui to the Core Value
GAO Yua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In the late of 1980s,Character Education resurg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America.The Character Education Movement is not a reform of moral education,but also a political movement on the aspect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core value in America.It is helpful for us not only to make clear of the history of reform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inAmerica,but also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intent behind the Character Education Movement-the persuit of the core value from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character education;core value;neoconservatism;political struggle
G649.1
A
1674-5485(2016)12-0108-06
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行动基金资助(PY2015007)。
高原(1987-),男,安徽蚌埠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