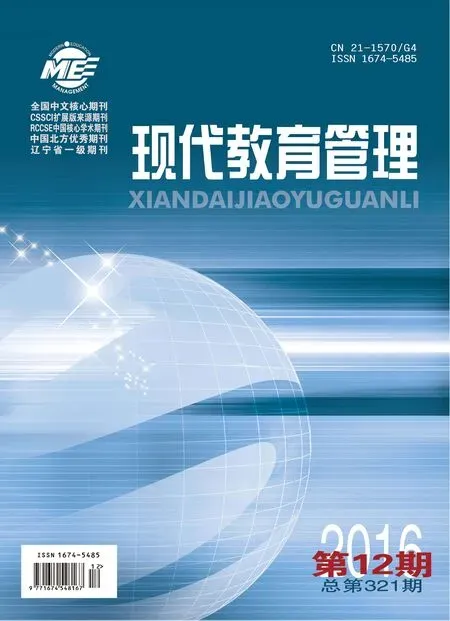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转向、模式变革与效用优化①
——基于美、英、荷、法等国的经验
2016-03-04徐蕾,常波
徐 蕾,常 波
(1.湖北科技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2.空军航空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
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转向、模式变革与效用优化①
——基于美、英、荷、法等国的经验
徐 蕾1,常 波2
(1.湖北科技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2.空军航空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
客观性、公正性和效用性既是高等教育评估的逻辑起点,也是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保障。近年来,美、英、荷、法等国高等教育评估呈现出生本性与发展性的价值转向,多元参与与协同治理的模式变革,提升效益与差异发展的效用优化。在借鉴与反思的基础上,我国高等教育评估需要坚持以生为本的评估取向,遵循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树立绩效自主的评估原则,尊重高校差异发展与特色发展;建立主体自觉的评估导向,提升高校的质量自觉;积极培育多元参与的评估体系,发挥结构性评估优势;健全监督问责的元评估建设,保障评估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信力,从而推进高等教育评估体系化和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高等教育评估;管办评分离;元评估
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高度发展,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迅速转型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高等教育质量随之成为关注的焦点。客观性、公正性和效用性既是高等教育评估的逻辑起点,也是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保障。近年来,世界各国均在高等教育评估价值取向、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式以及评估结果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与调整,对其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与反思,既可以了解与掌握高等教育评估的总体趋势与走向,又能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提供参照与借鉴,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与高等教育改革的纵深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一、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转向:生本性与发展性
大学既包含着为社会造就人才、创新知识、优化生活环境,也包含着“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修养大众身心,提炼民族品味,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公众的渴望提供固定的目标,充实并约束时代的思潮,便利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净化私人生活中的种种交往”[1]。
从高等教育制度及高等教育评估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美、英、荷、法等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历史悠久,先后出现了“教学开业证书制度”“入学考试”“校外同会证审”“高等教育认证”等评估机制,评估方式也由初始的政府主体评估,发展成今天的政府评估、高校自评、中介组织评估、学生评估等多元主体参与评估方式,逐步形成了富有特色、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评估模式与评估成果。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各国高等教育管理机构与研究人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澄清了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走向,即高等教育评估不仅是对高校办学水平以及对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估,其内隐性的价值追求应是高度关注和服务高等教育主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学生的发展质量,即学生在整个学习历程中所学的‘东西’(所知、所能做的及其态度)。学生在认知、技能、态度等方面的收益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标准”。[2]并且,高度关注评估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推动作用,即高等教育评估的目标不仅仅是对当前高等教育质量的定量分析,更是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分析,是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研判。
具体评估中,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认证模式”还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审核模式”,高等教育评估的关注点逐步从注重高校的全球声誉、综合排名与资源占有转向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将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以及学生就业情况、雇主评价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评估,呈现出以生为本,着眼发展的价值转向。这样,高等教育评估从“只见物”的评估转向为既“见物”更“见人”的评估,从以科研成果、科研经费、师资力量、办学规模等为重心的评估转向为以学生成长和发展为重心的评估,从以教师科研表现为重心的评估转向为以学生学习表现为重心的评估,从重学生在校学习结果的评估转向为既重学习过程又重学习结果,并重毕业跟踪的评估,呈现出生本性和发展性价值取向。
二、高等教育评估的模式变革:多元参与与协同治理
有学者认为,根据高等教育评估价值系统的要素,可以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评估分为四种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政府控制模式,即政府控制高等教育评估的整个系统与环节;以英国为代表的委托代理模式,即委托社会中介组织来实施评估活动;以荷兰为代表的叠加评估模式,即政府指导性地介入高等教育评估活动,并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对评估机构的评估活动进行再评估;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合作模式,即政府与社会中介评估组织密切合作,政府进行宏观指导与协调,但不直接参与评估活动。[3]
例如,法国高等教育评估的管理主体与执行主体是分离的,高等教育质量评鉴局作为全国唯一评估机构代表政府行使行政主体权力,选聘3500人左右的专家队伍(其中外国专家占20%左右)负责对全国所有高校、学科及教育专题进行专业评估,保障评估的权威性与多元性,并接受社会团体的监督。英国大学有着悠久的自治历史,同时关注公共价值和市场需求,建立了多元化的评估中介系统来实施评估活动。其中,高校作为自我价值评估的主体,负责自身的课程质量控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负责检查和评估大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审核决定大学拨款;专业机构和社会中介组织广泛参与,增强评估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广泛性和透明性。并且,学生作为评估的主体之一,其评估权力与价值亦受到重视和保障。美国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分权治理,教育部、州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其中,社会中介组织通过院校认证、专业认证和大学排名推进高校的质量改进,州政府使用绩效指标决定高等教育拨款的多寡和方式,教育部则通过对高等教育认证机构的认可和高等学校财政与行政管理最低绩效标准等方式间接影响高等教育质量与效益。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The CouncilforHigher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HEA)指导协调全国的高等教育评估活动,但不直接干预各评估机构的评估活动,允许他们推出各自的评估结果或大学排名。
尤值一提的是荷兰高等教育评估模式,荷兰高等教育评估由校内自我评估、校外社会评估和政府元评估三部分组成,协调分工,相互配合。校内评估作为高校质量的内在动力,由资深教师组成评估委员会负责校内教学与科研活动的质量评估与监测;校外社会评估作为高校质量的外部保障,主要由荷兰和佛兰斯认证机构、荷兰质量保证局承担,通过外部考察、内部自我评估和外部再考察对高校的教育质量进行整体考核。与众不同的是,由隶属于政府的高等教育督导团代表政府对高校自我评估和校外社会评估进行“元评估”,对评估的流程与结果进行监督和复查,从而保证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这种介于政府集权与社会分权之间的评估模式,使高校自我意识与外部推进统一协调起来,既确立了政府的导向作用,又激发了高校的自主发展,达到了二者的平衡。“甚至被一些学者誉为高等教育评估的荷兰模式。”[4]
从上述各国高等教育评估模式和评估经验可以看出,高等教育评估模式随着国别政府治理模式、经济发展需求、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人力资源变迁态势和社会文化变迁规律而各有千秋,不断调适,呈现出多元参与和协同治理的发展态势。既呈现出政府宏观指导、市场经济调控与大学自治发展三方协作的高等教育发展走向,也呈现出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参与评估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变革,体现出高等教育评估的客观性、公正性以及质量性、效益性的综合诉求。一方面,政府不再充当无限政府,不直接干涉高等教育评估,而是通过简政放权,以绩效拨款和最低标准的方式行使政府的教育治理职责,并确保高等教育实现培养人才、教学科研、传承文化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高校赋权增能,主动承担起质量保证与质量提升的主体责任,培育起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中的理性自觉;同时,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其在教育评估中的独立性、专业性和中介性,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网络化的高等教育评估服务。由此,在这种多元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中,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提高高等教育效益,达到政府、高校、社会、教师、学生、家长的良性互动、协同治理。
三、高等教育评估的效用优化:提升效益与差异发展
高等教育评估既是国家对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监督检查的重要举措,也是高等学校自我诊断、改进提高的基本手段。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评估既能为政府的高等教育治理提供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决策依据,也能为高等学校进行课程改革和管理改进提供合教育性的参考依据,还能为家长、学生、用人单位提供真实有效的择校参考和用人参考。它不仅关涉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治理模式,也关涉中观层面的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和高等教育治理的社会参与,微观层面的学生学业成绩提高与能力养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评估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质量的诊断性评估和总结性评估,还应是基于高等教育品质提升的发展性评估和生成性评估。考量高等教育评估指标、评估方式、评估过程的科学合理的同时也需要考量高等教育评估的效用价值。
美、英、荷、法等国都非常重视高等教育评估的效用价值,追求公平与效益的统一,通常是将评估结果与绩效结合起来,旨在通过成绩认定和绩效奖励,促进高校之间的公平竞争,提高高校的整体价值。例如,法国高等教育采用“合同制”政校管理模式,评估的结果直接关系到政府对高校的拨款额度与新期合同的签订,评估成绩优秀的高校将获得更多的政府拨款,并在新期合同制定时取得优先权和话语权,切实承担起质量保障与提升的重要责任。英国高等教育评估以“可以通过测量绩效、生产力和顾客的满意度来保证质量”[5]为基本理念,由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负责高等教育体系的质量审计,考核整个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率;由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教育结果的质量评估,考核学校的高等办学质量,从而将办学效率与办学质量统一到学生的成长发展服务中。其中,基于学生数、学科建设和教学活动的教学拨款在不同层次与类型的高校间大体相同,而以科研产出为依据的科研拨款则因校而异,鼓励优秀。美国高等教育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末即在高等教育评估中引入绩效因子,以期提高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提高高等学校科研产出数量与质量。通过评估、获得认证的高校能顺利获得联邦政府、州政府、专业机构、企业和个人的大量经费资助,以及良好的社会声誉与大众认同,从而在发展中占居明显的优势地位。荷兰在2000年引入了绩效拨款模型,将评估结果与绩效联系起来,从教学与科研两部分分配高等教育预算,所不同的是,在教学评估方面,评估结果与教育行政拨款没有直接关系,而以高校培养的学生数与新生数进行衡量,体现出学生在择校中对所选高校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的社会认可度。
与此同时,美、英、荷、法等国重视全面发展与差异发展、特色发展的统一,普遍开展了综合评估与分类评估的协调发展。通过综合评估可以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情况作出全局性、整体性、全面的评估,而分类评估则可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有针对性、区别性和有效性的评估,反映出不同高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例如,美国的综合评估中具有代表性有: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为代表的学校综合实力指标体系评估,以《普林斯顿评论》为代表的学生指标体系评估和以The Consus Group为代表的专家指标体系评估;分类评估中具有代表性有:卡内基教学促进会高校分类评估,《Kiplinger Personal Magazines》分类评估等。英国QAA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学术资格框架、学科基准、专业规格实施规则等,而分类评估则针对大学和非大学的多科技术学院、教育学院制定不同的评估标准。荷兰除综合评估外,还针对大学和高等职业学校开展分类评估,前者侧重学术价值,后者侧重职业价值。[6]这些评估方式既有助于政府整体规划高等教育发展,也有助于高等学校理性认知、明确界定自身的办学定位、办学目标和办学特色,开展差异化办学和特色化发展。
四、对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改革的启示
(一)坚持以生为本的评估取向
美、英、荷、法等国高等教育评估都高度重视学生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价值主体地位,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将学生的学业收获与职后表现作为评估的核心指标,评估的结果必须有效服务于学生综合能力、高校教学和科研质量的提高。反观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多为教学水平评估,甚少开展学生学业水平、学习行为、学习效果的专门评估,关注点基本在于学校的科研产出、师资配置,而学生质量和学生参与基本处于错位、缺位状态,学生在评估中也没有参与权、评估权和建议权,往往以一种在外在的、物化形式的学生数量、试卷分数、设计报告、零星座谈等指标存在于数据表格中,若隐若现,可有可无。并且,“评估制度安排忽视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如企业和家庭,造成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人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或利益诉求链条而导致利益诉求信息扭曲的结果”,[7]即与学生质量评价密切相关的用人单位和家庭多孤立于评估活动之外,或是完全被忽略,或是以零星方式表达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判断,难以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评估效能,无助于高校教育教学的整体改进与提升。
作为改进,我们必须坚持以生为本的评估取向,尊重并遵循学生的知识获得、技能提高、品德养成和心智发展等内生性需求,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为根本原则,以高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和管理方式的改进为评估结果的效用追求。高度重视学生、教师、用人单位和家庭在教学质量、课程改革、学校管理、学校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参与权、发言权、评估权和建议权,建立科学、多元、多维的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设计评估方法和评估流程,将专家评估与师生评估、社会评估结合起来,将学校办学效能评估与学生发展评估结合起来,将学生学业成绩表现与社会服务表现结合起来,回归高等教育的本体责任与价值。
(二)树立绩效自主、尊重差异的评估原则
科学性、客观性和公信力是高等教育评估的不懈追求。由于我国高校质量评估主体长期以来以政府为主导,评估指标相对统一,评估方式主要以专家进校查阅资料为主,评估指标具体结果不对外公布,评估结果效用低,高等教育分级管理、分类评估尚在摸索中蹒跚前行。就教育部2008年大学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结果来看,参评的198所大学中,160所获得优秀,占参评总数的80.8%;38所获得良好,占参评总数的19.2%;没有不合格的学校。这个结果显然无法真实反映出高等学校的办学能力、办学特色与办学个性,除了让参评高校皆大欢喜,实难让人信服。
作为改进,我们要切实推进高等学校分级分类管理和评估,尊重高校的差异办学,鼓励高校的特色发展。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现代化评估方法的技术,将阶段性评估与常态性评估结合起来,将文本数据评估与综合信息评估结合起来,尝试现代信息技术综合管理渠道与方法,进行动态评估与管理,真实反映出高校办学的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并且,要将评估结果与政策扶持、经费拨款、办学自主权有机的结合起来,以绩效促自主,以个性促特色。当然,再次强调分类管理和评估并无太多理论新意,变革的关键点在于,需要加快建立起科学化、体系化的评估标准与流程,处理好上述结合的方式、途径与尺度,切实发挥优者示范、中间警醒、后者奋进的鞭策激励作用,尚需评估专家、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和社会共同努力。
(三)建立主体自觉的评估导向
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外部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外因通过内因而作用于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成功的高等教育评估模式,往往是高校自我觉醒和外部推动的有机结合,美、英、法,荷等国都高度重视高校在评估中的主体地位,尊重高校的自我价值判断,引导高校主动自觉地承担起教育教学质量与水平提升的主体责任。反观我国高校评估,现有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与评估机制使得高校往往处于被动的评估地位、被动的应对评估状态,常是举全校之力,硬扣评估指标体系,肢解评估流程,突出“物质化的投入要素,数量化的产出要素和标志化的结果要素”等显性要素,进行象征性评估。[8]评估活动独立于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工作之外,独立于学校自主发展意识之外,变成了被迫接受的任务,被学校视为负担,参评心理抵触、自评数据造假、评估结果趋同的现象并不少见,基本上无法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必、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评建目标。并且,大一统的成长经历和层级管理体制往往使高校无法理性地认识自身的专业特色、地域优势和发展定位,一味追求专业齐全、校名高大、排名靠前,反而陷入了盲目狂热的发展误区。
作为改进,需要确立高等教育评估中高校的主体地位,唤醒高校的质量意识,让高校自觉承担起质量保障与水平提升的主体责任,从“要我评估”的被动抵触转变到“我要评估”的主动改进,主动将评估并构于教学改进、治理变革的实质性治理变革中,充分发挥高校自评自改的优势与实效性,提高高校的自我评估能力,不断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机制。政府也要切实进行简政放权,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通过有效的机制,将专业规划、课程设置、教学改革和教师管理的权力赋予高校,引导高校理性认知自身发展的目标与规划,客观评价自身的发展状况、优势特长和缺陷不足,冷静思索完善措施和改进路径,理智应对利益相关者的教育诉求。
(四)培育多元参与的评估结构
从美、英、荷、法等国高等教育评估经验来看,专业机构、社会中介组织、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参与高等教育评估业已成为提高评估专业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公信力的有效方式,并且其参与方式与尺度也将日益成熟。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的逐步深入,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高等教育改革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即要求:“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治理模式下的“社会评教育”。这些都是教育协同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的有力举措,其实质是管办评分离,分享参与权、评价权和监督权,将社会或个人可以承担、能做好的事交给社会或个人去做。
我们需要积极倡导、科学引导高等教育领域内利益相关者主动参与教育治理,形成责任分担、边界明确、共同参与、相互协调、彼此强化、合作推进的治理体系和评估体系,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结构性优势,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如充分发挥专业学会、行业协会、基金会等第三方社会组织的监测、诊断、指导等专业评估优势,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职业发展现状等学生综合素质评估和人才评估的专业性、中立性、独立性优势,发挥大众传媒、家长、学生在学校声誉建设与品牌经营评估中的公众评估优势。同时,将校外评估与学校自评结合起来,将用人单位评估与家长评估结合起来,将象征性评估与真实性评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主体多元、框架合理、权责明确、功能互补的高等教育评估结构。
此外,还可以尝试引入国际专业评估机构或是选聘国外评估专家,对高校办学水平、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师生素养进行客观、公正、中立的高水平专业评估,进一步树立高等教育评估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视野,增强评估指标设定、评估流程设计、评估方法选择、评估结果使用的专业性。这将有助于我们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教育教学方法,切实改进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促进我国高等学校的分类发展和整体优化。
(五)健全监督问责的评估保障
专业机构和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评估,能从不同的视角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相对全面、全局和具体的评估,也能为政府和公众提供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质量评测,从而为政府的高等教育治理和公众的高等教育认知提供良好的参考依据。但不同的专业机构和社会中介组织的评估能力、评估取向、评估标准各不相同,评估的结果也有差异。仅就2016年中国大学排名前3名来看,中国科研评价研究中心榜单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书连大学排名榜单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校友会网榜单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这对于缺乏专业背景和接触机会的公众而言,实属雾里看花。尤其我国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高等教育评估出发晚、起点低,他们是否能承担起政府下放的评估权、监测权是问题的关键,规范的资格管理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是其能力建设和发挥的有力保障。
我们需要积极推进资格认证与管理制度建设和元评估建设,保障评估活动与结果的公正、客观。评估活动在逻辑起点上存在的难题之一就是评估难免会带有一定的价值预设,从而影响到评估指标与评估结果。在不断研判、调试教育行政部门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保障教育行政部门评估的客观性、多样性的同时,在大力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整合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构,保障专业教育服务机构评估的独立性、科学性的同时,还需建立强有力的资格认证与管理与元评估,充分发挥政府对高等教育宏观指导和价值导向的功能。一方面要加强对评估机构的认证与管理,保障评估机构的公信力与公正性,另一方面对评估机构开展的高等教育评估过程和结果进行元评估,既承担起政府的高等教育治理职责,又能加强对评估机构的监督监管,从而保障高等教育评估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1][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译.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98.
[2]陈玉琨,杨晓江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9.
[3][6]张继平.颠覆与创新:高等教育评估的价值取向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7、78-80.
[4]Almeida Lajes M.A.Management and Quality 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 Portugal[J].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1995,(1):131-136.
[5][英]路易斯·莫利.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权力[M].罗惠芳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
[7]杜东东.关于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几个基本理论基础问题的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9,(2):30-31.
[8]刘振天.从象征性评估走向真实性评估—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反思与重建[J].高等教育研究,2014,(2):28.
(责任编辑:于 翔;责任校对:赵晓梅)
Value Diversion,Model Reform and Utility Optim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XU Lei1,CHANG Bo2
(1.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ning Hubei 437100;2.Aviation University of Air Force,Changchun Jilin 130022)
Objectivity,impartiality and utility are not only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but also the value of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In recent years,the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presented the value diversion on student-based and development,model reform on multivariate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utility optimization on promotion effect and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Britain,the Netherlands,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need to adhere to standard of students’development,set up the principle of performance,conscious guidance,participatory evaluation system and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to realiz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separate of regulation,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meta-evaluation
G647
A
1674-5485(2016)12-0029-06
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协同学视域下省域教育治理模式创新研究”(2015GA041)。
徐蕾(1976-),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科技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研究;常波(1970-),女,吉林长春人,空军航空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外语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