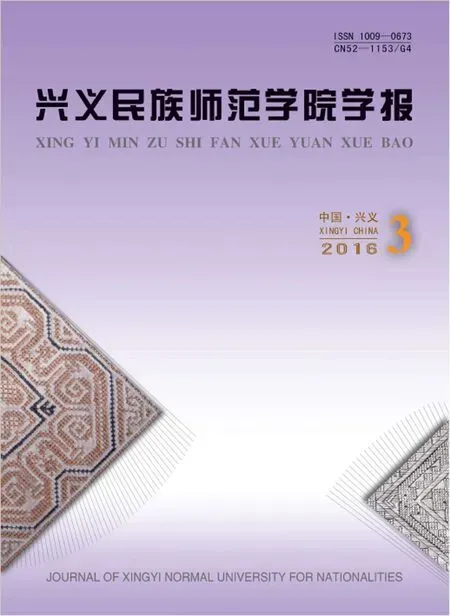阳明心学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感触教育模式的启示
2016-03-03高齐天
高齐天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阳明心学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感触教育模式的启示
高齐天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阳明心学围绕道德养成问题所进行的理性思考内容,对于今天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改革仍具有非常积极的启示作用。“知行合一”思想,给道德之知的教育传递留下了宝贵的空间。“格物致知”的重释启示我们,德性培养的过程是一个受教育者自我斗争的“正心”过程。“人人自有定盘针”,每个人都有善恶判断的内在标准。面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我们需要考虑到其内在德性标准的现实存在及其必然影响,发挥感触教育的优势。
阳明心学;知行合一;思政课;感触教育
王守仁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因筑室越城外阳明洞,人称阳明先生,其思想体系亦被称为“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在反思朱熹理学思想的过程中,围绕人的道德养成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命题,对后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却阳明心学的时代性、封建性因素之外,其中一些命题的致思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从事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改革仍具有非常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知行合一”命题及其启示
在人的道德实践中,朱熹重视道德之知的先导作用。“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1](152)这本是符合人的理性追求特点也是尊重意识能动性的提法。但这种“知先行后”的观点,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何谓有“知”?二是有“知”必然能“行”吗?在第一个问题上,朱熹认为“知”是对“天理”的认识。但这一定义却引发了必然的逻辑追问:人们能把握这个“天理”吗?如何把握?何时能把握?朱学认为天理虽高高在上,但却如“月印山川”一样分散在万事万物中,因此,人们需“格物”以“穷理”。对此,王守仁指出:“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2](119)“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2](4-5)如果以为格尽天下之物才能求得真知,那么,天下事物太多了,恐怕人的一生都难以做到,如此,人们不免要把自己的一生都困在知的圈子里,如何在行动中产生实际的道德影响?在第二个问题上,对于有知识的人未必有道德的知行脱节现象,朱熹的解释是:“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1](148)。这种以知的程度来解释知行脱节的原因显然缺乏说服力,全然没有王守仁从知的性质角度,用“未知”说法解释得干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2]4“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2](42)知行本体上是合一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2](42)“浅知”与“不知”的不同解释,引出的是不同的求知方法。朱熹“浅知”一解,表明道德学问功夫尚需在原有的“格物致知”道路前行,而王守仁“不知”一解,却是打开一条从真行到真知、知行并进的道路的前奏。
王守仁“真知必然真行”的“知行合一”思想,避免了人们因“知而不行”的个别现象而否定求知环节或德性教育存在的必要性,给道德之知的教育传递留下了宝贵的空间。今天,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阵地”、“主渠道”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在“知行”体系中对“知”的环节的重视。当然,如何通过理性的求真与实践的感悟,让大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达到真知而非假知,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正向发展,既是任何认识活动的实践目的性的需要,也是追求德育实效应该思考的方法问题。
沿着王守仁从“真知”到“真行”的逻辑线路,如果我们在其间加上“真信”作为中间环节,则会让从知到行的逻辑道路更加平直。相信不会有人对“真信”到“真行”的必然性表示怀疑,所需考察的就是“真知”与“真信”的关系了。从联系上看,“真知”是“真信”的必要前提,“真信”是“真知”的必然结果。从区别上看,如果说,“真知”还是停留在“知性”、“理性”范围,那么,“真信”则不再是表示纯是非判断问题,它主要体现认识在“非理性”的信念、意志、情感范围的延伸,包含着认识主体的价值取向与情感偏向,因而与道德行为的实现具有更直接的关联性。现在,在从事思政课理论课教学的队伍中,比较普遍的共识是:追求知识的正确性、真理性,以趋从人类理性追求的自然方向,把理论教学的目标尽力归结在使学生达到“真知”的节点。这种想法符合王守仁“知行合一”思想的逻辑, 也是对真知、真信、真行之间顺序推进的关联性的认同。但是,如果看不到“真知”与“真信”的区别,看不到二者所反映的“知”与“信”各自分属的不同领域,就势必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忽略学生个体情感和价值经验世界的存在,难以避免“知而不信”的结局,当然就意味学生得到的知是不能引起相应行为的“真知”。高校学生在接受教师的思政理论教育内容之前,本身就有着相对丰富的人生和情感经历,因此,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当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尽力唤醒他们在经验过程中对教学理解与接受可能包含的种种支持性内容,这正是“感触教育”所要强调的。只有重视与受教育者经验世界特别是情感经验和价值经验的结合,才能让受教育者知的过程同时成为一个信的过程,最终也必将成为知与行联系的强力粘合剂。
二、重释“格物致知”的启示
在求知路径上,王守仁反对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读和做法。朱熹说,“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得到十分,方是格物。”[1](283)这种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容易造成知而不行的知行脱节现象,另一方面,造成“物理”与“伦理”间的难以兼容性。“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2](119)王守仁反对“务外遗内”--求知于外部事物而忽略内心自律的做法,强调内求于心,因而重新注释“格物致知”。“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2](6)格物,是一个排除私欲、不以物累的正心诚意的功夫,籍此,方能恢复心之本体,达到自然能知,自然能行。
王守仁重释“格物致知”,将伦理认知从自然“物理”认识中区分开来,进而寻找到“正心诚意”——纯然德性砥砺的用功途径。同理,今天的高校思政课不同于以知识传授为目的的其他自然科学学科,教学的方法与侧重点当然就不一样。思政课教师的课堂知识能否让学生内化于心,成为他们品性素养的一部分,是确保甚至是衡量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根本标准。这一方面,要求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注意不同的德育引导。如《中国近代史纲要》作为公共政治课教学就不应将其仅仅作为一般性的历史知识传授课程,而应当在历史知识的回顾中有意识地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强意识,从而让他们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符合历史规律的选择有一个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自觉地培养正确的政治觉悟。另一方面,德性培养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斗争的“正心”过程,通过增加教学实践环节,设置道德情境,提供学生在事中磨砺的机会,结合生活实际感悟到道德的美好价值,来培养学生的正义之感、公正之心,自觉与自私自利观念和行为作斗争。在这两个方面,以实际的事实材料进行教学,以具体的实践过程进行体验,正是在强调经验式材料基础上引发内心触动的感触教育模式强调的具体做法。
三、“良知论”的启示
王守仁试图用“知行合一”解决知、行之间相脱节的现实矛盾,但结果是把问题的症结从知行矛盾转化到了真知与假知的矛盾中,何以求得真知,就成为新的难题。对此,王守仁认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2](6)“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2](971)既然良知有如此之能,那么寻找到良知,就自然能解决由知到行的逻辑必然性。
王守仁的“良知”范畴无疑带有先天性与超验性,但他并未将良知的理解简单地停留在一个神秘难测的层面。“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认识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2](14)这种说法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否定了良知的先验性。对于王守仁赋予“良知”的先天性与后天性兼而有之的矛盾属性,杨国荣的分析有一定见地:“逻辑上的先天性亦似乎表现为某种逻辑上的可能。……道德原则的作用固然离不开经验活动,但其普遍有效性在逻辑上惟有来自先天之知。”[3]似乎在人们心中的权威的神坛上,后天生成的事物并没有先天生成的事物所具有的优越性,王守仁只有靠隐瞒良知真实出身的方法,赋予良知一个先天的空壳才能让它的知善知恶的神通能力为人所信服,才具有“普遍有效性”。
王守仁“良知”的先验性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借用王守仁“人人自有定盘针”的说法,每个人都有善恶判断的内在标准,这个标准,在王氏看来非“良知”莫属,在今天看来,它应该是道德主体进行价值判断的基本观念,即价值观。价值标准虽然与真理标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但二者决非等值等效。价值观念作为来自道德评价者的内在标准,与道德评价主体的经验成长和主观感悟密切相连,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一种选择。高校大学生的年龄阶段,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定性的阶段,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价值标准,并以这种标准判定是非和决定行动。我们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必须首先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已经形成内在价值标准的大学阶段与尚未形成内在价值标准的儿童时期相比,我们需要选择的方法就会大不一样。
面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我们需要考虑到他们内在德性标准的现实存在及其必然影响,需要考虑如何合理运用或者改变这个标准或观念,否则就会遭遇到莫名其妙的接受阻抗。如果这个标准是合乎社会需要的、正确的,那么,教育工作者的再续教育可以轻松地利用这个标准作为基础,或者在抽象的理论教育中合理插入引发大学生内在标准赖以形成的感性经验共鸣的事实材料,大学生接受老师的理论知识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并且这种接受也绝不是简单的认识接受或纯逻辑认可的问题,而必然是让更加坚定的内在标准发挥“良知”一样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大学生已经形成的内在标准与社会标准不很一致甚至背道而驰,那么,这时就更能体现感触教育的作用了。感触教育此时的优势在于,它避免了结论性的理论内容与受教育者确定了的观念现实的直接碰撞,而是去触碰其作为人所共有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在重新进行的一次“虚拟经历”中让内心去作一次自主选择。虽然受教育者正常的认知和情感曾经在特殊的个性经历中变异出错误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并不意味着这种正常的认知和情感随着价值观的扭曲而扭曲和不正常,也不意味着正常的认知和情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永远只结出一种果子并且是坏果子。感触教育正是要通过外部经验材料召唤受教育者的认知和情感正常再现,并发挥其应有作用,向着歪曲的价值观阵营反戈一击,重塑新的正能量价值观,确保“虚拟经历”中的重新选择朝着正确方向靠近。
[1][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全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杨国荣.本体与工夫:从王阳明到黄宗羲[J].浙江学刊,2000(5).
责任编辑:杨欢欢
Revelation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for Feeling Teach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Course
GAO Qi-tian
(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Xingyi,Guizhou562400,China)
Issues of moral cultivation,which were thought rationally in Yangming’s philosophy,still hav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eaching mode reform in toda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thought of“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kept a rare place for teaching moral knowledge.To explain"Knowledge and Purpose"again,Wang told us that the course of moral cultivation is a one of rectifying the mind by educatees themselves.”Everyone has a compass”,so everyone has an inner standard for judging his behavior.Duri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to college students,we need think about the existe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inner standard so that 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feeling education.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courses;Feeling Teaching
1009—0673(2016)03—0068—04
G410
A
2016—04—15
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思政课项目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增强的思想路径--‘感触教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SZK010。
高齐天(1968— ),男,河南信阳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