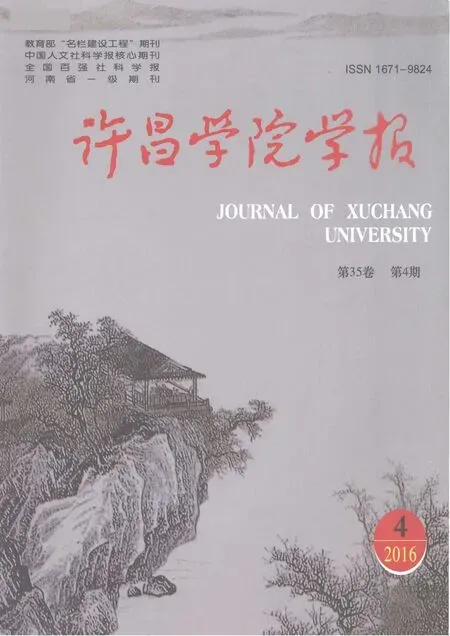钟嵘《诗品》与“知人论世”
2016-03-03葛刚岩
程 方,葛刚岩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钟嵘《诗品》与“知人论世”
程 方,葛刚岩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批评方法,它作为评论文学作品的一种原则不断流传和发展,在中国古代许多文论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批评方法的运用,钟嵘《诗品》也不例外。本文结合“知人论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发展状况,从诗歌发生、诗歌本质、诗歌风格三个方面深入探讨钟嵘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应用和发展。
钟嵘;诗品;知人论世;批评方法
作为“百代诗话之祖”,《诗品》集大成的批评方法是它成为诗学经典的重要原因。钟嵘《诗品》运用了“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其异同”、“喻以形象”、“知人论世”、“寻章摘句”[1]159等多种文学批评方法,在吸取前人批评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方法体系。其中“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是中国古代诗学中比较常见的社会历史批评,由于钟嵘所在六朝时代的诗歌批评是以审美为中心,因而历来学者对于《诗品》的“知人论世”都是简单带过,未有深入探讨过钟嵘《诗品》对于“知人论世”这一批评方法的运用。
一、“知人论世”的诠释与发展
“知人论世”出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192孟子原意并非是论诗,而是谈“尚友”的问题,不仅是交今世之友,还把交友范围扩大到古代。由于古人已往,唯留诗书作为交友的依凭,于是便引申出在颂诗读书的文学活动中知其人、论其世的文学批评观念。
孟子“知人论世”这一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论语》中多次出现“其言”、“其人”、“尚友”关系的论述:
吾日三省吾身……与朋友交而不信乎?[3]3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3]45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3]132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3]155
不知言,无以知人也。[3]211
儒家十分看重在修身、交友过程中的言行一致,认为言行一致是君子之德,认为在与朋友交往过程中要通过“文”、“言”来判断“其人”,“言而有信”之人方值得交往。“言而有信”指“言”与“行”一致。“言”为人外在的表现,“行”为人道德品质的具体实践,儒家要求言行一致也可以引申为要求“言”与“人”的一致,“知言”也就与“知人”分不开。《论语·季氏》说:“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3]177可知“见其人”是比“闻其语”更难的境界。而且儒家对“行”的重视远远高于“言”,因为“言”与“人”有距离,而“行”几乎就是“人”的显现、化身,因此“知人”便有“知其为人”、“知其行”的意思。孟子是在“尚友”的范围之内谈论“知人论世”的,他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述《论语》以“言”、“文”作为朋友“交”、“会”之凭借等等主张的影响,是对孔子有关“知言”、“知人”及论“文”与“友”之关系等言论的继承和发展。在孟子之后,荀子进一步论述了在读书过程中对“其人”的重视: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4]13-14
郝懿行认为“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之“方”为“依傍”之义,“言亲近其人而习闻其说,则禀仰师承,周遍于世务矣”[4]14。王先谦则认为“习”与“近”意相通,“言习其说即知是近其人”[4]14。无论“方”与“习”字如何解释,荀子是肯定“学”与“其人”关系的。而后面的“好其人”,郭嵩焘解释为“中心悦而诚服、亲炙之深者也”[4]14。无论是孟子的“知其人”还是荀子的“近其人”、“好其人”,都是将“学”(读诗书)与“其人”结合起来,对“其人”投入情感。
荀子之后,“知人论世”这一思想在司马迁《史记》中得到了发展。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品评褒贬蕴含了自身的情感,尤其是在为自己所敬佩喜爱的人物作传时,如《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5]421-422司马迁感叹“虽不能至,心乡往之”、“想见其为人”都表达了一种史学家在读史、写史过程中想要越千载与古人面晤心交的渴望。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5]632更是表达了读古人作品时,知古人经历、与古人共情的一种感受。这种“知人论世”观还被司马迁发展为“发愤著书”说: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6]4368
正是由于了解古人“其人”、“其世”,知道其伟大作品的背后是其运命的曲折悲惨和心境的痛苦郁结,司马迁才从其中看到了他们的生活经历与“发愤著书”的因果关系。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虽然依然带有儒家对道德价值追慕向往和著书立说以待后人的功用意味,却也将“知人论世”从儒家的道德修身层面拉入了文学批评层面,为后来钟嵘《诗品》中“怨”的文学发生论奠定了基础。
从传统儒家思想范畴发展出来“知人论世”并没有被六朝文人弃之不用,六朝文人只是改变了它作为儒家思想观念寓训勉以修身正德的面貌,去除了其中正襟危坐的道德意味,更多地关注个体身世际遇和情感。如果说司马迁是把“知人论世”朝文学批评的方向拉动了一步,那么六朝的谢灵运、刘勰就是分别从诗歌创作和理论阐释两个方面充分将“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原则进行了应用。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诗中每一首的小序都可以看作是对“知人论世”这一文学批评原则的应用。拟王粲诗之小序:“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7]149拟陈琳诗之小序:“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7]152拟徐干诗小序:“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7]154拟刘祯诗之小序:“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7]156拟应玚诗小序:“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7]159拟阮瑀诗之小序:“管书记之任,故有优渥之言。”[7]162拟曹植诗之小序:“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磋。”[7]164八首诗歌的小序皆以所拟诗人的生平际遇及个性特征把握诗歌的风格特点。正是由于在阅读诗人作品时把握住了“其人”、“其世”、“其诗”三者之间的关系,谢灵运才能拟出与原诗人相似风格的诗歌,从这一点来说,《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是从诗歌鉴赏和创作两个方面很好地应用了“知人论世”这一思想。谢灵运以诗歌创作践行对“知人论世”的运用,而刘勰《文心雕龙》则对“知人论世”说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阐释。《文心雕龙》中对“知人论世”的应用随处可见:《原道》篇“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8]2论述“圣”与“文”的关系;《时序》篇“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8]545,说明了文学风格与时代的关系;《情采》篇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虚假夸饰、繁芜失实的“为文而造情”,从创作角度表达了对“其文”所传达的“其人”情感的真实性的赞赏;《知音》篇“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8]600,则将文学创作和批评鉴赏两方面都与作者情志结合起来。
二、钟嵘《诗品》与“知人论世”
钟嵘《诗品》将诗歌与诗人的气质性格、品德、身世遭际结合起来考察,在前人的基础上,充分应用和发展了“知人论世”这一批评方法。“知人论世”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诗品》,其中许多诗学理论都是钟嵘在运用“知人论世”的基础之上而提出的。
(一)诗歌发生论
“知人论世”是“提供作家的整个身世和社会、历史背景材料,以把握该作家所有作品理解鉴赏的一种方法”[9]96。虽然“知人论事”多用于文学鉴赏,但钟嵘《诗品》的诗歌发生论却也是在运用这一批评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诗品· 序》写道:“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10]56钟嵘将诗歌与诗人的境遇、诗人的情感三者紧密结合起来,认为诗歌是诗人经历一定的境遇,心感而后歌之咏之。他重视“怨”这种情感,既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也借鉴了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中对诗人遭遇流离辛苦的人生经历的关注。如在“晋宏农太守郭璞”条中钟嵘认为“坎壈咏怀”为其游仙诗本旨,从诗人人生境遇和情感入手探讨郭璞诗歌的创作缘由。不仅如此,钟嵘在《诗品》中所引用的一些人物的佳话故事也表现了他在文学发生论中对“知人论世”这一思想的应用。如在“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中钟嵘摘录《谢氏家录》中故事一则:“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10]372此故事虽是摘录在谢惠连之评语中以表现谢惠连之才情对谢灵运亦有影响的,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交代了谢灵运的创作因由,表达了谢灵运之文学创作是在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下而发生的。又如钟嵘评江淹时用“郭璞索回五色笔”这样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来阐释“江郎才尽”的原因,也有将文学发生论与诗人禀赋、身世、际遇相联系的意味。
(二)诗歌本质论
汉末以来,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个体遭遇着离乱悲苦,个人生命之悲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钟嵘《诗品》描述了大量因时运际遇而心中悲怨的人的情感:“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0]56钟嵘这一段话所体现的既是“诗由情发”的诗歌发生论,也是诗歌应当“吟咏情性”的诗歌本质论。钟嵘认为诗歌抒发的是源于个人人生经历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是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本质原因。“‘《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10]56,钟嵘非常明确地指出诗歌是个人情怀的宣泄和抒发,能够使穷困之人安定心绪,使孤苦之人缓解愁闷,这不仅是诗歌的功能,更是诗歌体现人的喜乐哀怨和自然性情的本质,正是由于诗歌“吟咏性情”的这种本质,诗人创作和读者鉴赏才能分别从写诗、读诗的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理安慰。
钟嵘在对诗人进行评论时十分关注其“怨”情,在钟嵘看来,在众多情感中,“怨”情最能体现情之本质。他所强调的“情”是以“怨”为核心的生命遭际之情,他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10]106,评班婕妤“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10]113,评秦嘉夫妇“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10]249。在汉末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之中,钟嵘深切感受到诗人的哀怨与痛苦,清楚地看到这些诗人或为逐臣,或为弃妇,或壮志难酬,或生离死别,他们抑郁不平、悲愁愤恨等情绪积于胸中,感荡心怀,发言为诗。钟嵘认为诗人们这些情感都是与其个人身世经历密切相关的:李陵为名将之子,败降匈奴故“声颓身丧”;班婕妤失宠,充园陵故“怨深”;秦嘉夫妇往还曲折,故“可伤”……这些诗人的“怨”正是“其人”在“其世”遭遇各种曲折的个体心理感受,是完全脱离了儒家事功属性的“怨”。钟嵘正是以“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观念来分析考察诗人身世、遭际与诗作缘由,才能提出以“怨”为核心的“吟咏性情”的诗歌本质论。
(三)诗歌风格论
钟嵘三品论诗,将诗人诗歌风格分为国风、楚辞、小雅三类,并依此具体分析每一位诗人的诗歌风格。在分析诗歌风格时,钟嵘将诗人身世遭际与诗歌风格联系起来考察。如在“汉都尉李陵”条中详细介绍李陵身世境遇:“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10]106正是由于悲惨境遇才使李陵“文多凄怨”。“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10]106更是明确表达了诗人经历决定诗风这一观点。评刘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10]310,也是将诗人诗风与诗人经历结合起来。在评嵇康时,钟嵘将诗人性格与诗歌风格结合起来,历史上嵇康拒绝钟会,绝交山涛,鄙视权贵,狂放任性,钟嵘评论嵇康“过于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10]266,这句话正是将嵇康性格与诗歌风格合二为一所进行的评价,是在充分了解嵇康所处之时代风貌和其人生经历、个人性格的基础之上,联系其诗作而总结出来的。钟嵘评陶潜称其“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10]336-337,山樵暇注钟嵘此语曰:“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辞,所以能尔。”[11]42可知陶渊明以日常生活中事入诗歌,无一丝伪饰,文如其人,自然淳朴。钟嵘评陶潜,看到了陶潜德行、个性与其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称赞陶渊明人格与诗歌俱真淳,正是用了“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还有钟嵘在评谢灵运时,以一则佳话说明“谢客儿”之名的由来:“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10]201钟嵘指出谢灵运因“兴多才高”,所以“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复,宜哉”[10]201,这是以作家才性论其作品风格,而钟嵘所讲“谢客儿”由来的这则带有神秘色彩的佳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谢灵运之才高先天有之。另外杜室是奉道之家静室,谢灵运寄养于修道之家的经历是否也影响了他的诗歌风貌,这一点钟嵘虽未言明,但对照谢灵运之诗歌会发现谢灵运追求道家思想境界,向慕道家仙境、养生术和得道高人的情怀随处可见:“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7]70“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7]80“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7]141“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7]78……这些诗句都体现了道家思想对谢灵运诗歌的影响。“谢客儿”这则故事,后来多疑是后人羼入,因其无关谢诗,与钟嵘《诗品》体例不一,“钟氏若引故事,必以证诗人之诗”[10]207。但从钟嵘“知人论世”的运用角度来看,以此故事无关谢诗而入羼入之说可破,“谢客儿”这则故事正是钟嵘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挖掘了谢灵运其人才性和生长环境对其诗歌风格的作用。
结语
钟嵘为诗人寻源判风格,讲述诗人的人生经历、个性品德,谈论诗人的逸闻趣事,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对“知人论世”批评方法的应用和发展。汉末至六朝,社会动荡不安,诗人更多地关注自身,抒发人生无常、命若朝露的感叹,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钟嵘继承了传统的“知人论世”说,改变了其道德评价层面的伦理学内涵,而代之以更多审美层面的批评形态,钟嵘《诗品》中的诗歌发生论、诗歌本质论和诗歌风格论等诗歌理论都由钟嵘使用和发展“知人论世”这一批评原则进行了成功的阐释。
[1]张伯伟.钟嵘《诗品》的批评方法论[J] .中国社会科学,1986(3):159-170.
[2]孟子[M].宁镇疆,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
[3]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王先谦.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5]司马迁.史记[M]. 长沙:岳麓书社,1988.
[6]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黄节.谢康乐诗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8]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2.
[9]曹旭.摘句批评·本事批评· 形象批评及其他——《诗品》批评方法论之二[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4):94-98 .
[10]曹旭.诗品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1]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责任编辑:郑国瑞
Zhong Rong’s Shi Pin and Zhi Ren Lun Shi
CHENG Fang,GE Gang-y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Zhi Ren Lun Shi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ritical method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critical method, it's been undergoing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as used in many ancient critical writings, includingShiPin. By analyzing the deep meaning of this method,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critical method inShiPinfrom three aspects: the occurrence, essence and style of poetry.
Zhong Rong; Shi Pin; Zhi Ren Lun Shi; Critical methods
2016-3-28
程方(1990—),女,河南南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葛刚岩(1971—),男,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汉唐文学与文化。
I206
A
1671-9824(2016)04-0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