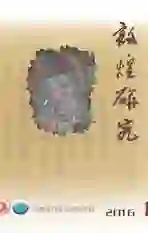敦煌伯3813唐判与宋代花判
2016-03-02沈如泉
内容摘要:敦煌文献伯3813所录唐代判词中,有数则判词与存世唐判如《龙筋凤髓判》等相比较都有明显的差异。其叙事均稍为繁复、滑稽戏谑的特征明显。上述特点显示伯3813唐判中部分判词已经开始偏离“临政治民”的功能,而逐渐带有世俗化与娱乐化的倾向。这些判词与南宋学者洪迈《容斋随笔》所述“世俗喜道琐屑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的特点相近。就文体渊源而言,敦煌伯3813唐判中部分判词虽无“花判”之名,却基本具备了后世花判的主要特点,实为宋代花判之滥觞。
关键词:敦煌文书;判词;花判;骈文;文体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1-0085-07
Abstract: P.3813 contains several court verdicts of the Tang dynasty that greatly differ from other verdicts of the time. Written with uncommonly complicated narratives and interesting details, these verdicts not only accomplish their trial function, but also tend to be close to life and entertainment. The authors additionally observe that the written characters are similar to the content of Rongzhai Suibi as written by Hong Mai. In terms of stylistic origins, the court verdicts of P.3813 can be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Hua-pan(verdicts in parallel style), 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referred to as such.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court verdicts; verdicts in parallel style; parallel prose; style
一 宋代花判的主要特点
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卷10“唐书判”条中曾提到当时有一种在世俗社会中流行的文体叫“花判”,该文记载:
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国初尚有唐余波,久而革去之。但体貌丰伟,用以取人,未为至论。[1]
近年来关于判词的文学性研究,特别是当论及花判的时候,学者们基本是以洪迈这段话作为立论基础的,如吴承学从文体学角度分析判词的《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及苗怀明《中国古代判词的文学化进程及其文学品格》等文章[2-3]。笔者亦尝撰《宋代花判新探》一文,对吴、苗等学者观点有补充和商榷[4]。
根据笔者考查,至迟在南宋初已成书的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就有关于花判的记录,这比洪迈《容斋随笔》中对花判的记录还要早。此外,在罗烨的《新编醉翁谈录》及南宋末年陈元靓所编《事林广记》中有更多明确标为花判公案的故事。二书共收录16条花判公案,其中13条内容基本一致,疑二书所录花判或源出一本,或彼此间有抄录关系。尽管此二书宋版早佚,传世刻本均经后世增删,不过学界仍普遍认为其中保留的宋代原始文献信息还是非常多的。结合这两部书中所记花判实例,我们可以认为洪迈对花判的描述基本符合宋代花判的特点,即宋代世俗喜闻乐道的花判其实源出唐判,不过其内容是以烟粉欢合、风月笑谈等琐细遗事为主,而“措辞滑稽”是花判的基本特征。宋代花判在文体方面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体现为:
第一,在花判公案中,滑稽戏谑的判词成为公案主体与关键。这类作品既不似《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许多判词要详细记载对案情的分析,也不似烟粉欢合类小说要对涉案人员情感纠葛、交往始末细细铺陈。花判公案中对案情的概括极其简略,有些细节甚至要依靠花判的内容来提供。
第二,宋代花判表现出文体的灵活性与综合性。唐判及北宋余靖判等均以典雅的骈文撰写,而宋代更多判文,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及刘克庄、文天祥集中的判词是用散体文写成,总之均是文体。而花判除以骈文撰就外,还可以诗、词为判,这是宋代花判对传统判文的新发展。
第三,花判公案中的断案常从市井人情出发,并不完全以法律条文为准绳。
目前我们对宋代花判的特点已经获得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也发现宋代花判源出唐判,但对从唐判到宋花判的文体演化路线了解的还不够清楚,其中若干细节尚待探讨。
本文试图说明敦煌伯3813唐判中部分判词从形式到内容都已蕴含了花判的一些基本要素,对我们探索花判起源颇具价值。
二 拟判是唐判发展为宋花判的关键环节
判词本为古代官吏断案之语,发展至唐代则因吏部铨选将其作为考试项目之一而特别为人所重视。自此,判词这种文体除了司法宣判功能外,也具备了人才选拔功能。对唐代科目选中试判的情况,吴宗国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五章“科目选”中有详细说明[5]。再结合《通典》等关于试判的相关记录,以下几点尤须留意:
1. 唐代,尤其在唐后期,考取拔萃科、平判入等是一般明经、进士及第者迅速升迁官职的捷径。这是造成选人无不习判的一个根本原因。对此,吴宗国已有论说。此外,据《通典》所述:“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其官。”[6]吏部铨选虽分身、言、书、判四项,实际在铨选中,书和判是结合在一起考核的,在考察判词内容的同时自然也就看到了考生书法;而察言观貌也是可同时进行的面试,无需分试。书、判为初试第一项,对身、言的考察应在试判通过后,在接下来的铨注环节里才有。若选人书、判不通过,则已淘汰出局,其他均无从谈起,这样就形成洪迈所说的“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的局面。《通典》还记载了“武夫求为文选,取书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6]360这样一条规定,也能说明书、判在铨选中的重要性。
2. 判词的评价标准除合乎法理外,更重文词。《通典》论铨选云:“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6]360这样看来判的评价标准就是“文理优长”,“文”自然指文辞语言要有文采,“理”是指判词内容必须符合法理人情。一篇合格判文不但要文辞雅丽,还应在判词撰写中体现出作者剖断案件、临政治民的能力。法学界学者对唐判研究较多,发现无论是实判还是拟判,基本能在唐律中找到司法依据,大都带有遵法理、顺人情的特点。
《通典》记贞观年间唐太宗尝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
“今吏部取人,独举其言辞刀笔,而不详才行,或授职数年,然后罪彰,虽刑戮继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对曰:“昔两汉取人,必本于乡闾选之,然后入官,是以称汉为多士。今每岁选集,动逾数千人,厚貌饰辞,何可知也。选曹但校其阶品而已。若抡才辨行,未见其术。”[6]363
这段对话中,太宗所云“吏部取人,独举其言辞刀笔”一语既说明判是最重要的考核项目,也表明对判词的评判还是以文辞为主。这与《通典》所载“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6]362也相符。至于杜如晦所说“厚貌饰辞,何可知也”,则说明通过外貌言语(身、言)考核人之不可靠。以判选人虽未尽善,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有效且相对公平的办法。后来,以判取人的考试方式一直沿袭下去,但具体的考核方式还是有所变化,因选人日多,考试也由简趋难。
《通典》载:
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6]361-362
由于考试题目从实判转为虚拟,这就为出题人命题及选人答判都向壁虚构创造了条件,而这正是判词撰写从实用化趋向文学化的一个关键。清人孙梅对此概括极好,他在《四六丛话》中论及唐代试判时有云:
唐以此试士,俾习法律,重其入彀,参之身、言、书之长。苟谢不能,不获与俊造选之列。选人以此拔萃,律学以此致身。于是润案牍以《诗》《书》,化刀笔为风雅。……设甲以为端,假乙以致诘。米盐琐细,不必尽丽刑章;蕉鹿纷纭,欲其稍介疑似。盗瓜逢幻,迹类子虚;锉草致伤,事同戏剧。[7]
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敦煌伯3813唐判中如《李膺溺死判》等数道判词就具有孙梅所说“润案牍以《诗》《书》,化刀笔为风雅”“琐细”“疑似”“迹类子虚”“事同戏剧”这些特点。而这些特点与宋代花判的主要文体特征也相近似。
三 伯3813唐判与宋代花判之关系
传世唐判如白居易《甲乙判》等,例用骈语写成。一道完整的判词一般分为判题和答判两部分。判题一般称“某某判”,说明案情,往往语极简略,多用甲乙代称涉案人员,与《通典》中所说的“假设甲乙,令其判断”相吻合。答判称“对”,用骈体写作,引经据典,堆垛故事,基本遵照唐代律令条文下骈体断语。这是唐判的一般行文结构与写作特点。然而敦煌文献中编号为伯3813的一组唐代判词中有部分判词与存世之唐代判词如《文苑英华》中收录的判文及《甲乙判》《龙筋凤髓判》等相较,却显得较为独特。
首先,伯3813唐判中数道判词判题叙事均稍为繁复,与常见唐代判词题目以三言两语简述案情不同。伯3813唐判中部分判词判题往往可视为一个情节较为曲折、内容相对完整的小故事,叙事性较强。
如《李膺溺死判》,判题曰:
奉判。郭泰、李膺,同船共济,但遭风浪,遂被覆舟。共得一桡,且浮且竞。膺为力弱,泰乃力强,推膺取桡,遂蒙至岸。膺失桡势,因而致殂。其妻阿宋,喧讼公庭。云其夫亡,乃由郭泰。泰[供](共)推膺取桡是实。[8]{1}
而《文苑英华》卷520所载《溺死判》与此案情相类,但判题仅寥寥数语,其文曰:
甲与乙同舟,既而甲惧水而投,因溺死。其家讼乙故杀,县断以疑。[9]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李膺溺死判》对李膺、郭泰同舟共济、覆舟争桡全过程的描述是完整、细致的,其中甚至包含了“且浮且竞”这样生动的细节。此判题虚拟明显,因为在整个案件中,当事双方一死一生,照理害人致死的郭泰不会不打自招,而死者妻子阿宋也无由得知案发细节,此事又别无旁证,本属一桩无头公案。但是拟题人却以叙事者全知视角,为读者也为文本中死者妻子提供了所有必要细节,以便构成诉讼条件。这显然是为敷衍成文而设置的机关,却刚好暴露了作者游戏笔墨的心态。
《文苑英华》所载唐判判题中也有个别情节稍显曲折、文字略为繁复的例子。卷538所载《孝女抱父尸出判》云:
钱塘人孙戬,少以迎涛为事。因八月迎涛,乘船冲涛,船覆至死。戬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设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尸出。县司以为纯孝,欲立碑。州司不许,乃禁媚容数日。[9]2749
孤立看待此文,似乎带有志怪小说的特点,不过假如我们将其与《后汉书·孝女曹娥传》比较一下的话,不难看出这不过是对史传文字的翻版。媚容的事迹与曹娥十分相似,反难引发联想,答判作者也只好说媚容“初均洛媛,持弱态以凌波;竟学曹娥,抱沉骸而出浪。论情足为纯孝,抚事不愧褒扬”[9]2749,基本属于照史直书、四平八稳的一份答卷,与《李膺溺死判》相比,明显缺少虚构的生动细节。
其次,滑稽戏谑的特征明显。一般唐判中涉案人物多泛称甲乙,即使有时为具体人物,但因案情无奇,文亦乏趣。伯3813唐判中则出现不少历史名人,他们涉案事件奇特,事迹虽皆出自杜撰,但与史书所载彼等生平、性格等又有关联。
如《李陵失弓马判》,题云:
奉判:弘教府队正李陵,往者从驾征辽,当在跸驻阵,临战遂失马亡弓。贼来相逼,陵乃以石乱投,贼徒大溃。总管以陵阵功,遂与第一勋,检勾依定,判破不与陵勋。未知若为处断?经纬乾坤,必藉九功之力;克平祸乱,先资七得之功。往以蕞尔朝鲜,久迷声教,据辽东以狼顾,凭蓟北以蜂飞。我皇凤跱龙旋,天临日镜,掩八纮而顿纲,笼万代以翔英。遂乃亲总六军,龚(躬)行九伐。羽林之骑,肃五校而风驱;倾飞之伦,俨七萃而云布。李陵雄心早着,壮志先闻,弯繁弱以从戎,负干将而应募。军临驻跸,贼徒蜂起,骇其不意,失马亡弓。眷彼事由,岂其情愿?于时凶徒渐逼,锋刃交临,乃援石代戈,且前交战。气拥万人之敌,胆壮匹夫之勇。投躯殒命,志在必摧,群寇詟威,卒徒鱼溃。是以丹诚所感,鲁阳回落日之光;忠节可期,耿恭飞枯泉之液。以今望古,彼实多惭。于时总管叙勋,陵乃功标第一。司勋勾检,咸亦无疑。兵部以临阵亡弓,弃其劳效。以愚管见,窃未弘通。且饰马弯弓,俱为战备,弓持御贼,马拟代劳,此非仪注合然,志在必摧凶丑。但人之秉性,工拙有殊;军事多权,理不专一。陵或不便乘马,情愿步行;或身拙弯弓,性工投石。不可约其军器,抑以不能。苟在破军,何妨取便。若马非私马,弓是官弓,于战自可录勋,言失亦须科罪。今若勋依旧定,罪更别推,庶使勇战之夫,见标功而励己;怯懦之士,闻定罪而惩心。自然赏罚合宜,功过无失。失纵有罪,公私未分,更仰下推,待至量断。[8]1597-1598
李陵,汉代名将,擅骑射,据《汉书》所载,天汉二年(前99),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后遭匈奴包围:
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10]
在唐判题目里李陵被安排为弘教府队正,随驾征辽东朝鲜。《汉书》记匈奴王用石头攻击李陵,重创李陵部队;而在唐判题中变为李陵投石,击溃了敌人。这显然是编写判题者有意的杜撰,颠倒事实的初衷或在于刁难考生,但结果却形成戏剧化效果。而答判者也顺水推舟,继续颠覆历史,汉代神射手到唐判里竟拙于弯弓而性工投石,并进一步把汉降将李陵吹嘘为大唐忠勇无双之士。
判词作者有时又会牵合本不相关的历史名人于一处,借助时空错位,造成一种“关公战秦琼”式的喜剧效果。如《石崇雇原宪涛井致死判》,题云:
奉判:石崇殷富,原宪家贫。崇乃用钱百文,雇宪涛井。井崩压宪致死,崇乃不告官司,惶惧之间,遂弃宪尸于青门外。武侯巡检,捉得崇送官司,请断。云:“原宪家途窘迫,特异常伦,饮啄无数粒之资,栖息乏一枝之分。遂乃佣身取给,肆力求资。两自相贪,遂令涛井。面欣断当,心悦交关,入井求钱,明非抑遣。宪乃井崩被压,因而致殂。死状虽关崇言,命实堪伤痛。自可告诸邻里,请以官司,具彼雇由,申兹死状。岂得弃尸荒野,致犯汤罗。眷彼无情,理难逃责。遂使恂恂朽质,望坟垅而无依;眇眇孤魂,仰灵榇其何托。武侯职当巡察,志在奉公。执崇虽复送官,仍恐未穷由绪。直云‘压死,死状谁明?空道弃尸,尸仍未检。检尸必无他损,推压复有根由,状实方可科辜,事疑无容断罪。宜堪问得实,待实量科。”[8]1597
石崇为西晋人,与贵戚王恺之徒以奢靡相尚,声誉不佳;而原宪为孔门高弟,生活清苦,个性狷介,一生安贫乐道,不肯与世俗合流。唐判中却将这两个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儿的人拽在一处,让石崇雇原宪涛(淘)井,时空错位、贫富反差,戏拟的意图非常明显。但是仅有此还不足以造成很强的喜剧效果,依照《唐律疏议》卷18《贼盗律》“残害死尸”条记载,唐代法律中有“诸残害死尸及弃尸水中者,各减斗杀罪一等”的规定,如果这则判词中的当事人用甲乙来替代,或者用两个具体而不知名的人物来命名,则此判最多成为法律的一个应用案例,我们读来不会发笑。可是当我们看到孔门那位高声宣称:“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的原宪为了一百文小钱就可以“佣身取给,肆力求资”,看到其 “面欣断当,心悦交关,入井求钱”的贪婪之状时,自然也就瓦解了我们心目中曾有的圣贤形象。将圣人变得庸俗、猥琐、无知是喜剧博取笑声的常用手段之一。
这种将正面人物出人意表地进行丑化,通过瓦解神圣而达到戏谑目的的判词还有前引《李膺溺死判》。李膺、郭泰二人,皆为东汉名士。李膺被誉为“天下楷模李元礼”,正因为他的品评,郭泰才名扬天下。郭泰本来也堪称人伦表率,史载:
(郭泰)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11]
在唐判中,两位清流领袖置身险境,为了一支能活命的桡而拼死相争,作为前辈与恩人的李膺最终因力弱被年轻力强的郭泰夺桡溺水而亡。这明显是拿古人开玩笑,借以讽刺人性的自私。判题所谓“郭泰、李膺,同船共济”其实也源自《后汉书》所记郭泰还乡时“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11]2225。尽管郭、李夺桡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但结局李死郭生似乎也事出有因。范晔称郭泰“身高八尺,容貌魁伟”,所以在争桡案中,他被安排成凶手。此外,建宁二年(169),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汉灵帝被宦官挟持,下诏捕杀李膺、杜密等名士百余人,并陆续杀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抓捕者千余人。郭泰讲学于家乡,以平素“不为危言覆论”,得免于党祸。作者将善于乱世存生的郭泰设想为“推膺取桡”,可能也是蓄意要调笑古圣先贤一下。
伯3813唐判中还有以明显违背情理的事件为主题,让历史名人充当风流孽债的配角,从而收到滑稽的效果。如《缪贤妇生子判》,题云:
奉判:黄门缪贤,先聘毛君女为妇,娶经三载,便诞一男。后五年,即逢恩赦。乃有西邻宋玉,追理其男,云与阿毛私通,遂生此子。依追毛问,乃承相许未奸。验儿酷似缪贤,论妇状似奸宋玉。未知儿合归谁族?[8]1599
历史上的缪贤是战国时赵国的宦者令,蔺相如的举荐者,在唐判里却被带上绿帽子。唐代宦者皆为阉人担任,自不能生育,判词一上来却说其婚后三年老婆给他生了孩子,明显是在吊读者胃口,让人猜想孩子的生父是谁。而宋玉,因为作过《登徒子好色赋》,赋中又赞美过东家之子,在唐判里就变为黄门缪贤的西邻,并与宦者的妻子私通有子了。
以上是通过判题虚拟的案件情节来分析伯3813唐判中的滑稽特点,其实在答判中这个特点进一步被放大。我们看到相关答判的陈述重点不像一般判词那样局限于对案情的法理分析,作者似乎更在乎这个故事本身,不惜耗费笔墨来填补判题中陈述不足之处。
如《缪贤妇生子判》答判云:
阿毛宦者之妻,久积摽梅之叹。春情易感,水情难留,眷彼芳年,能无怨旷?夜闻琴调,思托志于相如;朝望垝垣,遂留心于宋玉。因兹结念,夫复何疑。况玉住在西邻,连甍接栋,水火交贸,盖是其常;日久月深,自堪稠密。贤乃家风浅薄,本阙防闲,恣彼往来,素无闺禁。玉有悦毛之志,毛怀许玉之心,彼此既自相贪,偶合谁其限约。所欵虽言未合,当是惧此风声。妇人唯恶奸名,公府岂疑披露。未奸之语,寔此之由。相许之言,足堪明白。贤既身为宦者,理绝阴阳。妻诞一男,明非己胤。设令酷似,似亦何妨。今若相似者例许为儿,不似者即同行路,便恐家家有父,人人是男,诉父竞儿,此喧何已。宋玉承奸是实,毛亦奸状分明,奸罪并从赦原,生子理须归父。儿还宋玉,妇付缪贤。毛、宋往来,即宜断绝。[8]1599
答判对涉案三个人物的心理描写非常细致,阿毛作为宦者妻子的怨旷,宋玉对阿毛的日久生情,缪贤作为官员对披露真相的顾忌,这些在判题中都是缺失的,但在答判的推理过程中却逐一展现出来。
与此类似的还有《豆其谷遂宿饮被窃资判》,题云:
奉判:豆其、谷遂,本自风牛,同宿主人。遂邀其饮,加药令其闷乱,困后遂窃其资。所得之财,计当十匹。事发推勘,初拒不承。官司苦加拷谇,遂乃挛其双脚,后便吐实,乃款盗药不虚。未知盗药之人,若为科断?九刑是设,为四海之隄防;五礼爰陈,信兆庶之纲纪。莫不上防君子,下禁小人。欲使六合同风,万方攸则。谷遂幸沾唐化,须存廉耻之风;轻犯汤罗,自挂吞舟之网。行李与其相遇,因此 暂款生平,良宵同宿。主人遂乃密怀奸匿,外结金兰之好,内包溪壑之心,托风月以邀期,指林泉而命赏,啖兹芳酎,诱以甘言,意欲经求,便行酖毒。买药令其闷乱,困后遂窃其资。语窃虽似非强,加药自当强法。事发犹生拒讳,肆情侮弄官司。断狱须尽根源,据状便可拷谇,因拷遂挛双脚,挛后方始承赃。计理虽合死刑,孪脚还成笃疾。笃疾法当收赎,虽死只合输铜。正赃与倍赃,并合征还财主。案律云:犯时幼小,即从幼小之法;事发老疾,听依老疾之条。但狱赖平反,刑宜折衷,赏功宁重,罚罪须轻。虽云十匹之赃,断罪宜依上估,估既高下未定,赃亦多少难知。赃估既未可明,与夺凭何取定?宜牒市定估,待至量科。[8]1598
这则判词的判题也只是交代了案情梗概,而更多的细节是在答判中补充丰满起来的。比如“主人遂乃密怀奸匿,外结金兰之好,内包溪壑之心,托风月以邀期,指林泉而命赏,啖兹芳酎,诱以甘言,意欲经求,便行酖毒。买药令其闷乱,困后遂窃其资”一段,较之判题中“遂邀其饮,加药令其闷乱,困后遂窃其资”寥寥数语显然更为细致生动。
豆其、谷遂不是什么历史名人,可是如果留意谐音的话,豆其可能是“豆萁”,“谷遂”可能是“谷穗”,那么这道判就有拟人故事的特点了。拟人本是敦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制造幽默诙谐的文学手法,如《茶酒论》《百鸟名》《燕子赋》等。曹植《七步诗》借豆萁相煎讽骨肉相残,此判云谷遂对豆其“外结金兰之好,内包溪壑之心”恐怕也不是偶然巧合。而判词里“拷遂挛双脚”的严刑,也让人联想起用镰刀收割谷子的劳动场景。
上述特点显示伯3813唐判中部分判词已经开始有点偏离“临政治民”的功能,而文学想象成分逐渐增多,并具有世俗化与娱乐化的倾向。这些读来有趣的判词与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所述“花判”风格相近。这样看来,敦煌伯3813唐判中部分判词虽无“花判”之名,却基本具备了后世花判的主要特点,故将其视为宋花判之滥觞,或许是可以的。
当然,从敦煌伯3813唐判的出现到南宋花判的流行,这期间还有数百年的时间跨度,由于文献不足,我们至今尚难判断敦煌伯3813唐判中这些类似花判的作品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在当时及此后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文类,绵延不绝以致最终演变为南宋花判。我们现在所作的探讨仅仅是通过文本比较揭示出二者在书写特点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并进而推测其中应存在文体渊源关系而已{1}。
最后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在敦煌伯3813唐判中已经出现了文体特点与写作风格近似宋代花判的判词,但它们最初的创作动机却与花判不同,它们仍是为吏部铨选试判而作,并非为取悦读者而写,虽然事实上阅读它们难免会令人忍俊不禁{2}。同时,敦煌伯3813唐判带有“故事性”及“娱乐性”的特点,一方面恐怕是受到敦煌俗文学诙谐幽默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其拟题动机仍在于对考生“学术水平”的考察,如考生不能熟读经史子集,则面对以原宪、宋玉、缪贤、李陵、李膺、郭泰、石崇等历史人物而拟的判题恐怕是难以写出贴合人物身份的判词的。这与宋代花判只侧重游戏文字的特点依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参考文献:
[1]洪迈.容斋随笔[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129.
[2]吴承学.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J].文学遗产,1999(6):21-33.
[3]苗怀明.中国古代判词的文学化进程及其文学品格[J].江海学刊,2000(5):156-160.
[4]沈如泉.宋代花判新探[G]//新宋学: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8-116.
[5]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8-102.
[6]杜佑.通典[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360.
[7]孙梅.四六丛话[M].李金松,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86.
[8]陈尚君.全唐文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1600.
[9]李昉,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2662.
[10]班固.汉书:李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454-2455.
[11]范晔.后汉书:郭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9: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