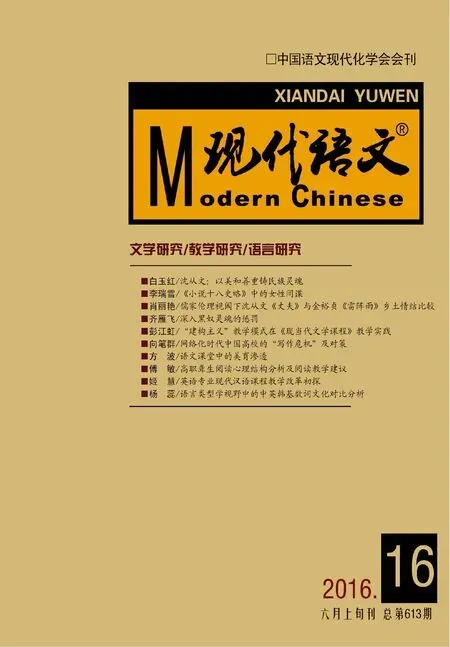从霸王别姬看人的生存状态
2016-03-02程振慧
○程振慧
从霸王别姬看人的生存状态
○程振慧
摘 要: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的小说家莫言,在话剧创作上也是卓有成就的。他以一种不同于传统戏剧又与当代极端的先锋戏剧有差别的创作姿态,创作了《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三篇优秀的剧作,显示出了其在戏剧创作上丰富的想象力和思想深度。文章主要从话剧《霸王别姬》中的女性形象来进行分析,从而彰显出莫言对于当下人的生存状态选择的一种思考。
关键词:莫言 《霸王别姬》 女性形象 生存状态
一、人性—人的生存境况
《霸王别姬》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史记·项羽本纪》,关于虞姬的描述只有寥寥几句:“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对于吕雉的描写也仅仅是把她作为人质置于垓下,着重阐述的她的狭隘、狠毒。由此可见,在传统的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语境中,虞姬只是作为和项羽的乌骓马同等地位的点缀和附属物而被一笔带过的,吕雉也仅仅是男性权力交换下的附属和牺牲品。对于这两个人物形象大家喜欢用善与恶、好与坏来评判,进而引申到人性方面,对于人性的问题,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曾经说过,人性的问题是无法用人的认知模式来解决的,“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包括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时,人的认知模式就不起作用了”[1]这样的回答一般会指向关于神的哲学概念上,那么究竟我们是谁,人之本性究竟是如何定义的,难道莫言仅仅是为了说明两个女性的性格善恶与正邪吗?阿伦特将这个问题指向了人存在的境况。作为从底层成长起来的作家莫言,他“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2]经历了幼年的辍学、贫困和饥饿,他对社会现实、历史、人性都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关注,特别是在对儿童、女性命运的书写中展现了他作家本身的责任和人文关怀。莫言曾经在一次专访中说过“这是一部让女人思索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女人的历史剧;这是一部让男人思索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男人的历史剧。”[3]这就正好跟阿伦特的意思不谋而和,那么莫言创造出的两位女性究竟是映射了什么样的人的生存境况呢?
二、正义的虞姬—被命运控制的人
虞姬作为该剧以爱情为至上的主角,她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角色。这一点显示了小说家身份对莫言话剧创作的影响,也正像莫言自己所说的他是站在自己想象的立场上去打扮虞姬这个形象的。
早期的虞姬是一个纯洁幼稚的小女孩,儿童的本性使她厌恶秦宫森严巍峨的高墙,对大自然的莺歌燕舞、小桥流水有着天然的向往与憧憬,亦或是对家乡有着难言的不舍与迷恋,所以她总是对男耕女织的生活怀揣着一种天真的幻想。这时的她以爱情为至上,带着小儿女的情怀的她爱也是自私的,为了爱情的专一,她丝毫不掩饰自己在丈夫面前的蛮横任性,也毫不留情地批驳范增的劝告,进而劝阻丈夫继承帝业。这与传统封建社会的女性作为臣服于男权下的“第二性”而存在,女性无论是宠姬还是妻子都只是男人的附属“在家从夫”的观念是有所差别的,在这里女性有着自我的意识,有着对自我未来生活的向往或规划。这是莫言对于现代女性命运思考的开始,早期虞姬生命中充满了青春的灿烂和对爱情至真的坚守,她真的就能摆脱自己历史上的悲剧命运吗?
这样的思考主要是通过虞姬与吕雉的唇战来完成的。她们的唇战是两个不同追求的女性在心灵深处遭遇的一次精神的遇合,也是虞姬成长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虞姬由对于权力、欲望的无知蒙昧状态中惊醒,听到吕雉所说“我也许会让汉王把你封为贵妃”[4]她明白了在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世界中,即使项羽放弃了王位,“成王败寇”的历史境遇中,自己只会成为一个被争夺的对象,那种田园式的男耕女织的生活只能是自己幻想中的残片。此时她已经从女孩成长成为了母亲,也正如项羽所言:“我多么想把我沉重的头颅伏在你光滑的膝盖上歇息片刻,我多么想让你柔软的小手抚摸我的颈项,像从前那样,像慈爱的母亲抚摸顽皮的儿子那样……”[5]她的爱也便化为了无私,为了爱情她能够真诚地跪在范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祈求得到帮助;她能够放弃自己从前爱情专一的想法,甘愿出走让夫。阿伦特在致奥登的信中曾经表达的那样,人在某种环境下会表现出一种不思考的行为,这种行为仅仅是为符合当时的大众期待而做出的无意义的行为,这种行为恰恰并不适于他的情形,这样他是彻底无助的,这种无助最大的悲哀是自身的毫不知情,虞姬后来所做的这一切选择并不是为自己的命运抗争,而是在无意识中陷入了对男性的崇拜、附庸与牺牲中。虞姬的自杀或许正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洁和项羽的尊严给自己的爱的一个最后的交代,无论是作为爱人还是母亲角色的虞姬依然难以摆脱在男性世界中自我意识欠缺的悲剧。正如莫言对虞姬介绍的那样“这个人物,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人物,不如说是一个文学典型更为合适”[6]。在这个典型人物身上体现着女性自身的纯洁、善良和正义,但也蕴含着她自始至终难以改变的悲剧命运,她始终是被命运控制着的悲剧人物。
三、邪恶的吕雉——推动自我命运的人
吕雉是剧作家倾情塑造的一个人物,莫言把她阐释为一个披着古装的现代人。在她身上保留了传统人物身上的权欲熏心、阴险狡诈、心黑手毒的品质,为了得到项羽,她一直变换着自己的骗术:
吕雉(冷笑)这是你们的定情之物,我的傻大王,当你在这里想断肝肠时,她已经把这美玉献给了汉王。
……
吕雉(故作悲伤)我那可怜的妹妹,倾国倾城的美人,她……她已经自缢身亡……[7]
这样的吕雉善于用骗术,显示出了人的邪恶的一面,但她却比传统人物可爱得多,莫言把吕雉作为女性最本真的属性突出显现出来,表现了一个不加掩饰的生命欲望的原始野性。她与刘邦的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感情世界长期得不到温存,她只有靠大女人的权势来流芳百世,她把男人看做自己肉体的附庸,她向往的只是他们年轻壮美的身体,因此无论她私通的是谁她都不会感到羞耻与不贞,她对于男人肉体的向往可以说是现代人的那种挑逗的程度,为了欲望她此刻将自己变为了伊甸园中的那条蛇。
在与虞姬的唇战中,激起了她内心作为女人对早已干涸的爱情的渴望,所以吕雉与虞姬干杯的理由是“为了你让我糊涂”[8],这是吕雉对自己是否真能抛下儿女情怀的一次怀疑,事实也证明吕雉确实陷于矛盾和内心的纠结之中,她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的这种冲突,一方面她为丈夫的帝业而自豪,带着对于权势的追求,她孤身一人来到垓下作为说客没有丝毫的恐惧;另一方面她难以完全无视自己作为母亲和女人的身份。在虞姬刚来看她时,她所表现的敏感、嫉妒和偏激的嘲讽便可看出她内心的脆弱与纠结。怀着对感情的幻想,她答应虞姬的计划,多次卑微倾情地对项羽诉说着自己的爱恋和内心的情感。她是一个疯狂的女人,从她的身上甚至能看到《雷雨》中繁漪的影子,当她觉得自己的爱情遭到践踏时,抱着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来毁灭他,所以她最后摸出匕首猛刺项羽。在这个人物身上莫言赋予她现代女性勇敢追求、不畏牺牲、敢爱敢恨的特质。其中也充斥着莫言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狡猾狂野如吕雉依然是以自己和孩儿的牺牲来完成自己丈夫的帝王梦想,自己对权势和名誉的追求依然要以丈夫为依托。对于爱情的追求只能以尊严的践踏来换取,甚至她也有和虞姬一样的愿为爱情放弃荣华“为大王生儿育女,操帚持箕”的打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吕雉对自我作为一个女性最需求东西的一种思考。即使自己靠着感情方面的压抑和空缺来完成自己流芳百世的大女人的梦想,其中会表现出一种性压抑的神经质的疯狂,但这恰恰是吕雉当时对自我人生境况的追求最了解最切合实际的思考,在这里男性与其说是女人的依附对象不如说是女人为实现自己的生存需求的利用对象。无论吕雉的结局是否得到男人的关怀和慰藉,这是她努力推动自身命运的一次勇敢地抗争。
四、正与邪的对立——人的生存境况
与其说莫言在霸王别姬中塑造的两个女性形象,不如说莫言在话剧中创造出了两个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两个人的选择,一方面有着吕雉的邪恶即对欲望的追求,对骗术的运用,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吕雉也是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如性欲的压抑,母女亲情的无法实现,但是她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明白当时自身最切实的需要;另一方面却又有着虞姬那样的心理,去适应一种当时环境而无意识中丧失思考的能力,而当下人对于虞姬的同情,对于吕雉的唾骂恰好说明了当下人生活的一种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大多数人陷入了生存的困境,这也许就是莫言在话剧中通过两个女性所表示的对于当下生存状况的理解吧。
注释:
[1]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时机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4页。
[2]莫言:《讲故事的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3]杨瑞春:《专访话剧<霸王别姬>编剧莫言 虞姬舞剑 意在吕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第26期。
[4]莫言:《我们的荆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5]莫言:《我们的荆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6]莫言:《我们的荆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7]莫言:《我们的荆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8]莫言:《我们的荆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程振慧 辽宁沈阳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1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