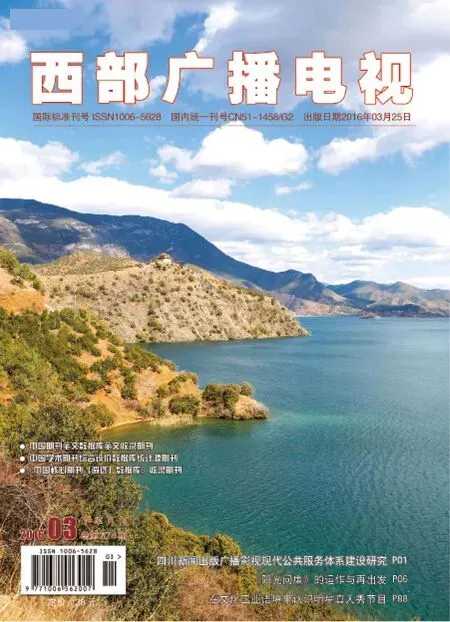基于在线社交网络的谣言传播机制浅析
2016-03-01孟婷
孟 婷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基于在线社交网络的谣言传播机制浅析
孟 婷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 要:本文从谣言的重要性模糊性特征入手,探究谣言是如何从个体扩散到群体,对谣言及传播网络的分析,有助于控制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谣言;传播机制;社交网络;临界大多数
在线社交网络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信息流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社交平台实名认证的产生,保证了用户的真实性;定位功能的出现,实现了传播的地域性;软件设备的后台运行,极大地增强了交互的实时性。然而,种种便利也为网络谣言的滋生和扩散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谣言的源头变得更为多元化,传播的实时性、影响力与传统传播方式不可同日而语,在此基础上,谣言传播扩散所带来的危害也大大增加。因此,对在线社交网络下的谣言传播进行相关研究,分析谣言传播的机理,为抑制谣言的传播扩散提供依据,是很有意义的课题。
1 关于谣言的研究
谣言像人的每一种说话方式一样,基本上是一个社会现象。[1]谣言自古有之,在《辞源》中释义为“民间流传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单从这个释义看,谣言并不具有贬义,在传播媒介仅限于纸笔及飞鸽传书的古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非常有限,对于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人们来说,谣言以生动的歌谣、谚语以及口耳相传的形式,更易于传播和交流,因此,在古代,谣言更多的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与一般信息不同,谣言中经常有一些残留的新闻成分,同时,在传播过程中缺少某些要素,或某些要素相互矛盾。上世纪40年代,奥尔波特提炼出谣言的两个基本要素,指出了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重要性和模糊性。[2]在此基础上,克罗斯进行了修正,他认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指出谣言受众的批判能力是影响谣言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胡珏提出,谣言=(事件的)关注度×(事件的)模糊度×(事件的)反常度,强调本身的反常性应是谣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伴随着网络社交时代的来临,巢乃鹏、黄娴认为,还应该把环境因素加上去,从而由服务器端,客户端和中介环境构成信源的往复任意传播。[3]除了上述客观因素,由于“偏颇吸收”的心理学现象的存在,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处理信息,寻找支持自己意见的证据。以上种种分析表明,谣言既具有一般信息的特征,即客观性,又存在传播者“偏颇吸收”所导致的主观性。谣言的特性决定了谣言在海量信息中更容易被人们发现和再传播,模糊性也给再传播提供了更多自主发挥的可能,在传播过程中获得的归属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成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传播动机。
2 传播网络分析
传播是一个过程,是参与者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符号交流和信息共享的过程,传播不是单向线性的,而是呈网络状的。传播网络正是人类利用符号手段所编织的交换讯息和思想的一种动态交换结构,基于这样的网络,个人完成自己的社会化过程,并将自己的生活编织进更大的网络中,从而使自己成为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一分子。传播网络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网络中的人际沟通关系为分析单位,分析网络中有关传播信息流的资料,从而弄清系统传播结构的一种方法。
格拉诺维特从时间量、情感强度、亲密关系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衡量一段关系的强弱度,强关系意味着两个个体间具有紧密联结的人际网络,这种内生性很强的网络决定着个体间接触的事物有很强的同质性,很难获取外部环境的信息。而个体获取外部信息的一个更有用的渠道则是来自于较疏远的熟人,也就是弱关系链,弱关系把这些较疏远的个体连接在一起,使不同个体所处的强关系群体的信息得到了交换,起着沟通不同派系的桥梁的作用。埃弗雷特.罗杰斯根据不同的信息流动模式,将人际传播网络分为互锁式人际网络和辐射式人际网络。互锁式人际网络是指网络中的任何两个成员之间都有关联,相反,辐射式人际网络是指除中心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有关联,其他成员之间互不存在关联。辐射式人际网络属于明显的弱关系,中心成员能与更多的外部成员交换信息。异质性代表着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思维方式,异质性传播网络的形成更具有难度,但是相比而言,具有异质性的个体所形成的沟通链能更有效地传播信息。
笔者认为,在某个谣言刚出现时,由于其模糊性及受众本身的批判性观点,它并不一定会引发关注,受众很可能不以为意,但如果在强关系网络内,特别是由这一集群的意见领袖发布后,谣言变得具有可信性,增加了受众传播这一谣言的意愿,直到谣言信息由弱关系网络传播扩散到另一集群,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回到谣言刚出现的时候,有些受众选择接受,有些则会选择忽略,这种现象可以用罗杰斯的“门槛理论”来解释,不同个体接受门槛不同,假设三个个体分别为a/b/c,a接受门槛为0,b接受门槛为1,c接受门槛为2,则在谣言传播过程中,a为最早接受的人,其次是b,最后影响c,而如果在这三个个体中不存在接受门槛为1的个体,则谣言则不会由a传播到c。
任何信息的扩散都有社会性特征,在这个扩散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临界大多数”。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中提到“临界大多数”概念,即在某一特定过程中,达到临界点后,该过程有了一种自我维持的能力。我们把这里提到的临界点看作传播过程中某一特殊的节点,同一群体内部的不同个体之间具有不同的采纳门槛。谣言传播从最开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际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传播方式的改变,当数量积累到这一特殊节点之后,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传播过程开始趋向稳定,有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能力。《创新的扩散》中出现的S型扩散曲线,显示了在创新扩散过程中,采用者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说明同一群体内部的不同个体之间具有不同的采纳门槛。D.J.Daley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谣言传播方式的数学模型,随着网络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引入可变聚类系数的无标度网络模型中,通过计算机模拟计算,得到一条与创新扩散类似的一条S型曲线。随着可变聚类系数的增大,谣言影响力最大值会有所减小,可变聚类系数对应为社交网络体系内的连接强度。
谣言从强关系网络到弱关系网络的传播过程,正是“临界大多数”的扩散过程:在强关系网络内,处于意见领袖角色或者采纳门槛最低的个体最先接收谣言信息,使谣言在这个强关系网络内扩散,经过一段时间或者得到一定量化积累以后,个体又通过各自的弱关系圈传播谣言信息。伴随这一过程,辟谣过程也逐渐进行,致使谣言传播有了自我维持的能力,从而进入一个稳定状态。而在这一过程中,信息公开、权威信息发布、社交网络关系强化等方式,均对抑制谣言传播有着明显作用。然而,由于“偏颇吸收”的存在,谣言的传播难以完全遏制。
3 结语
自媒体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使谣言对社会各领域、各方面的影响不断加强,理清谣言的传播网络,可以更有效控制谣言传播扩散。首先,从受众方面来说,要提高个体科学文化素质。在当代科技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更要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使他们可以利用所知所学,理性思考、客观评价,从而可以正确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期在面对互联网海量资讯时,可以主动对信息加以选择,不盲从;其次,应利用群体智慧。所有个体都处于不同群集之中,不管是强关系网络还是弱关系网络,个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不同个体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而由客观、理性个体组成的群体,更容易取其精华,形成有智慧的群体。群体行动新增的灵活性和力量,将有更多好的而不是坏的效应,从而使当前的改变归总仍是好的结果,当然,分享群体智慧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和渠道,要增加信息透明度,努力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增加公信力;“临界大多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节点,当谣言到达临界大多数点以后,它就有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能力,不管是传谣过程还是辟谣过程,都会导致谣言的影响范围更广,如何在谣言到达临界节点前控制其传播范围,减少谣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媒体和受众的共同责任。
参考文献:
[1]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2]巢乃鹏,黄娴:网络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6).
[3]卡斯·R·桑坦斯.谣言[M].张楠,迪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