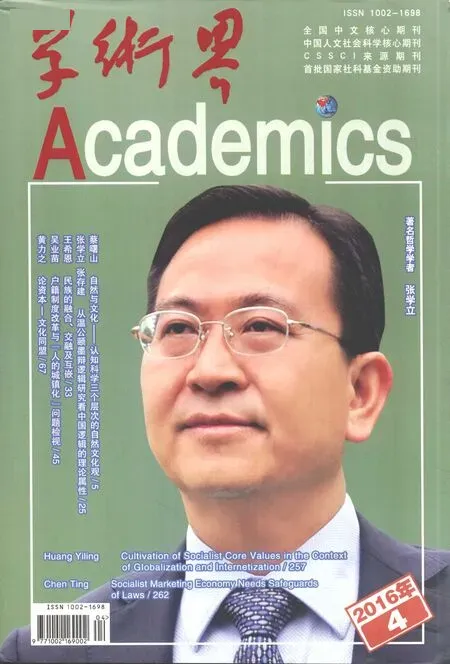清末民初时期关于国家理性和个人理性的论辩
——评梁启超宪政思想发展的两个主题
2016-02-28梁文生
○ 梁文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广东 中山 528400)
·学术史谭·
清末民初时期关于国家理性和个人理性的论辩
——评梁启超宪政思想发展的两个主题
○梁文生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广东中山528400)
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并且从国家理性出发,主张必经开明专制阶段才能实施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梁启超转而支持共和宪制,完成了由国家理性向个人理性的转变。梁启超宪政理念的实质在于保护公民权利,反对专制。
梁启超;宪政理念;国家理性;个人理性
一、引 言
清末民初,中国恰逢内忧外患之际,正如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列强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挑战,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富国强兵而提出回应的对策。〔1〕梁启超认为这个回应经历了“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转变过程,“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再从文化上感觉不足”。〔2〕在制度和文化层面,宪政改革才是强国之道,成为了当时的社会共识。这是一个从西方强国经验总结得来的普遍认识,成为那个时代主流的“思想气候”,可称之为“以宪法为驱动力进行国家变革的观念”。〔3〕
此时期存在三种主要的宪政观点:一是以清政府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实行维护君主专制的立宪制度;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借鉴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限制君权,保护公民的权利;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废除帝制,实行共和宪政制度。在“以宪法为驱动力进行国家变革”的思潮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是颇有社会影响力的。康、梁一贯主张清廷应该要进行君主立宪的宪政改革,戊戌变法事件更彰显其声望。其中,梁启超关于宪政的论述较为丰富,又因其宪政学说多变而颇具争议,因此,本文以梁启超为研究对象,更加能够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气候。
梁启超是立宪运动者,为世人公认。〔4〕然而,许多人不知道梁启超的宪政观就分为两个不同时期。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已为众知。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实行共和制宪法,梁启超亦欣然赞同。两个时期的态度和观点转变之快,固然可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辩解,“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其实,这个转变在梁启超的思想脉络里面是有迹可循的,笔者谓之为从国家理性到个人理性的发展过程。
二、梁启超宪政理念中的国家理性
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主张中国适宜实行君主立宪的宪政,并且在实行君主立宪之前,必须有一个“开明专制”阶段。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宪政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开明专制阶段,二是君主立宪实行阶段。梁启超在《开明专制》长文中对此作了详述。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中认为,世界各国分为非专制国家和专制国家两种。非专制国家较专制国家优胜,也是中国欲求达到之目标,然而中国现状态仍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梁启超进一步把专制国家分为完全专制和不完全专制国家,野蛮专制和开明专制国家。中国是不完全专制国家,原因是中国的专制未达到以完善制度实行专制之实的地步。但是,梁的重点是放在野蛮专制和开明专制的论述上。野蛮专制国家,其统治者只顾及自身利益而不顾及民众利益,乃代表了一种野蛮专制的精神。开明专制国家,其统治者虽则专制,然其目标以广大民众利益为上,乃代表开明专制的精神。简而言之,野蛮专制的治者利益与被治者利益相悖,开明专制的治者利益与被治者利益相合。从中国现实状况考虑,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专制传统悠久,遽然从专制变为非专制极为困难,且易致国家动乱,更为恰当的做法是先敦促清廷实行开明专制,由上及下改革,实现强国之后再行君主立宪。“有一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殚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5〕依其说,中国至少要花10至15年的“开明专制”,才能过渡到君主立宪。
梁启超的“宪政两阶段说”与其主张“三世之义”不无关系。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受其三世说影响甚巨,以致常常喜欢划分历史阶段。梁启超在康有为理论基础上推衍出自己的“三世之义”,“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而三世之发展,“与地球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阙之。”〔6〕梁启超主张的“三世之义”是与时间发展有关,不能即刻提前进入的。如果把“一君之世”对应专制时期,“民为政之世”对应宪政时期,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梁启超为何要在君主立宪之前设置一段长时间的“开明专制”阶段了。
从更深层次来看,梁启超的宪政两阶段说与其思想根源息息相关。首先,梁启超自幼深受传统思想熏陶,在儒学、佛学方面颇有造诣。当一个人遭遇社会突变,往往从其根基较深的知识构成中寻求思想支援。这往往形成了林毓生所谓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7〕传统思想的知识构成也可以解释梁启超为何成为改良派的代表之一。传统思想一般是由政府经过筛选后保留下的,特别是儒家思想本身就具有适应现世的特征,〔8〕因此,接受传统思想的知识分子往往属于体制内的利益集团分子,他们多为改良派,而不愿暴力推翻现有体制。梁启超虽然冀望中国成为非专制国家,但是他又不愿立即改变现状,而是希望通过改良实现君主立宪,故有“开明专制”的宪政阶段说。
其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儒家的经世致用因西方的冲击而受到严重侵蚀,且无力回应,致使中国政治处于一种没有文化方向的状态。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文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行动指南。梁启超亦不例外地成为这种思想过渡潮流中的一员。〔9〕从表面现象来看,西方列强的成功在于宪政。因此,宪政改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救国的良方。当然,西方的宪政模式不是单一的,有君主立宪、共和宪法等。然而,关于宪政的思想论述,以公民与国家孰先孰后的关系为标准,可分为应然论和实然论。应然论者认为,公民的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是由公民依社会契约组成的,国家权力应为保障公民权利服务,并且不能滥用。应然论多由霍布斯、洛克等学者从虚构的原始状态中推导出来的。最先宪政成功的国家,如英国,认同宪政应然论。实然论者不反对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但是强调国家优先于公民,其理由是国家不强何以保障公民权利?持实然论者多为后进国家,从客观现实出发,认为先强国而后安民。在理想层面,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是不变的。在清朝他反对专制,在民国他依然反对专制。他抱定的宗旨是实现民权政治”。〔10〕但是,在现实层面,梁启超选择的是宪政实然论,即先强国后安民,具体方法就是“开明专制”的宪政阶段说。
什么是国家理性?其含义复杂,德国学者认为国家自身拥有禀赋的理性,是不假外求的,国家就是依着这种理性而行动的。〔11〕实际上,显白地说,国家理性就是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采取理性的、有效率的行为达成目标,譬如,为了国家生存和安全而采取的理性行为。当然,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现代国家是一个理性化的进程,主要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国家理性是工具理性的进一步发展。〔12〕但是,两者的主体是最大的差别。国家理性的主体专指国家,工具理性的主体则十分广泛。另外,国家理性是源自近代西方政治的概念,三百年来经过了前后三期的定义过程。第一期定义主要以马基雅维利提倡的“国家利益至上”为代表。因为中世纪的西欧诸国均由权势家族、君主把持,如果提倡“国家利益”高于君主和政治家族的利益,则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统一,所以,此时的国家理性回答的是国家存在的“理由”或“理据”。在第二期,国家理性的概念追究民族国家应当具备何种心性与心智,何种国家情感、国家意志与国家目的。它表现为通过“启蒙”“革命”等运动,构建国家伦理。近百年来是国家理性定义发展的第三期。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膨胀,国家责任如脱缰野马不受束缚。因此,国家理性要求宪政制度等手段约束国家权力。〔13〕
梁启超的宪政阶段说,“最关心的不是开明专制,而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国家理性’”。〔14〕梁启超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方国家理性发展的第三期,那么,隐藏在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国家理性是何种理性?有学者认为,清末时期,知识分子围绕着“救国”与“建国”,三个阶段的理性一并齐来,应了“时间的丛集”的中国时代特征。〔15〕然而,仔细比照,梁启超的宪政阶段说与国家理性发展的三个时期颇有暗合之处,“开明专制”阶段对应于第一、二期的国家理性的定义,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开化民智。“宪政实施阶段”正是国家理性的第三期,通过宪政安排限制国家滥用公权。但是,梁启超能否真正了解国家理性的发展脉络,是颇值得怀疑的。他对宪政的理解或者更为深刻,那就是前述的应然论和实然论。梁启超很明白,宪政乃为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的,这是他一直孜孜以求的理想层面,这也是应然论者的目标。然而,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列强环视之下如何振兴,如何富强?客观情况驱使他从实然论出发,先强国后安民。可以说,在梁启超的思想脉络中,理想的和现实的两种矛盾观念互相纠缠,在不同条件下,选择哪一种都是合理的。
因此,在辛亥革命前期,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的“宪政阶段说”,是从国家理性出发,从宪政实然论出发,冀望构建一个强大的国家。
三、梁启超宪政理念中的个人理性
个人理性是对应国家理性而言的。如果说国家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延伸,那么个人理性更多倾向于价值理性。宪政实然论把国家放在优先于公民的地位,因此更强调追求国家强大的国家理性。而宪政应然论认为公民优先于国家,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应该限制国家权力。然而,撇开实然论和应然论的手段差异不论,两者都关注宪政的核心价值:公民权利,两者终极目标还是为了保护民权。一旦谈及公民权利,尚要解决何为“公民”的问题。“公民”是指一个社会或国家内所有人的集体,还是指单个人?唯名论认为人人有差异,“公民”应该是单数的,复数的公民(集体)是一个指称,不是实在的存在。相反,唯实论则认为“公民”是集体,是各个人汇集成的整体。如果把“公民”视为集体,那么这个集体极有可能等同于国家,如卢梭所说的“公意”,虽然卢梭把单个人叫做公民,把个体的结合者,“集体地称为人民”。〔16〕这种区分仍然未能解决公民的单数和复数哪个优先的问题。如果“公民”是互有差异的、不可替代的单个人,并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和权利,甚至每个人的权利是天赋的、平等的,那么“公民”必须具有个人理性。
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一样,也是与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关。个人理性是以个体性的出现为前提的。个体性是指个人意识的觉醒,个人拥有意志和自决的能力。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描述了个体性在近代欧洲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世纪的西欧封建制度要求个人泯灭个性,他们隶属于某个群体、教会或宫廷,“大部分人都默默无闻,个人性格很少被看到”,因为,“与作为某种群体的成员所共同享有的东西相比,区分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东西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情况在12世纪达到了顶点。〔17〕德国学者埃里希·弗罗姆也指出,中世纪与现代社会相比,主要特点是缺乏个人自由,每一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是被固定死的。〔18〕上述情形,正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称的“机械团结”社会。在机械团结社会中,每个个体是相同或相似的,他们没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缺乏社会分工,所以他们形成一个如环节虫式的社会,共享着相同的宗教信仰,重视刑法规范的调整。与此同时,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强调个体的差异性,个体之间形成紧密的社会分工,这种被称为“有机团结”的社会,不仅需要刑法规范,更着重民法规范的调整。〔19〕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从封建王朝迈向民族国家,个人理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迈克尔·欧克肖特所说,“人类个体性方面的成就改变了中世纪生活或思想的条件。”个体性先是在意大利出现,因为文艺复兴最先滥觞于当时的意大利,封建制度也最先在那里瓦解。个体性的出现,让个人意识到自我力量,从而提出了权利的要求。“每个权利意味着某种封建特权的废除”。当然,个体性的保护必须要求将个体利益转化为权利义务的国家工具,但是这个国家并非是传统的封建王朝,而为各个个体的代表,并且是具有相同民族特性的个体的代表所组成的现代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20〕同样,德国学者埃里希·弗罗姆也认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让中世纪的人逐步地“个体化”,并具备了自我力量,从而取得自由的权利。其中,文艺复兴让上层阶级个体化,宗教改革则实现中下层阶级的个体化。〔21〕从西欧的历史经验来看,个人理性应该早于国家理性出现。另外,权利是个人理性的核心,而个人理性是宪政的核心,理由在于宪政具体表现为法律,法律虽然在抽象层面规定整体公民的权利义务,但是在实际运作层面则表现为对个案中的个人权利的保护。不能保护各个个人现实的权利,国家的宪政实属无稽之谈。
个人理性是个人运用自己意志和理性,在生活中达到一种合理状态。什么是个人的合理状态呢?更深一层追问,就是人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埃里希·弗罗姆说,生命只有一个意义,这就是:自身活生生地去运动。〔22〕这样的答案无疑是说,人的本质存在于人的本身。活生生地去运动,也需要理性的行为。这样宽泛的答案并不能解答个人合理状态是什么。迈克尔·欧克肖特则认可康德的绝对命令,即自身就是目的,是绝对而自主的。他认为,一个人格追求自己的幸福是自然的追求,但是,自主人格存在一个普遍条件,就是“无论在他自己还是在他人那里,都把人当目的而决不是手段”。把人当作目的最重要的表现是,我们可以促进别人的幸福,但是不能以促进他人的“善”为借口而消灭他人的“自由”。〔23〕无论个人理性的概念如何抽象,如何争议不断,个人理性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而国家理性更多的是工具理性的深化。人可以组成社会,进而组成国家,如果没有人的存在,国家也只是无皮之毛。因此,重视人的本质才是根本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同样是宪政的永久主题。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的宪政观已从国家理性转向了个人理性。首先,他从赞同君主立宪到支持共和宪制,只是回归宪政的根本,把维护民权放在第一位。这正是个人理性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具体要求。其次,个人理性要求个人能够运用意志,理性地行动,从而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梁启超一直在建构一个“新民”的公民伦理的理想。“新民”既有私德又有公德,从而推动中国发展为现代国家。〔24〕西方“公民”一词也是从城市自治发展而来的,强调了公民参与和自治的能力。〔25〕梁启超的“新民”之目的,正是要提高民众作为“公民”应有的能力,无疑是重视个人理性的结果。当然,梁启超的“新民”说具有两大缺陷,一是他的“新民”理论不脱儒家“修身—治国”的模式,把私德与公德视为必然的关联关系,忽略通过制度建设来制约人性恶。二是他把“新民”伦理的成熟度与宪政建设直接挂钩,认为公民意识不强则不宜推行宪政。最后,与工具理性“单向”和“独白”的特性相比,个人理性则具有“双向”和“对话”的特性。所谓“单向”,就是只讲实效,不及其他,因此不能顾及人的多样性。“独白”则是相对于对话而言的。对话是双方互相协调,共同合作进而互相了解。独白即使考虑到对方的想法,也只是从策略角度出发,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实行自说自话式的行动。〔26〕与其相反,“双向”是指公民在理性行动时,不仅仅考虑自身利益,还考虑他人、社会,甚至国家等多方利益,从而平衡各方利益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这与“单向”考虑自身利益有重大区别。“对话”指公民最终采取的理性行为是通过多方对话而达成的,而不是独白式的专断行为。如果个人理性的“双向”和“对话”得到切实的贯彻,那么一个开放社会将会形成。进一步而言,每个公民依个人理性行事,把社团生活、良好社会以及公共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合理的状态,这就是公民社会应有之义。〔27〕体现公民个人理性的具体行动之一就是政治参与。梁启超认为,立宪政府是一个能够确保大多数人政治参与的制度。西方更多关注于政治参与的自由,而梁启超更强调政治参与本身,因为他相信政治参与能够建立一个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28〕尽管梁启超的宪政观与西方思想有所差异,然而,归根结底,他还是以个人理性为出发点,以达到维护民权的最终目的。
四、小 结
宪政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西方的宪政奠基于社会契约论。关于公民和国家的关系,社会契约论认为公民的天赋权利是首要的、平等的,公民通过契约建立国家,通过选举推选政府代表,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建立在公民的权利基础之上的,所以必须为公民的权利服务。为了防止国家和政府滥用权利,公民制定基本法律即宪法,从而制约公权力。虽然宪政的概念众说纷纭,但是毫无疑问,宪政主要指通过宪法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也有学者引申言之,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主要体现在行政力和司法权的分立和制衡。〔29〕由此看来,宪政的内在价值有二:一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现今世界各国的宪法一般由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的组成两大部分构成,乃其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
反对专制,保护公民权利,乃梁启超一以贯之的宪政理念,因此,梁启超的宪政观是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之上的,是符合宪政两大内在价值的。尽管梁启超提倡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与后来实行的共和宪制有别,但并不影响他的宪政观符合宪政内在价值的事实。另外,令人误解的是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的观念,然而,“开明专制”的目的首先追求国家富强,而后追求人民主权,这就是梁启超从国家理性出发的初衷。如果我们以同情的心理来解读,那么我们不难明白,一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坚持与妥协之间,可能存在诸多选择,但是保留民主和自由的宪政火种不息,仍然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
注释:
〔1〕John King Fairbank,The United State and China (Fourth Ed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p.193-195.
〔2〕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第7页。
〔3〕梁文生:《论孙中山在宪政实践中的实用主义》,《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4〕〔6〕〔10〕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12-13、3页。
〔5〕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梁启超全集》(第二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451-1486页。
〔7〕〔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页。
〔8〕〔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1-197页。
〔9〕〔14〕〔24〕〔28〕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0-211、182、169-193、143页。
〔11〕任剑涛:《国家理性:国家禀赋的或是社会限定的》,《学术研究》2011年第1期,第31-38页。
〔12〕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学海》2010年第5期,第114-120页。
〔13〕〔15〕许章润:《国家构建的法理图景》,《读书》2010年第9期,第29-35页。
〔1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页。
〔17〕〔20〕〔23〕〔英〕迈克尔·欧克肖特:《代议制民主中的大众》,《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87-88、88-92、90页。
〔18〕〔21〕〔22〕〔德〕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年,第61、71-72、340页。
〔19〕〔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172页。
〔25〕〔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梁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7-98页。
〔26〕张德胜:《儒商与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社会学之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27〕Michael Edwards,Civil Society, Polity, 2004, pp.90-92.
梁文生,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