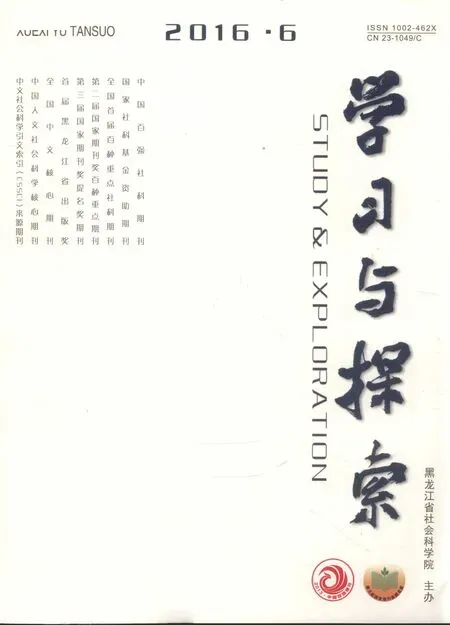从“再现”返回“表现”
——论当代诗歌写作的误区及突围
2016-02-28董迎春
董 迎 春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从“再现”返回“表现”
——论当代诗歌写作的误区及突围
董迎春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叙事把诗歌的再现推向了反讽的秩序化、单一化、中心化、复制化的写作趋势,背离了诗体语言的诗意、诗性凝聚的想象、审美空间。在重视“再现”叙事的同时也重视诗意的表现,在“再现”“表现”之间取得较好平衡的文学思维,有助于推动当代汉语诗歌的积极健康发展。
关键词:当代诗歌;第三代诗;朦胧诗;口语写作;表现/再现
诗之“表现”一说本无分歧,其诗意本位不言自明。这也是中国传统诗学与新诗以来的现代诗歌最基本的审美特征。朦胧诗之后,第三代诗出场,众语喧哗、极为热闹。诗歌由精英化、审美化逐渐转向凡俗化、审丑化,话语策略也由抒情诗(表现为主)转向叙事诗(再现为主)写作。这种再现式的叙事强调“诗到语言为止”(韩东)、“拒绝隐喻”(于坚),他们将表现的语言拉向日常客观物象的再现。这种再现的写作意识也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沙、沈浩波等颇为先锋的身体写作和下半身写作,以及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更为叛逆的废话写作(杨黎)和低诗歌(龙俊)等。
诗性思维趋向感性,更强调灵感与直觉,是人类极为重要的生命意识与认知途径。西方文化不断突破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即不断解构西方理性主义的价值中心。探讨当代诗歌的表现意识的诗学价值,对于增补、调整当代文化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再现偏重于模仿现实、关注客观物象。这种再现意识无疑与现实主义创作、大众文化的通俗性相吻合。第三代诗解构了朦胧诗的沉溺意象与透支抒情,不断用注重日常叙事的再现意识介入生活、关注日常,并以此解构、消解了朦胧诗以来的以语言为本体的表现意识。然而第三代诗、特别是口语写作一脉将再现意识推向了秩序化、中心化、标准化、单一化,渐渐忽视了诗学本体意义上语言表现意识。他们淡化与拒绝诗歌的修辞,这使得诗歌的表现力量渐于淡薄、式微。例如,第三代诗人中较有影响的伊沙,在20世纪90年代及新世纪较为重视以反讽为话语策略的再现,将反讽从修辞格转向一种认知态度,修复、增补了第三代口语写作中诗性缺失、智性不足的窘境,推进了当代诗歌的发展,但是反讽再现意识的运用仍旧改变不了当下汉语诗歌写作的单一化、雷同化现状。
一、失踪的“表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语写作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主流,其秩序化、中心化的写作趋势忽略了“表现”的价值与可能。重视日常经验、关注客观物象的“再现”意识忽略了诗体与语言意识,当代诗歌写作也自然遭遇到写作瓶颈。
古今中外诗歌在形式上体现为两种意识,即以抒情(表现)为主的意识和以叙事(再现)为主的意识。诗的抒情性与叙事性既是分离的,又在更多时候是融为一体的。诗歌以丰富的生活为前提,抒发了人类普适的(或然见出必然的)情感,通过一定语言形式、一定节奏(音乐感)以及各种修辞手段来表达诗人对世界、人生的存在认知以及意义、情感的独特感受。诗歌所要表现的也在于这样的诗歌意境和审美张力(也称为审美场或审美空间),召唤出读者相近的审美联想。“诗人是乐观的。他从语言内部寻找出路,他游戏于字形、字音、字义与书页的排版之间,像晶体一样,从限定的法则中造就全新的变幻的画面”[1]4,这就使得表现的诗歌充满了诗画之美、艺术之美,拓宽了诗艺表现生命意识的可能。
就古今中外的诗歌传统而言,诗歌无疑是“表现”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语言意识、诗体表现的自觉的本体追求。现代诗歌的发展往往将表现推向理想极致,探索隐秘的生命意识与人性遭遇时代挤压后所形成的存在体验。尽管表现/再现这两种不同的诗体意识构成了诗歌差异性技艺追求,然而现代诗歌的发展更着重于表现意识的思维与认同。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歌写作无疑是对现代诗歌书写理念的践行与深化。
当下诗歌创作自然也是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影响下的文学产物。纵观百年中国新诗(现代诗歌)的发展,象征主义在诗歌表现意识层面探索不少、成就颇大,对朦胧诗以来的现代诗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卞之琳的诗歌就充满了思辨美和知性美。他写道:“我要有你怀抱的形状/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鱼化石》);“眼底下绿带子不断的抽过去/电杆木量日子一段段溜过去”(《还乡》);“我喝了一口街上的朦胧”(《记录》);“友人带来雪意和五点钟”(《距离的组织》);“呕出一个乳白色的‘唉’”(《黄昏》);“记得在什么地方/我掏过一掬繁华”(《路》)。这类诗歌充满了现代诗歌表现的“思辨美”(beauty of intelligence),从中不难发现卞之琳的现代诗歌在生活的再现与诗意的表现之间找到了某种较好的平衡。卞之琳的学生、著名形式文论家赵毅衡教授曾指出他诗中的语言“嵌合”特征:“‘嵌合’的用法的运用,主要是‘实’动加‘虚’宾语名词。这类似于叶芝的诗,却更接近中国古典诗人‘炼’字后造成的效果。没有任何质感的(或质感不太好捉摸的)品质被作为质感词使用会扩大官感性范围,这可能是异类意象联网中效果最强烈的一种。”[2]237
超现实、变形、夸张、陌生化等现代技巧的运用,推动了现代诗歌表现形式与表现能力的实践过程,例如诗人兰波写道:“马车在天空上驰行”“公证人悬挂在他的表链上”“为早晨的牛奶,即上个世纪的深夜的喃喃自语阴郁至死”,天马行空的联想(幻想)颠覆了空间的秩序,让诗歌建构起诗意与诗性。在陌生化、新奇的视觉景观里再现了深度现实。“诗的比喻不必求相似,诗的象征不必求寄托。诗有自设无语言的魔力。虎纹可以‘冷’得像树皮,雨线可以‘懒’得像大腿,郁金香可以完整得像思想,当然清晨可以痛得像未做完的梦。”[2]276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由此获得了特殊的、神奇的、审美化、哲理化的文本效果与修辞力量,超现实的色彩是诗人情感的主观投射,不合现实的超现实想象引导读者在奇幻中试图理解深度现实。超现实、超验主义的写作对当下诗歌的语言表达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汉语凭借自身的隐喻特征和诗意自然展开的优势,吻合了现代诗歌的“表现”意识。
象征主义者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也将世界分成现象(现实)世界与本体(理想)世界两极,象征主义更认为这个世界既是二元又是一个统一整体,感应让彼此成为一种或此或彼、你中有我的整体合一关系,在时间上共存、在空间上互渗存在。显然,这种“感应”让象征主义的诗学实践在理论上指向了语言表现的无限丰富、广阔的话语空间。“作品不是对那些时时现存手边的个别存在者的再现,恰恰相反,它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3]。
现代诗歌的表现意识必然表现为诗体意识的回归,它也不断克服再现对现实的直接介入。现代诗歌的表现性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将现实简单地处理为社会现实与现实主义意义上的认同。现实主义一直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心话语,它的话语特征无疑是现实的、叙事的、还原的,再现的。而朦胧诗的出现无疑让这种朦胧、晦涩的语言表现展现出了现代诗歌的朦胧之美和张力之美。但是朦胧诗不久就被“第三代诗”的口语写作(再现的叙事话语)所取代。“口语写作”源于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中于坚、韩东、伊沙等诗人的写作,他们重视叙事的再现与物的还原的冷抒情、零度叙事,改变了朦胧诗高蹈的、矫情的抒情话语,让诗歌回归到对时代、社会的客观关注,这无疑是积极的、有效的,再现性的现实话语与现实精神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但发展多年之后,“口语写作”呈现出中心化、秩序化、模式化、雷同化的现象,其审丑化、粗俗化的价值立场值得警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是进行语言为本体、诗艺探索为主的写作,他们有效地回避了现实的直接介入,打通了现实与精神,直接介入与现代技巧之间的融合,既保证了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和时代意识,同时也进入了表现意识的现代诗歌写作,因而在现实的批判性与诗艺的表现性之间找到一个较好平衡。王家新、西川、陈东东、张曙光等知识分子诗人不仅继承了朦胧诗以来的精英话语,还关注时代性、经验性的叙事再现,强化了诗歌的时代与社会关怀意识,同时也重视精神性、艺术性的技艺探索。以陈先发、杨键、谭延桐、李青松、鲁西西等为代表的神性写作追求诗歌、哲学、宗教结合,不断打破精神边界,其表现意识则走向了直觉的、灵感的、感官的、超验的精神创造。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更具有文学探索上的难度、高度,它是艺术、文化、宗教融为一体的写作尝试。神性写作作为一种精神、传统、艺术性、宗教性的诗写追求,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间”自然生长,但其形成的精神合力与诗体意识却成为一股不可小看的诗潮,张清华《鄙俗时代与神性写作》[4]、枕戈《80后之“神性写作”与“口语写作”》[5]、荆亚平《神性写作:意义及困境》[6]等文章均对神性写作进行了评论。以昌耀、海子为代表的孤寂的“大诗写作”表现出语言回归的本体意识、深刻的知性与生命情怀,语言布满了思辨的张力与深沉。“大诗写作”又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性、神性写作的超验性的进一步发展,趋向“诗与真理、民族与人类合一”的大抒情成为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某种典范,也影响到新世纪以来的积极有效的当代诗歌书写与精神担当。
再现的叙事话语自然清新、易读,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口语诗歌更是隐含着某种秩序化、中心化的趋势。诗评家罗振亚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叙事“对所指的轻视逃离使诗歌降格为情绪层的发泄,关涉日常生活具事、琐屑的指称性语言叠印则使诗歌远离了深度,削弱了可贵的思索和表现功能。对‘此在’形而下的过度倚重,淡化了对蕴涵着更高境界的‘彼在’的关注,这势必因缺失对灵魂世界的介入和乌托邦性质而流于庸常平面,只提供一种时态或现在现场,而无法完全将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性经验。叙事含混啰唆,绘声绘色缠绕枝蔓,臃肿枯燥,文本模糊,亏损了诗性的简洁和纯正”[7]。“口语”作为语言解构了朦胧诗以来的过度抒情(表现),但是其又重新落入新的话语窠臼。再现的叙事的口语写作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在叙事性特征方面可以与戏剧性的冲突、矛盾相转化,在形式技巧中则可以借用口语写作中的语言机智、幽默诙谐,增加诗歌表现的感染力量,语言机智则表现出了诗人的“聪明主义”以及对语言独特的处理与设置能力。“为什么诗本来就遵循‘聪明主义’?因为诗给我们的不是意义,而只是一种意义之可能。诗的意义悬搁而不落实,许诺而不兑现,一首诗让作者和读者乐不释手,就是靠从头到尾把话有趣地说错。读者不是在读别人的词句,而是想读出自己。因此,一首好诗是一个谜语,字面好像有个意思,字没有写到的地方,却躲藏着别的意思。谜底可以是大聪明,谜面必须小聪明,谜底似有若无不可捉摸,谜面才让人着迷。”[8]
当代诗歌写作中的日常化、平民化、大众化、快感化的“口语写作”的再现特征,纠结于平淡、庸常情绪的展现,却丧失了汉语诗歌的语言之思和知性之美。当然对于具有某种独特知识与精神背景、并经过一定的文学训练的专业读者来说,他们还是能够接受或者正确理解现代诗歌的难懂性问题的。“阅读诗,就是诗本身在阅读中表现为作品,是诗在由读者打开着的空间里产生了迎接它的那阅读,阅读变成读的能力,变成能力和不可能之间,变成同阅读时刻连在一起的能力和同写作时刻连在一起的不可能之间的敞开的交流”[9]。可见,专业读者带有某种深度体验、认知能力的阅读,必然能够提升汉语诗歌的现代主义技巧,同时在存在式的再现与表现的可能之间找到合法化的阐释前提。
理解与阐释当代诗歌也自然需要读者有较好的“感受力”。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对“感受力”是这样强调的:“我们通过艺术获得的知识是对某物的感知过程的形式或风格的一种体验,而不是关于某物(如某个事实或某种道德判断)的知识。……艺术作品提供了一类被加以构思设计以显示不可抗拒之魅力的体验。但艺术若没有体验主体的合谋,则无法实施其引诱。”[10]现代诗歌的情绪暗示与幽暗意识,渐被读者感知、认同,诗歌产生了较好的文本效果、传播力量。诗歌是时间的形而上学的沉思,哲理上的思辨、知性之美,推动了诗歌表现意识在较广泛的诗人群体与读者群接受与认同。
重视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现代表现技巧,就不得不要求进行现代诗歌的普及化教育,不断培育汉语诗歌重审美化、艺术化的诗体意识,这样才能有效维系、推动当代汉语诗歌的健康发展。“现代诗歌”是借助现代语言,使用现代修辞(隐喻、陌生化、通感、超现实主义等)、表现现代人的价值与情感的可能、方式、生命的存在意识不断觉醒为主题的诗歌。当代诗歌在坚持诗意、诗性的表现的前提与基础上突围,这必然也关乎写作的主观状态、价值立场,“表现”的意识往往要与现实“再现”保持某种距离,不断在“再现”与“表现”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扩充当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丰富性。
汉语诗歌当下突围的路径之一,就是让诗歌由当下走向反讽中心主义叙事的再现,重返表现意识下诗体语言的关注与深度拓展。叙事的话语的中心化和秩序化已经挤压、损耗了诗歌的表现,如何在汉语的“再现”与“表现”之间找到某种诗艺平衡,变成一种或此或彼的写作关系,无疑是当代诗歌最应重视的问题意识之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代诗歌的再现性写作已经到了问题必须正视的时刻,重新认识语言的表现意识更有待进一步深化与探索。
二、“表现”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叙事,通过对事物的还原与再现,解构了朦胧诗重视意象与抒情的审美特征,但是发展中也呈现出口语化、琐碎化的审丑疲劳,走向复制化、单一化的写作趋势。消解诗性、损耗诗意的“非诗”再现写作拒绝了诗之“表现”功能和语言上对诗性、诗意的追求,当下诗写中的“再现”叙事背离了语言与技巧上的“表现”追求,诗歌创作出现了雷同与复制现象。走向极端化、中心论的口语策略,过分强调再现与叙事,远离了诗的语言表现意识,远离了审美与思想的艺术追求,对当代诗写产生了极具危害性的误导。
从语言与时代、文化的关系观照“表现”意识的缺失与拒斥,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不能正确理解诗歌的“难懂”,缺少诗学意义与诗体意识上的自我认同。当下诗歌逐渐走向以反讽作为策略的日常主义写作,反讽叙事的再现优势重视日常、介入生活,而最大的误区在于规避了语言的表现可能与诗意表现的话语意识,远离了诗歌作为艺术的开放性、差异性、多元性、可能性的探索。
法国象征主义马拉美明确提出的“难懂”是对西方现代文学始祖波德莱尔的感应、象征一说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成为现代诗歌重要的美学规范与追求。因为难懂,诗歌也多了阐释的可能。诗歌保持与生活的适当距离,有助于诗体语言对生命意识深处的勘探。“难懂”推动了汉语诗歌的深度、难度、高度写作。80年代中期以来,后朦胧诗、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大诗写作等诗潮都坚持“诗”的表现意识,与“非诗”的再现意识保持距离,通过“难懂”的文学性(诗性)追求对抗“再现”的叙事的凡俗化、粗卑化。
第二,现代诗歌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诗人自我存在的生命意识,表现意识的深度勘探有助于寻找生命的深度现实,更丰富地理解生活自身。再现的叙事往往仅停留于现实生活对人性的干扰与影响,缺少深度的文化反思与文本力量。
当下诗歌写作折射的生命意识缺少深度,诗的表现意识与手法表达单一、雷同。这种生命意识仅仅拘执生活、现实层面,阻碍了当代诗歌对生命意识探索的表现可能。坚持语言的深度、难度的写作自然与再现的中心话语保持距离,这种身份边缘化、诗性的写作追求,有效地保持了诗人的孤寂,也有助于他们深度地勘探与思考自我。孤寂蕴含着对时间的形而上沉思,保持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体验深度的生命意识,把语言从日常的再现意识解放出来。在孤寂的边缘,语言裂变,思想生成。诗人作为理念人,通过创造特定的意象呈现出诗歌的表现价值。
第三,当代诗歌是现代诗歌的一种精神与自由理念的投射,现代性关怀与表现推动了当代诗歌的发展。再现的中心化叙事由于过度关注现实,吻合了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但忽视了现代主义表现的文学空间。再现的写作关注现实,却缺少现代主义的语言技巧与形式探索,较少关注潜意识、深度自我。
现代诗歌无疑是现代主义艺术创作理念探索在前的文体与类别,现代主义则指向精神表现的种种可能,诗之表现丰富了当代诗歌的精神哲学与文化可能。“文化是价值、激情、感官、经验的汇总之地,它更关注的是人们感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11]。文学的大众化变成一个不可争论的事实,当下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甚至文化自身,均走向了利益化、大众化。从文体来讲,诗歌这种形式无疑是精英文学的代表,也是当下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最为坚实的经典与根基的组成部分。“让诗凭借语言成为艺术,让诗成为介质关联诗人与更深的生命体验、成为与读者对话与共鸣的艺术触媒,诗歌就是这么一种诗性、智性的艺术,慰藉生命,触摸灵魂”[12]。现代诗歌对幽暗精神世界的勘探也成为另一种生命事实、真相,导引人类精神生活的方向与可能。这种深度的心理和主观现实无疑是再现话语的日常事实、现实的克服与提升。现代诗艺在表现技巧基础上自由飞翔,让诗从现实返回内心,从再现的客观性、可接受性走向语言表现意识的诗性、神性。
第四,写作本身是一种书写机制,现代诗歌的表现意识的现代书写强调了多种可能。当下诗歌写作意味着在现代性的审美与价值维度不断践行先锋性、探索性。
再现的叙事话语不自觉地让诗歌滑入到诗歌的散文化、事件化的写作境地,缺少语言的精致性、丰富性。而作为现代诗歌的写作无疑应该与艺术、思想性紧密关联。“写作就把人物的实际言语当成了他的思考场所”[13],再现的写作去精英化、反审美的创作观念,规避了诗之表现,逐渐失去了现代诗歌的诗性。写作本身则意为表现,它不断通过艺术性、思想性的写作认同强化了写作自身的边缘性和对抗性,在当下文化中诗歌写作尤其表现出这种鲜明的话语立场与文化认同。追求诗歌的哲理性、审美性、生命性、艺术性,是一种对诗歌本体探索性写作的“是”的写作,也是带有否定、消极、虚无、绝望的“不是”的抗争性写作,它同时也成为一种差异的、增补的、审慎的、自由的文学体制内外的写作。
三、可能与突围
西方诗歌同样特别强调一种知性美、思辨美、哲理美、艺术美,诗人在音节、节奏等表现形式上展开探索,让西方诗歌也转向了表现的形式与肌质。但是西方诗歌深受古希腊理性哲学影响,关注、重视叙事的再现,诗歌通过理性、知性去展开诗人的思辨色彩、诗意之美。诗歌的叙事性也不同于小说的叙事,它最终的落脚点仍在诗歌的诗意与诗性。中国诗歌传统一开始就重视抒情的表现特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道、禅美学、意趣、意境等传统诗学,均表现出空灵、诗性的审美话语特征,更侧重于感性的“表现”与意味,这也是中国传统诗歌与西方理性为中心叙事话语相差异的特点所在。
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歌在传承西方现代抒情诗传统方面接受了象征主义、意识流等艺术观念与表达技巧,但是发展到了当下,诗歌由于朦胧诗过度抒情与政治话语的纠缠,使得当代诗歌有意味的抒情逐渐失效、单一化,使得诗歌失去自身的表现可能。从语言入手,“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则紧抓此点,不断地去审美化、解诗意化,提出了“拒绝隐喻”等诗学观念,使得诗歌从表现的透支中转向了叙事的清新、自然,其平民化、日常化带来亲切与清新的诗风,有效地修补了当代诗歌书写与发展路径。90年代末伊沙的反讽叙事诗歌也融入西方现代诗歌的知性、理性、哲理、思辨,拓展了诗歌的文本效果。“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反讽’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辞策略……‘反讽’成为中心化、主流化写作趋势也意味着某种潜在危险。反讽作为一种成熟修辞,唯有对其积极引导,充分利用‘反讽’的积极修辞表达效果,在精神与情操上不断强化诗人的责任意识、艺术信心、生命信仰、终极关怀,中国当代诗歌才有可能书写积极的、歌唱的、诗学的、语言本体的生命之诗。”[12]反讽诗歌“再现”的现实介入意识,吻合思辨、知性话语的认同传统。但是,过于“再现”的诗歌由于再现本身的可叙述性、奇观性、视觉感、易阐释性,让诗歌也走向了纠结“再现”的话语误区,单一性、单义性、去想象力、缺少深度现实理解能力,使得汉语诗歌在当下背离了表现意识为本体的诗意追求。
当代诗歌书写主流中的再现叙事话语极易拼贴化、碎片化,而绝大多数诗歌写作者因为缺少综合写作的知识背景与深度现实揭示的能力,使再现叙事呈现了趋浅化、庸俗化、粗陋化、极端化的写作趋势,再现的叙事变成现实主题“应景”的写作,延缓与忽略了当代诗歌语言的自然生长、自我繁殖、裂变、创造的可能。表现意识的诗歌更强调一种情绪色彩的铺陈与表现,它通过带有情感暗示的意象让读者参与其诗的想象与联想,从而在写作者与读者之间找到某种深度的情感体验、情感共鸣、审美认同。因此,朦胧诗以来的诗歌走向综合的语言本体意识的创造可能,“叙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叙事,以及由此携带而来的对于客观、色彩特色的追求,并不一定能够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赋予诗歌以生活和历史的强度。叙事有可能枯燥之味,客观有可能感觉冷漠,色情有可能矫揉造作。所以,与其说我在90年代的写作中转向了叙事,不如说我转向了综合创造。”[14]“叙事大规模‘入侵’现代诗,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类型与变种。认真评估新锐叙事的功能、性质和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叙事性在新锐诗中取得最大的突破是已从技术手段、修辞策略,上升为现代诗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带来的最大益处,是大大提升诗人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但理想的状态,应是抒情性与叙事性的有机溶解,达到‘鸡蛋清’状态。叙事,应成为一种‘有限制的情境授权’。”[15]相对而言,表现的诗歌则是艺术的某种可能,去完整性在诗句之中留存了许多可以联想的旁白、韵味和意义的不定点。
从隐喻的意象到象征的通感,再到直觉主义、超现实、超验主义的幻象,意象、通感是诗歌的重要的修辞技巧。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的本我、自我、超我的认知,把诗歌的表现从日常的经验世界拉向了神奇魔幻、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深度体验,通过梦话、呓语、幻想、冥思,完成了诗歌的超验本我、自我、超我的塑造可能。这个“本我”世界必然指向了艺术本体,指向了诗歌作为艺术重要表现形式的开放性、可能性、生成性、丰富性。“艺术作品中一切不具有功能的东西——因而一切超越单纯存在律法的东西——都被消解了。艺术作品的功能正在于其超越单纯存在的超越性……说到底,既然艺术作品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排除所有的虚幻特征就更加突显了其存在虚幻特征。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16],最终诗歌获得了本体论、艺术性的回归,凝聚了诗意、诗性的幻象之美、诗性之美。诗歌的文本效果在相似性、连接性之间找到了关联,既有主观的情绪性的现实投射,也尊重传统获得强化语言的途径。时空在主体的超验的想象、幻想中获得了某种情感基础,创造了现实无法再现的诗意之美、魔幻之美。考察诗人运用的意象、把握诗歌的整体情绪并展开合理想象,生成了艺术的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思想性(难度、深度、差异性、哲理化)。隐喻、象征、超现实、超验的情绪在“幻象”中获得了某种统一、穿越,聚集成当代诗歌表现、表意以及诗体回归的可能。
诗歌书写是众多艺术样式中最为本质的一种生命状态,它是人类现实、实用、理性、功能思维之外的另一种替补、僭越,它为生命主体提供了探索精神世界的可能。从诗歌的诗意性、理想性特征来看,它更接近于将来时,而再现的现实则指向过去时和完成时,诗歌这种“文体”意识,强化了诗意的创造、想象的表现可能。当代诗歌书写推动主观心理真实的同时,也为客观现实生活指明某种精神方向。诗人通过语言这个媒介不断沉思现实生活之镜,从现实的适定关注中凝视、洞悉自我的存在境遇与深度现实,清醒而智慧地感受生命主体的精神在场。
诗歌意味着将来时、理想形态的自我生活建构的启示与可能。“‘完成式’的诗歌形式被否定,作品在绵延不绝的‘瞬间’中生成,打破了有限与无限之界限的‘我’从此与诗、与物同在,载入不朽的史册,面向遥远的未来”[1]5。在诗歌阅读与创作实践中,许多诗人依凭超验与超现实的幻想能力颠覆时空,在自我想象中找回现实的精神投射,关注诗性、诗意的前提,捕捉现实不能描绘、展现的深度与可能性的生命体验,赋予读者神奇的审美空间。由此,当下诗歌书写成为现实生活的某种精神抚慰,不断消解现实的生命焦虑,实现艺术的净化与升华,并过艺术的创造过程,提升、凝聚对自由精神状态的体悟。
参考文献:
[1]蓬热 弗.采取事物的立场[M].徐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海德格尔 马.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2.
[4]张清华.“鄙俗时代”与“神性写作”[J].当代作家评论,2012,(2).
[5]枕戈.80后之“神性写作”与“口语写作”[C]//中国诗歌研究动态.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6]荆亚平.神性写作:意义及困境[J].文艺研究,2005,(10).
[7]罗振亚.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叙事诗学[J].文学评论,2003,(2).
[8]赵毅衡.刺点:当代诗歌与符号双轴关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0).
[9]布朗肖 莫.文学空间[M].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1.
[10]桑塔格 苏.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5.
[11]伊格尔顿 特.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2.
[12]董迎春.论当代诗歌的孤寂诗写及诗学建构——关于诗歌本体论可能的探索[J].南京社会科学,2012,(2).
[13]巴特 罗.写作的零度[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0.
[14]西川.大意如此[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3.
[15]陈仲义.中国前沿诗歌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57.
[16]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M].阎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7.
[责任编辑:修磊]
收稿日期:2016-0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朦胧诗以来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研究”(11BZW096)
作者简介:董迎春(1977—),男,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文学博士,从事当代西方文论及中外诗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6-0144-06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