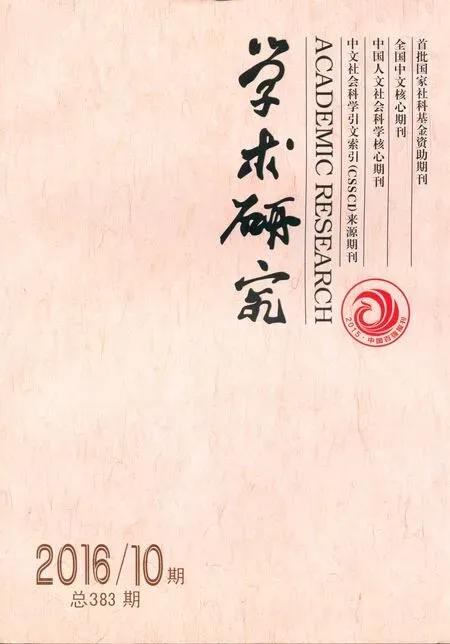城市空间、资本运作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
2016-02-27戴维哈维汪民安勇等
[美]戴维·哈维 汪民安 赵 勇等
〔中图分类号〕C0;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6)10-0145-07
文 学语言学
城市空间、资本运作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
[美]戴维·哈维汪民安赵 勇等
〔中图分类号〕C0;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6)10-0145-07
时间:2016年6月16日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翻译整理:王行坤(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汪民安(主持人):欢迎哈维教授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作客,因为我们文化研究院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文化,尤其是关于北京的研究。我们这边的同事都读了哈维的很多书,因此,也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哈维教授。北京的城市面貌最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让人很容易想到19世纪巴黎的城市改造。哈维教授关于巴黎的那本书几年前已经在中国出版了,影响非常大,这本书翻译为《巴黎城记》,①见哈维:《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译者注其实它的名字原叫“巴黎:现代性之都”,后来出版社改成《巴黎城记》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畅销,不过从销售角度来说确实是成功的。“现代性之都”是本学术书,“巴黎城记”听起来则像是通俗读物。顺便说一下,那本书的中文版是我写的序言。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围绕着哈维教授的研究、著作来进行,也可以就其他问题来和哈维教授一起讨论。
赵勇:我在读《后现代状况》这本书的时候,记得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时空压缩”,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而且确实能够解释现代性的境况。这本书是1989年出版的,现在进入到一个更快的时代,我就想问哈维教授对时空压缩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新的认识?
哈维:这本书问世大概有25年了。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过类似的话。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永恒的革命力量,会不断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改造。现在的时间概念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从发展来讲,资本赚钱的速度以纳秒为单位进行衡量,计算机可以在纳秒时间内完成交易,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这在1989年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金融市场的时间概念,跟1989年时是完全不一样的。1995年的时候,全球的股票市场开始一体化,现在演变成为一个统一的网络。贸易每一毫秒都在发生。现在的问题是,贸易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对现实会产生影响。现在股票市场就像量子力学一样,贸易都是数学和量子意义上的。人类对这些越来越难以控制,因为现在华尔街三分之二的交易都是由计算机驱动的,而不是由人来操控。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就会突然造成危机,而人类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现在新的时空维度。
我觉得空间关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巴黎城记》中,开始的时候我考察的是巴黎地图上铁路的位置。最开始什么也没有,后来则发展出很长的铁路线。今天早上我看到中国的高铁地图,在2005年之前高铁还完全不存在,现在则到处都是。所以现在这个时空压缩概念还是有效的,这是因为资本的革命性力量,是这些力量造成了这些变化。我们人类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前两天我在济南遇到一位95岁的老太太,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村子。但现在年轻人都可以坐高铁了,这些人是怎么交往互动的呢?这个可能会给家庭关系造成危机:年轻人生活在一种时空里面,老太太生活之另外一种时空里面,这会造成很严重的紧张关系。如果你问问年轻人,他们想不想过以前那种生活,他们肯定不愿意。所以我觉得,我所谈论的趋势,现在还在往前发展,我们谁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接下来会有人工智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新事物,让我们对劳动过程会有全新的界定,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会走向哪里。这就是资本的本性,驱动事物发展得越来越快。
赵勇:您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种时空关系进入到文学艺术当中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哈维:我不是文学方面的作家,但我会读小说,有些小说的结构很有意思。例如,我很喜欢大卫·米切尔的小说《云图》(Cloud Atlas)。①大卫·米切尔(1969—):英国著名作家,欧美文学界公认的新一代小说大师。小说《云图》出版于2004年,并于2012年改编成同名电影。——译者注我觉得那个里面时空关系特别有意思。50年前我们肯定无法理解里面的现象。米切尔通过时空关系对里面的故事进行了某种拆分组合,因此刚开始读的时候很难理解整个故事发生了什么。当你习惯他的逻辑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我最近没有读小说,因为我在读马克思。当然马克思的著作就像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想起一个笑话:刚开始读马克思的时候,我非常紧张,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于是我用棕色的纸包住了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封面,所以当我带着《资本论》出门的时候,总是用纸包住封面,跟别人说这是托尔斯泰的小说。一年过去了,我还拿着那本书。我就跟别人说我读得很慢,因为我要试着读俄文版的。(提问:您《资本论》读了多少遍?)我教授《资本论》的第一卷,至少讲了60多遍。我每年至少讲一次,讲了有40多年了,有时一年会讲两次甚至三次。主要是讲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讲的没有这么多。(提问:您对马克思的解读很有原创性,而且主要是学术研究。)但在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势力还是很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力量也很强。现在年轻人没有那么强的反对态度,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更愿意读马克思,去试着理解马克思。
蒋洪生:我的问题是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城乡关系的。在中国毛泽东时代,提出过城市的乡村化和乡村的城市化,你认为这种理论和实践现在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您认为您的理论在缩小城乡差别方面,会有何贡献?如果不可行的话,为什么?
哈维: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提出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这很重要。如果你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那么阅读马克思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马克思的探索工具历史唯物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我觉得你的问题就要放在历史语境里:我们谈论的是资本主义机制还是其他什么?资本主义机制会说,资本肯定会破坏乡村社区生活的农业基础。列斐伏尔在1960年代末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法国农民消失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剩下的区别只是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当时没人会说这种过程会成为全球现象。我去过拉美、中国和中东,我认为普遍存在着对农村社会的冲击。围绕这个过程,存在很多的斗争。我现在戴的这顶帽子就是来自于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组织。他们这个组织是要保护农村的生活方式,给他们提供资源,从而帮助他们。我很喜欢这个组织,我也喜欢他们的政策,但我觉得他们现在很困难。过去十年中,他们成功地占领了两片土地,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占领了一百多处土地。我认为现在的趋势是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这是我在读文献时看到的一个术语)。我喜欢阅读马克思的原因之一是,他谈到了资本的运动规律。列斐伏尔在1960年代末说的这个运动规律,在当时还没有触及世界其他地区,但假以时日,最终都会波及到的。这种触及的程度到底有多深,我认为现在我们能看得更加清楚了。就国家政策来说,你要么对抗这种运动规律,要么顺应这种规律。你们应该告诉我,中国政府走的是哪个方向。我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在顺应这种规律,即便政府矢口否认。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的现实。
蒋洪生:所以您觉得现在发生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乡村和城市日益趋同的过程,不再有乡村地区?
哈维:不,我觉得这里我们要引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这个概念。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也有农村,但在那里居住、生活、劳作的人们认为自己跟城里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同样的情景喜剧,同样愚蠢的新闻。马克思曾经说过乡村生活的愚昧落后,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很愚昧落后。所以乡村有的时候给城里人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地方,你可以在那儿来一番生态旅游,但其实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
蒋洪生:关于您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概念,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城市和空间问题给予太多的关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很多关于城市的讨论,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论住宅问题》等。因此我想要问的是,为什么您要提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概念?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认为空间问题从属于时间问题。您对此作何评论?
哈维:在我的著作中,我想要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详细论述过的问题,虽然他们对空间问题有所提及。但地理不仅关乎空间,同时也关乎环境,关乎方位构成(place-formation)。认清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们对于方位有某种忠诚感。如果地理学是关于空间、环境和方位的话,那我没有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及这些要素。马克思的分析都是有预设的,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假设,资本主义在全球各地都已同等程度地确立,处于完全的竞争中。但所有的空间性竞争都是不完全的垄断竞争,在转移成本很高的社会,就要保护当地的生产者。我喜欢的一个例子是啤酒生产。啤酒是很沉的,而且不易保存,因此每个镇子都有自己的啤酒厂,所以在镇上就属于垄断竞争。这种现象持续到1960年代。在美国,你在什么地方,就喝什么地方的啤酒。我住在巴尔的摩,就没有喝过丹佛的啤酒。但现在啤酒都是全国性的了。然后我们有进口的啤酒,如比利时、荷兰和丹麦、中国的啤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出现集装箱化之后,转移成本降低了。所以从现实来看,马克思关于平滑的没有障碍的竞争的假设是错误的,这就导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产生问题,因为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上的。但是在垄断竞争的情况下,没有一种普遍的价值规律,在不同的地方存在着不同的价值机制。这些价值机制有时决定于自然价值,如转移成本;有时决定于政治价值,如关税。比如说在1960年代末,全球劳动力市场在地理上存在很大分化,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地方是完全隔离的,有自己的价值机制,欧洲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机制。中国和俄国都不在这个体系内。后来全球化就将这些劳动力市场整合到了一起,因此原本差异很大的价值机制就开始慢慢融合。于是美国的工人都要跟中国、菲律宾和墨西哥等国家的劳动者竞争,所以美国工人不高兴。这是他们支持特朗普的原因。
从地理学的角度,你可以看到资本的运动规律是怎样运作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错了,只是说马克思的分析被某些假设制约了。如果我们足够现实主义的话,那我们就要认识到,这些假设是可以修改的。1945年以来资本体系逐渐打破贸易壁垒,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组织的目的。这很有意思:就好像说全球资本主义力量让这个世界去符合《资本论》第一卷的预设(即消灭垄断性竞争,实现完全竞争——译者注)。所以,当下的世界越来越接近马克思的描述。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的推论,如果世界的确如此的话,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会越来越严重,现在所有的数据都显示,1%的人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而马克思所描述的正是如此。我们当下的世界比之前更加明确地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作出的预设。这就是为什么要引入空间竞争、垄断竞争、地理结构等概念的原因,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法认清这个世界。
王洪喆:我读了您的很多作品,我的问题来自您的著作《资本之谜》。①本书已有中文版,见哈维:《资本之谜》,陈静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译者注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您提到:“当代复兴共产主义的尝试者通常发誓要放弃国家控制,并且寄希望于其他组织形式来取代市场力量、资本积累作为安排生产和分配的基础。扁平化管理结构而不是严格的等级制度,自我组织的、并且进行自我管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协作组织被视为新形式共产主义的核心。”②同上,第217页。译文有所改动。——译者注不知您是否能具体谈谈“放弃国家控制,并且寄希望于其他组织形式”是什么意思?依我的理解,这里您是否在暗示,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重新结盟是未来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必由之路,只不过在这一次的结盟中,将是无政府主义者而非20世纪的工人国家和政党,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哈维:首先,这里我可能有一点机会主义。我在北美、拉美和欧洲所遇到的年轻人不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或者传统的左翼政党的激发,而是由我所称之为的“非意识形态的文化无政府主义”所激发。这就是他们行动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组织方式。好比说占领华尔街运动。如果你看看土耳其的抗议运动的话——例如盖齐公园抗议,这并不是工人阶级起义,但的确是某种起义。抗议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在伊斯坦布尔,我认识的好多年轻人都参与了。去年我去了巴西有三、四次,但只有2013年都市起义还算规模比较大。我们见识过伦敦暴乱,斯德哥尔摩和巴黎的占领运动,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以及希腊的宪法广场暴动。你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的头脑里全都是“虚假意识”,因此这些人毫无希望。但一个优秀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分析者应该问,这些运动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这些运动里的阶级内容和反资本主义内容。这就涉及到长期以来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理解。列宁说这是工人阶级的第一场运动。但如果我们仔细辨别话,公社参与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运动的回应非常关键,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开始的时候,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没有准备好,应该停下来,但运动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发展。马克思就得决定他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回应。跟巴黎公社相关的第一个政策是取消面包工人的夜班,这是一个劳工问题。第二个政策是跟租金有关的问题,属于城市问题。马克思考察了公社全部的立法,然后说这是反资本主义运动。当然,巴黎公社的参与者有无政府主义者,有共产主义者,有激进的资产阶级,有女权主义者,各种各样的人都参与了。所以他写作《法兰西内战》,说这是一场阶级运动。他论述的基础是人们的所作所为,而非人员的阶级成分。所以我认为这对马克思有很大的影响。
我对城市运动很感兴趣,而且我要搞清,城市运动是否有阶级内容,是否有潜在的反资本主义要素,比如盖奇公园和巴西的抗议所展现出来的要素。所以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整合,形成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这个并不是很难做到。当马克思讲资本的时候,他讲到价值的生产。他说,如果价值不能在市场上实现,那就等于说价值不存在。在《大纲》③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通称为《大纲》。——译者注里马克思说,为了理解价值,你必须理解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关注生产,认为价值的实现是次要的。这部分是因为《资本论》第一卷主要关注生产,价值实现不成其为问题。价值实现的问题主要在《资本论》第二卷,但很少有人读第二卷。所以我在书里就提到,如果你没读第二卷,就无法理解资本。其实在价值实现的环节和生产环节一样,也存在阶级斗争。在生产环节资本家可以提高工人工资,但是可以通过高房租把工资夺回来。所以这就是巴黎公社房租减免政策的重要性所在。问题在于,围绕价值实现这个环节的阶级斗争与围绕生产的阶级斗争,并不具有相同的阶级内容。在我所去过的所有城市(包括北京)中,抗议的主要原因都是高地价,高租金,高房价。谁受到了伤害呢?所有人!传统左派一定会说,我跟你不是一个阵营,你是资产阶级,虽然你反对高租金。巴黎公社将这些问题与生产问题放到了一起。结果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对日常生活问题更加敏感,并试图构建反资本主义的另类的生活条件。另外,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环境问题也非常敏感,他们对于方位也更为忠诚。我想跟他们团结起来,但是他们不想团结我,因为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者。但很多很重要的激进地理学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是个地理学家。伦敦非常保守的皇家地理学会一直努力想把克鲁泡特金营救出狱,就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地理学家。他们还给他寄书过去,好让他在狱中完成自己的地理学著作。不管怎样,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时期。巴黎公社的实践肯定了我的观点:事关价值实现时,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会呈现出不同面相。这是我想要传达的重要方面。
汪民安:在《资本主义的的17个矛盾和终结》①见David Harvey,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译者注这本书中,您提到解决异化的问题,提出要把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宗教信仰的人道主义结合起来。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是革命的人道主义? 因为人道主义很少有人提了,而且也受到了很多批判。
哈维:我们得回到这个观念:要改变这个世界,但不是通过一个神秘的过程,而是需要人类集体性地参与。有很多种人道主义,如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但那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在我看来,真正有效的只有革命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可以源于很多要素,并不需要宗教来激发,你不必信教。我很清楚拉美的解放神学。像尼加拉瓜的天主教教士在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也是受到天主教解放神学的影响。不过后来教皇叫停了这些神学运动,但我对那些参与解放神学运动的神父充满敬意。我想说他们也是革命人道主义者,就像法侬一样,他们都加入到改造世界的行动中。但这变得原来越来难,部分是因为共产党是在自己的系统里面考虑这些问题的,即革命是一个科学问题。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等概念尤其持批判态度。关于马克思本人,长期以来也有一种争议性观念:马克思开始是人道主义,后来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但我的看法是,马克思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正是这种科学社会主义让他做出判断说,不要搞巴黎公社,你们还没准备好。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在1968年的巴黎,共产党不支持学生运动——这本来应该是一场革命运动,因为他们不喜欢街上学生的做法。实际上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也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他们最后没有很好地组织革命力量。我认为马克思在晚年认识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局限,他并没有放弃这种科学分析,但他认识到了其中的局限。这也是我为何如此看重他的《法兰西内战》的原因,我很重视他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不管怎样,我还是相信科学的分析,但最后你还得抱有信念,努力行动,因为我们不可能进行科学预测。
汪民安:问点轻松的问题:您最喜欢哪个城市?为什么?
哈维:我居住的城市,我都喜欢。我现在住在纽约,但我有时住在里约热内卢。我是里约热内卢的荣誉市民,我很喜欢那里。我也喜欢西班牙的科尔瓦多。我喜欢这些城市主要是因为街上的生活。我喜欢科尔瓦多是因为那里的建筑。
汪民安: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个华裔的地理学家段义孚,也是人文地理学大师,请问您怎么评价他?
哈维:段有一些神秘。我很喜欢他的书,但我觉得他的立场有点文化精英主义了。没有阶级斗争。
汪民安:本雅明谈论的巴黎跟您讲的不大一样。本雅明的书里也没有阶级斗争,您怎么看?哈维:不,他里面有阶级斗争。
汪民安:阿多诺批评他的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哈维:如果你对日常生活的政治感兴趣,喜欢观察人们如何感受拱廊和街道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本雅明对理解那些很细微的感受会很有帮助。在我的《巴黎城记》中,当我试图去理解巴黎的时候,阅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巴尔扎克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但是他懂得城市生活。我很喜欢雷蒙·威廉斯,他有很多社会批评的作品,但他认识到社会批评作用有限,因此不得不自己创作小说。你可以用小说去表现矛盾,去展现情感结构,这些是没法用社会科学批判来完成的。我觉得本雅明也想尝试做这样的事情,来抓住对于方位的情感和感受。在我最喜欢的城市里,街道上有很多能触动你的感觉和感受。在我看来,日常生活的政治与劳工和劳动的政治同等重要。如果我强调日常生活的政治的话,有很多人会指责我:你不关心工人阶级!其实不是这样,但我的确要强调日常生活的政治,因为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蒋洪生:约翰·霍洛维(John Holloway)①霍洛维(1947—):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与哲学家,爱尔兰人,现任教于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Puebla)。其作品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引起了很大争论。——译者注也强调日常生活的政治,您怎么看待他的观点?
哈维:他是个疯子,当然是好的意义上的疯子。我之前跟他私底下有过争论,他想要发表,但我没同意。他认为《资本论》的起点是财富,因此财富的概念对理解马克思的政治是根本性的。当然,世界是由财富构成的,表现为巨大的商品堆积,但他不同意商品的概念对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才是根本性的。而马克思明确说过,我的理论的起点是商品。另一方面,他关于革命人道主义有很多洞见。
蒋洪生:他算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哈维:应该不是,他更多是出自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跟意大利的“自主主义者”②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强调工人(劳动)优先于资本的自主性。主要代表人物有特龙蒂(Mario Tronti)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译者注更为接近。他们想搞清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怎样运作的。在我看来,马克思既对价值感兴趣,也对非价值(non-value)和反价值(anti-value)感兴趣。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和反价值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反价值主要是和工人相关,在我看来这是特龙蒂和奈格里所正确认识到的观点。我认为霍洛维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霍洛维与哈特和奈格里的工作有很多契合之处。在马克思那里,反价值也是根本性的。奈格里会说到“工人的拒绝”(refusal of the worker),霍洛维会说到“工人的尖叫”(scream of the worker),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对马克思的正确解读。
汪民安:列斐伏尔当了三年出租车司机之后才开始对城市感兴趣,才想要研究城市。我想问的是,您是因为什么对城市感兴趣的? 因为什么契机对城市和空间感兴趣?
哈维: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地理学家威廉·邦奇(William Bunge),③邦奇(1928—):美国地理学家,1970年代在加拿大多伦多开过一段时间出租车,最后定居在魁北克。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有《理论地理学》,石高玉、石高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译者注他也做过出租车司机。他说(我也同意),出租车司机才是最好的地理学家。但问题是,他们不像过去那样熟悉城市了,因为现在有了GPS,他们被去技术化了。我对城市研究感兴趣,是因为我和出租车司机的交谈。
其他学者:能否谈谈您的学术生涯,现在是否还有转变?
哈维:我还没有那么老,所以还在学习。马克思问过这样的问题:谁来教育教育者?我认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有多重学术背景。我和社会运动紧密结合,也是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比我更清楚街头生活,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接触社会运动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我比他们知道得更多。最关键是,很多重要的左派思想并不是来自学术界,而是来自于大众的不满。我学习的另外一个对象是我的学生,他们也在教育我,尤其是那些来自于不同学术背景的学生。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我从一所精英大学来到了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大学,④哈维指的是他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来到了纽约的纽约市立大学,后者是一所公立大学。——译者注这让我可以学到更多。事物和人都在转变。今天的问题和30年前的问题已经不一样了。30年前我们有福利国家,有很多的政府介入,还有一些为工人谋福利的政党。这些后来在政治上都被毁灭了。现在我们应该在新的层面和新的范围内,重新开始这些工作。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那就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及其对应的政治权力结构,都会产生相应的反对力量。我们看从1945年到1975年——那是美国的福特主义时期,那个时期有大公司、大企业,相应地有大工会和一些为劳工谋福利的民主政党。现在的公司都采用网络化、扁平化的管理,雇佣的工人也非常少。所以现在的左派也提倡网络化、扁平化的组织方式,而不是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从而在政策上进行调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左派的组织方式是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镜像。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难以想象,真正的反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左派无法逃脱这种镜像。
其他学者:我想问的是,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还是光有社会运动就够了?
哈维:很明显,我们需要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很多对传统政党的不满,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反思。我没有参与过政党,但是我经常和政党合作。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有构建批判性立场的权利。但是在政党纪律面前,你就没有这种权利。我和很多左派政党都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如果有人想了解情况,他可以和某个组织的成员坐在一起进行讨论。但我对自己的理论没有那么自信,我没有觉得,在政治组织里他们要听我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党,但应该和历史上的政党要有所不同。左派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总想回到过去,想像列宁或者卢森堡那样去解决问题。我想到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话: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们得把自己从先辈们的传统中解放出来,虽然我们很珍惜那种传统。马克思说要创造我们自己未来的诗歌(poetry of future),而这种诗歌必须对我们当下的现状以及可能有所言说。我们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新的组织形式。我们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创立自己的组织,而不是回到一百年前的政党。我得说,很多左派其实很保守,这让我很不舒服。我之所以爱读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总是愿意重新思考问题。他对自己研究过的问题总是会进行新的思考,然后得出新的结论。他总是会进行自我批评。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吸纳到我们的政治里,不然我们就会重复过去,最后变成一场闹剧。
郑以然:我想问一个关于“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概念的问题。
哈维:我其实不用“空间正义”这个概念,为此还有人批判我。我使用的是“地域正义”(territorial justice)。我之所以不用空间正义这个概念,是因为对我来说,空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有一篇《空间作为关键词》(Space as Keyword)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谈论了绝对的空间、相对的空间和关系性空间(relational space)之间的差别。说到正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绝对空间、相对空间还是关系性空间?而列斐伏尔谈到过物质的、概念的和居住的空间。这意味着什么呢?例如,以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为例。恐怖主义的空间是什么? 这是一种关系性空间。但人们很害怕,感受到恐惧。这对美国军事策略会产生影响。之前他们会占领绝对空间,但现在是关系性空间的问题。因此现在就很麻烦:怎么控制恐怖主义的关系性空间?因为你不能在军事上占领关系性空间。而地域正义是绝对空间的正义,例如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有更多的教育资源。
陶东风:哈维教授是第一次来北京,不知您对北京的印象是什么?和您之前的认识有没有出入?北京污染严重,有人提出把首都跟北京分开,对于北京城市面临的一些问题,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哈维:其实我不知道要把北京和首都分开的事儿,但很多城市都有过类似的做法。我没有特别的印象,昨晚因为天黑也没看到什么。但我看到有很多地标性建筑,有很多交通,车辆行驶缓慢。这是一个地标性的资本之都/首都(capital city)。
责任编辑:王法敏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讲座教授;汪民安,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北京,100089);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蒋洪生,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北京,100871);王洪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北京,100871);郑以然,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讲师(北京,100089);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北京,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