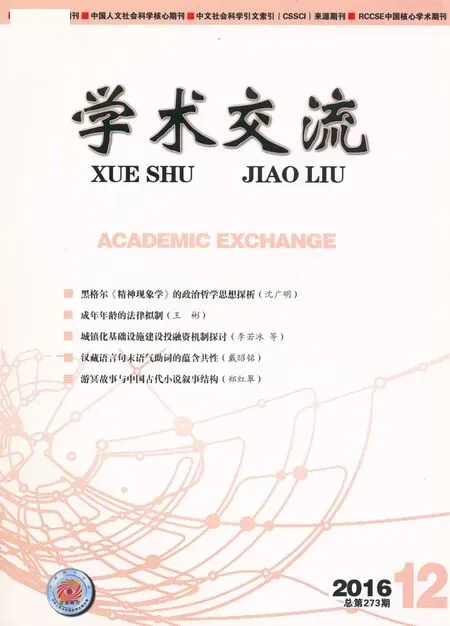东京审判管辖权的理论疏解与当代意义
2016-02-27徐持
徐 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法学研究
东京审判管辖权的理论疏解与当代意义
徐 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东京审判的管辖权问题多年来一直争议不断,关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有无管辖上的“越权”和“失职”等问题。战后审判的特殊性和国际刑法发展的阶段性造成了东京审判管辖权确立的困难,东京审判管辖权并非没有瑕疵,但其合法性和正义性不容置疑。东京审判管辖权的确立赋予国际刑法以刚性,促进了国际刑事责任的个人化,阐明了“选择性司法”的危害,为国际刑法的当代发展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法律遗产。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管辖权;国际刑法
一、问题的提出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正式承认同盟国有权实施“严厉的审判”清算战争罪行。据此,同盟国于1946年1月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刑事法庭(通常称之为“东京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指控他们都曾参与计划并实施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这场审判也被称为“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管辖权问题多年来一直争议不断,是东京审判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长威廉·韦伯爵士,以“在整个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刑事审判”[1]的发言宣布东京审判开始,表明同盟国让轴心国国家领导人个人为战争罪行负责,创设“核时代法律进展的至关重要的里程碑”[2]的勃勃雄心。即便这场世纪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创造了历史,但仍要面对一个最基本的法律问题,即东京法庭作为清算日本战争、战争犯罪和战争责任的国际军事法庭,其管辖权是如何得以确立的。
国内外学者关于东京审判管辖权的研究已有很多重要成果,21世纪初期之前,中国学者最具价值的研究成果莫过于直接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法律顾问等亲历者的一手记述、法学文集等文献史料和研究成果的问世*参见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倪征燠:《从容淡泊莅海牙》,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向隆万:《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也相继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东京审判研究的专著、译著、资料汇编与论文,这些研究从宏观的角度揭示出东京法庭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对涉及管辖权问题的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战争罪以及个人刑事责任、“官方身份无关性”等基本原则进行了阐释。反观日本,在东京审判庭审前后,虽然正面评价东京审判是日本知识界的主流声音,但日本民族主义者,包括辩护律师团中的一些成员,发起了对东京审判的彻底批判,他们指责这场特殊审判的真正目的仅仅是满足胜利的同盟国的复仇欲望,质疑同盟国起诉战败国家领导人的合道义性。为了支持这种论点,他们从管辖权角度指责东京法庭实际上是胜利国恣意创设的,让战败国领导人负上侵略战争发动责任的法律是事后法,是“胜者的正义”等。而这种言论得到了美国学者理查德·麦尼尔教授的支持,在其于1971年出版的代表作《胜者的正义:东京战争罪行审判》一书中,将东京审判视为巩固美国战后在日本以及亚太地区霸权地位的手段,这部著作也被视为英语世界东京审判研究的重要参考。
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大量审判一手档案资料的发掘、收集和整理,东京审判的法学研究走向深入,东京审判管辖权问题研究也更多地在微观层面展开。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利用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一手档案,尝试解明东京审判中的不起诉问题的经纬;二村円香从转型正义角度分析东京法庭作为战争罪行特别法庭的作用;户谷由麻以及博伊斯特、卡莱尔则在东京审判判决书乃至庭审记录之外,利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保存的东京审判档案,对东京审判管辖权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3]也有中国学者从历史实证的角度,提出东京法庭拥有管辖权的新论证,指出东京法庭审判反和平罪的实践是建立在国际法禁止性规范及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责任的基础上的,是对国际法的新贡献。[4]
可以说,东京审判既是一部战争断代史,也是一部法治截面史,对东京审判管辖权问题的研究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冲突,以事实为基础,以正确的审判认知为前提展开细致讨论。
二、东京审判管辖权的法律渊源
东京法庭得以组建并运作,是美国、中国、英国以及最后对日本正式宣战的苏联在1943—1945年间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和决议的结果。《开罗宣言》提出惩罚日本的侵略;《波茨坦公告》确认《开罗宣言》并规定了战犯审判问题;《日本投降书》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接受将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置于盟国占领当局之下的安排;中美英苏莫斯科会议授权盟国占领当局处理有关日本投降的所有事项,盟国占领当局因而获得设立法庭、发布和保证实施法庭宪章的权力。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将军以盟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批准国际检察局所拟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称“东京法庭宪章”),并签署《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东京法庭正式成立。可以说,“这一国际法上难以归类的军方行为为东京法庭本身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但至今仍被批评其正当性尚不充足”[5]。
事实上,同盟国审判战犯的愿望由来已久,最早见于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平条约》,这是第一次在国际条约中明确承认了个人的刑事责任。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莱比锡审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根据凡尔赛和约,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等应当接受审判,但此前没有设立国际法庭,不得不把被控战犯送回德国法庭受审,由于德国政府的抵抗和不合作,1921年的莱比锡审判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闹剧,设立国际法庭的想法在法学家们中间开始酝酿。1942年同盟国在圣詹姆斯签订协议,建立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UNWCC),这也是建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第一步。[6]当时中国代表特别提出在远东也要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法律制裁,随后的《波茨坦公告》强调对日本战犯进行国际法律审判和制裁,其目的在于驱逐不负责任的黩武主义,并且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战后秩序。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文明的审判”概念在1945 年7 月就已经有了。[7]正如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的开篇陈词所述:“文明才是最终的原告,如果这些司法行为不能防止将来再发生战争,那么文明本身很可能将被毁灭。”[8]73
三、法庭宪章的管辖权规定及东京法庭的法律属性
东京审判的多数判决书申明,“法庭宪章,对法庭是决定性的和必须遵守的法律,除法庭宪章明确规定者外,法庭并无任何其他管辖权”[9]。从法律角度来看,东京法庭的管辖权条款在东京法庭宪章中居于基础地位,是法庭进行审判的起点。因此,辩护方的最佳策略就是质问法庭的管辖权和法治原则,同样的情况在纽伦堡审判中也发生过,也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中。因此,辩护方在东京审判的开始就有一系列质问法庭合法性和管辖权的行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依据“东京法庭宪章”第5条,远东战争罪犯由东京法庭审判。所谓战争罪犯,尤指被控犯有第5条(甲)款反和平罪的行为人。而甲级战犯以外之人的刑事追诉,根据《日本投降书》,则建立了其他50个特别战罪法庭,由各同盟国国家依属地原则分别行使国内管辖权。
宪章规定的管辖权涉及人、罪、时间三个维度。其一,时间方面,起诉追溯到1931年9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这反映出东京审判的主题是日本在1945年之前的侵略政策,国际检察局试图准确地反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以实现国际刑事审判所具有的承认功能和发现真相的功能。法庭记录副本显示,国际检察局试图查明日本战争罪行而不是隐瞒信息,包括一些被核心指控忽视的罪行。[10]12
其二,审判追诉对象限于个人,东京审判考虑的是,战争罪行最终都可以归咎于个人,国际刑法要防止个人躲藏在国家主权的庇护之后。东京法庭的某些不利条件,如法庭的狭义授权、日本军政档案的缺失等,迫使检方努力利用现存的国际法体系,从中找到并充实使政府的军政领导人为大规模暴行承担责任的办法。这又反过来促使东京法庭的法官们阐明法庭本身对于领导人责任问题的观点,为个人刑事责任的理论提供了许多创造性的法律解释。无论如何,东京法庭可能是最早开始解决国家领导人个人责任这个复杂问题并探索适用的法律原则的先例开创者。另一方面,这要求存在个人可以直接援引而无需国内法作为中介的犯罪构成要件。这一前提同时要求国际核心罪行的构成要件获得普遍承认以及国际法上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得到确立。三类犯罪中,“普遍被接受的反和平罪的构成要件,对人民的安全保障具有最重要的价值,但它仍未产生”[11]。随着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塞拉利昂以及柬埔寨和黎巴嫩混和法庭,特别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相继设立,国际刑事裁判获得长足发展。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不缺乏起诉的动因,但反和平罪的国际审判再也没有启动过,由此可见,对于在法律上确切地描述此项罪行的特征并说明起诉的理由,各国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其三,追诉的罪名规定了反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1946年4月29日,首席检察官季南向法庭呈递的起诉书中,55项诉因又分为反和平罪、杀人罪、其他普通战争犯罪及违反人道罪三大类,与宪章规定的三类罪行并不完全一致,突出了普通战争罪中的杀人罪,将其单独列为一类,但三分之二的罪状都集中在反和平罪上,鲜明地反映出东京审判是以对反和平罪的起诉和审判为中心的。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是与特定地点的确切事件相对应的,反和平罪则不同,涉及政府的一整套组织行为。日本的政府系统与紧密集结在元首周围的纳粹政体不同,其职责分散在以天皇为最高领袖的好几个决策中心*日本内阁、枢密院、总参谋部等政府机构有着彼此关联的各种权限,全体内阁成员都是枢密院成员。之间。要确定个人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所承担的责任是很难的,为了弥补这种模糊性,宪章中加入了“共谋”这一原本属于美国刑法体系的概念,作为独立的诉因。[8]75这种法学理论极大地化解了检察官的工作难题。尽管论证的过程非常艰难,包括庭长韦伯和法官帕尔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国际法上从来就没有共谋的概念,但最终法庭对日本自1928年以来的政治史和军事史进行了审判,由此证明确实存在一个阴谋,各被告人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日本在亚洲扩张政策的策划或执行。
东京法庭作为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的性质在法学上已经是共识,虽然1948年11月,土肥原贤二和广田弘毅两名被告人的美国辩护律师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认为东京法庭只是“美国的军事法庭”,试图否认东京法庭作为国际军事法庭的性质。[12]美国最高法院的最终立场表明,麦克阿瑟将军是依照《波茨坦公告》、凭借根据《莫斯科宣言》组织成立的远东委员会(FEC)的政策指令代理组织法庭的,虽然建立东京法庭的基本原理并未记录在《波茨坦公告》的第10条规定里,但即使不考虑基本原理(一般国际法或者《波茨坦公告》以及《投降文书》),也可以毫不含糊地认定东京法庭是国际军事法庭。[13]31东京审判深受美国的影响,但在人类历史上,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第一次走到一起,就是为了努力实施所有国家今后将共同遵守的文明准则,肯定了在神圣的国家主权之上,还存在着国际法律规范,这是东京法庭最重要的法律基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东京法庭为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开辟了道路。
四、主要管辖权争议及其评析
(一)管辖中的美国因素
这一质疑最初由广田弘毅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时提出,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完全缺乏成立法庭的权力。另一个与之相关的质疑是批评东京法庭的法官都来自于战胜国,是“胜者的法庭”,认为这使得确保一个合法、公正和不偏不倚的审判在法庭审理开始之前就失败了,这两项质疑后来几乎被所有的被告反复提及。[13]32-37作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享有在这个战败国重建民主政治的一切权力。《日本投降书》中,日本天皇和政府均承诺遵守和服从盟军最高司令官或由盟军指定的其他代表的命令和决定,这使得麦克阿瑟将军能够超越权限去执行《波茨坦公告》的条款。东京审判的判决也明确了麦克阿瑟并非作为美国公民如此行事,而是作为同盟国之代理的身份。关于不符合美国宪法的质疑,美国国内法律并不适用于国际法庭,相反,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权力审查麦克阿瑟将军的行为。此外,东京法庭关于袭击珍珠港的认定也显示出,法庭并不像人们通常相信的那样,深受美国诉讼计划的控制。与之类似,认为麦克阿瑟一手操纵了裕仁天皇的起诉豁免也没有得到原始文献的证实,事实上,麦克阿瑟并没有官方或非官方的决定裕仁天皇处遇的权力。[10]13东京审判中来自新西兰的大法官诺斯克罗夫特在1949年3月《给总理的备忘录》中写道,“法庭的决定是基于所有能够得到的证据,并且是在给予反对意见最充分的发表机会之后才做出的,而且我相信那是不偏不倚的”[14]。与纽伦堡的先例不同,“东京法庭宪章”赋予被告充分的辩护权,被告方可以对审判表示异议,在当时倾向于立即处决这些战犯的强烈氛围下*1945年曾有人主张关于战争罪的现有法律和公约已经不足以处置南京大屠杀这种性质和规模的罪行了,索性彻底舍弃法律的细枝末节一枪毙了罪大恶极之徒,更有利于实现法律的追求。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国务卿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就持这种观点,理由是他们的“罪行太过黑暗”,已经“凌驾于司法程序的范畴之外”,丘吉尔也抱有相同看法,觉得最好“把他们排成一行,然后枪毙”。,被告们获得的辩护机会实在令人惊叹。“东京审判冗长乏味的英美刑事诉讼程序让所谓胜利者复仇的枪口哑了火”[15],在日本律师高柳贤三和清濑一郎的率领下,被告们利用这一点质疑了审判的合法性以及起诉书中最基本的罪状,仅在法庭上,辩方就获得了187天的时间来回应检方的控诉。对被告辩护权的保障正是对“胜者的法庭”进行反驳的明证。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亚洲,美国始终坚持由他主导的双边机制。东京法庭的判决都要经过麦克阿瑟的批准,而纽伦堡审判是法庭一锤定音,这意味着东京审判的终审权存在瑕疵。另外,人们对东京审判的评价不高与当时的世界局势有很大关系。在东京审判即将终结时,同盟国由于冷战而分崩离析,审判席上的代表国之间正在发生冲突,并在亚洲许多地区进行着殖民战争,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也逐渐偏离起初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理念,忙于创建自身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等[16],这一切都使得东京法庭基于对法和正义的追求而确立的管辖权蒙上渐趋浓重的阴影。
(二)管辖中的双重标准
在亚洲,同盟国对战犯的审判表现出报复和希望两种情绪,惩罚日本侵略政策和重建民主日本的愿望同样强烈,报应和预防两种刑罚理念交织在一起。事实证明,正是政治主导下的立场摇摆和国际司法正义的理想之间的矛盾,使得东京审判比纽伦堡审判遭受了更多的非议和批判。换言之,战后审判的特殊性和国际刑法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造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管辖权确立的困难。在东京发表了反对意见的法国大法官贝尔纳认为,“一方面按照国际法惩罚新罪行很困难,另一方面是二战大规模暴行之后不可能发慈悲,侵略战争是非法的,但起诉是对人而不是对事使东京法庭对于远东的犯罪行为采取了一种偏颇的做法,对于卷入暴行的日本官员也是进行了不平等的对待”[17],这些疏失不能不说是东京审判的一大缺憾。东京法庭在决定被告人名单时有一定的任意性,即便依照被告仅具“代表性”的观点来看,某些被遗漏的被告和罪行仍然十分显著:裕仁天皇、宪兵队头目、极端民族主义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因侵略中饱私囊并参与铺平“战争之路”的实业家财阀均未被起诉;对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的强制动员、强迫成千上万的非日籍女子充当“慰安妇”的罪行未被追究;罪恶昭彰的731部队被准予全面免责,日本在中国施用化学武器的证据也没有得到认真追究。
天皇裕仁和其他许多战时商业、政治领袖的命运都是在东京法庭之外决定的。出于美国“统治”的需要,让天皇和皇室免责,把所有责任推给了东条英机。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天皇的缺席是如此醒目的不公正,“一位首要的发起人逃避了一切追诉,跟他相比,其他被告无论如何只能算是共犯”,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责任,“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18]以双重标准衡量法庭管辖的人与罪,不仅不利于对东京审判被告的诉讼,而且有损国际司法的正义。现在人们都承认,对某些罪行不予起诉,对某些日本官员未经审判而释放的举动在很长时间里阻碍了人们更好地了解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这也是日本国内长期集体失忆的来源。日本政府没有组织任何追究战争责任的审判,恰恰相反,它所做的是迅速为战犯开脱罪责,并设法尽早在靖国神社供奉战犯。日本浪漫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延续至今。而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甚至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坚持和强调自由民主政治,这也是造成战后德国和日本对待罪责的态度存在天壤之别的原因所在。
五、东京审判管辖权问题的当代意义
第一,作为国际刑法的奠基者,东京审判将侵略战争及其组成部分直接犯罪化,并实施国际刑事制裁,赋予了国际刑法以“刚性”,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法治的里程碑。它宣告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国际刑事审判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被告人,更在于公开记录历史,并通过这一手段在对立各方之间重新建立谅解和信任。国际刑法正在持续不断地影响国内法。有些国家甚至通过制定或者修改国内法,规定了本国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并将普遍管辖权作为本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进行合作的法律基础。[19]这也标志着国际刑事管辖新时代的来临。
第二,进一步明确了个人国际刑事责任,使国际刑法的长矛穿透了国家主权的 “铠甲”。东京审判管辖权之确立明确向全世界宣告,万国之上,还有人类。换言之,要求国际审判机关的管辖权超越国家主权,即国家主权享有的豁免权必须退让。东京法庭对一个战败的侵略国家领导人仅享有有限管辖权,但以此为借鉴,弄清对全世界所有个人具有普遍管辖权的常设国际刑事机构的必要条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战争罪、反人道罪、种族灭绝和酷刑已经构成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的主要暴行,这意味着一国政府对其本国公民或者其邻国滥用主权将被认为是犯罪。2016年3月21日,国际刑事法院(ICC)第三审判庭判决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副总统让-皮埃尔·本巴·贡博犯有反人道罪(谋杀、强奸)和战争罪(杀人、强奸、抢劫),这是国际刑事法院首次判决强奸作为战争手段的犯罪行为,亦是该法院首次判决高级将领以指挥官责任的形式为下级士兵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20]国际刑法的进步是无可争议的,在这个意义上,东京法庭管辖权对个人刑事责任尤其指挥官责任之确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第三,东京审判管辖权确立的种种缺陷,告诉我们应尽力避免国际刑事司法中的“选择性司法”现象,严格区分合法性与正当性。国际法庭离不开政治的角力,但需要牢记的是,“妥协是艺术,但不是正义”[21],政治、外交、经济等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刑事司法产生影响,但是它们的影响必须在国际刑事司法的体系内规范地加以处理。如果用过去的教训指导未来的进程,那么创造一个独立、公平、有效和拥有连续制度性记忆的常设国际刑事司法制度势在必行,它必须从权力政治的反复无常中解脱出来。
[1] [日]藤田九一.东京审判:人道的正义还是胜者的正义[M]//[日]田中利幸,[澳]蒂姆·麦科马克,[英]格里·辛普森.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5.
[2] Röling.The Tokyo Trial and Beyond: Reflections of a Peacemonger[M].Antonio Cassese, ed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3:65-68.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M]//程兆奇,龚志伟,赵玉蕙.东京审判研究手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23-160.
[4] 管建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享有管辖权的新论证[J].法学评论,2015,(4):95-108.
[5] Helmut Satzger.国际刑法与欧洲刑法[M].王士帆,译.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5:376.
[6] [德]格哈德·韦勒.国际刑法原理[M].王世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
[7] 姜津津,季卫东,程兆奇.东京审判是“文明的审判”[N].光明日报,2014-09-01.
[8] [法]艾迪安·若代尔.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M].杨亚平,译.程兆奇,注.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9]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M].张效林,节译.向隆万,徐小冰,等.补校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7-18.
[10] Yuma Totani.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 ThePursuit of Justice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Ⅱ[M].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11]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53.
[12] 刘仁文.东京审判与国际刑事司法[N].人民法院报,2015-09-03.
[13] Boister, Neil, Robert Cryer.The Tokyo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 Reappraisal[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14] [新西兰]安·特罗特.诺斯克罗夫特大法官[M]//[日]田中利幸,[澳]蒂姆·麦科马克,[英]格里·辛普森.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11-112.
[15] [荷]伊恩·布鲁玛.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M].倪韬,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78.
[16] [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M].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34.
[17] [澳]米凯尔·何佛笙.贝尔纳大法官[M]//[日]田中利幸,[澳]蒂姆·麦科马克,[英]格里·辛普森.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27.
[18] [荷]伊恩·布鲁玛.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M].倪韬,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57.
[19] 盛红生.论国际刑法对后冷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影响[J].法学评论,2016,(2):103-112.
[20] ICC Trial Chamber III declares Jean-Pierre Bemba Gombo Guilty of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DB/OL].https://www.icc-cpi.int/en_menus/icc/press%20and%20media/press%20releases/Pages/pr1200.aspx,2016-03-21.
[21] [美]M谢里夫·巴西奥尼.国际刑法导论[M].王秀梅,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34.
〔责任编辑:马 琳〕
2016-02-29
徐持(1981-),女,吉林双辽人,博士研究生,吉林警察学院讲师,从事中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研究。
D997.9
A
1000-8284(2016)12-01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