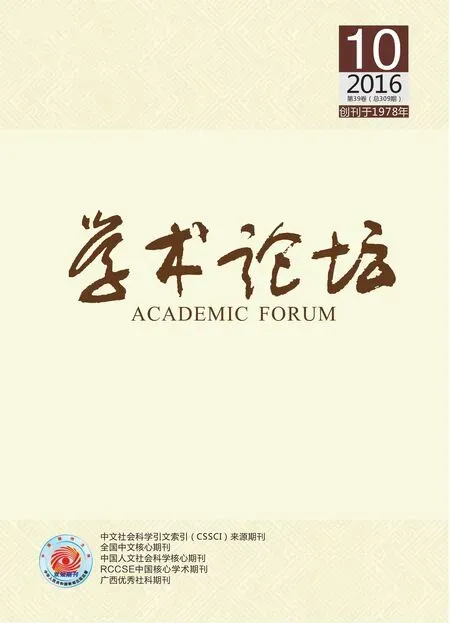桂学溯源:20世纪上半叶桂学的生成与学术渊源
2016-02-27洪德善
洪德善
桂学溯源:20世纪上半叶桂学的生成与学术渊源
洪德善
桂学虽是新近才正式提出的一门学问,但它是有着深厚的根基和渊源的。在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史学研究“二重证据法”后,民俗学、民族学也成为与古史互证的重要学科而受到重视,“三重证据法”时代实际已经开启。广西相对封闭的环境和众多历史悠久的世居民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地区之一。再加上在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治理下的广西成为全国“模范省”,以及抗战全面爆发后大批文化人迁入广西境内,“桂学”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是当代桂学最主要的学术渊源。
桂学;渊源;三重证据法;民族文化
桂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潘琦于2009年正式提出了桂学的定义,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桂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民族性,把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文化研究透,就能撑起“桂学”的“一壁江山”[1]。其后不断有学者对桂学的定义、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研究的方法等作了深入的阐释而使桂学逐渐清晰。但寻找到桂学的根基,为这一学派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仍是桂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胡大雷所言:“桂学研究的追溯学术之源,成为桂学研究者自信的基础,成为桂学研究学科化的起步。”[2]
李建平认为,康有为1894年在桂林写的《桂学答问》和《桂学答问序》可视为桂学的先声[3]。袁君煊认为,北宋末年,孙伟在桂林做幕僚时就开始传其所学,这是目前所见关于“桂学”的最早记载[4]。胡大雷则提出,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建设和40年代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使“桂学”的发展迎来了机遇,桂学服务社会的特色也逐渐得以明确[5]。还有学者将“桂学”的文脉追溯到了上古时代,甚至远古时代,这对桂学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但如仅限于时间上的推演,而不将其纳入更宏大的叙事话语体系中,以及缺少学理的支持,构建起来的桂学的渊源体系是不牢固的,也是难以支撑起桂学研究者的自信的。因此,探寻桂学的渊源,要回归到中华民族宏观叙事语境及时代学术话语体系下来考察:20世纪20—40年代,是广西第一次全面登上国家话语讲台的时代: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融入了时代的学术潮流;新桂系在“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下把广西建设成了全国的模范省;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无论在前线,还是作为后方,贡献都可圈可点——台儿庄战役、昆仑关战役、桂林抗战文化城、西南剧展使广西进入了全国的视野,甚至是国际的视野,这正是“桂学”博兴的时代。
一、时代学术潮流促使了“桂学”诞生
首先,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与一个人物紧密相关,他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1927年北伐胜利前夕,王国维因无法承受时代巨变的冲击,于北京颐和园投湖自尽。王国维决绝逃离的时代,确实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北伐胜利,国家完成了统一。虽然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但它带来的经济、文化、教育、外交上的变化是令人振奋的。为重拾中华民族的自信,学术界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探索热情持续升温,努力地通过文献、考古材料、民俗学与民族学材料来重构中华文明古国的自信史。王国维的生命终结了,但却是他引领的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开始。
一方面,正如王国维所说的,这是一个发现的时代、新学问博兴的时代:“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
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为今之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6]
另一方面,西方田野考古学引入并在中国根植下来。考古学上不断有新的发现,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轮廓通过出土文物得以初步展现,这不仅大大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触发了一个由王国维引领的学术研究方法论革新的时代:“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之。”[7]今天我们的“三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无疑都是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开创出来的。虽然,“三重证据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正式概念的提出,但受到王国维的方法论的影响,民俗学、民族学证据法的实践在20世纪前半期就已经开始,“三重证据法”的时代实际已经开启。如,当时的学者陈志良提出的“民俗古史”的概念就是很好的证明。陈志良指出:“所谓‘民俗古史学’者,是民俗学与古史互相结合而阐明其种种现象的思想。就是用民俗学的材料来对付古史,用民俗学的方法来处理古史,用民俗学的现象来解释古史,用民俗学的观念来决定古史。使得古史上的种种不得其解,前人误解的问题,得民俗学的帮助而另得新解,同时民俗上的诸问题亦得古史上的证明而知其来历。”[8]
其次,学术的兴起、成长壮大,须有广阔的学术阵地,即学术成果的刊布载体——各类杂志报刊。而这个条件正是在这一时代初步具备了的:“民国(1919—1936)时期,在‘科学救国’的理念引导下,新式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大批海外留学生,以启迪民智、普及科学、促进学术交流为宗旨,创办了大量的学术期刊,形成‘期刊热’。期间,学术期刊走上了成长、发展、不断成熟的道路,其繁荣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个时期的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拓展了学术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具有良好的信息传播作用,并为我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9]
二、广西的省情为“桂学”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广西地处南部边疆,民族众多,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这里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得以较好地维持,无疑是搜求“三重证据法”之民俗学与民族学证据的理想区域。广西的这一区域优势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就被认识到了——这里是可以为解决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贡献的。此其一。
其二,与此时广西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1925年春,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完成了广西统一。新桂系在主政广西期间,曾因在北伐战争中取得较突出的战绩而在全国树立起了广西的良好形象。后因接连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中失利,新桂系的实力与形象都遭受重挫,被迫退守广西。为了发展实力,争取再度崛起,新桂系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推行了一系列建设广西的“新政”。
历经数年的建设,广西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政治较为开明,经济基本自给,公私机构厉行节俭,社会治安良好,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成为全国甚至世界关注的焦点,颇得中外人士的好评:1935年,胡适南游,当时广西的社会气象给他留下了四个好印象:一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二是俭朴的风气;三是良好的治安;四是崇尚勇武的“武化”精神。胡适对广西各界厉行节俭特别赞赏,其《南游杂忆》中的一段记叙,读者莫不为之感动:“有一天晚上,邕宁的各学术团体请我吃西餐,——我在广西十四天,只有此一次吃西餐——我看见侍者把啤酒倒在小葡萄酒杯里,席上三四十人,一瓶啤酒还倒不完,因为啤酒有气,是斟不满的。终席只有一大瓶啤酒就可斟两三巡了。我心里暗笑广西人不懂喝啤酒。后来我偶然问得上海啤酒在邕宁卖一元六角一瓶!我才明白这样珍贵的酒应该用小酒杯斟的了。”[10](P107-108)美国传教家艾迪博士这样赞扬广西:“在中国各省中,在新人物领导之下,有完备与健全之制度,而可以称为近乎于模范省者,唯广西一省而已,凡中国人之爱国而具有全国眼光者,必引广西以为荣。”[11]
广西全省的新气象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吸引了大批的学者来作“广西现象”和民族学、民俗学的学术考察研究。20世纪20年代末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一阶段,全国视野下的“桂学”研究出现了第一次小高潮。相关学科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
这一点:覃乃昌在《20世纪的瑶学研究》一文中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瑶族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从20世纪20年代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与瑶族有关的文章约70篇[12]。覃彩銮在《壮学的发展与前瞻》一文中指出,壮学的开创者是西方学者,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开始有中国学者对壮族进行研究,陆续发表或出版了一批论著[13]。过伟在《广西20世纪民俗采录研究简史》一文中,把20世纪广西民俗之采录与研究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00—1949年,但列举的开创性成果实际也是指向20年代后[14]。
三、抗日战争形势的转变为“桂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全面抗战爆发后,淞沪会战一役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但由于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接连失利,上海、广州等城市相继陷落,大批文化人和文化教育机构内迁广西桂林、昭平、宜山等地。桂林更是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而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重镇,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城”。
伴随大批文化人内迁桂林,大量的刊物也转移到桂林,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刊物也创办起来。比较有影响力的,如中国第一种旅行类杂志——创刊于1927年的《旅行杂志》,因受战争的影响,1942年全部转移到桂林编印,其对西南地区的民风民俗是颇为关注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在1939年推出学术型会刊《建设研究》,成为广西的一个重要学术阵地;1940年,广西省政府公余生活进修社创办《公余生活》半月刊,1940年第3卷第8-9期合刊,被辟为“广西民俗学专号”,专门刊载有关广西民俗的文章。
云集广西的文化人,大多数在从事抗战文化活动,也有一批学者,潜心于八桂地域文化的研究。广西的独特文化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如广西的铜鼓、桂林的石刻及佛教摩崖造像、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谣等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把“桂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四、相关学者群出现及丰富的学术成果标志“桂学”初步形成
20世纪20—40年代,“桂学”的研究已经出现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学者群体。刘锡蕃、严复礼、商承祖、庞新民、费孝通、岑家梧、王同惠、唐兆民、贾农、黄芝岗、吴广略、魏觉钟、吴彦文、陶保桓、徐晓明、徐松石、魏鼎勋、路璋、张震道、陈志良、徐益棠、潘质彬等学者,都参与到“桂学”的研究中来,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但凡大学问,必有大学问家。以研究者的学术贡献为中心来考察,刘锡蕃、徐松石这两位广西本土学者和上海籍学者陈志良是桂学奠基时期颇有成就的大学问家。
刘锡蕃,又单名介(1885—1968),广西永福寿城人。曾任桂林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所长、桂林民族师范学校校长等职。他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作田野考察,所著《苗荒小纪》《岭表纪蛮》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28年和1934年出版发行,《广西特种教育的动向》载《建设研究》1939第1卷第3期、《研究广西民俗的我见》载《公余生活》1940第3卷第8-9期合刊、《宜山都安河池三县苗瑶种族及其婚丧概况》载于《建设研究》1941年第6卷第4期、《广西两大系派民族的由来及其文化的演进》《现阶段的广西瑶族》分别载《广西通志馆专刊》1948年第1期、第3期。
徐松石,又名仲石(1900—1999),广西容县人。20世纪20—40年代,多次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所著《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壮族粤族考》分别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39年、1946年出版。覃彩銮先生在《壮学的发展与前瞻》一文中,认为徐松石先生开启了壮学研究的先河,是壮学研究的开创者[13]。
陈志良,又名之亮,上海人。上海沦陷后,陈志良辗转内迁到桂林。曾任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教师、桂林汉民中学教师、桂林中央银行职员。其生平鲜为学界所知,其学术贡献亦大多淹没不彰。然而,他对“桂学”的贡献堪称巨大。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桂林佛教考古第一人,系统研究广西铜鼓之第一人,当时广西民族学、民俗学领域著述最多产者之一。
1939年冬,陈志良在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任教。他利用假日,开展对桂林西山古迹的调查,最后形成《广西古代文化遗迹之一探考——桂林丽泽门外的石佛古寺及西湖遗迹考》一文发表于《建设研究》1940年第3卷第1期,堪称桂林佛教考古之先驱;陈志良的《铜鼓研究发凡——广西古代文化探讨之一》一文载《旅行杂志》1943年第17卷第2期。他在此文的引言里提出“铜鼓文化”的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并希望广西的公私机
关承担起这一课题。如此,“广西的铜鼓文化”将在世界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一席,这富有远见卓识的思考,也正是今天桂学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陈志良采集岭西各族民谣3000余首编成的《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1942年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出版。与陈志良同是“说文社”会员的桂林文士朱荫龙,作《赠陈志良诗并序》称颂其对民间歌谣收集的贡献:“自吴琪、李调元而后,此调绝响200年矣。”[15](P32)此外,陈志良还在《公余生活》《说文月刊》《社会研究》《风土什志》《文史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广西特种部族的新年》《僈俗札记》《广西的社》《广西特种部族的舞蹈与音乐》《东陇瑶之礼俗与传说》《广西蛮瑶的传说》《广西异俗记》《广西特种部族的艺术——为桂岭师范公演作》《罗城布苗的礼俗》《西南诸宗族的木契之研究》等著述数十篇。
五、结 语
地域学不仅要立足于所在区域,还要努力在更大区域的文化(文明)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为这一体系作出独特的贡献,这是我们创立一门学问、构建一个学派的真正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全国的、全世界的学者来共同参与研究,使地域学和地域学派享有国际声誉。
“桂学”这一概念在当代的提出,显然是受到了“敦煌学”“藏学”“徽学”等的影响。其中之“敦煌学”与“藏学”乃已为世界公认之显学。而正如陈志良先生在《铜鼓研究发凡》一文中指出的,“桂学”是有成为国际“显学”的潜质的,这也应是今天桂学学派努力的方向。
敦煌学是以敦煌简牍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藏学主要以藏族的历史与宗教为主要研究对象,徽学主要以徽州文书为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支撑起来的地域学中的显学。那么,桂学的学术支撑点是什么?广西是一个民族自治区,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之一,民族文化与区域建设即是桂学的支撑点。从众多历史悠久的世居民族的文化基因中探寻文明发生的动力与运行机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以增进民族、国家间的理解与互动,响应“一带一路”的国家重大倡议,是支撑桂学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基础。
[1]潘琦.关于桂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6).
[2]胡大雷.地域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以“桂学研究”为例的探讨[J].广西民族研究,2014(4).
[3]李建平.桂学溯源与界定初探[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1).
[4]袁君煊.孙伟与桂学之开创[J].广西社会科学,2012(5).
[5]胡大雷,李晓明.“桂学”研究与广西文化——胡大雷教授访谈录[J].贺州学院学报,2014(2).
[6]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J].科学,1926(6).
[7]王国维.古史新证[J].燕大月刊,1930(1-2).
[8]陈志良.民俗古史学刍议[N].贵州日报,1942-02-23.
[9]刘峰,范继忠.民国(1919-1936)时期学术期刊研究述评[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8(3).
[10]胡适.南游杂忆[M].北京:国民出版社,1935.
[11]艾迪.中国有一模范省乎?[J].宇宙旬刊,1935(6).
[12]覃乃昌.20世纪的瑶学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3(1).
[13]覃彩銮.壮学的发展与前瞻[J].广西民族研究,2014(6).
[14]过伟.广西20世纪民俗采录研究简史[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0(3).
[15]魏华龄.朱荫龙诗文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陈梅云]
洪德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桂林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江苏南京210023
G122
A
1004-4434(2016)10-01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