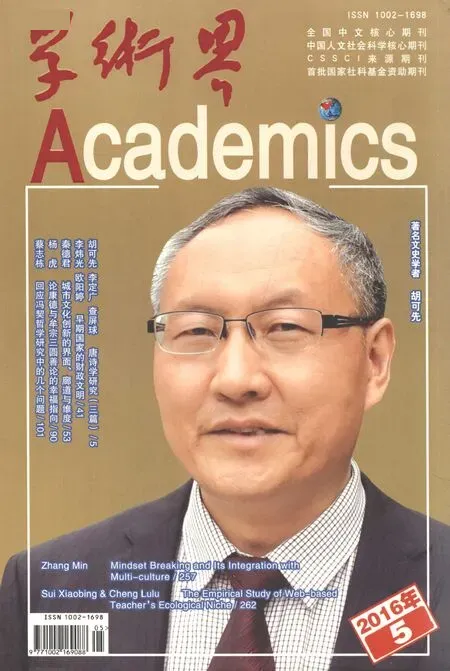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考实
2016-02-27李定广
○ 李定广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考实
○ 李定广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200234)
杜甫卒葬争议,是一个聚讼近千年的悬案,主要有二说: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说;大历五年秋冬之际卒葬岳阳说。本文全面清理相关文献,发现“岳阳说”的三个依据或可疑或扞格,而“耒阳说”证据更充分坚实,主要有两个事实:所有唐五代至宋初人祭拜杜甫墓者全在耒阳,绝无一诗一文涉及岳阳;北宋至明代人均曾为核实杜甫墓而进行过实地考察,证实唐宋元明四朝岳阳无杜甫墓。两大书证:正史新旧《唐书》杜甫本传。“耒阳说”之所以一直无法说服“岳阳说”,主要原因在于无法弭平元稹《杜工部墓系铭》“旅殡岳阳”之言。其实唐人在三种意义上使用“岳阳”一词,元稹所谓“旅殡岳阳”之“岳阳”指衡岳(衡山)之阳(南),实指耒阳,而非指岳州(今岳阳市)。杜甫大历五年夏五月卒葬耒阳应是事实。
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
与李白相比,杜甫的生平研究要清晰得多,唯一至今争论不休的是杜甫生命最后一段历程,即杜甫死于何时何地,葬于何处。千年来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的是: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卒葬于湖南,四十三年后的元和八年(813)其孙杜嗣业迁其灵柩归葬于其故乡河南。但杜甫卒葬的具体时间地点却存在严重分歧,主要有二说: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说(简称“耒阳说”);大历五年秋冬之际卒葬岳阳说(简称“岳阳说”)。虽然“耒阳”“岳阳”都在湖南,“大历五年夏”“大历五年秋冬之际”也仅差半年,似乎影响不大,但这关系到杜甫最后在湖湘漂泊时期所作一大批诗歌的确切系年问题,进而也影响到对这批诗歌的确切解读。
“耒阳说”出于唐郑处诲《明皇杂录》〔1〕以及两《唐书》之杜甫传(《旧唐书》卒年误作永泰二年),后世支持此说者有全部晚唐五代人及绝大部分宋人,近代以来主要有汪静之《李杜研究》、傅东华《李白与杜甫》、傅庚生《杜甫诗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朱东润《杜甫叙论》、金启华《杜甫诗论集》、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等。“岳阳说”出于北宋吕大防(1027-1097)《子美诗年谱》及王得臣(1036-1116)《麈史》,基本观点是大历五年夏杜甫自耒阳北还襄、汉,秋冬之际卒葬岳阳,后世主此说的主要有南宋人鲁訔、黄鹤,清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现当代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李春坪《少陵新谱》、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缪钺《杜甫》、陈贻焮《杜甫评传》、莫砺锋《杜甫评传》、张忠纲主编《杜甫大辞典》等。
此外,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则试图调和二说,认为大历五年夏卒于耒阳,葬于岳阳。
近十多年来,此争议波澜再起。自傅光先生《杜甫研究·卒葬卷》〔2〕上世纪末出版以来,先后有莫砺锋先生的《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3〕张忠纲、赵睿才先生的《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4〕霍松林先生的《杜甫卒年新说质疑》,〔5〕王辉斌先生的《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商评》,〔6〕《再谈杜甫的卒年问题——兼与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商榷》〔7〕等提出质疑,捍卫“岳阳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近七百万字的巨著《杜甫全集校注》亦持“岳阳说”。仅有刘明立先生的书评《杜甫卒葬研究的重大进展——兼评〈杜甫研究·卒葬卷〉》〔8〕支持“耒阳说”。
看来,不仅历史上杜诗学权威仇兆鳌、萧涤非等都支持“岳阳说”,当今重量级杜甫专家亦大都持此说。“岳阳说”的依据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杜甫有长诗《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述耒阳聂县令给他牛肉白酒,他饮食后到县投诗感谢,可知杜甫并非死于白酒牛肉(仇兆鳌即如此理解);第二方面是根据杜甫卒前在湖湘所作诗歌呈现的信息,推断某些诗歌作于“耒阳之后”,即由耒阳北返襄、汉途中;第三方面是根据元稹《杜工部墓系铭》所谓“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9〕一语。
关于第一方面杜甫是否死于白酒牛肉,与是否卒葬耒阳是两个问题,虽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但可从宋初王洙(997-1057)《杜工部集序》的详细记载得到合理解释:
大历三年春,下峡,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尝至岳庙,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具舟迎还。五月夏,一夕,醉饱卒,年五十九。……观甫诗与唐《实录》,犹概见事迹。……宝元二年十月王原叔记。〔10〕
王洙申明这段记载的史料来源是杜甫诗与唐《实录》,杜甫之卒在代宗朝,所谓“唐《实录》”应为令狐峘所撰《唐代宗实录》(今佚),可见其可信度之高。由这段记载可知杜甫在大历三年沿三峡入楚,大历五年夏四月避长沙臧玠之乱南下衡州(有《入衡州》长诗为证),寓居衡州以南的耒阳,寓居耒阳期间又曾沿耒水、湘水北上至衡山南麓的岳庙,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送白酒牛肉并用船将杜甫迎回耒阳,所以杜甫才有《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诗,其后在五月夏,一夕,醉饱卒。“醉饱”者应仍然是白酒牛肉。杜甫自大历五年夏四月寓居耒阳时间长达一月,耒阳令赠白酒牛肉自非一次。宋以后崇杜爱杜者极力辩其诬,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考量。
“岳阳说”的第二方面依据即推断某些诗歌作于“耒阳之后”,确有一定道理,然毕竟属于“推理”,难以坐实,所谓诗无达诂,对同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就将“岳阳说”者定为老杜自耒阳回棹北返所谓绝笔诗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一诗系于“耒阳之前”,〔11〕该诗中“三霜楚户砧”一句被“岳阳说”者作为杜甫大历五年秋仍在世的证据(大历三年下峡入楚至五年秋,在楚正好三个秋天)。其实“三霜”一词在古诗中是“晚秋之霜”的意思,不能解为三个霜秋,如牟融《送陈衡》“十年双鬓付三霜”,“三霜”与上句“十暑”属借对。“岳阳说”者又认为《长沙送李十一衔》中“洞庭相逢十二秋”是杜甫大历五年秋仍在世的证据。其实古诗中常用“十二”表示数量之多,未必是确数。古代诗歌中的数目字有很多特殊情况,如周年与虚年,确数与虚数,平仄对仗的迁就,以及作者记忆的误差等等,若一概坐实作为考证之基,则很容易出问题。而对于“岳阳说”者认定为“耒阳以后诗”的《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诸篇反驳最全面、最有力的大概是钱谦益:
自吕汲公《诗谱》不明“旅殡”之义,以谓是年夏还襄、汉,卒于岳阳。于是王得臣、鲁訔、黄鹤之徒,纷纷聚讼,谓子美未尝卒于耒阳,又牵引《回棹》等诗,以为是夏还襄、汉之证。案《史》,崔宁杀郭英乂,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此大历三年也。是年至江陵,移居公安,岁暮之岳阳,明年之潭州,此于诗可考也。大历五年夏,避臧玠之乱入衡州。《史》云:“溯沿湘流、衡山,寓居耒阳以卒。”《明皇杂录》亦与史合,安得反据《诗谱》而疑之?其所引《登舟》《归秦》诸诗,皆四年秋冬潭州诗也,断不在耒阳之后。《回棹》诗有“衡岳蒸池”之句,盖五年夏入衡,苦其炎暍,思回棹为襄、汉之游而不果也。此诗在耒阳之前明矣,安可据为北还之证乎?以诗考之,大历四年,公终岁居潭。而诸《谱》皆云是年春入潭,旋之衡,夏畏热,复还潭,则又误认《回棹》诗为是年作也。作《年谱》者臆见揣度,遂奋笔而书之,其不可为典要如此。吾断以《史志》为正,曰:子美三年下峡,由江陵、公安之岳,四年之潭,五年之衡,卒于耒阳,殡于岳阳。其他支离傅会,尽削不载可也。当逆旅憔悴之日,涉旬不食,一饱无时,牛肉白酒,何足以为诟病,而杂然起为公讳?〔12〕
由此看来,“岳阳说”的第二项根据亦没有说服力,唯一“可靠”的有说服力的就是第三项依据,即元稹《墓系铭》所谓的“旅殡岳阳”。
由于元稹是杜嗣业迁葬乃祖的见证者,其《墓系铭》“旅殡岳阳”之可信度极高,自仇兆鳌至今的权威杜甫专家之所以顽固坚持“岳阳说”,正是认定这一点。而“耒阳说”的证据虽然远比“岳阳说”丰富坚实,但由于无法化解或弭平元稹“旅殡岳阳”之言,故而只能自说自话,难被权威专家接受。然而,真相只有一个,笔者在探求真相的过程中,搜罗两说的全部正反证据,发现最重要的事实和书证皆支持“耒阳说”,而元稹《墓系铭》“旅殡岳阳”这座大山亦终于被移开。详述如次。
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以下两个事实使得“耒阳说”证据无比坚实:
其一,所有唐五代至宋初人祭拜、悼念杜甫墓者全在耒阳,绝无一诗一文涉及岳阳,也无杜甫的迁葬地河南偃师。
韩愈《题杜子美坟》一诗中明确指出“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然此诗曾受到“岳阳说”者质疑。〔13〕中唐李观(字元宾)曾为杜甫作传,亦谓杜甫死于耒阳。〔14〕《(嘉庆)大清一统志》引中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柩归葬于偃师县。”〔15〕阮阅《诗话总龟》引唐耒阳令诗云:“诗名天宝大,骨葬耒阳空”。〔16〕晚唐宣宗大中年间,李节过耒阳作《耒阳吊杜子美》诗,有云“惆怅杜陵老诗伯,断碑古木绕荒丘”。晚唐咸通十二年(871)罗隐任衡阳主簿时,曾多次亲自到杜甫墓上去祭奠。如罗隐《经耒阳杜工部墓》:“紫菊馨香覆楚醪,奠君江畔雨萧骚。旅魂自是才相累,闲骨何妨冢更高。騄骥丧来空蹇蹶,芝兰衰后长蓬蒿。屈原宋玉邻君处,几驾青螭缓郁陶。”从“闲骨何妨冢更高”可知,罗隐似是相信冢中埋有杜甫遗骸的。罗隐《湘南春日怀古》云:“少陵杜甫兼有文。……松醪酒好昭潭静,闲过中流一吊君。”这是罗隐在“湘南”吊杜甫。罗隐还有《耒阳》诗(一作《题杜甫集》)感叹杜甫墓被水浸坏。
作为长沙人的齐己极其崇拜杜甫,曾多次到耒阳去祭拜杜甫墓。齐己《次耒阳作》诗道出赴杜甫墓的路线:“绕岳复沿湘,衡阳又耒阳。不堪思北客,从此入南荒。旦夕多猿狖,淹留少雪霜。因经杜公墓,惆怅学文章。”又齐己《吊杜工部坟》:“鹏翅蹋于斯,明君知不知。域中诗价大,荒外土坟卑。瘴雨无时滴,蛮风有穴吹。唯应学太白,魂魄往来疲。”如果杜甫墓在岳阳(或岳阳有杜甫墓)的话,齐己从长沙到岳阳比到耒阳路途更近,又怎么会舍近求远呢?
其他悼杜唐诗如崔珏《道林寺》:“白日不照耒阳县,皇天厄死饥寒躯。”曹松《哭陈陶处士》:“白日埋杜甫,皇天无耒阳。”贯休《读〈杜工部集〉二首》:“不知耒阳令,何以葬先生?”皮日休《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谁知耒阳土,埋却真神仙。”韦庄《耒阳县浮山神庙》:“地有唐臣奠绿醽。”杜荀鹤《哭陈陶》:“耒阳山下伤工部。”杜荀鹤《经青山吊李翰林》:“谁移耒阳冢。”吴仁璧《还罗隐书记诗集》:“耒阳城畔青山下,兰麝于今满逝波。”(按,“耒阳城畔”指杜甫墓,“青山下”指李白墓)郑谷《送田光》:“耒阳江口春山绿,恸哭应寻杜甫坟。”
五代至宋初悼杜诗如裴说《题耒阳杜公祠》:“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孟宾于《耒阳杜公祠》:“一夜耒江雨,百年工部文。”王玄《吊耒阳杜墓》:“才高忧负国,身没耒阳城。”孙何《读杜子美集》:“世系留唐史,丘封寄耒山。”张方平《读杜工部诗》:“耒阳三尺土,谁为剪蓬蒿。”
有一点须在此稍作一辩。有“岳阳说”学者曾质疑:为何中唐罕有而到晚唐才有许多文人祭吊杜甫墓?在此须要说明的是,杜甫在世以及去世后,其地位一直不甚高。杜甫与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孟浩然都有交往,杜甫对他们的诗都赞美有加,但没有留下他们对杜甫的称赞之辞。李白在世及死后有魏颢、李阳冰等分别为之编纂全集,杜甫没有,至大历中后期始有友人樊晃为其编《小集》,仅收其作品二百多篇。自盛唐的《河岳英灵集》《国秀集》到中唐的《中兴间气集》《极玄集》皆不收杜诗。杜甫地位真正与李白平起平坐,是在韩愈、元稹、白居易三人的大力抬杜之后,至晚唐顾陶《唐诗类选》、〔17〕韦庄《又玄集》始收杜诗。故到晚唐方有许多文人吊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其二,北宋至明代人均曾为核实杜甫墓而进行过实地考察,证实唐宋元明四朝岳阳无杜甫墓。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引王观国《学林新编》云:
元祐中胡资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碑序》曰:“蜀乱,先生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于耒阳。”王内翰注子美诗曰:“大历三年,甫下峡,入湖南,游衡山,寓居耒阳,五年,一夕,醉饱卒。”元祐中吕丞相作《子美诗年谱》曰:“大历五年夏,甫还襄汉,卒于岳阳。”某尝考究杜陵及襄、汉、岳阳,皆无子美墓,惟耒阳县有子美墓,前贤多留题,则子美当卒于耒阳也。〔18〕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六《衡州衡阳郡·古迹》载有“杜甫墓”。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五十五《衡州·古迹·杜甫墓》有考曰:
《寰宇记》:“在耒阳县北二里。”又《旧史》云:“归葬偃师。”而《唐诗纪事》裴说经杜甫坟有诗云:“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又韩持国过杜甫坟有诗云:“三尺孤坟在,空留万古名。风骚谁是主?天地太无情。入夜月虚白,逢春草自生。耒阳江色迥,吊罢恨难平。”〔19〕
所引《寰宇记》即《太平寰宇记》,乃五代入宋的乐史所撰,其可信度向为宋以后人所重。又《舆地纪胜》同卷《古迹·杜甫迁葬偃师》有考曰:
《唐诗纪事》云:“适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楚,旅殡岳阳,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又《皇朝类苑》云:“杜甫终耒阳,槁葬之。至元和中,其孙始改葬于巩县,元微之为《志》。而郑刑部文宝谪官衡州,有《经耒阳子美墓》诗,岂但为《志》而不克迁?或以迁而故冢尚存耶?”〔20〕
所引宋江少虞《皇朝类苑》一段最早出于司马光《温公诗话》,通过考察肯定杜甫“槁葬”在耒阳,但对元稹《墓志铭》有所疑惑,认为有两种可能:或是元稹只作了《墓志铭》而实际上杜嗣业并未迁葬成功,或是即使迁葬成功但耒阳故冢确实仍存。
明以前文献凡提到杜甫墓者,均在耒阳。虽然杜甫之孙杜嗣业在杜甫去世四十三年后将杜甫灵柩迁至河南偃师,但北宋人曾专程到偃师去考察杜甫墓,却未能确认所葬位置,故唐宋元明文人祭奠杜甫皆在耒阳,没有在偃师的。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六:“杜子美坟在耒阳,有碑其上。……偃师首阳山在官路,其下古冢累累,而杜元凯墓犹载图经可考。其旁元凯子孙附葬者数十,但不知孰为子美墓耳。”〔21〕所言杜元凯即杜甫远祖杜预。明代文献始确认偃师杜甫墓的位置。《弘治偃师县志》载:“杜甫墓在县西。”〔22〕《明一统志》载:“杜甫墓在偃师县首阳山。甫,唐人能诗者,卒耒阳。”〔23〕
据现存文献考查,清代嘉庆以前文献没有提及岳阳有杜甫墓者。又,从古代地理学上看,除了湖南、岭南、赣南三地外,全国各地的文人若欲赴耒阳吊杜甫墓,必经岳阳,如果岳阳有杜甫墓,那唐宋元明文人为何经岳阳不吊也不提及,而偏偏要越山渡河南奔至耒阳?
除了上列两个基本事实,“耒阳说”还有两个最有力的正史书证,那就是新旧《唐书》杜甫本传。
其一,《旧唐书·杜甫传》载:“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24〕两次强调杜甫葬在耒阳。首先需要辨明的是《旧唐书·杜甫传》的史料来源问题。有“岳阳说”者认为,《旧唐书·杜甫传》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元稹《墓系铭》,《旧唐书》编者将元稹文中“岳阳”改为“耒阳”,所以《旧唐书·杜甫传》的记载是不能相信的。这一说法属于想当然耳。史学界一般认为,《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德宗以前主要是照抄唐代各代皇帝的“实录”及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德宗以后兼采碑志、杂史、别集、谱牒中相关史料。唐代宗及其前的唐史尤其如此,“《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25〕已为史学常识。《旧唐书》中每以史臣口吻称唐朝为“我朝”“我唐”“本朝”等,如笼罩《杜甫传》的《旧唐书·文苑传序》即云“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显然是照录唐代当朝史臣的“实录”之原文,而非五代后晋《旧唐书》编撰者赵莹、张昭远、贾纬等史臣的口吻。杜甫之卒在代宗朝,令狐峘所撰《唐代宗实录》及其参撰的《唐书》130卷(二书今佚)必是主要照录的史料。前引宋初王洙(997-1057)《杜工部集序》自称所述杜甫生平乃“观甫诗与唐《实录》”,所谓“唐《实录》”应为《唐代宗实录》,可见《唐代宗实录》至宋初王洙时尚未亡佚。比较《旧唐书·杜甫传》与元稹《墓系铭》对杜甫生平的介绍,差异甚大,显然不是直接取材于《墓系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杜甫传中全文引用了元稹的《墓系铭》,同时又强调“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显然,《旧唐书》史臣并不认为元稹《墓系铭》所谓“旅殡岳阳”与卒葬耒阳有矛盾,否则定会有所解释,不会在同一篇文章中自打耳光。看来,元稹所说的“岳阳”并非指岳州(今岳阳市)。
其二,我们知道,欧阳修、宋祁编《新唐书》的宗旨之一就是对《旧唐书》进行纠错补阙,《新唐书》在记载杜甫之死时,汲取了苏舜卿的意见,〔26〕认为《旧唐书》所载杜甫卒于“永泰二年”时间有误,纠正为“大历中”,至于《旧唐书》所云杜甫因食白酒牛肉而一夕卒于耒阳等信息,则认定正确而未改,其文曰:“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27〕《新唐书》的再次确认,尤值得重视。两《唐书》虽难免也有种种瑕疵,但作为正史,其总体上的权威性不容轻易否定。
通过以上对两个“事实”和两个“书证”的考辨,“耒阳说”的证据已十分坚实,下面移除“岳阳说”的最后防线,即元稹《墓系铭》所谓“旅殡岳阳”之“岳阳”一词的含义。
唐人口中“岳阳”一词的含义其实并不简单,从唐人的用例看,至少有三种含义:
一是特指“岳州”,即今天的岳阳市。今天的岳阳市唐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称呼“岳州”,有时也称“岳阳”或“巴陵郡”或“岳阳郡”。如张说的《岳阳早霁南楼》,孟浩然的“波撼岳阳城”等。“岳阳”的这一含义或用法,最为今人所熟知。
二是用为泛称,意指“山之阳”,“岳”即“山”,“岳阳”即山之南。此用法由来已久,《尚书·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解释道:“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阳,水北亦曰阳。”〔28〕宋傅寅《禹贡说断》注此“岳”字:“即今晋州霍邑县霍山。”〔29〕“岳阳”即指今山西霍山(太岳山)之阳。兹列举唐人用例如下:1.唐代山西的霍山之阳(南),亦称岳阳,并设岳阳县,《新唐书·地理志》第二十九《晋州》载有:“岳阳,中。东有府城关。”〔30〕晋州即今山西南部的临汾市,岳阳县在今临汾市东北;2.四川普州铁峰山之阳(南),唐人也称岳阳,普州辖县安岳县的县治,唐人亦称岳阳,至今四川安岳县的县城仍名岳阳镇。贾岛《访鉴玄师侄》《夏夜登南楼》等诗中屡屡提及的“岳阳”即此。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卷八《贾忤旨》载:“(贾)岛至老无子,因啖牛肉得疾,终于传署。后崔骑评事倅岳阳日,为诗悼之。岳阳,普州地名,今因创墓在岳阳山上,山下有岳阳池。”〔31〕;3.李白在江夏(今武汉)所作诗多自注“江夏岳阳”,如《望黄鹄山 江夏岳阳》《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江夏岳阳》《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江夏岳阳》,〔32〕李白自注的“岳阳”指的是黄鹄山之阳(南);4.“昭潭”在今湖南湘潭市东北二十公里的昭山之阳,相传周昭王南征不复,没于此潭,故名“昭潭”。盛唐类书《初学记》卷八引《湘州记》:“岳阳有昭潭,其下无底,湘水最深处。”〔33〕此“岳阳”,显然不是指岳州(今岳阳市),而是指昭山之阳(南)。
三是特指五岳之阳(南),“岳”特指我国名山“四岳”或“五岳”中任意一山。“四岳”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五岳”则增加中岳嵩山。此用法先秦两汉以来即有之。如《诗·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毛传:“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34〕又《文选·张衡〈思玄赋〉》:“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李善注:“岳,五岳也。”〔35〕东岳、西岳、南岳杜甫皆有诗作,皆题名《望岳》,此“岳”即为特殊简称。又如元稹《陪张湖南宴望岳楼稹为监察御史张中丞知杂事》诗题中“望岳楼”之“岳”即特指南岳衡山,因诗中有“今日高楼重陪宴,雨笼衡岳是南山”。元稹既特称衡山为“岳”,则其所谓“旅殡岳阳”之“岳”,用法可知。虽五岳皆简称“岳”,但衡山简称“岳”,唐人用例更频繁,像衡山南麓有岳庙,衡山脚下的书院,称岳麓书院。又杜甫《寄韩谏议》诗曰:“今我不乐思岳阳。”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卢元昌注以此诗为韩谏议隐居衡岳而作,此“岳阳”显然指衡山之阳。又中唐张仲素《燕子楼诗三首》曰:“适看鸿雁岳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此“岳阳”即衡岳之阳的意思,因为“衡阳雁断”是古人的常识。还有马戴《送韩校书江西从事》诗有句曰:“雁背岳阳雨,客行江上春。”大雁所背之“岳阳”当然指衡山之阳。
由上可知,唐人对“岳阳”一词有三种用法,元稹所说的“旅殡岳阳”之“岳阳”属于哪一种呢?联系元稹《墓系铭》上下文语境,谓杜甫“旅殡岳阳”应是有特定地点的,又联系元稹在其他诗文中如前引《陪张湖南宴望岳楼稹为监察御史张中丞知杂事》亦以一个“岳”字指代南岳衡山。故其“旅殡岳阳”之“岳阳”应当为上述第三种用法,即指衡岳(南岳衡山)之阳(南),而杜甫的卒葬地耒阳县,唐时归属于衡州(衡阳郡),正是在衡岳之阳(南)。当然以上述第二种用法解释也可通,因杜荀鹤诗有“耒阳山下伤工部”之语,故此“岳”指耒阳山亦通。惟有上述第一种用法指岳州(今岳阳市)与前列两个“事实”及两大“书证”严重扞格,最不可取。难怪宋刻本蔡梦弼《草堂诗话》卷二在引用元稹《墓系铭》时引作“旅殡耒阳”(当是蔡梦弼臆改)。
最后,对于钱谦益为代表的折衷派认为杜甫“卒于耒阳,殡于岳阳”一说,结合唐代卒葬的社会风俗,稍辨其非。据相关学者研究,唐代的丧葬形式,大致有“归葬”“权葬”“迁葬”三种主要方式。“归葬”即归葬祖茔,是唐代最普遍、最为时人认可的丧葬方式。但有时或因为时局动荡不安,或因为财力不足,或因为岁时不便等某一个因素限制,又不得不采用“权葬”,“权葬”就是权且安葬在祖茔以外的地方,又称“权厝”“权殡”,也即元稹所谓“旅殡”。杜甫卒时,“时局动荡不安,财力不足,岁时不便”三个因素竟然同时具备,尤其是“岁时不便”的因素,使得杜甫之葬不可能远离耒阳。据前考,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夏五月,地处南方的耒阳正是一年中最高温的时节,就地殡葬自是必然。
杜甫二子宗文、宗武皆流落湖湘而卒,今湖南岳阳市平江的所谓杜甫墓,当是宗文或宗武墓,大概是后人因对元稹“旅殡岳阳”产生误解遂附会为杜甫墓。
结论:杜甫大历五年夏五月卒葬耒阳应是事实,其卒前一年诗歌当据此重新编年。
注释:
〔1〕郑处诲《明皇杂录》载:“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中华书局,1994年,第47页。
〔2〕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3〕莫砺锋:《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2期。
〔4〕张忠纲、赵睿才:《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文史哲》2001年第2期。
〔5〕霍松林:《杜甫卒年新说质疑》,《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
〔6〕王辉斌:《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商评》,《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7〕王辉斌:《再谈杜甫的卒年问题——兼与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商榷》,《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8〕刘明立:《杜甫卒葬研究的重大进展——兼评〈杜甫研究·卒葬卷〉》,《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9〕宋蜀本及明清诸本《元氏长庆集》俱作“旋殡岳阳”,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及他书所引俱作“旅殡岳阳”。
〔10〕见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240页。
〔11〕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209页。
〔1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一百十《兴尽本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13页。
〔13〕韩愈此诗,本集未收,过去一般认为出自刘斧《摭遗》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自宋蔡梦弼《集注草堂杜工部诗》提出质疑后,持“岳阳说”者纷纷质疑为伪作。其实此诗在宋代除了注杜诸书多所引用外,其它与注杜无关的多种文献亦皆有录载。如宋谢维新《事类备要》前集卷七《地理门》引韩愈《题子美墓》,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四引韩愈诗“今春偶客耒阳路”,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十八《地理部》引韩愈《题子美墓》等。“岳阳说”者质疑为伪作未免武断。
〔14〕见《杜诗详注》所引,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260页。
〔15〕见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百六十三所引《元和志》。今传残本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未见此条。
〔16〕阮阅:《诗话总龟》卷四十五《伤悼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26页。
〔17〕《唐诗类选》今佚,但今存顾陶序中提及收李杜等人诗,只未收元白诗。宋曾季狸《艇斋诗话》:“顾陶《唐诗类选》二十卷,其间载杜诗,多与今本不同。”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杜子美集无〈遣忧〉诗》:“余家有唐顾陶大中丙子岁所编《唐诗类选》,载杜子美《遣忧》一诗,云……”
〔18〕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96页。
〔19〕〔20〕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2020、2021页。
〔21〕赵令畤:《侯鲭录》,中华书局,2002年,第162页。
〔22〕魏津:《弘治偃师县志》卷一,明弘治钞本。
〔23〕李贤:《明一统志》卷二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055页。
〔25〕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2页。
〔26〕苏舜卿《题杜子美别集后》:“又本传云:‘旅于耒阳,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此诗中乃有《大历三年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将适江陵》之作及《大历五年追酬高蜀州见寄》,旧集亦‘大历二年调玉烛’之句,是不卒于永泰,史氏误文也。览者无以此为异。景祐三年十二月五日长安题。”见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十四,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27〕〔3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738、1001页。
〔28〕〔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29〕傅寅:《禹贡说断》,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31〕见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932页。
〔32〕俱见李白集两种宋刻本及元刻本,清王琦注本将各篇“江夏岳阳”皆删去,可能以为四字费解。
〔33〕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190页。
〔34〕〔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06页。
〔35〕〔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215页。
〔责任编辑:黎虹〕
李定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魏晋唐宋文学及文论。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融资政策与学术支持〔*〕
- 我国宪法文本中“文化”表述的剖析〔*〕
- 占有保护理论与实践问题之反思〔*〕
- Discussion on Great Ruins Presentation Method
—— A Case Study of Wuhan Panlong City Archaeological Park - Research on the Variability and Impact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Era〔*〕
-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ief Activities from the Municipal Office in Wartime
——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Municipal Health Arch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