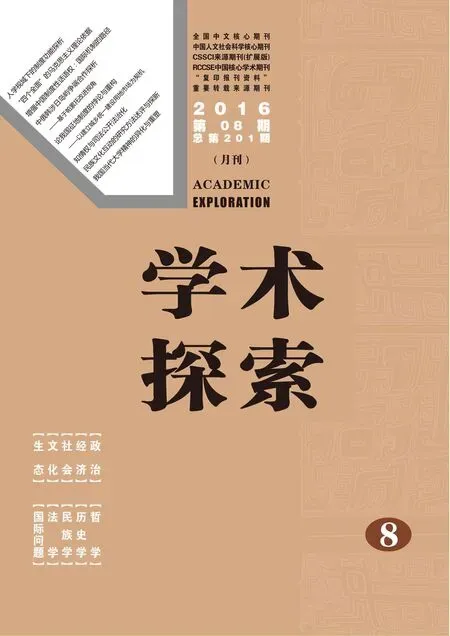“四个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
2016-02-26王培洲
王培洲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四个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
王培洲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91)
“四个全面”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维度上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四个全面”是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的统一。深刻理解“四个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才能从原则高度上把握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新时期的重大意义。
四个全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道路;实践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布局。“四个全面”作为新时期的治国理政思路,不仅有历史洞见和现实意义,更具备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和内涵。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1](P2)此即说明“四个全面”的理论来源必然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其“本质本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2](P26)如果注意到“四个全面”生成前后中央政治局的两次集体学习,便可发现“四个全面”作为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四个全面”提出一年前,就如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安排的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四个全面”提出不久,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两次学习的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部分,无疑对“四个全面”的生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恰恰说明“只有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这个根本上加以学习,我们对‘四个全面’才能理解得更深透,落实得更有力”。[3](P33)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四个全面”作为社会主义新探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
一、认识论依据: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标签,马克思本人始终坚持“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4](P92)列宁则强调“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5](P419)其实,“四个全面”的提出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下提出的富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和方略。“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背后有着强大的实践基础——中国道路。近现代中国的发展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产生的实际问题,都在实践逻辑的框定下寻找解决方案。革命阶段我们要在“三座大山”压迫下实现民族独立;建设阶段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发展初期我们肩负着“四个现代化”历史任务,需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6](P314)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今,我们处在历史新时期,面临“两个一百年”和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目标,仍要继续蹄疾步稳地全面深化改革。“在现代化问题上,中国别无选择”,[7](P21)在各种“新常态”中我们必须安稳渡过改革深水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实现科学地现代化建设,凸显“中国现代性”。[8](P47)将“四个全面”放在马克思主义整体视域中审度,便会发现其正是在发展语境中对中国历史实践的理论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作为“四个全面”的背景输入,意味着“四个全面”的提出就带有着强大的实践性特征。“四个全面”在历史实践中产生,也是在解决今后中国“如何更好地实践”这一时代命题。“四个全面”不是虚招,也不是空想的形而上学范式。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我们树立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下的科学化实践方案和路径选择,前者为目标提供永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后者为目标提供实践的制度保障,是实现目标的“两翼”;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新实践提供必要的政治保证。由此可见,“四个全面”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条实践逻辑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9](P90)“四个全面”不仅彰显了实践逻辑,背后也有一条深深的理论逻辑。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10](P39~40)这说明,我们党“始终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11](P114)“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结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大理论成果,无疑具有这样一个“理论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探索。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1987年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轮廓,十五大“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问题”。
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全面”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其在新的历史起点形成的问题意识正是来源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基本理论。它与“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一脉相承,这个“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全面”面对着新时期的新问题,为发展质量、动力、秩序和保障等提供理论支援,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探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逻辑”这一度的时候,就已经走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式的隐喻。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逻辑始终是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逻辑和历史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意义链,在历史演进中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完成统一。“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12](P12)“四个全面”是从实践和理论来把握历史的,在历史维度中,“四个全面”的历史语境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这就使“四个全面”回应了“历史性要求”,具有极强的历史感,也加深了其实践和理论的双重逻辑。
二、方法论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其方法论精髓正是因为我们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认识和实践的重要法则;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四个全面”被时代赋予新的眼界和理论抱负。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我们要用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思维去想问题、办事情。一,“四个全面”中的四个组成部分绝非是机械的排列组合,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四个全面”才是一个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内涵的顶层设计。理由是,如果孤立地看待“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其蕴含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改革开放之前就已提出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当今中国解决现代化问题的关键一步,可以追溯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到“深化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从严治党则是我们党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以来的政治优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这就是说,如果孤立地看待和践行“四个全面”,则会使“四个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的功效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实现“四个全面”的整体性升华,赋予其“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13],即“四个全面”是一块“整钢”,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确立了这个整“体”,才能发挥效“用”,“体”和“用”,结构和功能在整体性中得到最大化统一,以整体性眼光看待“四个全面”,才能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时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得到全面整合和全面推进。二,“四个全面”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每一个“全面”都具有内在相关性,“其中任何一方面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不关系到其他方面”。[14](P17)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在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时已经明确指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5](P3)在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协同”成为五大发展新理念之一。只有坚持联系的观点,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每一个“全面”在耦合机制中实现互动,“四个全面”中蕴含的“一体三翼”“目标—路径”分析法才能形成“战略布局”,在实践中发挥实效。三,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路,“四个全面”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四个全面”作为方法论依据,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科学发展,确保完成第一个“一百年”的发展任务。发展目标的升级意味着发展环境的变化,“四个全面”深刻说明了发展仍是硬道理,但这其中的“道”和“理”处在各种发展问题中:经济进入新常态,GDP增速放缓,面临“三期叠加”难题;民主、法治、公正诉求不断增加,使我们要不断思考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6](P19);文化认同问题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迫在眉睫;社会风险加剧,民生之忧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资源趋紧、环境污染迫使我们不得不转变发展观念,“绿水青山”如何变为“金山银山”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课题。“四个全面”正是形成于这些“发展问题域”,即“四个全面”在我们不断实现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这也构成了其能实质性解决发展问题的合法性。正是基于此,有国外学者认为“‘四个全面’理念对于治国方法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转型的问题给出了答案”。[17](P5)
因此,用整体、联系、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眼界来理解“四个全面”才能把握住其本质的那一面,才能理解推进“四个全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能让我们更深地理解“四个全面”的结构,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则告诉了我们“四个全面”的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中,“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8](P104)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有着鲜明的群众指向,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4](P285)“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9](P1096)“四个全面”立足唯物史观的起点——“现实的人”,“四个全面”的形成本身就是在践行群众路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深化改革在于“分好蛋糕”,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红利,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用制度保障公民的权利;全面从严治党最大限度地践行着“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四个全面”共同构成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P3)从群众中来的理论才是“彻底的理论”,才能真正“掌握群众”,[4](P9)才能“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20](P367)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人民群众形成发展和改革共识,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群众史观正使目前党和国家大力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了理论依据,这样就确保了“双创”能在实践中发挥最大功效。
继续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理路,如果说理论“把握群众”是群众史观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那就说明了我们还应当重视思想、文化、理论、观念等所代表的社会意识。在唯物史观中,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但社会意识往往对社会实体性内容有着强大的反作用。社会意识作为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眼中“批判的武器”,毛泽东将其指认为“自觉能动性”,卢卡奇称之为“阶级意识”。李泽厚在其《现代思想史论》中讲道:“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历史观……也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21](P212)“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P11)意识形态就是“主义”,作为一个国家“需要的理论”,具有对实践的科学指导意义,有“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从革命导向的新民主主义到建设和发展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凝聚民心,汇聚共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断提供精神资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世情、党情的价值标准和实践依据,以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起步和扎实推进。在当今历史新时期,“四个全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精髓,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从意识形态意义上来讲,“四个全面”是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组成,具有战略意义。之所以有战略意义,是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在意识形态意义上是一个整体原则,这个原则构成了支撑中国道路的科学方法论。这就意味着“四个全面”产生于中国道路,又是中国道路的精神表达。在作为意识形态的“四个全面”中,我们要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落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之中;要将中国梦、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联系起来,共同作为“五位一体”建设的思想支撑。“四个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将持续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
三、价值论依据:价值立场与价值取向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研究方法与整个马克思主义都是一致的”;[22](P19)其“追求的既是科学真理,又是价值信念”。[23](P5)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有价值理论,而且有着鲜明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要在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刻画出中国独特的道路和具体内涵”[7](P18)。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十分鲜明,无论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两个绝不会”,无论是社会演进的“三形态说”(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还是“五形态说”(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统摄下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体现。“要正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价值之争’的实质,要遵循一个重要原则,即历史原则。”[24](P9)正是在这个历史原则之下,《共产党宣言》中所要实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前提的联合体便被除去了乌托邦色彩,才可以作为一个远大的共产主义信念被我们理解。《宣言》中的联合体从价值论角度来理解就是一个价值共同体,是在唯物史观中建构的科学社会主义理念和价值,具有实践意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契合,“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23](P4)
因此,共产主义信仰、实事求是精神,为人民服务理念等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基本价值立场,“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三讲”“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正是从这个价值立场出发,依据这个价值立场进行实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今天,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对“新的历史特点”之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是共产主义信念的当代表述,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四个全面”下的“五位一体”建设就是一种“有原则高度的实践。”[4](P9)
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的规定性之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当前社会高扬的价值取向,“四个全面”始终遵循着这种价值取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公民层面的价值取向是“四个全面”价值表述的应有之义。“四个全面”在树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价值目标之下,全面深化改革正是通过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富强民主,突显社会平等公正;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实践;全面从严治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关键少数”必须首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担当者,必须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优化政治生态进而为整体进而科学实践“四个全面”布局。可见,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搭建的价值平台,“四个全面”既是一个价值承诺,又是一个价值动力,在实践中实现了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存在着一个“世界历史理论”,将其放在价值论中考量同样具有深刻的内涵。“四个全面”体现了中国道路的独特目标和价值,是依据中国国情,面向中国问题,展开中国实践的科学解释,并具有实践价值和意义。这样,我们就在全球化进程中自觉地增进和实现着价值认同,我们就避免了将我们实践上的努力拿到“他者”的符号领域中去兑换价值和意义,避免了成为别人发展的一个注脚、一个价值镜像,从而有力地回应了“历史终结论”。
[1]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王遐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法论探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7).
[3]冷溶.习近平“四个全面”哲学思维[J].理论导报,2015,(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李泽厚.九十年代李泽厚对话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4.
[8]侯才.哲学的伦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塑[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3]曲青山.党的十八大与“四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J].中共党史研究,2015,(3).
[14]吴晓明.“四个全面”是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部署和实践纲领[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6).
[1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7]周明海.海外视野中的中共治国理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J].探索,2015,(4).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2]马俊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3]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4]姜迎春.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特点[J].学海,2009,(4).
〔责任编辑:左安嵩〕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WANG Pei-zhou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100091, China)
To understand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we should return to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Marxist theories. The thought is based on the system of Marxist scientific ideology in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value theory. That is, it is the unity of practic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logic,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value position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We mus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xist basis of the proposal,so that we can grasp the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strategic blueprint in the new era.
four comprehensives; Marxist theory; China model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KS020);中共中央党校重点课题(DXZD201301);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及特色学科重大科研项目(GDZT201304)
王培洲(1987— ),男,河南濮阳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执政党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社会思潮研究。
D616
A
1006-723X(2016)08-0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