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地理
2016-02-25薛巍
薛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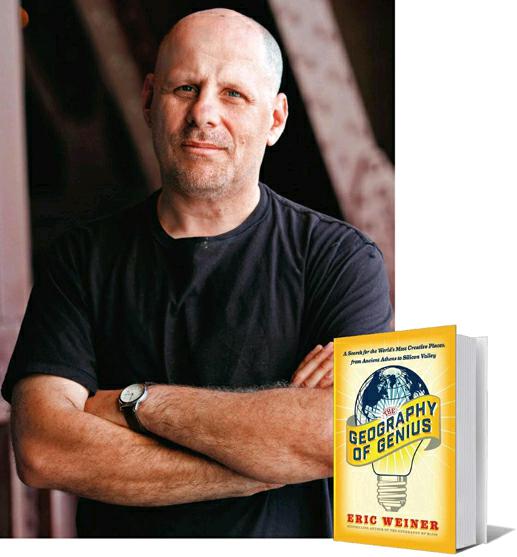
埃里克·韦纳和他的著作《天才地理》
为什么硅谷是不可复制的?
如今硅谷是天才汇聚之地,世界上有好多地方都在努力复制硅谷,从英国(泰晤士谷)到迪拜(硅谷绿洲)。除了少数例外,它们都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美国记者埃里克·韦纳说,原因之一是他们以为硅谷是一个公式,忘记了它是一种文化,是特定时代和特定地点的产物。而复制硅谷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太急切了。政治家希望他们还在位时就看到结果,总裁希望到下一个季度就看到结果,而雅典、杭州等这些创意城市都是长期酝酿的产物。那些希望复制硅谷的城市和国家都以为他们需要创建一个没有冲突的地方,而冲突和张力实际上是动力。
韦纳把硅谷的历史追溯到了1912年的无线电产业。他说,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个偶然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推动了硅谷的兴起。美国国会通过法律要求所有的船只都要拥有舰对岸无线电。那时硅谷已经有了新兴的无线电产业,随后开始繁荣起来。硅谷兴起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的业余爱好者文化,在个人电脑时代,很多人自己在家鼓捣电脑。这其中有白手起家和反体制的成分。人们跑到那里是为了逃离某种东西,但他们又不是在主流之外。天才们都是“局内的局外人”。他们有着局外人的视角,可能是移民或者难民,但他们又足够置身于局内,能够影响主流。
韦纳认为,如今“天才”这个词被使用得太泛滥了,有足球天才、营销天才,以及其他各种天才。天才的意思应该是指那些超越了他们所在领域的人。“天才”一词前面不需要任何限定。如果你要说某个人是营销天才,那他就不是一个天才。我们不会说莫扎特是一个音乐天才,或者爱因斯坦是一个科学天才,我们只说他们是天才。他们已经超越了他们特定的领域。他对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说:“现在我们在养育无数小莫扎特、小爱因斯坦,还有人说每个人身子里都有一个天才。用天才来描述足球运动员或者营销经理,这是对真正的天才的贬损。”
有人说天才是天生的,有人则认为后天培养才是决定性的。近来流行的是天才源自苦练,练够1万小时就能成为天才。韦纳则提出: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天才是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地方出现的一群杰出的头脑和优秀的创意。他写道,历史测量学发现,“天才并不是随机出现的——西伯利亚一个,玻利维亚一个——而是扎堆出现的,如在公元前450年的雅典,公元1500年的佛罗伦萨。问题是为什么会是这样。这肯定不是因为遗传。那些黄金岁月来去的速度比基因的变化快得多”。那是因为什么?气候?钱?运气?韦纳说是因为文化。
天才之都的三大特征
2008年,韦纳在《幸福地理》一书中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他在新书《天才地理》中聚焦了七个地方,试图揭示是什么使它们成为文化、政治、技术进步的中心。这七个地方是雅典、硅谷、杭州、佛罗伦萨、爱丁堡、加尔各答和维也纳。在西方仍处于黑暗年代的时候,宋朝的杭州出现了几百年的科学和文化繁荣。爱丁堡在18世纪晚期发生了一场苏格兰启蒙运动,涌现了亚当·斯密、休谟等思想家。佛罗伦萨出现过文艺复兴。加尔各答在1840到1920年之间,因为英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碰撞而产生了生机勃勃的智识生活。维也纳则有过两个天才时刻:莫扎特、贝多芬的年代,它是音乐中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心理学和艺术的中心。
这七个地方几乎都是城市。“虽然我们会受到自然的启发——林中漫步,瀑布的声音,但是都市环境更有利于激发创新。如果如非洲谚语所说,养一个孩子要举全村之力的话,养一个天才需要一座城市。”
在每个地方,韦纳参观了历史古迹,采访了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当地人,试图呈现使它们获得天才的黄金年代的历史条件。“宋朝的杭州很繁荣,当欧洲人还在忙着从头发里捉虱子、琢磨中世纪何时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在忙着发明、发现、写作、绘画。”
他在杭州采访了马云,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韦纳写道:“马云坚持说他是百分之百的中国制造,但他的成功故事是混血的。中国人对传统的尊敬加上美国人的进取精神。”那为什么中国没出现更多的马云?是因为害怕风险吗?马云说不是,“你看看中国人在赌场或者马路上的表现。中国人是大赌徒”。马云说遏制了中国人的创造性的是教育体系,尤其是可怕的、令人头脑麻木的考试。考试是无穷无尽的痛苦的根源,也是创造力的杀手。
马云还跟他说,造成中国人创造力不如西方的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丢失了它的文化,它的宗教。那些宗教的教导包含许多给人启发的思想,对创造性思考有用的思想。“在我跟eBay或者其他人竞争时,我从来不用西方人的方法,我用的是道家的方法。当你推我的肚子时,我不会推回去。相反,我会打你这里,这里。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要用智慧,聪明地打,要一直保持平衡。”西方人的方法是拳击的方法,马云的方法是冲浪者的方法。
在杭州,韦纳一边品茶,一边想到,他曾经遇到一个人,以前每天都要喝六七杯咖啡,但后来改喝茶了,因为咖啡让人思考得更快,而茶让人思考得更深入。这大概能够解释中国和西方天才的差异,西方人喝咖啡,所以能够获得电光石火般的洞见,而在东方,因为吸收的速度更慢,因此他们都具有长远的眼光。
韦纳在书中讨论了金钱对创新的作用。历史上的大部分天才都出自中等和中上等阶级,这些人有足够多的钱去追求他们的爱好,但钱又没有多到让他们陷入自我满足的地步。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的绽放是由于美第奇等家族的资助,今天,硅谷的美第奇家族是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人。天才不能抽象地存在,它们需要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韦纳总结说,所有天才的沃土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都具有多元化、洞察力、混乱(diversity,discernment,and disorder)这三个特征。洞察力可能是其中最重要也最被忽略的成分。曾经有人问美国化学家、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莱纳斯·鲍林,如何想出好的创意,他回答说很简单,“你有许多创意,然后扔掉不好的创意就行了”。创意城市也是如此,只不过范围更大。它们既是磁石,也是过滤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选择支持哪些项目。在硅谷,是风投资本家扮演这一角色。
创意城市还都是开放的体系,乐于接受外来想法。它们还都比较混乱甚至动荡。美国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发现,在充满政治阴谋、动荡和不确定性的地方创意产业都很繁荣,大概是因为冲突能鼓励年轻人考虑更加激进的世界观。
最后,天才们都是跟他们的环境合拍的。贝多芬很熟悉维也纳郊外森林的韵律,并从中找到了灵感。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脚踩的泥塘搅动了他的内心。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时拜访了格拉斯哥许多商人和码头工人。这些天才的创造方式不是从外界回撤,而是更深入地卷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