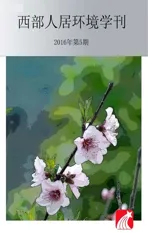怀念我的父亲黄光宇
2016-02-23黄剑
黄 剑
(AECOM景观规划设计副总监,美国LEED AP认证专家,美国城市土地协会会员,中国景观设计师协会会员)
怀念我的父亲黄光宇
黄 剑
(AECOM景观规划设计副总监,美国LEED AP认证专家,美国城市土地协会会员,中国景观设计师协会会员)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
10年有如弹指,往事依然清晰,而且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而美好。我愿意相信,那些杰出的人类先贤们都化作了闪耀的群星,在历史的长河中用他们的智慧指引后人不断前行。父亲只是一个普通人,但在我的星空中,他是最亮最暖的那一颗。10年的时光已经洗淡了悲伤,留下的,是闪亮的回忆和无尽的感激。
童年印象中的父亲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40岁。文革期间,在支援三线建设的政策引导下,母亲从上海调到自贡,带着我和哥哥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那时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父亲在重庆教书,一年只有两个星期的探亲假,难得与我们见面。据说,我小时候是个很大方的孩子,见谁都自来熟,可是因为很少见到父亲,他一抱我就哭。那时候,四川定量一个月只有二两糖票,父亲在云南、上海等糖不限量的地方出差,都尽量买些糖果带回来。母亲说,他来自贡探亲的时候,常常早上天不亮就背上背篓,来回30多公里山路,去老乡的集市上买回来便宜的肉、蛋、鱼给我们改善伙食。我不记得那时候的父亲。
后来全家终于搬到一起,住在当时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东村的半栋小楼里,楼下是厨房和小门厅,楼上是两间卧室。父母的卧室也是他们的书房,阿婆(按照老家的规矩,我管奶奶叫“阿婆”)、我和哥哥睡在另一间,和爸妈的房间只有一帘之隔。有时候我半夜醒来,父亲还在台灯前工作。但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父亲多半已经出门了。别的孩子们经常和父亲母亲一起上公园、去游乐场,或者去游泳池玩水,这样的记忆于我几乎是空白,我也不记得他给我讲过睡前故事。倒是母亲为了让我坐得住,早早教我认了些字,我便可以自己坐在小板凳上拿本书看很久。在这样的忙碌中,父亲和母亲抽时间在门前砌了一个水泥台子,母亲在那里洗衣服,我和哥哥在那里打乒乓球。他们还在旁边砌了一个种植池,种上一株腊梅。冬天,母亲把腊梅剪几枝放在屋里,浅黄的花瓣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味,爸爸和我都一直非常钟爱腊梅。父亲还曾经带着我和哥哥在附近种了几棵芋头。可是,父亲母亲都那么忙,小学典型的《我的xx》作文,哥哥写的是《我的妹妹》,我写的是《我的哥哥》。
后来我长大一些,父亲仍然是经常出差。在他有限的在家的时间里,他或者在接电话,或者和来访的客人谈话,或者在伏案写作,或者和学生站在铺满整个客厅的地图前讨论问题。有时候出差间隙回家换件衣服,又要奔赴下一站,中间只一两小时的时间。母亲一边调侃他拿家当旅馆,一边手脚麻利地为他收拾好干净的衣物,顺便为他简单做碗面条,还不忘往楼下焦急等着送他去机场的司机那里喊话:“马上就下楼……”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做作业一边听着外边的动静,一不留神,父亲已经又踏上了旅程,不见了身影。这样的场景在我家堪称典型。
我的父亲要不在出差,要不在工作。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家长会,他也不知道我上几年级,他在不在家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对父亲的印象都很模糊,但是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那就是,父亲爱我。
老顽童
在这样的童年印象中,和父亲一起玩耍的时光就显得特别稀罕,而且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和父亲一起去一个水库划过船,那也是印象中仅有的一次钓鱼、抓贝壳的经历。夜里突然停电,世界变得漆黑一片,屋里伸手不见五指。父亲带我摸黑出门,一抬头看见繁星满天,简直美得难以置信!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那么多的星星!父亲跟我一起找北斗星,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我们一起玩的时候,父亲是个老顽童!他笑起来天真无邪,高兴起来可以手舞足蹈。我还记得他兴致勃勃地带我观察蚂蚁、跟我描述追野兔的情景。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一直是一个充满好奇心、活泼乐观的大孩子,从来不摆家长架子。我们经常说他在家里的地位是最低的,人人都可以“涮”他。有时候母亲拿出家长的威严批评教育我和哥哥,父亲还作为我们的“盟友”,跟我们一起挑战或者“反抗”,在母亲面前高呼:“反对有理!抗议无罪!”
听母亲说,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够呛,关在牛棚里写检查,钢笔都写坏了好几支,每天被押去劳改,那样的情形年复一年,想必是非常令人绝望。父亲的衣服破了要借根针来缝补都被红卫兵没收,严加监视,怕他自寻短见。他的乐观和坚强支撑着他熬了过来,而且还能拿那段经历来自嘲、打趣,笑傲人生。
三十而立
父亲很少说教,他对我们的各种歪理都有兴趣倾听,而且如果觉得有道理他就能够接受。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我和哥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谓言传不如身教。记得有一次父亲拿孔子的“三十而立”教育哥哥,说男人一定要有事业心,应该尽早确立事业方向,不然难以立足养家云云。我听了就插进去追问一句:“那女生呢?”父亲楞了一下,一时语塞。我马上就笑话他:“还教授哩,连孔子的话都讲不明白!”父亲一点都不生气,和我们笑成一团。后来当我自己迈过30岁的人生门槛,再回想起来当时的场景,觉得男人和女人在价值观上确有不同,父亲当时的犹豫或许是对的,“三十而立”在通常意义下对男性的指导意义未见得也适用于女性吧。
父亲对先哲的话常有创见。他相信“有容乃大”,虽然经历过许多坎坷,见识过各色人等,父亲的心地一直是善良的,在他的眼里没有坏人。但是当我读“人性本善”的时候,父亲却提出异议,认为“人性本无”。他不能接受“人性本恶”,但他也举出很多例子,说明个体的性情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十分显著。不过,父亲认为,虽然“人性本无”,但是“向善”是每个人应该付诸努力的方向,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或许正是这样的心态,父亲广结善缘,连系里看门的大爷,扫地的老工人,都跟他很相熟。
少小离家,笨鸟后飞
父亲很少跟我谈他自己的经历。我只记得一次他跟我讲起他的童年。父亲是7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家境贫寒,阿婆给他做的鞋子从冬穿到夏,天天赤脚上学,到了校门口才从怀里掏出鞋子穿上,即使冬天也是这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读书很用功,一直靠成绩好取得公费补贴,中学就保送到杭州,大学也是保送,而且没有毕业就做辅导员,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执教生涯。
父亲自认没有任何天分,全靠勤勉乐观、能吃苦、不服输的精神支撑自己。他非常痛惜在文革中耽误的10年光阴,感叹之余更希望我能珍惜时间,多学多问之外特别要学好英文。那时候父亲已经意识到生态规划领域虽然国内少有知音,国际上却有不少同行,于是他开始积极拓展对外交流。他发现学术交流中事事需要依靠翻译,而往往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图,就下定决心要学外语,那时候他已经50岁,平时就已经忙得快没时间睡觉了,父亲自嘲说这叫“从零开始,笨鸟后飞”。他刻苦学习英文,经常向人请教,勇敢地拿着字典去攻克一本本英文学术专著,遇到不懂的单词就在随身带的小本上记下来,抄满了好多本,积累起来的英文卡片更是放满了一抽屉。后来他去哈佛大学做讲座,虽然还是需要翻译,但日常交流基本可以应对。
我初中时英文很差,一度在及格线上挣扎,父亲没有直接批评过我,但他跟我分享他的经历和教训,真诚地希望我不要像他那样在交流中受制于语言的障碍。后来,我的确英文颇有起色,有时也能帮助父亲做些翻译的工作,父亲很为我自豪,对我的翻译总是表示高度信任。
爱生如子
父亲很早就离开家独立生活,这样的生活历练不但没有让他变得圆滑世故,反倒使他一直保有纯净真挚的赤子之心。他的学生们最爱他的绝无门第之见,极为平易近人且不拘小节。他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展开讨论或者开玩笑,畅想中国城市规划的美好未来,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做不完的事情。我曾经总结,父亲最喜欢的就是和学生们在一起,最自豪的就是学生们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的学生听了都深以为是。
父亲一方面对学术的要求精益求精,学生的论文总是逐字逐句审阅,每到毕业季,床上桌上堆满论文,他经常看到半夜,连页码错了都要一个个改过来;另一方面,他对学生关怀备至,视同己出,让大家都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父亲在实践中感到规划必须和其他相关学科有更多互动,不拘一格拓展学科架构,对地理信息系统、经济地理等跨界学科都虚心求教,广开大门招收跨界人才,在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规划界可谓开先河的导师之一。对这些学生,父亲更是悉心培养,没有半点保留。我们的家也是大家的家,学生们在家里常常讨论问题到深夜,可是欢声笑语不断,大家都累并快乐着。他的团队不仅在学术上不断创新,更是学校里公认最有活力和最温暖的设计团队之一。
他一门心思在工作上,难免其他事情心不在焉,闹出各种笑话,比如,住旅馆开着门被顺走了相机,或者敞着背包打电话被偷个精光。建设北海分院的时候,条件很艰苦,大家需要自己买菜做饭。他的学生跟我爆料,好几个人都煮饭忘了时间把锅烧干了,不过最大的那个窟窿是父亲贡献的。记得有一张照片,在北海分院的一个周末,学生们在楼上唱卡拉OK声音太响,父亲需要打电话讨论工作,但又不想让同学们扫兴,于是自己抱着电话躲到桌子底下,捂着耳朵打电话谈工作,正好学生拍了下来,引为笑谈。
一夜白头
我大学毕业那一年,199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哥哥没有起床,安静地离开了人世。父亲失去了他的爱子,我失去了挚爱的哥哥。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坚强的父亲也忍不住恸哭不已。中年丧子之痛竟然让父亲一夜白头,曾经满头黑发的父亲,第二天就多了许多花白的头发,而且看上去苍老了很多。我忘不了那天晚上父亲几乎用恳求的语气,希望我在他们的卧室打地铺睡觉,唯恐再失去这唯一的女儿。爱他的学生们纷纷赶来安慰,并且安排父亲和母亲第二天就离开重庆,去杭州的朋友家暂住,不让他们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留下来料理了哥哥的后事。
可是三天以后,父亲就回来恢复了工作。他用工作来平复自己的伤痛,而且加倍珍惜时间。本科毕业后我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决定报考清华建筑系的研究生。父亲心里其实何曾不希望我留下,但他选择默默地支持了我。去清华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父亲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总是尽量抽时间和我见面。我们在清华一起散步的时候,父亲真诚地跟我探讨了他对“浪漫”的看法,虽然只是短短的闲聊,但给我很深的影响。父亲认为,梁思成和林徽因那种充满家国情怀的浪漫才是他欣赏的浪漫,只有儿女情长未免太局限了。不过他也感叹,时势造人,这样的浪漫很难再有。经历过时代巨变的父亲,总是鼓励我从更加开阔的角度去看人生、看世界。当我提出要出国留学,以及回国时选择不回重庆,父亲都充分的支持和理解,任我远走高飞追寻自己的梦想。我永远感谢父亲的开明和宽容。
四面碰壁居士
父亲是一个极富远见的开拓者,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城市规划学科的远大构想激励着他不断前行。父亲非常反对规划就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论调,在他看来,城市规划是实践性非常高的学科,他强调规划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他力主“产学研”三结合的工作模式并身体力行,他是城市规划学科学术带头人,也是重庆建筑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并组建了山地城镇与区域研究中心,倡导成立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建设专业委员会。
早期的规划工作都是免费的,分文不取,而且十分辛苦。父亲很崇拜徐霞客,把调研当作旅行,甘之如饴。他带领学生们走遍了云贵川的城市和乡村,取得许多山地城镇的一手资料和实践经验,并逐步形成自己对山地城市的认知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对我国山地城市应该走生态之路的信念越来越坚定,提出了“山地城市学”的构想。他很形象地跟我描述了典型的山地城市的发展模式,对比“摊大饼”的平原城市如北京,山地城市更应该考虑顺应地形的特点,比如重庆的多中心模式,他说“就像一串红苕”,沿着主要的道路,形成不同的组团,灵活布局,在空间格局上也更加丰富多样。
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内地,父亲的知音并不多。在很多地方,领导们不理解、不接受他的生态规划理念及对城市发展的远见,削平山地做平原规划,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发展比比皆是。父亲对于这些不考虑因地制宜、忽略生态环境的规划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心急如焚。他不断地参加会议、写文章、做讲座、摇旗呐喊,像一位永不言弃的战士,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有一段时间他的事业受阻,十分苦闷,他提笔写下“四面碰壁居士”贴在墙上自嘲自勉,但依然奋力前行。
随着自己的阅历增长,我越来越了解到城市规划对一个城市、地区的深远影响,越来越敬佩我的父亲。城市规划需要前瞻的想象力、对社会的深刻认知、以及对城市发展的远见卓识。父亲在世的时候热切地渴望团结更多人跟他一起探索山地城市规划的生态之路,他对学科框架的设想充分显示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胸怀。10年过去,他的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同行认可接受,“生态”从大家陌生的学术词汇变成今天家喻户晓的常识概念,他的生态规划理念也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若是父亲能够多活10年,看到有这么多同路人,一定能感到“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的欣慰吧!
父亲劳碌和奋斗的一生正好赶上共和国从一穷二白起步开拓城市建设的时机。他是第一本《城乡规划》统编教材最年轻的编委,也是最早深入西藏、广西、海南等地的规划师之一,并且大学刚毕业就参加重庆市的总体规划。半个世纪热情饱满的工作,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50年教书育人,换来了桃李满天下。父亲说他自己是70岁的年纪,30岁的心。他还有很多的构想有待实践,很多的愿望需要努力呢!
2004年春天,父亲和母亲赴美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路过旧金山,在渔人码头附近的草坪上小憩,看海天一色的港湾美景,父亲愉快地给我打电话:“50年都没有这样放松的休息过了!”我知道,这是他的真心话。没想到仅仅两年后,2006年的秋天,劳累过度的父亲就仓促的离开了我们。人生聚散终有时,我宁可相信,父亲的离世是蒙苍天怜惜,召他回去安息。
感谢父亲,在我成长的重要阶段,为我树立了一个善良、正直、开明、乐观的榜样;感谢父亲,他在专业上的开拓、实践及洞见,不断地鼓舞我、引领我前行;感谢父亲,因为他热爱事业、热爱生活、热爱家庭。
爱因斯坦说过,爱是一切的答案(Love is the answer)。
谨以此文献给我挚爱的父亲。
(编辑:苏小亨)
In Memory of My Beloved Father Huang Guangyu
HUANG Jian
2016-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