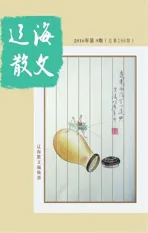瑞金:摇篮的咏叹
2016-02-23江洋
江 洋
瑞金:摇篮的咏叹
江 洋

江洋
解放军退役大校。现为辽宁省作协会员、辽宁省散文学会秘书长,《辽海散文》编委。出版过个人文集《盗火集》《净水微澜》《盗火者说》。
瑞金,叶坪,远远地大字写着: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在“一苏大”会址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我和存青轮流站上去,照相,挥手,揣想当年的样子,掏出一纸“文件”来宣读。那是共和国第一个工农政权诞生的地方。我想,当时的场景一定很热烈,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工农代表,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冒着被杀头抄斩的危险,来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的庆典,行使了人民的权利,大家鼓掌,欢呼,热泪眶涌……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是多少工农大众期盼了多少年多少辈的时刻。
这个政权叫中华苏维埃,而“苏维埃”则是取自俄语“会议”的意思。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那时,许多事情都要听从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一个叫“共产国际”的遥控领导,他们是马列主义的“正宗”,而且资助了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活动经费,因此中国共产党就不断有人在那里驻在,近耳聆听和传达最新指示。于是,共产国际那些抽象的、概念的甚至是过时的指示,就时断时续地传递到正在与敌人捉对厮杀的中国工农红军那里。那时似乎就体现了党的绝对领导,你听也得听,不听就得撤职、开除。而那些指示,有时对路了,起到了较好作用;有时跑偏了,使中国革命蒙受巨大损失。
成立中华苏维埃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指示。1930年8月,那些远在欧洲的革命领袖们,吃着面包,看着报纸,心里却惦记着中国的革命。不知凭什么心血来潮,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该有一个共和国了,于是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苏维埃的“会议领导”模式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此时的毛泽东、朱德们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刚刚在赣西南站住脚跟,准备全力迎击蒋介石的第一次大围剿,而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立即积极响应,这个当时只有31岁的中共领导人、激进领袖头脑发热起来,他马上指示红军主力部队攻打长沙,期望一个早上就在那里成立中华苏维埃。结果当然是以卵击石,年轻的红军还远远不到那个实力,损失惨重。接着,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也对成立中华苏维埃之事十分上心,多次指派毛泽东和朱德抓紧筹办。
历史有时无比地简洁和单纯,只是我们后来人为地涂抹上各种油彩,使它失去本色。
这个苏维埃政权的到来是否如一个早产儿,从来无人断言。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为了筹建这个苏维埃,我们的红军将士做出了无数牺牲,我们的当地群众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它的存活竟不到三年!
有人说,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也有人说,这是一次伟大的预演。
拂去那些油彩,我们想问:尝试什么?尝试着当国家领导人的滋味?预演什么?预演怎样管理一个在几十年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听话的,中共领导人也是听话的。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尽管四次推迟开会时间,又反复斟酌开会地点,最后终于选择了瑞金这样一个相对敌人较远、便于疏散会议人员、经济基础较好、地方党组织比较得力(时任县委书记是能力超强的邓小平)的地方,时间则定在1931年11月7日——与早年的十月革命相对应。会场是在距瑞金城十几里外的叶坪村,一个叫谢家祠堂的地方。据说,为了迷惑敌人,毛泽东还特意派人在几十里外的长汀布置了一个假会场,结果那天真的引来国民党飞机的轰炸。
会场并不大,房屋主要是木制结构,周围就是几间简陋的办公室。主席台也很简陋,用木板搭成的,上下的两个小梯子也是木头做成的。主席台讲桌是一块长条木板,很难想象,这里能够成立一个共和国,一幢房子、一座院子甚至一个房间就是共和国的一个部,好像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
开会是共产党人的强项。这次会议开得不无隆重,最后,本来不是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执行主席,这说明了他在群众中的威望,而他刚刚在3天前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遭到批判,被免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我想,毛泽东是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下“登基”的,尽管从此名满天下的“毛主席”之称取代了以前的“毛委员”“毛党代表”“毛总政委”甚至“毛师长”的称谓,人们从不习惯到习惯,到敬仰,到虔诚,到神化。
据所有的史料,没有显示毛泽东如何得意,甚至不知道毛泽东是否讲了话,只是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群众庆祝活动,他“充满了笑容”,并且为新的政权题了词。我宁可相信,如毛泽东那样雄才大略、志存高远的政治家,不会对当时这样一个“土皇帝”怎样得意和知足。我猜他想的是党内斗争的复杂,他已经想到了几十里外虎视眈眈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只是一时忙于军阀大战,腾出手后就会卷土重来。
虽然红色根据地已经有了21个县、5万多平方公里的地盘,有了250万的人口和近7万人的红军队伍,但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目前的一切“成果”都是变数,只要敌人重兵一来就得重新洗牌,共产党还没有资格说在哪里安家。
可颇有勇气和激情的共产党人还是热热闹闹地过起了自己的“共和国”日子,充分展示着自己的创新才能和管理能力,好像已经准备好花大血本完成这次“伟大”的排练。他们把瑞金改名为“瑞京”,与曾经有皇帝坐殿的北京、南京平起平坐;他们组成了几十个委员会,上百个政府部门,高效率地发布各种文件规定——短短三年中,召开常务会49次,发布法律条文上百个,组织各种活动不计其数。一切一切都是按照管理一个国家进行的,直到小小的叶坪已经实在盛不下这个政府了,才在一年半后整体搬迁,将“共和国”迁到了瑞金西边的沙洲坝,那个小学课本上讲过的毛主席曾经为当地百姓挖井的地方。各个政府部门全盘复制,又是一个建筑群,甚至比先前更排场体面。而毛泽东只做了不到三年的“一把手”,随即就被排挤和架空,除了留下一个“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感谢毛主席”的美誉,只能四处调研,甚至后来“无公可办”,直到长征出发。
80多年后,我和存青来此参观,感受这里的辉煌与壮阔。作为共和国的后来人,作为从小受着党的红史教育成长的人,我对共产党和共和国是无比虔诚和崇敬的。这里留下了大量的红色建筑群,管理得如同花园一般,每天勤快的工人们,大概都和我一样怀着崇敬和虔诚去尽心工作,不断有来自各地的游人到这里参观膜拜。这是瑞金人的骄傲,是80多年前用生命、鲜血,用自己家里仅存的谷米、腊肉,用自己手扎的灯笼,用自己嘹亮的山歌舞蹈,用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换来的骄傲。
瑞金,取自“以金为瑞”之意,一个吉祥富有的名字,可在那个年代里却充满了战火血泪。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短暂的共和国在成立了不到三年之后,就不得不带着自己沉重的政府,加入转移和突围的行列。一场演出结束了!可这庞大的剧团却不甘心丢下所有道具,他们像蠕虫一样移动,在由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形成的“甬道式”保护中,政府机关的人只听到枪响,却见不到敌人,他们心疼共和国的公章、文件、账本,心疼辛辛苦苦攒起来的办公“家底”,他们雇挑夫,借士兵,甚至自己人拉肩扛,抬着这个年轻而臃肿的 “共和国”艰难前行。这导致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付出了重大伤亡,本来预计一天的掩护延至三天以上,一场湘江战役,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以至在前线指挥的军团长彭德怀大声怒斥:“这是什么行军突围,这简直就是搬家!”
试想,当初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国家机构,何以至此?
今日瑞金的两处“红色建筑群”仍然十分壮观,景区的建设和管理绝对达到一流水准,花园式、景观式,很容易让人误会当年的中央机关就是在花团锦簇的环境中办公。
两处的景观都按照原来的机构重新修建和复制了纪念馆,而且多与现在的中央机关相对应,称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个展馆除了介绍当年的红色历史外,还有这个机构的后来沿革,直到现在的工作成就,最后都不会忘记把现在的领导人也摆出来,让他们与七八十年前的先辈排列在一起。
我去过一些祖祠,那里只供奉 “列祖列宗”,还很少见到将现在活着的、差了许多辈的后人放在一起“供奉”。大概是我们现在的领导急于证明自己地位的重要,或者功绩的类比?
反正我知道,毛泽东后来再也没有回到过瑞金,他“重上”过两次井冈山,却在那里驻足不前,大概不是一个偶然。是对当年“登基称帝”的不屑,还是对摇篮往事的纠结?他那纵横恣意的诗词中,写过会昌,写过大柏地,写过不周山,写过龙岩、上杭、宁化、清流、归化,写过武夷山、赣水那边,却没有写过瑞金。应当不是疏忽,不是淡忘,也许是缺少激情?所有历史的未知和空白,只能任人猜测、评说和咏叹。
在那个“……从这里走来”的大横幅下,我五味杂陈。
责任编辑 潘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