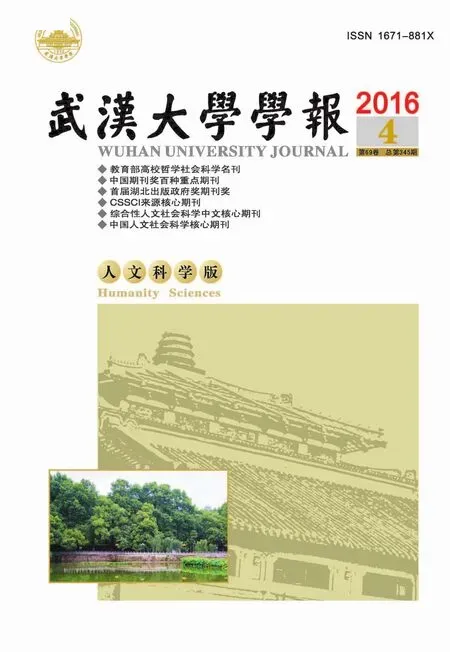涵义、指称与分析性
——科恩对卡茨新内涵主义的反驳为什么是错的
2016-02-21苏德超
苏德超
涵义、指称与分析性
——科恩对卡茨新内涵主义的反驳为什么是错的
苏德超
摘要:在《分析性和卡茨新内涵主义》一文中,科恩反驳了卡茨的“涵义调节指称”论题。他认为,卡茨关于涵义不能决定类型指称和外延指称的论证,以及卡茨关于分析句是弱必然真的论述,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科恩的反驳并不成功。我们有理由选择卡茨新内涵主义而不是传统内涵主义。
关键词:卡茨; 科恩; 分析性; 内涵主义; 弗雷格论题
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指以弗雷格在涵义、指称和分析性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理论。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6.该著是卡茨一系列思考的结晶。在此之前,精简而全面的论述参见J.J.Katz.“The New Intensionalism”,inMind,New Series,1992,Vol.101,pp.689~719。是20世纪语言哲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在弗雷格看来,表达式拥有涵义和指称,这两者并不相同。但是,由于涵义被理解为指称的决定者,因此,涵义和基于涵义得到理解的分析性,就有被指称化和外延化的危险。卡茨认为,作为指称概念的涵义和分析性,构成了弗雷格式内涵主义的关键。这两个概念“为20世纪语言哲学和语义学制定了议程”*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3.,潜在地制约着20世纪语言哲学的大多数讨论,并造成两极分化:持内涵主义语义学的哲学家,如弗雷格和卡尔纳普,主张涵义在表达式与对象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持外延主义语义学的哲学家,如罗素和蒯因,特别是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否认涵义有此功能;同时,分析性也受到质疑。
卡茨*参见J.J.Katz.“The New Intensionalism”;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卡茨:《意义的形而上学》,苏德超、张离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原版J.J.Katz.TheMetaphysicsofMeaning.Boston:MIT Press,1990),尤其是其中的第二章。相信,这一切都源于“涵义决定指称”这个著名的弗雷格论题。他提议重新阐释涵义,把涵义与指称的决定(determine)关系弱化为调节(mediate)关系,以回击内涵主义面临的挑战,并得到一个薄版本的分析性。卡茨新内涵主义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科恩*参见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in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icalResearch,2000,LXI(1).却针锋相对,认为卡茨的提议行不通:首先,卡茨的核心论题并不成立,因为涵义的确决定着表达式的指称;纵有未决情形,也没有挑战弗雷格式内涵主义。其次,卡茨新内涵主义不能解决自然种类词项的指称难题。第三,卡茨新内涵主义会造成分析句为假,导致分析性毫无用处。
从文献上看,科恩的反驳对卡茨新内涵主义似乎具有决定意义。在他之后,几乎不再有系统讨论卡茨新内涵主义的论著出现。在卡茨新内涵主义的集大成之作《涵义、指称和哲学》(即Katz2004)出版时,也只出现过一些零星短篇书评。颇为有趣的是,在这部遗作
里,科恩的反驳论文并没有出现在参考文献中*这可能跟卡茨生命最后阶段身体的糟糕状况相关。在这部遗作里,卡茨说:他要特别感谢David Pitt和Amour-Garb,因为,“由于健康原因,我已经没办法凭一己之力完成它了”(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XIII)。。
本文试图捍卫卡茨的核心观点,并论述科恩的反驳并不成功。在第一部分,我会说明,卡茨视角下旧内涵主义的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卡茨新内涵主义为何能消除这些问题。在第二部分,我将论述,科恩未能证明,弗雷格式的涵义决定了表达式类型和例子的指称。在第三部分,我会为科恩针对卡茨提出的自然种类词项指称难题给出一个解决。在第四部分,我将运用卡茨的理论来处理分析性难题。如果这一切都正确,那么,在科恩二难中,我们就有理由放弃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转而选择卡茨新内涵主义。
一、 为什么需要卡茨新内涵主义
在处理同一陈述等难题时,弗雷格区分了涵义与指称,并在实质上将这两者的关系刻画为:
(E)一个词项的所指就是落入其涵义之下的东西*参见G.Frege.Translationsfrom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GottlobFrege.Peter Geach & Max Black(eds.).Oxford:Basil Blackwell,1952,p.57。。
不能落入涵义之下,就无法成为词项的所指。因此,一个词项,或者说一个表达式,它的涵义就是它指称的决定者。此即“涵义决定指称”论题。后来卡尔纳普进一步把涵义定义成从可能世界到其中的外延的一个函数*参见Rudolf Carnap.MeaningandNecessity,second e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239,242。。这样内涵就被外延界定。同时,由于逻辑学家惯用逻辑语言改写自然语言表达式,涵义间的关系就顺理成章地演变为逻辑关系。两方面一结合,自然语言语义学就只能以“逻辑/指称”为基础了。语言哲学研究越来越依赖逻辑技术和外延解释,源头在此。
然而,卡茨指出,弗雷格式的、以指称决定者自居的涵义概念存在着以下三个困难*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p.20~32。。
一是约束太强,会排除一些真正的外延。比如,“汉口”的涵义是“汉江汇入长江的入江口”。要是汉江改道,同时汉口这个城市并没有迁移,那么,根据弗雷格论题,“汉口”就不再指称汉口这个城市。这违背了语言事实。维特根斯坦的摩西论证*参见L.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trans.G.E.M.Anscombe.Oxford:Basil Blackwell,1953,第79~81节。、普特南的机器猫论证*参见H.Putnam.Mind,Language,andReality:PhilosophicalPapers,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p.143~145,243~244。和克里普克的“蓝色金子”论证*参见Saul A.Kripke.NamingandNecess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18。等,同属这一类问题。
二是约束太弱,造成涵义的不确定。不同的涵义可以决定相同的指称,如,以下涵义都能确定地指向数2:(1)偶素数,(2)1的后继,(3)17减去15的差……然而,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者无法指出哪个涵义是正确的。在他们看来,这些涵义的不同既不相干也不重要,他们需要的是外延等值。或者,对这一等值加上模态解释,像卡尔纳普*参见Rudolf Carnap.MeaningandNecessity,pp.23~30。所强调的,内涵同一,当且仅当外延必然同一。就算这样,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者也处理不了以下难题:一些外延必然为空的表达式,像“圆的方”、“最大的数”,其涵义并不相同,而根据弗雷格式内涵主义,它们的涵义相同。蒯因翻译不确定性论证*参见W.V.Quine.WordandObject,Massachusetts:MIT Press,1960,第28页起。,起因就是外延等值说:不同的翻译在外延上等值,所以,我们无从选出正确的那一个。
三是约束错误,导致自然语言句子的不可理解性。理由如下:弗雷格式内涵主义者会在分析一个表达式的涵义时,使用逻辑技术。对他们来说,P→(P∨Q),是有效的推理式,因此,从任何一个句子P,都可以分析出它的涵义包含(P∨Q);以此类推,任何一个句子的涵义,都将包括所有其他句子的涵义。因此为了理解一个句子,哪怕是最简单的句子,我们也不得不去理解这个句子所在语言中的所有句子。然而我们不可能理解一门语言中的所有句子。这样,我们将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句子*此处对卡茨的论述有实质修正。卡茨的论证基于以下主张:在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之下,自然语言所有的句子会同义,并有同一个指称,每个句子都是真的。但他关于这些结论的论证并不正确。事实上,他的论证,要依赖于双条件句P↔(P∨Q)而不是单条件句P→(P∨Q),但双条件句明显为假。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p.30~32。。
卡茨诊断,造成以上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弗雷格式内涵主义者将涵义指称化,且将涵义关系逻辑关系化。要消除这些问题,他提议,退回到语言学内部,涵义要去指称化,涵义关系要去逻辑化,他把这样的涵义理论叫做“自治的涵义理论”(ATS)。在这一理论下涵义被界定为:
(D)涵义是句子语法结构的一个方面,该方面决定了句子的涵义性质与关系*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17;参见J.J.Katz.TheMetaphysicsofMeaning,pp.64~66;J.J.Katz.“Analyticity,Necessity,and the Epistemology of Semantics”,in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icalResearch,1997,57(1),p.8。。
涵义性质和关系,指表达式和表达式之间在涵义方面具有的性质和关系,比如,一个表达式有意义、无意义、是否有歧义、是否是冗余的;两个表达式是否同义,是否反义等。
跟弗雷格式的涵义理论一样,在ATS中,涵义依然是决定者;但又跟弗雷格式的涵义理论不同,在ATS中,涵义不决定语言之外的指称,只决定语言之中的涵义性质和关系。自治的涵义理论之所以能自治,是因为,“其理论词汇不包含任何来自指称理论的概念(也不包含来自处理语言与其论域的联系的任何其他理论)”*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17.;所有对涵义性质与关系的解释,只涉及涵义的概念和涵义事实上所具有的部分学结构(mereological structure)。这一自治具有重要意义:在语义外在论者想要摧毁意义时,它让“意义理论跟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中的理论处于同等地位,并因此延续了意义理论的生命”*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20.。
在自治的涵义理论之下,弗雷格式的涵义概念所遇到的三个困难自然消失。涵义不决定指称,所以,反事实条件下的指称问题不再出现。同时,一个表达式的涵义是什么,不再取决于定义和逻辑推理,而只取决于语言内部这个表达式事实上具有的部分学结构,这可以通过语言学调查等经验方法获得。这时,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句子的涵义包含了所有句子涵义的情况,因此,第三个困难也没有了。至于第二个困难,以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为例。“gavagai”的准确翻译是什么:“兔子”、“兔子的阶段”还是“兔子未分离的部分”?在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之下,田野语言学家只能求助于外延,而任何外延场合都让以上选项同时为真,于是翻译不确定性出现。在自治的涵义理论中,涵义是涵义性质与关系的决定者,我们可以通过引入涵义性质与关系来排除这一不确定。比如,田野语言学家可以问受调查者:“gavagai”有没有跟“兔子”、“兔子的阶段”、“兔子未分离的部分”中哪一个同义?如果没有,它跟某个表达式之间是否具有像“手”跟“手指”的关系?……当然,这要求双语者出现。蒯因反对引入双语者,甚至认为这种引入也无济于事,因为双语者并非总能做出“唯一正确的句子关联”*W.V.Quine.WordandObject,p.74.。卡茨相信,“排除内涵证据”是不确定性的一个根源*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29.,但这一排除是学派性的偏见。双语者能否做出正确的句子关联,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蒯因的论证依赖于可能做不出。卡茨并不否认这一可能性,但他强调,“蒯因所想要的可能性其否定也是可能的”*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29.。从现实中存在着大量准确翻译这个事实来看,兼有语言学家身份的卡茨,比兼有逻辑学家身份的蒯因,可能更正确。
二、 涵义与指称的新关系
卡茨为涵义与指称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他借用皮尔士的术语,将表达式划分成表达式类型(type)和表达式例子(token):前者指一门语言中的一个表达式,后者指一个表达式的一种具体使用*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205;又J.J.Katz.TheMetaphysicsofMeaning,p.39;J.J.Katz.“Analyticity,Necessity,and the Epistemology of Semantics”,p.9。。例如,本段首句出现了两个“的”字,作为语言类型,它们是相同的;作为语言例子,它们是不同的。这一划分暗示了语言实在论立场:在语言类型范围中,不存在语境因素。以此为基础,卡茨提出:
(MED)涵义调节指称:要阐明表达式类型或者表达式例子指称的条件,涵义并不充分,但是,它是必要的*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47;又J.J.Katz.“Analyticity,Necessity,and the Epistemology of Semantics”,p.9。。
可见,卡茨既区别于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他们认为涵义充分决定指称),也区别于外延主义(他们认为,对于决定指称,涵义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然而,科恩反驳了这一说法。他认为,涵义的确充分地决定了指称;就算不充分,也不构成对弗雷格内涵主义的挑战;并且,如果涵义不能决定指称,那就更谈不上调节,它将不再必要。关于必要性的反驳,我们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讨论。本部分只讨论对不充分性的反驳。
卡茨提出MED的动机,是要在外延主义的攻击下保留内涵主义。跟普特南(1975)和克里普克(1980)一样,卡茨注意到,如果涵义存在于头脑之中,并且涵义决定指称(弗雷格论题),那么,头脑之中的某个东西就会决定头脑之外的指称。但普特南这些外延主义者的论证表明,指称的决定者不可能存在于头脑之中。因此,要保留内涵主义,就只能否定弗雷格论题。
具体来说,就表达式类型指称而言*参见J.J.Katz.“Analyticity,Necessity,and the Epistemology of Semantics”,pp.10~11;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p.52~55。,卡茨认为,我们难以单凭涵义给出包含了关系形容词的表达式类型指称。如,“x是一头很大的动物”与“x不是一头很大的象”,这两个句子可以同真。如果“大”有一个类型指称的话,那么,x就既在这个类型中,又在这个类型外。就表达式例子的指称而言*参见J.J.Katz.“Analyticity,Necessity,and the Epistemology of Semantics”,p.9;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51~52。,卡茨提出,鉴于语言的非字面使用,尤其是唐奈兰提到的错误描述下的指称问题*参见K.Donnellan.“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inThePhilosophicalReview,1966,(75),pp.281~304。,比如,“角落里的那个喝香槟的男子”,可以指称一位喝水的女子,表达式例子的指称无法单由涵义来加以确定。
关于例子指称,科恩认为,相应的决定关系存在,只要我们“在语言例子的指称跟使用这个例子的说话者希望去讨论的那个个体之间做出概念区分”*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120.。并且,他注意到,“除非我们把一个表达式的例子指称等同于这个例子的说话者希望去讨论的那个个体,否则,卡茨就不会威胁到‘涵义决定指称’这个弗雷格论题”*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121.。为什么例子所指不同于说话者所指呢?科恩说,这源于克里普克对语义所指与说话者所指所做的区分*克里普克的区分,参见Saul A.Kripke .“Speaker’s Reference and Semantic Reference”,in P.A.French,T.E.Uehling & H.K.Wettstein (eds.).ContemporaryPerspectivesinthePhilosophyofLangua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pp.6~27.Reprinted inPhilosophicalTroubles,CollectedPapers,Volume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99~124。。他相信,对此“克里普克(1977)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理由”*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121.。
这极其费解。克里普克(1977)针对的不是卡茨,而是唐奈兰(1966)。唐奈兰为了处理错误描述下摹状词的指称问题,提出摹状词有两种使用:一种是属性的使用,如,“角落里的那个喝着香槟的男子”,指称角落里那个喝着香槟的男子;一种是指称的使用,“角落里的那个喝着香槟的男子”,指称一位喝水的女子。后一种使用,在唐奈兰看来,类似于专名的使用。可是,克里普克认为,唐奈兰对这类现象的处理,既“不充分”,又显得“多余”:不充分,是因为专名也会出现错误使用的情况;多余,是因为通过区分说话者所指和语义所指,就可以处理所有类似的现象*Saul A.Kripke.“Speaker’s Reference and Semantic Reference”,p.117.。语义所指,属于语义学范畴,是语言的约定;而说话者所指,则属于语用学范畴,它由语言约定和语境因素共同决定*参见Saul A.Kripke.“Speaker’s Reference and Semantic Reference”,p.111。。唐奈兰的属性使用,得到的是语义所指;指称性使用,得到的是说话者所指。
不难看出,语义所指与说话者所指的区分,并不对应于例子所指与说话者所指的区分。由于语义所指是语言内的约定,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它对应于卡茨的类型所指;例子所指由语言与语境共同决定,因此与卡茨的例子所指更接近。卡茨认为,一个表达式例子的指称由其所属类型的涵义和其例子的涵义共同决定*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51;J.J.Katz.TheMetaphysicsofMeaning,pp.144~148。。这就暗示表达式例子的涵义可以跟表达式类型的涵义有所不同:因为存在着非字面使用和虚假描述。当类型涵义与例子涵义一致时,表达式的这次使用是字面的,如果字面使用且不存在虚假描述,那么,它的所指就是其类型所指。事实上,无论卡茨还是克里普克,都愿意把自己的工作基础追溯到格赖斯*参见J.J.Katz.TheMetaphysicsofMeaning,pp.147~148;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52;Saul A.Kripke.“Speaker’s Reference and Semantic Reference”,p.109。。
在这种理解下,我们就不能对例子所指与说话者所指做出有效的、有利于科恩的区分。因此,科恩对涵义不能决定例子指称的反驳,并不成功。
下面我们来检查科恩对涵义不能决定类型指称的反驳。科恩的要点有二:第一,索引词与指示词没有类型所指,这是弗雷格主义者会承认的;第二,对含有关系形容词的表达式的指称,弗雷格主义者可以给出一个很好的处理*参见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p.122~124。。
关于第一点,科恩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弗雷格主义者会捍卫这个论题:每个表达式的涵义都决定了它的类型指称”*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122.。这也许是正确的,甚至卡茨也承认这一点*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205。。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理论中划出一条边界:在这边的涵义可以决定指称,在那边的涵义无法决定指称。同时,我们还得保证,这样的边界并非任意武断。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者愿意承认,指示词和索引词的涵义无法决定它们的类型指称,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类型指称,只有例子指称。但这一承认,并不是来自理论的自觉确认,而是来自对理论之外障碍的让步。
关于第二点,科恩提议,弗雷格主义者也许可以“把关系形容词语义学化归成类-指示词(demonstrative-like)语义学。”*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122.在指示词语义学未得到很好刻画前,这一说法是在回避问题。当然,这一回避可以采用很技术的方式,就像科恩所举的例子,“大”的语义可以这样界定:Val(〈x,d〉,“大”),当且仅当,x跟d一样大*参见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p.123~124。。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选一个东西作为“大”的样本,凡是跟这个样本一样大的,我们就把它叫做大。有了这样一个人为的绝对标准,就不会出现一个东西既大又小的情况。然而,科恩似乎没有考虑到恶性后退问题,用跟某物“一样大”来界定“大”,用什么来界定“一样大”呢,又用什么来界定对“一样大”的界定呢?为了终止恶性后退,就不得不离开内涵主义立场,转而将这一系列概念完全外延化、指示词化:什么叫大,这(大的样本)就叫大;什么叫一样大,这(跟大的样本一样大)就叫一样大。不难发现,如果把指示的内容代入,这里头已经有循环存在;并且,由于关系词完全指示词化,我们就无法真正指出两个一样大的东西来。因为一个东西的大,跟另一个东西的大,不是同一个“这”。退一步说,就算科恩的提议成功了,也只是表明,有些表达式的类型外延,无法由它的涵义决定。这个结论,正好是卡茨需要的,尽管弗雷格内涵主义也有同样的结论。但这个结论,于卡茨新内涵主义而言,是一个例证;于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而言,却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例外。这种例子很多,“自然语言有一个关于涵义的巨大开放集,这些涵义并不是弗雷格式的涵义”,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卡茨式的结论:“对自然语言而言,弗雷格式的涵义概念并不正确。”*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50.
三、 卡茨新内涵主义与自然种类词项的指称
在上一节,我们论述了,科恩未能成功驳倒涵义在指称决定上的不充分性。在本节,我们将论证,在反驳涵义对指称决定的必要性上,科恩也失败了。
对内涵主义而言,自然种类词项是有名的麻烦制造者。外延主义者就是用它们来驳斥内涵主义的。例如,普特南说,为了得到一个像“铝”这样的自然种类词项的外延,我们所需要的涵义不只是“轻金属”、“银色”、“可延展”、“不生锈”……因为这些涵义“也适用于钼”*H.Putnam.“Is Semantics Possible?”,inMetaphilosophy,1970,1(3),p.150.参见H.Putnam.Mind,Language,andReality:PhilosophicalPapers,Vol.2a,pp.215~271;H.Putnam.Mind,Language,andReality:PhilosophicalPapers,Vol.2b,pp.196~214。。为了挑选出正确的外延,我们必须知道自然种类词项所指成员的本质特征,而这些特征,唯有靠经验科学才能得到。因此,从根本上说,自然种类词项的语义知识就是关于它们的所指物的经验知识。这些经验知识,构成自然种类词项的实在定义。
卡茨反击以上论证的要点如下:一方面作出让步以保守内涵主义:自治的涵义不决定指称,所以,语义知识不必是自然科学所发现的经验知识;另一方面坚持阵地,一个自然种类词项的类型指称,由它的涵义(名义定义)和它的实在定义共同决定;涵义依然是必要的*参见J.J.Katz.“Analyticity,Necessity,and the Epistemology of Semantics”,pp.16~20;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63,pp.128~137。。
科恩论证说*参见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p.128~130。,在确定自然种类词项的外延方面,卡茨式的涵义毫无必要,理由有两个:
一个是,卡茨式的涵义在确定自然种类词项的指称时毫无用处。设落入某个自然种类词项T的涵义之下的事物集和落入到它的实在定义之下的事物集分别为S和R,依卡茨上述观点,T的外延将是S∩R;并且,S≠R,否则,词项T的所指将完全由涵义决定,这非卡茨式的自治涵义的应有之义。而T的外延S∩R,要么等于R,要么小于R。如果S∩R小于R,表明科学发现的实在定义过宽,真正的实在定义并没有找到。因此,只能是S∩R=R。如此,则词项T的外延完全由它的实在定义决定,它的涵义于此毫无用处。
另一个是,卡茨式的涵义在确定自然种类词项的指称时完全错误。这种自治于一门语言内部的涵义,完全依靠该门语言的熟练说话者的语言直觉,这种直觉并不总跟科学发现的、外在于语言的实在定义相一致:语言知识跟科学知识是两回事。如果词项T的涵义跟自然科学发现的实在定义相冲突,那么,S∩R=φ。这时,为了保证词项T有一个所指,我们必须将卡茨式涵义删除。科恩举例说,“鲸吃浮游生物”,按卡茨式涵义,鲸会是一种鱼。但是,没有任何鱼是鲸,因此,“鲸吃浮游生物”,就不是关于真实存在的一种大型海洋生物的描述。这当然很荒唐。为了避免这一局面,我们唯有删除卡茨式的涵义。
然而,科恩的反驳并不成功。自然种类词项的卡茨式涵义与其实在定义的关系有两种:它们一致或者不一致。科恩所谓的毫无用处发生在两者一致时,而他所谓的完全错误,发生在两者不一致时。跟科恩的看法不同,这两种情况的存在,不是卡茨新内涵主义的反例。
在第一种情况下,两者一致,这就表明,卡茨式涵义的内容是实在定义的一部分。如果实在定义决定了自然种类词项的指称,那么,卡茨式涵义作为它的一部分,对于这一决定就是必要的。的确,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定义做了所有的工作”*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128.,但是,这工作里,有卡茨式涵义的贡献。这一贡献既有实质的方面,因为卡茨式涵义就是实在定义的一部分;也有认识论的方面,因为,科学家的研究必须部分地求助于自然种类词项的卡茨式涵义,即科学家得到研究结果前,只能在卡茨式涵义上使用自然种类词项进行交流。
在第二种情况下,两者不一致。这要复杂一些。仍然讨论科恩的例子,“鲸吃浮游生物”。长期以来,“鱼”被当成是卡茨式涵义的一部分。后来科学发现,“鲸”的实在定义不包括鱼,也就是说,它的卡茨式涵义与实在定义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卡茨承认,“鲸”的所指在相应的涵义上为空*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p.63~64。。但他建议,我们应当把问题归约成类似唐奈兰所指出的“虚假描述”下的指称问题*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65。。这时,我们面临着选择,要么承认所指为空,要么让涵义发生改变。科恩正确地看到了承认所指为空是荒唐的;也看到了,如果让涵义发生改变,其改变的方向就可以是实在定义,而实在定义在头脑之外,这就相当于让卡茨承认,涵义在头脑之外——作为内涵主义者的卡茨显然难以认可。可惜的是,科恩只看到了涵义在实在定义面前的退步,却没有考虑到,存在着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里,涵义在实在定义中得到了保留。比如,“翡翠”就是这样。科学发现,它并不指称一类物质,而是两类:硬玉和软玉,这两类物质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同*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65。。在这样的例子里,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并没有因新的科学发现而去改变词项的涵义,而是在旧的涵义下,进行了新的区分。也就是说,当卡茨式涵义跟实在定义冲突时,放弃卡茨式涵义的做法,并非必然,而要取决于现实世界的某些偶然特征和科学理论的简洁性要求。甚至我们可以反事实地设想,假如人类并不是哺乳类,地球上所有的哺乳动物跟鱼一样生活在水中,那么,科学家就很可能对“鱼”作“翡翠”式的处理:保留“鱼”的早先涵义,而不是去掉它,然后在这一涵义之下,做出更精细的分类:鱼包括哺乳类和非哺乳类。这一反事实的做法在指称功能上跟通行做法等效。
退一步说,就算发生了科恩指出的涵义被修改的情况,卡茨的新内涵主义还是有可取之处。涵义被修改,无非是义项的增减。如果增加,按照卡茨的处理,这没有降低涵义的重要性,“反倒是加强了它”*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65.。至于减少,卡茨似乎没有讨论,但我们还是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离开涵义,我们根本不能独立地解释语言中的涵义性质与关系,比如,分析句为什么具有分析性。也许涵义是错误的,但一旦发现语言中存在着这样的错误涵义,我们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语言共同体中的人,会把错句子看成是分析为真:比如,鲸是鱼。并且,卡茨式的涵义还可以解释,在这种共同的错误之下,同一个语言共同体中的说话者为什么可以成功地交流。依照科恩的反驳,这些交流总是错误的,不可能成功。
当然,涵义的改变会跟外在的实在定义相关。但这种相关,并没有摧毁卡茨的内涵主义立场。卡茨新内涵主义,不同于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他并不设定一个不可变的思想世界,他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自然语言的事实出发。词项的指称会发生改变,这是自然语言的一个事实。如果科恩的反驳成立,我们甚至可以说,当把鱼当成是“鲸”涵义的一部分时,并不是内涵主义的,而是外延主义的。以此类推,任何词项的涵义性质与关系都不可能在语言内部单独得到确立。从根本上说,这是对的。卡茨新内涵主义,其研究前提是一门语言的既成事实:熟练说话者对于该门语言中事实上所拥有的直觉。至于这些直觉如何形成,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中。虽然他希望语义研究独立于逻辑和外延,但其独立程度也仅限于此。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涵义是决定所指的必要条件,还有别的理由。比如*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52。,表达式的使用如果是非字面的,那么,它的例子所指就不是类型所指。这个时候,要确定它的所指,其涵义依然是必要的,它的涵义是我们理解其语境意义和所指的条件。基于格赖斯的理论,卡茨和克里普克(1977)都同意这一点。
四、 卡茨新内涵主义与分析性
分析性概念是哲学中一个聚讼不断的焦点概念*参见梅剑华:“分析性、必然性和逻辑真理”,载于《哲学分析》,2014年第5卷第1期,这是汉语学界对分析、先天和必然等概念的关系所给出的较为全面的综述。。弗雷格区分出两种分析:“房屋中的横梁”式的分析和“种子中的植物”式的分析*参见G.Frege.TheFoundationsofArithmetic.Oxford:Basil Blackwell,1950,pp.100~101。。跟康德主张前一种分析不同*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A6/B10~A8/B13,译本第8~9页。,弗雷格主张后一种,他把分析命题刻画为可以通过逻辑规则和定义得到证明的命题*G.Frege.TheFoundationsofArithmetic,p.4.。卡尔纳普沿着弗雷格的道路前进,用意义公设替换了定义*Rudolf Carnap.MeaningandNecessity,pp.222~229.。蒯因进一步将弗雷格式的分析命题分成两类:逻辑真理,和可以通过同义替换转化成逻辑真理的命题*W.V.Quine.FromaLogicalPointofView.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22~23.。后两种刻画本质上都是将分析性看成是一种逻辑真理*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张健丰在评析蒯因同卡尔纳普在分析性上的争论时,就注意到,在某些地方,蒯因也将分析看成是内在于一个特定语言中的概念。于此参见张健丰,“超越的分析性与内在的分析性”,《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年第2期,尤第14页。如果这是真的,蒯因就非常接近卡茨的观点。。而真是一个指称概念,这就表明,他们实际上将分析性概念外延化了。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导致蒯因在分析性上持怀疑论,因为,如果逻辑真理是那些单凭涵义为真的命题,这就会威胁到逻辑的纯外延性解释。跟他们不同,卡茨要回到康德式理解,让“分析性重归‘房屋中的横梁’概念”*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 p.41.。在他看来,分析性概念,是一个部分学(mereological)概念,而非一个逻辑(logical)概念。关于分析性,他的核心直觉是:
(G)一个简单句的涵义是分析的,其充分条件是,它的涵义完全被包含在它的(某)一个词项的涵义中*J.J.Katz.“Analyticity,Necessity,and the Epistemology of Semantics”,p.12;更为精确的刻画,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44。。
例如,“猫是动物”,这个句子的涵义就被包括在“猫“这个词项的涵义中。
卡茨式的分析性概念至少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从一个句子可以逻辑推出的命题,并不算作这个句子的涵义;另一个是,分析句有可能为假。有第一个后果,就回避了本文第一部分谈到的弗雷格式的涵义概念所带来的约束错误问题:虽然P→(P∨Q),但是(P∨Q)并不是P的涵义。因此,理解P时,不必以理解(P∨Q)为前提。
科恩看到了第二个后果。他正确地指出,“要是涵义的确决定着指称”,我们就可以针对“分析句的真说点什么”*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124.。弗雷格涵义概念之下,“猫”的涵义决定了猫类,“动物”的涵义决定了动物类,“是”的涵义决定了类之间的包含关系。因此,“猫是动物”为真。但是,在卡茨的分析性概念之下,由于分析性只是语言内部的涵义之间的关系,跟所指无关,因此,我们就也无从知道,这样的句子事实上为真还是为假。并且,我们也无从知道分析句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因为句子的分析性“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世界中的性质、关系和个体”*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125.。如此一来,分析性概念就显得毫无用处。
不过,卡茨的分析性概念并非这般无用,分析性可以跟弱必然真这样的模态指称概念相关联*参见 J.J.Katz.“Analyticity,Necessity,and the Epistemology of Semantics”,p.24;更技术化的阐述参见J.J.Katz.Sense,Reference,andPhilosophy,p.60。。卡茨指出,如果一个句子p的涵义在(G)的意义上是分析的,那么,p就是弱必然真的。而分析句表达了弱必然真理,即是说,它要么是逻辑真理,要么存在着一些让它的指称词项不为空的可能世界(满足者世界),它在这些世界中都为真。
科恩在普特南机器猫论证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归谬论证*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p.131~132.,来反驳卡茨在分析性和弱必然真之间做出的关联。仍旧考察“猫是动物”这个句子。假定卡茨的关联正确,再设想:有一个世界w完全类似于我们的世界,只有一点不同:我们世界中叫“猫”的,是猫;w里叫“猫”的,是机器猫。机器猫的所有现象学性质,跟我们的猫完全相同。我们世界的语言是English,w中的语言是Shmenglish。除开“猫”的实在定义不同,这两门语言完全一样。根据卡茨的分析性定义(G),“猫是动物”在English中是分析句。由于卡茨式的涵义不包括实在定义,所以,English跟Shmenglish的不同不足以影响到这个句子的分析性。科恩就此推论:“猫是动物”这个句子“在Shmenglish中是分析句”*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131.。根据卡茨建立起来的关联,这个句子就是弱必然真的。然而,这个句子“在Shmenglish中必然为假”:因为在w里,猫不是动物而是机器。“既然它是必然假的,它就不可能弱必然(真),更谈不上它的分析性。”*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131.
科恩归谬反驳的关键是找到以下矛盾:“猫是动物”,在Shmenglish里,既是分析的,又不是分析的;既是弱必然真的,又是必然假的。然而,这两个矛盾并不存在。“猫是动物”,在English和Shmenglish中的涵义性质和关系没有变化,因此,在一个语言中是分析的,在另一个语言中也是分析的。以科恩设定的“猫”的卡茨式涵义为背景,“猫”在w中所指为空,w并非“猫是动物”这个句子的满足者世界。因此,这个句子在w中为假,无损于它的分析性,它当然可以在Shmenglish中是分析的。所以,它也就是弱必然真的,虽然它在w中为假。
科恩能找到他所谓的矛盾,还在于他窃取了论题。卡茨跟科恩关键的不同在于:讨论分析性时,卡茨从语言内部的涵义出发,而科恩则试图从语言之外的所指出发。根据卡茨的新内涵主义,“猫是动物”,在English和Shmenglish中,是分析的;因而必定存在着这个句子的满足者世界,并且这个句子在所有满足者世界中为真。至于分析句的满足者世界,是否为现实地说出这个句子的那个世界,跟这个句子的分析性毫不相干。一个句子是否具有分析性,跟说出这个句子的世界的特征无关。分析性跟弱必然真的关联,也不要求,说出这个句子的世界就是它的满足者世界。然而科恩的推论,需要这样的相关性。这就表明,他在论证中,要么偷运进了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涵义决定指称),要么偷运进了语义外在论和相应的推论(涵义由外在因素决定、同一的必然性)。由于卡茨本来就要反对这两种观点,因此,这种偷运表明他犯了“窃取论题”的错误,他的论证至多只表示,卡茨新内涵主义跟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或语义外在论不相容。
当然,要是w中的科学家经验性地发现了Shmenglish里的“猫”的实在定义,这就会影响到Shmenglish的语义,进而造成Shmenglish跟English的分化。如果Shmenglish没有接受相应实在定义,那么,w并非“猫是动物”的满足者世界。讨论同上。如果Shmenglish接受了相应实在定义,“猫是动物”的确不再是分析句。然而,这里还是不存在科恩想要的矛盾:English中的“猫”跟Shmenglish中的“猫”涵义不同,分析性作为涵义性质与关系的一种,自然也不相同。
五、 结语
关于涵义,内涵主义者有内在与外在两种理解。如果像卡茨那样作内在理解,的确会得到一个一贯的、内在的必然性概念,这是分析的和概念的必然性,但涵义就不能决定指称。相反,如果作弗雷格式的外在理解,涵义决定指称,就不会出现分析句为假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得不到一个一贯的、内在的必然性概念。科恩认为,这就是我们*不包括语义外在论者。在涵义问题上面临的“二难”*参见J.Cohen.“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or,If You Sever Sense from Reference,Analyticity is Cheap but Useless”,pp.132~133。。由于科恩认为卡茨式的、离开指称概念得到界定的涵义理论不可能成功,所以,他更愿意选择弗雷格式的内涵主义:用指称性概念来刻画涵义。
如果本文的主要论证没有错误,我们就已经论证,卡茨对涵义的新刻画可以回避弗雷格式的涵义刻画带来的三类困难;同时,他对涵义无法决定指称的论证是成功的;并且,卡茨新内涵主义在自然种类词项的指称问题和分析性问题上,并没有出现科恩提到的那些错误。虽然,卡茨新内涵主义还缺乏更为细节化的阐述,尤其是关于类型指称理论,但是,鉴于这一理论所拥有的一系列优点,比如,在刻画分析的必然性时所具有的流畅性和内在一致性,让意义理论脱离逻辑学和外延理论获得了独立等,在科恩二难中,我们有理由相信,选择卡茨新内涵主义是有前途的。
●作者地址:苏德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sudechao@whu.edu.cn。
Sense,Reference and Analyticity:Why Cohen’s Argumentations against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 is Wrong
SuDechao(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In “Analyticity and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Jonathan Cohen argues against the Katz’s thesis that sense mediates reference.He holds that Katz fails to defend the proposition that sense cannot determine type-reference and token-reference,and that analytic sentences express weakly necessary truths.This paper argues that Cohen’s rejection cannot succeed because of some mistakes.If this is right,then it is preferable to endorse Katz’s new intensionalism.
Key words:Katz; Cohen; analyticity; intensionalism; Frege’s thesis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4.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ZX058)
●责任编辑:涂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