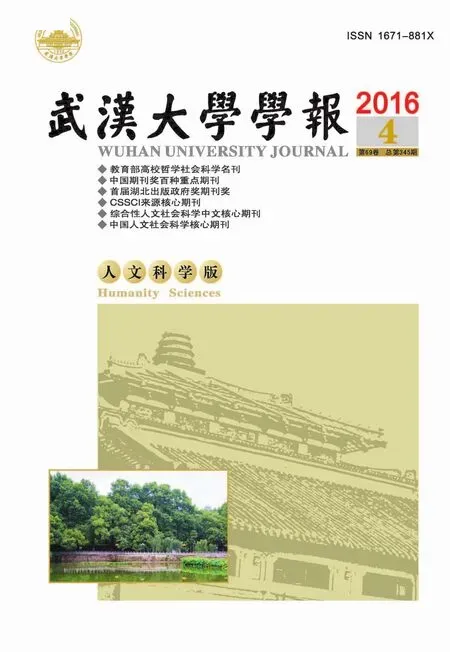存续抑或消亡
——日本乡村发展现状探析
2016-02-21俞祖成
俞祖成
存续抑或消亡
——日本乡村发展现状探析
俞祖成
摘要:伴随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日本乡村地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针对这一现象,日本学界展开激烈争论,先后形成“界限集落论”VS“乡村存续论”以及“地方消亡论”VS“田园回归论”的观点争鸣图景。尽管如此,不管是“界限集落论”和“地方消亡论”所担忧或预言的日本乡村已(将)走向衰落之现象,还是“乡村存续论”和“田园回归论”所强调的日本乡村所具备的高度强韧性及其重建(再生)可能性,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获得有关日本乡村现状的基本认知:日本乡村虽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但在各种有利因素的支撑下顽强地获得了存续并避免了衰亡。
关键词:界限集落; 乡村存续; 地方消亡; 田园回归
2016年2月24日,紫金传媒智库就日本乡村治理问题采访笔者时提出一个问题:“日本还有无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日本人过年等有无返乡情节?”对此,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方面,在日本普通市民看来,首都东京之外的地区均可被称为“田舍”(即乡下或地方之意)。这种市民潜意识的形成显然受到“首都优于地方”的传统观念以及“东京一极集中”现象的影响。作为其社会表征之一,凡是开往东京方向的交通路线均被称为“上行线”。与之相反,凡是从东京开往地方的交通路线均被称为“下行线”。另一方面,从现实情况的视点来看,尽管日本在2015年底的城市化率已达到67.7%*数据来自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推算。参见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16年度国土交通白書》,http://www.mlit.go.jp/hakusyo/mlit/h16/index.html(2016年4月20日最終アクセス)。,但仍存在至少32.3%的农村人口数量。换言之,目前日本仍存在为数不少的以农业、林业或渔业等第一产业为核心的农山渔村地区。这些乡村地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地理位置较为优越、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平地农村”以及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中山间地区”。构成这些乡村地区的基础性社区单位被称为“集落”,是指村民为了顺利开展维系生计或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共同劳动和协同作业,以家庭户为单位组建而成的自组织,可发挥农业生产协作、生活互助以及地域资源维护和管理等社会功能*小田切徳美:《農山村は消滅しない》,岩波書店2015年,第77~78頁。。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最新统计,截至2015年2月1日,日本全国共有138,256个农业集落,其中仍在发挥社会功能的农业集落约占总数的97%(134,329个)*参见日本農林水産省《2015年農林業センサス結果の概要(確定値)》(2016年3月25日公表),第130頁。。
在“城市易融入、乡村能回去”的状况下,绝大多数出身于乡村地区的日本市民仍对作为“心灵之原风景”的故乡怀有浓厚的怀旧情结(类似我们的乡愁情节)。我们不难发现,每逢元旦、黄金周以及盂兰盆节等重大节假日,日本社会都会出现不逊于我国的大规模返乡人潮,并常常导致高速路堵塞、新干线和机场等人满为患。颇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将“返乡”称为“归省”,其中,“归”是指“回家、返乡”之意,而“省”(かえりみる)的字面意思为“回头看、往回看”。有日本学者指出,这里的“省”来源于《论语·学而篇》中的“吾日三省吾身”,即意为“反省、自省”。因此,日语中的“归省”,并非指单纯的“返乡”,而是侧重强调回家看望父母,祭拜祖先并追思先人足迹,进而以此为参照反省自身,从而内含着某种“宗教性”蕴意。
限于文章篇幅,笔者无意对日本乡村得以存续的因素进行全面考察,仅就其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以期抛砖引玉,为中日乡村治理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素材。
一、 “界限集落论”VS“乡村存续论”
正如张鸣先生所指出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过程,农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张鸣:《乡村社会的下降线——漫谈中国农村的百年变迁》,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8页。更进一步说,“在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以凋敝为主调的‘农村问题’”*张玉林:《乡村环境:系统性伤害与碎片化治理》,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9页。。日本也不例外。
最早洞察到日本乡村走向凋敝的学者是大野晃。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社会学者的大野氏基于高知县乡村地区的田野调查,提出脍炙人口的“界限集落论”。该理论包括4个核心概念:(1)存续集落:未满55岁的人口占集落总人口的50%,同时集落接班人得以确保,从而使得集落生活主体得以再生产;(2)准界限集落:虽然未满55岁的人口占集落总人口的50%且目前集落接班人勉强得以确保,但由于集落接班人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得到确保,从而使得该集落沦为界限集落的预备军;(3)界限集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集落总人口的50%,同时独居(空巢)老人住户数逐渐增加,由此导致集落的共同生活功能衰落,继而陷入社会性共同生活难以维系的状态;(4)消亡村落:人口和住户消失,进而导致集落消亡*大野晃:《山村环境社会学序说》,农村渔村文化协会2009年,第22~23页。。
客观地说,界限集落论的提出,首次为日本乡村的衰落现象敲响了警钟并对日本乡村治理政策造成重大影响。然而,界限集落论充其量不过是预言性理论,并无法完全客观描述日本乡村的全部现实真相或准确预测其整体发展趋势。为此,同为社会学者的山下祐介提出严厉批判,认为界限集落论将对日本乡村的未来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并招致市民的误解。山下氏继而认为,界限集落论至少存在三大理论性缺陷:第一,过度重视老龄化率;第二,量化统计方式导致对集落多样性和属地性的忽视;第三,“老龄化率的上升→界限集落的出现→集落的消亡”这一单线式演变法则并不符合其后20多年的社会事实*山下祐介:《限界集落の真実:過疎の村は消えるか》,筑摩書房2012年,第28~32頁。。基于这种批判,山下氏立足于丰富的田野调查数据,撰写出颇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力作——《界限集落的真相:过疏化乡村真的消失了吗?》,从而形成所谓的“乡村存续论”。
二、 “地方消亡论”VS“田园回归论”
后来的事实证明,界限集落论最终确实未能实现其理论预言。然而,虽然时至今日日本乡村在种种有利因素的支撑下并未走向消亡(或衰败),但持续走向衰落却是不争的事实。加上日本岛国固有的强烈危机意识,界限集落论以另一种更加极端方式粉墨登场,即所谓的“地方消亡论”。
从2013年11月起,曾相继担任岩手县知事、总务大臣以及日本创成会议座长的增田宽也等人在日本著名杂志《中央公论》上陆续发表有关日本人口变化的系列文章(后被学界通称为“增田报告”)。翌年,增田氏将“增田报告”编著为《地方消亡》一书出版发行*増田宽也:《地方消灭》,中央公论新社2014年。,随即在日本社会掀起轩然大波。概括而言,地方消亡论的主张包括以下三点*増田宽也:《地方消灭》,第29~68页。。
第一,根据一般社团法人北海道综合研究调查会等的统计数据加以推算,2010年-2040年的30年间,20岁-39岁的女性人口锐减50%以上的市町村数量将达到896个(约占地方自治体总数的49.8%)。增田氏等人将这些地方自治体统称为“可能消亡的都市”。另外,在这些“可能消亡的都市”中,人口规模将在2040年锐减至1万人以下的地方自治体数量将达到523个(约占地方自治体总数的29.1%)。
第二,地方消亡趋势所带来的最终后果是,人口将高度集中于大都市圈,形成所谓的“人口黑洞”,从而导致日本市民只能生活于人口密度极高的社会。增田氏等人将这种社会形态称为“极点社会”。
第三,为了避免“极点社会”的形成,日本必须努力剔除有碍于出生率提升的各种因素,同时集中投入资源,建设“地方中核城市”,以此作为“防卫和反转战线”,从而有效阻止地方人口的流失。
至于“地方消亡论”的提出动机,增田氏直言不讳地解释为“鉴于日本国民和政治家们对人口减少缺乏应有的危机感*茂谷浩介·増田寛也:《誰も知らない人口減少の本当の怖さやがて東京も収縮し、日本は破綻する》,载《中央公論》2013年,128(12),第32~33頁。”。在地方消亡论的巨大冲击下,安倍政府于2014年9月新设“城镇·人口·工作创生总部”,果断出台并积极实施作为日本新国家战略的“地方创生战略”。
我们必须承认,地方消亡论采取定量方式对地方(乡村)的疲敝度进行量化和显性化,以“消亡可能性”为口号,成功唤起日本社会对于人口减少的危机感并促使国家出台地方创生战略,从而掀起地方(乡村)再造运动热潮。然而,众所周知,定量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天生缺陷,容易遮蔽大量不易量化的因素,同时容易引发地方(乡村)居民的恐慌甚至导致他们的自暴自弃。对此,那些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现场主义派”学者随即对地方消亡论展开猛烈批判。
日本著名社会学者小田切德美基于其多年的田野调查经验指出,日本乡村地区所具备的“强韧度”远超增田氏等人的想象,它们并不会轻易地走向消亡。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小田切氏举出了山口县东部A集落的实例。据其介绍,A集落目前仅有5名居民(均为老年人),并且作为接班人的后代均移居其他城市。按照地方消亡论的标准,该集落已然不可能获得存续,100%将走向消亡。然而,该集落通过组建“集落农业组织”,成功获得农林水产省面向发展条件不利地区所实施的“直接支付制度”的补助金,从而实施了一系列集落振兴活动,进而吸引他们的后代回归故里协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另外,通过设立“收获庆祝专场”,促进世代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作为这些努力的直接成效之一,那些工作退休的后代们主动回归集落,成为该集落的继承人。通过这个案例可知,那些所谓即将面临消亡的集落,仍拥有超乎寻常的存续能力*小田切徳美:《農山村は消滅しない》,第31~36頁。。
与此同时,日本各地逐渐出现与“地方消亡”和“极点社会”逆方向而行的“田园回归”(逆城市化)之潮流。小田切氏指出,目前日本城市居民对乡村地区的关心度与日俱增,我们可以将这种时代新动向称为“田园回归”。当然,田园回归并非仅指代城市居民移居乡村的行动,而是意味着市民对乡村地区的关心度逐渐获得深化的动态过程。这种“关心”包括市民对乡村地区的生活、生计、环境、景观、文化、社区以及对乡村居民的某种共鸣等要素,进而最终促使他们形成移居乡村的想法或决心*小田切徳美:《農山村は消滅しない》,第176頁。。
作为田园回归现象不断得到强化的现实根据,小田切氏指出以下四点:第一,根据舆论调查显示,日本青壮年群体移居乡村地区的意愿不断高涨;第二,青壮年群体移居乡村地区的咨询件数不断增多;第三,中国地区(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以及山口县)的人口过疏化地域出现流入人口、幼儿及少年人口增加的现象;第四,在地方消亡论中被认定为“可能消亡地区”中出现移居人口增加的现象*小田切徳美:《農山村は消滅しない》,第176~185頁。。另外,2015年,小田切氏等人基于大量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提出一个让人为之振奋的论断:“日本能够形成‘地方(市町村)消亡VS田园回归’的社会对抗轴。”*小田切徳美ほか:《はじまった田園回帰:現場からの報告》,農村漁村文化協会2015年,第13頁。
另外,同为“现场主义派”学者的山下祐介亦对地方消亡论持批判立场。山下氏认为,地方消亡论的理论缺陷在于过度强调“大国经济理论”和“归核化理论*归核化的日语表述为“選択と集中”(concentration in core competence selection and concentration)。”,同时将城市仅仅视为吸引青年人聚集的场所*山下祐介:《地方消滅の罠:〈増田レポート〉と人口減少社会の正体》,筑摩書房2014年,第196頁。。与地方消亡论不同,山下氏认为“田园回归与婚姻和出生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并提出“从制度上实现市民的两地居住/多地域所属”的解决对策,即通过制度改革准许居民同时拥有城市和乡村双重户籍,从而使得城市居民能够利用周末等休假时间回到农村从事农业活动,从而实现市民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山下祐介:《地方消滅の罠:〈増田レポート〉と人口減少社会の正体》,第255頁。。
三、 “衰落却未衰亡”的日本乡村
日本乡村虽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但在各种有利因素的支撑下顽强地获得了存续并避免了衰败。
关于这种认知,我们还可以从一组数据中找到最强有力的论据。如图1所示,从1980年-2015年的35年间,日本的城市化率从59.6%迅速攀升至67.7%。按照这个速度,至203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将到达73.1%。与此同时,如图2所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急剧推进,日本农业集落的数量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少。然而,让我们颇感惊讶的是,同时期内日本农业集落的数量仅减少3%左右,其中还包括那些由人为因素(乡村合并以及水电站建设等因素)所导致消亡的集落。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从2010年-2015年的5年间,日本的农业集落数量不减反增(总共增加3815个集落),从而强有力地印证了日本田园回归派学者的论断:“迄今为止,日本绝大多数的农山村仍得以存续。”*小田切徳美:《農山村は消滅しない》,第216頁。而在我国,根据文化学者冯骥才的统计,中国近十年有90余万个村落消失,平均每天消失200多个*陈晞:《与冯骥才对话:古村保护不能只为“旅游”》,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4月1日,第8版。。我国每天消失的村落数量比日本每年消失的村落总数还要多,这让我们感到震惊!
四、 结语
在明晰了日本乡村“衰落却未衰亡”的不争事实之后,我们禁不住想追问的是,造就其现状的有利因素到底是什么?以笔者的田野调查经验来看,日本乡村几乎不存在我国乡村正在面临的环境污染、户籍枷锁、养老困难、治理混乱、儿童留守、农民子女上学困难以及方言危机等棘手问题*关于我国乡村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请参阅《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所刊出的笔谈专栏系列文章“聚焦大变局中的中国乡村”(一)。,这主要得益于战后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的城乡融合政策,使得乡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福利保障、义务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等领域获得了与城市相差无几的政策待遇。
鉴于我国的乡村治理乱象,我们首先需要研究日本乡村得以存续的制度性因素并从中提炼出有益启示,以帮助我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正如张玉林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如果说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或‘善治’并不是单靠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考核就能完成,也必须有农民的组织化参与作为保证,那么如何开放并接纳农民的组织化参与,就主要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张玉林:《乡村环境:系统性伤害与碎片化治理》,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2页。”限于本文篇幅,笔者将另撰《地方自治制度框架下的日本乡村治理机制》一文,着重考察和分析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乡村居民在团体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制度保障下,如何通过自治会/町内会等居民自治组织以实现其乡村“善治”?
●作者地址:俞祖成,日本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政策科学研究科,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日本 京都 6020898。Email:yusosei@126.com。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4.004
基金项目:●日本学术振兴会2016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青年研究B〕(16K17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