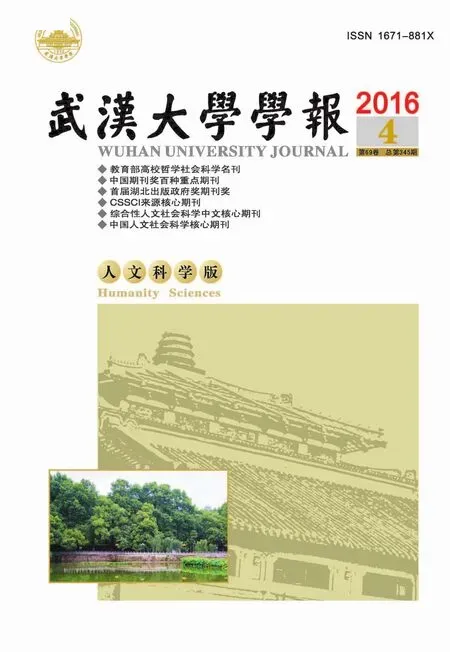农村家庭养老之殇
——农村老年人自杀的视角
2016-02-21刘燕舞
刘燕舞
农村家庭养老之殇
——农村老年人自杀的视角
刘燕舞
摘要: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是中国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生存困难、疾病痛苦、精神寂寞等是导致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家庭、家族、村组、民间组织和国家等支持主体的缺位或支持不足是导致农村老年人陷入困境后选择自杀的深层原因。更为根本的是,农村社会近几十年来所遭遇的制度与文化变迁,使得农村老年人丧失了可以获得任何支持的权威和权力。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治本之策,是要强化村组集体的社会服务功能。
关键词:家庭养老; 自杀; 乡村治理
慈勤英教授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撰文讨论了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问题,她认为主要体现为家庭内子女对年老父母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家庭养老,由于现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经济理性的畸形发展与农村空巢、独居、留守老人家庭日益增多及普遍化等客观形势的双重制约,使得家庭养老在当前农村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提出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重发展的建议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困境*慈勤英:《家庭养老:农村养老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第2期,第12~15页。。笔者深以为然。根据我们近几年来在农村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当前农村居家养老建设滞后与家庭养老乏力所带来的最为恶劣的后果是严重的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自2014年7月31日始,笔者关于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研究报告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有关部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后,党和政府已经和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并在预防和干预农村老年人自杀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例如,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提出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统一由55元提高到70元,对高龄和失能老人要健全福利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等等。近两年来,导因于对弱者的同情和底层社会问题所引发的情感共鸣,我国社会各界亦开始关注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但是,客观地说,笔者认为,各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其本应有的高度。因此,本文不揣浅陋,试就此问题做进一步表述,既图与慈勤英教授一文形成相互补充,也望引起各界更多思考和重视。
(一) 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基本状况
按照判断抽样的办法,我们根据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经济状况因素,分别在南方、北方和中部地区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地区就农村老年人自杀展开田野调查。根据田野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质量,我们以6省(南方地区的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中部地区的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北方地区的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从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因素综合考虑来看,本文所说的南方、中部与北方是基于地理意义上的南中北的划分但又与之不完全相同的划分方法,更为详细的说明可参见:刘燕舞:《论区域比较作为方法及其在自杀研究中的应用》,载《中国研究》2012年第14期,第83~104页。)24村1980年以来的农村老年人*按照统计惯例,本文所说的农村老年人是指60岁及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自杀死亡数据所揭示的最主要的基本特征做些描述。
第一,从自杀死亡的绝对数字和自杀率来看,自1980年以来,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数占全人群自杀死亡数的比例是最高的,为48.84%;其次为农村青年人,占比为33.85%;而中年人在绝对数上相对较小,所占比例为17.31%。从年均自杀率的角度看,农村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是较高的,分别为230.94/10万、48.27/10万;而农村中年人自杀率介于前述两者之间,其自杀率为26.18/10万。
第二,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表明,农村老年人自杀中,超过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该人群的比例高达65.6%,60岁至69岁区间段的自杀者仅占34.4%。
第三,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显示,在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者中,具有各种疾病的病痛者占比达到了78.43%,其中,失能与半失能的病患老人自杀者占比高达46.08%。
第四,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时间区间分布来看,根据费立鹏等人运用中国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的数据测算所公布的1995-1999年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水平为82.8/10万*Phillips,et al.“Suicide Rates in China,1995-1999”,inLancet,2002(359),p.836.,我们发现,在我们所收集的数据中,1990-1994年间的水平比较接近费立鹏先生所披露的数据。与之相异的是,在整个1980年代,农村老年人自杀属于低水平运行,自1990年代初期特别是中后期开始走向高位运行,这种剧烈转变显然属于病态或反常状态,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不同的自杀死亡人群在总体自杀死亡数据中的分布占比可以更明显地看到。例如,在1980年代的10年间,农村青年自杀死亡人数占全人群自杀死亡数的比例约为64%,而农村老年人在同时期仅占约15%。在1990年代,农村青年自杀死亡占比约为38%,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占比却上升至约40%,进入2000年以来,农村青年人自杀死亡占比下降到了约10%,而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占比则急剧升高到了接近80%。这种绝对数字占比的翻转性变化表明,在中国的自杀预防和干预工作方面,当前和未来较长时间内,农村老年人自杀仍将是我们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二) 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直接原因
从直接原因来说,生存困难、价值缺失、情感绝望、摆脱疾病痛苦、生气出气、逃避责任、减轻家庭负担、替家庭成员承担责任、殉节、报复、威胁等因素都是导致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原因。但我们所收集的数据表明,导致农村老年人自杀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种。
首先是生存困难。其占比达到了全部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的36.51%。生存困难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最直接的维持生存的日常生活资料如粮食的缺乏或不足,其二是日常照料的缺失特别是长期的日常照料缺失使得即使在粮食等日常生活资料具备的情况下也无法生存。
其次是为摆脱痛苦,其中主要指身体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也包括部分身体疾病所衍生的精神痛苦,其占比近26%。总之,在造成老年人自杀死亡的直接原因中,生存困难与疾病痛苦占比超过了60%。
从时间变化的角度来看,自2000年以来,前述第一序位和第二序位的生存困难和摆脱痛苦是最为主要的直接原因,其占比在该段时间中继续上升,前者占比高达42.15%,后者高达31.4%,两者合计占比超过该人群在该时段中所有自杀死亡的73.55%。这进一步说明,如何解决农村老年人的生存问题与疾病问题将是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预防工作中亟待重视的最为直接的关键问题。
排第三序位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生气出气,其占比为9.52%。
其他诸如情感绝望主要是指老年人对子辈的情感慰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因而自杀,这种情况亦占有一定的比例,约7%,一定程度上,它也可能是前述因素的衍生品。惩罚报复则是为了针对子女不孝而以自杀作为寻求救助手段的一种办法;减轻负担则主要是指减轻子女或配偶的经济负担和日常照料负担。不过,这些主要发生在2000年以前,2000年以后则明显减少了。
(三) 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深层原因
前文已述及,农村老年人自杀最主要的两大直接原因是生存困难和摆脱疾病痛苦。这些直接原因换种表述方式后可以发现其更为深层的道理,也即是说,农村老年人在进入老年期后是否能够活着,简要来说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按时足量获得粮食蔬菜等基本生存资料且要能够在自身支持或任何外力的支持下,这些粮食蔬菜能够吃得下去和吃得成,通俗来说,就是要保证老年人不饿死。其二是疾病在自己或外力的支持下能够得到治疗,通俗来说,就是要保证老年人不病死。其三是要在晚年生活中能够满足情感慰藉的需求,从而在不饿死和不病死的基础上,还要能够做到不寂寞死。唯如此,农村老年人自杀才不会出现或即使出现也会很少而不会呈病态式的自杀潮的形势出现。当前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问题恰恰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太理想而导致的。
解决上述三个问题,老年人需要依靠的可以提供支持的主体:一是老年人自己,二是老年人以外的其他主体。在老年人自己方面,如果配偶双方均健在的话,那么又能构成互相支持,如果缺失一方,就只能依靠单个的自己。问题的悖论在于,如果老年人依靠自己能解决上述三个问题,那么,他们基本上也就不存在自杀的风险。现实情况恰恰是,老年人随着年老使得自身机体各项功能均严重衰退,特别是对于那些失能或半失能的患有疾病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几乎无法依靠个体来解决晚年时所遭遇的生存、生活与疾病困境。因而,老年人一旦走到了这一步,就必须要依靠他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力量的支持来获得继续生存和生活的可能。其他主体则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子代、家族或宗族、村组集体、民间组织如老年人协会、国家。而且,对于丧失各种能力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为了维持生存和生活的索取或需求毫无疑问是没有任何回报的,也就是说,其他支持主体对老年人的支持势必应该是无偿的。但凡老年人自身能够提供有偿服务的货币购买力或其他补偿能力,那么,客观上他们的境况就可能不会走到要采取自杀的一步。然而,老年人依靠什么因素可以从那些支持主体那里获得支持呢?
我们先考察子代的支持情况。
在传统时期,老年人之所以在年老后能够获得来自子代的无偿支持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一是宗法制度的权力或权威保障;二是子代反哺之义的伦理保障。在前者来说,因为宗法制度保障了老年人的权威,特别是老年人主宰家庭内部经济生产与财产分配的权力,可以保护老年人在失去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后能够凭借这样一套文化模式的支撑来获得生存与生活资料。因而,除非个别家庭有重大变故,否则,在一个稳态社会中,一般的老年人都不至于年老后就会走向无法生存和生活的境地。在后者来说,作为子代,其在孝道文化的影响下,都知道羊有跪乳之恩和鸦有反哺之义的生物伦理所以,不管父辈机体如何衰老,他们大体能够出于基本的人伦而尽赡养的义务。
当然,我们也知道,传统社会时期老年人权威获得和保持所依赖的宗法制度及其形态——宗族等并非完美的。相反,笔者以前在讨论农村青年人的自杀时便可见其余威所在*刘燕舞、王晓慧:《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研究——基于湖北省大冶市丰村的个案分析(1980-2000)》,载《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第65~79页。。在解放运动兴起以后,这套制度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和瓦解。代而取之的是村组集体和国家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后,老年人的地位尽管相较于传统时期来说已经弱化很多,但因为有村组集体和国家对原有宗法制度下宗族等功能的承接,老年人的生存与生活困境并未立刻显现。
举例来说,在疾病治疗上,农村有简单的合作医疗体系的保障,这在解决老年人一些较小的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了很好的功能;在养老问题上,当时村组集体的分配体系一般都是按照“人六劳四”或“人七劳三”的规则分配粮食的*也即按照基于公平原则的按人口均分60%或70%的总量粮食,剩余的40%或30%的粮食则基于绩效原则按劳动工分的累积分配的规则。,这些都保障了老年人的弱势地位所带来的生存能力不足的方面。同时,对于那些确实不孝顺老年人的子女,尽管传统时期的宗族或家族已经退潮从而不进行调解干预,但村组集体可以对之进行很好的调解,对于子代行为特别恶劣的还可以办“学习班”对之进行教育。调解干预的效果一般都很好,其作用并不比传统时期的宗族或家族的作用差。一位当年生产队的老队长介绍说,对于子女不孝顺父母的,如果队里面去做工作而子女仍不听且“屡教不改”的,作为队长,他可以在安排生产劳动时将劳动量特别大和难度特别大的工作安排给这类人来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以示惩戒。也因此,一般来说,子代在受到村组集体的劝说、教育和纠纷调解后,都能维持一般的水平,而不会做得过于出格。是以,在那段时期,农村老年人自杀仍然很少。当农村由集体主义体制逐渐向个体主义体制转型时,绝大部分地区宗法制度及宗族形态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因而,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与新时期解放出来的青年人的最后斗争。其代价,便是笔者此前讨论过的农村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妇女的自杀问题。
然而,在新的个体主义体制语境下,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结构抑或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因为市场理性的作用,一切传统的制度、文化模式或权力结构都彻底解体或式微,人们开始生活在仅以市场规则作为主要行动指针的时代。集体和国家的退出,原有传统的权威结构不再,老年人变成了独自面对市场社会的个体。因而,在遭遇新的诸如生存、生活、疾病和精神困境时,他们既很难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来自家庭内部特别是子代的支持,也难以获得来自集体或国家的有效支持。
集体或国家的支持主要应该来自于三个方面:适度普惠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以及对于赡养纠纷有效的干预和调解。但事实是,在新农合和新农保两项制度没有实行之前,这些原本应该提供的医疗支持和养老支持在农村是长期缺乏的。目前尽管提供了一定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但由于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尚不足以解决根本性问题。因而,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老年人生存与生活的风险,但毕竟没有起到根本性的扭转作用。对于家庭内部纠纷特别是赡养纠纷的调解,村组集体一般将之视为家庭内部的私事而越来越少参与干预调解,一些老人在碰到这类困境时尽管寻求乡村两级的救助,但他们一般都会运用现代法治话语鼓励老年人自己到法院去寻求救助。问题在于,一方面,即使子代将老年人逼到了濒临自杀的边缘,作为亲代的老年人也不忍心到法院去起诉子代;另一方面,即使少数老年人活着的意志特别强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向法院寻求救助时,却总因为司法干预的乏力而无积极效果,最终,老年人还是得独自面对自己的困境。
当然,如果这些都缺失后,能够有一些民间组织,如老年人协会存在且能够实质性地发挥作用的话,当前及未来的农村老年人其生存和生活境遇可能还不至于如此悲观。然而,现实表明,这类民间组织的发育是非常滞后的,很多地方尽管也有所谓的老年人协会组织,但大多只是停留在墙壁上和宣传纸板上,而从未从宣传纸板上走下来真正地进入到老年人的生活世界中。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老年人自身之外,其他支持主体均缺失或严重乏力,其结果即是,饿死、病死或自杀就成了必备的选项之一。其中,很多老年人在自己走上这条道路时,在饿死、病死与自杀的三项选择之间,他们往往会基于生存绝望或摆脱疾病痛苦的考虑而选择自杀作为他们人生的归宿,这既是个体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四) 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治本之策
如何治理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笔者在其他文章中主要从治标的角度讨论了诸如完善和强化新农保和新农合制度、开展司法援助、启动政府问责、弘扬孝道、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建设、加强老年人协会组织建设等诸多层面。本文试图从治本的角度简要抛砖。
从顶层设计的治本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要化解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当务之急应当是重建社会主义性质的村组集体,特别是完善和强化村组集体服务社会的功能。农村老年人自杀能否得到干预和有效缓解,从根本上来说,以我们当前的国情来看,想回到过去,显然没有可能性,也是没有头脑的做法。因此,一切所谓复兴宗族、恢复传统的道统的做法,在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洗礼的农村,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同时,如果继续将农村老年人推向市场,那么,他们的自杀只会变得更加严重。唯一可行的治本之策,就是要加强村组集体的功能建设,让村组集体更多地成为除了传达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末梢外,更重要的是要强化其社会服务功能。事实上,无论是解放前的宗族,还是解放后的村社,它们本质上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特征,都是一种集体的组织。只不过前者属于血缘联结的集体团体,后者则是基于地缘联结的集体社会;前者在保护老年人的同时却压制了年轻人的自主性,牺牲了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妇女的福利,而后者则能够在保护所有村社集体内部的弱势群体方面相对平衡地着力。笔者认为,这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含义。
●作者地址:刘燕舞,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liuyanwu0202@126.com。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4.0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SH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