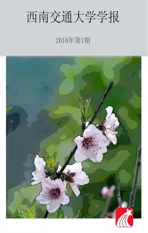英雄书写与诗意建构——武侠小说中大侠生命体验的审美维度
2016-02-19安汝杰
安汝杰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英雄书写与诗意建构
——武侠小说中大侠生命体验的审美维度
安汝杰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关键词:武侠小说;英雄书写;诗意建构;生命体验
摘要:武侠小说中英雄书写的江湖世界具有现实性和寓意性,是武侠小说中大侠生命体验的诗意空间。武侠小说中有实有虚的武功招式,是大侠的心境状态和性格特征的反应,与大侠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有着强烈的审美韵味。可分为故事性与抒情性文本的武侠小说的英雄书写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不同的书写模式诗意地设置故事情节以呈现大侠的生命体验。悲苦寂寞是一种崇高和唯美的文化意象,是武侠小说家进行构造故事情节的原初动力,是大侠生命体验的审美归宿。
Heroic Writing and Poetic Construction—Swordsmen’ Life Experiences in Wuxia Novels on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AN Ru-jie
(SchoolofHumanities,SoutheastUniversity,Nanjing211189,China)
Abstract: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jianghu world of heroic writing was the poetic space of swordsmen’s life experience in wuxia novels. Actual and virtual moments of fighting skills with strong aesthetic appeal in wuxia novels were reflections of swordsmen’s state of mind and characters, 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swordsmen’s life experiences. Heroic writing of wuxia novel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f narrative and lyric styles, having no fixed patterns, and different writing models had been set up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plots in a poetical way revealing swordsmen’s life experience. Bitterness and loneliness were a cultural image of sublime and aestheticism, being the original motivation of wuxia novelists in their conception of plots as well as aesthetic attachment of swordsmen’s life experience.
上个世纪以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实实在在的生命存在感和精神归属感也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难以寻找,媒体传播的迅速更新并没有拓宽人类的交往空间,也没有更好地激发人类的生命体验,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和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使寂寞单调的独立作业成为一种常态,城镇化推进中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大厦更是将个体的生命体验抛之云边。人们日渐习惯于一种缺乏激情的生活,早已忘记传统社会中崇武尚侠之举曾经激起过民众无限的精神向往和生命体验,而“侠客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尚武天性的一类人”〔1〕,因此人们迫切需要大侠精神的鼓励和英雄事迹的熏陶,以应对社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武侠小说中大侠生活的江湖世界承载着大众童话式的想象和梦中的英雄向往,“‘江湖’包容万千的‘文化意象’,给以‘江湖’为题材的文学艺术贡献广阔的‘叙事空间’”〔2〕,陶醉于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的“文化意象”能够减轻枯燥单调生活给当代人造成的心理压力,“使人得到一种心灵的洗礼和平添一种高尚的情操”〔3〕,并能忘却烦恼。因此,从审美维度探讨武侠小说大侠生命体验的特征与内涵就成为了当今武侠小说研究的又一思路。
一、江湖世界:大侠生命体验的诗意空间
武侠小说空间“构建的是非现实、超现实的时空”〔4〕,目的是为小说中英雄大侠的生命体验营造一种特有的诗意审美氛围。大侠行走的诗意空间是“江湖世界”,又称之为“武林”。武林中有“武侠”,武侠之“武”,表现为外在的“功夫”,武侠之“侠”蕴含着“义气”,江湖世界中的事情则因英雄的存在而气象万千,为此,“英雄形象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审美品格”〔5〕,这正是武侠小说英雄书写的特质。为使这种特质得以展现,武侠小说描写时通常会设置一些特有的、典型的诗意空间。例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就曾生活于古墓里,寂寞荒凉的空间使二人发生了那种难分难舍而又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射雕英雄传》开篇就让郭靖母子饱尝沙漠之苦,而非毫无障碍地让郭靖师从“江南七怪”学武练艺,这样描写的目的是为了能全景式地展示大侠郭靖的成长经历。在武侠小说的英雄书写传统中,缺乏逆境历练的童年对于大侠来说是有缺憾的,是有损于大侠完美形象的。古龙的武侠小说《绝代双骄》也有类似的空间营造。主人公江小鱼出生不久就无辜受到剑的伤害,之后又不幸流落到“恶人谷”,恶人谷是天下“恶人”聚集之所,是“武林禁地”,但成长于恶人谷的江小鱼却心地善良从未产生恶念。“恶人谷”这一空间的布置有着鲜明的对比性,生存环境的恶劣反衬的是人性的向善,小说作者的用意不言而喻。
总的来说,诗意空间的营造通常分为现实性的和寓意性的。现实性诗意空间的营造通常依托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例如《越女剑》就以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为历史背景来叙述,故事的发生地自然是鱼米之乡的浙江;《天龙八部》以历史上的“宋辽战争”为背景,将故事空间布置在雁门关。武侠小说作者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根据故事情节发展来布置空间,便是最具有现实性的诗意空间营造方式。而寓意性的诗意空间则是小说作者为满足英雄书写的需要,通过虚构的艺术手法来布置大侠生命体验所特有的、暗含弦外之音的非世俗世界。《神雕侠侣》开篇就描写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诗意空间——古墓。古墓亦被称为“活死人墓”,是“终南山下,飘逸之风,神雕侠侣,绝迹江湖”〔6〕后的生存世界。“写意性”的古墓是一个人迹罕至的诗意空间,这一空间的营造有着两方面的英雄书写寓意:一是杨过和小龙女在这种诗意空间中相亲相爱,产生真切的爱恋;二是暗含着两人的感情唯有在“古墓”这种诗意空间中才能维持,一旦离开此地走向世俗,就会风云激荡,不被世俗所容。之后英雄书写的推进也验证了这一点,最终成为世人倾心爱慕的英雄大侠杨过,还是和小龙女重归了古墓。“古墓”是杨过和小龙女之间感情的起点和终点,有着“以圆为美”的审美内涵〔7〕,不管他们到哪儿去过,终究还是只能回到古墓的诗意空间中去体验生命之真。
武侠小说的诗意空间与戏剧的演出舞台相类似,大侠的生命体验和英雄事迹都要在这一舞台上发生和展开,因而独具审美意蕴。武侠小说的诗意空间营造各呈异彩、蔚为壮观,它不仅是英雄书写的载体,也是英雄生命体验的审美场域,“灵台方寸,尽在一念之间”〔8〕。这种审美场域的呈现尽管千姿百态,但也总是大侠生命体验的诗意空间。
二、功法虚实:大侠生命体验的审美基点
武侠小说重在书写英雄(古龙语),英雄则在虚实功法中体验生命。武侠小说之“武”,就是一些有实有虚的“武功招式”,这些虚实功法在大侠生命体验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大侠生命体验的审美基点。追根溯源,中国武术可谓是博大精深,在漫长的上古时代和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习练武术是枪炮等武器主导战场之前打击敌人和防御自卫的最佳方式,武术受到朝廷和民间的重视。唐代女皇帝武则天开设武举取士以来,武术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宋朝以降,武举制度大力发展,平民子弟可以通过参加武举考试而改变自己的命运,由此民间社会刮起一股强劲的习武风气,这为以宋代为故事背景的武侠小说的武功描写提供了素材。《水浒传》里的武功招式就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习武之风,小说中豪侠都有自己的拿手武艺,豪侠义士们仗剑走江湖断不是全然虚构而来(例如燕青拳至今仍然流传在民间)的。
《水浒传》标志着武侠小说创作的成熟,为后世武侠小说提供了写作范式。至清代,一批以《七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小说曾一度风行。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武侠小说创作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武侠小说创作的高峰,创作中心逐渐由上海、南京转向天津和北京,出现了代表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北派五大家”(这些作家当时全部生活在北方,并大多以天津为创作中心,因此得名;五大家早于金庸等新派,故又称旧派),即还珠楼主(奇幻仙侠派)、白羽(社会反讽派)、郑证因(帮会技击派)、王度庐(悲剧侠情派)和朱贞木(奇情推理派)。除五大家之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向)等,他们大都是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泰斗,其中“平江不肖生首次掀起了中国现代武侠狂潮”〔9〕。北派五大家的功夫招式风格不一、各有特色。还珠楼主属仙侠怪诞一派,融剑仙传说、神话故事和武侠传奇为一炉,想象瑰丽、气象万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剑仙神魔世界”〔10〕,其武侠名著《蜀山剑侠传》系列令人叹服。白羽的江湖世界有着世俗化的倾向,把大侠生命体验的江湖世界和世俗社会沟通起来,用反讽与批判的手法来刻画江湖世界。白羽擅长于大侠悲剧场景的书写,他把大侠英雄难以平复的内心争斗、恩怨情仇的人生体验把握得很是到位,其英雄书写也悲情激烈、回味绵长,别有一种审美韵味。郑证因熟悉江湖世界的法则,熟知各种帮会的前世今生和组织规则,他特别善于描写武功招法,轻功硬功、内外功法、独门暗器,样样精通,写得活灵活现、形象逼真。王度庐则是以情感见长,有道是“刀剑无情、英雄有义”。朱贞木是一位书写大侠英雄的集大成者(有新派武侠小说之祖的美称),特别是在武功描写方面,诸多奇招怪式都出自其手,对后世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武侠小说中武功招式大体分为写实与写虚两种情况。以《水浒传》、《七侠五义》及“北派五大家”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武功描写”基本上是写实的,而“新派武侠小说家”(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代表)的武功描写基本上是写虚的。纵观“北派五大家”的武功招法,其中不乏奇幻的元素在内,然而终究还以写实为主,小说中不仅有以“形意拳的代表套路‘五行拳’”,还有“以‘走转为圆’为核心的‘八卦掌’”〔11〕,实战的描写更是充满各种“战阵”(例如八卦阵、罗汉阵等)。这些拳术和战阵都存在于中国武术的庞大体系中。而“新派武侠小说家”特别是金庸对武功路数的描写不仅有着强烈的诗学韵味,同时也是大侠的生命体验和性格特征的反应。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武功不仅仅是一种克敌自卫的手段,更是大侠人生体验的审美基点、人物性格的反映。陈家洛(《书剑恩仇录》)的百花错拳、乔峰(《天龙八部》)的降龙十八掌、杨过(《神雕侠侣》)的黯然销魂掌、张无忌(《倚天屠龙记》)的乾坤大挪移等无不与大侠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从百花错拳到乾坤大挪移,这些奇幻武功无不与掌握这种功法的大侠的英雄性格和气质吻合,是大侠生命体验的产物。《神雕侠侣》中大侠杨过的黯然销魂掌的独门绝技来源于我国南北朝著名诗人江淹《别赋》中的诗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12〕。杨过和小龙女于绝情谷断肠崖分开之后,杨过不分日夜地守候在海边,形容枯槁、面容憔悴,百般无奈之中随意发挥,一掌就将坚硬无比的龟壳打得粉碎,从此创作出一套包含“无中生有”、“孤行只影”等十七个招式的新武功。这套武功招式是真切的生命体验,与大侠的感受密切相关,是大侠的心境状态的反应,忽而徘徊空谷、忽而孤行只影的武功招式同时构成了大侠生命体验的审美基点〔13〕,反映了大侠功力的深厚和体验的深刻。与其说这些招式是武功之“虚”,倒不如说是大侠杨过的生命经验。黯然销魂掌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现实中的人也没法习得,因此只是一种虚写。古龙武侠小说中对大侠的武功描写则虚幻得有些不着边迹:陆小凤有无招胜有招的“灵犀一指”,李寻欢的“神刀”出刀即毙命。西门吹雪更是神奇无比,他吹的不是“雪”而是“血”,闪闪剑光杀敌于无形之间,只见到“西门吹雪在吹他剑尖上的血”〔14〕。其实不管作者如何描写武功之“虚”,也都是为了表现大侠的生命体验。
三、故事情节:大侠生命体验的诗意呈现
不同的英雄书写方式会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审美感受,这正是武侠小说故事情节的魅力所在。从武侠小说的文本类型来看,武侠小说分为“故事性”文本与“抒情性”文本。从数量上来看,“故事性”文本以绝对优势压倒“抒情性”文本。“抒情性”文本之所以是抒情性的,就在于运用英雄书写而将故事情节做了淡化处理,更加突出了大侠的生命体验。
武侠小说《越女剑》以“吴越争霸”为历史背景,用较短的篇幅叙写了越国大夫范蠡和越女阿青之间的爱恨情仇,“再现了勾践在吴越争霸时期的复仇精神”〔15〕。勾践向越国复仇遇到了挫折:吴国剑士不但剑利术精,且善用兵法,越人不敌。而放羊女阿青的出现却轻易地击败了吴国八剑士,范蠡以之为奇,于是将阿青接到府邸,终于使越国剑士观摩到了神剑的影子,这神剑的影子就能使越国天下无敌。此时越国在薛烛的指点下也造出了利剑千万,于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勾践向吴国发起了进攻,终于大破吴军。但是对范蠡来说攻破吴国并不是他克吴的唯一目的,他是更想见到被献给夫差的美女西施。正当他和西施见面时,阿青却出现了,因为她已经喜欢上了范蠡,并以剑气伤了西施,不过阿青最后因西施的美貌而黯然离开了……这种“单调的”看似缺乏“完整性”的英雄书写,却使范蠡的英雄形象非常丰满。
除了个别情况外,武侠小说的英雄书写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塑造一种“模式化”的故事情节。总的来说,有六种结构形式:群雄争霸式、英雄夺宝式、复仇成长式、反抗入侵式、官府绞杀式、链接历史式等。群雄争霸式、英雄夺宝式、复仇成长式等是单纯的江湖模式,反抗入侵式、官府绞杀式、链接历史式等则是或融入历史真实,或编制情节反映历史,或根据历史进行适当虚构等。“新派”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故事情节的展开便是以清朝末年“义和团运动”为历史背景的。丁剑鸣(河北保定太极门丁派掌门人)与清政府成员索善余交往甚密,拒绝听从柳剑吟(丁剑鸣的师兄)的良言相劝,一意孤行地靠近官府,疏远江湖英雄,后来却遭官府杀害。其时“义和团”威势正壮,柳剑吟为了报杀弟之仇而成为了“义和团”成员。然而,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其内部在针对清政府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形成了反清灭洋、扶清灭洋、保清灭洋三大派。柳剑吟因反清遭到暗算而死于非命,柳的女儿柳梦蝶和弟子娄无畏为了报仇雪恨,于是在京城“校场口”设下擂台,按江湖规矩向岳君雄(保清派人物)提出比武,挑战方和应战方各邀天下英雄助阵,一时间“龙争虎斗,震动京华”〔16〕。但列强侵入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为讨好各国列强,竟下令剿杀反对洋人的义和团,于是遭遇国恨家仇的擂台之争便成为了无所谓输赢的争斗。数十年后,经过一番生死考验的柳梦蝶终于手刃了隐居多年的岳君雄,报了轼父之仇。尽管如此,但在经历了杀父之痛和失夫之悲的生命体验后,柳梦蝶最终还是决定出家为尼。这场争斗既是太极门柳梦蝶、娄无畏的复仇之战,也是义和团内部反清派同保清派矛盾的总爆发。梁羽生武侠小说把江湖世界和真实历史进行嫁接,其小说中英雄侠客的恩怨情仇和国家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17〕,大侠的生命体验与人格精神之美随着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故事情节的展开被诗意地呈现。
相对于梁羽生较为单一的历史书写模式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的英雄书写模式更显出多样性。金庸武侠小说的故事情节较多采用一种经典的江湖书写形式(如《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等多牵涉英雄夺宝情节),但也有一部分经典著作是以宏大的历史背景为书写依托的(如《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古龙的英雄书写模式则更具匠心,其武侠小说的故事情节结构紧凑、进展快速,通常依靠人物之间的对话来阐明事情的前因后果,结局往往出人意料,可称之为破案模式(如《陆小凤》系列、《楚留香》系列);其小说中的人物陆小凤、楚留香,通常是独自一人深入险境,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依靠精确的推理、不懈的坚持与超人的武功,揭开一个又一个奇玄难解、错综棘手的“谜团”;古龙武侠小说的语言句式不长,但明晰、浅显、流畅,如“依旧是长安,长安依旧,人也依旧”〔18〕,其简短有力的语言有一种诗的节奏和韵律,这种语言所勾勒出的故事情节更能诗意的呈现大侠的生命体验。
总而言之,武侠小说的英雄书写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可能风格多种多样,不同小说家的作品可能按照同一个模式进行书写,这完全取决于小说作者的书写意图:借助故事情节的设置来诗意地呈现大侠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
四、悲苦寂寞:大侠生命体验的审美归宿
越是悲苦寂寞的内心体验,就越具有审美价值。武侠小说中大侠都具有那种无可言说的内心痛楚,他们将注意力从关注外界转向关注自身,使自己的内心升起一种超越感性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这种由内心体验激起的对自身使命的崇敬构成了大侠生命体验的审美归宿。
金庸武侠小说的英雄书写更倾向于从历史找到突破口,即将大侠的生命体验放置于民族矛盾突出的时代背景中,让大侠的生命体验随着文化差异造成的民族冲突的激化而逐渐深刻。金庸的书写并没有离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资源,他擅长于将大侠的生命体验通过人物的气质性格来体现,从而使大侠形象丰满,并使阅读者产生一种高亢激昂的兴奋,这就是金庸英雄书写的独到之处。
金庸充分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来塑造乔峰这类大侠,竭力展现大侠的英雄气概。文化教育及其所生活地域的文化氛围能够成就一个大侠,同时也能够导致一个大侠的毁灭。成就一个大侠即是说乔峰受到汉文化的熏染,成为了英雄;大侠的毁灭就是说乔峰在辽与宋的战争中处于两难境地(乔峰本是契丹人,受的是汉文化教育),于是选择自我毁灭的方式结束抉择的痛苦。小说中的乔峰不能被视为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生命个体,而是一种象征(符号存在),悲苦寂寞是乔峰生命体验的审美归宿,其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和美学意蕴早已经脱离了族群国度的界限,而成为了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对此覃闲茂指出:“普通大众再平常不过的无意义的喧闹很难将大侠的生命体验铸造为永恒。越是那种特立独行,那种极度的‘悲苦寂寞’,那种令人一想起就不寒而栗的时空笼罩下的悲苦寂寞,也越是能够以审美的方式传达出大侠生命体验的真实。”〔19〕这恰好是金庸英雄书写的美学意蕴。
古龙笔下的大侠常常以“浪子”的身份出场,其作品中的悲苦寂寞的英雄形象与金庸文本中的经典大侠形象(郭靖、乔峰等)大不相同。古龙武侠小说中的大侠是“浪子”,因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而没有归属感,于是放逐心灵、居无定所,这种漂泊无依的浪子生存现实与悲苦寂寞的体验,赋予了大侠“自我完善”与“人格独立”的特质,即便其中牵涉到感情纠葛、暴力打斗的场景,“也是将其指向大侠的生命体验与社会意识层面的”〔20〕。作者进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探索生命的悲情与无奈,揭示大侠个体生命的悲苦和寂寞。例如,《萧十一郎》中萧十一郎平日以扶弱济贫、行侠仗义为生活的动力,过着潇洒风流的生活,却身不由己陷入了神器宝物“割鹿刀”的争斗中,被世人误解为欺世盗名的“江洋大盗”,其“恶名”也因此为江湖英雄所不齿,但他却孤身一人抗争于江湖世界,创造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奇迹”的英雄事迹。他常哼唱那首名为“孤独狼”的曲子,其实在他那挺拔傲岸、忧郁孤独的身影背后却隐藏着无以言说的悲苦寂寞。大侠们一生常以悲苦寂寞为伴,但他们坚持自己的侠义理想,宁愿悲苦一生也不向世俗低头,始终在痛苦中谨守大侠人格和精神家园。
大侠的悲苦寂寞具有诗意审美性,悲苦寂寞蕴含着太多的美学元素,当它成为大侠生命体验的审美归宿之时,同时也成了武侠小说家进行构造故事情节的原初动力。唯有真正感受到美的存在,才能体会到那种绵延悠长、余味无穷的文化回响,大侠悲苦寂寞的生命体验才有可能达到极限,“人生之花,愈长愈香愈浓”〔21〕。当一位大侠真正体验到了悲苦寂寞时,悲苦寂寞就已经构成其生命的一抹亮色,大侠的人格才可称之为完美,也才最具有审美魅力。“华山派”的一代宗师风清扬,其剑术已经进入了无招胜有招的“化境”,是“进入‘逍遥而游’境界的‘绝世武功’”。他在体验了人情冷暖、江湖险恶后,主动退出江湖隐居于华山。晚年时期他在“思过崖”将人生的经验传授给令孤冲时说:世上最具有威力的功夫不是“独孤九剑”的无招胜有招,而是“阴谋诡计”。这是风清扬生命体验的总结。经常体验悲苦寂寞思想才能高远脱俗,风清扬就是悲苦寂寞的象征符号,“一个真正的‘大侠’,必定是‘高贵的人’,也必定是‘孤独的人’。‘高贵的人’使大侠成为真正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人,而‘孤独的人’则使大侠总是成为不合时宜、艰难前行的先行者”〔22〕。当悲苦寂寞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在大侠精神深处呈现出高雅而又亢奋的一面,当武侠小说英雄书写的侠、义、情呈现为大侠悲苦寂寞的审美归宿时,武侠小说便会诗意地构筑起大侠生命体验的崇高和唯美。
五、结语
武侠小说的诗意空间异彩纷呈,它不仅是英雄书写的载体,也是英雄生命体验的审美场域,是大侠生命体验的诗意空间。武侠小说之“武”,是因为虚实共存的“武功招式”,这些虚实功法在大侠生命体验中具有重要位置,是大侠生命体验的审美境遇。武侠小说的英雄书写不管采用哪一种模式,完全取决于小说作者的书写意图:借助故事情节的设置来诗意地呈现大侠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悲苦寂寞不仅是大侠的内在心灵体验,更是其侠、义、情融为一体的诗意存在方式,这种超越感性的诗意存在激起的生命体验构成了武侠小说中大侠生命体验的审美归宿。
参考文献:
〔1〕文敏.魏晋南北朝咏侠诗的人物美〔D〕.西南大学文学院,2010:1.
〔2〕安汝杰,刘晓燕.江湖——中国武侠电影的隐喻空间〔J〕.昭通学院学报,2014,36(4):81-84.
〔3〕安汝杰.荒原驰骋的侠士:论鲁迅的侠义精神〔J〕.唐山学院学报,2015,28(2):73-75.
〔4〕宋文婕,韩云波.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模型——以还珠楼主研究为例〔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0(6):111.
〔5〕王鹏程.明清小说草莽英雄形象系列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11.
〔6〕张媛.金庸小说中的终南山形象及其文化特质〔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5-59.
〔7〕王培娟.从中国古典诗词小说看古代圆美观的艺术内涵〔J〕.东岳论丛,2013,(5):152.
〔8〕熊桂玉.佛教心灵哲学与精神文明建设〔D〕.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55.
〔9〕韩云波.平江不肖生与现代中国武侠小说的内在纠结〔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7(6):34.
〔10〕孔庆东,蒋炯毅.论《蜀山剑侠传》的超越生命观〔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2):70.
〔11〕周彬,李艳翎.传统武术的哲学审思〔J〕.体育学刊,2007,14(2):67.
〔12〕张海明.江淹《别赋》《恨赋》写作时间及本事新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34-37.
〔13〕金庸.神雕侠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42.
〔14〕古龙.陆小凤传奇〔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221.
〔15〕吴秀明,黄亚清.金庸武侠小说与地域文化现代性构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0(2):46.
〔16〕梁羽生.龙虎斗京华〔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2.
〔17〕王舒婷.《儿女英雄传》中“侠”与“情”的新变〔D〕.辽宁大学文学院,2012:22-25.
〔18〕古龙.英雄无泪〔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126.
〔19〕覃闲茂.金庸人物排行榜〔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5:178.
〔20〕陈中亮.现代性视野下的20世纪武侠小说——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为中心〔D〕.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2:15.
〔21〕周仲强,吴秀明.孤独的生命体验与诗意书写——武侠小说男性叙事的审美考察〔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2):84-90.
〔22〕韩云波.“三大主义”:论大陆新武侠的文化先进性〔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2):67.
(责任编辑:杨珊)
Key words:wuxia novels; heroic writing; poetic construction; life experience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1-0049-06
中图分类号:I054
作者简介:安汝杰(1987-),男,河南商丘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小说美学、武术历史与文化研究。E-mail:601136154@qq.com。
收稿日期:201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