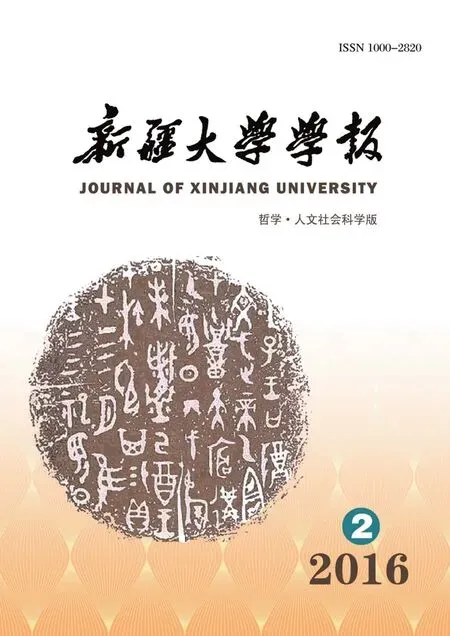现代性境遇下的刘亮程散文*
2016-02-19胡新华
胡新华,王 敏
(1.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0;2.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继小说《凿空》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刘亮程的散文集《在新疆》荣获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刘亮程也成为继韩子勇、周涛、沈苇之后,新疆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刘亮程作为移民新疆者的后代,生在新疆并在疆成长起来的作家,其写作不同于长久扎根于斯的情感书写,也不同于流寓者发现风景之旅的状写,他的文字是介于二者之间复杂、矛盾情感的结合体。正因如此,对移民世界的关注,对传统乡村图景的描绘,成为他各类题材创作的主要内容,并有着深刻的个体思考,传达出了一种冥思的哲学意味。具体来讲就是刘亮程在创作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思考,思考的指向和内容并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特征和为人赞叹的雄伟奇特的自然景观,也不是简单的“西部精神”的书写,而是深度开掘人与自然环境、时代变化、现代精神之间的快乐与痛苦、有限与永恒的意义。这种写作的姿态与自我意识集中体现在他关于新疆乡村书写的众多散文中。
一、刘亮程笔下的移民乡村
乡村是刘亮程作品中重点表现的意象,也是他进入文学世界的重要叙事抒情单元。早期的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以及《刘亮程散文选集》中就反复地强调乡村。人、牲畜、庄稼、田间的虫类及野草等构成了乡村中更为细小的图景。一般认为,刘亮程的乡村反映了乡村和谐、惬意、宁静的生活全貌,是乡村原生态的展示,这种生活的情境恰恰也是刘亮程面对自然冥思的结果,在荒凉之处植根诗意的生命。如此的评述几乎成为刘亮程文学创作的断语。但实质上,这些特点的归纳仅符合对他所认识的北疆农村的书写。
从西汉开始,移民以时断时续的方式介入西域(新疆)。乾隆中期后,“在北疆,由于经历战火后的北疆原有人口大为减少,几乎是‘千里空虚,渺无人烟’,所以清政府积极鼓励内地人携眷移驻北疆的乌鲁木齐、巴里坤和伊犁等地,但不得携眷移驻游牧部族聚居之地”[1]。在各县的乡土志中关于北疆各县志的人口氏族记载中也均显示无世家大族,大体以移民为主,如《迪化县乡土志·氏族》记:“迪化自兵燹后,烟户萧条,土著稀少,其汉民由内地迁徙而至者,或军遣,或防戍,或贸易,多系只身流寓,并无富村巨族及宗祀谱谍可纪。”[2]13《阜康县乡土志·氏族》:“无世家大族,以见在言之,李、杨、高、段、王五著姓也。”[2]18《绥来县乡土志·氏族》记:“谨考本境无世家巨族,屡遭兵燹,承平后关内迁居者有之,关外各处迁居者亦有之。无大姓成族可编。”[2]78《呼图壁乡土志·氏族》记:“兵燹遗黎,均朴野愚氓,无世家巨族可录。”[2]89总体而言,有清一代,北疆移民类型大体有军屯、犯屯、商屯、民屯(含贫民自流)等几种,拘于新疆地广人稀的特点,这几类屯垦戍边的移民者以安插的形式在绿洲从事生产。另外从人员的组成上看,军、犯、商、民等本身在迁移过程中并不具备宗族的关联性,甚至对传统宗族伦理的继承而言,可能存在着因文化程度较低而出现近似空白的情况。而在建国后,移民新疆的范围从陕甘扩大到其它省份,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移民新疆的难度,国家层面也延续了屯垦戍边的历史政策,社会主义建设与保卫边疆并举。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的移民,新疆移民与故土乡村的内在联系被地缘隔断,导致了乡村社会固有的宗族观念的失效。也即是说“乡土中国”中的宗族与血缘关系在村落中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广意义上的地缘关系,即“老乡”观念的兴起。来自甘肃、陕西、四川、山东、湖南、河南、山西等省份的移居者持不同方言在“老乡”的称谓中谈论着各自家庭的境况,得意的神情中分明又透露出迷离。因而在这里,“当‘家’、‘故乡’、和‘社群’从视野中彻底消失的时候,大约是可怕的”——实质上则是乡村中的社会关联度的降低,即具体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关系的能力的降低。在《我改变的事物》中,刘亮程讲出在同一房子里的板凳上与坐在路边木头上商量出来的结果是绝不相同的。如果能够确定在同一间房子商量事情的人员之间的亲密度胜过于在路边木头上商讨事情的人们,那么刘亮程确实抓住了一个众姓杂呈的村庄在人际伦理关系上的凝合性特点。相反,人际圈子的散零也就造就了“一个”意识的生成:“孤单成了一件事情。寂寞和恐惧成了一件大事情。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而它们——成群的、连片的、成堆的对着我,我的群落在几十里外的黄沙梁村里,此时此刻,我的村民帮不了我,朋友和亲人帮不了我。”[3]48这种源于人际疏离的孤独对个人是致命的,个人在群落中无法找到可归依的去处,正因如此,在刘亮程关于这类村庄的特点的定义中,他给予了哲学意义上的命名:“每个村庄都很孤独。”[3]75
可见,刘亮程要说明或者阐述而非描述的村庄并不是物质生活意义上的住所,而是诉说着历时秩序上空间层面的困惑与荒芜,指涉的是孤独背后的身份认同体与归属源于何处的问题。众多移民家庭以散成满河星的状态分散在绿洲上从事农耕生产,在较长时间内,身体的存在与身份的认同,故土与异乡的畸恋,使个体精神在资源上产生了混乱甚至匮乏感而无法确证自己,势必要通过归属感来实证自己的存在。换而言之,当传统社会的信赖体系已经崩溃,新的信赖体系尚未建构起来,必然会生成一种无所傍依的漂泊或流浪感。
这种情愫也一直延续到2003年创作的《先父》。在《先父》一文中,刘亮程以生命之河作喻,从下游往回追寻数代祖先而陷入浑然不觉的暗夜中,爷爷奶奶的时代仅是经过而非停驻,这层话语透露的含义就是祖辈在他生活中的缺失。甚至到了父亲一辈时,父亲也被“丢掉”,自己的童年因没有父亲对家族历史的讲述,也失去了对家族根脉的掌握,所以有着深深的焦虑:“你死去后我的一部分也在死去。你离开的那个早晨我也永远地离开了,留在世上的那个我究竟是谁?”[4]7
此外,如果说刘亮程在一些散文中演绎了对漂泊的无可奈何、迁移中的孤独和恐惧、家族式的伦理规范失效,那么他对家族谱系的寻找可以视作对根的追溯或家族历史的建构。千差万别的文化因子瓦解了传统宗族人际的共同体,对家庭这样一个共同体文化的记忆也呈现碎片化,“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5]40。“事实上,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而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了起来。”[5]94刘亮程对父亲和先祖的书写,试图续写家族谱系的缘由即是无根的焦虑,尤其是后起一辈离开故土外,只能靠他人言说建构起对家族的记忆。人类对自我存在的思考,未尝不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一个诘问,关于刘亮程散文具有生命哲学意蕴的评价,大概也是来源于他对移民家族失去根脉的反向追寻。
总的来说,刘亮程是以村庄剩余者的身份来书写异乡人在新疆乡村中的弱者形象,尤其是民国时期至建国后的移民,符合了中华民族朝着现代化梦想迈进的总体特征,即人口的流动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守土卫疆,而更具有了建设的意义。但在这种总体的流动情形中,乡村结构的变化、家的不可抵达、返乡的焦虑与家族谱系的缺失,这些前现代的遗留问题和变动不居的现代性境遇重叠为一起,成为刘亮程乡村书写的一个面向。
二、村落文明的传承
刘亮程的南疆散文主要是以维吾尔族聚居乡村为关注对象,村民大多是维吾尔族人,不同于他所认识的北疆的移民村落,大部分村庄的存在时间长达千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乡村结构。村落也大多处在古丝绸之路上,地缘与历史的原因决定了南疆村庄生态特点,即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传统手工业的发达,商业贸易的意识明显强于北疆,由此也形成了乡村巴扎。不同村落的村民往返于巴扎之中,乡村之间的流动性加大了村民个体生活的社会化,这种乡村中的巴扎在新疆时间内展开,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混沌时间中铺展成为一种极为难得的悠闲自在。可以发现,刘亮程在关于南疆乡村的书写中,照样以月亮、树、狗与驴等作为散文创作的结构结点,但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人际关系上;在思考的层面上,也已经不同于对北疆乡村书写的玄思,而更多地是面向了乡村之变,在农商混杂的乡村中观察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化关系,如《月光里的贼》、《树倒了》、《狗的路》、《牙子》、《龟兹驴志》、《五千个买买提》、《生意》等。再如《最后的铁匠》、《逛巴扎》、《暮世旧城》等则明显采取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的写法,以理智目光洞穿了异质文化,在丰富迷人的人文历史中,向着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迈进。刘亮程的散文也是他关注村民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生存与发展的境况,并对此进行详细与情境化的描述。需要指出的是,刘亮程对南疆乡村的关注,不同于“他者”意义上的猎奇,而是充分尊重文化间性进行的表达,从北疆乡村中思索自身何处来何处去的形而上问题转向了日常生活,在具体可感的文化行为中体现“文化并不是所有权的问题,而是一个转换、共同经历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所有种类的相互依赖性”这样一个普遍的标准。因此,我认为在某种层面上讲,刘亮程南疆散文的“稳中有变”与北疆散文中“动中求稳”的命题相比,更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人性的实况都应扎根于沉潜与循环的生活中。
比如在《最后的铁匠》一文中,传承了千年的“打铁”在历经数个朝代的消逝后仍强劲地存在于南疆的小城中。“他们家族共有几十个打铁的,吐迪的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子,跟他同在沙依巴克街边的一条巷子里打铁,一人一个铁炉,紧挨着……”[4]53并且,铁匠有着严格的家规,手艺都必须获得师傅的认可,才能另起炉灶经营,假若制作的铁器质量上存有问题,那么,整个家族均会以此为耻,家族的荣誉遭到败坏,这是不被允许的。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不曾使手艺失传,得益于稳定的家族结构中的手口相传和严格的家族规范。而在现代化面前,手工业制作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包括老城也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阻挡的消逝。众所周知,老城对长久生活其中的人们而言是一个保留完整过去的场域,而对紧逼而来但尚未到达的未来,则使老城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在过去选择的道路存在许多条,有很多的地方安顿身体和抚慰灵魂,而“如今,我们只剩下现代化这一条道路了”[4]126-127。
这就构成了民族地区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的悖论。如何在现代化发展面前传承和保护手工业这个命题,使得刘亮程的散文多了一个面向,甚至可以说,刘亮程从个体的哲学式体悟走向了文化、历史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他在《暮世旧城》中写道:“那是老城死去的部分,已经成为根。”[4]123这也正是他认识的北疆与南疆的区别,即使有着消逝,但依然有根可循,文明的碎片可以指认出曾经存在的事实。但更重要的是对千年如斯的当地人而言,现代化究竟为何物,未来的情况如何,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知道,现代社会对前现代社会的摆脱意味着吉登斯所说的“脱域”的生成,在时间上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同时也昭示着一个新的环境形成。所处其中的人与物从前现代稳定的空间与时间边界中脱逸出来,进入到变动、躁进的现代社会中。在《祖先的驴车·坎土曼的事情》中,刘亮程可谓真切地把握住了群体的心理变化:“龟兹人只用两件农具:坎土曼和镰刀。前者种,后者收。两种都是手工打造。”龟兹、库车人用这两件工具面对世界。他们不改变,我们变来变去,最后被这些不变的东西吸引。我们来到它们身边,想问:你们为何不变。突然又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悬在头顶:我们为什么要改变[4]139。
实质是乡村共同体中将祖先的遗产作为基本物传承下去这一过程在现代社会面前被瓦解了。但是对于前现代与现代共存来说,这种脱域并不完整,也就是存在着悖论式的情境。从我们的现代生活经验出发,乡村缓慢、悠闲的节奏只能是一曲挽歌,所有的乡村经验均在消散。老城的消失同乡村依附于现代城市的意义是一样的,老城的作用是手工业品借巴扎的集散功能从事交易,也可以想见,城市的活力植根于周围乡村的生产。按照现代化要求出现的城市则颠倒了这种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使乡村成为城市的依附,并逐渐边缘化,乡村也就成为了“现代都市的一个象征性的乡愁之所”[6]21。但是农民的悠然淡定从何而来,仅仅是依靠所谓比北京时间晚两小时的新疆时间?刘亮程留下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现代化的推进在遭遇主体行动的惰性或者是抗拒时,应当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调和。或许这也是具有着不同现代性状况的中国大地的魅力。
要而言之,刘亮程的南疆散文开凿了他散文创作的新面向,在地域上,从天山以北指向了天山以南;在文化上,从传统农业文明指向了的农商文化;在现代性情状上,也呈现了稳定的乡村结构在现代化面前的基本特点和百姓心理。也因此,他的散文更为丰厚,为我们整合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新疆形象。
三、新疆时间与现代性
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在新疆》,刘亮程创作的面向明显有了更大的跨越。如果说《一个人的村庄》是对个人在乡村中前现代与现代条件下移民生活的具体情状的描绘,那么在《在新疆》中则体现了一个关于群体在现代性动力下时空分离的特性。无论是个体的孤独还是群体的怀旧,在很大程度上均指涉到了乡村的现代性境遇。
但是,如果我们对现有的刘亮程散文研究的成果和他南疆散文书写的特点进行考察的话,便会发现二者之间在现代性的总体描绘中,还是存有一定的差异。以往的评论聚焦为刘亮程散文中北疆乡村世界中宁静和谐特征的分析。众多的评论均大同小异地指出:在北疆,刘亮程的创作实际上解开了乡村的神秘面纱,以别样的风景建构添补了我们对乡村世界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抵达乡村的深处,他也以自己生命的体验促使我们对十分熟悉的家园重新进行定义,乃至确认,也就顺应地得出黄沙梁是现代与传统交锋过程中的“乐园”这一结论。我们发现,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误读。比较契合刘亮程散文世界的意义应该是北疆与南疆的倒置,他对南疆的书写更接近家园的最后作用,在北疆乡村书写过程中的所谓宁静与和谐在南疆乡村中才是现实的存在。如《通往田野的小巷》中提到,库车农民就与他们的民歌一般在长久的岁月中缓慢积淀着生活的淡然,即使是库车的毛驴也“一步三个脚印”[4]75走在上千年的乡村道路上,人与驴都按照自在的悠然状态行进着,再漫长的道路,再紧要的事情,都不会改变这种舒缓的节奏。在新疆,维吾尔族人在现代喧嚣中对古老传统的坚守令人惊叹:“人类先发明了坎土曼,然后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得到启示,把坎土曼的头扳直,变成了现在的铁锨。但库车人为何把坎土曼这个古老工具坚守到今天,使用几千年……几十年前,工厂生产的坎土曼也曾大批运到南疆,试图取代铁匠铺的手工坎土曼,可是,那些坎土曼没卖出几把,哪来的,原回到哪去了。”[4]137-138
刘亮程指出坎土曼是经过铁匠用传统的制作方法“一锤一锤地精心打造一件器具时”[4]138,心中升腾起的是对物件的崇敬,也不由自主地在内心中构建起包含深情的图景,物与情是统一的。还需明确的是在悠然与坚守背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也存有焦虑,不同于乡村结构瓦解后根的追寻,他们的困惑是指向未来的,不是空间层面的现代性,而是关乎时间历史上的现代性。
“新疆时间”成为刘亮程回到创作意义的起点。“新疆时间”的称谓揭示了“何地”与“何时”的关系,“何地”实际上就区别了普遍使用的北京时间,使之具有了某地的特殊性,成为一个属于自我定义的区域时间,赋予了行动范围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更重要的是为时间添置的方位修饰语,也就从物理时间进入到心理时间,以此遮蔽或试图抗拒普遍、统一的行为,为“落后”“慢半拍”等获取了可资慰藉的托词。在《新疆时间》一文中,刘亮程直言“新疆一直存在着两个时间”[4]191,这句话的意义在于区别时间概念,表明了不同人群对待时间的态度。用我国通用的北京时间试图保持的是一致性,“它意味着,事或者人,按照时钟和日历的共同标准,具有着时间上的一致性。就是说,现在,人们是按共同的时历标准,来判断他人和事件与他的同时性[6]118”。用新疆时间一则是上千年的传统生活习性使然,也是保持自我的独特性。因此,“新疆给了我一种脱离时间的可能,一直向后走的可能”[4]191。这种可能性意欲在已经变为一致的时局中逆向而行,希冀保持着地方性的差异而做出努力,背后的意义分明指向了回溯性的族群崇拜,这种崇拜的心理抚慰在于:“人在追逐蕴含现代性的生活价值之同时,维持了一种关于根的想象,不至于因为在地理上或文化上已经离乡背井,而变得空虚彷徨。”[7]而南疆的时间,似乎停住了,时间流程中主体的不愿变动,或者缓慢接受变化的特点,时间的纵向变为了横向。亘古如斯的传统农商文明致使当地民族在现代化面前重新检验和重新界定自我民族的关系和认同时,对待历史与文化遗产的态度同短时期短岁月中的情感体验是不同的。尽管在“新疆时间”慢半拍的节奏中形成的均是一种回溯机制,但是在根或起源的问题上,带有明显区隔,无根焦虑同生存的去根产生的是“无”与“有”的矛盾,换言之,即是历史的虚无与实有层面上的矛盾。由此可知,刘亮程在关于南北疆的散文中,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情感态度,即浅陋与深沉的情感体验对位,个体的孤独与群体的光荣怀念所依附的“新疆时间”最终也会在要求一致性的现代性面前轰然瓦解。“几千年的土,一时间全落下来”将历史的终结毫不客气地展示在我们面前。面对“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所有人”[8]的现代性,“新疆时间”注定也是无效的。
总而言之,刘亮程苦心营造的乡村生活图谱,既是他本人作为移民的体验,也是他观察审视新疆南北疆乡村生活所思,尤其是南疆的书写,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却又融入到民族文化中予以了真切地揭示,这种写作的姿态实属难能可贵。可以说,移民者的刘亮程正试图抹去身份标识,进行着内部自我的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