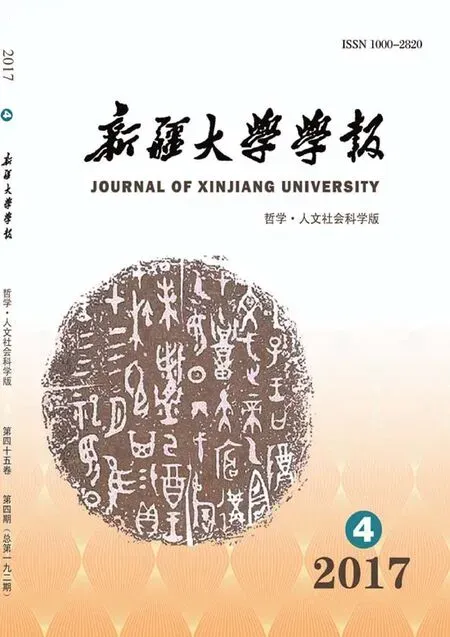学衡派借力新人文主义的尴尬*
2016-02-18李巍
李 巍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学衡派的文学主张便是《学衡》之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寥寥数语,便可在国粹、中正、无偏等字眼中辨出学衡身上的传统文化色彩。由此不难揣测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要特色,诸如:反对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译介,张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以及专门的国学中经史子集的专题研究,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佛教研究的专题论文[1]9-10。但就其在《学衡》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数量、质量以及影响来说,主要兴趣还是集中在第一点上。第一点特别彰显了对当时主流思潮的反驳,学衡派与当时主流思潮自然也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一点也被公认为是学衡派沉寂几十年的原因。
尽管与主流思潮相左,但学衡诸君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知识不可谓不渊博,对自己理论主张的论证不可谓不周密,为什么他们那些关于诗歌、文学的主张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引起什么巨大的波澜便很快复归沉寂,仿佛被历史遗忘一般。“从总体上看,学衡派于小说少有创作的实践,但是却能多诗,吴宓、吴芳吉、胡先骕诸人且有诗集行世,更是颇有造诣的诗人。所以,毫不奇怪,他们对于中国新旧文学的见解更多的是集中在诗的问题上,而且更不乏值得重视的见解。”[2]202尤其是学衡诸君不仅对于西方思想十分了解而且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所以他们不缺乏所谓西化的思想,更不缺乏中国古典诗歌所需要的一切技巧和功力。学衡之主张与主流思潮格格不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学衡之主张势单力薄无人摇旗呐喊也是无可非议的存在,而这些都与新人文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又或者说是因为新人文主义的介入更加阻碍了学衡派文学主张的传播和被接纳。若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讨论学衡派的诗歌理论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关系。而在此之前还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学衡派的诗歌理论主张有哪些?第二,为什么学衡派要选择新人文主义作为其诗歌理论上的哲学依据和支撑。
一、学衡派的诗歌理论
学衡诸君对诗歌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文学有“常”有“变”
不同于胡适等人把文言和古诗看成死了的文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古诗词依然有其价值存在,因为这些诗歌里面都蕴藏着一些永恒的因素,即他们所说的“常”或柏拉图所说的“一”。这个“一”的存在便是他们昌明国粹的重要原因。
学衡派昌明国粹的理由有三:“第一,新旧乃相对而言,并无绝对界限,没有旧就没有新。第二,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不同,不能完全以进化论为依据。不一定‘新’的就比‘旧’的好,也不一定现在就胜于过去。第三,历史有‘变’有‘常’,‘常’就是经过多次考验,在人类经验中积累下来的真理。这种真理不但万古常新,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3]不难看出,其“常”“变”之论酷似刘勰的“通”“变”之说。
他们一致认为从根本上说诗无所谓新旧之说,只有真伪之说。他们认为自己反对的是无病呻吟的伪诗而不是新诗,拥护的是真情实感的真诗而不是旧诗。
(二)新诗之新在内容而在形式
既然他们反对所谓伪诗而非自由诗,那他们必然有自己关于诗之为诗的见解。事实上,他们确实提出了自己的“新诗”概念,认为新诗之新在于内容而不是形式。如吴芳吉提出来的“诗的自然文学”以及“两种新诗”的观点。“诗的自然文学”意指诗乃人类情感的产物,只要是充分表达了人们的感情同时又赏心悦目的诗都是好诗。吴芳吉之好诗显然参照古诗标准而来,自古华夏的诗歌都以情感见长,从毛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到清朝袁枚的性灵说以及王渔洋的神韵说,无不是此种理论的拥趸。西方自然也有一切好诗源于自然情感的流露这种诗学主张,但西方浪漫主义的情感,是狂飙突进的,是大声疾呼的,是自由奔腾的,与我们带着中和味道的赏心悦目相距甚远。骨子里依然是中国内蕴的“诗的自然文学”说明,诗歌的好坏其实是跟白话、文言没有关系,因为不存在所谓的文言感情和白话感情之分,这其实是将内容与形式相分离。而“两种新诗”更是将新诗分为两种然后表明自己的诗歌主张。第一种是欧化的用白话作的新诗;另一种是将欧化的东西引入旧形式之中所做的文言诗。吴芳吉曾这样说过:“余所谓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故新派之诗,与余所谓之新诗,非一源而异流,乃同因而异果也。”[4]
吴宓则将文言诗和白话诗的争论转变为新诗体和旧诗体的争论。吴宓以材料和形式为标准将诗歌分为四种,一是旧材料旧形式,二是旧材料新形式,三是新材料旧形式,四是新材料新形式。他认为自己所做的诗属于新材料旧形式的诗,而名震宇内的徐志摩选择的是新材料新形式的诗。但吴宓认为自己的诗与徐志摩的诗在根本上是一样的,正如他所说:“虽彼此途径有殊,体裁各别,且予愧无所成就,然诗之根本精神及艺术原理,当无有二。”[2]205
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是有大量实践的,《学衡》杂志上曾发表过大量的旧体诗,但是内容毫无疑问是表达现代人的一些情思,例如有歌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这类诗的代表有吴芳吉的《巴人歌》;有抨击当时黑暗政治的,这类诗的代表有王越的《蒙师之死(示众)》;也有表达诗人忧国忧民之思的,这类诗的代表有吴宓的《壬申岁幕述怀》四首等。
(三)无格律何以成诗
通过学衡派对于新诗的界定来看,旧的形式自然可以表达新的思想,这也算是为古诗特别是为古诗格律的一种辩护。当然他们也强调诗歌是要变的,例如吴芳吉曾说过传统的诗要适应当今的时代至少在三个方面不可不变:其一,今世民国,为诗应有民国的风味,面不同于汉魏唐宋,“此格调不能不变者也”;其二,传统的诗虽包罗宏富,但除少数人外,难免四个共同的毛病,“贪生怕死,叹老嗟卑”“吟风弄月,使酒狎倡”“疏懒兀傲,遁世逃禅”“赠人咏物,考据应酬”,面处今之世,当有共和国民高尚优美的品行和适应开明活泼的生活,“此意境之不能不变者也”;其三,诗贵有学,明体达用,今之学诗者,往往以故事为典雅,以僻奥为渊博,以出处为高古,以堆砌为缜密,不知文学艺术为何物,“此辞章之不能不变者也”[2]203。但是这些变显然还是指内容的变化,不是形式的变化。吴芳吉并不反对新诗,他认为诗的发展应该是多元的,当时兴起的白话诗只是丰富了诗歌表达的一种形式而已,并不能就此取代中国古典的格律诗体。他们将诗歌的形式和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分开来看,认为两者是可以分开的,所以他们强调的新诗一直都是不废格律的。
事实上其他人把诗歌的格律看得非常之重要,甚至认为格律是诗歌不可或缺的成分。吴宓给诗的定义是:“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或笔法具音律之文,或文字表达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5]62在对文与诗的比较中说:“今进而论其外形之差别,即诗必具有音律(metre),而文则无之也。然文与诗皆有节奏(rhythm)。”[5]69他还说:“作诗之法,须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即仍存古近各体,而旧有之平仄音韵之律,以及他种艺术规矩,悉宜保存之,遵守之,不可更张废弃……镣铐枷锁之说,乃今之污蔑者之所为,不可信也。至新体白话之自由诗,其实并非诗,决不可作。”[5]97可以说,吴宓在此表达了诗之为诗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具备音律。而且坦率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所谓自由诗压根就不是诗,鲜明地表达了诗歌格律的不可丢弃。
单从学衡派的诗歌理论来说,它最能体现的是一种中国的中庸哲学,而且其理论之源泉明显与中国古典诗学脱不了干系。他们一方面要求昌明国粹,一方面又强调要融化新知;他们一方面强调传统诗歌有变化之必要,同时又声明格律的不可变化。有趣的是他们不同于闻一多,虽然闻一多也强调诗歌要有格律,但是这个格律可以不同于古诗词格律,是一种适应白话新诗的新格律。而学衡派所强调的格律一直都是中国旧有的诗词格律,认为这是诗歌传统所积淀下来的具有永恒性质的精髓,因此不可废除。从他们的诗歌主张来看,如果他们以中庸之道作为自己的哲学依据并不是不可,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舍近而求远,这么大费周章地跑到美国去寻找新人文主义呢?
二、学衡派为什么要选择新人文主义
学衡派选择新人文主义而不用中庸之道是有原因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理论主张的契合
新人文主义作为当时西方社会的一股哲学思潮,它所要传达的理念与学衡派君的主张正好有重合一致的部分。新人文主义主张人性的二元论,人性中存在着善恶之间的永恒斗争,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能够抑恶扬善以理控欲。主张理智反对科学主义和浪漫主义。白璧德认为这些都流于自然主义、机械主义,而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着自己的一套“人事之律”要遵守。所谓“人事之律”就是一种以理制欲的道德观,所以新人文主义也反对人道主义的无差别的泛爱,主张有选择的同情。这些观点与儒家中庸之学说甚是贴近。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概括来讲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多’融合的认识论、‘善恶二元’的人性论、以理制欲的道德实践论。”[2]47“一”和“多”是柏拉图提出来的概念,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至善的理念和繁复多样的具体事务。其二是指集约、纲纪与博放、自由。柏拉图、白璧德都强调两者的融合是十分重要的,二者缺一不可,否者都容易造成不良的后果。
这些理论正好让学衡派诸人找到了昌明国粹的理论依据,并以此来支持他们关于诗歌理论的主张。中国古典诗歌强调格律的重要性,格律本身正是以理制欲的体现,中国也有“发乎情止乎礼”的深厚传统。这诗歌中的格律自然也可以被解释为“一”了。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明为什么旧格律就是那恒久不变的被继承下来的精髓,这无非还是学衡派借新人文主义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而已。学衡派诸君有很多都是国学班出身的,同时也是旧体诗的高手。面临新诗不断占领他们才能发挥的领地,他们自是无论如何也要抢回阵地的,新人文主义就是夺回阵地的一件有力武器。
再看自由体的白话新诗,可以说毫无顾忌,漫无节制,以胡适为代表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白话自由新诗渐入极端。这一点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里面所提到的作新诗的八个不要中可以看出,这正是一种只讲“多”不讲“一”的体现。而郭沫若所代表的浪漫派新诗,更是在白话自由诗的激流之上,让内心情感得到更加肆无忌惮的猛烈喷发,这种喷薄激荡的情感完全不符合以理制欲的新人文主义,也严重背离发乎情止乎礼的传统规范。这恰恰是学衡派深恶痛绝的,而新人文主义的某些观念又正好为此反击提供了理论支撑。“白璧德崇尚古典主义,主张遵守文学的纪律,反对卢梭之后的浪漫主义。这对胡先骕及《学衡》同人有直接的影响。”[1]156
再者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白璧德对孔子和佛教很是推崇,使得学衡派诸人感到尤为亲近。但需要说明的是学衡派绝不是纯粹的守旧派,从他们的诗歌理论来看,他们并不反对现代思想内容的表达,诸如民主科学等等。他们既要保存我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又要同时吸纳国外文化中那些历久不衰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他们所要达到的是中西贯通而不是所谓复古,事实上他们与国粹派是水火不容的。他们也求变革,但是不想通过马克思式的、激进的、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而是渐进的。他们相信精神层面的改变不可能靠革命而瞬间改变,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管怎么说新人文主义思想与学衡派主张相契合这点是学衡派选择新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中国固有文化陷入一种认同危机
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当时的思想家们都纷纷将这种罪孽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学说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由于当时环境的刻不容缓,又由于经历了经济技术救国和政治制度救国的失败后,中国人急需用一种革命的、激进的方式快速地推翻之前的旧有文化,所以新文化运动要求变革的呼声便占据了主流,并且由于其急于求成所以难免有失偏颇,流于简单化。不管怎样,当时之国粹派、复古派,在世人眼中不仅有落后之嫌更有冥顽不化之意,甚不得人心。这种对文化的不认同必然会连累到文学,所以当时大多数的文人学者对于文学也是采取一种激进的革命态度,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任何与之沾边的都有被抨击之可能,连汉语本身都未能逃脱这种激进的责罚,许多学者甚至觉得中国的文字最好也不要了,拉丁化的字母才是进步的象征,更何况想要守住古诗词格律的学衡派。
这种对于整个原有文化的激进、否定,让一些想保存中国文化精髓部分的学者不得不从外部寻找理论依据。学衡派诸君便是如此,他们有心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却又不能从早已人人喊打的传统文化中寻求其价值的支撑,所以只能求助于外国的理论,而新人文主义便在这种时候出现。
虽然学衡派的诸君并不是复古主义者,他们也反对那种令人讨厌的复古调子,但是他们所要表达毕竟是一种渐进的、改良式的文学发展路子,特别是他们对于中国古典诗歌里旧格律的继承和强调更加剧了与主流思潮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可以拿此后不久的闻一多做比较,闻一多是中国白话新诗新格律的主要倡导人之一。闻一多主张诗人应该是戴着镣铐跳舞,要作有格律的诗歌。尽管他的音尺理论是来源于西方,但是他的诗歌理论却并不是完全西方的,其中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也是很明显的。可是为什么他们这些人的新格律诗歌就可以传遍大江南北,影响范围遍及九州而学衡派的诗歌却不能呢?学衡派诸人的诗歌并不缺乏现代人的情思,也不是没有艺术美感。这主要是因为闻一多的新格律诗已经摆脱传统,有着与中国传统诗歌不一样的诗歌形态,另外就是他的音尺和格律是新世纪之音尺和格律,完全不同于古代,极为重要的是这些主张的理论支撑都是来自西方。
而学衡派诸君强调中国传统中的精华精髓部分要原封不动地保存,不能丢弃,这当然要与当时主流意见相左。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主张破旧立新,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主张弃旧立新,就凭他们对于旧的态度便能够得到一大批的信徒。所以学衡派就不得不绕个弯,以一种西方的思想来论证自己诗歌理论主张的合理性,这可以说是一种迫于形势的压力吧。
(三)新人文主义思想的西方身份
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庸作为儒家哲学的一部分在当时已经被知识分子阶层视为要抛弃的文化糟粕了。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流派还是自由主义流派对传统儒家文化都是持着鄙视的态度,中国整个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处在一种反对儒家文化的狂热之中。所以如果学衡派明目张胆地将中庸之道作为理论主张的哲学依据,不但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反而会带来巨大的麻烦。
中国当时已经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屈辱了大半个世纪了,国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到极大打击,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是又恨又敬,一方面恨他们对我们的欺辱,另一方面敬他们比我们先进。整个智识阶层无不把西方作为学习的对象,都想从西方社会寻找到治国救民的灵丹妙药。所以在当时很多人都提倡西化甚至全盘的西化,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无不唯西方马首是瞻,仿佛只要是西方的就一定是好的。不难想象,当学衡诸君在哈佛大学听到白璧德颇具复古、中庸内核的新人文主义时那种内心的激动,在先进的西方找到保存国粹的新知,安能不趋之若鹜。所以借用新人文主义这样一个西方的理论做学衡派诗歌理论的支撑会更有影响力,也契合当时人们崇欧的心态,同时也表明了他们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宗旨,所以干脆就引进美国的新人文主义思想。
第二点与第三点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当时没有对中国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出现认同危机,即使新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西方思想,学衡派诸君也不一定就会选择它来作为自己理论的哲学支撑,我想顶多是把它引为同道罢了。同样,如果新人文主义不是来自发达的西方社会而是来自印度或者非洲,即使中国出现了文化认同危机,即使它与学衡派的理论主张有相似之处,它也不一定会被学衡派成员拿来作为自己理论的哲学支撑。
三、新人文主义为什么
没能助力学衡派得到普遍认同?
(一)崇古与革新相左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一直在大规模全方位地否定传统。也就是说当时能与国人相适应的思想不在于新旧而在于立意是革新还是崇古。新思潮也可以是崇古的,如新人文主义。旧思潮也可以是革新的,如浪漫主义。新人文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崇尚古典主义,尤其是其代表人物白璧德对于佛家、孔子以及印度哲学的推崇。虽说这一点更符合吴宓、梅光迪等人的诗歌主张,但依据当时中国的情况,与崇古相比,革新显然更能符合其思想品味。任何带着革新思想倾向的理论都更容易得到国人的支持。而虽然新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但其本质是向古的,这点很难与当时中国思想界那种革新的急迫相调和。本已在发力点上与中国思想界背道而驰,白璧德又对佛教及孔子露骨推崇,而儒家在中国当时之名声,早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此这般,又怎么可能让学衡派树立什么正面形象呢。
新文化的主将胡适在刚一开始主持新文化运动之时也是相当激进,他甚至说文言古文都是死了的文字,在当今时代应该用活的白话来做文章。但是之后他受到学衡派等其他人的影响又转向倡导所谓整理国故,却被大家一致指责为落伍份子,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与激进的革命派意见相左的下场。无论是以何种形式来倡导中国古典的传统的东西都会被视为落伍的、不可接受的,即使是套个西方理论的马甲,也是于事无补。
(二)非战斗本性难以契合国人品味
学衡派强调的融化新知,新人文主义的借鉴古典,都是指向中西方文化中那些永恒的、万古常新的东西,但这些万古常新的东西毕竟年代相隔甚远,虽都是西方先贤圣人之语,但毕竟都是过时的理论,而当时的仁人志士并不能直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治国救民的方法,就算有也太难带入。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包括诗歌在内的许多文学文化形态视为一种工具,一种可以救国救民的工具。像梁启超的欲兴一国之国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观点,便是将小说作为一种工具来用。还有胡适、陈独秀等人也都是将诗歌小说等看成变革社会的工具。而左联的崛起更是直指文学的现实介入功能和强大的政治鼓动性。而学衡派的整个理论都是远离政治的,新人文主义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仅是可以作为哲学理论引导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可以应用到文学领域进行文学批评,还可以作为一种强大的国家政治理论为国家的未来提供一条出路,这正是其政治性、战斗性的体现,这也正是当时的国人所迫切需要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就算是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言,其依然是一种直接介入现实的姿态。现实主义自不必说,浪漫主义的战斗精神和自由本色都是中国人救亡图存所急需的东西。就连现代主义的文学也都隐藏着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批评,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文学式反抗。所以整个现代文学都是在充斥着救国救民的主题之下展开的,任何偏离方向的行动都有可能被视为不务正业。而学衡派抄起新人文主义的大纛,不温不火地搞起人性论,那中国之现状何时得以改变,中国之惨状何人能去收拾。这种没有契合战斗性、政治性的理论主张自然得不到大家的好感。
(三)格局太小,上限已定
有一点值得强调,学衡诸君并不是因为受到了新人文主义强大影响力的波及(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席卷欧罗巴一般),进而拜服在白璧德的门下,而是因为新人文主义与学衡诸君的原有主张有一致的地方,当他们偶然得知新人文主义之后,便如获至宝般地去介绍新人文主义并把它当做自己理论主张的一种哲学支撑。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人文主义远没有像当时其它的思想那样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力,例如当时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已经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思潮,影响巨大。胡适所推崇的杜威、罗素的哲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巨大影响力。而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力与前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它的影响更多地限于当时的美国哈佛大学以及白璧德的门徒们。可以说不是白璧德塑造了学衡思想,而是某些已经形成的想法使学衡诸君主动亲近了白璧德。
所以新人文主义虽然是应时而生的一股新思潮,但是囿于它本身的影响力范围,在其指导下的学衡派在中国的影响也已注定了上限。
(四)人所丢弃正是我欲所得
虽然新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与时代同进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在中国却是极不合时宜的,中国当时所缺少的正是新人文主义所要极力抗拒和反拨的。所以单从这点看,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已经不是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学衡派得到认同了,而是新人文主义到底能不能帮助学衡派得到认同,它底是起支撑作用还是作阻碍之力。
新人文主义在西方的发端自有其理所应当的背景,它发端于对理性主义漫无节制发展的反抗,意在抵制工业文明之下人欲的不断扩张。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揭示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无节制的发展,人欲的无限制膨胀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沉重灾难。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就是在这种时代的背景下产生,它是在伤痕累累之后所酝酿出的回归之花,当然是向工业文明之前的克制回归。
很显然它本身也是对当时主流思想的一种反驳,这种思想包括以卢梭为代表的感情的浪漫主义和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而中国自古就没有这两种思潮,也不存在这两种思潮的大发展,更不存在这两种思潮因之而起的工业文明基础,相反国人正缺少这样的思想。国人依据深信不疑的进化论原则(物竞天择适者生),还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西方文化正在反思的东西。尤其是科学主义思想在民国初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其新鲜的,也是十分先进的。中国刚刚摆脱落后清王朝的统治,很多知识分子还在科举制度阴影的笼罩下没有走出来,还如孔乙己般地生存着,中国的思想完全没有启蒙,民智尚未开化,更奢谈其无节制的发展了。在还没有走出第一步的情况下就想走第二步无疑是行不通的,而学衡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本该在中国工业化大发展之后才该有的思想提前上百年与国人见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人把学衡派贴上复古派的标签并对之大加挞伐也是情理之中的。太超前和太落伍的东西都是不能引起人们共鸣的。
四、结 语
学衡派的诗歌理论固然有很多在当代都可资借鉴的内容,尤其是学衡派主将们渊博睿智的辩解论述更是让今人敬佩。但是其理论主张的哲学依据与当时的时代相悖,时代要求激烈的战斗情怀,挽救危楼于水火,学衡却讲起克制的律诗节律,慢条斯理地以理制欲。新人文主义产生于西方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而中国在当时并不具备这种大工业充分发展的时代背景,只是刚刚走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皇帝的幽灵还一直在闪现。其所需要的正是一种十八世纪发生在西方世界的启蒙运动,而学衡诸君却直接越过这些台阶,进入超前的阶段,自然不能被理解。所以导致本意是要借力西方理论作为后盾,最后却反成为了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