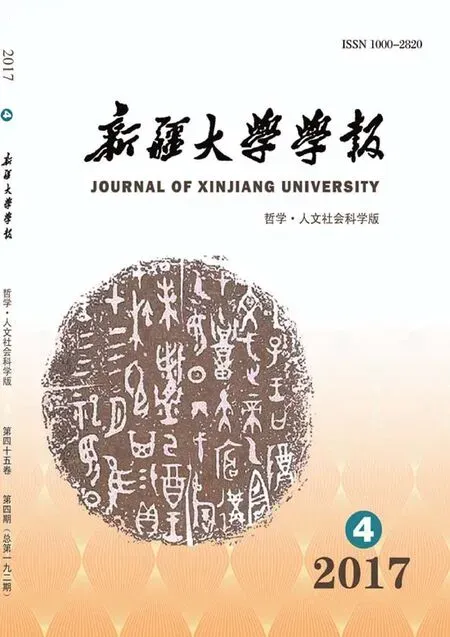居民幸福感研究评述
——基于测度方法、影响因素与区域实证的视角*
2016-02-18朱金鹤王军香
朱金鹤,王军香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0)
幸福感是由满足感和安全感主观产生的欣喜与快乐的情绪。近年来,学界对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取向——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且大部分学者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人通过情感和认知,根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而心理幸福感倡导者则认为幸福不仅仅是快乐,更是自我实现与人生意义的自主、能力、需求的一种满足感[1-2]。
幸福感因地域、宗教信仰、群体习惯、经济状况、社会结构、资源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对幸福感的研究百家争鸣。有鉴于此,本文从幸福感的内涵、测度方法、区域实证分析、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等方面,展示现有研究的最新进展,识别当前研究现状的不足之处,厘清居民幸福感研究线索,以期对未来幸福感的研究有所启示。
一、理论研究:前沿理论动态
古希腊早在几千年前就对“幸福”产生了兴趣,但相对西方学者,我国对幸福感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学者才开始对关于居民生活质量的幸福感进行关注。对于幸福感这一概念,从政策制定者、各学者到普通大众都在对其加以完善。虽常被视为人们对自身生活境况的状态描述,但它的概念尚缺少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定义。归纳起来,学者们主要从快乐论与满意度、各学科角度来阐述它的内涵。
(一)快乐论与满意度
对于幸福感内涵的研究,国外学者是从快乐论角度切入的。有学者认为,快乐与实现依幸福的取向不同而不同,快乐并不是幸福的全部内涵[3]。然而,Kahneman D,Diener E,Schwarz N却提出不同意见,他依据快乐心理学原理,认为幸福感是试图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快乐,因而快乐与幸福感在一定意义上是等同的[4]。在追求个人目标及感受快乐的同时,King L A,Napa C K将幸福感理解为“快乐”和“意义”的有机统一[5]。Diener认为,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两个基本成分的整体评价。前者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满意判断的程度;后者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绪体验,包括愉快、轻松等和抑郁、焦虑、紧张等两方面[6]。
(二)不同学科对“幸福感”内涵的异样理解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幸福感的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调查研究便层出不穷地出现。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逐渐渗透到心理科学,幸福感研究温度骤升。我国大部分学者对幸福感的理解侧重于从三个学科角度入手:
1.心理学角度。幸福感是对生活满意度和个体情绪状态的一种综合评价,是人们对自身生存质量的关注和感受,并与乐观、适应性、焦虑与抑郁等心理健康行为密切相关。有学者以个体生活质量满足程度为出发点,认为幸福感是一种包括对生活质量认知的、自我认同及欣赏的、反映人们对自身生存质量关注的主观感受的综合评价[7]。对于幸福感的情感与认知成分而言,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综合体现了个体的生活质量[8]。
2.社会哲学视角。最具代表性的是邢占军的体验论主观幸福感,他对生活质量意义和心理健康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的理解主要在于两者的差异性,他认为前者在于社会群体体验,而后者多考虑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个体体验[9]。有的学者尝试整合主观幸福感(SWB)与心理幸福感(PWB)的概念框架与测评指标,建构综合的、统一的幸福感理论框架,并提出幸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快乐与意义的统一、享受与发展的统一[10]。幸福感同时也与主体行为的感知相契合,也是基于主体同一性的个体幸福感。
3.经济学角度。学界对幸福感的经济学研究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等基础之上的,一般聚焦在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11-12]、主观幸福感的测度及指标可靠性、幸福经济学理论等角度[13]。其中,在城市最优规模设计方面,金琳通过引入中间变量(人均收入、政府财政支出、图书拥有量、教育机会和交通状况)的计量方法,130个样本城市的居民幸福感与城市规模进行分析,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14]。在政策含义的阐述方面,赵婉君以心理学“幸福跑步机”为核心理论,以财政支出为切入点,探索政府经济行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提出政府应制定关注民生、关注人类幸福的柔性政策的观点[15]。梳理文献可发现,经济学领域的幸福感研究分三部分:一是幸福感指标体系的构建;二是对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影响因素的评价分析;三是各分类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二、居民幸福感的量化:社会调查、数学建模与主客结合
在幸福感的测度方面,由于研究者的思考角度不同,因此采用的测度方法和模型也有所不同。现有文献的幸福感测度与指标体系选取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社会调查:幸福指数量表、调查问卷及访谈
对居民幸福感进行社会调查,是一种有目的、可靠性高的、能够真实反映居民幸福感水平与影响因素的有效途径。有学者通过构建幸福感量表体系以问卷调查、统计评估形式来对幸福感进行测度[16];Watson,Clark和 Tellegen编纂的《积极、消极性情绪量表》及Waterman A S编制的《人格展现问卷》等,均从心理学角度借助统计学工具对幸福感进行量化[17-18]。多数学者认为,问卷调查更能反映居民对幸福感的需求、群体特征及社会状况。如陈惠雄从六个方面16种指标,对浙江省居民展开大规模的幸福感问卷调查[19];邢占军在体验论主观幸福感的基础上,编制了一个包含54个项目、10个分测验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验证了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由身心健康体验和享有发展体验两种成分构成。随后,该量表被用于城市居民中的一些特殊群体,例如老年群体、青年群体、女性群体、大学生群体、研究生群体、教师群体以及农村居民,都具有良好的测量学特性[20];还有学者通过对幸福指数指标构建体系及测量表编著方面的研究,认为指标考核方面主要涉及经济社会结构、自然环境状况、安全保证系数、人际关系状态、家庭氛围情况、公共服务水平等[21-22]。
(二)数学建模: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
许多学者通过构建幸福指数测评模型和函数方程的形式对幸福感进行量化测度,主要模型包括个人效用函数[23]、福利函数[24]、阈值效应的模型[25]、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26-28]、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收入方程[29]、回归树方法[30]及日重现法[31]。其中,在以“攀比理论”为基础的个人效用模型中,田国强测出个人效应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达到某个临界值后,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刘米娜、杜俊荣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住房不平等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住房的绝对不平等是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同时住房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向关系,而住房面积对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型分布[32]。还有学者通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湖北省武汉市、宜都市和神农架林区三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33]。
(三)主客结合:幸福指数构建
将主客观因素结合后合成幸福指数的方法在经济学幸福感研究方面有较多突破,具体操作将指标按主、客观决策层进行分配处理,这样有利于将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有效的结合起来,更具科学性。苏绮凌、陈文科也支持此种测度方法,并从幸福感的基本内涵出发,紧扣政府可作为为目标,构建了一套由11项评价领域34个评价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对2013年海南居民幸福指数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4]。
三、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影响因素剖析与区域实证
在提升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方面,学者们意见各异,大部分人主张从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增长[35-36]、收入[37-39]、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主体职能[40]、年龄、婚姻、职业(邢占军,2011)等因素方面对幸福感展开测评。总体而言,居民幸福感与收入分配、群体对象关系密切,具体如下学者们的研究:
(一)因素剖析:收入分配与群体特征
Stevenson B,Wolfers J认为,幸福和收入在达到一个相对饱和点之前大致呈正向的线性关系[41],可以认为经济收入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42]。相反Sacks D W、Stevenson B等根据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新程式化事实研究表明,不存在所谓的收入与幸福的饱和点[43]。总之,对于人类而言,攀比心理是人之常情,因此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自然地成为幸福感提升的制约因素,而相对收入更为甚之。例如:Applasamy V等通过对照组实验发现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呈正效应[44]。Becker G S,Krueger A B;Frey B S,Gallus J,Steiner L也得出相应结论,认为幸福感来自比较且与相对收入有关[45-46]。Easterlin提出“伊斯特林悖论”,他认为发达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收入提高缓慢,甚至停滞所以形式收入的增加不会增进人们的主观幸福[47]。
但同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异。(1)以老年人群体为例,薛新东、程明梅从养老制度、健康教育、医疗卫生、休闲活动等方面,对农村、城镇老年人进行不同程度的幸福感提升研究[48]。(2)以农民工群体为例,邵雅利、傅晓华采用对比分析及时间序列方法从婚姻、文化水平等方面对新时期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并对农民工生活质量的提升方向进行预测性的阐述[49]。(3)以农村居民为例,有的学者(李小文,黄彩霞;2014)应用序列逻辑回归的统计方法,从社会比较理论的视角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进行了论证与分析,得出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的有婚姻状况、年龄等个体因素和与朋友亲密度、生活纠纷等社会因素的结论。居民的性别、年龄、学历和家庭所在地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于飞、王会强从农村政策、家庭生活、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四个维度对河北省农村居民进行调查,并证明了这一点[50]。(4)以学生群体为例,性别、年级、独生子女情况等方面的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5)以城乡居民综合群体为例,顾杰、魏伟等(2015)通过统计分析,认为社会人口学特征、兴趣爱好、压力应对方式、未来目标等是制约十堰市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
(二)区域居民幸福感实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关于农村农民幸福感的研究
国内对幸福感区域实证的研究首先是从幸福城市的评选开始的,并出现多元视角下对幸福社会的探讨,随后在对区域幸福指数的对比分析,找寻区域幸福感影响因素中,对农村地区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尤为热门[51]。李想、李秉龙等利用对北京、辽宁和河北三省市调查获得的1 033个农户样本,分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其中,得出收入、年龄、健康状况、对合作医疗满意度等因素对所有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均有正向显著影响的结论[52]。还有学者基于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的农民幸福指数调查,从家庭收入满意度、物价满意度、邻里关系、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自己的身体状况、执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分析当前影响农民幸福指数的因素,并指出提高40~59岁青壮年的幸福指数,将有助于迅速提高当地农民的幸福感[53]。Petrunyk I,Pfeifer C通过德国居民家庭收入和失业状况等生活满意度的东西差距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54]。
2.关于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研究
有些学者聚焦于城市公众居民幸福感的测评与比较。赵峥、宋涛以绿色发展为视角,从内外因素出发发现长三角各城市居民的绿色发展幸福感差异显著[55]。也有学者对幸福感与满意度的对比感兴趣,卢扬帆(2014)从主观幸福感内涵出发,借鉴罗纳德·英格哈特范式,采用层次分析法及专家咨询调查法对全国7个省市及广东省的民众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公众主观幸福感(感性幸福)与现实生活质量满意度(理性幸福)存在明显反差的结论。徐延辉、黄云凌通过对城市低收入居民绝对贫困与相对收入的比较分析也得出类似结论[56]。
3.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的研究
在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方面,王曲元对云南丽江、甘南夏河和北京密云地区的居民幸福感采用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他认为,幸福程度并不与经济收入高低显著相关,人们是否幸福,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谐,生活环境的舒适等因素[57]。张爱萍认为,应实施教育优先、医疗提质等方面确保博州、巴州蒙古族居民的幸福感提升[58]。
在对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及少数民族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幸福感影响因素、居民满意度测评、幸福感水平的测度等方面。其中,张爱萍、刘敏以伊犁州600名柯尔克孜族城镇居民为对象,发现居住隶属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住宅面积、家庭子女数、居住地、子女教育支出是影响该地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59]。申亚莉(2013)对兵团哈萨克族职工也做了类似研究。居民幸福感水平具体可借助幸福指数来测评,朱金鹤、李崇等将其分为机会、生活、经济、社会与环境幸福指数五类,并对兵团居民幸福指数进行测度,发现兵团整体幸福指数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态势[60]。
四、居民幸福感提升研究:对策与路径
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均具有社会发展的实践性,因此,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会涉及相应的政策建议及实现路径,基于此,对策研究便在幸福感提升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相关的对策建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物质基础:居民幸福感与经济社会包容发展
拥有财富不一定就拥有幸福,但是没有财富,生活在贫困中是一定没有相对持久的幸福的。因此,重视“幸福指数”,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GDP,恰恰相反,为了提高“幸福指数”,必须大力发展经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收入-幸福悖论”依然存在,但在经济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前物质基础(包括金钱、地位等)依旧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途径[61]。因此,经济社会发展是幸福的“根基”,经济富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只有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才能不断适应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类需求[62-63]。
(二)利益分配:居民幸福感与社会公平
多数学者将居民幸福感程度的差异归结为收入分配的不合理[64]、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就业的不公平等因素[65]。唐嵩林将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途径概括为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增收、改革工资收入分配制度、以税收调节行业收入分配制度三类[66]。这种观点被许多学者所赞同(董旭方,2015)。在对弱势群体幸福感研究方面,邹安全、杨威认为,就业和创业支持与保护及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培训对弱势群体幸福感提升很有必要[67]。
(三)政府职能:居民幸福感与区域协调发展
在行使政府权利,构建服务型政府以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学者们主要聚焦于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缩小城乡差距等内容。如罗泯强调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关键是缩小城乡、地区差距,因此,政府政策应当向弱势群体适当倾斜[68]。除了政府职责以外,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成负相关关系,陈工、何鹏飞对中西部、农村和低收入居民的损害程度出发发现民生财政支出规模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而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规模则会损害幸福感[69]。
五、结语:评述与展望
本文梳理了幸福感的跨学科前沿理论动态、幸福感的内涵、测度方法、影响因素、区域实证与提升对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动态,研究发现:居民幸福感的测度方法分歧较大,主要运用社会调查、数学建模、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亟待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的居民幸福感理论框架将多种方法有机结合;尽管幸福感不可避免地受到心理、价值观、群体习惯、宗教信仰等主观因素影响,但经济状况、分配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等客观因素才是居民主观感受的“助推器”,直接影响制约着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幸福感区域实证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而当前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对策研究多从经济手段、利益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等几方面展开,具有碎片化、局部化和“泛”相关性的趋势,迫切需要将居民幸福感与包容性增长、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密切结合,实现高屋建瓴、系统全局性统筹。基于此,本文对以往研究的不足与可延伸之处作以下总结:
第一,居民幸福感研究理论、量化方法存在一定的分歧。国内外研究多侧重在需求与体验理论、个体的主观感受、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缺乏对主观与心理幸福感内涵、主观与客观因素的统一整合。而幸福感的测度方法也多采用幸福感量表法,该方法易受人情感心理的影响,研究结果避免不了会因情绪波动或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票否决”式的偏差。因此,当前亟待建立一个完整的居民幸福感理论框架,同时将调查问卷法、静态分析法、动态分析法三者结合起来,既有利于理论与方法的融合,又为实证研究作支撑。
第二,居民幸福感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影响因素分析尚需深入。现有文献多注重对特殊群体(老年人群体、大学生群体、病理群体等)的幸福感进行测评,但各群体幸福感影响因素截然不同,甚至有些地区性的幸福感研究与特殊群体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确定有天壤之别。因此,如若对区域性的居民幸福感进行研究,各群体、各阶层、各区域的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确定需深入分析,以求达到求同存异的效果,这一点可能是下阶段研究的主要趋势所在。
第三,与居民幸福感相关的区域实证研究针对性相对薄弱。从目前学者们对于幸福感的区域实证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并不深入、系统。幸福感的研究本是与区域的协调发展密不可分,但目前多数研究焦点仍停留在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环境状况及主观幸福感测度方面,缺乏对区域协调发展机理的认识。而西部边疆地区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或从政府职能角度,或从社会包容性发展角度,抑或以和谐社会构建为视野,由此得出的结论虽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但均缺乏对特殊区情尤其是民族文化、边疆安全、贫困区真实需求的认知与分析。因此,在考虑居民幸福感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各区情可能更客观、符合居民幸福感提升的本质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