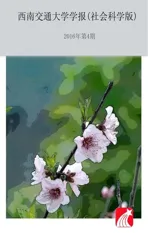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批评研究
2016-02-18张小璐
张小璐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批评研究
张小璐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关键词:赋学批评;《七十家赋钞序》;张惠言;创作论;文体论;历史批评;摘句批评;比较批评
摘要:《七十家赋钞序》是清代一篇重要的赋学批评文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这篇赋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学理渊源上,张惠言熔铸古今,继承了情因物感的创作论和诗为赋源的文体论,并将其熔铸在序文之中;在批评原则上,张惠言主要着眼于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和推尊赋体这两点;在批评方法上,这篇赋论主要运用了历史批评、摘句批评和比较批评。总而言之,从这篇赋论中我们可以观照出张惠言的赋学研究气魄。
张惠言,字皋文,江苏武进人,常州词派的领袖,也是阳湖文派的奠基人。《七十家赋钞》是他编选的辞赋选本,选录战国至北周的辞赋作家七十位,辞赋作品二百零六篇。《七十家赋钞序》①正是这部辞赋选本的序跋,它体现了张惠言关于先唐辞赋的观念,展现了清代学人的辞赋观。
《七十家赋钞序》不仅是一篇选本的序跋,更是一篇重要的赋论,引起了后代学者的高度关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诠赋》、王水照《历代文话》、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等著作中都完整收录了这篇赋论。那么这篇赋论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学界对此研究甚少。至今为止,只有李倩倩的《张惠言的学术传承与赋学思想——以〈七十家赋钞序〉为中心》一文对其做了研究。李倩倩主要基于骈文这个角度,认为《七十家赋钞序》是“清代学者骈文的代表作”,“显现了清代常州学者融合骈散的骈文创作理念”〔1〕。
本文将立足赋论这一文学类型,结合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知识,对《七十家赋钞序》进行新的思考。
一、《七十家赋钞序》的学理渊源
作为一位博古通今的清代学人,张惠言在学术研究上往往吞吐庞杂,熔铸古今。《七十家赋钞序》就是在吸收了前人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兼收并蓄、推陈出新之作。在赋论中,张惠言继承了情因物感的创作论以及诗为赋源的文体论,并将之与自己的赋学观完美融合,展现了一代学人贯古通今的学术魄力。
(一)情因物感的创作论
张惠言认为他所编选的《七十家赋钞》,“通人硕士,先代所传,奇辞奥旨,备于此矣”〔2〕。这部备辞赋一家之学的辞赋选本,是在一定的选录标准指导下进行的。
在《七十家赋钞序》中,张惠言首先提出了这一标准:“论曰:赋乌乎统?曰:统乎志。志乌乎归?曰:归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统乎情志,归于雅正”,这正是张惠言赋学观的主旨。
在序言中,张惠言论述了情志产生的机制:
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变化:天之漻漻,地之嚣嚣,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隹林木,振硪溪谷;风云雾霿,霆震寒暑;雨则为雪,霜则为露,生杀之代,新而嬗故;鸟兽与鱼,草木之华,虫走螘趋;陵变谷易,震动薄蚀;人事老少,生死倾植;礼乐战斗,号令之纪;悲愁劳苦,忠臣孝子;羁士寡妇,愉佚愕骇。有动于中,久而不去,然后形而为言。于是错综其辞,回啎其理,铿锵其音,以求理其志。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作家的感情不是主观产生的,它来源于外界事物的触发,即张惠言所说的“物之变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自然界的山川草木以及四时更替,“天之漻漻,地之嚣嚣……陵变谷易,震动薄蚀”;另一方面则是生命中的各种遭际,尤其是不幸的境遇,“人事老少,生死倾植;礼乐战斗,号令之纪;悲愁劳苦,忠臣孝子;羁士寡妇,愉佚愕骇”。张惠言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对情感的产生机制作了分析,可谓全面允当。但这种分析角度并非张惠言首创,它是对钟嵘《诗品序》中“物感说”的借鉴,现引文如下: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单衣,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娥?)入宠,再盼倾国。〔4〕
《文心雕龙·诠赋》云:“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只有因物兴情,才能义归雅正。张惠言强调情因物感的创作论,正是从源头上探寻雅正之情。
(二)诗为赋源的文体论
诗为赋源的观念来自汉人的诠释。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说:“学诗之志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馋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意。”〔5〕这是在间接说明诗为赋源。在《两都赋序》中,他则将“诗为赋源”的观念直接明了地表达了出来:“赋者,古诗之流也。”晋人皇甫谧撰《三都赋序》,始将《毛诗序》所言“诗有六义焉,二曰赋”结合起来,从文体论的角度归赋源于诗。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融合了《诗大序》和班固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丰富其说,以六艺之说确立了诗赋同源的理论思想:“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艺附庸,蔚成大国。遂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3〕后世的赋论相沿成习,咸以此为圭臬。
在清代古体赋论家的话语体系中,诗为赋源是考察赋的学理渊源的共同话语。程廷祚在《骚赋论》中指出:“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盖风雅颂之再变而后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赋也者,体类于骚而义取乎诗者也。骚之出于诗,犹王者之支庶封建为列侯也;赋之出于骚,犹陈完之育于姜,而因代有其国也。骚之于诗远而近,赋之于骚近而远;骚主于幽深,赋宜于浏亮。”〔6〕王芑孙《读赋卮言》亦云:“赋自不关妙悟,然诗曰言志,赋亦诗余。”章学诚《文史通义》:“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又诗赋本《诗经》之支系。”〔7〕
张惠言作为古体赋论家,亦响应“诗为赋源”的的话语系统。他在《七十家赋钞序》中云:“周泽衰,礼乐缺,《诗》终三百,文学之统熄,古圣人之美言,规矩之奥趣,郁而不发,则有赵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辞表旨,譬物连类,述三王之道以讥切当世,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鬯,不谋同偁,并名为赋。故知赋者,诗之体也。”他将赋归于诗,推动了古体赋论向前发展。
曹虹在《中国辞赋源流综论》中对“诗为赋源”的论断有这样的评价:
赋为古诗之流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把握,毋宁说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在辨别源流中寓正本清源之意,以建立某种批评标准和价值尺度,这一思想方法贯通于《汉书·艺文志》及《两都赋序》关于诗赋源流关系的论述中。“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论断,与其说在于揭示赋体的文学渊源,不如说旨在肯定文学的经义标准和“忠孝”内容,确立“大汉之文学,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历史地位。〔8〕
以此类推,张惠言在《七十家赋钞序》中,强调“赋者,诗之体也”。这是古体派赋论家推尊赋体的表现,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士人心态中根深蒂固的经学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诗为赋源”将“法度”和“经义”糅合成一种价值观,由此在文学史上确立了儒学的官方化和正宗化地位,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二、《七十家赋钞序》的批评原则
清代是赋学发展的又一高峰,辞赋选本在这个时期层出不穷。一种文学热潮的出现总是和当时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七十家赋钞序》的批评原则也是在这些环境的影响下应运而生,即贯穿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和推尊赋体的编选动力。
(一)贯穿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
关于情志,既可以是“感于哀乐”的个人情感,也可以是“以风其上”的家国之志。张惠言主张“志归乎正”,在赋作的批评中,立足于赋“宣上德而尽忠孝”的社会功用,强调君臣之义的雅正之情。
雅正之情首先表现为对作品中君臣之义的张扬,张惠言对屈原《九歌》的评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比如,《湘君》,张惠言评为:“此离骚所谓哲王不悟也。”〔8〕《云中君》,张惠言评为:“言君苟用己,则可以安览天下,惜此会之不可得也。”《东君》,张惠言评为:“伤顷襄也。嗣政之初,如日方出,岂意声色是娱,终于杳冥乎。”《国殇》,张惠言评为:“以忠死,故比国殇。”
更为重要的是,曹植的《洛神赋》一直被认为是描写男女爱情的赋作,张惠言则另辟蹊径,以君臣之义来解读其中的情感,完美地契合了情归雅正的赋学观。在评论曹植的《洛神赋》时,张惠言引用了何焯的观点:
何义门云:《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以作为此赋,亦屈子之志也。又云:《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月廿九日禅代,十一月遽改元黄初。陈思实以四年朝,而赋云三年者,不欲亟夺汉亡年,犹之发丧悲哭之意,注家未喻其微旨。何氏之言,真能以意逆志,于此更可知《高唐》、《神女》之义。
在《洛神赋》的结尾,张惠言又有这样的表述:
何云:“恨人神以下,皆陈思自叙其情。君王指宓妃喻文帝,不必以序中君王为疑。”案何以君王指宓妃,或以为凿,不知古人寓言,多有露本意处,如《九歌》、《湘夫人》,屈平以喻子兰,篇中‘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其见意处。湘夫人可称公子,宓妃亦可称君王也。
乾嘉时期,政治大一统,个人情感大多隐匿于家国和修身的意志中。张惠言这种统摄于雅正之志的批评,正顺应了时代潮流。
(二)推尊赋体的编选动力
从先秦到清代,诗和文作为独立的文体,已经发展成熟,诗话和文话日臻体系。随着文学观念的演进,赋作为一种文体,从诗和文中独立出来,激发了时人研究这种文体的热情。清人在总结前代赋作、编选辞赋作品的同时,开始注重对历代赋作规律的探讨和对历代赋论的整合。这是尊体观念使然。
乾嘉时期,为了提高赋作的地位,赋论家就赋体文学的合法性与正统性考镜源流,远绍诗骚。律赋派的作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为其正位。纳兰性德的《赋论》云:“本赋之心,正赋之体,吾谓非尽出于三百篇不可也。”〔9〕王芑孙《读赋卮言·导言》亦云:“飙流所始,同祖风骚。”又言赋义曰:“夫既与诗分体,则义兼比兴,用长箴颂矣。单行之始,椎轮晚周,别子为祖,荀况、屈平是也;继别为宗,宋玉是也。追其统系,三百篇其百世不迁之宗。”〔6〕
律赋派如此,古体赋派亦不甘示弱。程廷祚力倡骚体,写成了《骚赋论》上、中、下三篇。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对“辞赋类”作出的说明,表现出其“以古是尚”的赋学取向。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序》称:“凡赋七十家,二百六篇,通人硕士,先代所传,奇辞奥旨,备于此矣”,其所选赋作断自六朝,强调情感的表达,以雅正统乎情感,具有鲜明的复古倾向。可见,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序》正是在尊体观念的推动下产生的。
三、《七十家赋钞序》的批评方法
《七十家赋钞序》作为一篇赋论,能够在赋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除了以情为本的赋学观、诗为赋源的渊源论外,兼收并蓄的批评方法也是重要的原因。
作为一篇渗透赋学观的赋学批评论作,张惠言清醒地认识到批评方法的重要性。批评方法总是和批评目的、批评效果联系在一起:要达到什么样的批评目的,就会使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就会影响到其批评效果。张惠言在《七十家赋钞序》中共选择了二十二位赋家进行批评,主要使用了历史批评、比较批评和摘句批评等批评方法。
(一)历史批评
最早的历史批评出现在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其在论文学流派的变迁时写到:“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非能擅美,独映当时”〔10〕。这种历史批评是在写历史的过程中谈及文学,多少带有无意识的倾向。
张惠言在对赋家进行批评时,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批评方法。他将所有的赋家统属于荀况、屈原两大系统:
周泽衰,礼乐缺,《诗》终三百,文学之统熄,古圣人之美言,规矩之奥趣,郁而不发,则有赵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辞表旨,譬物连类,述三王之道以讥切当世,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鬯,不谋同偁,并名为赋。
他按时代先后,根据世有相因、人有嗣承的规律,有选择地对其中一些赋家进行了探本溯源式的批评。比如,评荀况云:“其原出乎《礼经》”;评贾谊,“其原出于屈平”;评司马相如,“其原出于宋玉”;评班固,“其原出于相如”;评阮籍,“其原出于庄周”;评曹植,“其端自宋玉”;评陆机、潘岳,“其原出于张衡、曹植”;评江淹,“江淹为最贤,其原出于屈平《九歌》”。张惠言的这种考镜源流的历史批评正是其深通历史源流的表现。
(二)比较批评
广义的批评是无处不在的,离开了比较,评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在《七十家赋钞序》中,主要体现在对风格相近的赋家或者前后继承的赋家的比较批评。
一方面,张惠言对风格相近的赋家进行了比较评论。例如,对屈原及其弟子的比较批评,云:“比物而不丑,其志洁,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为也,与风雅为节,涣乎若翔风之运轻赮,洒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莱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为之,其质也华,然其文也纵而后反”;比较荀况和孔臧、司马迁时,云:“刚志决理,輐断以为纪,内而不污,表而不著,则荀卿之为也……及孔臧、司马迁为之,章约句制,奡不可理。其辞深而旨文,确乎其不颇者也。”比较张衡与王延寿、张融时,云:“张衡盱盱,块若有余,上与造物为友,而下不遗埃墟,虽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苶。及王延寿、张融为之,杰格拮摋,钩孑菆牾,而俶佹可睹,其于宗也无蜕也。”比较班固与左思时,称:“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无瓠,孙而无弧,指事类情,必偶其徒,则班固之为也”,“及左思为之,博而不沈,赡而不华,连犿焉而不可止”。
另一方面,即使是因袭相承的赋家,其赋作的特点也会有所流变。对此,张惠言也做了比较。比如,评论班固与司马相如说:“则班固之为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比较阮籍与《庄子》时,称:“则阮籍之为也,其原出于庄周,虽然,其辞也悲,其韵也迫,而忧患之辞也。”曹植与宋玉的区别在于:“其端自宋玉,而枿其角,摧其牙,离其本而抑其末,浮华之学者相与尸之,率以变古”。通过这种纵横交错的比较批评,使得我们对先唐赋家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从中也可以窥见张惠言对赋史的了然于心。
(三)摘句批评
摘句批评法也是《七十家赋钞序》中运用较多的批评方法。其核心是“断章取义”,以个别代替一般,以一句代替全章,兼有暗示、举例、鉴赏等作用。在先秦典籍,如《孟子》、《荀子》、《左传》、《国语》中,经常记载各国使者摘引《诗经》,断章取义以言志或作为外交辞令的情况,后世文学评论的“摘句法”当滥觞于此〔11〕。后世的文学批评中,经常用到“摘句法”,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都使用了“摘句批评”。
《庄子·天下》篇中批评了先秦各家学派的论著,是最古的一篇批评中国学术史的文章。张惠言在对二十二位赋家进行批评时,亦从《庄子》中撷取了诸多语辞,以求达到断章取义、点石成金的效果。比如,在评价扬雄时,用到“缘督以及节”,语出《庄子·养生主》“缘督以为经”〔12〕,缘督含有顺着自然之道的意思,巧妙的点出了扬雄赋作自然洒脱的特点。评价张衡“上与造物为友”则是化用了《庄子·天下》篇中“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评价阮籍时,评为“言无端厓”,同样出自《庄子·天下篇》:“荒唐之言,无端厓之辞”。最为称道的当属对司马相如的评价,评曰:“循有枢,执有庐,颉滑而不可居。开决宦突而与万物都,其终也芴莫,而神明为之橐,则司马相如之为也。”“循有枢”、“颉滑有实”本于《庄子·徐无鬼》“循有照,冥有枢”、“颉滑有实,古今不代”。《天下》篇中对庄子之学评之为“芴漠无形,变化无常”、“神明往与”,郭象分别释为“随物也”、“任化也”。张惠言试图借用庄学随物任化的理念,来揭示司马相如控引天地、苞举万物的赋才。
张惠言从《庄子》中摘句最多,此外,他还从其他史志中大量引用以作点评。如在点评屈原时,化用了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的“其志洁,故其称物芳”,评其为“其志洁,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点评贾谊“其趣不两,其于物无勥,若枝叶之附其根本”,化用的是司马光《家范》的“如枝叶之附于根干,手足之系于身首,不可离也。”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摘句批评使言简意赅的语言中包蕴无尽的言外之意,不仅体现了张惠言渊博的学识,也反映了其对赋作的深刻认识。
总而言之,《七十家赋钞序》是一篇集中体现张惠言赋学理论的文学批评著作。它在继承前代诗为赋源的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情为本的赋学观,并交错使用多种批评方法对唐代以前的赋学家进行评论,展现了有清一代学人吞吐庞杂的研究气魄和学术能力。
注释:
①见张惠言著《七十家赋钞》卷一,道光元年合河康氏刻本。下文中所引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均用此版本,不再出注。
参考文献:
〔1〕李倩倩. 张惠言的学术传承与赋学思想——以《七十家赋钞序》为中心〔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3,(6):28-30.
〔2〕张惠言,著.黄立新,校.茗柯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7.
〔3〕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修订本)〔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114,148.
〔4〕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7.
〔5〕班固,撰. 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378.
〔6〕徐志啸,编.历代赋论辑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74,78.
〔7〕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61:21.
〔8〕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综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05:59.
〔9〕王运熙,顾易生,主编.清代文论选(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32.
〔10〕沈约,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76 .
〔11〕张伯伟.钟嵘《诗品》的批评方法论〔J〕. 中国社会科学,1986,(3):168.
〔1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3:84.
(责任编辑:武丽霞)
Criticism of Zhang Hui-yan’s Seventy Fu Chao Xu
ZHANG Xiao-lu
(CollegeofLiberalArts,AnhuiUniversity,Hefei230039,China)
Key words:Fu criticism; Seventy Fu Chao Xu; Zhang Hui-yan; creation theories; stylistic theory; historical criticism; sentence criticism; comparative criticism
Abstract:Seventy Fu Chao Xu is an important Fu Criticism in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study of this ode. We may find that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is book is the inheritance of creation theories based on senses from perception of objects and the stylistic theory of Fu originating from poems, which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elude of the book. In the principle of criticism, Zhang Huiyan focused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monarch and respect for the style of Fu. In terms of criticism method, he adopts historical, sentence and comparative criticisms. In general, we can witness Zhang’s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Fu in this book.
收稿日期:2016-03-28
作者简介:张小璐(1990-),女,安徽桐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E-mail:1430255069@qq.com。
中图分类号:I207.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0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