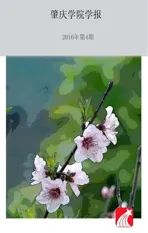《己卯年雨雪》与抗战文学的新叙事
2016-02-17颜同林王丽婷
颜同林,王丽婷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新世纪岭南文学研究】(栏目主持人:黎保荣)
《己卯年雨雪》与抗战文学的新叙事
颜同林,王丽婷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主持人语:熊育群是广东文坛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知名作家,以散文名世,其散文集《路上的祖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后转攻小说创作。《连尔居》《己卯年雨雪》为其至今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他系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从事过建筑设计、新闻、出版等工作,后弃工从文。其作品既显工科人的细致,又兼记者的敏锐以及学院派的灵气与厚重。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2016年1月出版。古语云“十年磨一剑”,他是“十四年磨一剑”,用了14年的时间来调研、采访、阅读与写作。可见这是一部用心用力的大作、杰作。
主持人:黎保荣
熊育群的小说《己卯年雨雪》是一部“和平之书”,小说从作者家乡汩罗江两岸1939年8月的抗日史实出发,从日本人与中国人交错互动的视角来写当地抗日战争,考察军人与平民在战场中的特定状态和心理,追根溯源地探究了侵略战争的罪恶本质,并建构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新叙事模式。其中包括采用了双线并行与交叉错综的叙事结构,以此来突围传统战争文学较为单一的叙事视角;借鉴了复调的叙述方式,将对战争的反省,人性的复杂放置在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审美空间之中。小说具有可读性、传奇性,颇见作者的用心与用力之处。
《己卯年雨雪》;新叙事;双向视角;复调叙述;传奇性
当代知名作家熊育群的家乡是湖南岳阳,在日夜流淌的汩罗江两岸,大小村庄遍布于这片湖区。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会有不同;风电雨雪,看似平常却见异色。当人们把目光回溯到1939年农历己卯年的八月,虽然同样是在秋季,虽然也是常见的风雨天气,但是这年八月却格外的特别和血腥。以营田、推山咀、大湾杨、马头曹、南渡桥、新市、河夹塘等为具体地名的村庄或集镇,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区域,经历了一次次无比惨烈的大型战役。作为长沙会战的前沿之一,中日两个国家的军队屯集于汩罗江两岸,双方敌对的军人、平民,以及这些人物背后的万千家庭,都聚焦于此。在战争地所发生的硝烟与故事,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失去了记忆,相反,它会因为摧残人性的酷烈、因为乡土的熟悉而永远定格了下来。——熊育群的童年记忆,虽然没有战争,但更多的是这些战争远去后留下来的村庄与市镇,以及年长的亲人与乡民,因此,油然而生的是一份铭记痛苦记忆的勇气与担当。十多年之间,熊育群一直酝酿与构思着这部纪实性作品,一步一步地进行着扎实的史料搜集和实地调研工作。记述地方抗战史实,反思战争本性,便有了这部沉甸甸的力作——《己卯年雨雪》。
故事的梗概并不复杂:1939年中秋前后,一名叫武田千鹤子的日本女人踏上了中国国土,目的之一是慰问自己新婚之后便辞别家乡、远赴中国打仗的丈夫武田修宏,在岳阳营田战地终于与丈夫短暂团聚。两人随后在随军行进过程中遭遇了埋伏,武田重伤生死未卜,千鹤子则被中国军民俘虏。俘获押送她的核心人物是祝奕典,因其与祝氏关爱之人王旻如相貌十分相像,侥幸得以活了下来。千鹤子先是受到祝奕典等人仇视,随着双方了解不断深入,她后来得到祝奕典、左坤苇夫妇,以及左太乙等一家人的救助与关怀。期间千鹤子诞下了与武田修宏的孩子,而武田修宏死里逃生,历经千辛万苦寻找妻儿,最后孩子找到了,自己却难逃命运的安排而被击毙。故事最后以千鹤子被押送至战俘营,祝奕典则因窝藏日本人而被判了十年监禁而告终。
《己卯年雨雪》立足于特定地域,以抗战新叙事见长,其引人入胜之处,不仅仅在于塑造了武田千鹤子、武田修宏、祝奕典、左坤苇和左太乙等一批血肉丰满的军民人物形象,展现了战争下人性的善与恶、恩与怨、仇恨与宽恕等主题,更重要的是,作家用独具匠心的叙事技巧,为我们怎样讲述这一个故事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一、双线并行、新颖多样的叙述结构
与大多数文学作品的单一结构线索不同,《己卯年雨雪》为了追求故事内容的丰富新颖和情节结构的跌宕起伏,强化陌生化,设计的是双线甚至是多线条的叙述结构,中间还用明暗结合互补的方式加以缝合。“小说家詹姆斯曾略带夸张地说:‘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五百万种方式。’每一种讲述方式都会在读者身上唤起独特的阅读反应和情感效果,因此如何讲述直接决定着这种效果能否得到实现。”[1]叙事学理论告诉我们,同一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的叙述方式,研究叙事文学作品应该研究故事是如何被叙述的,如何叙述对于作品来说十分重要。熊育群在《己卯年雨雪》的新叙事形式无疑体现出了作家的个人化思考。
首先,从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以看出,作者有意以中日两对不同恋人的遭遇与命运为主线,即以武田修宏与武田千鹤子,祝奕典与左坤苇为中心开展故事情节。两条线索并非是平行不相交的,两对恋人之间的故事也不是彼此孤立的,他们之间有着密切而错综的联系,这就涉及到了隐藏于其中的桥梁——曾经喜欢祝奕典并差一点与之结合的王旻如,是王旻如被日军残暴杀害之后,报仇心切的祝奕典俘虏了千鹤子,故事一下子就进入了恩怨分明的胶着状态。千鹤子和王旻如之间冥冥中注定有着某种联系,祝奕典“第一次看到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长相如此酷似……日本女人与中国女人原来是一样的”。在后续情节中,这种似曾相识得到了扩大。譬如,千鹤子还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左坤苇还跟着千鹤子学日本礼仪,千鹤子喜欢庄子,收藏《史记》,自幼背诵《论语》,崇拜诸葛亮,迷恋《红楼梦》……甚至连武田修宏也推崇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的典故“雪夜访戴”“竹林七贤”和“兰亭雅集”;中国与日本的很多节日也是相通的,中国的清明节和日本的盂兰盆节都是祭祀祖先的日子,武田夫妇的家乡日出町也时兴过中秋节;中国的陌生面孔能让他们想起自己家乡的亲人,武田修宏看到的那个像自己舅舅的老人,他给老人烟抽,并想营救老人,虽然老人最终还是惨遭杀害;左太乙也让千鹤子联想到自己家乡的老人,“在她的印象里,这个老人似曾相识,她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在志高湖还是经冢山?反正是日出町远处的什么地方”;甚至中国村庄土墙上的牵牛花和日出町的也一模一样。关键的一点是,千鹤子还会讲汉语,大体听得懂一些当地方言,使得她与祝奕典等人之间的沟通消除了语言上的障碍,拉近了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完全陌生者之间的距离。在双线并行中,正是这些情节与感情上的许多支架,像血管一样密切相通,让两条并行线索较好地交融在一起,相互之间产生丰富的关联。
其次,作者在小说中还采用了新颖多样的叙述方式。一般来讲,小说的叙事顺序主要分为顺叙、插叙、倒叙和补叙之类。顺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一种叙述方法,它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反映人物事件的经过与原委,使用顺叙便于确定文章的中心和布局,方便安排材料,写作起来也相对顺手,使得文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这也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叙述性文学作品常用的叙述方式。但是,如果单纯使用顺叙又会给文章带来平淡无奇的感觉,难以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小说的结构涉及人物的配备,情节的处理,环境的布置,章节段落的划分,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结合,等等,这些都要通过作家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加以巧妙的编织,形成为一个生气贯注的有机整体。”[2]好的小说必然离不开好的叙述方式,倒叙、插叙和补叙的使用则弥补了顺叙结构的不足,使得文章跌宕起伏,悬念丛生,无形中丰富了文本的阅读内容,从而引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
《己卯年雨雪》对这种复杂结构的运用,使得作品的情节有了波涛起伏般的变化,有助于增强作品的层次感,深化作品内涵。小说以千鹤子访亲被俘为开端,以其被送往战俘营告终,故事叙事时间长度为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除了祝奕典的故事与其并行发展外,故事中大量穿插了千鹤子的人生回忆,武田修宏的战争体验和变化;以及左太平、左太乙、左坤苇、王旻如等人悲欢离合的小故事。小说主体以现实发展为主,插叙了大量回忆性片断或情节,比如千鹤子在昏迷时回忆起母亲在少女时代教她如何伺候未来的丈夫,以及她和武田修宏结婚时的场景,他们在日本作为普通人生活的一幕幕展现在读者面前;祝奕典也在故事的发展与推进中,回想起与左坤苇的美好爱情,他和王旻如的阴差阳错……诸如此类,都是这部小说吸引读者的匠心之处。
二、双向视角、多种声音的复调模式
小说是一种叙事的艺术,叙事文本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都要受角度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调节。”[3]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效果,而所谓视角,是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4]可见,视角作为叙事要素之一,与叙事作品的整体风格互相应和,共同体现创作者独特的创新思维与能力。叙事视角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建构叙事文本的基点,是作者与文本的心灵结合,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不论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的虚拟世界;同时,帮助读者进入叙事虚构世界当中,找到打开作者心灵的钥匙。总之,叙事角度选取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小说艺术成就的高低,同样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小说的风格设定和技巧、节奏,等等。
熊育群在小说《己卯年雨雪》中,叙事视角上有意将日本人作为主角,并站在他者的立场展开叙述,与以前同类题材的抗日作品截然不同。作者在长篇“后记”中就曾提到“我要写一对日本恋人和一对家乡的恋人”的故事,“中国作家写抗战题材小说鲜有以日本人为主角的”,作家的理由是“一场战争是两个国家间的交战……任何撇开对方自己写自己的行为,总是有遗憾的,很难全面,容易沦为自说自话”。作者觉得“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我想,超越双方的立场,从仇恨中抬起头来,不仅仅是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而是要看到战争的本质,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寻找根本的缘由与真正的罪恶,写出和平的宝贵,这对一个作家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正如优秀的叙事作品“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5]一样,作家发现的侧面不同,体现出来的精神也是不同质的。这种以日本人为主角进行叙事的创作手法,无疑成了此书中的一个亮点,为作者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知名学者孟繁华在其著作《叙事的艺术》中提到,“视角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叙事艺术的结构,对于提高叙事艺术的表现力提供了众多的方式。我们大概都会承认,同一个故事会由于叙述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6]75在论述叙事视角的选择意义时,他认为视角选择的多样性表明“众多的作家是在促进创作多样化的发展,是在探寻‘怎么写’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比起一种叙事视角来说,多种视角毕竟能满足更多的审美消费需求”[6]36。无疑,这一说法有的放矢,是小说叙事研究的一种深刻见解。叙事视角的选择和设定,对于小说《己卯年雨雪》创作的成功有着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小说《己卯年雨雪》在叙事模式上还借鉴了复调小说的发展模式。复调小说理论是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研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有着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7]。而小说《己卯年雨雪》在人物描写、内部声音上,尤为注重人物心理活动和想象描写,这是“复调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尽力从敌我双方的自然转换、不同声音的对话与冲突来展示双方人性的丑恶与美好,凸现人物思想上的不断变化与矛盾。其中,我们认为这一“复调”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战争与和平的反省,以及对敌国态度的换位思考上。千鹤子由最初仇恨中国人,随着与中国人的深入接触,慢慢地理解和接受了祝奕典等人,并最终与他们达到了心灵上的融合。她认识到“说支那人奴性十足是错误的。这里的人看不到一点奴性”,千鹤子不再为“圣战”辩护,典型的如“祝奕典杀侵略自己国土的人,杀杀死自己心爱女人的人,又有什么不对”,她最终选择了完全站在中国一方,站在正义一方。在被俘期间,她不断反思战争的意义,作者有意让我们从一个日本女人的视角来认识和解读战争,即由最初所认为的“我们日本人有责任把支那从白人手中解放出来”,指责中国“是一个不争气的邻国,它过去太自大了,从不向外面学习,搞洋务运动只是学些坚船利炮的东西”;到质疑“那里真的是日本人的希望吗?中国人真的需要我们去为他们做事?为什么还要打仗呢”;再到彻底否定“‘太可怕了,简直是地狱!’国内的报纸把战场描绘的那么壮观、美妙,英雄都是那么勇敢、高尚,这里看到的无非就是杀人,那些报导多么无知”。
与千鹤子相似,武田修宏的心路历程同等重要,他让我们从一个日本士兵的角度更彻底地认识到了战争的本质。武田修宏首先是认同战争,不伤及无辜,但逐渐把枪对准了中国平民,在习惯了杀戮的同时也在慢慢思考:“这种行为是否恰当?我们是为了和平才破坏和平吗?和平真的离不开战争?为什么所有的战争都在说捍卫和平?”这本身就是悖论,“为了和平而破坏和平”,这种军国主义者灌输的荒诞逻辑在小说中大量存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蒙蔽了像武田修宏这样的军人。最后,他开始不断反思战争中的士兵,和鼓动战争的领导人,希特勒鼓舞人心的话,让他感到反感,他觉得“人这种动物真是盲目”。“为何战争就能使人发疯?这真是正义的‘圣战’吗?日本是优秀民族,希特勒也称德意志为优秀民族,他们在欧洲大陆开了一个个‘舞场’,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杀人?”“既然是为亚洲人的自卫自存,理应受到支那人的欢迎,但为何看到的全是仇恨和恐慌?这两年的经历,武田修宏遇到的全是反抗和战斗。强迫别人就是应该的吗?好东西为什么他们不接受?支那人真的那么愚蠢,连好歹都不分了”“靠杀人来实现的主义会是好的主义吗”。小说中类似的句子、段落有很多,从中不难发现,不论是千鹤子,还是武田修宏,都有其内心不同声音的对话,在本真的犹疑与怯懦之间,在自诩的正义与真理之间,在残忍的屠戮与伤害之间,这些飘荡在人生歧路上的各种声音,总是突然而至,处处让人产生一种不信任感、不真实感,并从内部否定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同样道理,站在身份斑驳的“抗日英雄”祝奕典的角度来看,虽然他无法放下对日本人的仇恨,但随着与千鹤子的深入接触和对她的了解,也觉得“她温顺、礼貌、善解人意,她完全是她自己了”“他观察日本女人一段时间后,心里就开始纠结,越是纠结越是仔细的观察,越是仔细的观察越发现她不同于她的同类”,慢慢地祝奕典也对千鹤子产生了愧疚心理,“他觉得自己对她太狠了。他把她的一生毁得干干净净”,而人与人之间的谅解,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的。至于左太乙、左坤苇等人,超越了简单的冤家路窄的复仇心理,他们与普通民众不同的地方,同样存在于他们能在具体的人与事中进行独立思考,同样存在于他们对人性普遍真善的常识以上的判断。所以,在小说的情节推进过程中,越到后来,中日军民在中国血与火的战场上相逢,渐渐消泯了各自国籍的标签,和平共存的主题也得到了凸现。
三、传统战争文学叙事技巧的借鉴与创新
《己卯年雨雪》具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和浪漫主义特征。小说从开头到结尾,所穿插的命运预言、奇幻情境和离奇的情节,等等,都是十分普遍的。类似“比较典型的运用了通过幻想反映现实的表现方法”[8]一样,传统战争文学的叙事元素,给小说作品带来了强烈的可读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想象诉求。
以小说人物而论,中心人物之一的祝奕典是作者笔下的抗日英雄,但“他一会儿是篾匠,一会儿是跑江湖的船帮,一会儿杀日本梁子,一会儿又与土匪纠缠不清,隐身江湖,任性而为,从无约束”;同时又有着脆弱柔情的一面,他对王旻如用情至深,对左坤苇和孩子都是体贴关怀、充满爱意,甚至对千鹤子后来的态度也转变为关怀和怜悯,内心充满愧疚。与祝奕典形影不离的是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响刀,其来历十分罕见:“打成一把五行刀,师徒俩都会病一场。师傅知道他们的病除了累,还有神灵的惩罚,当那刀兀自鸣响的时候,师徒俩就开始头昏脑胀,师傅听到了灵的哭泣。他知道打出这样的宝刀是一种罪孽”,这把夺命的五行刀甚至会“自言自语”,它有着嗜血的本性,“它在指挥自己杀那个日本兵”,祝奕典没能来得及思考“刀自己就在行动了”“响刀开始成为传奇。它注定不凡。”一把宝刀的出世,仿佛是吸取了天地的精华,带着杀戮和罪孽,这种写法颇具传统武侠小说的风韵,让人读来叹为观止。佩刀之人自然也是非凡之人,祝奕典“一直贴身带着这把响刀,母亲手中的一根线他不用剪而用刀断开,他用刀给人剃光头、刮胡子,用刀把笋切得纸一样薄……他眼到刀到,不差分毫”。在迷魂一样的杨仙湖上,祝奕典能够出入自如,“人们谈论他就像谈论神灵一样充满敬意”。显然,如此种种关于冷兵器及其主人的描述,大体延续了传统战争文学中对英雄人物的神性化塑造,虽带有明显的夸张和浪漫主义倾向,但并没有影响小说事件真实性的曲折反映,作者通过这种文学书写的方式凸现出人物的英勇和传奇,相对于概念化叙述更能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而另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左太乙。左太乙是小说中最亲近自然和回归本真的人,他通晓老子、庄子和《周易》,从不带着世俗的眼光和心境来看待外界。他“一步步沉浸到了老子、庄子和《周易》的世界,从陶渊明、王维、柳宗元的诗中寻找着慰藉,最终心皈道教”。左太乙爱鸟、护鸟,为了远离乱世,他躲到大湾杨“上到荒洲,与鸟为伍,更无人世的纠葛了”,世界在发生着变化,但他在鸟的世界里,看到“纯净、自在、悠然、轻盈、忘我……”。在战争年代里他坚持寻找内心的回归,“一个人长期在湖中生活,沉思默想,迷恋孤独,渐渐地他开始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了,时间却在为他慢慢打开”。与仇恨日本女人相反,他视千鹤子为国人、亲人,在战争中,无辜的女人需要的是保护,而不是无情的屠戮。试想,如果没有左太乙,千鹤子能存活下来么?最令人称奇的是,最后他的死也成为了一个不朽的传奇,老人消失后踪迹无处可寻,等找到他时,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他的尸体竟然没有腐烂”,他的相貌“一天一变,好像许多个人的模样”,就连左坤苇甚至都不能确定这是自己的“爷”,而这个神奇的老人仿佛还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左太乙的死又成为了大湾杨人们口里的怪事——“死的怪”,村民以七大怪来总结他的人生。总之,作者在左太乙身上,展现了他对自然,对道,对人性的终极追求,其目的之一便是与战争的发动者、渔利者、嗜血者进行鲜明的多维对比,人性的美丑、善恶自然也昭然若揭!
对于战争中普通人物命运捉摸不定的安排,也成为了小说中的创新之处,作者以此来体现出人在战争中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荒诞感和无力感。这种命运的安排在对武田修宏的描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自踏上支那国土开始,他就越来越相信命运了”,他认为“战场上谁会死,什么时候死,其实命运早已做出了安排”。比如,战场上井上被安排在后面最安全的地方,死的却是他,让武田修宏“觉得生命真是无常,命运似乎早就注定了一切,人的努力也许都是徒劳的”“战场上谁会死,什么时候死,其实命运早已做出了安排。有人置身枪林弹雨毫发无伤,有人躲在战壕却被打死。只有命运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细节时,莫不感慨万千:桑野想方设法躲避死亡,但他却死了,被流弹击中;井上总是调侃大家会帮他们把骨灰带回去,但井上却死了,自己连骨灰都没能留下。幸存下来的人也像是命运的安排,如村民黎哲秋的家人惨遭杀害,自己为家人去白水亲戚家找食物却逃过一劫……这些都体现了战争的荒诞性和命运的不确定性,既像梦魇一样带有传奇色彩,也对战争本身的特质进行了彻底的解剖。
四、结语
熊育群的小说《己卯年雨雪》,采用了双线并行与交叉错综的叙事结构,以此来突围传统战争文学较为单一的叙事结构;同时借鉴了复调的叙述模式,将战争的反省、人性的复杂放置在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审美空间之中。作为一部难得的“和平之书”,小说从日本人的视角来写战争,考察日本人在战争中的特定状态和心理,追根溯源地探究与否定了战争的本质,而不只是以单向的视角,仅仅提出控诉和指责。这样在反思中大力向前推进,既建构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叙事模式,也在主题上进行了新的尝试。作家这一努力,使得小说作品具有可读性、传奇性,也足以见出作者用心与用力之处。
[1]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58-159.
[2]孙子威.文学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01.
[3]卢伯克.小说技巧[M]//方土人,译.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80.
[4]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
[5]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
[6]孟繁华.叙事的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29.
[8]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00.
(责任编辑:卢妙清)
The Rain and the Snow in 1939 and New Narrative of Literature of Anti-Japanes War
YAN Tonglin,WANG Liting
(Collegeof Literature,Guizhou NormalUniversity,Guizhou,Guiyang 550001,China)
ract:The Rain and the Snow in 1939 is one of Xiong Yuqun’s novels,which can be called“the Book of Peace”.The novel,starting from the anti-Japanese historical facts in August1939 thathappened in M iluo River on both sides of the author'shometow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people,w rites about the Anti-JapaneseWar of the local,investigates them ilitary and civilians'certain status and psychology in battle fields and explores the evil nature of invasion w ith trace to the source,and then constructs new narrativemodesw ith unique and distinctive style himself.These include:narrative structure of parallelmodel and cross-complex,which is a reform of the simple narration of the conventionalwar literature;the narration mode of polyphony,placing the introspection of war and the complex of humanity in an aesthetic,specific and rich space.The novelpossesses readability and legendary show ing the author’sgood intentions.
ords new narrative;dualperspectives;polyphonic narration;legendary
I207.425
A
1009-8445(2016)04-0001-06
2016-04-09
颜同林(1975-),男,湖南涟源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