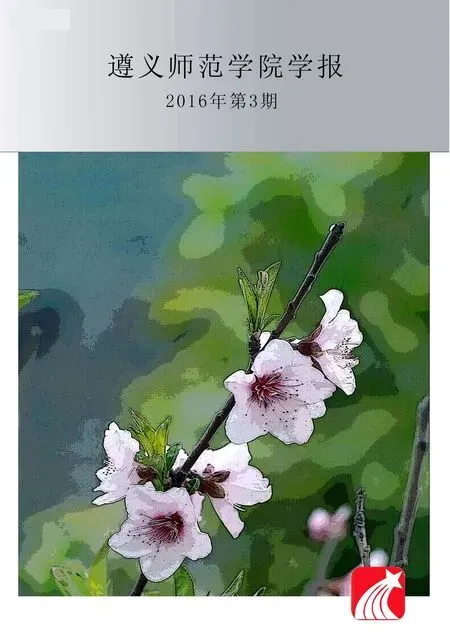现代性与民族性:许地山小说文本的双重追求
2016-02-15廖晓梅
廖晓梅
(龙岩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福建龙岩364000)
现代性与民族性:许地山小说文本的双重追求
廖晓梅
(龙岩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福建龙岩364000)
在以西方文化为圭臬的五四时期,“先进”的现代性目标往往被作为“落后”的民族性的参照与对立。许地山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呈现了现代性和民族性双向交流并融合的状态。许地山的文学实践试图建构现代小说发展的这样一种新的可能性:现代性和民族性并重才是一种适合中国民族特性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性;民族性;双向交流和深度融合的小说叙事的双重追求
现代性和民族性的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现代性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是环境、制度、艺术概念及形式的转变,更是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构造的转变。”[1]现代性昭示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形成,是新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特质。而民族性则是“有生命力的,可以进行自我更新的优秀的传统。”[2]五四时期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挽救中国。”[3]新文学发展初期,现代小说漠视、鄙弃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方式,而进行西化、欧化革新是五四小说追求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五四文人以决绝的姿态,“收纳新潮,脱离陈套”积极探索诸多先锋性的变革。“五四小说现代的思想主题获得了现代的存在形式,小说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者之间结成新的有机联系。”[4]在这样一个文学演变剧烈的语境中,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许地山却独而不群,在他所深耕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呈现了现代性和民族性双向交流并融合的状态。许地山以他的文学实践试图建构现代小说发展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现代性和民族性并重才是适合中国民族特性的现代化道路。虽然许地山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处于一种边缘的位置,但不可否认他的艺术实践是五四时期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线。本文尝试从价值取向、叙事技巧和审美范式三个维度去解读许地山的小说文本,希望能在现代文学史上对许地山的研究增添些许帮助。
一、叙事的现代性追求
近代中国是在外在暴力的冲击下开始了被迫现代性的进程。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引进和争取现代性是时代最强音。在这极具变革精神的时期,中国小说如何突破传统籓篱,完成现代模式转变是五四作家必须直面的问题。五四文学从现实需要出发,吸取运用包括西方现代主义在内的先进文学资源,实现与传统的决裂,从而达到社会变革,与西方同步的目标。许地山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和发起人之一,他的小说创作中也彰显了现代性的特点。许地山主张文学是写实性的,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一共收集12部短篇小说,其中有7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都是写的传统文化烙印在人物精神深处所导致的人生悲剧。在《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中,描写了一对不知礼节的新婚夫妇,由于在孝期间开了些玩笑,妻子就被送回娘家,最后郁郁而亡的故事。作家悲愤地感慨:他并不是没有反抗礼教的勇气,是他还没得着反抗礼教的启示。许地山的探索绝不仅此,他的创作中受到加缪的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在他笔下不断对存在进行探寻。许地山小说人物的结局基本都是以悲剧收尾:《女儿心》中父女即将相认父亲却死了;《商人妇》中惜官变成印度人,再也回不了家乡了;《枯杨生华》中云姑饱尝了失子之痛。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成为许地山小说表现的主题。《缀网劳蛛》中尚洁与她的丈夫难以沟通,选择独自生活。《命命鸟》中相爱的敏明和加陵虽然殉情,但二人所想却迥异。许地山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卑微的小人物,往往在极端化的处境中去寻找存在。《商人妇》中的惜官不再是传统弃妇叙事模式中的弃妇,也不同于五四文学中“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娜拉”们,她四处漂泊,历经无数的苦难,最终成为了经济、精神皆独立的新女性。惜官的蜕变过程彰显了人的意志和尊严,这种的蜕变离不开宗教的影响。可以说,宗教意识是贯穿于许地山整个小说世界的。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等融于许地山小说之中,这使得他的小说散发着浓郁的宗教气息,他笔下的人物由于获得宗教的抚慰,而达到洞彻人生、执着生命的境界。宗教观念引入小说的尝试使得许地山在追求现代性的道路上独树一帜。
许地山积极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技巧和表现手法。“五四”时期,“叙事人身份的变化和白话文运动汇合在一起,使小说创作的天地显示出空前的魅力,这是个性化叙事和风格自觉意识发展生成的文化环境。”[4]许地山在小说创作中实现了从全知到限知的现代叙事视角的转变。《商人妇》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是一种“叙事者=人物”的模式。小说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叙述者“我”是一个倾听故事的配角,只叙述“我”听到、看到、想到的。故事的主人公惜官讲述她的人生经历,全文她也是在讲述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这是内聚焦型视角叙事,极大的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仿佛事件就那样在读者面前一一展开。而在《慕》这篇小说中采用外聚焦型视角叙事,即叙事者〈人物,叙述者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和叙述。这是一种客观的叙事视角,小说中只有客观的人物对话和景物描绘。在陵妈和一夫役的对话中展开了一个爱情悲剧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给读者留下了许多谜团,姑娘为什么把所有东西都丢了?姑娘看一封信却可能会闹出人命?……谜团没解开,小说就以车夫离开结束了,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文学期待。许地山运用叙述视角是灵活多变的,常自由变换叙事人称。在《黄昏后》中,作者在开头交代完人物关系,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后就隐退了,主要的故事则是由文本中“父亲”这个人物用第一人称叙述来完成。《缀网劳蛛》主要采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以尚洁为小说的视角人物,所以叙述者无法对其它人物比如史夫人、尚洁丈夫等内心展开描述。而为了叙述的顺利,许地山在小说开头和结尾适当混合使用全知叙述。《醍醐天女》中“我”倾听印度朋友讲述的一对年轻的印度夫妇在树林遇险的故事,叙事的视角始终是“我”。这样的“我”既有第一人称的亲历性,又有第三人称的全知性。
传统小说中常有直接跳出,单纯的评论性干预。许地山在小说创作中尽量避免这样的干预,只是偶然和读者进行间接的对话,通过采用较为隐秘的借人物之口或者以叙述者的内心感想来评判小说中人物的行动。《铁鱼的腮》中最后雷先生因为失手将一个装有自己用尽一生心血研制的新式潜艇模型和图纸的小箱子掉下海里,他急得跳下海去。许地山在小说的结尾借雷先生的朋友黄先生之口感叹:想着那铁鱼的腮,也许是不应该发明得太早,所以要潜在水里。这是作者何等冷峻的质问!
“开笔突兀”成为自晚清小说效法西方小说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自觉的叙事现代性追求。许地山的小说常以景物、场面、对话来开场,《铁鱼的腮》以警报解除后浩浩荡荡耀武扬威的壮丁队伍游行的场面开头,随即描述了一个怀抱新式潜艇模型和样图的报国无门、潦倒不堪的老科学的人物形象。这二者形成强烈的反差,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还巢鸾凤》一开场就犹如是个电影特写镜头,写出南方那美丽初夏情景,细腻刻画了一位官宦小姐那清丽柔美的形体、气质。《法眼》是以两个囚犯的对话展开叙述,在小说中叙述主体非常隐蔽。
结构意识是许地山在小说创作中最突出的现代性因素。许地山小说结构多变有序,基本上以纵式这一中国传统结构为主,以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来营构小说,但也有不少小说是包含多层立体复式的结构,充分运用了倒叙、插叙、补叙的手法营造了错落交织的时空。比如《商人妇》基本都是惜官对往事的回忆,《人非人》中叙述的事件发生的就一天,可是描述的时间却是十几年。可以说许地山在试图突破传统小说的结构,在叙述人称、叙述技巧等方面都做了大胆的尝试。绝不仅此,许地山是一位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作家,他运用隐喻象征的手法,将宗教理念融入创作中,使得他的小说在叙事模式上呈现一种宗教图式结构。比如《商人妇》、《玉官》采用了“漫游、求索”的结构叙述了两个中国最普通的卑微而弱小的村妇在历经磨难最后寻找到信仰和尊严。惜官成长为一位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的新女性,玉官完成从“吃教”到“信教”的蜕变。这都是一种“天路历程”的结构模式。而《缀网劳蛛》则是一个典型的圣经隐喻结构,尚洁的经历类似于《圣经·约伯记》的结构模式。原先拥有不断的被剥夺-好友相劝无果-顿悟-再次拥有。尚洁被迫离开家园,在外漂泊,最终回到家园。尚洁面对惊涛骇浪般的外界冲击,却始终拥有一颗平静坦荡的内心。最终尚洁完成了从附属的奴隶到拥有独立人格女性的蜕变。而不管是惜官、玉官还是尚洁,她们的蜕变是基于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人生抉择。许地山通过对这种宗教图式结构的书写,展示了固有的秩序所受到的冲击和瓦解。惜官读了《天路历程》和《鲁滨逊漂流记》,这两本书给了她许多安慰和模范,《缀网劳蛛》中尚洁的丈夫听了牧师的讲道和读了《马可福音》幡然醒悟,玉官抛弃了看不懂的《易经》而选择了白话《圣经》,这些人物在外来文化和现代观念的影响下都获得了救赎。
二、致力于小说民族性的建构
民族性的建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一直追求的方向。中国的现代历史风雨飘摇、苦难深重。认同危机、价值焦虑是20世纪初中国人遭受的最大的精神危机。在五四这个历史转型时期,现代性和民族性因空间的隔膜产生了时间上的滞差。五四时期的主流选择是毫无保留抛弃旧传统。许地山却是独而不群,他冷静的对待历史,面对我国民族精神与文化,在其《国粹与国学》中明确提出要发现和发扬我们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许地山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践行了这一理念,将小说旧的形式相关的一些本质资源充分开发,立足于小说民族性的建构。
中国小说源于志怪、传奇,形成独特的传奇故事的叙事模式。许地山在小说创作中体现对故事性传奇性的营构,呈现出了“对于离奇情节的偏嗜”。他编撰了许多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而巧合和偶然成为他情节设计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杨义先生曾经高度评价许地山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开端期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传奇小说家。许地山精心的营构故事,积极的吸取民间文学的营养,所以许地山早期小说异国情调和地方色彩浓厚,小说大量以闽、台、东南亚、印度为背景,展示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并在小说中巧妙地呈现大量的巧合和偶然。
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范式是含蓄简洁、意境深远。许地山的小说基本都是短篇小说,写得极为凝练。句式简短、节奏明快,遵循中国传统散文的叙事风格。许地山的不少小说都是运用全知视角,连贯讲述。在许地山的小说情节发展迅速,几乎没有枝蔓的叙述,往往在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或者写到重要场面才展开叙述,其它情节则一笔带过。所以许地山小说中许多看似粗线条的叙述,却体现了简洁凝练的艺术追求。例如《女儿心》的女主人公麟趾在寻找神仙过程中历经千辛万苦,许地山却有意忽略许多细节,也没有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去描绘麟趾内心的激烈冲突,甚至与当年想杀死全部家人的父亲重逢时,许地山也只是简笔描述为麟趾只是期盼着和父亲相认。但正是这样的粗线条叙事,突显麟趾执着而简单的信念。《缀网劳蛛》讲述尚洁被丈夫抛弃,独自到士华后,尚洁历经千辛万苦暗地托人给女儿带东西。面对突如其来遭受的外界强烈的冲击,许地山只是简洁描述了尚洁独在异地的生活,许地山留给读者一片自由想象的广阔天地,读者能深深触摸尚洁那始终平静的内心。许地山小说散发一种空灵之美。“许地山文笔空灵,当代作家中罕有其匹。”[5]
许地山非常善于营构意境。在他笔下,一些传统意象往往信手拈来,并得以巧妙组合。在《梨花》中雨中梨花的意境、可爱调皮的少女、诗意盎然的语言构建了这篇短篇小说的独特韵味。在许地山作品中不仅黄昏、秋月、残阳、茅舍、化蝶等古典意境不断得到激活和展现,并且使它们与人物故事产生了相互映照的绝妙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许地山的小说中意象的引入增加了情节叙事的多重意味。在《命命鸟》中对仰光瑞大光塔的多次描写预示着敏明与加陵的爱情遭受外力的阻挠越来越大,让人对敏明与加陵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光”的意象起到了创造结构张力的作用,光不断变幻着,日光—佛光—月光,敏明与加陵的爱情经历了萌发—发展—受阻—寂灭。而这些意象不但参与了叙事也丰富了主题,使得这部小说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所以在许地山笔下意象的运用看似与西方现代派的意象手法相同,但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对境界的追求。而异域文学意象与民俗生活景观的融入是许地山创作的重要特色。比如命命鸟、仰光的涅槃节、优钵昙花等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马来半岛上的棕林、金的塔尖、银的浪头等的描写充满了浓浓的东南亚风情的异国情调和深刻的寓意。
中国文学以诗入小说的现象源远流长,这是中国古典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作用是变化发展,千姿百态的。但近代以来,诗入小说逐渐被摒弃,到了五四时期,已然很少见到诗入小说了。茅盾就曾批评旧小说在人物出场来一出西江月或者什么古风,实在没有美感。从中国现代文学以降,以诗入小说的作品都被认为是同中国旧文学有血缘关系。其实诗入小说自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各自的美学功能,这是小说创作的民族形式,是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许地山的小说常常穿插着诗句。他在小说中不拘一格的引入诗词,甚至引入粤讴、缅甸的“恩斯民”曲调。这些诗词起到渲染小说氛围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作用。在其小说《换巢鸾凤》中几段粤讴不但衬托出一位南方官宦小姐的柔美清丽,而且把一位少女对爱情的痴恋刻画得细腻动人。《缀网劳蛛》、《枯杨生花》等开篇一首诗就引入主题,而且将诗意寓于情节之中,使得意境更显隽永悠长。
三、结语
许地山的小说总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而又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这熟悉的感觉体现了许地山对本土审美形态和审美心理的认同和自信,而这新质的阅读感受则是许地山自觉的变革精神带给我们的创新。这是许地山寻找的五四短篇小说的表达方式。在新文学发展的初期,现代性与民族性被置于对抗的两极,五四小说疏离了民族传统,甚至建立了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的话语范式。这样的后果是逐渐偏离了文学平民化、大众化的初衷,甚至导致了自身失语。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具体特征。[6]所以正视和建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是每个民族存在、成长的内在追求。许地山的创作中呈现了现代性和民族性双向交流并融合的状态。这使许地山的小说创作显示出独特的魅力。这就是许地山为处于民族困境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探索的一条适合中国民族特性的现代化道路。许地山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追求在此后中国文学发展中持续得到回音。中国现代文学逐渐立足于本土立场而不断调整现代性追求。
[1]江萍.文学的现代性中几个概念问题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综合版),2012,(2):101.
[2]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71.
[3](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491.
[4]孟悦.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J].文学评论,1985,(3):78-79.
[5]金庸.浙江港台的作家-金庸回应王朔[N].香港:明报月刊,1999-12.
[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11.
(责任编辑:罗智文)
Modernity and Nationality:the double pursuit of Xu Dishan's Novels
LIAO Xiao-mei
(Literature and Media Institute,Longyan University,Longyan 36400,China)
ct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of Westernization,The modernity goal of"advanced"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national reference and opposition of the"backward".Xu Dishan's novels present the state of the two-way communication between modernity and nationality.He tries to construct a new possibility of the modern novel development:both modernity and nationality are suitable road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modernity,;nationality;Two-way communication and depth of fusion of the double pursuit of novel narrative
I207.427
A
1009-3583(2016)-0062-04
2016-3-06
海西青年攀登项目“现代性视野中的许地山”(Lyxy2011005)
廖晓梅,女,福建龙岩人,龙岩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