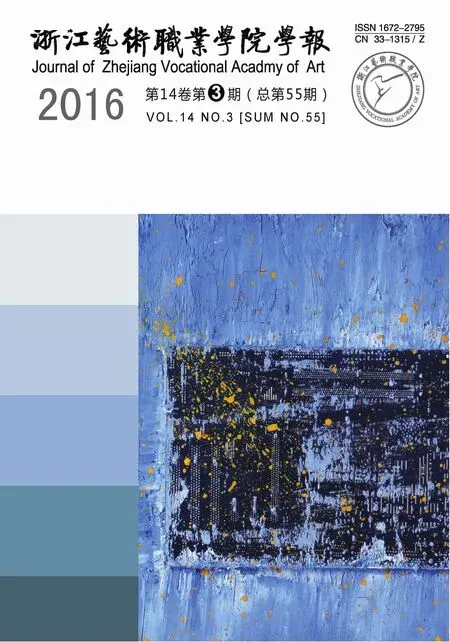论“高级的平庸”:艺术史观念下的当代艺术∗
2016-02-14赵笺
赵 笺
论“高级的平庸”:艺术史观念下的当代艺术∗
赵 笺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艺术正表现出这样的特征:一种由同质化造成的平淡和无趣——尽管表现形式上趋近于无限,其内涵却近乎于零。这种“高级的平庸”似乎表明:当代艺术是片段的、支离破碎的、个人体验式的。然而尽管无法被纳入到传统艺术史的叙事逻辑当中,“高级的平庸”却并非当代艺术所应当呈现出来的正常状态。一方面,当代艺术标志着艺术被哲学所取代,其意义的建构应当以哲学的方式完成;另一方面,形式限定原则对于当代艺术依旧有效,当代艺术必须依赖某种形式构建起不逊于以往的艺术价值——这既是“高级的平庸”的破解之道,也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
当代艺术;艺术史;价值判断;形式限定
2015年上半年,在接受中国媒体的一次专访中,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艺术展总策展人奥奎·恩维佐(Okwui Enwezor)被问及这样一个话题:全球的成功艺术家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同质化同样呈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拼贴、波普、影像等等手法都差不多,这让看多了世界各大双年展的观众心中认为当代艺术有一个“高级的平庸”趋向,即每个人都做得很好,但是看上去都差不多。这位策展人的回应是,威尼斯双年展绝不会出现“高级的平庸”,每一届的双年展肯定都推陈出新展现出和上次不一样的方面。然而,这样的回答似乎并不怎么令人信服。因为“高级的平庸”所指向的,并不是一个创造性问题——没有人会否认当代艺术的创新与前卫,人们甚至对此已经开始感到麻木——而是一个艺术史观念下的价值判断和认定问题。
面对艺术,人们除了观赏并且获得某种审美愉悦之外,往往还会习惯性地去探究作品的历史价值。所谓“历史价值”,简而言之不外乎这样两个方面:它与之前的艺术间的关系,以及它所能揭示出的某种未来艺术的发展趋势与方向。可以说,这种价值判断(无论其判断依据是什么)的累积,构成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艺术史文本的基本面貌;而随着这种“基本面貌”不断被强调并固定成型,艺术史成为了一种强势的力量——它承前启后、流传有序,并站在一种价值观的高度上俯瞰一切的艺术并加以取舍。然而面对当代艺术,今天的人们却陷入到了一种空前的危机和惶恐当中:许多打着艺术名号的作品,我们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更不知其将去向何方,因而无法将其纳入固有的艺术史框架中;但是人们不敢妄言它们没有价值,因为这些作品看上去无不制作精良、形式独特且充满机心、难以捉摸。至此,“高级的平庸”一说粉墨登场。用这样一个词去描述当代艺术的某种现状似乎是恰当的:“高级”,体现的是艺术作品呈现出的质量,这在当代艺术中具体表现为作品制作的精度、难度或者是某些看似简单的形式下作者所投射在作品中的心智;“平庸”,则不仅仅在于同质化生活所带来的作品面貌的雷同,而是更在于当面对一件当代艺术作品时,你很难进行一个价值评判,即认定某一件作品好于另一件。过去那种所谓的“伟大的艺术”的说辞,在当代艺术领域中显得如此苍白。正如阿瑟·丹托所言:“尽管艺术还会以我称之为后历史的样式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其存在已不再有任何历史意义了。”[1]由此丹托阐发了他的著名观点“艺术的终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终结”的是艺术叙事而非艺术事实,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艺术史的终结。这是一个并不新鲜却一直被热闹讨论的话题,尤其对于艺术史的研究者们来说,如果当代艺术写作不再以历史意义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而只是对于现象的记录和描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艺术史”真的就此完结?
一、叙事终结:艺术史写作的危机
在讨论当代艺术问题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传统艺术史的观念。简单来说,传统艺术史写作的基本方法是,把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编排在一个时间的序列中,使其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故事的一部分。以贡布里希的著作《艺术的故事》为例,他的故事从法国南部拉斯科的史前岩穴壁画和一些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原始艺术开始,但这却不是贡布里希所讲述历史的真正起点。在全书第二章的开始贡布里希写道,“我们今天的艺术,不管是哪一所房子或者是哪一张招贴画,跟大约5000年前尼罗河流域的艺术之间,却有一个直接联系的传统,从师傅传给弟子,从弟子再传给爱好者或摹仿者”[2],进而他指出埃及艺术的“无比重要”,而整个西方艺术史也由此拉开了序幕。艺术的历史,在贡布里希看来就是一个孜孜不倦追求新思想的过程:接过埃及人艺术财富的希腊人,在建筑、雕塑、装饰陶器上发展出更为自然和现实的风格,贡布里希称之为“伟大的觉醒”;而12世纪后半叶哥特式风格超越罗马式风格,以及13世纪末意大利艺术家再次超越法国艺术家所进行的绘画艺术的革命,背后都离不开某种新思想的推动;从乔托开始,艺术史变成了“艺术家的历史”,其发展模式依旧是后人以新的思想和趣味去不断超越前人……今天,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毫无疑问早已成为这一类型艺术史写作的典范——当然,他的描述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关于该书当中具体问题的讨论并非本文重点,因此也无需赘述。无论如何,通过《艺术的故事》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传统艺术史是叙事的历史。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也是如此。故事有起因、经过和结果三部分,故事情节从一个结尾进展到另一个结尾,前一个情节往往被当作当前情节的史前史。故事情节需要连贯性,需要有可追溯的结果、原因和影响,每件事最终都得以解释。”[3]
梁启超在1902年所撰写的《新史学》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如同一般历史写作那样,事实上贡布里希的艺术叙事背后,同样有着强烈的进化论色彩。这种进化的模式是如此完美以至于传统的历史写作者很难摆脱其套路:在艺术史的背后,存在着某种规律和准则(一种类似于“时代精神”式的东西)支配着事物不断地向前发展;在此引领下,“大师”和“杰作”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了叙事线索的各个环节当中,例如文艺复兴涌现了达·芬奇和卡拉瓦乔,而1937年的轰炸悲剧造就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这些人物和作品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都是应运而生的,是时代精神的承载和产物。尽管今天的研究者们不断提醒自己和读者,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不能简单地类比和等同,就像贡布里希很少说某个时期的艺术要优于其前代的艺术,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往往还是容易陷入到进化论根深蒂固的影响当中去。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发展与进步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成为了传统艺术史家判断价值的标准:就西方而言,这种观念从瓦萨里的写作开始,直到贡布里希依旧十分鲜明而强烈。
如果说进化的观念在一切的历史写作中都有所体现的话,那么对于绝对价值的标榜,则是艺术史写作的特殊之处。举例来说,蒸汽机的改良引起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因此被看作人类技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但到了科学全面繁荣的今天,蒸汽机的价值早已微乎其微,其意义只是作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之物被记录下来。但类似的状况发生在艺术上却大不一样:米隆的《掷铁饼者》,尽管今天看到是罗马时期根据米隆的青铜原作仿制的大理石摹品,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将其认定为希腊艺术“伟大觉醒”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尽管已距今两千五百年,这件作品仍被视作“空间中凝固的永恒”在多个博物馆受到人们的瞻仰和膜拜。在人们看来,伟大的艺术既是时代精神的载体,同时也具有跨越时代的绝对价值。朱光潜先生在卢浮宫观摩《蒙娜丽莎》后感叹:“凡是第一流美术作品都能使人在微尘中见出大千,在刹那中见出终古。”[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认为,艺术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窥见艺术史观念中的“艺术”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它既凝聚了其所处年代的时代精神和品质,又具有某种超越时间、阶级、种族的永恒价值。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涉及当代艺术写作问题时,传统艺术史的研究者大多表现出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一个最直观的理由是,许多当下的艺术现象由于距离我们太近,还未能真正显示出其来龙去脉和根本价值,因此当代只言修志,尚未能谈到治史,所谓“当代艺术史”不过是一个伪命题。从历史经验看,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像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野兽主义(Fauvism)、立体主义(Cubism)这些名称的出现,都来自当时人们的讽刺和贬低;凡高一生穷困,其艺术在他有生之年始终未被人们认可;1910至1912年间,罗杰·弗莱组织展览向英国观众推介以塞尚为代表的法国现代艺术时,被公众和媒体称为“骗子”和“诈骗犯”……这些艺术史上的小插曲无时无刻地提醒我们,冀望去准确把握自己身处时代的艺术往往是困难的,真正的艺术价值需要经过时间的积淀和考验方能显现。
这种将历史交由时间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但需要注意的一个实际情况是,即便我们拥有等待的耐心,但当代艺术所带来的价值失位,以及传统艺术史叙事的戛然而止,还是会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艺术史写作问题有所忧心。对于这种状况的处理方式之一是,从根本上否定当代艺术,认为其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场无聊闹剧,而艺术终究将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例如从1991年开始,针对当代艺术的危机在法国出现了一轮持久的辩论,肇始的是三本左派刊物《精神》《电视纵览》《周四事件》,主要参与者为多麦克、克莱尔、塞纳、普拉代尔,论战过程中又有像波德里亚和福马罗利这样的人物的加入。辩论中针对当代艺术的观点主要有:“当代艺术枯燥无味(多麦克、克莱尔、勒·博、莫里诺[Molino]、塞纳);它不能引发审美感受(多麦克、克莱尔、塞纳);它在思维层面上弄虚作假,为的是掩盖其空洞、毫无意义的本质(波德里亚、多麦克);它毫无内容(塞纳、多麦克、波德里亚);确切地讲,它四不像(多麦克、克莱尔、塞纳);没有审美标准可以适用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有参与者);它无需任何艺术才华(多麦克、克莱尔);它是历史中枯竭的艺术(莫里诺、勒·博、塞纳);它是过度历史化的产物(同上);它不再是具有批判性的艺术(戛亚尔[F.Gaillard]、布努[D.Bougnoux]、莫里诺、塞纳);它纯粹是市场的产物(所有参与者);它是艺术圈及其在国际上、在美国以及上流社会的关系网阴谋策划的产物(多麦克、克莱尔、福马罗利、塞纳、波德里亚);它是官方的艺术(多麦克、克莱尔、福马罗利);它只能在美术馆的庇护下生存(多麦克、克莱尔);它与公众隔绝,后者对其一无所知(所有参与者)。”[5]这些质疑基本涵盖了我们今天对于当代艺术的所有负面看法,但显然,这些看法大多是从“艺术—历史”的传统视角出发,将当代艺术置于一个广阔的艺术框架下加以审视。这个框架以现代主义为界,现实主义之前的核心词是审美,之后则是形式——塞尚孕育了立体主义,再到抽象主义,接着是极简主义,最终走向观念艺术的空、白、无……至此,观念艺术似乎还是可以被纳入到这个所谓的艺术史的序列当中的,但实际上已经十分勉强;很快的,当代艺术狂飙突进且漫无目的式的生长,使得一切将其纳入到某种体系中的努力都变得徒劳。
回到“高级的平庸”。这种说法听上去还算客气,但就本质而言与上文中的质疑实际是一回事。无论如何人们承认,当代艺术是一种新的东西,而在现代主义艺术史叙事的理解中,“新”往往代表了进步。但眼下,这种进步似乎和以往艺术史中任何一个阶段的情形都不一样。在从前,一种新的风格在其出现之初或许会遭受质疑和嘲笑,但很快的,总有一些“有识之士”——那些睿智的艺术史家或是艺术批评家——会为普罗大众揭示这些新艺术、新风格中尚未为人所认知的价值所在。但在当代艺术中,即便是专家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他们无法用一种连贯的方式解释这些艺术作品的前因后果及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对艺术作品的解释只能归结为个人的经验和阐释,甚至艺术家本人的动机也可被忽略。在艺术的固有法则、规范及判断标准都失效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人人都可以是独立的(不依赖于任何专业指导的)艺术欣赏者和鉴定者。因此,所谓“高级的平庸”,它所指向的与其说是当代艺术的危机,实际上更像是艺术史写作的危机——这一点从上文中的那些才子们对于当代艺术激烈却又概念化的言辞攻击中可见一斑:审美、趣味、本质、批判……以往所有的标准都失效了。
二、艺术史观念外的当代艺术价值判断
当代艺术当真如此不堪吗?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应当是某种开启真理的场所,因为“比起艺术作品,自然和日常世界有一种坚硬的外壳,使得心灵较难于突破它而深入了解理念”[6];但他同时也提醒我们,“无论是就内容还是就形式来说,艺术都还不是心灵认识它的真正旨趣的最高的绝对的方式”[6],这也成为了“艺术终将终结”说法的理论基础。而阿瑟·丹托,与其说他是艺术终结论的提出者,不如将其视作“艺术终结”的宣告者。在他看来,20世纪60年代的波普艺术以真正哲学的形式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是艺术,而某种和它一模一样的东西——一个普通的布里罗盒子,一个普通的汤罐子——却不是艺术,特别是当艺术品与真东西是如此相似,以至无法加以分辨的时候。至此,如同黑格尔预言的那样,精神意识到了自己,便抛弃美的艺术这个旧情人,投奔哲学的新欢,即艺术被哲学所取代。按照这样的理论,当代艺术是某种从根本上不同于且高于传统艺术的东西,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成为某件悬挂在墙壁上的装饰品为目的,而是指向精神和观念本身。举例来说,杜尚著名的小便池绝非一个审美沉思的对象,也不具有任何视觉形式上的意义,而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哲学问题:为什么这是艺术?在1917年以如此方式对传统的艺术概念提出如此问题,这样的创举构成了杜尚以及这件作品的伟大之处。其实不仅仅是小便池,当代艺术中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都具备这样的品质:作品并非强行传递和表达艺术家的某种观念,而是引发人们去思考了某个问题。向自己、向他人乃至向这个世界发问,并引起一段思考的过程,这难道不是一种哲学的方式吗?就此而言,阿瑟·丹托认为当代艺术的出现使得哲学取代艺术成为现实的观点,并非一种自说自话式的痴人说梦。
“假如艺术没有进化到将‘什么是艺术’这个哲学问题纳入艺术的核心区域,那么以上的情况(艺术哲学与普通人对艺术的兴趣极少产生关联——本文作者注)就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随着艺术进化到哲学,)艺术哲学不再站在艺术之外,用不相关的、外行的眼光打量这一主题,而成为这一主题的一种内在表达。看起来似乎是,全部的艺术品只剩下为哲学所感兴趣的那么一两件,以至于没有为艺术爱好者留下余地。”[7]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当代艺术在某些时候被诟病为一种不堪之物的原因,人们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些虽然被称作是艺术、但却与之前的艺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突破,例如用空间的观念替代绘画、雕塑和建筑,用运动的观念替代舞蹈、诗歌、电影,以及用声音的观念替代音乐……而是一种认识上的革命:艺术不再面对和依托贯穿过往和未来的整个历史,它不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真正具备了某种绝对意义上的独立性。这种转变令以往那种在历史中寻求意义的做法失去了价值,事实上也沉重打击了一大批原本被认为具有非凡历史判断力和洞察力的艺术专家。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传统艺术史中的“艺术”也表现出一种超越时间、阶级、种族的永恒价值,但这种“永恒”却是在被编排进一个历史序列当中之后,在一定的背景和上下文关系中凸显出来的。相比之下,当代艺术的全部核心在于作品所提出问题的意义(抑或是黑格尔所说的“纯粹思考”)——我们姑且将这些问题都看作是哲学层面上的,像“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将要去向何方”这样的哲学命题,无不是能够超越历史、超越高低优劣的判断,构成一种永恒的价值。而今天许多鱼目混珠的当代艺术,在忙着制造奇特外形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样一种价值的建构。许多艺术家毫不羞耻地声称,他们的艺术不追求任何意义,而是完全来自个人的生活体验——这样的说辞不仅虚伪造作,而且显然有违艺术家应当具备的本质。
如此说来,当代艺术的核心是一种类似于哲学的、超越历史的、无差异的东西,但这并不代表承载了哲学命题的当代艺术因此就没有了优劣之分。尽管本文作者认同阿瑟·丹托有关艺术叙事终结的观点,但对丹托所言所有艺术都是同等和无差别的艺术(all art is equally and indifferently art),却有不同的见解。本文的观点是,即便是当代艺术,其好坏也是有所区别的,标准不在于作品背负的哲学命题本身,而是表达手法的高超与拙劣,即形式限定的原则。这听上去是一个十分老套的概念。按照传统的艺术观来看,如果“纯粹思考”是一件当代艺术作品的内容,那么表现这一思考的手法就是作品的形式——虽然在许多学者的阐述中,当代艺术的“形式”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存在和依赖某种“形式”,是当代艺术还能被纳入“艺术”范畴的根本原因;而形式限定的原则,则是针对一切艺术加以判断的根本标准。
这里的“形式”当然不是指具体的传统艺术技法,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形式”几乎是一个极其广义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概念,它甚至可以挑战人类认知的底线,而这也为其带来了诸多昭著的恶名。1987,美国黑人艺术家塞拉诺推出他的摄影作品《尿液基督》,照片中受难的基督雕像浸泡在艺术家自己的尿中。之后,这件作品被美国的一家艺术机构授予一项视觉艺术奖,并受资助进行了三个城市的巡展。然而,此事却遭致一些宗教团体以及大量民众的不满,认为该作品有渎神之罪;随后,该事件愈演愈烈,影响从地方扩散至全国——有25名国会议员签署联名信,要求“国家艺术捐助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of Art,简称NEA)完善评审、资助制度,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尽管塞拉诺在解释自己的动机时,认为将耶稣置于尿中,表现了圣洁与污秽、善良与邪恶的二元关系,但此事依旧作为当代艺术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被记录了下来。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 1994年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览“界限之外”计划展出黄永砯的作品《世界的戏剧》,作品是一个爬满昆虫和爬行动物的容器,生物在当中互相吞噬。最终因为动物保护组织和蓬皮杜艺术中心工作人员的干预,作品只展出了一个空空的容器。这两个案例所展示的,都是当代艺术作品对于某种“神圣”的亵渎:前者亵渎宗教,后者则亵渎了生命。在传统艺术史中,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神圣之物,并且向人们传递着神圣的理念——道德、友爱、牺牲等等。但是当艺术转变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哲学是比宗教、道德更高的范畴——难道它不能对宗教和道德展开思考和批判吗?抛开那些令人感到不快的体验,塞拉诺所考虑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及黄永砯所暗示的生存环境,事实上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而如果观者愿意尝试着放下那些来自于传统艺术观的神圣观念,我们很容易会在这样的作品中获得些许有益话题和严肃思考。
当代艺术“形式”的另一方面恶名则来自它的虚无主义倾向,然而某些时候,“无”本身也构成了当代艺术的一种表达形式。打开《寻常物的嬗变》一书,扉页上写着这样的文字——哈姆雷特:你什么都没有看到吗?皇后:什么都没有,但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这种无即是有的观念,不禁令人想到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1958年时的展览《空》(The Void)。艺术家将一个空空如也的房间作为他的展览——抑或者说作为他的作品展示给公众。此刻,“空”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克莱因作品的形式;艺术家用这样的形式引发人们对于艺术展览乃至艺术品概念的反思。这是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称得上是运用了一个恰当的形式表达出了某种引人思考的观念。另一个在笔者看来相对不太成功的例子是,2001年马丁·克里德(Martin Creed)凭借《时亮时灭的灯》(The Lights Going On and Off)为他博得了特纳奖,作品就是一个空房间里一盏时亮时灭的灯。这件作品的获奖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反对者甚至向房间墙上扔鸡蛋以示抗议。客观地说,这件作品多少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赋予过多图像、信息与意义的作品的调侃和对抗,但从形式限定的角度而言,这件作品显然缺少足够的“形式”来引发人们头脑的运动,以至于公众对其的普遍反应就是无聊。这个案例揭示出以下的道理:“无”应当只是当代艺术表达时所采用的一种“形式”,“无”所指向的应当是某种引人思考的内容;如果什么都不去表达,本质上毫无意义,那么针对当代艺术无聊、无价值的批判就一点也不冤枉了。
三、结 语
至此,我们再一次回到“高级的平庸”问题上。事实上,“平庸”代表了如今当代艺术的某种状况,而“高级”只不过是以一些故弄玄虚的东西对平庸加以装点的方式。如果说,艺术作品能够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直击人们的内心,从而引发思想上的涟漪,那么用“平庸”去评价它肯定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当下的现实是,当代艺术往往无法激起人们思考的兴趣,呈现出一种自娱自乐、索然无味的状态。在形式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当代艺术本该展现出异常丰富多彩的面貌,但是对于意义的无止境的消除,却使得其看上去异常的空洞、无趣和不知所云。不可否认,当代艺术对于传统艺术史的反叛是从解构开始的,但是解构只是当代艺术在某个特殊阶段的表现特征——就像在伊夫·克莱因的时代,当代艺术刚刚崭露头角,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势、巨大的艺术史传统,此时不断地对其加以解构是有必要的。而且必须认清的是,那一时期的当代艺术所解构的,是艺术史的传统而非其自身;换而言之,当代艺术自身恰恰是在对传统艺术史的解构中建构起来的。按照黑格尔—丹托的理论脉络,当代艺术出现的意义在于其作为艺术走向哲学的标志,那么从哲学上加以建构显然比无休止的解构更能体现当代艺术的本质。用恰当的“形式”去引发哲思从而建立起自身的价值,这是当代艺术应当具有的正常模式,也是“高级的平庸”的破解之道。
[1]沈语冰.20世纪艺术批评[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285.
[2]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55.
[3]理查德·豪厄尔斯.视觉文化[M].葛红兵,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7.
[4]朱光潜.永恒的《蒙娜·丽莎》[M]//.无言之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1.
[5]伊夫·米肖.当代艺术的危机:乌托邦的终结[M].王名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0-31.
[6]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
[7]阿瑟·丹托.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M].陈岸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68.
(责任编辑:黄向苗)
“The High⁃grade Mediocre”:Contemporary Art in the Concept of Art History
ZHAO Jian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s showing such features as more the forms of expression less the connotation inside.Contemporary art cannot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rrative logic of art history but the other method.First,in the area of contemporary art,art is replaced by philosoph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meaning should be done in a philosophical way.In addition,contemporary art must rely on some kinds of art forms to build the value which is as good as the past.It not only is the way to break the“mediocre”,but also provides a useful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contemporary art;art history;judgment of the value of art;restrictions of art forms
J110.9
A
2016-06-02
赵笺(1983— ),男,江苏南通人,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艺术史研究。(南京210013)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新时期主流美术的转向”成果(项目编号: 2013SJB760034);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