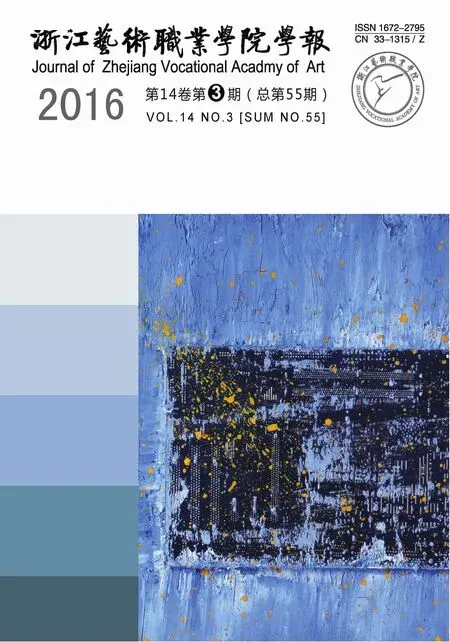食物、性与狂欢:《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夫的吃喝∗
2016-02-14胡鹏
胡 鹏
食物、性与狂欢:《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夫的吃喝∗
胡 鹏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笔下最鲜明、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从物质文化角度分别由食物、性、狂欢等方面来对这一角色进行分析,从而指出吃喝表象下的深层逻辑及其对整个戏剧情节发展的推动作用。
食物;性;狂欢;《亨利四世》;福斯塔夫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富有特色、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他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其所展现出的“福斯塔夫式背景”描绘了“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他的活动为我们展现出早期现代英国社会日常生活的绚丽图景。但正如安妮·巴顿(Anne Barton)指出历史剧和喜剧中的福斯塔夫其实是不同的,从文类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1]凯瑟琳·理查森(Catherine Richardson)指出:“倘若我们想充分理解莎士比亚的戏剧如何产生(戏剧)效果的话,就需要追问他是如何构思台词和(剧中)物品的。”[2]从这点来讲,福斯塔夫的戏剧功能正是作为物质客体的话语中心及物质客体的多种潜在含义而存在着。本文将主要分析《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所展现出的日常生活状态,因为这是莎士比亚第一次描写下层/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福斯塔夫是剧中当之无愧的主角,这种从贵族、伟人到大众、小人物的转向正体现出其早期现代日常审美意识的觉醒。①在《亨利四世》上下两部中,福斯塔夫一人的台词约占20%,位居第一。而且正是《亨利四世》给莎士比亚带来写作生涯的巅峰,福斯塔夫的角色得到了大众的广泛喜爱,伊丽莎白一世甚至下令让莎士比亚为福斯塔夫单独创作了后来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3]福斯塔夫身份的问题无法避免地必须同其戏剧功用和意识形态功用联系起来。就像格林布拉特在其名篇《看不见的子弹》一文中分析指出福斯塔夫是作为颠覆性的多种声音的集合体,却被权力有组织地含纳并最终销声匿迹。[4]但与此对照,他对涉世未深的王子产生负面影响,其对法律和秩序的拒绝是“正确和必需的”,即便这样“莎士比亚自己也从未否定过福斯塔夫”。[5]126本文则试图将福斯塔夫作为《亨利四世》的中心加以分析,特别是其形象与吃喝乃至整个戏剧的关系,指出福斯塔夫的吃喝逻辑及哈尔王子即位后必须对他进行抹杀的原因。
一
虽然福斯塔夫的舞台形象异常生动鲜明,但有时我们也会因为实际上某些方面的文本证据匮乏,而其中福斯塔夫和饮食的关系就是一个谜。虽然他被刻画成大腹便便,但正如多佛·威尔逊(Dover Wilson)指出:“我们从没看到或听到福斯塔夫吃东西或想吃东西,而只有屠夫妻子胖奶奶的一盆龙虾。”[5]27而有关福斯塔夫饮食的实际指涉仅仅出现在快嘴桂嫂的话中:“肥膘大妈,不是来了吗?不是管我叫快嘴桂嫂吗?她来是要借一点醋,还跟我们说她那儿有一碟上好的大虾,你听了就想要几个吃,我不是还跟你说伤口没好,不能吃虾吗?”[6]399显然在这里,福斯塔夫的饮食并不重要。他的贪吃是由他人证明的,所以观众不会在舞台上看到。但即便如此,福斯塔夫也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最明显的证据是皮多在熟睡的福斯塔夫口袋里找到的若干纸片:
波因斯
烧鸡一只 二先令二便士
酱油 四便士
甜酒两加仑 五先令八便士
晚餐后的鱼和酒 二先令六便士
面包 半便士
太子
唉呀!真是骇人听闻!仅仅半便士的面包就灌了这么多得要死的酒![6]275
我们看到哈尔王子在野猪头酒店跳过了贪吃而更强调了福斯塔夫嗜酒的习惯,但他之前将其视为暴食者,特别是嗜肉。因此我们看到福斯塔夫实际上是暴食者和嗜酒者的合体。虽然其他角色总将他和食物联系在一起,他自己则坚持对酒的喜爱。
实际上开设于依斯特溪泊(Eastcheap)的野猪头酒店本身就是依斯特溪泊本身的转喻,因为这一片区曾经是“中世纪的肉类市场”,因此一般和屠夫及肉类生意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哈尔询问巴道夫:“那老野猪(old boar)还是钻在他那原来的猪圈(old frank)里吗?”[6]410,故意将福斯塔夫比作野猪。[8][9]同样桃儿称呼他是“一只满满的大酒桶(a huge full hogshead)”一大桶酒,[6]418也将他和大木桶以及野猪头结合。福斯塔夫一直和屠宰生意有关,在戏剧中同时被当做贪吃的嗜肉者和肉本身。因此哈尔才会随意叫福斯塔夫是“我的美味的牛肉”。[6]306此外,野猪头是一道传统基督教食谱,从而将福斯塔夫与暴政之王(the Lord of Misrule)联系起来。
福斯塔夫四人抢劫过路客商正就地分赃,可没想到反而被伪装的哈尔王子带人吓得丢下赃物而逃。随后他们晚上又在酒店碰头,哈尔王子准备拿福斯塔夫开涮,他命令福斯塔夫出场:“叫瘦牛肉进来,叫肥油汤进来!”[6]254。福斯塔夫先变成了肋骨肉,后又成了价值更低的油脂。舞台上的福斯塔夫成为了食物,会被食用——通过揭露他的懦弱与谎言,哈尔对其进行了比喻性屠宰:“给我来一杯酒,堂倌!”[6]255随后又重复了一遍,而当他得到想要之物后,喝醉的福斯塔夫成为一大景致。因为像其他常见的恶人角色一样,他占据着最靠近观众的舞台位置,其直接的身形动作更增强了醉酒的形态。[10]舞台上一饮而尽的动作成为了福斯塔夫身份的表征,无数有关福斯塔夫的图画和绘画都展示着他好酒的特点。
我们看到福斯塔夫如何猴急地将酒杯一饮而尽,哈尔回到了其食物想象,将这一场景和黄油的融化扭曲联系在一起:“你看见过太阳(泰坦巨人)跟一碟黄油接吻没有?——软心肠的黄油,一听见太阳的花言巧语就熔化了。要是你看见过,你一定认得出眼前的这个混合物。”[6]255在哈尔的阐述中,主体和客体混合了。肥胖的福斯塔夫也许是太阳前熔化的一块黄油,也许是熔化黄油一样“熔化”酒水的太阳。同样哈尔的“混合物”指向了福斯塔夫——他是由肥肉和酒构成的不协调混合物,或者福斯塔夫和酒就像画面中的两种液体物质。满身大汗的福斯塔夫以成为一块黄油结束,呼应了前面哈尔肥油汤的描述。
在哈尔持续描述福斯塔夫的同时,福斯塔夫也念念不忘自己的酒。他抱怨“酒里也掺上石灰水”[6]112,他的观察其实是对年龄的自我讽刺,“这个世界里哪儿还找得到勇气,十足的勇气?你要是找得到,就算我是他妈的一条肚子瘪了的青鱼(肚子瘪了的青鱼,指排卵后的青鱼。这大胖子喜欢用他能想到的最瘦的动物和自己作比)”[6]255。福斯塔夫将自己描述成与其体格和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物体。即便如此,他还是指向了食物。瘪了的青鱼即是排卵后的青鱼,与脑满肠肥的福斯塔夫完全相反。进一步而言,瘦小的、生存时间短的青鱼是宗教节日四旬斋的食物,是福斯塔夫这类快乐角色所最终拒绝的。[11]通过对这种食物的提及,福斯塔夫利用了青鱼的文化内涵来再次强调其自身人物角色的重要特征。
剧中对待食物的不同观点显示出福斯塔夫和哈尔的差异。哈尔将福斯塔夫看做食物,同时福斯塔夫自己强调喝酒是其角色特质,将杯中之酒当做其身份表征,唯一的消极提法是四旬斋的青鱼。福斯塔夫持续对瘦肉和四旬斋食物的谴责:“可是和我交战的要没有五十个人,我就是一捆萝卜。”[6]258萝卜,细小的根茎支撑着硕大的头部,是有关虚弱的另一象征。福斯塔夫之后就描述浅潭法官皮包骨头的外形:“他要是把衣服脱光,简直就十足像一个生杈的萝卜。”[6]453
终于,哈尔无法再忍受福斯塔夫关于盖兹山抢劫事件的谎言,他骂道:“这个满脸热血的怂包,这个压破了床铺,骑折了马背,浑身是肉的家伙——”[6]260福斯塔夫成为会了锅里的动物油脂,但是其与食物自身的联系得以强调。在下篇中,福斯塔夫对大法官说他是“一直狂欢夜的蜡头,大人,整个是脂油做的”[6]385[12]。威尔逊提示我们早期现代tallow语义学上的可能性:“‘油脂/肥油’,通常讽刺、羞辱用以称福斯塔夫,并未得到正确理解,我们需要知道两个事实:首先,它指伊丽莎白时期的脂肪油,也指烤油或板油或动物脂肪提取油;其次,也指人的汗液,部分可能是因为与suet一词类似,与肥肉类同,像是由于身体的热量所溶出的。”[5]28因此福斯塔夫的一走路就出汗,哈尔早前就评论“福斯塔夫流得那一身大汗,跑起路来倒给枯瘦的大地浇上不少油”,为接下来将福斯塔夫比作食用的动物埋下伏笔。在野猪头酒店,福斯塔夫这样回应哈尔:“他妈的,你这饿死鬼,你这鳝鱼皮,你这干牛舌头,你这公牛鸡巴,你这咸鱼”。[6]260福斯塔夫颠倒了哈尔食物比喻的要旨,他用风干的食物来描述哈尔王子,暗指其瘦弱冷漠。干牛舌头意味着哈尔贫乏的修辞能力,而其余则暗指与其精力充沛、性欲旺盛的反面。福斯塔夫同样将哈尔比作食物,但是仅仅是与自己对比,王子只是少量进食用以果腹。
在角色扮演一幕中,福斯塔夫扮作国王,将自己比作被宰待售的动物。他采用了反证(ex negative)的修辞策略:“听凭你把我提着脚后跟倒悬起来,跟一只吃奶的兔子或是跟卖鸡鸭的门口挂着的野猫似的。”[6]269正如哈尔挑战了扮演其父亲,福斯塔夫也挑衅哈尔将其当做待售的肉。他恰当地将自己比作倒挂的死兔子,回忆起了战场上的羞辱,即将骑士脚跟倒悬使其蒙羞。而今哈尔假扮其父亲的角色预示着他即将成为国王以及对福斯塔夫的处置,表明了其最终抛弃了“野蛮王子”的面具:“有一个魔鬼变作一个肥胖的老人模样,正在纠缠着你,有一个大酒桶似的人正在伴随着你。你为什么要结交这样一个充满毛病的箱笼、只剩下兽性的面柜、水肿的脓包、庞大的酒囊、塞满了肠胃的衣袋、烤好了的曼宁垂肥牛,肚子里还塞着腊肠、道貌岸然的邪神,头发斑白的‘罪恶’、年老的魔星、高龄的荒唐鬼?”[6]271此处复杂的比喻戏剧性地制造出哈尔和福斯塔夫构成身体-食物指涉上的张力。哈尔对福斯塔夫的宗教定义是“恶角”,是传统宗教剧中的邪恶角色。而这些指涉又逐渐转变成食物的想象,并最终成为了烤熟的动物。此处三种食物中,第一种酒是福斯塔夫最爱的液体,第二种腊肠,最后一种肥牛。福斯塔夫变成了填充上等食物以供整个宴会食用的动物。而后两个指涉则暗示着剧中更广泛的福斯塔夫-食物比喻。哈尔特别将福斯塔夫比作“曼宁垂肥牛”,曼宁垂是埃塞克斯的一个城镇,“以圣灵节集市著称,特别是烤全牛”。[13]哈尔选择和地方传统相关的动物可被视为另一种历史节目中充满英国性的物件;此外,这一指涉强调了通过福斯塔夫具现的节日庆典氛围。莎士比亚反复将福斯塔夫比作节日中食用之肉,例如波因斯问巴道夫:你主人是不是还肥得像马丁节(Marlemas)前后杀的猪牛似的?[6]40811月11日的圣马丁节上会“杀牛、羊、猪和其他动物,为过冬做准备,因为冬天新鲜的食品会变得短缺甚至于无”[14]。波因斯的话有两种互补的阐释:福斯塔夫本身就是节日,或者他是节日上待宰的动物。在文本中国所有其他有关福斯塔夫和肉的类比中,后者决不能忽略。最明显的有关福斯塔夫作为特别节日上美味的肉食比喻是桃儿的话:“你这婊子养的,巴索罗缪(Bartholomew)市集上出卖的滚圆的小肥猪。”[6]206这里的指涉又将福斯塔夫和伦敦8月24日举行的一年一度狂欢节——圣巴索罗缪节联系起来,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伦敦最流行的节日之一。这一来自于福斯塔夫最爱的妓女的绰号,又与其身体闭塞带来的性饥渴相连;桃儿在性与经济上都依靠福斯塔夫,节日上尽情享用的小肥猪,公开显示出桃儿的食肉和性欲望。
二
哈尔表述福斯塔夫是肉的第二个指涉物体是“腊肠”。动物的内脏是一种流行且便宜的食物。福斯塔夫的肠子,其便便大腹中的内脏是其自身的转喻,是作为其身体最重要部位而常常被提及。如“肥肠fat-guts”以及“带着你的肠子跑”。[6]239巴赫金就解释说如肠子等内脏是与狂欢传统相关的高度意义化的食物:“腹部不仅仅是用以吃和吞,它也被吃……进一步说,内脏与死亡相关,与屠宰、谋杀有关,因为取出内脏意味着杀戮。同样也与诞生相关,因为腹部也繁殖。因此,关于内脏的意象中,诞生、排泄、食物都连接在一个怪诞的节点上;这是身体地理学的中心,上层和下层组织相互渗透。这一怪诞想象是物质身体下层组织矛盾状态的最爱的表达方式,其既破坏又生产,既吞咽又被食。”[15]巴赫金对拉伯的解读,可以准确的描述作为食物的福斯塔夫丰富了戏剧中比喻的物质性特征。
福斯塔夫的肠子在被解读为反抗身体政治中又获得了更多层次的意义。作为狂欢文化的具现,福斯塔夫的“反抗首先就是腹部”[16]87,其作为修辞的中心作用就是成为戏剧情节的马基雅维利权力政治的反抗和物质他者。从这点上讲,莎士比亚将腹部作为相反的意识形态,福斯塔夫则是有叛乱潜质的贪婪的肚子。哈尔为福斯塔夫改名为“大肚子约翰爵士”,则戏谑地承认并打击了福斯塔夫肚子所代表的权力。在戏剧开场,亨利四世通过介绍性独白中高度凝练的意象表达出其统治的千疮百孔,他谈到“不久以前在自操干戈的屠杀中,刀对刀,枪对枪,疯狂地短兵相接”[6]204。佛朗索瓦·拉罗克(Francois Laroque)在将这一意象解读为反对福斯塔夫不受控制内脏的物质呈现:“自然引导了将附属的‘内部’与福斯塔夫肚子或‘内脏’的等同,其作为狂欢事物的食物和内脏的一部分。”[16]91
作为继承人,哈尔暗示着国内局势的动荡威胁着其父的王位。然而,他已经决定在继承王位之后变得跟他严厉且独裁的父亲一样。他知道这将疏远扮演代理父亲角色的福斯塔夫。这就解释了哈尔在角色扮演场景中冷酷的食物类比,即莎士比亚设计展现出其最终对福斯塔夫的拒绝和否定。也是在福斯塔夫质疑其皇室权威时哈尔不能忍受福斯塔夫的腹部的原因:
福斯塔夫:你以为我怕你跟怕你爸爸一样吗?不,我要是那样,但愿我的腰带断了!
太子:唉呀,要是你腰带断了,你的肠子还都不耷拉到你膝盖下面来了!你这家伙,你肚子里哪儿还有容纳信心、诚实和天良的地方啊!光装肠子和隔膜还不够呢![6]305
福斯塔夫怪诞的肠子和膝盖具体化了其畸形而缺陷的角色;这位膨胀的吃货没有高贵、无形的美德,有的仅仅是他自己享乐的肠胃。其放荡而堕落的身体不会惧怕未来的国王,权威的力量将把福斯塔夫吞噬。
在《亨利四世(上篇)》中,权力的主题和吃、食物的主题最终在战场上合而为一。当福斯塔夫强调为王而战时,最明显莫过于他对荣誉和骑士精神的蔑视和不屑:“咄,咄,左不过是供枪挑的,充充炮灰,充充炮灰(food for powder)。”[6]319战争充满了对人类血肉的渴望,在最终的战斗中,莎士比亚戏剧化地支持着福斯塔夫的肠胃。作为一个节日角色,福斯塔夫明显不该放置在战场上,正如他告诉观众:“愿上帝别再给我铅吃啦!光是肚子里这点肠胃,我已经重的够瞧的了。”[6]342这是福斯塔夫首次关心其肚子安危,对他而言,武器仅仅是和平时期用以自我表演的道具:
福斯塔夫:……你要的话,我可以把我的手枪给你。
太子:给我吧。怎么,在这盒子里吗?
福斯塔夫:不错,亨尔,滚烫的,滚烫的。它可以让一个城市的人都不省人事。[太子自盒中抽出一瓶酒]
太子:怎么?现在是玩笑捣蛋的时候吗?[把酒瓶掷向福斯塔夫,下][6]343
福斯塔夫的双关是混乱的,他的身份表征也是不合时宜的。作为一个不变的节日创造物,福斯塔夫不能在战争期间退场。为了继续其早期表征,他想象自己是对叛乱角色的烹饪治疗处方:“潘西要真还活着,我就把他的皮给剥得稀烂。要是他找到我头上来,那就没得说的了。要是他不来找我,我偏偏一心一意地找他,那就让他把我切作烤肉好了。”[6]343福斯塔夫自我描述为烤肉,也是其常用的反证风格。
而福斯塔夫与肉的类同以及福斯塔夫肚子主题在战役的决定性瞬间达到高潮。哈尔与霍茨波、福斯塔夫与道格拉斯的战斗——前者是对等的,而后者则是不对称且滑稽的,以霍茨波的死亡和福斯塔夫的倒地装死告终。哈尔赞扬了荣誉和骑士,认出了福斯塔夫:
怎么,老相好?难道你这一身的肉,还保不住一口气吗?可怜的杰克,再见吧,失去你比失去一个正经人更使我难过。假使我只知道享乐,一想起你,我心头会感到沉重。死神在今日的血战中大肆凶威,猎取了许多人,谁也比不上你肥fat a deer,不久你就要开膛了;现在,对不起,请你在血泊中和潘西一起安息。[6]349-50
这里哈尔使用了狩猎的象征主义,而deer与dear的双关常常出现在伊丽莎白时期的爱情诗中,用以表达对这位胖朋友的哀悼。显然,他又提到了福斯塔夫反抗的肚子;哈尔将亲眼看着福斯塔夫这头肥鹿被开膛破肚(把死尸开膛,涂上香料和药,好保存尸体)。在哈尔将他比作死去的肥鹿之前,福斯塔夫就以及被多次比作鹿。他含糊地自称为“流氓rascal”,但在早期现代英语中则含有“年轻、瘦弱或鹿群中的下等品种”等含义。在爱德华·贝里(Edward Berry)对莎士比亚与狩猎的研究中,他讨论了哈尔在战场上希望对福斯塔夫开膛破肚的场景:“开膛破肚取出内脏以便进行腌制或烹饪显然是一头死鹿不可避免的命运,特别是处于盛年‘血肉充盈’的肥鹿……作为一个男人,福斯塔夫是卑鄙的,因此实不再此列。这里主要强调了其不光彩,然而,哈尔自己却没有察觉到的是对血液的保留:他没有躺在血泊中,而是在血泊中。作为一头鹿,福斯塔夫很难‘躺在血泊中’;尽管又老又肥,他已非壮年,哈尔忽略了这一事实。”[17]哈尔准备将福斯塔夫开膛取出内脏也可以另外解释:“从尸体上取出内脏是荣誉,因为准备用相连来保存尸体以免遗留在战场的乱尸堆中。”[18]哈尔也暗示了这种仪式将给福斯塔夫一种骑士的荣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斯塔夫的开膛破肚物质化了其大腹中的多样性。
但是,放荡的狂欢国王的身体再次起身,宣告着其作为一种变质食物的状态:“开膛了?你要是今天给我开膛,明天我就让你给我腌起来吃下去。”[6]350福斯塔夫解释了周围食人欲望以及狂欢复活延缓他们的实践。他拒绝被开膛,与作为意识形态反面的霍茨波形成相连对比,霍茨波实践了战士的荣誉精神并最终成为了食物:
霍茨波:不,潘西,你就是尘土,只能供——
太子:——蛆虫吃,潘西,再见吧。[6]348
最终,英勇的潘西将被吃掉,而福斯塔夫则没被杀掉,保留了其硕大的肚子。福斯塔夫和霍茨波是两个极端,一位是对享乐孜孜以求,一位则是对荣誉念念不忘,哈尔必须回避两者以便成为他理想中的完美君王。他可以从肉体上杀死荣誉的模范将其变为蛆虫的食物,同时他必须等待适当的机会放弃、否定享乐原则的具体化身。
三
福斯塔夫身体有反抗的肚子必须被驱逐出权力中心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其性别。性别批评家们谈论着福斯塔夫代表着对历史上描述的男性同性暴力和权力阴谋的一种女性威胁:福斯塔夫蔑视荣誉和军人的勇猛,他在战场上的怯懦,他的有始无终,他的装死,他的肥胖,以及对肉欲的纵容都暗示着早期现代英格兰区分精神/肉体、高雅/粗俗、男性/女性类比系统中的娇弱和女性气质。[19]
哈尔从一个野蛮王子到强权君主的转变需要否定拒绝一切女性气质。福斯塔夫是女性特征的具体化身,他的身体不仅仅是贪婪的肠胃,也是诞生事物的子宫。即便他持久的对女性的性欲也意味着这些男性权力戏剧中的女性,正如霍茨波告诉他的妻子:“这个世界不是让我们玩娃娃和拥抱亲嘴的。”[6]47丽贝卡·安·巴赫(Rebecca Ann Bach)就将福斯塔夫作为历史剧中怯懦男人群体的中心:“福斯塔夫是柔弱的,在历史剧中像个女人,因为他是个懦夫,他自我放纵,而且他所有的欲望都失去了控制。福斯塔夫不像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真男人,热爱生命、喜欢女人。历史剧中突出那些和福斯塔夫分享品质的男人都是柔弱的。福斯塔夫在历史剧中与其他柔弱角色(如浅潭、毕斯托尔等)共享了怯懦。”[20]
福斯塔夫甚至想象尝试自己的身体有某些跨越性别的装束:“真是的,我浑身的皮耷拉下来就跟一个老太太宽大的袍子似的!”[6]299同样这种思想也被哈尔接受,他想象着非现实的角色表演:“我就扮潘西,让那个该死的肥猪装他的夫人,摩提麦小娘子。”[6]254然而,福斯塔夫告诉佩吉其扮演的母亲角色过度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我现在在你前头走起道来,就活像一头母猪,把生下来的一窝小猪都压死了,就剩下你一个。”[6]380他也认识到其身份是由肠胃所决定的:“我这个肚子里装满了一大堆舌头,每一个舌头都不说别的,只管宣扬我的大名。只要我肚子能变得大小再合适一点,我简直就可以是全欧洲最敏捷灵便的人了。全是这大肚子womb,这大肚子,我这大肚子,把我给毁了。”[6]473意为谁只要看见我这么个肚子,就可以立即认出我是福斯塔夫。这里的福斯塔夫肚子里的一堆舌头,呼应了序幕中介绍《亨利四世(下篇)》的拟人化的谣言,一开场就是“‘谣言’上,浑身画满了舌头”[6]366[21]。福斯塔夫明显的多嘴多舌的大肚子就像女人一样,因此对试图控制所有公共话语的国家政权是个威胁。此外,更重要的是,福斯塔夫的肚子像子宫,是反政府权威对应话语产生的潜在根源。
被赋予怪诞子宫和其他女性特点的福斯塔夫对失去母亲的哈尔同样是个威胁。严格讲来,哈尔即使在母亲缺席时也否认其存在,当父亲的信使前来通知他时:“把他送回给我母亲去。”[6]263因为他的母亲已死。哈尔的玩笑暗示着他对母亲的缺席没有任何哀痛,而且在他的世界也不欢迎母亲。福斯塔夫的圆胖、给予生命的、物质身体由于非常物质化而威胁到了哈尔。[22]瓦莱丽·特莱博(Valerie Traub)认为哈尔将女性气质和物质象征结合起来一并进入其父亲的法律和秩序世界,他必须否认和破坏作为“无处不在的母性物质化”能指的福斯塔夫:“哈尔发展成为男性主体不仅仅依靠从身体依赖和想象的身体共生状态的区别和分离,也是依靠与这些状态相联系的性格祛除:母亲,物质。哈尔在《亨利四世》下篇中对福斯塔夫公开的否认和羞辱……表明了他需要使将这种内心威胁具体化。”[23]
对吃的欲望和母性角色的吸收补足了吞噬一切的福斯塔夫的原始焦虑,由是修复了承担欲望和恐惧的这些消失的身体部分。作为哈尔的转移了的母亲角色,福斯塔夫表现出的对身体享受和物质客体的欲望必须在哈尔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加以否定和抹杀。休·格雷迪(Hugh Grady)就指出:“福斯塔夫主体性的源泉就是欲望。戏剧中他的智慧和行为动机就是著名的拉康所谓导致现代主题在无尽的链条中从一个客体到另一个的欲望‘逻辑’。”[24]615因此作为未来的君主,哈尔必须着眼自己对权力的迫切欲望并消除威胁其最高追求的福斯塔夫随心所欲的物质欲望。为了否定作为物质世界欲望和享受的福斯塔夫,哈尔将他当做“塞满了罪恶的大地球”[6]429。
这些部分和抹杀的想象也可以从政治层面进行阐释,性别化的福斯塔夫身体与《亨利四世》中土地的表征重叠。作为一个明显的英国角色,贪吃嗜酒的福斯塔夫成为了英格兰土地自身的清晰类比物,亨利王在想象结束内战时这样说道:“这片土地焦渴的嘴唇将不再涂满她自己亲生子女的鲜血。战争不再用壕沟把田野切断,不再以敌对的铁蹄去蹂践地面上娇小的花朵。”[6]203
地上的壕沟贪婪地喝着自己孩子的鲜血,而这正是在自相残杀(civil butchery)中流出的。这一意象强烈地指出了剧中其他贪婪的饮者,那些从未觉得有足够的酒能涂抹其唇的人。“吸血的大地对血液的渴望就像他对酒的渴望一样!”[16]91哈尔在其否定的独白中将福斯塔夫和大地联系在一起:“别狼吞虎咽了,要知道坟墓为你张着嘴,比任何别人要阔大三倍。”饥饿的大地将吞噬福斯塔夫并实践渗透在两部《亨利四世》中的欲望;在哈尔否定福斯塔夫的时刻,吞噬者被吞噬了,福斯塔夫随后消失在《亨利五世》的舞台上,仅仅在《亨利四世(下篇)》的收场白中提到了这一戏剧所迎合观众创造的食人/食肉想象:“如果诸位的口味对肥肉还没有腻的话,我们这位微不足道的作者就打算把这故事再继续下去。”[6]524
我们一定要还原解读福斯塔夫及其作用的物质客体,那是唯一的属于在颠覆性的节日消费精神中反抗权力的狂欢秩序的物体。失序之王(lord of misrule)和肉片仅仅是福斯塔夫众多化身之一,而与莎士比亚最成功的戏剧角色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文化解读超过了任何单一的解读,消除了任何解读的封闭性。拉尔斯·恩格尔(Lars Engle)指出,福斯塔夫不但符合一个享乐主义者的节日和消费逻辑,更在其对自由的追求中显示出高度的经济实用主义:“福斯塔夫通过明显的自我意识也具现并促进了狂欢和节庆:他知道谁为狂欢买单,也确信不是自己。不论我们是从巴贝尔(Barber)或从巴赫金处得到狂欢理论,这种策略性的节日在福斯塔夫身上则包含了对所有狂欢化已有概念的调整。……巴赫金没有对狂欢节carnivals(欢庆为先)和市集fairs(经济为先)加以区分……他没有看到他所推崇的市集简单语言与降等的价值规则在早期现代市场和集市供需中的可能关系。”[25]
从这点来讲,任何集中于将福斯塔夫当做巴赫金式狂欢的解读尽管正确,但却也忽视了福斯塔夫自己意识形态的扭曲和在困境中圆滑的处事手段。从他在野猪头酒店的债务管理到滥用国王的招牌再到诈骗法官浅潭,福斯塔夫完全是一个狡猾的经济动物。他不但是个著名的放荡者,同时也不能简单将其周围的客体看做狂欢或消费的物品,它们也具有交换价值。格雷迪也和恩格斯持有相似观点,他认为即便在传统的狂欢角色中,福斯塔夫也是从中世纪后期残余秩序到早期现代伦敦熙熙攘攘日益增长的个体市场经济的转移角色:“在现代性的新文本中,狂欢化的福斯塔夫及其世界具现了现代性中急迫的主体性对愉悦和美追求的潜力。它们不再出现于公共的庆典中,而是在从公共形式和开放到所有新可能性和个体想象危险的过程中成为个体的、主观的、自由的。因此福斯塔夫创造了狂欢的一种视角,即通过将新教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推动而再次语境化并赋予新意义的狂欢。”[24]621所以作为在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群体中的再次语境化,福斯塔夫成为了文化的媒介。
[1]Barton.Shakespeare’s“Rough Magic”:Renaissance Essays inHonor of C.L.Barber[C].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1985:131-148.
[2]Richardson.Shakespeare and Material Cultur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4.
[3]Bate,Rasmussen,eds.TheRSCShakespeare:William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M].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7:898-899,892.
[4]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Renaissance England[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21-65.
[5]Wilson.The Fortunes of Falstaff[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4.
[6]莎士比亚.亨利四世[M]//新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吴兴华,译;方平,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7]Weinreb,et al.The London Enyclopaedia(third edition)[M]. London:Macmillan,2008:263.
[8]Chambers.The Elizabethan Stage:Vol.2[M].Oxford:Clarendon Press,1923:443-445.
[9]Hemingway,ed.A New Variorum Edition of Henry the Fourth Part I[M].Philadelphia:Lippincott,1936:124-125.
[10]Weimann.ShakespeareandthePopularTraditioninthe Theater:studies i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dramatic form and function[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189-191.
[11]Burke.PopularCultureinEarlyModernEurope[M]. Farnham:Ashgate,2009:261-266.
[12]Melchiori,ed.The Second Part of King Henry IV[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75.
[13]Brewer.TheDictionaryofPhraseandFable[M]. Philadelphia:Henry Altemus,1898.
[14]Brand.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Chiefly Illustrating theOriginofOurVulgarCustoms,Ceremonies,and Superstitions[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877:216.
[15]Bakhtin.Rabelais and His World[M].trans.HelenceIswolsky.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163.
[16]FrancoisLaroque,“Shakespeare’s‘Battle of Carnival and Lent’:The Falstaff Scenes Reconsidered(1&2 Henry IV)”,Shakespeare and Carnival:After Bakhtin[M],ed.Ronald Knowles.Basingstoke:Macmillan,1998.Pp.83-96.
[17]Edward Berry,Shakespeare and the Hunt:A Cultural and Social Stud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p..133-4.
[18]Frances Teague,Shakespeare’s Speaking Properties[M], Lewisbu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33.
[19]Jean E.Howard and Phyllis Rackin,Engendering a Nation:A Feminist Account of Shakespeare’s English Histories[M].London:Routledge,1997.P.166.
[20]Rebecca Ann Bach,“Manliness Before Individualism:Masculinity,Effeminacy,andHomoeroticsin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A]A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s Works,vol.II:The Histories[M].Ed.Richard Dutton and Jean Howard.Oxford:Blackwell,2005.pp.220-243.p.231
[21]Frederic Kiefer,“Rumour in 2Henry IV”[A],Shakespeare’s Visual Theatre:Staging the Personified Character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63-100.
[22]Bruce R.Smith,Shakespeare and Masculinit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0.
[23]Valerie Traub,“Prince Hal’s Falstaff:Position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Body”[J],Shakespeare Quarterly40.4(1989):456-74.P.464,471.
[24]Hugh Grady,“Falstaff:Subjectivity between the Carnival and the Aesthetic”[J],Modern Language Review96.3 (2001):609-23.
[25]Lars Engle,Shakespearian Pragmatism:Market of his Tim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121.
(责任编辑:周立波)
Food,Sex and Carnival:Falstaff’s Eating and Drinking in Henry IV
HU Peng
Falstaff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and popular characters in Shakespeare’s plays.The analysis of Falstaff through material culture such as food,sex and carnival,can help to point out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Falstaff’s eating and drinking inHenry IV.
food;sex;carnival;Henry IV;Falstaff
J803
A
2016-06-15
胡鹏(1983— ),男,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讲师,莎士比亚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莎士比亚、20世纪西方文论、比较文学等方面研究。(重庆40003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莎士比亚戏剧早期现代性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YJC75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