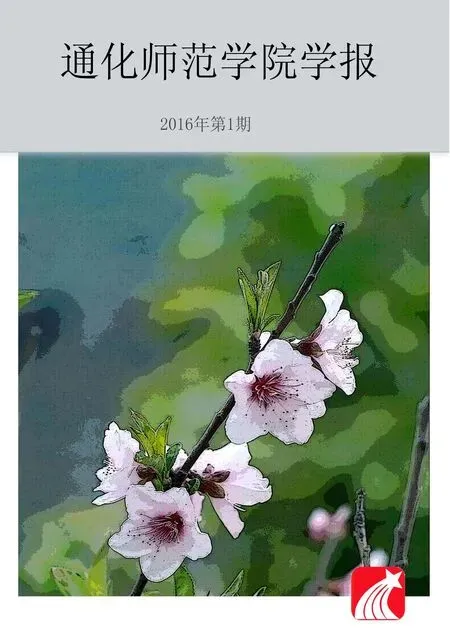逆写“彩虹国度”的宏大叙事
——论库切小说《耻》的历史叙事策略
2016-02-13蔡云,脱颖
蔡 云,脱 颖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逆写“彩虹国度”的宏大叙事
——论库切小说《耻》的历史叙事策略
蔡 云,脱 颖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耻》(Disgrace)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90年代轰动一时的作品。对该作品的研究大都从隐喻、互文性、女性主义视角进行分析。笔者结合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从历史、文本、再现的视角对小说文本进行全新解读,分析作者如何通过书写各色“他者”的“小历史”挑战、甚至颠覆南非官方叙事的“大历史”,呈现小说作者对彩虹国度宏大叙事逆写的脉络,从而展现作家对历史与文本、话语与再现等关系的拷问。
《耻》;历史;文本;宏大叙事
澳裔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写于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成立新共和国后的第五年,小说使作家卫冕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也为世界各地关注新南非的人民提供了一幅复杂、生动的新南非全景图。《耻》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评论界的热切关注。尤其是小说中白人女性露西遭到三个黑人轮奸的描述引发了南非国内许多人士对库切的批评,认为他的小说有损南非民主新政权的形象[1]9。《耻》中的历史元素与南非历史政治现实的关联,库切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再现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新南非的真实状况成为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尽管批评家们大都认为库切在《耻》中一改以往预言式创作的作风而采取现实主义手法对大多数黑人掌权后的新南非共和国进行描绘,但大多数评论家只将《耻》置于南非后种族主义的历史语境中,认为小说展现的是白人殖民者后裔在后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遭到黑人打击报复、生命财产时刻受到威胁的厄运。然而笔者认为,库切所关注的,是超越种族矛盾、全南非各族人民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其采用的历史叙事策略也不同于以南丁·戈迪默为代表的一批南非现实主义作家。在美国拿到文学博士学位、饱受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潮侵染的库切赞同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关于为 “他者”和“属下”代言往往易沦为其压迫者、反而强化压迫体制的看法[2]234,加之自己白人殖民者后裔并用英语创作的作家身份,库切避免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再现南非的历史,而是通过将各种后现代写作技巧和创作思想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来挑战历史、作家乃至语言的权威,通过书写小说中人物的“小历史”来挑战、甚至颠覆官方“大历史”的历史叙事策略来为“他者”和“属下”发声,从而完成作家反抗压迫、关怀边缘人的人道主义使命。正是通过运用这样独特的历史叙事策略,库切使小说《耻》中各个人物的“小历史”得以逆写,有关新南非“各色人种实现民族和解”“土地所有权回归黑人”以及“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宏大叙事。
一、各色人种实现民族和解的现实窘境
在1994年成功举行首次多种族大选、宣布成立新共和国前,南非有着近350年白人统治的历史,种族主义在南非的长期统治造成南非各民族、黑白人种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地位上差距甚大,种族隔离制度导致种族仇视情绪蔓延。消除种族隔离后的新南非,将团结与和解作为国家指南,并希望最终建立一个“彩虹国家”(“彩虹国度”是由南非大主教提出,指各色种族、民族和平生活于其中)。然而,长期的种族矛盾和种族仇恨并不会随着新政府的诞生而自然消亡,因此,如何在避免暴力革命威胁的同时,实现各种族之间,尤其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和解成为新政府的首要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正是背负着这样的期许应运而生,“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作用被用心理——社会的术语描绘成——‘治愈国家’,该委员会担负着,说明真相能得到和解,并最后帮助造就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希望。”[3]413然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真的可以从种族隔离时期犯有罪行的人那里获得真相吗?即使罪犯坦白了自己犯下的罪行,他就能获得受害者的赦免并最终实现和解吗?库切通过小说《耻》中性骚扰有色学生的卢里拒绝接受调查并就此事进行忏悔的小历史对真相委员会的职责和功能进行质疑,从而挑战、甚至颠覆了南非官方关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实现各种族、民族和解的宏大叙事。小说男主人公卢里是一位白人教授,在开普敦技术大学任教。五十多岁并经历两次离异之后,卢里对待性生活十分随意。先是通过招妓和与身边女同事发生关系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后来又诱骗自己《浪漫主义诗人》课上的一位女学生梅拉妮与之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在几次违背梅拉妮的意志而强行与之发生关系并修改其上课出勤记录后,卢里的丑事终于曝光,遭到校方的调查。由于受害人梅拉妮是有色人种,卢里是白人,并且两人是师生关系,存在着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因此校方专门成立了调查听证委员会就卢里性骚扰梅拉妮的事进行调查。尽管校方听证会的主席和成员一开始就对卢里强调,“这是个调查委员会,其功能是听取双方对此事的陈述并提出建议”[4]54。然而,当卢里表示承认梅拉妮对自己的指控时,却被听证会要求就其性骚扰丑闻的真相进行详细交代,进行忏悔,并就此事发表一份发自真心的声明,“然后,我们才能决定是否接受并减缓处分”[4]60。显然,这里的调查听证委员会的职责和功能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惊人地相似:受害人公开讲出他们被害的经历;作恶者就受害人的指控揭开自己的行为,坦白交代,以证明有资格获得特赦。在这里,库切通过卢里面对学校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时闪烁其词,拒绝配合的行为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试图通过“说明真相并进行忏悔”从而实现种族和解的宏大叙事进行了颠覆和挑战。首先,卢里并没有对听证会交代事情的真相,只将自己与梅拉妮之间发生的事情归结为“爱欲”所致。其次,当听证会要求他发表一份发自他内心的声明时,卢里质疑听证会是否有能力从自己发表声明的措辞中判断它是否发自他的真心。最后,当听证会主席马塔贝给卢里最后一次机会让其悔过以保住自己的教职时,卢里予以回绝:“在这民间法庭上我承认有罪,这样的承认应当足够了。说什么也谈不上悔过的事。悔过属于另一个世界……”[4]64由此可见,卢里既没有向听证委员会供述事情的真相,也无法就其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表示真心忏悔,因为到此时为止,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所犯的错误,内心并没有受到触动。与学校听证会无法触动卢里一样,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没有能够触动大多数在种族隔离时期犯下罪行的白人,面对黑人受害者所提出的申述和指控,大部分没有受到触动的南非白人退缩到笨拙的支吾其词、闲散的苦涩和怀旧的老窝里去[3]415,没有对事件做出回应,使得调解无法真正达成,因而种族之间的和解无法实现。在小说的末尾,经历了女儿被三个黑人轮奸、自己被烧伤事件的卢里在回开普敦的路上专门绕道去梅拉妮家拜访她的父亲艾萨克斯,去向他阐明自己对梅拉妮所犯下的过错,向其道歉,“我和她尽管年龄相差很大,但事情本来是有可能有不同结果的,但我没能做出努力……我请求你们原谅”。[4]191然而,艾萨克斯对卢里的道歉并不满意,他最终迫使卢里去给梅拉妮的母亲下跪方才罢休。由此可见,就算犯罪者坦白交代自己犯下的罪行并进行忏悔,也未必能够获得受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给有色人种造成的伤害、黑白人种之间的积怨并非在语言层面就能够达成和解,必须通过施害者采取实际行动、经过长时间的弥补和救赎才有可能最终实现。
二、土地所有权回归黑人的无情嘲讽
南非的白人殖民者自17世纪踏上这片土地,就开始肆意掠夺黑人的土地。出于种族主义目的,南非白人政府一直通过颁布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相关土地法律来强化南非白人对土地的垄断权利,以确保南非的绝大部分土地控制在白人殖民者手里。到1913年《土著土地法》实行之前,仅占人口五分之一的南非白人占有南非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七,剩下不到百分之十五的土地被划为保留地,给占南非人口五分之四的黑人居住和生活。新政府成立之初,一方面允诺要将被白人强行剥夺的黑人土地还给黑人,采取了诸如1994年11月8日颁布 《土地回归权利法》、1996年通过正式宪法规定公民的土地回归权利等举措;另一方面,由于邻国津巴布韦发生黑人老战士驱赶白人农场主的事件,政府为安定南非白人农场主的人心,主张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土地问题,避免暴力流血冲突。政府这一将土地所有权回归黑人,同时黑人与白人农场主在新南非和乐共处的宏大愿景注定无法实现。因为《土地回归权利法》规定黑人能够要求归还的仅限于1913年6月19日以后被强行剥夺的土地,而非自1652年以来被白人殖民者强行剥夺的土地。而1913年《土著土地法》等法律明确了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占有权,加之1993年临时宪法又将财产列为公民的权利,非依法律不得剥夺。其结果是,黑人只能通过法律手段诉诸面积极小的土地,且回归进程缓慢,“在1995年至2000年五年内,仅有10%的土地申诉受到调查和交付’土地回归权利委员会’讨论,而在6.9万起土地申诉中,获得解决的不过4000起,仅为5.7%”[5]383。新政府并没有改善土地占有的极端不合理状况,十多年土地改革的不顺使得无地或缺地的农民对政府的“画饼”行为颇为失望,加剧了黑人与白人农场主之间的矛盾。库切正是通过小说《耻》中黑人农民佩特鲁斯的土地扩张和露西为保住农场遭受厄运的小历史颠覆了新南非关于“土地回归黑人”的这一宏大叙事。小说中的佩特鲁斯一开始是露西雇到农场帮工的助手,平时帮种菜、种花、看狗、打理农场,周末协助露西到市场上去卖农副产品。佩特鲁斯勤劳、努力、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比爱丁杰等老派农场主更愿意学习和掌握新技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手段进行领土扩张。经过长时间的申诉,佩特鲁斯先是从土地事务处那里申请到一笔够买一公顷土地的资助,又购买了露西农场的半公顷土地,使自己脱离农场帮工的身份,成为拥有土地的农场合伙人。但是,佩特鲁斯并没有打算就此打住,他有一个妻子、几个孩子和一个即将生产的女朋友,不会也不能满足于永远耕种那一公顷半的土地,“佩特鲁斯是想把露西的土地都接过去,然后,再把爱丁杰的那一片也接过去,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要大到足以在上面放养一整群牲畜。”[4]132佩特鲁斯一直给露西暗示,提醒她一个白人女性自己独自在农场生活不安全,提出让露西成为自己家庭的一部分以获得保护。后来,当露西因被三个黑人轮奸(其中一个是佩特鲁斯的亲戚)而致怀孕时,佩特鲁斯提出由他来娶露西,来给露西提供庇护,“他(佩特鲁斯)是在提议组成联盟,是一个协议。我提供土地,就此得以享受在他的翅膀的庇护。他要提醒我的就是,不这样做,我就无人保护,成了可供猎杀的猎物”[4]22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向“土地回归权利委员会”申诉土地的过程漫长,手续繁杂,土地重新分配不是通过强力而是需要通过市场购买土地,且需国家对购买费用以及其后试用土地的费用给予财政支援,加之白人农场主往往不愿意抛售土地,所以,像佩特鲁斯这样无地或是缺地的农民就会通过非法的手段设法从像爱丁杰和露西这样的白人农场主手里抢夺土地。至此,库切通过书写佩特鲁斯非法扩张领土的小历史颠覆了官方关于将黑人遭到剥削的土地回归黑人的宏大叙事。而小说中的露西代表的则是南非土地改革运动中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自己土地的阿非利卡白人农场主。“阿非利卡”南非白人指的是祖先为荷兰裔的南非白人,他们在南非白人中占多数,是最早到非洲殖民的移民群族。他们与其母国荷兰关系疏离,三百多年在非洲的生活使他们早已落地生根,方方面面都已经本土化,“在整个非洲大陆的白人中,他们是唯一不自认是欧洲人而自认是非洲人,不自认为是移民而自认为是土著的族群”[6]388。尽管在黑人眼中,他们是白人殖民者或殖民者的后裔,但他们认为自己是讲“阿非利卡语”(即南非荷兰语,南非共和国的十一种官方语言之一)的“阿非利卡人”,是地地道道的南非人。由于阿非利卡白人将南非视为自己的国家,没有其他退路,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方面显得特别顽固。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和掠夺,使得南非土地的近百分之九十都掌握在白人农场主手里,因此,在新南非土地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阿非利卡白人农场主作为南非社会最保守的势力,因其占有过多的土地,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强烈抵制土地改革。由于新南非的国有土地大部分已被部落村社所使用,供政府可资分配的土地太少,因而政府提出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让白人农场主交出土地,以便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或缺地的黑人,可阿非利卡农场主们就是不愿意出卖和放弃土地。在小说《耻》中,库切通过露西遭到强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也不愿意离开南非,不得不通过将土地拱手让给佩特鲁斯来换取自己留在土地上生活的小历史来挑战官方关于“和平解决土地问题”,黑人与白人农场主和平共处的宏大叙事。露西是荷兰裔南非白人的后代,土生土长的阿非利卡南非白人,六年前以公社成员的身份来到萨莱姆镇,在父亲卢里的帮助下买下了这个位于东开普敦的小农场,在这里生活了整整六年。露西告诉父亲自己热爱这个地方,想要在此好好耕种,做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她雇了个农场帮工佩特鲁斯一起开垦农场,养狗,种植菜园、花房,周末到集市上去卖花和农产品,过着典型的小农场主的生活。然而,作为独自一人生活的白人女农场主,露西这看似平静的日子下潜藏着危机。卢里对女儿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的不安感很快得到了应验。一天,毫无征兆的,三个黑人闯进农场,轮奸了露西,抢走了卢里的汽车,将房子洗劫一空,并杀死了所有的狗。露西对待和处理暴行的方法让卢里深感不解。首先,当警察上门来调查取证时,露西只是提及了父亲遭受殴打和屋子受到洗劫,对自己被三个黑人轮奸的事情只字不提。其次,面对卢里让她卖掉农场到别处安全过活的提议,露西断然决绝。在遭受轮奸的第二天,露西就打算回农场收拾东西,然后像以前那样生活。在女儿遭到强奸后,卢里认为露西再不离开,会有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降临在她身上。然而,几次与露西交谈之后,卢里意识露西“她肯定不会离开,她太固执,在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中陷得太深”[4]151。之后,当露西终于将自己如何遭受三个黑人轮奸的细节告诉卢里时,深感绝望和痛苦的卢里提议要么由自己出钱送露西去荷兰,要么露西将农场卖给佩特鲁斯离开萨莱姆镇到别的地方生活,然而,冥顽不化的露西仍然坚持留在农场上生活,“要是就这是为了在这里呆下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呢?……如果我现在就离开农场,我就是吃了败仗,就会一辈子品尝这失败的滋味。”[4]180。无论前路多么凶险,露西执意不肯放弃自己的农场,不愿意放弃自己选择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露西遭受暴力的事件并不是单一孤立的事件,“在土改一再拖延的过程中,无地黑人‘擅自占地’,白人农场主驱逐黑人佃户和工人,农场主遭到袭击的事件频有发生”[5]384。对于强暴自己的三个黑人,露西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个人恩怨,“那完全是在泄私愤,那时候带着那么多私愤。可他们为什么那么恨我?”[4]174面对露西的疑问,卢里认为那三个黑人是出于历史的原因 (即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引起黑人的仇恨和愤懑)对露西施以暴行。然而,除了种族主义仇恨,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土地改革进程中白人农场主的不配合或者抗拒行为,也许才是像露西这样的白人农场主遭受强暴和抢劫这类暴力事件的导火索。虽然库切的小说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正如卢里所说,佩特鲁斯与露西遭受暴力的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卢里刚到萨莱姆镇投奔露西时,佩特鲁斯就提醒卢里露西独自在农场生活“有点儿危险”,而在露西遭到轮奸和抢劫的当天,天天都在露西身边的佩特鲁斯却不见踪影。之后在佩特鲁斯庆祝自己获得土地转让权的晚宴上,露西认出的那个参与强暴她的黑人男孩证实是佩特鲁斯的亲戚。后来,当佩特鲁斯得知露西怀孕后,他多次向露西提出与之结婚来保障她的安全,其目的却是获得露西的土地。至此,库切通过书写露西遭受暴力,最终忍辱让出土地的小历史展示了土地改革过程中无地或缺地黑人与白人农场主之间的矛盾,颠覆了新政府关于和平解决土地问题,黑人与白人农场主和平共处的宏大叙事。
三、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困境言说
新南非成立之初,非国大领导人由于对南非当时和未来的形式估计得过于简单,曾对人民做出许多许多承诺,使南非人民对新政府和未来生活产生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在结束了三百多年的种族主义统治、实现政治协商之后,曼德拉曾兴奋地宣告:“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着手让我们的孩子们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并开始清除无家可归、饥饿实业等状态。”[5]373南非人民也以为自己将迎来人人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与新政府领导人和人民的希望相去甚远。尽管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黑人的生存状态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种族隔离的余孽未消,黑人与白人之间积怨仍深。同时,长期的种族主义统治使得白人掌握了整个南非的经济命脉,企业、工厂、商店和各团体的重要职位仍然把持在白人手里,造成黑人与白人之间贫富差距仍然巨大,黑白人种之间矛盾突出,由此导致的恶果是犯罪与暴力事件频发,人们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在小说《耻》中,库切通过书写卢里、露西、爱丁杰以及佩特鲁斯等白人及黑人不幸生活的小历史,从而挑战官方关于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宏大叙事。首先让我们看看以卢里、露西和爱丁杰为代表的白人在新南非过着怎样的生活。因为被学生梅拉妮控告性骚扰,并且拒绝配合学校发表一份悔过声明,卢里遭到学校除名,丢掉了大学教授的工作并被取消一切津贴。他怀着振作自己、重聚生活力量的心情到东开普敦赛莱姆镇女儿的农场上,满以为能过上平静、安乐的生活。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连串打击。首先,卢里手头拮据,生活陷入窘境。由于性骚扰丑闻被学校除名并被剥夺一切津贴,卢里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当他想找活儿干时,露西建议他去替自己农场曾经的雇工佩特鲁斯干活,从佩特鲁斯那里获得工资。昔日的大学教授不得不向昔日的黑人奴隶出卖体力来换取生活来源。其次,卢里和露西的人身时刻受到威胁。当露西被三个黑人轮奸、卢里被殴打并被烧伤之后,卢里发现自己每天都生活在恐慌之中,生怕暴徒再次归来,厄运再次降临在自己和女儿身上,“一听到门前小路上嘎吱嘎吱地响起踩着碎石的声音就提心吊胆……”[4]158。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没有错。参与强暴露西的三个黑人中的那个小男孩回到了农场,住在佩特鲁斯家,并被证实是佩特鲁斯的亲戚。小男孩回到农场后三番两次偷看露西洗澡,被卢里逮住并施以教训,可卢里和露西却无权将他撵走。最后,卢里无家可归,居无定所。由于卢里坚持让露西要么将遭到轮奸的事情报告警察,要么离开农场换个地方重新生活,导致二人关系紧张,卢里离开农场返回了开普敦位于大学附近的住处。然而,回到家的他非但没有感到一点儿回家的味道,迎接他的是被洗劫一空的家:衣服、音响、音乐磁带、唱片、电脑、刀叉盘碟、家用电器以及所有的酒和食品都被搬走了。“决不是一般的入室行窃,进来的是一支扫荡队,把现场搬得一干二净…是贫富再分配运动的有一场战役。”[4]195而当他得知露西怀孕而赶回农场时,又因教训偷看露西洗澡的黑人男孩而与露西产生分歧,便被露西请出了农场。当得知露西决心生下孩子时,卢里决心留在露西身边保护、照顾露西直到她生下孩子。因此,无家可归的卢里只得在离农场最近的格雷汉姆镇租下了一间屋子,并且在他帮贝芙·肖做义工的诊所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窝,在那里用买来的煤气炉给自己做饭,每天两次给狗喂食,打扫狗圈,下午时分将狗的尸体运到医院的焚化炉亲自焚烧,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护狗员,诚如梅拉妮的父亲艾萨克斯所说,“强者坠落到如此境地”[4]186。而露西呢,尽管她热爱这片土地,用心经营农场,可作为独自生活的白人女农场主,她的农场受人窥视,人身安全时刻受到威胁。一方面,她得应付以佩特鲁斯为代表的正在进行扩张土地、想要得到农场的无地或缺地黑人。在她惨遭强暴之前,“佩特鲁斯就巴不得露西退出农场”[4]157;而当她因被轮奸而怀孕后,佩特鲁斯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让露西嫁给她,做她的第三个妻子以换取自己的保护。佩特鲁斯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得到露西的农场。另一方面,露西认为自己被三个黑人轮奸并非偶然事件,自己随时可能要再次遭到被强奸和抢劫的厄运。在遭受轮奸的过程中,露西感到那三个男人存心使她害怕,他们好像是在泄愤,用尽手段来伤害她,威胁她,更让她觉得恐惧的是,“我觉得自己身处他们的领地,他们已经瞟上了我,还会回来找我”[4]176。不管轮奸露西的那三个黑人是出于种族仇恨,还是出于想要将露西驱赶出农场以获得土地,露西在这片土地上的平静生活宣告终结。尽管露西对农场感情很深,尽管她不想放弃自己的土地、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过生活,然而正如佩特鲁斯在向卢里提出娶露西时所指出的,“可在这里,那很危险,太危险了,女人必须结婚”[4]225。最终,怀有身孕并想要继续留在农场上生活的露西只得向佩特鲁斯屈服,同意放弃土地、成为佩特鲁斯的第三个妻子,将土地转让给佩特鲁斯以换取他的庇护,而自己则过上一无所有的生活,“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狗一样”[4]228。至于独自留守南非的白人农场主爱丁杰,等待他的是没有希望、危机重重的未来。爱丁杰是德国后裔,妻子过世后子女返回德国,只剩不愿意离开南非的他留下苦苦坚守农场。爱丁杰在自己家中安装了安全门,农场周围竖了一圈围栏,栽了铁丝网,装了报警器,按照要塞的样子建农舍,并且随身佩戴一把贝雷塔手枪,因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救自己,警察救不了你,根本救不了,这你得清楚”[4]112。然而,正如卢里和露西所指出的,就算这样全副武装,爱丁杰能留在农场上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他的土地迟早要被佩特鲁斯这样的土地扩张主义者接管,他后脑勺迟早得挨枪子,因为发生在卢里、露西身上“这样的事情每天、每时,每分钟,在全国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生”[4]110。在这里,库切通过卢里、露西和爱丁杰等人的遭遇,颠覆了南非新政府关于人民安居乐业的宏大叙事,小说中人物所遭遇的事件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反映了南非当时的社会现状,根据新政府成立五年之后的官方数据,到了1999年,南非的失业人口为467万,失业率仍然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而社会治安的糟糕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偷盗抢劫各种犯罪作案频繁而破案率极低。根据警方资料,“南非每天有52人遭谋杀,每30分钟发生一起强奸案,每9分钟有一辆车被盗,每11分钟发生一起武装抢劫案”[5]375。白人农场主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而以佩特鲁斯为代表的黑人也并没有过上他们所期望的幸福生活。如前所述,作为露西农场上的帮工,佩特鲁斯拼命干活,帮露西保住了向集市供货的菜园;他挖地、清理灌溉系统,帮露西经营着农场。然而,在通过申述从土地事务处得到一笔可以买一公顷地的资助之前,辛劳半生、儿子已成年的佩特鲁斯没有能力盖一间自己的房子,而是带着妻子一直住在露西为他们安了电灯的旧马棚里,那里没有天花板,也没有能被称为地板的地面,生存条件简陋不堪。《耻》中佩特鲁斯的境况代表着新南非广大黑人的生存境遇,他们虽然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仍掌握在白人手里,黑人仍然是贫穷、失业和犯罪的代名词。除了具体人物的刻画,小说《耻》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流民、游民全景图。在卢里焚烧狗尸的医院,以焚化炉为中枢形成了一个小社会,每天都有一群妇女和儿童在那里等待送到这里的第一批医疗废弃物袋,从里面找出可以卖的注射器、小别针、绷带和药片等。而一些无家可归的游民白天在焚化场四处转悠,晚上就背靠焚化炉睡觉来取暖。由此,库切通过书写卢里、露西、爱丁杰、佩特鲁斯、无名流民和游民的小历史挑战,甚至颠覆了官方关于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宏大叙事,展示了新政府成立后南非社会动荡不安的严酷现实和各色人种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
四、结语
由于其南非白人的身份和南非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作家的小说创作“对南非历史政治现实介入与否以及如何介入”[7]12,即库切小说的“历史叙事”策略成为库切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与以南丁·戈迪默为代表的一批南非现实主义作家用自己的小说创作深度介入南非历史、反映南非现实,揭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残害人民的创作手法不同,库切质疑历史书写的客观真实、警惕为受压迫的各色“他者”代言的各种尝试、挑战作家乃至语言的罗格斯中心地位。小说《耻》正是通过书写卢里即使丢掉职位也绝不肯向学校听证会坦白和忏悔、露西即使被轮奸也不愿放弃土地、佩特鲁斯不择手段进行土地扩张的历史挑战、颠覆乃至逆写了“彩虹国度”关于新南非各色人种实现种族和解、土地所有权回归黑人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宏大叙事,小说在质疑历史真实性、语言与再现客观性的同时体现了作家将反权威、反压迫的解构精神诉诸于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情怀。
[1]大卫·阿特韦尔.库切、争议与耻辱[J].外国文学研究,2011(5).
[2]Ania Loumba,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M].New York:Routedge,1998.
[3]海因·马雷(南非).南非:变革的局限性 [M].葛佶,屠尔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J.M.库切.耻[M].张冲,郭整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郑家馨.南非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秦晖.南非的启示: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19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7]Susan Van Zanten,Gallagher,A Story of South Africa:J.M. Coetzee’s Fiction in Context[M].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责任编辑:章永林)
I106
A
1008—7974(2016)01—0096—06
10.13877/j.cnki.cn22-1284.2016.01.018
2015-08-17
2015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帝国时代库切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15WW002);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青年专项项目 “历史叙事的颠覆与重构——基于新历史主义的库切小说研究”系列成果之一(QNYB13020);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四批“教师成长基金”项目“后帝国时代库切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系列成果之一(EDF2015014)
蔡云,博士研究生,副教授;脱颖,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