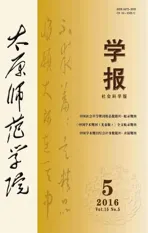“鬼”字释读的效力与魅力
2016-02-13袁劲
袁 劲
【语言学】
“鬼”字释读的效力与魅力
袁劲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沈兼士因袭中国传统而又融入时代新变的“鬼”字解读兼具阐释的效力与魅力。《“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厘定“鬼”字本指“类人异兽”,经受住了时间检验;考虑到时代语境,此解读还蕴含着“打鬼”的微言大义与言说智慧。追寻“鬼”字释读的脉络,兼及其未曾全面施行的新训诂学构想,可知沈兼士对传统训诂的改造已融入时空结合、古今对接与跨学科论证等新观念。这种根植于本土“解字”传统又兼取西学而有所损益的理念与实践,如同一座待采的富矿,对于今日方兴未艾的文化关键词研究不无借鉴意义。
鬼;新训诂学;关键词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鬼”字早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便已出现。轴心期以降,“鬼”义便已多层绽放,《易·既济》爻辞载有“高宗伐鬼方”之事,《墨子》创立“明鬼”之说,而《楚辞》多摹“山鬼”之象。时至中古,本土民间信仰又与外来释教义理相融合,遂形成根植于原始文化而施及当下的庞大“鬼”字释义体系。在今日主流与官方话语中,与迷信相关的鬼神义项已多被科学思想所涤除,但“小鬼头”、“讨厌鬼”、“鬼点子”等民间话语却依旧鲜活。如果借用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标准衡量,“鬼”字无疑是中国文化情境及诠释里“重要且相关的词”,并在特定的思想领域内“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1]7“鬼”字实为关键,却不易索解。俗语有“罔两易图,狗马难效”之谓,强调言人人殊的不确定性。可以想见的是,穿透纷繁复杂的释义而探源“鬼”字的来龙去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所谓“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文心雕龙·神思》),“鬼”字的被污名与边缘化遭遇,使得原本立体化的释义体系被熨平,同时也丧失了释义背后的多重语境。当然,所谓“发其关键,直睹堂奥”(《二程遗书附录》引范祖禹评程颢语),一旦破解时过境迁积淀而成的“门户之见”,便可收获文字演变背后更为丰富的文化叙事密码。对于今日学者而言,拿起“鬼”这一枚key word,叩门启钥,进而探得传统文化之“神”,实有中西两条学术取径:既可沿着文化关键词研究的西学路径跟进,亦可遵循清儒戴震所谓“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与是仲明论学书》)的传统训诂展开。前者可视作他山利器,在引进吸收后为我所用;后者本就是看家本领,当下亟需拂去蒙尘砥砺其术。相较于“词语的政治学”(陆建德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传统经典训诂基础上的“解字”亦不曾丧失阐释的效力与魅力——沈兼士在1936年的释“鬼”可为证。
一、旧事重提:陈寅恪经典之论与所论之经典
陈寅恪先生曾言:“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2]202这句精当的概括业已成为种种国内关键词与文化史著作的“高引文献”。对于此项“标准”,多数学者日用而不察焉,仅仅止步于“引用”却未能按图索骥。于是,陈寅恪立论所据的“原始文献”也就无人问津者久矣。其实,陈氏之论原本出自写给沈兼士先生的一封信——在引用者笔下,这一背景信息往往只会以注脚或参考文献的形式顺带一提。在信中,陈寅恪高度评价了沈兼士所作《“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不惟直言“欢喜敬佩之至”,更以“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标准称赞其开创价值:
大著读讫,欢喜敬佩之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2]202
于继续“解字”而“作文化史”的后学而言,陈寅恪先生的经典评论无疑具有导航性,可仅仅铭记“定义”而不参照“足以当之无愧”的原著,便难免留下浅尝辄止乃至买椟还珠的遗憾。在关键词研究已然形成庞大“学术场”的今天,这一桩因陈寅恪经典之论而掩盖所论之经典的旧事,仍有重提的必要。或者说,早在1936年,作为关键词研究先行者的“鬼”字探源便具备了阐释的效力与魅力。它对于今人的启示,也不应只是一条高度凝炼的理想标准,因为“定义”背后还包含着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具体的方法论价值。
以今日“关键词”、“观念史”乃至“语义学”等种种成熟的研究方法观之,沈兼士先生的这篇文章亦堪称解读“鬼”字的精彩个案。遵循“从语言文字学着眼研究鬼字之语根”[3]188的总体思路,该文先由“鬼”、“畏”、“禺”的音义“连锁性”判定三字原指一物(即类似人形的异兽),进而勾连从“鬼”之字形、声音诸字与“鬼”之引申义及其转语,再佐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殷墟卜辞相印证,最终勾勒出“鬼”之字形演变、字义引申和语辞分化的历史脉络。经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论证,在这篇“鬼”字的“文化史”终篇,作者得出四点结论:
(1)鬼与禺同为类人异兽之称。
(2)由类人之兽引申为异族人种之名。
(3)由具体的鬼,引申为抽象的畏,及其他奇伟谲怪诸形容词。
(4)由实物之名借以形容人死后所想象之灵魂。[3]199
“原始人舍具象的组织之外不能作抽象之悬想。”[4]202如郭沫若所言,“鬼”字所指由现实中的异兽、异族转变为想象中的死人灵魂,这是一个逐步抽象的过程,其内在的线索正是由异常之形而衍生出畏惧之情。结论(4)是今日常用义,在不自觉之中也多被视作“鬼”字的原始义。平面化的理解遮蔽了“鬼”字原本丰富的衍变脉络,也使得早期义项日益边缘化乃至长久埋没。溯洄观之,这篇经抽象而回归具体的探寻文章,其实内含了“鬼”、“畏”、“禺”三字的“连锁”与相关“字族”的印证两大步骤。探得“鬼”字原始意义的(1)可谓结论之结论,就论证过程而言,固然有古人王充《论衡·订鬼》与近人章炳麟《小学答问》“夔神魖也”条相关论说的启示,但最重要的依据还是“鬼”、“畏”、“禺”音义之间的“连锁性”。拨开字形衍变与说解歧叉的干扰,“连锁性”落实为“甶”这一共有的构字符号,这也正是推断出三字原指一物的关键证据。至于结论(2)和(3)中引申逻辑的明晰,则要得益于“从与鬼字有关之诸形声字观察其主要之意义”[3]192的研究取径。在此步骤中,所印证的范围包括从“鬼”形之字、从“鬼”声之字、鬼之引申义及其转语,由此推导出的公式便是从异兽到异族、由丑恶而生畏的字义流变,亦即“鬼为禺属之兽,其状丑恶,故丑从鬼”[3]193,“人以怪兽之状奇诡,望之生畏,而愧之与畏,对待成词,凡对外畏惧者,内省必惭愧,犹威之与畏,亦相互为用”[3]195者云云。
倘若将解字者曾提出的“文字学之革新研究”与“纵横两方面的训诂研究法”等设想联系起来,还能发现“鬼”字探源所暗含的方法自觉。早在1919年,沈兼士便认为,“凡文字,皆系应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法,以·,─,│,凵,□,×,┼,……诸简单符号组合而成。前者谓之造字之元则;后者谓之字体之最小分子”[5]1;明乎此,便可“综合各最小分子,以观各元则之应用”[5]1。据“造字之元则”与“字体之最小分子”所言,“鬼”、“畏”、“禺”三者皆遵循会意元则,而基于象形元则的“甶”(兽头之描摹)即便称不上是“最小分子”,也至少发挥了“共同分子”的音义勾连作用。沈兼士厘定“鬼”字本指“类人异兽”可谓自成一说,这种受到许慎“一线光明”启发却又不局限于《说文解字》“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汉字构形分析,直到今天还依旧经得起检验。如《汉字源流字典》便采用此说,认为“鬼”字“本义当指类人、丑陋、诡谲而出没于山林的大猩猩等猿类动物”[6]887。沈兼士解读“鬼”字之效力可见一斑。
二、字里乾坤:“鬼”、“鬼子”与“打鬼节”
为何“解字”具有“文化史”的价值?陈寅恪先生没有明说。如果是单纯地借助形、音梳理字义,似乎还配不上“文化史”的美誉。那么,“文化史”因何得名?在解读“鬼”字过程中,沈兼士所运用的语料与论证多次涉及鬼禺之属“形态丑恶,人皆畏恶之”[3]190的先民生存体验,以及“鬼为似人之异兽,傀儡为象人之木偶,鬼之引申为傀儡,亦犹禺之引申为偶”[3]191式的原始祭祀遗存。其实,除了原始生存图景的勾勒,文中涉及现实的几处细节也值得拈出来琢磨一番。沈先生交待立论缘由时曾言,探源“鬼”字的近因乃是读到日本学者出石诚彦的《鬼神考》。出石氏的考察涉及宗教史迷信鬼神之由,认为中国“鬼”字之语根源于死者及其灵魂。沈兼士以为其说不确,遂借助文献及文字的重新梳理一探究竟。在今天看来,此举不唯商兑旧说以正视听,似乎还多少带有落款所谓“打鬼”之意味。“打鬼节”本是藏传佛教节日,法会之后通常有祛除恶魔的神舞,也就是老北京人俗称的“打鬼”。以最为著名的雍和宫神舞为例,“打鬼舞”自第五幕起便是佛祖派遣天王、护法、度母擒获鬼魔并终将魔王斩首的集体表演。[7]按照通常理解,解读“鬼”字的文章写成于“打鬼节”,落款提及时间上的凑巧多半是“因文及事”,顺便为学术色彩较浓的“鬼”字探源添上一笔当下的鲜活与民间的趣味。
然而,事实恐怕并没有如此简单。孟子尝言,读书须知其人而论其世。将此篇文章置入时空坐标轴观之,“打鬼节”的言外之意或可见一斑。落款“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时维华北自治的后一年与北平沦陷的前一年。沈兼士身处北平,当切身感受到时局的危急。也正是在这一天,中共发出《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要求大会讨论对日绝交宣战等紧迫问题。沈兼士的落款是否与此相关,目前尚无确切文献可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如此假设:如同读《说文解字》时发现许慎在字形上“指示后来研究者一线光明之途径”[3]190,闻讯后的沈兼士似乎看到了扭转时局的“另一线光明”,欣喜却不便直言的他想到了眼下的“打鬼节”,遂借佛祖派天王、护法、度母合力“打鬼”的典故期许全国抗日功成。也正是基于此,他才不忘在文中两次提及“打鬼”即“打鬼子”的训诂依据:“今人亦常呼异族外国人为鬼子”[3]193,“诸夏之外,异种别族,形色容有异于中国者,遂亦呼之为鬼矣。古代有鬼方鬼国,近人犹谓外国人为鬼子,殆犹是旧习古语也”[3]196。“鬼子”固然是“鬼”字义项的构成部分,但涉及前者得名之由,沈兼士所强调的重点有二:自古异族(古语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与丑恶伤人。故训与现实中的形象及其感情色彩高度吻合,是影射亦是警醒。旨在清除鬼怪亡灵之说,而又语涉当下步步紧逼的“鬼子”,解字者的爱憎褒贬蕴含其中。
落款翌年,北平沦陷,沈兼士对“鬼子”的憎恶与“打鬼”的期望依旧。此点可援引另两篇论文的近似落款为证:《吴著经籍旧音辩证发墨》落款为“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四日写于北平寓庐之抗志斋”;又,《、杀、祭古语同原考》落款为“二十八年除日写于北平寓庐之识小斋”(关于此点,漠涵《关于沈兼士在抗战期间若干问题之考辨》一文亦有提及,并对沈兼士抗战期间的气节与操守有若干举证。见《档案天地》2013年第12期)。考虑到托词寓志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智慧(典型者如清初的“复明”浪潮,以谐音相关;相近者如余嘉锡的“不知魏晋堂”,暗示北平沦陷后的“人心思汉”[8]723),与其说“打鬼”、“除日”与“抗志”是无需节外生枝或“过度阐释”的节日与斋号,倒不如说这前后呼应的三者更像是微言大义式的心志独白。近日,有学者撰文重提“学术抗战”之“守”与“攻”,表彰前者保全文明种子之功与后者重塑文化自信之力。[9]抗战前后的学术研究,如杨树达《春秋大义述》、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周祖谟《胡三省生年行历考》种种,皆以回溯历史来照亮时下所需的“攘夷”气节。沈兼士先生的释“鬼”,于梳理典籍驳斥异说之中,暗寓“打鬼”的言说智慧,亦可谓借关键词研究而行“学术抗战”的绝好范例。
时过境迁,和平时代的“打鬼节”已恢复了本身的宗教气息与民俗色彩,沈兼士的“鬼”字研究亦成旧事。然而,七十多年前对关键词“鬼”的解读却并未丧失阐释的魅力。2013年4月23日,宣讲家网曾刊发题为《亚洲需设“打鬼节”》的时政评论[10]。针对日本左翼政府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该评论号召亚洲二战受害国共设“打鬼节”,以便在日方“拜鬼”周期揭露其侵略暴行。因“拜鬼”而行“打鬼”,评论员自陈这一构想源于民间打鬼习俗的启发——七十七年前,沈兼士探源“鬼”字的那则落款正与此遥相呼应。
三、“操斧伐柯,其则不远”:沈兼士的新训诂学展望及其启示
与沈兼士同时代的胡适,在评论清儒阮元《性命古训》时曾言:“阮元的性论的重要贡献还在他的方法,而不靠他的结论。他用举例的方法,搜罗论性的话,略依时代的先后,排列比较,使我们容易看出字义的变迁沿革。”[11]449沈兼士解读“鬼”字连及背后更为宏大的新训诂学构想,亦可如是观。阮元训“性”而沈兼士释“鬼”,所解之字与结论虽有不同,却同样采用了传统训诂学的方法。胡适受到阮元“剥皮”功夫的启发,在哲学史中注重考察观念的历时演变,较早实现了传统训诂理念及方法的“跨学科”应用。身为语言学家而又身处中西交汇潮流之中的沈兼士选择了改造,引入“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沈兼士认为:“大凡做一种学问,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在科学的研究之基础上,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是缺一不可的。”具有理论总结性质的《文字形义学》便据此设想分为上篇叙史、下篇论理的框架编辑,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4页)疗治传统训诂之弊:
古代所谓训诂,只是随文解义,略无系统,及清代小学家兴,始知分别之,以《说文解字》为本义,以其他训诂书为引申假借之义,于是训诂之学乃粗具体系。輓近学者复知《说文》所说尚不足以代表文字之原始意义,且每字之原始意义亦不尽具于一般训诂书中。盖语言之历史较文字之历史为悠久,载籍所用之文字,仅有已经多次变化之语义故也。文字意义之溯源,恰如考古学家之探检遗迹遗物然,重要之目的,往往深藏于地层之下,非实行科学的发掘,不易觅得。故探检字义之原,亦须于古文献及古文字中披沙拣金,细心搜讨。文献方面应直接观察其历史情形,玩味其文句解释,文字方面应从形音义三面贯串证发其当然之义项。苟意图省事,蔽于后世训诂家之所说,将不易达到比较圆满之结果。[3]186
以上关于改造传统训诂而行新训诂学研究的初步设想,出现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开篇。沈兼士对“鬼”字的解读兼具效力与魅力,其中奥妙正在于斯。站在今天回望,此论对传统训诂弊端的透视与施行文字考古的展望,虽成学界共识却也不失借鉴价值。传统训诂与文字、音韵之学并称“小学”,其早期功用在于辅翼经学,故训诂专书《尔雅》有“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的价值美誉。与此功能相应,“旧训诂学偏重于逐词、逐字推求它的本义,很少顾及词义系统和语义发展规律”[12]7,亦即前引沈兼士所批评的“随文解义,略无系统”。当然,传统训诂学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也曾提出一些方法,如《说文解字》的“三训”(形训、音训、义训)与《助字辨略》的“六训”(正训、反训、通训、借训、互训、转训)。但正如引文所论,语言先于文字,倘若局限于传统解释而不能借文献“直接观察其历史情形”、就文字“形音义三面贯串证发其当然之义项”,纵有所得也难称圆满。
所谓有破有立,沈兼士指出传统训诂之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自然涉及“圆满”的标准是什么,又该如何实现。且看作者自己的解释:“大凡整理一种学问,欲得真实圆满之效果,首在以精密之方法,搜集可供研究之确实材料。”[13]11所谓“精密之方法”落实到训诂学而言,应是涵盖“训诂学概论”、“代语沿革考”和“现在方言学”在内的“纵横两方面的训诂研究法”[14]8,而其中每一部分(例如方言)也应“纵横两方面综合起来”[15]46,并“利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之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15]49。沈兼士的新训诂学构想连同《文字形义学》的撰写均未能完全实现,却并不影响时空结合、古今对接与跨学科论证等新观念的可行性。尤其是“现在时”维度的引入,一变“考证死文字”而为“整理活语言”[15]45,遂使训诂学由经学附庸而蔚为大国。
与训诂学科独立相配套的是研究者的自主,此亦胡适所谓不迷信旧说而唯以材料说话是也。材料有正副内外之分,除了《说文解字》、《尔雅》等传世文献作为“正材料”,“可供研究之确实材料”还涉及钟鼎、甲骨刻辞等“副材料”[16]382,以及“古代社会之状况及原人之思想”[16]383。执“精密方法”而研“确实材料”,沈兼士强调《说文解字》“未必尽合于古人造字之旨”[17]24,故只宜“看作考释古文之起点”[16]383——释“鬼”而能探其源,突破《说文解字》等传统释义的阻隔实为最关键的一步。由此,回到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今日训诂学之标准”,沈兼士的如下判断可为解答抑或印证:“应用‘象形’‘会意’两原则的文字,大都直接的或间接的传示古代道德风俗服饰器物等的印象,到现在人的心目中。”[14]6-7“鬼”字如此,他字亦然。如果说,陈寅恪为新训诂学设定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行业标准,那么,沈兼士便是通过“纵横两方面的训诂研究法”为如何“解字”与“作文化史”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指南。
《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学术砥砺切磋的愿景固然美好,但“可以”还暗示着未必如愿的另一向度。随着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关键词研究”在我国繁荣,作为本土之玉的“解字”传统却逐渐式微,这无疑是重“引援”而轻“挖潜”的一大遗憾。其实,今日常言的“关键词研究”实有中西两条学术路径。即便将西学引发的国内“关键词研究热”追溯至1995年初的《读书》译介,其传统还是无法与根植于轴心期的“老子关键词研究”(《韩非子》之“解老”“喻老”)和“先秦儒家关键词研究”(《墨子》之“非乐”“非命”)同日而语。“关键词研究”的本土路径肇始先秦而绵延历代,时至中西新旧思潮激荡的近现代,依旧有沈兼士的“鬼”字解读彰显着中国经典阐释传统的效力与魅力。那么,于当下学林而言,饱览西学武库洋洋大观后亦不妨回眸身后“材木不可胜用”的幽谷。其实,传统文化如同埋藏玉璞,亦似丛生树木,“攻玉”也好,“伐材”也罢,纵使配有“切玉名刀万里来”(陆游《忆山南》),亦不妨再赋上一曲“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诗·豳风·伐柯》)。
陈寅恪曾言:“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8]512中西对流,传统学术之弊恰可借外来之学弥补,所谓“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亦即改造而非弃置,沈兼士解读“鬼”字的成功正在于此。本文于雷蒙·威廉斯文化关键词研究潮流之外,提请关注文化关键词研究的中国路径,并非简单肤浅的比附,其中用意或可借唐人南巨川《美玉》诗句作结:“抱玉将何适,良工正在斯。有瑕宁自掩,匪石幸君知。”
[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来函[C]//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C]//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郭沫若.郭沫若先生来函[C]//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沈兼士.文字学之革新研究(字形部)[C]//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6]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8.
[7]阿巴德夫.打鬼节[J].人民中国,2000(8).
[8]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G]//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2007.
[9]王子墨.“学术抗战”的守与攻[N].光明日报,2015-08-12.
[10]胡思远.亚洲需设“打鬼节”[EB/OL].http://www.71.cn/2013/0423/710663.shtml.
[11]胡适.胡适全集(第六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2]周大璞.训诂学初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13]沈兼士.广韵声系叙及凡例[C]//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沈兼士.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C]//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C]//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沈兼士.文字形义学[C]//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C]//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C]//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张琴】
YUAN Ji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The Effect and Attractivenes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ho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Ghost” by Shen Jianshi is the unity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history and reality, effective and attractive. In Shen’s opinio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ghost is the human-like creature, which is proved in the proceeding research. In context of times, abundant connotation and wit of discourse can be found in Shen’s interpretation. In fact, the new exegetics that introduced by Shen Jianshi include spatial-temporal f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demonstration. This aesthetic ideology has a very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oday.
ghost; new exegetics; the study of key words
2016-05-03
袁劲(1989-),男,山东枣庄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元典关键词研究的学术路径与方法论探索》(2015111010201)
1672-2035(2016)05-0092-05
H1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