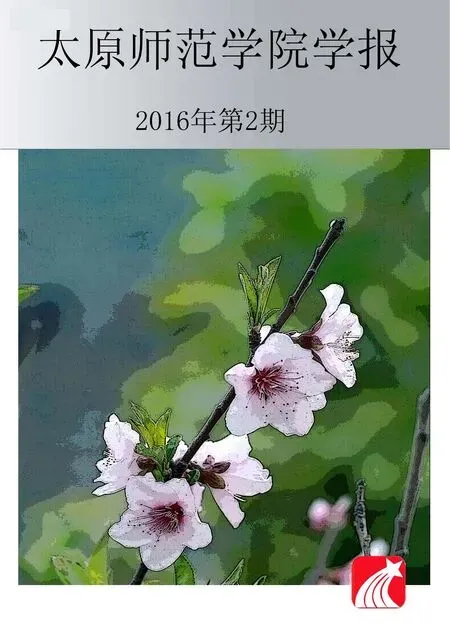人类的纯洁状态与灾难的替补
2016-02-13曲立伟
曲立伟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
【哲学】
人类的纯洁状态与灾难的替补
曲立伟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
[摘要]中西思想史上有两位非常特别的思想家:庄子和卢梭,他们都对人类的文明状态怀有一种天然的戒心,卢梭相信在文明开化之际(野蛮与成熟的文明时期之间的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曾经有一个最纯洁的时期,而庄子描述了一种至德之世。而按照德里达的“替补逻辑”,纯洁之境不可能是一种过去存在过的状态,而是指向未来的可能性。庄子的描述引导我们去思考:面对德里达所指出的灾难的替补,在何种预备中,至德之境才能在未来的某种状态中出现:一是自因而限;二是无为而化。
[关键词]德里达;卢梭;庄子;至德;纯洁状态;灾难;替补
无论是儒家学派还是道家学派都非常注重心性修养,其追求的境界乃是庄子所说的“至德之世”下的圣人境界,这一境界中的人处于一种“纯洁状态”。和庄子类似,卢梭相信在文明开化之际(野蛮与成熟的文明时期之间的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曾经有一个最纯洁的时期。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关注了卢梭所描述的这一“纯洁时期”。但是,德里达出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对卢梭思想进行了批判,解构主义的原则使得任何所谓某个时期出现的“纯洁状态”都成为了乌托邦的虚构。如此一来,我们亟待追问的是:“人类的纯洁状态如何得以可能?”它是一种过去存在过的状态还是未来的可能性?
探寻一种人的至德之世是《庄子》的重要目标。这一至德之世或许并不是一个具体历史年代的记载,而是一种境界的描述。这种境界可以存在于社会状态之前、之中、之后。
如何理解这一至德之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纯洁状态”的追求是否可能,我们试图直面德里达的解构原则以及他以之为论据对于卢梭“纯洁状态”的质疑,从义理和心性修养的可能性上分析庄子至德之境的重要构成因素,进而探寻一条通向人类纯洁状态的道路。
一、卢梭对于人类纯洁时期的描述以及德里达的解读
卢梭在对人类语言和社会的起源的追问过程中,处处显示着一种对于某个时期人类纯洁状态的相信。但是德里达却用“灾难的替补”这一后现代主义的原则使得那种“人类纯洁状态”变成了乌托邦式的幻想,那么卢梭眼中的“纯洁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通过灾难的发生转变成一种文明开化状态的呢?
(一)作为自然状态的圣歌
卢梭所理解的“人类纯洁状态”产生于欧洲特有的基督教传统,因此它总是关涉“上帝”。他将这一由上帝所导向的“人类纯洁状态”描述为“圣歌”的阶段。所谓的圣歌,本是教会音乐术语。在这里,卢梭用这个术语表示一种学会说话之前的说话,这种状态人既不能很沉默又不能说话,这是一种没有音节的声音,与其说是一种语言不如说是一种音乐,它就是圣歌。音乐出现以前根本不存在语言。
“奥古斯丁指出,言语不能取悦上帝,人们只能以欢快而模糊的音乐向上帝说话:‘如果我们不采用没有音节的声音,就不能保持静默,也不能在狂喜状态中表达这种狂喜,那么,我们不向一位不能直呼其名的存在进行这种无言的欢呼,还能向谁欢呼呢’”[1]362。
为什么圣歌阶段会被称为一种“纯洁状态”?因为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拥有一种自足的“快乐”。
“在这种状态中,人享受什么样的快乐呢?人所享受的丝毫不是外在于他自身的东西,而仅仅是他自身的存在;只要这种状态存在,他就像上帝一样自足。”[1]363这种状态是一种起源发生时所产生的“界限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界限状态是否是一个纯粹在场的状态呢?它是否曾经现成地存在于历史的某个时期呢?
(二)与社会起源相关的人类三种状态
按照《语言起源论》,新生的社会服从三种状态的发展规律,前两种状态属于史前状态(包括野蛮状态的猎人和原始状态的牧民)。而在第三种状态中,人才在社会化的进程中接近他自身(从事耕作的文明人)。卢梭非常关注第二种状态到第三种状态的过渡。在这种过渡状态的考察中,卢梭发现了一个人类最纯洁的时期,这一时期,实际已经区别于第一种和第二种状态。但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人类告别了这个“黄金世纪”。德里达《论文字学》中指出:
最早有的居民以及最后才组成民族的地方是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人们要更容易独立行事,因为在那里产生社会的需要并不迫切。
假定地球上四季如春,假定有丰富的水源、牲畜和牧场,假定人们在摆脱自然的控制之后一度散居各地,我们难以想象,他们会放弃原始的自由,会放弃适合其懒惰天性的独往独来的田园生活,而心甘情愿地忍受奴役、劳苦,以及由社会状态必然带来的不幸。[1]372
(三)灾难:文明的起源
如果这种自然状态一直保持,人类终将不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这是一种静止的状态,然而变化和不安不会源自这种静止状态。只有通过外在的偶发事件才能破坏人的状态,破坏这个黄金时期。而偶发事件相对于这种人类的纯洁状态无疑是一场灾难。一场灾难带来了语言和社会的起源,在卢梭看来,他只是上帝“手指的简单动作”:
上帝希望人和睦相处,他以手指触动地轴,并使它对准宇宙的轴心。我发现,这一细微的动作改变了大地的面貌,决定了人类的使命:我远远听到一群疯子的欢呼;我看到人们在建筑宫殿和城市;我看到艺术、法律和商业的诞生;我看到民族的形成、发展和解体,它们就像大海的波涛自涌自息;我看到,人们为了共谋发展而汇聚在住所的一些地方,他们将世界其他地方变成了可怕的荒漠,为社会的联合和艺术的使用竖立了界标。[1]376
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在静止状态中我们看不到一点灾难的痕迹。后一种状态得以产生的动力并不源自第一种状态。这就是卢梭所描述的社会和语言起源时所发生的:上帝的手指动作带来了人类命运的改变,带来了人类的文明状态,也带来了邪恶的起源。邪恶的外在性决定了它必然源自虚无,手指的细微动作从虚无中导致了革命。这一手指动作者也许是上帝,因为只有他的力量才是无限的,才使这场灾难得以可能。但也许不是上帝,因为上帝既然是善的就不希望发生灾难。而灾难的发生却超出上帝的善的意志。因为这是一种理性不能理解的偶然性,“我必须考察和探索不同的偶然性,这些偶然性在使人陷入腐败的同时也完善了人的理智,在使人社会化的同时也使人变得邪恶,并且使人和世界从遥远的古代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1]375
在第一种和第二种状态中,人类本来是处于分散状态的:“我认为原始时代是人从分散状态过渡到群居状态的时代,可以把人类群居时代定为一个历史时期”[1]366;“他们分散各地,几乎没有社会,几乎没有言语”。[1]369分散状态的人类“孤独无依、缄默不语”,没有产生社会和语言的需要,没有文明也不是野蛮,既不是自然也不是社会,而是处在诞生过程中的社会。这时的人唱着圣歌,享受着自足的快乐。这种状态被德里达称为“准社会”。
这场灾难却使得人们由分散的原始状态聚集起来。那么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呢?如果灾难属于自然的缺陷,那自然的缺陷就是自然借以与自身分离的灾难,这种灾难还是自然的东西吗?
(四)灾难的替补:德里达的解读
1.灾难:非必然的必然性
东西方史前文明的记载中都有关于灾难的记载,尤其是洪水,无论是《圣经》中的洪水故事还是中国的大禹治水,这些灾难的记载都值得重视。
德里达认为,在卢梭所关注的两种人类状态之间发生的事情是一种非必然的必然性。包含着一种残酷游戏的灾难。“如果社会是在灾难中产生的,那意味着它们是偶然产生的。卢梭将《圣经》中的事件自然化了;他将人类的堕落变成了一种自然过程。同样,他也将游戏者上帝掷骰子的行为,将他的运气或取胜变成了应受谴责的堕落。”[1]378
他认为灾难的发生并不是毫无缘故的,它既不是自然状态内部的东西,也不是自然状态的衍生物,而是自然状态的第一次“转向”。而正是在自然事件和社会的产生所导致的邪恶之间存在一种协同的替补性,才显示了上帝的存在。社会的产生是对自然灾难的一种替补。而这种替补是本源性的,如洪水、地震、火山爆发之类的灾难使原始人恐惧,但也使他们聚集起来,以弥补他们的共同损失。这是上帝让分散的人们聚集起来的手段。社会的产生平息了自然的灾难。它起调整作用,没有这种调整灾难就是致命的。在这里德里达发现了一种替补结构(社会对于纯粹自然状态的补充),在他看来,这种替补结构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起源。也就是说德里达认为灾难性的替补、社会的恶与人类自然的分散状态构成两个相对立的序列,对于自然状态的替补结构才使人类语言、文明和社会起源得以可能。这种替补结构和德里达的“分延”概念同属一体。也就是说,起源事件永远是带着相互差异的替补结构,并且其意义是无限推后的、是延期的,而不是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事件。
2.对第二状态到第三状态的过渡的理解
开端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一个单线的进展过程。卢梭在讨论从第二状态到第三状态的过渡时提到了一个正在诞生过程的社会,德里达将之称为“准社会”。人类在经过了农业社会以后出现了向原始社会的倒退。灾难事件的发生使得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种线性式的发展。
对于历史事件和开端纯洁状态的分析不能使用结构分析,因为结构分析并不能把种种灾难事件考虑在内,结构总是因为灾难而归于零点。“要指出(这种准社会)在循环过程中随时出现的持久可能性。这种原始时代的准社会状态事实上可以存在于社会状态之前或社会状态之后,也可以存在于社会状态之中和社会状态期间。”[1]369无疑,德里达认为这种准社会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一种界限,一种随时可以循环而至的界限,它可能存在于任何时期。而这种界限在划出的时候,它已经被越过了。“社会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点,是一种纯粹的、虚构的、不稳定的、难以把握的界限。人们在到达这种界限时就越过了这种界限,社会在哪里开始就在哪里推迟。他自存在之时就开始衰落。”[1]388
德里达认为卢梭描述的准社会状态并不是社会的前夕,也不是现成的社会,而是“诞生的过程,是不断的出场”。这种出场并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作为发生的过程显示出未来的可能性:“在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状态……它已经是社会、情感、语言、时间,但它尚不是奴役、偏爱、音节、韵律和间隔,替补是可能的,但尚没有任何东西发挥作用。”[1]382德里达把“过渡”产生的事件称为“节日”,因此卢梭所提出的田园圣歌的“纯洁状态”发生在过渡性的“节日”之中。但是卢梭的节日排除替补的游戏。在节日之前,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中,没有连续性的体验;而在节日之后,替补游戏开始发挥作用而产生间断性的体验。节日之后的替补时代是乱伦禁忌的时代。德里达对于卢梭的节日这样理解:“节日之前没有乱伦,因为没有乱伦禁忌和社会。节日之后没有乱伦,因为它遭到禁止。”[1]383乱伦禁忌可以说是发生在社会起源之际,同时也是道德的起源。乱伦禁忌和纯自然状态的替补性运动构成了对于准社会状态“流动性界限”的分延(差异+推延)的理解。
二、纯洁境界的一种新理解——至德之世:庄子之境
如果我们认同德里达描述人类文明起源和准社会状态所使用的“流动性界限”的分延原则,那么就不存在一种在某个过去的时间点发生的起源“纯洁状态”。因为在纯洁状态显现在场的时候,已经被“替补”的分延游戏污染了。那么人类文明诞生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历史学”事件,而是一个身处于“未来维度”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追问:人类文明的开化之际,到底发生了什么?庄子给了我们另一种解读方式。
(一)至德之世的描述
在庄子看来,至德之世是一个超越伦理的时期,这是一个人类没有是非和善恶之分的时期,此时有道德之实而人不知其名。人类心灵处于一种浑沌态。此时人的德性被称为至德,至德又名上德,下德以德为德而上德不以德为德,追求道德行为是上德行为的替补之物,“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第三十八章)。上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唐·裴休《黄蘖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
庄子这样描述至德之世: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胠箧》)(本文所引《庄子》段落全部引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面引文只标具体篇名)
如卢梭一样,庄子对人类纯洁时期的描述谈到了一种分散状态。这种状态是在尧舜禹之前的十二古帝王时期,作为圣人的德治时期,这时“民至死不相往来”。也就是说,人们之间是不需要交流的,名言未出。道德和礼仪并没有产生,而是原始的家族状态。在这样一个状态中,“山无蹊遂,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马蹄》)“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让王》)“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含哺而熙,鼓腹而游”(《马蹄》),“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天地》)。
其实对应于卢梭思考的社会和乱伦禁忌的产生、法制状态的出现,中国在这个圣人之德治的时期之后出现了礼仪治邦的状态。而德治状态对应于德里达研究卢梭所提出的准社会状态,中国的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圣王时期”,在《礼记》中也有与庄子相类的记载。孔子曾感慨自己没有遇到这一圣王时期,“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发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礼记·礼运篇》)礼名的出现加剧了作为大道的德的消隐。圣王时期并非无礼,只是如人饮水,作而不知,圣王时期之后并非没有德只是礼和德不再相根系。作为善名的礼立而作为上德的道体亏。名实分化,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分延开始破坏纯洁状态。这是智识开化的过程,上德以智识分化而成伪。
(二)至德之境的可能性
如同德里达所指出的“节日”,至德之境并不是一个卢梭所描述的乌托邦式的完全在场的状态。既然至德之境并不是一个历史上存在过的某种“现成状态”,它指出了一种通向未来的、“节日”般的纯洁状态的可能性,那么我们需要如何作为才能为这一“节日”的来临而做好准备呢?庄子的描述引导我们去思考:面对灾难的替补,在何种预备中,至德之境才能在未来的某种状态中出现呢?
1.“自因”的界限——自足
“在这种状态中,人享受什么样的快乐呢?人所享受的丝毫不是外在于他自身的东西,而仅仅是他自身的存在;只要这种状态存在,他就像上帝一样自足。”[1]363
按照卢梭的理解,“节日状态”中的人们有一种像上帝一样“自足”的快乐。这种自足是纯洁的“节日状态”的根本特征。因此对于“自足”的考察将是进入理解这一状态的必备条件。
卢梭的追求这种自足性源自古希腊存在论传统中的规定——“实体”。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这一概念奠基于整个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式的完全在场的追求。从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一概念开始,最高存在者就是从“自足性”得到经验的——“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这个曾被斯宾诺莎定义为“自因性的存在”的概念促使了整个近代的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合流。我们知道,在斯宾诺莎看来,作为“自因者”的实体有四个特点:第一,它的本质就包含存在。第二,它是无限的,它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否则它就不是自因的。第三,实体是唯一的。第四,实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切认识都包含在实体之中,但实体并不是这些认识的总和。
从斯宾诺莎的理解来看,这种自因性的概念和卢梭所理解的“纯洁之境”同样都是德里达所批判的“完全在场”追求。我们试从这个概念的内涵来加以分析:自因者不以他者为因,而却可以成为他者之因,但我们要注意到:自因者不以他者为因的“因”和可以成为他者之因的“因”只有具有不同的内涵时,这一自因性概念才能得以可能。如果自因者与他者不发生现实的因果关系,自因性概念才能得以成立。否则的话,自因之物为何会自因便说不清楚,因为在因果之链中,如果某物作为他物之因,那他物又必有另一他物作为因之因,如此无限后推下去。这样如果拿出一个自因者作为结束因果之链的终结者,实际是超出了人类的理性原则而成为“神学的”:自因者为神。这个作为“实体”的神在近代就演化成近代科学数百年来追求的“自然界存在的机制性原因”。这个原因显然带有数理性的特征。这种数理性的存在因为自认为可以成为一切存在者的原因,而无限地扩大自己对于整体存在者各个领域的干涉。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庄子思想的立足点——“无为”,自因者恰恰不能成为他者之因。也就是说自因者不能直接作用于他者,自因者与他者之间有一种无为“化境”在牵连,从因果性角度看,自因者恰恰是通过自我限制而与他者无涉的,即不参与“他者”的因果链条。否则,自因者便会受制于他者,而与他者成为一种交互关系,造成某种自因性的异化。我们从自然科学和数学原理的近代自因性存在的特点就可以看出这种存在者与机制交互的异化已经逐渐显露。自因者恰恰不应是作用于物的数理性机制存在,而是有限性的存在,它因自限而自因。
2.无为顺化
庄子追求的逍遥境界无疑给这种自因性的理解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庄子追求无己无待而游于天地。我们下面借助庄子的这种境界对自因者与他者之间的“顺化”关系加以阐明。我们已经在德里达的引导下分析了原始的替补性,借助这一成果,我们知道作为实体性的存在的自因性如果与他者发生因果性交涉,必然会被这种替补性的分延暴力所破坏,所以德里达实际已经否定了以卢梭和斯宾诺莎为例的整个形而上学的“完全在场”的追求。但是庄子的思想早就体验到了德里达的“替补的分延”经验,“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德充符》)。“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大宗师》)庄子和德里达一样指出了一个替补性的概念而言“命”,能正确对待这种替补性,就是正确对待命。庄子为我们指出了正确面对这种原始的替补性的方式。我们已经解释了在因果之链(甚至德里达的替补之链)中,自因者只能自我限制,也就是说自因者面对链中的他者是无为的。“命物之化而受其宗”,而面对命之行,因为心智不能探其根本,于是“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德充符》)“与物相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无心而任化者。不蕲为立于不败之地,而默应帝王之道者也。”[2]249
无论分延的不在场还是因果链的在场,都是天命的运行。在场和不在场的划分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正如德里达所说:当划出一条界限的时候其实这条边界已经被越过了。而自因者并不执着于在场或不在场而就是顺从划界同时的越界之一越。这一越就是郭象在《庄子注·序》总结庄子思想时所说的“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3]3。
德里达所指出的“流动的界限”并不是人的思想所要面对的对象,至为关键的是要使心灵与其分延性相通而不流于分延,自因者怀着一种无为的态度而顺化他者之性。顺物而物自化,自因者并不刻意或者直接改变他者,而自因限制自己在因果链和替补链上的作用,立于自身之正。他者的变是被自因者所“化”,也可以说因果之链和替补之链起作用的原始性恰恰在于自因者的自限之中。
要做到无为而顺物之性,修炼“忘”的境界无疑是庄子寻找的一条重要道路。“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忘吾有四肢形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达生》),“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北游》),“相忘以生”(《大宗师》),“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天地》)。
只有心灵不执着而顺化于替补性的分延,也才能为忘。执着于分延性的灾难和暴力我们就会“永不相忘”。我们在日常体验中也曾感受到,越趋于“极端”的事物越难忘,越行乎“中庸”的越可忘,如鱼之相忘于江湖。“忘”境实际是和心性修炼中追求的“时中”是同一道境。而庄子在解释真正的忘时说:“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谓诚忘。”
至德之境本身就是缺席和在场游戏于“忘”的一种至中(过渡)之境。它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而是德里达所形容的一个流动的界限。“它是一个点,是一种纯粹的、虚构的、不稳定的、难以把握的界限。人们在到达这种界限时就越过了这种界限,社会在哪里开始就在哪里推迟。”[1]388而庄子的思想境界为我们立身于这一流动的界限赢得“至德之境”提供了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沈一贯.庄子通(卷三)[G]//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第10册).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
[3]郭庆藩(辑),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责任编辑冯自变】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2-0005-05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曲立伟(1984-),男,山东莱州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
[收稿日期]2015-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