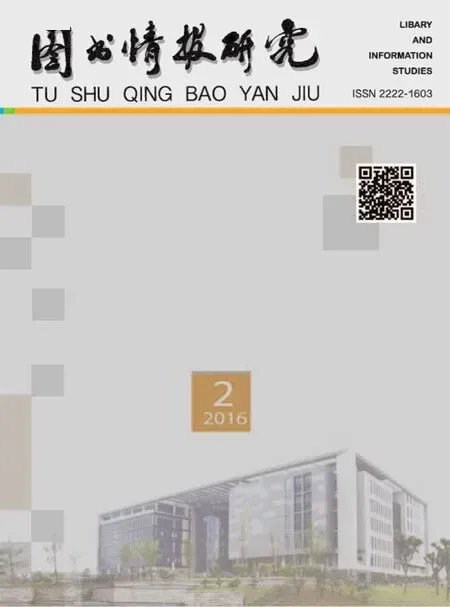民国时期古籍丛书出版的主要方式*
2016-02-12崔建利
崔建利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聊城252059)
民国时期古籍丛书出版的主要方式*
崔建利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聊城252059)
逐一介绍民国时期古籍丛书出版的三种主要类型:雕版印刷、影印和排印。传统的雕版印刷在民国时期古籍丛书出版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主要以私刻为主,坊刻与官刻则相对稀少;影印(照相石印)和铅字排印成为这一时期图书出版的主流印刷手段,影印主要有原样影印、缩印、对原书行格重新剪切拼接后重印以及将原书内容重新抄写后再摄影缩印等四种样式;在工艺上,与传统雕版印刷、影印相比,铅字排印体现出一定的优越性,而在形式上,民国初期的铅印古籍丛书大多完全模仿雕版古籍的装帧方式,使得其版面构造、行款、装帧等与雕版古籍几无二致。
民国古籍丛书雕版印刷影印铅字排印
从出版方式上看,民国时期的新出古籍丛书主要有雕版印刷、影印和排印三种类型。
1 雕版印刷
“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千百年来,雕版印刷等传统的印刷方式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1]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现代印刷术的传入,古老的中国雕版印刷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雕版印刷在我国作为一种主流印刷术毕竟有着千余年的历史,多快好省的洋装书在很多民国文士心目中怎么也无法取代雕版古籍的那份厚重和典雅。再加上当时社会离乱纷争,传统雕版古籍日渐减少,所以,许多学人、显宦或藏书家等仍乐于用传统雕版印刷来刻印典籍。从刊刻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雕版古籍丛书主要以私刻为主,坊刻与官刻古籍丛书则相对稀少。
1.1 私刻
私刻亦称家刻,是指私人出资校刻图书。由于刻书人以自己的名望为重,往往对于书本进行精细的校订或选择优秀的善本作底本进行刊刻,所以私刻本的质量较高。就不同社会阶层来看,藏书家是民国时期私刻古籍丛书的主体。“这些人大多各有专长,且私家藏书丰富”[2],象陶湘、董康、徐乃昌、刘承干、张钧衡、刘世衍等人为代表的藏书家暨刻书家,他们往往凭借着自己对古籍善本的浓厚兴趣,利用各种途径收集宋、元、明孤本,并不惜工本加以翻刻,其刻本精美程度、校勘水平直追宋元珍版。比如董康刻书从来不顾惜本钱,校勘、写手、刻工都聘任高手,纸墨之选亦精益求精,所刻《诵芬室丛刊》、《读曲丛刊》等刻工甚精,艳称书林,魏隐儒曾称曰:“董氏刻书重视质量,纸用上等棉连或六吉料半,墨选上等黄山松烟或五百斤油。选择底本也非常认真,均经校勘而后付梓,为藏家所称誉。”[3]陶湘所刻《百川学海》、《儒学警悟》等,则堪称影宋本之典范。安徽南陵徐乃昌“朝访残碑夕勘书,君家故事有新图。衣冠全盛江南日,儒吏风流总不如”[4],其所刊刻的影宋本《随庵丛书》、《唐女郎鱼玄机诗》,影元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苍崖先生金石例》等都摹刻逼真,刀法工致,成民国私家雕版古籍之精品。贵池刘世珩摹刻的《玉海堂影宋元本丛书》、《宜春堂影宋巾箱本丛书》等亦为时人所尚。
民国时期私刻古籍最多的当属浙江南浔刘承干。其嘉业堂藏书楼汇集了当时散佚的多家藏书约1.3万种,18万册,“收藏遂富甲海上”[5]。依靠丰富的藏书,刘承干共刻印了二百多种古籍,其中就包括《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大型丛书。刘氏刻书精益求精,曾聘请著名版本家缪荃孙为所刻之书作校,请最善于摹写各类字体的湖北人饶星舫为书版写手,请享有“天下第一好手”之誉的武昌人陶子麟进行雕刻,故嘉业堂所刊之书以精美典雅著称。刘氏刻书不是为了营利,或自藏,或送给学人,于近代古籍的传承和流布,功不可没。版本学家胡道静曾赞曰:“所致孤秘,枣梨以行,于是老儒之占毕,介士之孤愤,系一线于不坠,主人之功为尤不可没也”[6]。
1.2 坊刻
古代书坊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又称书肆、书林、书堂、书铺等。书坊所刻的书,版本学界称为“坊刻本”或“书坊本”。书坊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和流通最重要的载体,从书籍的总生产量看,坊刻本的比例要远远大于官刻和家刻。但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新的印刷技术的推广,传统意义上的书坊大多采用新式印刷技术而变为现代印刷企业,如开设于明代万历间的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其刻书远近闻名,久盛不衰,“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7],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书坊之一,直到建国后的1954年才关门,但从清末开始,扫叶山房便开始采用新兴的印刷技术,陆续添置铅印、石印等新技术设备,到民国时期已完成从以雕版印刷为主的书坊向现代印刷企业的转型,基本上不再从事雕版印刷业务了。其他仅存的一些书坊,大多变为以承揽雕版刻书业务为生的刻字铺或贩卖新、旧图书为主的书店。所以,民国时期传统意义上的坊刻本古籍并不多见。当然,有些书坊也自行编纂并刊刻一些古籍丛书。像创建于民国十二年(1923)的扬州著名书坊陈恒和书林,坊主陈恒和念及乡帮文献“零落殆尽”,于是有编刻《扬州丛刻》之意,“谋之恒娘,恒娘大喜,遽出私蓄以佐其成。于是搜集先哲所著凡廿四种底本,别写付刊,命之履恒职校勘之事,五阅寒暑乃克毕工”[8]。可见,为了这部《扬州丛刻》,坊主陈恒和几乎是全家上阵,甚至动用了老伴的私蓄。《扬州丛刻》不仅是近代以来扬州文献的首次大规模结集出版,同时也堪称民国时期坊刻本的典范之作。当然,《扬州丛刻》的刊刻主旨在于传承和流布乡帮文献,这与传统意义上以营利为目的甚而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的坊刻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就这点来看,《扬州丛刻》又具有浓厚的家刻特征。
1.3 官刻
官刻本即由“各级官府及其附属机构所刻的书”。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并不存在专门的官府出书机构,但官府及其附属机构组织编纂出版的图书并不在少数,只不过这些书大多是通过相关出版企业采用现代印刷技术进行出版的。比如广东省政府组织编纂的大型地方古籍丛书《广东丛书》,即是委托商务印书馆用影印或排印的方式出版的。云南省政府组织编纂出版的《云南丛书》,虽是刻本,但大部分是对所收丛书子目原版片进行的重新刷印,只对个别绝版子目进行了重新刻版。当然,有些政府部门或其下属单位也偶有组织或出资编纂并刊刻古籍丛书之举,像浙江省图书馆1916年所刻《蓬莱轩舆地丛书》等。
2 影印
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影印主要指照相石印,即以照相底片为转印材料进行制版印刷,不会改变原始文献的版本特征,故被称为影印。照相石印可以完整地复制或再现古籍样式和版本特征,因此成为民国时期古籍复制暨大型古籍丛书出版的重要方式。
照相石印是制版照相术应用于石版印刷的产物。同雕版印刷与手写或手绘直接上版的石印相比,照相石印具有诸多优点,正如民国时期的版本专家孙毓修所言:“摹写上版,虽字画不改,终觉貌似而神遗,摄印则神貌兼至,其善一矣;古书多一斟录,则多一谬误,故书贵原本,摄影既不烦斟录,自不失本真,其善二矣;镂版可以传久而不能速成,摄印则可速成而亦能传久,其善三矣。”[9]从应用范围来看,民国时期的照相石印几乎可以和铅字排印分庭抗礼,成为当时应用最广的两种古籍丛书出版方式。
“1840年,照相术通过照相石印术首次应用于印刷,并于1859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照相石印术需要将书页的照相底片投影到用感光乳剂处理过的石头上,到1882年,这种技术已经变成了上海西式印刷机构中最重要的工序之一。”[10]79通过美国人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所著《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中的这段引述,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照相石印术的主要机理及其在中国的大致发展历程。通俗地说,照相石印术主要是通过对底本照相的方法,先将图文制作在转印材料上,然后再将转印材料上的图文转移到石面上进行印刷,这一过程又称“落石”。照相石印不仅可完全复制底本原状,印刷速度也大大提高,正如时人黄协埙在《淞南梦影录》中写道:“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竞日而就,细若牛毛,明如犀角。”[11]因为照相石印可以将所拍底片任意缩放,因此,民国时期通过照相石印出版的古籍丛书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2.1 原样影印
即将原书摄影后按原书开本大小进行石印。这种方式可以对底本进行原样复制,特别是采用彩色照相技术后,所印新书采用与原书一样的装帧方式,几可达到乱真的程度。缺点是纸张耗费多,成本高,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除非有公家或私人出资定制,或藏书家为复制某些稀有文献而进行少量印刷,一般很少在市场化出版中采用这一方式。
2.2 缩印
即将原书摄影后缩小开本进行石印,以达到节约成本或减少书籍体积的目的。因雕版古籍字体不会太小,经适当缩印后仍旧无碍阅读,但书的开本、体积小了,易于存放和携带,既减少了商家成本,又适应大众阅读的需求,因此,缩印成为民国时期古籍影印最为普遍的出版方式。大型古籍丛书中的子本缩印除了可以减少丛书体积外,还起着使整部丛书在外观、开本方面整齐划一的作用。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中就有许多影印本,无论原版开本多大,在除去版心后,一律缩印成为32开本;同样,在影印《四部丛刊》时,将所影印古籍均缩印为高200毫米、宽132毫米的小开本,只是在各书前牌记中,对该书所据原底本的尺寸大小作了记录。除了上述单页缩印外,还有拼页缩印,就是根据原书版面和字体大小,把原书若干页拼在一起分成若干栏,拍照后再缩印:或是原书两页分上下栏拼成一页,或者是原书四页分上下栏拼成一大页,还有的甚至是原书九页分三栏拼成一大页,等等。拼页缩印多用在影印大型套书或丛书时,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即将《四部丛刊》的四页缩拼成一页,改线装为平装或精装而成。另外像开明书店影印的《二十五史》等,都是拼页缩印。
2.3 对原书行格重新剪切拼接后重印
雕版古籍刻印完成后多将每页自版心对折进行装订,每半页多少行、每行多少字也成为该书最重要的版本特征之一。影印古籍丛书时,为了增加该丛书每页的内容以相应减小该丛书的页码或体积,除了上面提到的去掉版心后将两半页拼接成“亲密无间”的一页外,还可以将某种书里下一页的一两行甚至半页剪切后拼接到该页上面,把原书一页半、或两页、三页甚至更多页合并成一大页,摄影缩小后石印。这样可以在保持丛书内容完整的前提下大大减少整部丛书的册数,不仅售价降低,而且方便了阅读和典藏。
2.4 将原书内容重新抄写后再摄影缩印
这种方法影印的古籍与手写上版的石印古籍在版式特征上完全一致,多为正楷手写体上版。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用手写件照相底片制版,一是用手写件直接上版。与剪拼缩印只是部分改变原书行款相比,这种抄本缩印(或石印)则完全改变了原书的版式特别是字体特征。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扫叶山房出版的大量普及性古籍丛书或日常用书,主要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除照相石印外,因印版材质不同,还有珂罗版印刷、照相铜版、照相锌版等印刷方式。珂罗版即玻璃版,属平版印刷,铜版和锌版则属凸版印刷,它们主要采用照相底片落石制版,故也被称为影印。珂罗版、铜版、锌版等印刷方式具有印刷精致、准确、复制效果好等优点,适宜印制较为精致的绘画艺术品和层次细致的真迹手稿等,但由于制版及印刷成本较高,在古籍丛书印刷中并未被广泛应用。
3 排印
“铅字排成夺化工,聚珍活板得毋同。文章有用原无几,省却灾梨易奏功。”[12]这首诗描绘的是铅字排印对于传统雕版印刷的进步意义。其实,铅字排印不仅与传统雕版印刷相比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对于石印术也略胜一筹:“雕版印刷的缺限在于一块书版只能使用一次,并且最多只能印刷2 000份高质量的复本;石印则对印刷机和石版的磨损十分严重,如果使用凸版印刷,新发明的钢制印刷机和一套活字字范与字模可以使用50次以上。”[10]36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的这一观点,基本上可反映出近代以来印刷术更新或演变的过程和动因。麦都思所谓的“凸版印刷”,到了民国时主要是铅活字印刷。因此,民国时期的活字排印本主要是指铅印本。铅活字印本很早即已问世,1436年朝鲜排印的《通鉴纲目》,是世界上最早的铅活字本。但世所公认的铅印术是1450年德国人谷腾堡发明的。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设立的铅印机构陆续迁入我国境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嘉兴诗人孙泓参观后在其《洋泾浜杂诗》中写道:“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字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13]说明当时的铅字排印术还是相当原始的。1859年,在上海美华书馆担任技师的美国人姜别利改进了汉文活字规格,定出了7种标准,奠定了汉文铅字制度的基础。到20世纪初期,仅上海就有包括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内的40多家新式出版企业普遍采用了新式铅印术和印刷机器。
民国初期的铅印古籍丛书,在形式上大多完全模仿雕版古籍的装帧方式,栏、界、中缝齐全,双叶单面印刷,线装等等,使铅排古籍的版面构造、行款、装帧等与雕版古籍几无二致,俗称“线装铅印本”。为了使铅字排印古籍在字体上看起来更像雕版印刷,几个有实力的现代出版企业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聘请当时最优秀的刻字工为各自企业雕刻字模,因宋版古籍最为世人崇尚,因此,这些字模多以宋体字为标准,称为仿宋字。像商务印书馆聘请黄冈陶子麟以唐末刻本《玉篇》之字体,用照相方法在铅字坯上直接镌刻,制成一号、三号“仿古活字”。杭州丁辅之、丁善之兄弟摹拟北宋欧体刊本字体,将楷书笔画和宋体字的间架结构融合在一起,设计了一种新的印刷字体,名曰“聚珍仿宋”字,1917年被中华书局收购,用来排印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及其他众多书刊。《四部备要》不仅成为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的标志性成果,也被视为民国时期铅字排印本古籍丛书的典范。此外,商务印书的《国学基本丛书》、上海杂志公司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都使用了铅排方式。
[1]贾鸿雁.民国时期古籍丛书出版的成就与影响[J].图书馆杂志,2003(1):76-78.
[2]杨嫚.民国时期古籍丛书出版研究[J].图书馆论坛,2005(5):235-237,231.
[3]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201.
[4]王国维.题徐积馀观察随庵勘书图之二[M]//吴无忌,编.王国维文集·观堂集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569.
[5]缪荃孙.嘉业堂丛书序[M]//《嘉业堂丛书》经部第一种《周易正义》(第一册).嘉业堂民国七年(1918)戊午刻本.
[6]胡道静.周子美撰集书目二种序[M]//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学林漫录(十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226.
[7]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35-36.
[8]陈恒和.《扬州丛刻》跋[M]//陈恒和,辑.扬州丛刻.1930年扬州陈恒和书林刻本.
[9]孙毓修.涵芬楼秘笈序[M]//孙毓修,编.涵芬楼秘笈.民国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10][美]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M].张志强,潘文年,鄯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1]黄协埙.淞南梦影录卷二[M]//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8.
[12]李默庵.申江杂咏·机器局印书[M]//丘良壬,潘超,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2.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85.
[13]孙泓.洋泾浜杂诗[M]//王韬.《瀛蠕杂志》引.长沙:岳麓书社,1988:197.
(责任编校骆雪松)
The Main Ways of the Publication of Ancient Book Seri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ui Jianli
Can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59,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 main publishing ways of ancient series of books one by one.The traditional woodblock printing sill took a place in publishing these books,with the private printing being the dominant method and bookshop printing and official printing being comparatively less.Photocopying and typography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printing book in that time.Photocopying mainly includes four patterns,namely,untouched photocopying,reduction printing,reprinting after the shearing and splicing of the original line format and reduction printing after copying the original contents.In terms of technolog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woodblock printing and photocopying,typography shows its superiority while in terms of format,most of the ancient books printed through typograph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mitated completely the way of binding of woodblock printing,making them strikingly similar in the aspect of layout structure,line format binding and so forth.
the Republic of China;ancient series of books;woodblock printing;photocopying;typography
G256.22
崔建利,男,1969年生,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发表论文50余篇。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研究”(项目编号:12YJA870002)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