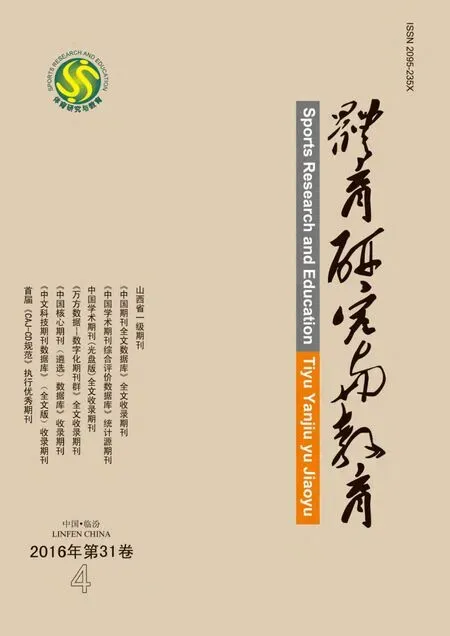从竞技到游戏:未来体育发展的新路径
——基于体育史的反思
2016-02-12李佛喜
李佛喜
1 前言
当代竞技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竞技的全球化,如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奥运会、遍布全球各地的ATP、WTA和足球世界杯、世锦赛等,然而当代竞技似乎忘记了它为什么而出发。运动场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第一精神”仍根深蒂固;运动员服用各种深知有害于自身健康的禁药;运动场下观众只要“第一”不惜用暴乱、污言秽语、人身攻击来宣泄情感;赛场外国家间把竞技变成政治交往的手段,如柏林奥运会上希特勒将它演变成传播纳粹的舞台。这一切不禁让我们反思,对于顾拜旦先生所言的“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的竞技观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如何来化解这一“泛竞技化”问题?思考现代竞技该走向何方?笔者以体育历史的发展沿革和现实的状况为基点来探讨竞技的未来发展道路。
2 从游戏到竞赛——竞技概念的一种解读
国内外学者关于竞技的概念讨论有很多。“在对待竞技起点的问题上说法不一,主要观点有劳动说、活动说、教育说、战争说、巫术宗教说以及多源说等”[1]。 张军献认为:“竞技就是身体活动性游戏。”[2]杨其虎则认为:“竞技体育只是含有更多文化内涵的复杂游戏而已。”[3]德国的笛姆对竞技的定义是:“从广义上来说,竞技运动就是游戏,从狭义上来说,竞技运动是有组织的身体性游戏。”[4]从上述关于竞技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很多学者倾向于认同竞技的逻辑起点是“游戏”。但也有学者认为将游戏作为竞技的逻辑起点是不妥当的。“虽然游戏与竞技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竞技的本质必定不在游戏之中,‘竞技本质游戏论’是不科学的论断……认为竞技是身体性运动竞争的技艺”[5]。
对于竞技本质的解读可以从它的历史发展轨迹中探寻。阿伦·阿古特在《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的开篇章就阐明他认为的体育内涵,即“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基本模式,一个去区分游戏(play)、有组织的游戏(games)、竞赛(contests)、体育(sports)的初级模型”[6]。从他的思路中可以看到体育的前身是游戏,中间还包括有组织的游戏和竞赛,体育是随着人类历史推进逐渐发展而来。乔治·维加雷洛的《从古老的游戏到体育表演》一文也是沿着相同的思路来阐释体育(或竞技),即体育表演是由人类最原始的简单化、生活化、休闲化的游戏逐步演变、升级到表演的高层次上来。从历史上看,游戏是最先开始的人类文明活动之一。“赫伊津哈得出了这样一个权威的结论: 文明决不脱离游戏, 它不像脱离母亲子宫的婴儿,文明来自于社会的母体,它在游戏中诞生, 并且以游戏的面目出现。文明是在游戏之中成长的,是在游戏之中展开的, 文明就是游戏。”[7]此后游戏开始有了更为紧密、有序的组织。早在公元前776年希腊就组织了第一届古代奥运会;到了中世纪体育以“骑士体育”和“平民体育”相存,再到近代由法国的顾拜旦积极组织下,恢复了古代奥运会的形式,形成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雏形;到了当代,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竞技渗透到地球的各个角落。游戏从人类的简单悠闲活动变成了体现人类历史、文明的竞技。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竞技可以解析为:它是由游戏到竞赛的历史演变,即竞技存在于历史进程中,并表现于人类的生活实践,随着人们的认识而不断丰富。它是一个概念史。
3 对现代竞技的批判
如果将人类高级竞技发展的进程从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古代奥运会开始算起的话,到当代已经走过了近2800年的历史。它一路伴随着国家的兴衰、战争的起落、物质的更替,这些也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到了现代,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它经历了如马克思所言的“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物质比历史上的总和还要多的物质大繁华”后出现了“异化”。如辛格于在《游戏的人》中所言:“如此这般,在现代社会中,竞技体育逐渐远离了纯粹的游戏领域……。在现代社会中,竞技体育脱离了其本来的文化过程,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8]体育原本追求的公平、正义、身心健康、平和、超越等崇高理念开始被蒙蔽或是被忽视。
3.1 竞技商业化对利益的追求
竞技的发展需要以经济作为基础。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奥运会为了保持自身的“业余性”“纯洁性”“非功利性”是不与经济、商业有挂钩的,但经济问题却成为想举办奥运会国不得不考虑的棘手问题。“蒙特利尔奥运会欠下了10亿美元的债务,增加了纳税人20年的负担。蒙特利尔陷阱让多个成员国谈虎变色,国际奥委会陷入了极度的窘境”[9],因此,萨马兰奇先生不得不提倡商业化行为。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它不仅不亏钱反而实现了盈利,进而有了后来奥运会的良好发展。但当代竞技却太过于商业化而忽视了竞技本身。现如今国内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马拉松赛事,“从2010—2014年,短短的5年时间,由最初的12场增加到如今的50场,翻了4倍多……但国内目前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尤其是城市马拉松比赛,往往是受城市利益的驱动,把城市的发展放在首位,而马拉松比赛该呈现的精神则逐渐被人淡化遗忘。”[10]2012年的广州马拉松赛,两名选手比赛中意外猝死;同年的北京马拉松赛有1千多名选手不同程度的受伤;2016年广东清远马拉松出现“近两万跑友参加,其中当天共发生12 208例伤病,1名选手在ICU留院观察。”[11]体育项目竞技化、商业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商业化成了竞技本身!更为可怕的是可以为金钱而打假球、吹假哨、打激素、赌球等有损于竞技本身的行为——横行霸道、毫无畏惧。
3.2 竞技科学化对工具的崇拜
在经历了信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们可以利用电脑、手机做到“天涯若比邻”的视频聊天,点击搜索引擎便可知“家事国事天下事”,利用各种人工智能机器可以享受“悠然见南山”的休闲生活。科学技术同样也改变着竞技的规则和形态。网球场、足球场上利用“鹰眼技术”来挑战裁判的权威,利用高科技的“鲨鱼皮”游泳衣我们可以让运动成绩飞涨,高效的科技器材刺激运动员的生理机能以提高运动能力。这一切都是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改变。科学技术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但科学技术就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最高质量的生活和最完美的竞技吗?答案是否定的。科学技术更像一把双刃剑:科技越是触手可及,我们就越难以逃脱它的“掌控”。“2009年罗马游泳世锦赛上,为期8天的比赛共43次刷新31项世界纪录,比两年前的墨尔本世锦赛多了27项,也比历史上创造世界纪录之最的1976年蒙特利尔世锦赛多了14项”。[12]这与高科技泳衣的广泛使用密切相关。教练员们更热衷于利用各种数据来组织训练和分析比赛,但却忽略了运动员本身的精神状态。“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超越,给伦理道德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对社会而言,普遍的富足与相对的贫困同在,无限的机会与巨大的风险并存;对个体而言,科学理性对主体性的张扬与理性化官僚体制对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压抑同在,物质生活的富足与精神生活的贫乏并存。”[13]在科学化背后的技术竞技时代,可否找到让未来竞技良好发展的道路更值得深思和琢磨。
3.3 竞技理性化对道德的忽视
理性是人类所独有的,是区分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的根本。席勒认为们人有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感性冲动“是由人的物质存在或者说是由人的感性天性而产生的。它的职责是把人放在时间的限制中,使人变成物质,而不是给人予物质。形式冲动“来自人的决定存在,或者来自人的理性天性;它竭力使人得以自由,使人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得以和谐”。[14]所以,理性是我们成为人的必要因素。但必须指出,在竞技场上我们有时过于利用我们的理性,却忽略了人性道德。阿姆斯特朗服用禁药,遭到终身禁赛和剥夺七个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头衔的处罚、田径世界冠军阿曼特尔·蒙茨霍服用违禁药物后,被给予其禁赛两年、“马家军禁药事件”为我国田径事业蒙上了不可抹去的阴影。竞赛为了夺得冠军是我们的理性所驱使,但以不择手段的服禁药、故意使用高科技工具提高成绩、肆意妄为的破坏竞赛规则甚至是无视、践踏体育的道德底线等行为就需要批判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理智的这个世界虽然作为纯然的自然只能被称为感官世界,但作为自由的体系却可以被称为理知世界,也就是道德世界。”[15]在理性后:“只要思辨理性完全彻底地坚持纯粹理性的理想,它就能驳斥无神论和神学庸俗化的倾向,而使纯粹理性保持其纯洁性,从而为理性的实践应用保留了领地,以便建立起“道德学”。[16]竞技是人类实践的高级形式,但仅仅停留在理性这一层面的话,导致的结果是人的“不道德”,那么竞技体现人对自身的超越就无法显现,甚至会扭曲人性而走向极端理性。
3.4 竞技职业化对人本的缺失
现代竞技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竞技的职业化。早在古希腊奥运时期,就有了如当今职业化的影子。“各个城邦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优胜成绩,不惜重金来收买其他城邦的运动员,被雇佣者如果获得冠军,他的身价就是500个杜拉克,这些钱在当时大约能购买500只羊……大部分(运动员)是出卖给俱乐部的,如果需要可以变更国籍”。[17]当时的职业运动员们为了获得更好成绩所带来的回报,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以致于古希腊著名三大悲剧家之一的欧里庇得斯讽刺奥林匹亚的胜利者,称他们是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对城邦没有任何贡献却受到人们的奉承。到了现代竞技场上,除了与古代如职业运动员为金钱可以“无所不为”的问题外,还出现了竞赛场上“无人”的困境。职业赛场上种种对于“人”的忽视,无论是运动员、对手、球迷、教练员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职业化运动员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取得良好的比赛成绩,但现代竞技里有时仅仅是把运动员当成创造纪录的“工具”、当成“团结人民”的政治手段、成为娱乐大众的“玩具”。我国110米栏运动员刘翔,在2008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因“受伤退赛”,遭到一些人的无情辱骂甚至是人格的诋毁当属案例典型。种种现象看似是职业化所带来的,拨开云雾实际是竞技职业化下“人本”的缺失。职业化的赛场上我们由于对纪录、胜利、荣誉的过分激情、疯狂、炽热的追求,使我们忽视了我们对面的对手,把他们看成了我们必须打倒的“仇人”、把与自己所支持倾向不同的人当成“敌人”、把赛场变成了如古罗马时期的恐怖、血腥、无人性的斗兽场。久而久之,职业化下的竞技体育会变味,“人”也将会在赛场上消失了。
4 从游戏到竞技——未来体育发展的新路径
从游戏到竞技是历史的轨迹,但从竞技到游戏则是未来体育发展的新路径,是竞技的另一种升华,是人的另一种解放!从游戏到竞技是历史的,但从竞技到游戏则是人文的。前一种游戏单单是指人在有钱有闲后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后一种则是对于人类自身的超越,是一种美的状态,是美的目的。如席勒所说:“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14]在这里,游戏是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统一。它象征着自由,而“游戏竞技”不仅仅是单纯回到游戏本身,且也不需要“分家”,反而需要使它们“亲如一家”,它们是“和则兴、分则衰”的关系。
4.1 游戏中人文的回归
现代竞技中常常缺乏对人自身的关注。从生理层面讲,人都具有竞争性和攻击性,但如果将竞技放在这一层面讲,那么我们与大自然中的动物为争夺食物、对象、领地而不惜一切相互厮杀又有什么不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虽拥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私欲但也拥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情心。虽拥有无限的激情但也拥有高尚的节制,虽拥有无尽欲望但也拥有知足常乐的心。竞技需要有游戏的加入,让它来调节感性的冲突和形式的冲突,使人建立在竞技之上而高于竞技、超越竞技,使人回归到人身上。事实上,竞技是展现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个大舞台(前提是建立在游戏精神上),当竞技以“游戏竞技”存在,竞技场就是人类的文明剧场,在这里人类离文明很近!网球赛场上我们会因为无意打中对手或是压到边线得分而向对方挥手表示道歉,跆拳道或武术比赛开始时我们会鞠躬或抱拳表示相互尊重,篮球场上撞到对手会主动帮忙扶起等。如果运动场上只有胜负、输赢、利弊,上述文明行为必定是稀缺的。如果不把比赛只是当成一场游戏的话,那对手就是不得不消灭的“敌人”。为了要赢,体育规则可以随意破坏;为了不输我们可以口出不逊、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竞技是人所需要的,但人更需要游戏的精神。
4.2 游戏中自由的释放
在康德看来,自由既是道德的可能又是前提;在席勒看来游戏就是自由的一种实现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物质极大丰富,因而有足够的游戏时间而终将获得自由;而游戏就是自由的另一种实际存在和表现方式。但现实中人们很多时候只把游戏理解成“玩一玩而已”、单纯的“唯乐原则”、“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一层面的话,就会造成诸多的问题。俗话说,“童年是游戏的童年,也是快乐的童年”。小孩子们玩捉迷藏、老鹰捉小鸡、跳飞机格是快乐的,自由的。但也许是时代变革得太快,我们并未能及时赶上,上述的儿童的游戏早已经不再像以往那么流行了。同时,现代社会还有一种特有的现象即“成年儿童化”和“儿童成年化”。无论是成人或是小孩都喜欢沉浸在网络的美丽虚拟世界中,看电视剧、玩电子游戏、购物等。这样的一种自由和快乐是人的最终追求吗?冯友兰先生曾提到人生有四个层次的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18]如果我们的生活仅仅在物质享受的层面,那么这四个境界中只能算得上自然境界和功利的境界而已,并且这一切似乎与康德、席勒、马克思所言的自由的人都相去甚远。游戏还是游戏,但怎么理解、怎么玩却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竞技中的游戏精神也许就是解开这一问题的钥匙,回到“老鹰捉小鸡”最纯真、最质朴、最快乐的游戏中而得到自由,因为当你游戏的时候才是完整的人。
4.3 游戏中幸福的追寻
幸福是人类所共有的追求,也是永远的历史难题。历史上的哲人对于它的探讨不胜枚举。苏格拉底认为至善就是幸福;孔子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获得“知”是幸福;卢梭则认为将欲望管辖在自己力所能及即可得到幸福;席勒则认为在游戏冲动中与美同在即是幸福的。的确,当将游戏置身于生命当中人能得以自由和快乐。赛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场面: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双方都极其渴望获得胜利,用尽全身的勇气、智慧、力量、汗水去拼搏每一分、每一秒,但竞技比赛的冠军只有一个,最终总有失败者要无奈而痛苦的接受失利。但如果此时胜利者能给予失败者一个深深的拥抱并用善意的语言去安慰,而后失败者也以赞美的语言去祝福胜者。这一刻,胜负的意义会被超越,幸福会在彼此间荡漾。对中国而言,这一层面的幸福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即可寻得。中国是一个拥有游戏文化的国家,赫伊津哈推崇中国古代的游戏精神:“游戏的性质在中国比希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古代中国, 几乎每一个活动都呈现出仪式性竞赛的形式: 涉水、登山、伐木、采花都表现出游戏的成分。……他注意到中国人在游戏、竞赛和战争中的“礼让”精神, 实在是难能可贵。在中国, 为荣誉而进行的竞争也可以倒过来变成礼貌的竞赛。”[19]关于幸福的智慧,老子就曾言道:“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止下。”[19]仅仅竞技、争斗、杀害、利益、名声不是我们最为智慧的,只有在“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游戏”中才能把握住幸福的真谛而拥抱幸福。
5 结语
弗洛伊德建构了人的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超我”的层级是人生生不息、坚持不懈、乐于进取精神的展现,是人道德、自由、幸福的站点。从游戏到竞技就如从“自我”到“本我”的飞跃,而从“竞技到游戏”则是“本我”到“超我”的上升。这一切也如马斯洛所描述的:在满足了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被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后的“自我实现”。从竞技到游戏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反省后的超越,是未来竞技新的生命力所在。
[1] 孙玮.竞技与游戏[D].长春:吉林大学,2010.
[2] 张军献,沈丽玲.竞技本质游戏论——本质主义的视角[J].体育学刊,2010(11):1~8.
[3] 杨其虎.再论竞技体育的游戏本质[J].学理论,2015(5):105~106.
[4] 笛姆.竞技运动的本质与基础[M].福冈孝行译.日本:政法大学出版局,1974.
[5] 刘欣然,余晓玲.竞技本质非“游戏论”——就本质主义立场与军献兄商榷[J].体育学刊,2011(3):7~13.
[6] 古特曼.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2.
[7] 何道宽.游戏、文化和文化史——《游戏的人》给当代学者的启示[J].南方文坛,2007(6):15~24.
[8] 山本德郎,赵京慧.竞技体育是否已经远离了游戏的范畴——对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的探讨[J].体育文化导刊,2005(1):33~34.
[9] 童昭岗,等.人文体育——体育演绎的文化[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
[10] 刘乐,储志东.我国马拉松“热”的“冷”分析[J].当代体育科技,2015(20):147,149.
[11] 余亦鹏最受伤马拉松?清远两万人参赛现1.2万例伤病[EB/OL].http://news.jxntv.cn/2016/0324/7754467.shtml.
[12] 沈克印,周学荣,周丽萍.体育科技与体育伦理理性整合的支点——由高科技泳衣引发的伦理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7):5~8.
[13] 沈克印,周学荣,葛小军.自由的限度: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运用的哲学思考[J].体育学刊,2010(4):27~30.
[14]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5] (德)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M].郭大为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6] 张溢木,王乐.试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理性[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4~6.
[17] 史友宽.古希腊竞技体育衰退的原因[J].浙江体育科学,2011(3):26~28,42.
[18]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9] 老子.道德经[M].欧阳居士注译.北京:北京画报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