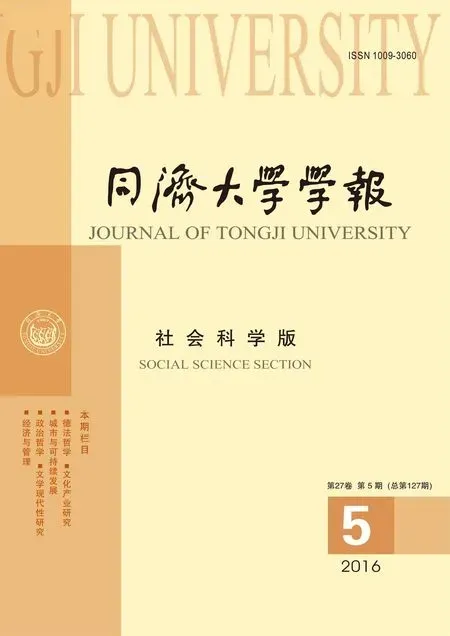《秘密》的开篇场景:沉默和言说
2016-02-12钟碧莉
钟碧莉
(1.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092;2.帕多瓦大学 文学与语言学学院,意大利 帕多瓦35137)
一、对话的前提是打破沉默
不少读者发现弗朗西斯科和圣奥古斯丁在开篇由始至终都没有和对方说过一句话,在笔者看来,其根本原因是,两者都分别沉浸在自我的沉默——沉思中。开篇序言明显被特意分割成两个对话部分:(1)弗朗西斯科和真理女神的对话;(2)圣奥古斯丁和真理女神的对话。这两个部分在叙述结构上存在着某种对称关系:
(1)弗朗西斯科—沉默,沉思生死之事 (2)圣奥古斯丁一直隐身—沉默
真理女神出现 弗朗西斯科看到圣奥古斯丁(出现)
真理女神出场介绍 圣奥古斯丁出场介绍(由彼得拉克描写,本人沉默)
彼得拉克沉默,真理女神打破沉默①弗朗西斯科除了刚开头问了真理女神的身份外,就没有任何一处地方直接描写他所说的话语;间接地提及他说话是在真理女神表明自我身份后,弗朗西斯科由于无法忍受女神身上的光芒而陷入了沉默:“她察觉到这点,在短暂的沉默后,她又开始讲话;在问了一系列详细的问题后她终于将我引向了长谈。”圣奥古斯丁沉默,真理女神打破沉默
真理女神和弗朗西斯科对话 真理女神和圣奥古斯丁对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与真理女神对话前弗朗西斯科和圣奥古斯丁两人都处于自我的沉思之中。真理女神好不容易才打破了弗朗西斯科的沉思/沉默,引导他和她对话,因为他一直在沉思人类“生死”的问题;为了“打破”他的沉默,真理女神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动用自己言辞的鼓动力量:“interumque et interum in verbaprorumpens,minutisinterrogatiunculis me quoqueutsecummultacolloquerercoegit.”(Breaking again and again with her words,with detailed questions she finally leads me to a long conversation.)在谈话后,弗朗西斯科感到自己增长了见识,而且他现在终于可以直视真理女神而不必畏惧她身上的光芒了。
现在,走出沉思、被打破沉默的弗朗西斯科开始要讲话了,因为他开始发现旁边的圣奥古斯丁时,他(或许是激动地)第一次说到“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沉默”;然而此时,真理女神却突然阻止了他言说的欲望。为何真理女神要抢在弗朗西斯科前面和圣奥古斯丁讲话呢?难道真理女神阻碍了弗朗西斯科的言说?这显然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首先,她是来帮助他的;而且,全书后面整整三卷都是他和圣奥古斯丁的交谈,为何偏偏在开篇的序曲中她要进行“阻碍”?显然真理女神并不是在阻碍,而是在为他们俩后面的长谈做准备。我们可以假设非常有趣的一点:即便弗朗西斯科率先和圣奥古斯丁说话了,圣奥古斯丁也是不会应答的,因为他本人正陷入自己的深思之中,就如同刚开始的弗朗西斯科一样。圣奥古斯丁由于沉思而一言不发,而他的沉默必须先由真理女神来打破;只有在沉默被打破以后,两人才能顺利地对话。
即便是圣奥古斯丁,他也是在真理女神的恳切请求下才答应和弗朗西斯科谈话:“我请求你,虽然没有什么比沉默的思考更令你愉悦,打破你的沉默,让我听见你神圣、愉悦的声音。”[tamessirerum omnium iocundissima sit taciturnameditatio,silentiumtamenistud,utsacra et michisingulariteraccepta voce discutias(break)oro]圣奥古斯丁在听到请求时甚至还带有推迟,他认为真理女神比自己的地位高,因此,更为适合对弗朗西斯科进行教导。在这番看似是谦虚的“推脱”中,圣奥古斯丁声明 “您是我的导向、我的指引、我的主导、我的主人”,在此却显得十分暧昧:在此他明显引用了《神曲》中朝圣者对维吉尔的台词,而我们知道维吉尔最后是无法带领但丁进入天国的——他的异教局限使得他无法洞悉上帝的意象,因此,维吉尔的角色背后带着某种“否定”的色彩——他所代表的并非是最权威的;圣奥古斯丁此时暧昧地将这句话运用到真理女神身上,似乎也在表明了他对真理女神某种“否定”的意味,那是因为圣奥古斯丁本身代表着某种“沉默”的力量。而且,在全书看来,圣奥古斯丁对于真理女神的引用甚少,他仅仅在第一卷中两次提到她而已,两次的提及都和彼得拉克自身的言辞相关。相反,弗朗西斯科对于真理女神的呼唤则贯穿《秘密》全书:他在第一、二、三卷分别都呼唤真理女神,让她为自己作证。这种呼唤暗示着某种“共谋”,即某种需要真理女神来为自我证言的态度。同样地,弗朗西斯科也暗暗对圣奥古斯丁进行了相似的否定:在刚看到圣奥古斯丁的瞬间,在圣奥古斯丁还未开口的瞬间,弗朗西斯科就说他有着高贵的罗马口音(romanafacundiagloriosissimi);此处细节和《地狱篇》的开篇场景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相似:朝圣者刚遇到维吉尔的幽灵时也听到维吉尔开口说话前就说“他的声音由于长时间沉默而变得嘶哑”。(《地狱篇》1:62-63)相似的相遇,相似的在未听见声音前便仿佛听见言说的声音,圣奥古斯丁的出场隐隐约约地影射了维吉尔。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文本的源头,但丁的《神曲》可能比《哲学的慰藉》更为靠近彼得拉克的意图,从隐蔽的维吉尔形象我们看到了一个连环的、隐秘的否定:圣奥古斯丁对真理女神的否定;弗朗西斯科对圣奥古斯丁的否定。这里隐藏的正是沉默和言说两股力量的对抗。这个疑问将带我们走进下一个问题:真理女神身份的寓意。
二、言说和沉默:两种力量的对抗
在这部分笔者将论述:真理女神的真实身份是彼得拉克的言说化身,正是言说给他带来了最高荣誉,因此,圣奥古斯丁代表的沉默/沉思才对真理女神做出如此隐晦的否定。这两股力量也可总结为:行动/沉思;入世/出世。
首先,真理女神不同于波埃修斯意义上的“哲学”,亦并非但丁所指的“信仰”。为何波埃修斯不需要他的女神打破沉默呢?因为他从来就未打算沉默,他开篇的第一句话便是:“在我独自沉思这些事情,并且决定把我的苦衷书写出来的时候……”①[古罗马]波埃修斯(Boethius):《哲学的慰藉》,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本文所引用的《哲学的慰藉》均出自该版本。(《哲学的慰藉》第一卷,I)这意味着至少波埃修斯并非完全沉默,他打算将自己的所想写出来,用文字的方式来对自我进行言说。反观弗朗西斯科却一直在冥思,并陷入了一种患病似的苦恼之中。沉思并没有治疗好他的顽疾,反而令他越发的消沉,就在这个危机瞬间,真理女神——言说的力量出现了;这股力量将弗朗西斯科从自我的沉溺、静默的冥想中拉出来,重新激活了他言说的能力。
其次,真理女神所代表的是一种世俗的、尘世意义上的言说;这种言说既不同于斯多亚内敛、避世式的内心独白,也不同于基督教充满暗喻、预象的修辞,而是一种潜入到这混乱的世界、这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以构建自我、为自我赢得荣耀的言说。对于彼得拉克而言,“言说”是一个具有实质力量的行动。她的自我介绍向我们暗示了她本身就是言说的力量,彼得拉克自己的文本就是最好的答案:《秘密》中真理女神的自我介绍——她将自己的出场归结到彼得拉克的诗歌《阿非利加》,这可是波埃修斯或但丁对各自的女神都没有敢做的事情。①[美]约翰·弗里切罗(John Freccero):《但丁:皈依的诗学》(Dante:The Poetics of Conversion),朱振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卡塞拉之歌》(Song of Casella),第228页。通过文本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但丁曾在《神曲》中也引用过自己的诗句:在《炼狱篇》第2歌中,卡塞拉为了让新来的灵魂开心,便唱起了《飨宴篇》的第二歌《爱神在我心中和我谈论》,最后却受到了加图的训斥,这和波埃修斯刚一登场就训斥世俗诗歌的缪斯的哲学女神是如出一辙的。因此,弗里切罗认为:在《神曲》整个皈依性的语境框架下,“回顾先前的诗歌成就所象征的,更可能是超越而不是回归,是自我批判而不是自我满足”。真理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我就是那位,你用考究的技艺在我们关注的(nostra curiosa)《阿非利加》中描写的她;我就是那位,你,如同底比斯的安菲翁(Amphion)那样,用诗艺为她在遥远西边的阿特拉斯山建造了驰名而壮美的宫殿的那位,(如此建筑)显然是出自一位诗人之手。
她不仅引用彼得拉克自己的诗作介绍自己,而且还将《阿非利加》称为“我们”(nostra)的诗歌,这就表明了她不仅是言说,更是属于彼得拉克的言说。“我们”一词将真理女神和弗朗西斯科两者放在同一阵线上——甚至可以说她就是他的言辞的一个分身。彼得拉克一开场就引用了自己的诗歌的行为恰好代表了他对自我言辞的肯定。更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阿非利加》是圣奥古斯丁严厉批评的、困扰弗朗西斯科的沉重锁链之一——荣耀的象征,他甚至劝弗朗西斯科放弃《阿非利加》的写作,以专心地思考自我/死亡:“放弃你正书写的历史吧:罗马人的荣耀已经够多了。把《阿非利加》留给它的子民吧,因为你既不能提升西庇阿的或者你自身的荣耀:他的荣耀不能更大了,而你只能在后面悲惨地跟着。”(《秘密》第三卷)在圣奥古斯丁眼中,《阿非利加》就是困住弗朗西斯科、阻碍他最终皈依的枷锁;但彼得拉克却别有用心地将对于圣奥古斯丁而言是“主人、导师”的真理女神放在《阿非利加》的文本环境中出场,这是怎样一种隐晦的、对沉默的对抗。沉默和言说两种力量在相互对抗着,圣奥古斯丁让弗朗西斯科放弃对劳拉的爱,放弃《阿非利加》的书写,实际上就是让他放弃诗歌的言说而重新陷入沉默,放弃世间的荣耀而归于沉寂;而正是由于《阿非利加》,彼得拉克于1341年在罗马卡皮托利山上被罗马元老院加冕了桂冠(Laureo)。既然真理女神是彼得拉克自我言说的分身,是他世俗诗歌的象征,这也就很顺利地解释了为何在后面的三卷中她再也没有说话的原因:因为已经获得言说能力的弗朗西斯科已经可以取代真理女神的位置,进行自我的言说了。戏剧中不需要两名同质的角色。
以《阿非利加》为代表的彼得拉克的言说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创作,它同时更是生活道路的选择:追求宗教式或者哲学(斯多亚)式的出世,还是追求尘世的荣耀?是投身隐居的僧侣生活,还是留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继续生存?真理女神的身份在得到阐明后,我们现在可以转向第三个问题了:圣奥古斯丁为何在开篇总要保持沉默?沉默在宗教上或者哲学上,或者对于人文主义的修辞学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三、圣奥古斯丁的沉默:基督教和斯多亚的结合
彼得拉克是在视力得到提升后才能看到圣奥古斯丁的;但是他之前没有发现圣奥古斯丁在场,一部分原因是自身智识上储备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圣奥古斯丁从未主动说过任何一句话。从真理女神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把沉默的冥想看作比一切别的事物更为重要;由于沉默,他并不愿意进行对话,并不愿意从自我内化式的沉思中走出来。这里的沉默不仅仅是没有言说,更标志着缺乏外界行动。对于彼得拉克而言,各种言辞的方式:包括自我言说、对话、书写都是一种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的行动;在《论隐逸生活》中彼得拉克就表明,虽然隐逸的生活对于哲学家来说是最可贵的,但是:
没有什么行动“尽可能地拯救和帮助更多的人更幸福,更值得。一个人假如做出这个行动我并不认为他就背离了人的高贵义务,也没有失去他人类的本质和人文主义的头衔”。①[意]彼得拉克:《论隐逸生活》(The Life of Solitude by Francis Petrarch:De Vita Solitaria,trans.by Jacob Zeitli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24,p.322.)
对于彼得拉克而言,凭借修辞的力量,言说和书写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文本或者作者,而是可以延伸到实质性的世界中;而沉默则意味着某种不作为、不行动,既包括了基督教式真理的沉默,也包括了斯多亚式的避世。斯多亚认为推崇对美德的渴望就是行善,然而它过于注重内心的指向使得它忽略了外在的对现实生活可以产生实际影响的行动;彼得拉克追求修辞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他希望利用修辞术将冥想中静默的道德和智慧表达出来。
言说在本质上是一种修辞②这里的修辞、言说不仅仅是指说话的技术,它同时也包括书写的技术。下文将写到圣奥古斯丁批评弗朗西斯科在舌头和笔头间琢磨修辞,是浪费光阴。因此,和沉默相对的言说的力量包括说话和书写。。克里斯泰勒(P.O.Kristeller)的研究奠定了修辞学在整个文艺复兴思潮中的地位,人文主义者对于修辞的态度反映在他们对待学院派、基督教和异教思想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上,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的冲突、冲撞在彼得拉克身上得到了非常清晰的体现。纵观彼得拉克的《秘密》《论隐逸生活》《论人的无知》和《回忆信笺集》等几部作品,可以看到他本人对于言说,更准确而言是修辞,也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他认识到言说——修辞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在人类身上发生作用,乃是因为它能激发人的激情(passion),能打动人的“心”——圣奥古斯丁认为灵魂所在的地方——从而激起人们对美德的追求。他甚至将言说的力量看得比道德的例子更能够触动人心:
修辞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的生活,我们可以从阅读众多作品,从每日的生活中得到答案。我们看到多少同时代的人们,对于他们连美德的例子都毫无帮助,但他们却仅仅由于某人的言说,便突然从一个极其邪恶的生活方式转变到一个完美有序的(生活方式)。③笔者译自彼得拉克的 Familiarium rerum libri,traduzione e cura di Ugo Dotti,collabrazione di Felicita Audisio,Torino:Nino ArganoEditore,LibroI,9,6和英文版Letters on Familiar Matters,trans.Aldo S.Bernardo,3vols,New York:Italica Press,2014.
假如说圣奥古斯丁认为修辞是低于真正的智慧(虽然彼得拉克也没有否认这点),那么彼得拉克则认为好的修辞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表达真正的智慧的。一名好的道德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可以运用修辞技巧阐释道德的演说家。修辞是一种工具,既可以被用在好的地方,也可以被用在坏的地方。对于圣奥古斯丁而言,好坏之分的界限在于其最终是否导向信仰、是否理解上帝的启示。人类的各种言辞技术是为解开圣经种种的喻象而服务。但对于彼得拉克而言,言说力量的“好”在于它可以为道德哲学服务,在大众中传播美德,激起人们追求美德的欲望。言说可以用动人的声调、生动的比喻、切身的个人体会使得大众明白美德的重要性,这一点也是彼得拉克认为无论是诗人还是修辞家都应该做的事情。彼得拉克推崇的两位修辞家——加图和西塞罗都认为真正的修辞是不能脱离美德和智慧的:加图认为修辞家就是“一位有说话技巧的善人”,而西塞罗则认为修辞本身就是既有智慧也注重辞藻地说话。①[意]彼得拉克:《两种命运的补救方法》[On Two Faces of Fortunes:De remediisutriusquefortune,I,ix;Rotterdam:1964,pp.31-32,引自 Errold E.Seigel,“Ideals of Eloquence and Silence in Petrarch,”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65,26(2),p.158.]彼得拉克说:“因此,如果你在追求演说家的头衔或者修辞的真正荣誉,你首先应该注意美德和智慧。”②[意]彼得拉克:《两种命运的补救方法》[On Two Faces of Fortunes:De remediisutriusquefortune,I,ix;Rotterdam:1964,pp.31-32,引自 Errold E.Seigel,“Ideals of Eloquence and Silence in Petrarch,”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965,26(2),p.158.]对于他而言,修辞是和高于它的哲学相行不悖的,它可以帮助哲学更好地得到阐释,为人所理解。圣奥古斯丁式的非此即彼即将修辞和智慧完全对立起来,但彼得拉克从贺拉斯和亚里士多德身上看到了词句的力量,他坚持认为假如修辞能够为真正的哲学家所掌握,那么就可以用来造福人类,因为,更多的人会因为被打动而去践行德性,彼得拉克努力地在哲学旁边为修辞留下了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彼得拉克也认为真正的哲学是高于修辞的,真理总是归于沉默,但修辞往往和大众、城市联系在一起:那些拥有高超修辞技巧的演说家不就被彼得拉克形容为是一群喜欢城市、喜好混迹大众、用花哨的演讲技巧来取悦大众以获得名誉的人。③彼得拉克:《论隐逸生活》,第540页。但在长达三卷的对话中,彼得拉克让他笔下的圣奥古斯丁多次对修辞进行了批评,无论是言说还是书写:
如果他的修辞技巧已然提供他足够的胆量以及堆满冗词赘语的仓库,那么此人的演说仪态将会显示出他并没有定义事物所需的。(veramsibi rei diffinitenotitiam)……为何你从不察觉真相而耗费生命在文字的世界?发鬓斑白,额生皱纹,你却仍消磨在童稚的胡言乱语之中。④此处引用的中译本来自彼得拉克:《秘密》,方匡国译,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48-49、50页。(《秘密》第一卷)
他继而又指出人类言辞的有限性和空洞的本质,认为彼得拉克在修辞上面浪费时间是幼稚而疯狂的,圣奥古斯丁认为无论是彼得拉克的雄辩术抑或是他的书写技艺,和真理、和认识自我——思考人类的有死相比,都是琐碎而毫无意义的追求。
告诉我,还有什么比只浪费时间于言语的学习、言说的欢愉,而漫不经心地怠惰于其他事物更幼稚、更疯狂的呢?在无知中,你可曾看见自己的行为应受谴责,就像那些小鸟,它们似乎从自己的歌唱中得到很多乐趣,以至歌唱至死。……我常听到你抱怨,看到你因为言词而陷入沉思,为了你的唇舌笔墨(ec lingua neccalamus;neither your tongue nor your pen)无法精确表达那些对你来说亲切易懂的事物而感到恼火。那么,既不能涵盖所有的事实,又不能控制已然包含的,如此悠闲而虚弱的雄辩到底是什么?⑤此处引用的中译本来自彼得拉克:《秘密》,方匡国译,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48-49、50页。(《秘密》第二卷)
人类是无法依靠修辞来得到不朽、到达永恒的,因此,圣奥古斯丁警告弗朗西斯科说:“你这弱小的一分子,必须明白在多大程度上你可以依赖自身的语言力量。你该为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去追求一些无法得到的东西而感到羞耻。”⑥此处引用的中译本来自彼得拉克:《秘密》,方匡国译,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48-49、50页。
践行修辞术的演说家也是彼得拉克在《论隐逸生活》中讽刺的对象:“他们就是那些在城市游荡,对着大众长篇大论地谈论美德和罪恶的人。”⑦彼得拉克:《论隐逸生活》,第324页。讨论美德和真理应该留给真正的演说家和哲学家,而不是这些诡辩家,彼得拉克如是说;因此他否定的其实并不是修辞术,而是那些利用修辞术在大众面前尽说些辞藻华丽、实质却空洞无物、却冠上谈论美德名义的诡辩家。正因为如此,彼得拉克更加坚持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掌握修辞术,这样,他们就可以向大众阐述真正的智慧和知识,因此说:“治疗、打动灵魂的工作应该留给真正的哲学家和演说家。”⑧彼得拉克:《老年书信集》,(Letters of Old Age:Rerum seniliumlibri,trans.Aldo S.Bernardo,Saul Levin,and Reta A.Bernardo,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II,p.861.)(care for souls and move them should be left to true philosophers and orators)在彼得拉克眼中,诡辩家总是和喧嚣的城市、粗俗的大众相联系,他们是厌恶沉默的:
演说家们(orators)有一种尤其古怪的性格,那便是他们喜欢大城市,喜欢在大众面前,这倒和他们的才能相符。他们诅咒隐逸,讨厌并反对沉默(silentiumiudiciorum)——内心做出决定的状态。①彼得拉克:《论隐逸生活》,第534、424-426页。(《论隐逸生活》,534)
而真正的哲学家,归根到底应该逃离城市,远离大众,在隐居秘密的地方进行思考。②彼得拉克:《论隐逸生活》,第534、424-426页。弗朗西斯科对城市就充满厌恶和绝望:
谁能描绘那地上最令人失望不安的城市,它狭窄阴暗的土槽汇集了世间所有的污秽?什么样的刷子能够去除那令人作呕的景象:街道满是病患、肮脏的猪和咆哮的狗,车轮噪音辗磨着墙壁,四轮马车于十字路口呼啸而过,大群乞丐疯狂冲上围着夫人……这一切毁了任何人所习惯的对通向生命美好道路的感知能力,带走了头脑的平静,并打断了文艺的学习。③彼得拉克:《秘密》,方匡国译,第82、83页。(《秘密》第二卷)
圣奥古斯丁也非常赞成他的观点,他引用了贺拉斯和彼得拉克自己的作品加以回应:“‘所有的作家都热爱山林而逃离城市。’你本人也在一封信里用不同的话语表达相同的意思:‘森林为缪斯女神所钟爱;城市与诗人、作家为敌。’”(《秘密》第二卷)④彼得拉克:《秘密》,方匡国译,第82、83页。
四、沉默和追求的荣耀
赛伊格尔(Jerrold E.Seigel)认为,虽然沉默在彼得拉克的作品中有多种含义,但它往往和对修辞的怀疑联系起来。⑤赛伊格尔(Jerrold E.Seigel),“Ideals of Eloquence and Silence in Petrarch,”p.158.对于修辞的怀疑亦即对于和修辞联系的大众、尘世的怀疑,这点在《熟人书信集》中的《登旺度山》一文体现得尤其明显:此处的沉默和《秘密》的沉默共同阐释了彼得拉克的犹豫不决和反复。我们发现,圣奥古斯丁在开场奇异的沉默代表的是一种拒绝的态度;到达旺度山峰的彼得拉克同样表现出相似的沉默。德林(Robert M.Durling)曾将彼得拉克在山峰的皈依过程和圣奥古斯丁在花园的皈依过程相比较,⑥德林(Robert M.Durling),“The Ascent of Mt.Ventoux and the Crisis of Allegory,”Italian Quarterly,1974,18(69),pp.19-22.其中和圣奥古斯丁皈依最为分裂的一点正是彼得拉克的沉默:他没有朗读出来⑦无声阅读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Mazzeo教授却告诉我们,直到罗马帝国晚期,才有无声阅读,而且不出声地阅读即便在整个中世纪也是一件不常见的事情。有大量的史料表明中世纪的抄经院是一个嘈杂的地方:抄经员一边大声朗读一边抄写。Mazzeo指出这也是为何在《忏悔录》中当圣奥古斯丁看到圣安布罗西乌斯(St.Ambrose)在静默地阅读时才如此的惊奇(《忏悔录》第六卷)。因此,Mazzeo的结论是:沉默是一种倾听自我内心声音、对内在自我的专注。详见“St.Augustine’s Rhetoric of Silence”的第190-191页。,甚至拒绝了和格拉多的对话,没有让格拉多聆听自己的预言。彼得拉克描写自己在阅读以后,“直到我们下到山脚,再也没有人在我这里听到一句话。”“我沉默地思考着人类是多么的愚蠢,居然忽略了他们最为高贵的部分而将自己虚度在许多琐事之中……”⑧“Ascent of Mount Ventoux”(登旺度山),from Davy A.Carozza,and H.James Shey,Petrarch’s Secretum,With Introduction,Notes and Critical Anthology,Bern:Peter Lang,1989.彼得拉克不仅自己陷入了沉默,也让他的兄弟格拉多陷入了沉默:实际上,在另一篇研究中,康士塔布(Gile Constable)认为,在整个下山过程彼得拉克再也没有提到格拉多,仿佛他被永远地留在山峰似的。⑨Mazzeo,J.A.,“St.Augustine’s Rhetoric of Silence,”Journal of the History Ideas,1962,23(2):175-196,p.23.格拉多在书信的后半部分完全被“沉默”,仿佛他不再存在一样——他既听不到彼得拉克任何一句话,读者也再没有听到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沉默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在场,正如弗朗西斯科在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发现圣奥古斯丁的存在一样。两人的沉默拒绝了彼此的交流,乃是因为他们各自选择的道路就是对立的:尘世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对立。
在登旺度山的过程中,彼得拉克屡屡描写自己和兄弟格拉多截然不同的行走选择:格拉多选择一条更为险峻、艰难的道路而彼得拉克自己选择的是一条平缓但异常漫长(甚至有走错路的危险)的道路,这显然和格拉多在1343年成为僧侣有非常大的关系。彼得拉克频频表明他对僧侣生活的出世和平信徒生活的入世,或者说尘世和宗教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在两者间的徘徊和挣扎,这同样也是《秘密》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两种道路的选择在这里具象化为对永恒/信仰的追求和对尘世/荣耀的追求间的摇摆不定。彼得拉克在《论隐逸生活》中不止一次提到教士生活的崇高性,他自己十分赞赏这种生活方式,但却迟迟不愿意自己去履行。他的三心二意和摇摆不定在弗朗西斯科身上也可以看到,在面对圣奥古斯丁的责备时,他争辩到:“我不愿称它为‘放弃’,‘推迟’更确切。”①彼得拉克:《秘密》,方匡国译,第140、142、152页。(《秘密》第三卷)。彼得拉克对宗教生活的推迟其最为核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无法放弃尘世的荣誉。上文也提及过,圣奥古斯丁所职责弗朗西斯科的两个方面:对劳拉的爱和进行《阿非利加》的写作,这归根到底还是彼得拉克对荣誉的难以割舍。弗朗西斯科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
我很确信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他必须追求此生足以期待的、合理的荣耀,……因此,我认为正常的顺序是,凡人应该首先考虑俗事,然后才是永恒之物;因为最合逻辑的顺序是从短暂到永恒,而非从永恒到短暂,后者是不可能的。②彼得拉克:《秘密》,方匡国译,第140、142、152页。(《秘密》第三卷)
但甚至就在我们谈话时,许多重要的事情,尽管凡俗,但还是需要我去关注。③彼得拉克:《秘密》,方匡国译,第140、142、152页。(《秘密》第三卷)
但如同他调和修辞与哲学一样,彼得拉克本人也尽力地想要调和这两种生活方式:真正的哲学家应当关心人类,在人群中利用修辞在人们心中激起对美德的渴望,而不是像中世纪苦行僧般远离人群,隔绝世界。特林考斯曾在他一篇研究人文主义者宗教态度的文章里面提出,彼得拉克试图想要论证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差异不是本质上的而是程度(degree)上的:
如果追随信仰和神职人员间的差异变得没那么明显,这不是意味着只有专业的神职人员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和信徒;就是意味着平信徒也可以成为教徒只不过他们更容易受到外界危险和干扰(的威胁)。……那些曾赋予中世纪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特权和特殊地位、优势被淡化了,平信徒和神职人员之间的差别成了程度上的差别,而且这个程度在缩小。④Charles Trinkaus,“Humanist Treatises on the Status of the Religious:Petrarch,Salutati,Valla,”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1964,(11),pp.7-45.
特林考斯认为彼得拉克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宗教信仰逐渐地转向个人化、内心化,并试图缩小平信徒和神职人员间的差距;其原因在于他无法放弃对尘世荣耀的追逐,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留在大众中间讲述他的道德哲学(他唯一欣然接受赋予自己的头衔);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希望继续写作,桂冠诗人正是他的目标,而他创造的哀伤的情人形象也是他获得名声的途径之一。和沉默退回自我,甚至对世界无动于衷的“洁身自好”的做法相比,彼得拉克更希望回到属于人类的俗世之中。
圣奥古斯丁在一开始就犯错了。他一开口就让弗朗西斯科记住“你终将一死”;但在《秘密》的第一句话就已经点明了:弗朗西斯科由于思考人是“如何来到和离开世界的”而无法入眠——这就说明不同于圣奥古斯丁的责备和训斥,弗朗西斯科已经对人的有朽性进行了足够多、足够深入的思考。而正是这样的思考使得他最终没有接受圣奥古斯丁的关于放弃“爱与荣誉”的建议——他一直被悬置在两条道路中间,他不断地在推迟自己皈依的时刻;那是由于弗朗西斯科发现唯有以自己作品的不朽——荣誉的不朽才能对抗人类肉身的有朽;由此,彼得拉克在开场时候才短暂而隐晦地说他的这本小书不是为了名声或者大众的肯定,“我脑海中有更为宏大的东西”(maioraquedammensagitat)。“更为宏大”指的既不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来自于善变群众的肯定,也不是稍纵即逝的名声,而是一种不朽的、流传千古的荣耀!彼得拉克作为一名诗人,他获得“不朽”的手段就是他的诗艺,于是他让真理女神在出场的时候就说道:“你,如同底比斯的安菲翁(Amphion)那样,用诗艺为她在遥远西边的阿特拉斯山建造了驰名而壮美的宫殿……”,诗艺/诗歌言辞的力量被比喻为安菲翁的音乐魔力——他用自己的技艺建起了底比斯的城墙。城墙作为中世纪城市的象征,代表着稳固、安定和无坚不摧;但是代表沉默的圣奥古斯丁则质问他:“当你看到古老的城墙便也问问自己,那些亲手修建它们的人哪儿去了;当你看到新的墙壁也问问自己,’它们的建造者将去何方’。”①彼得拉克:《秘密》,方匡国译,第149页。通过告诉弗朗西斯科即便最为古老的城墙,其建造者——作者也将会消失在历史中最终无人知晓,他坚决地否定了弗朗西斯科想要通过自身言说来获得不朽的欲望。为了更加击中弗朗西斯科,他甚至引用了《阿非利加》的诗句:“你的书死了,你也会消逝;/第三次死亡在等着你。”(《秘密》第三卷)虽然如此,弗朗西斯科依然不愿意放弃对荣耀的追求,因为他发现除了以此来对抗腐朽和流变以外别无他法,圣奥古斯丁越是强调人类的有朽,就越是加强了弗朗西斯科追求不朽荣耀的决心——就是圣奥古斯丁最终无法完全说服弗朗西斯科的真正原因,一开始他的言说出发点就定错了。
五、结 论
通过对《秘密》开篇场景的讨论,笔者认为彼得拉克的真理女神实际上就是诗人自己的言说力量的化身,这股力量可以打破人的沉默,使得他们进行对话;这股力量同样可以化作行动的、对外部世界产生实质的影响。彼得拉克如此强调言说的力量,乃是因为他试图利用言说的力量——他的诗艺去创造仅属于自己的作品;去创造不朽的荣耀。虽然彼得拉克对于荣誉的追求使得他更倾向于异教思想,但实际上他所有的行动还是一个晚期中世纪式的人。那是因为彼得拉克的追求荣誉并不是想和他的希腊前辈们一样,试图跨越人和神的界限;在内心深处他是十分清楚并认同人的有限性和神的无限性的区别。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众多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迁,尤其是基督宗教体系的松弛和疲软给曾经坚实的基督教思想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一旦思想基石开始变动,人们总需要寻觅另一种“永恒”(亦即“不朽”)来填补心中的空缺,只不过彼得拉克选择回归到自身之中去寻觅而已。因此,当他发现原来的宗教真理难以解释他所遭遇的一切后,变化所带来的焦虑驱使他,除了宗教的永恒之外,再去寻找另一种永恒,那便是诗人长青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