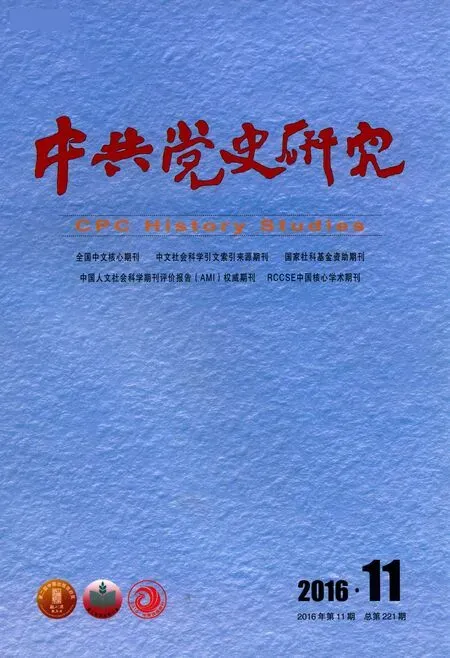国民革命语境中的中共政权口号及其阶级意蕴
——兼与《从“平民主义”到“革命民众政权”》一文商榷
2016-02-11于化民
于 化 民
·探索与争鸣·
国民革命语境中的中共政权口号及其阶级意蕴
——兼与《从“平民主义”到“革命民众政权”》一文商榷
于 化 民
中共政权主张在大革命进程中几经变更,其实质是对国民革命中阶级关系和未来政权性质及阶级构成判断的变化。“平民政权”口号并未将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阵营和未来革命政权之外。“革命民众政权”与前者在阶级规定性上亦无原则上的不同,也称不上党内不同政权思想的整合。真正摒除资产阶级于未来政权构成的标志,是中共五大“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口号的提出。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妥协和国民党新右派的形成,是引起中共政权主张变化的主要政治因素,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则是导致变化的直接原因。
国民革命;平民政权;革命民众政权
大革命时期中共政权口号的变化,实际上折射出党内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特别是阶级关系的不同认识。也可以说,客观如实地分析考辨中共政权口号的内涵,可为准确理解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路与内在逻辑提供一把钥匙。拙文《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平民政权”思想的演进轨迹》(《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对中共在国民革命中提出的“平民政权”口号作了初步的梳理考察,认为这一多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主张,不仅是对中共二大所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延展和深化,还成为中共从简单照搬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向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国家政权理论的重要标志。新近读到周家彬《从“平民主义”到“革命民众政权”——大革命初期中共党内政权思想的分歧与整合》(《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以下简称周文)一文,亦是通过分析陈独秀与瞿秋白政权思想的异同,提出党内存在“国民本位”和“平民本位”两种革命逻辑,最后在“革命民众政权”名义下整合了分歧。周文对拙文某些观点有所质疑,读后多有启发,细思之后仍有难以苟同之处,归纳为以下三个问题略作申说,以期引起学理上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平民”与“平民政权”中是否包含资产阶级?
周文主要质疑拙文的,是认为瞿秋白提出的“平民政权”为四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联合执政,并把瞿秋白的“平民政权”等同于中共三大提倡的“平民的民权”。既然要讨论“平民政权”的问题,就有必要回归历史语境,简要追溯一下“平民”概念的缘起与流变。
在中国传统政治语汇中,“平民”被用来泛指与世族官宦相对应的黎民百姓。在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则是指除贵族骑士以外的社会下层,主体是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以后,作为一个与“民主”密切关联的近代政治术语,“平民”概念才真正在中国流行开来。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是较早较多使用“平民”概念并提出“平民政治”口号的人。他在五四运动前发表的《平民独裁政治》一文便提出:“平民政治的真精神,就是要泯除一切阶级,都使他们都化为平民。”*《平民独裁政治》,《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此后,又陆续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文章中阐发自己的观点。李大钊指出,“平民主义”源自“Democrocy”一词,原意是指“人民的统治”。平常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它是为中产阶级装潢门面,而特权政治却在内幕中施行。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将发展为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即“工人政治”。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真实的纯正的平民政治,而“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平民主义》,《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由此看来,李大钊所说的平民政治就是民主政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涵义自不相同,而“真实的纯正的‘平民政治’”是阶级差别完全消灭之后才会有的一种理想政治。
继李大钊之后,瞿秋白是中共领导人中较多谈论“平民”问题的。刚刚回到国内的他,在1923年1月17日为《晨报》所写的杂感中说:“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最低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3页。。他还指出,帝国主义出于吞灭中国的野心,与军阀官僚等封建势力相勾结,“决不愿有平民的民权运动建成真正的独立国家”,而中国的平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消灭封建制度,才能间接地给帝国主义以打击,建立“平民的统一国家,平民的地方自治政体”。他把这种新的国家政权称之为“平民的政权”“平民的共和国”。*《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33—34、81页。由此可以看出,在瞿秋白所说“平民的民权”与“平民的政权”“平民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平民通过争取民权的斗争去创建平民政权和平民国家;另一方面,平民政权和平民国家为实现平民民权提供政治和法律上的保障。
要准确地理解这一问题,还应当特别注意瞿秋白与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和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的关系。中共三大的主要贡献是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党的工作中心此后转向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张太雷、瞿秋白三人负责中共三大的文件起草和会议筹备工作,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就是由瞿秋白起草的,其中明确提出“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党纲草案既指出资产阶级“苟且偷安”,极易向列强和军阀妥协,同时又强调,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阀压迫之下,“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劳动平民便一天一天失掉了他们生活的保证”,“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根本上不能不冲突;而劳动平民及无产阶级的解放,尤其与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根本上不相容:国民革命之进行,是必不可免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39、136、140页。。这个草案虽然经过陈独秀修改,但出自瞿秋白笔下的“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一句话得以保留。可以说,它反映了瞿秋白本人对政权问题的思考和认识。1923年8月,共产国际派鲍罗廷来华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瞿秋白成为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并且参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他在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三民主义时提出:“国民党的民主主义来源于其他一切先进国家民主运动的经验,同时作了相应的修改。因此,除了所谓直接的人民权利之外,我们还实行直接的人民民主。就是说,全体公民不仅有选举权,而且有倡议、否决和召回国家官员的权利。”*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9页。他的提议亦为正式文本所采纳。
在此前后,瞿秋白接连发表文章为新三民主义造势。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平民”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比如,他把国民党称作“平民的政党”*《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88页。、“代表大多数平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国民党与下等社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92页。,把新三民主义称作“现实的革命原则”,“是平民意志的结晶,是平民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农民、工人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意志之表示”,它“代表全中国平民的利益”,是“平民组织团结力量以达到革命的旗帜”*《中国革命史之新篇》,《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84页。,把未来的革命政权称作“真正的平民共和国”*《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88页。。他还最先把新三民主义与平民政权联系起来,主张民权主义就是要建立“中国平民群众的政权,使政府真能代表全民族”,“国民党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代表全中国平民的利益的,所以能组织平民,集中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作战,这是国民党应有的责任,也是平民应有的责任”*《中国革命史之新篇》,《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84页。。为此,他号召“商人、农民、工人、学生、教育界”都来参加作为“平民的政党”的国民党,“凡是平民都应当为我们的将来——真正独立自由的中国而奋斗”*《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88页。。
在瞿秋白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中,“平民”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内涵也不固定。除了“平民”,瞿秋白还经常使用“劳动平民”一词用以代指工人阶级*《帝国主义的佣仆与中国平民》,《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18页。,有时又把“劳动平民”与无产阶级并提*《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17页。。在大多数情况下,“平民”被他用来泛指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下等社会”,亦称“下等阶级”,以对应于“上等社会”和“治者阶级”“智识阶级”“上等阶级”。在他看来,“各国的革命都是下等阶级(平民)反抗上等阶级的行动,所以革命党必定是代表下等阶级利益的政党”,“国民党始终是下等阶级的政党,是革命的政党,是代表大多数平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国民党与下等社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90、392页。。如此反复地强调国民党的“平民”特色,强调建立“平民政权”,其用意不外乎配合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拉近中共政权主张与新三民主义的距离,以适应国共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现实需要。无论是“平民的政权”还是“平民共和国”,都与中共三大党纲草案中的“平民的民权”是相通的,并非如周文所认为的那样,是两个“完全不同”、互不相干的东西。
政权口号的背后是对阶级关系的分析与认定。“平民政权”是否包含资产阶级,仅仅字面上的解析是不够的,还要看瞿秋白是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的。在写于1923年6月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中,瞿秋白对近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现状与特征,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与国民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导源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这些对抗力之中,劳动阶级固然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特性而尚弱,现时只有民族主义的觉悟;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外国资本的侵略却正在日益加紧,自然而然促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的民族运动,得最宜于组织最易有团结的无产阶级之猛进,当能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向民族革命;以至于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而促成伟大的长期的世界社会革命,彻底颠覆帝国主义”*《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08、90页。。在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讨论中,他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种,指出尽管现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将会革命。不要害怕资产阶级的壮大,因为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在壮大,我们不能采取与他们分离的办法阻止他们的发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68页。。现在看来,这种区分方法过于简单化了。所谓大资产阶级主要是指依靠帝国主义的买办势力,这部分人本来就是革命的对象。在他们与以小商人、小作坊主、自由职业者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之间,还有着一个主要由工商企业主组成的中等资产阶级。对后一部分人,还是要联合他们一起从事国民革命。
三个月后,瞿秋白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国民革命观。文章主旨在于肯定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说到了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瞿秋白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能生出社会主义来,只有它能造成社会主义公有生产资料的技术基础,能造出数量多而觉悟深的革命无产阶级。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成就的地方,“资产阶级还能做革命的进取”的地方,无产阶级应当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君主诸侯及军阀”,同时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民权革命的社会及经济的内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然而并不因此而对于无产阶级没有很大的利益。民权革命不但不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扩充、推广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民权革命不但代表劳工平民的利益,而且代表全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下,资产阶级之统治工人阶级是不可免的。因此可以说,民权革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多,而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少。然而,说民权革命绝对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那却是蠢话。*《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94—195、201页。此文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2期,原题为《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改为现标题。后来他还更加清楚地说过,平民中“包含了利益相反的种种阶级”*《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84页。,分明就是指处在剥削者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处在被剥削者地位的工人阶级。
那么,民权革命对无产阶级的利益体现在哪里?瞿秋白认为,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使无产阶级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经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进步。在封建军阀之下没有别的方法行向社会主义,只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民权主义的共和国。“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民权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种子才能开始萌动”,“在民权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中,无产阶级方才有活动之自由及广泛的政治运动之可能,——这是无产阶级的成熟及经验之必要的前提”,“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在原则上,在实际应用上,在国内政治经济上,都是绝无疑义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民权革命中愈有组织系统,愈集中,愈彻底,就能愈多地保证他们的利益。他还说,无产阶级与其他平民在民权政权和共和主义方面是有统一意志的。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小商人实行坚决的民权革命,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应把“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作为民权革命的最近目标。无产阶级的最后目标是社会主义,随着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日益取得重要地位以至于领导权,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95、222、207—209、221页。
由此可见,在反帝反军阀的国共联合战线酝酿和建立初期,瞿秋白是最早认识并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他较早地看到中国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军阀面前有着“畏怯妥协”的天性。但是,至少在这一阶段,他并未因此否定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并未否定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组成部分。断言他此时已将资产阶级排除在“平民”和“平民政权”之外,既缺少充分的文献依据,也明显有悖于中共三大确定的联合战线政策,逻辑上是很难说得通的。
二、“五卅”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认识的重大变化
如果说,中共领导人对于国民革命是反帝反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认识达到高度一致,那么最令他们感到困惑和纠结的,还是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看法存在明显分歧。就其基本倾向而言,仍以正面肯定居多,以强调团结和联合为主。这种情形在孙中山逝世到五卅运动期间发生了明显变化。
从性质上看,平民政权是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多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这是没有疑问的。中共期冀通过国民会议的召集来实现这样一种新式政权,认为旧的国会制“或者对于资产阶级可以将就,而对于劳动平民绝对不能相容”,可以通过国民会议创造“代表真正大多数劳动平民的制度”,进而创造出“真正的民主政治”*《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58、60页。。中共设想的国民会议不是单纯的议事机构,而是一种政权的组织形式,通过国民会议产生的政府是一个由工农商学各阶层共派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在1923年8月、1924年9月、1924年11月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宣言和主张中,中共一再号召社会各界迅速召集国民会议。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决定接受冯玉祥邀请北上,并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两大主张。中共随即发起大规模的国民会议促进运动予以配合。国民党本来就是由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构成,成分庞杂。还在孙中山在世时,张继、谢持等国民党老右派即蓄意生衅,排挤中共。孙中山遽尔病逝,不但使方兴未艾的国民会议运动失去了一面旗帜,更让国共联合战线的内部危机凸显出来。以孙中山学生自居的戴季陶,接连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个小册子,公开质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维护“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名,向共产党人发起攻击。除来自戴季陶主义的理论挑战,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同样引起共产党人的警觉。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人民在中共的组织领导下,实行全市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起初对运动抱同情和支持态度的上海上层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镇压面前开始妥协和屈服,无条件地结束总罢市,还通过扣压各地捐款逼迫罢工工人复工。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让中共不得不重新审视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实际作用。
作为中共最活跃的理论家,瞿秋白积极投身于同国民党右派的论战,加大了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力度。他重申,在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基于共同的利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能够建立联合战线,“这种共同利益若仍旧存在,敌人的离间利诱是难于破裂这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则各阶级间的共同利益尚属存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自然能够维持下去”*《三论阶级斗争——甚么是阶级?》,《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页。。“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各阶级的,城市中的小商人(有时大商人也来参加)、工人、农民,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各阶级的人们都需要这样的革命”,当然,“革命的队伍里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他们是与买办阶级不同,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可是与工人、农民大不相同……他们恐怕工农的力量大了,他们将因此受害,不能尽其所欲地来剥削工农,因此他们对于革命终有些疑惧”。工人并不怕资本主义的强大,资产阶级却在怕工人势力的增高。所以,“在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参加,工人也参加,但是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必定不能使之落入资产阶级的手里”。*《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391、392页。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有很深的经济基础,如果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很快便会和敌人妥协,而客观上工农群众已经要求革命,积聚实力,准备决死的斗争,自然而然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来做国民革命的先锋和领导者。因此,这一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39、40页。
国民党右派认为阶级斗争学说不适用于国民革命,工人阶级的斗争会把资产阶级吓得走向反动,进而分裂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瞿秋白反驳道,国民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工人阶级承受着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的双重剥削,自然不能不开始斗争,这种斗争从一开始便是革命的阶级斗争。难道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忍受中国资本家的剥削,同时又能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中国资产阶级要利用工人的力量争民族的解放,便应当牺牲自己的目前利益: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当然也反抗中国资本家同样的压迫;中国资本家不能自动的减轻压迫,便只有受反抗。假使中国资本家因受反抗而竟反动,以至于勾结军阀、帝国主义,那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就尤其必要。他还指出,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代并未主张无产阶级独裁制。真正的民权主义,只有拥护保障真正平民的政权。共产党所主张的,正是在国民革命时代必须革命的,各革命党联合的,对于保皇党、帝国主义党、军阀党、买办党、土豪党,对于一切反动势力的独裁制——国民革命的革命派独裁制。*《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467、469、479—480页。瞿秋白认为,中山舰事件表明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内新右派的形成,提醒有出现新的军事专政的危险,“中国稚弱的资产阶级,现在既然还留在革命营垒之中,始终需要军力来代表他。新右派暂时和帝国主义妥协之可能较少;他在既得相当的领袖地位之后,为求巩固此地位起见,不得不向前进取几步——北伐。因此,北京屠杀后在全国范围内之革命联合战线之中,自然还包含着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竟还保持着部分的领导权。于是,北伐的革命战争,便可以说是代表这一联合战线反抗买办阶级统治的战争”。他有意识地使用“革命平民”一词,将其他革命阶级与资产阶级区别开来,“革命平民——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之参加、赞助革命战争,其倾向必然与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平民是要以实现国民会议为旗帜而战;革命平民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376、378页。在瞿秋白看来,资产阶级与其他革命阶级的政治分野日趋明显,其妥协性会给革命造成严重危害,他对可能出现国民党新军阀的警示更是有预见性的。
与瞿秋白看法类似的还有邓中夏和恽代英。邓中夏鲜明地主张,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不是附属于资产阶级,应当通过斗争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这不仅包括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生活待遇的改善,还包括政权的取得。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还是把以帝国主义和军阀为对象的国民革命和以资产阶级为对象的社会革命作了区隔:“资产阶级固然是我们的仇敌,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是我们目前最厉害的两个仇敌。我们必得参加国民革命先打倒这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得到初步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邓中夏全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8页。在国民革命阶段,基于“某一共同目标即共同利益”而“共同行动”的各阶级联合战线是必不可少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际帝国主义一面摧毁中国的手工业与农业,一面又阻止中国实业的发展,工农商学各阶级均受其困,各阶级因其民族境遇之相同,各阶级利益又不期然而然有趋于共同之一点,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必不因其阶级间部份特殊利益之故,而致限制与障碍此一联合战线之建立与成功”*《工农商学联合战线问题》,《邓中夏全集》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81页。。恽代英也提出,无产阶级要为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而斗争,“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恽代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无产阶级要联合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现在我们不问资产阶级是否一定要反动的,我们应该联合他们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以资产阶级只要在不压迫农工的时候,在国民革命的运动上总是友军。这一点,共产党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有人说共产党不要联络资产阶级来实行国民革命,然而过去的事实证明最努力联合资产阶级的,还是共产党”*《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恽代英全集》第7卷,第364页。,不过,“大商人,资本家,名流,学者,律师,教职员,一切在社会上所谓比较有地位或者自以为有地位的人,常常是反革命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恽代英全集》第7卷,第195页。。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根源进行了剖析,强调要对资产阶级开展有原则的斗争。毛泽东指出,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他们的目的是“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页。为此,他们对民族革命采取了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刘少奇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当无产阶级起来参加革命时,或要求生活改良时,资产阶级就马上反动起来了,“工人阶级在某一个时候,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强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页。。周恩来着重强调:“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在工农与资产阶级发生矛盾和斗争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方面,代表工农利益,“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其要求不能超过民主政治的范围。但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就连一向十分看重资产阶级的陈独秀,也对资产阶级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他坦承,“五卅运动起时,我们绝不死守成见,我们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国民党右派不承认阶级斗争,陈独秀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针锋相对地加以批驳:“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他列举历史事实证明,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阶级。工农群众的力量,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集中和发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504、505页。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一开始既带有反动的倾向”,“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当然,陈独秀还是没有把新右派和老右派(指西山会议派)等量齐观,他认定老右派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站在敌人那边了”,而对于新右派,仍“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550、552页。
与此同时,中共对于政权问题有了一个新说法,即受到周文格外重视的“平民的革命政权”。这个提法最先出现在陈独秀1925年8月下旬发表的《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一文。文章说:“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不能和力争民权自由的争斗分开;民族的建立正在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中;而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没有平民的革命政权,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连争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工人阶级应联合一般平民和同情民族运动的军人,与用武力破坏民族运动、蹂躏民权的奉系军阀斗争,“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500页。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阐说,强调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不但在国民革命中中共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即使是国民革命成功后转入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那时,在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确认了“平民的革命政权”的口号。会议决议指出:“最近的革命运动,当然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现时这一历史的时期”已是“全国民众起来争中国解放和民众政权实现时候”*《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63—464页。。中共作为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应当提出包含“革命民众政权”的政纲,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指出前进的道路。仔细体味陈独秀的文章和中央的决议,其立论的逻辑还是从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着眼的,强调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并非表达未来政权阶级构成的变动。决议同时使用“革命民众政权”与“平民政权”两个概念,没有着意加以区别,也可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对中共而言,即便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并不代表马上与资产阶级分道扬镳,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是要尽可能地拉住资产阶级,将其留在联合战线内。1926年2月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指出,资产阶级在“渐渐的脱离民众的国民运动”,然而他们希望以出卖群众运动换取帝国主义的让步,只能是自己骗自己,“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真正妥协,暂时还没有可能。所以以后资产阶级的对抗帝国主义,还是不可免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3、54页。。7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对此有更加详尽的分析。报告指出,国民革命的前途不外乎两种:要么是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要么是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拿住小资产阶级,并联合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中共要力争第一种前途,就不能不“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巩固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资产阶级不过是想用改良的方法向帝国主义要点东西,一旦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便存在着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可能性。可是,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我们应该明白了解现时中国的革命,毫无疑义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在估计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力量中,便非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及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鉴于此,中共应当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以防其将来之妥协;一方面极力巩固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促进资产阶级之革命化,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半封建势力)。”*《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70—171、168、169页。既不能“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的危险,也不能过早地敌视他们,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换句话说,就是对资产阶级既要联合,又要斗争。
三、昙花一现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妥协,中山舰事件和国民党新右派的形成,国内政局发生的这一系列严重变化,加剧了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的疑虑和不满,促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评估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并不得不重新思考资产阶级在未来政权中的位置。但是,直接推动中共决定对政权主张作出重大变更、对未来政权的阶级构成加以新的界定的,却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国革命是1926年冬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此时布哈林已取代季诺维耶夫,实际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他在会议上的发言系统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要点是:在革命的初期即第一阶段,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队伍中寻找支点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即开明的民族资产阶级、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是革命的极其重要的动力之一;第二阶段,无产阶级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目前是第三阶段临近的时刻,标志是大资产阶级被排除在外,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结成联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8—19页。。斯大林在会议上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专门谈到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问题:“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一九○五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有一个差别,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中国共产党可不可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呢?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参加。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张仲实、曹葆华译:《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99、100页。。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贯穿了斯大林、布哈林的观点,指出中国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个革命国家,不会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71—672页。。
国际新决议1927年1月送达上海后,引起了中共中央内部的不同反应。彭述之对决议内容表示反对,陈独秀的态度有所保留,只有瞿秋白“无条件接受决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131页。。依据决议的基本精神,瞿秋白写下了7万余字的长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系统阐述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看法。瞿秋白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并不是无条件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而是有条件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国革命虽是资产阶级的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然而农民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要求,必定和世界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之社会主义要求相结合,而形成直接从国民革命生长而成社会革命的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487、484页。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基于自身利益,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并且会力争革命的领导权,以造成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妥协的资格。民族资产阶级一旦争得领导权,就会停止革命,造成一个形式上的独立国家。可是,帝国主义仍能继续支配中国的一切经济,中国经济就会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产阶级就会代替现在的官僚地主阶级,做帝国主义的“政治买办”。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无产阶级就要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要争取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城市贫民及兵士,不断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妥协主义的影响,隔离民族资产阶级而使之孤立,“要用‘劳工阶级的方法实行国民革命’,以苏维埃的方法创造国民会议制度的平民共和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527页。邓中夏则指出,中国的革命政权即非土耳其式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俄罗斯式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是“中国自己的第三种形式”,这就是“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邓中夏全集》中卷,第1260页。。陈独秀也不由自主地受到国际新决议的影响,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民革命的前途,一种“是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另一种“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之下,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只有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脱离帝国主义之统治,才能够力图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才能够不一定经过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答沈滨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第268页。。这个表述显然与他之前主张的“二次革命论”有所不同。
受共产国际委派,罗易率代表团前来传达贯彻执委会七大决议,指导中共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大召开距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已经过去半个月。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一直把蒋介石看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公开叛变似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即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国际代表团实际上成为中共五大的主导。罗易在大会上多次发表讲话,对国际新决议的相关问题作出说明。他在谈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时说,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超出资产阶级的领导,革命领导权要转到非资产阶级人物手中。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国民革命将同帝国主义妥协而告结束,中国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地,从而有利于稳定资本主义。要取消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把领导权转到更加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手里。当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不是由资产阶级分子而是由更加革命的阶级领导的殖民地革命所完成时,那么消灭封建主义的目的就不再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它开创了一个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中国革命客观上只有一个前途: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只有当革命的主观力量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时,才会失去这个前途”。*《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97、399、405页。在讲到中国未来的政权形态时,罗易又说,中国革命“是一种崭新的革命方式,将建立一种新型的革命政权。因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盟领导下进行的,在一定时期革命政权就不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它将是小资产阶级政权,确切地说,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权”。革命所建立的以这三个阶级为基础的政府,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而是三个阶级的专政机关,是民主专政的机关。这种政权的性质与无产阶级专政有区别,是一种介乎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政权形式。无产阶级是这个政权中的决定性因素,它将防止民主主义变质的危险。革命的发展已建立了一个客观上具有民主专政性质的政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要负责切实运用这个革命政权机构,为加强非资本主义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第403—404、412—413、405页。他所说的这个“客观上具有民主专政性质的政府”,显然是指由国民党左派主导的武汉国民政府。
陈独秀所作的大会政治报告,是根据罗易提供的提纲起草的,自然遵从了国际新决议的基调,但从中很容易发现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自相矛盾。报告一方面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妥协性,断定“资产阶级不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也不会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出某些让步,资产阶级左派就会叛变革命”,并且判定,四一二政变后大部分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但另一方面又说:“虽然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但我们要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运动,不仅要吸收小资产阶级,而且要吸收大资产阶级。”*《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第351页。可以看出他在执行国际决议和坚持个人观点之间左右为难的窘迫。他还说,现在还不应把武汉政府看成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这个政府只是走向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途径。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构,以便今后建立起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并进而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第358页。这也显现他与罗易对武汉政府性质判断上的差异。涉及资产阶级与未来革命政权的关系问题,中共五大通过的文件和决议主要阐明了以下观点。
第一,靠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也是国际新决议对中共提出的要求。这个任务靠资产阶级是无法完成的。原因有二:一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反封建势力的成分;二是资产阶级是从地主阶级产生出来的,依然同地主阶级保持亲密的结合,甚至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众的工具(如买办)。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剥削农民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仇视农民革命,不但不能为民权自由而奋斗,反而作民权自由的敌人,更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以促进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4—65页。
第二,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资产阶级的妥协与背叛是必然的。从五卅运动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建立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看见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将走得太远,客观上危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于是开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运动移转到他们的指挥之下。目前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即封建分子、大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革命。*《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0、49页。资产阶级因不能阻滞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所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竟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是想用军事的胜利统一中国,然后与帝国主义妥协,使中国大多数民众仍被剥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01页。
第三,今后的革命动力将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中国革命的第三阶段,“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中共过去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今后的迫切任务是继续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建立一个左的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9、50—51页。革命要在坚决反抗反革命联盟的斗争中,更加向前发展。共产党必须领导劳苦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等反动派,“中国革命将要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74页。。
第四,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政权。“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00页。。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做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7页。国内外的客观条件都利于中国革命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的阶段。依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本性,国民革命的政体应当是民权的,可是对其他阶级必须是独裁的。凡是不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且反对革命的,都应当以无情的手段加以对付,这是国民革命中的唯一原则。*《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06页。
至此,“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政权主张,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得到正式确立。这表明,中共彻底抛弃了曾经是革命同盟者的资产阶级,将其归入反革命的阵营,从而否决了在未来国家政权中给资产阶级保留位置的可能。中共五大对当时阶级关系的分析是不科学和不符合实际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正如李维汉后来所指出的,是“没有把叛变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和虽处于动摇中而仍然应该尽可能争取的民族资产阶级区分开来,将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将中等商人划入小资产阶级,并将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混同看待,这种阶级划分是错误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85页。。这固然与中国资产阶级来源和成分复杂、经济利益和政治面目差别极大,客观上又无法提供一个科学的划分标准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共当时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水平不高,在阶级分析中常犯“公式化”“定型化”的毛病,易为资产阶级不同派别代表人物的言论迷惑,而忽视了他们转变政治立场和态度的可能。据此制定的政权主张,包含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就在“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提出后两个月,曾经的国民党左派代表汪精卫在武汉发起“清共”,与蒋派实现合流,由是小资产阶级也被认为背叛了革命,从革命阵营中剔除出去。革命动力从广州时期的四个阶级联合,变为武汉时期的三个阶级联合,到南昌起义再变为两个阶级的革命,进入创造工农苏维埃政权的时期。由于从提出到完结只有区区两个月的时间,很难说“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口号在客观上发生了多大作用。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对于国民革命时期中共政权主张的变化,笔者与周文有些看法是相同或相通的。其一,都承认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和瞿秋白的革命思路是不同的。姑且不论是不是如周文所说存在国民本位和平民本位的两种革命逻辑的区别,两人在革命路径选择上的确表现出明显差异。其二,都认可中共政权主张在大革命中有逐渐激进化的倾向。其三,都同意对资产阶级看法的变化是导致中共政权主张变化的基本因素。至于与周文的歧异,可大要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平民的民权”和“平民政权”并非“完全不同”,其阶级内容是一致的,资产阶级是包括在“平民”和“平民政权”范畴中的,“平民政权”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其次,中共对资产阶级看法的变化不是始自平定广东商团,商团早就被判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从一开始就是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对象。中共四大已经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能够表明中共对资产阶级看法陡变的征象,是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和五卅运动后对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揭露。再次,中共将资产阶级排除在未来政权构成之外的想法,不是萌生于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前后,亦不是确定于1925年10月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中共政权主张的实质性改变发生在1927年四五月间召开的中共五大,其标志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提出。最后,笔者以为,并不存在如周文所说的在“革命民众政权”口号下的政权思想“整合”。周文的观点能够成立,至少需要几个前提:一是“革命民众政权”与之前的“平民政权”(有时也称作“平民革命政权”)性质尤其是阶级规定性有所不同,属于另外一种政权主张;二是“革命民众政权”与之后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性质尤其是阶级规定性相同,属于同一种政权主张;三是“革命民众政权”口号提出后,为全党普遍接受,全党认识都统一到这个口号上,并通过一定形式(如中央正式决议、宣言、文告等)表现出来。从史实和文献看,这几个方面的证据都不充分,断定发生过这样的“整合”未免有些言过其实。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 吴志军)
The Slogan and Class Implication of the CPC’s Political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nd A Discussion with the ArticleFromthe“CivilianDoctrine”tothe“RevolutionaryPeople’sPoliticalPower”
Yu Huamin
The claim of the CPC’s political power experiences many changes in the revolution process, and its essence is the change of the judgment on class relations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nature and class constitute of the future political power. The “civilian power” slogan doesn’t exclude the bourgeois from revolutionary camp and the future revolutionary regime. The “revolutionary people’s political power” has no differences of principle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class from the former, and can not be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political ideas in the party. The mark of excluding the bourgeoisie from future regime is the proposal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the small bourgeoi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slogan in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bourgeoisie’s compromise and the form of the new rightist in the May 30th Movement, is the major political factor causing the changes of the CPC’s political power claim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instructions are the direct cause of changes.
D231
A
1003-3815(2016)-11-01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