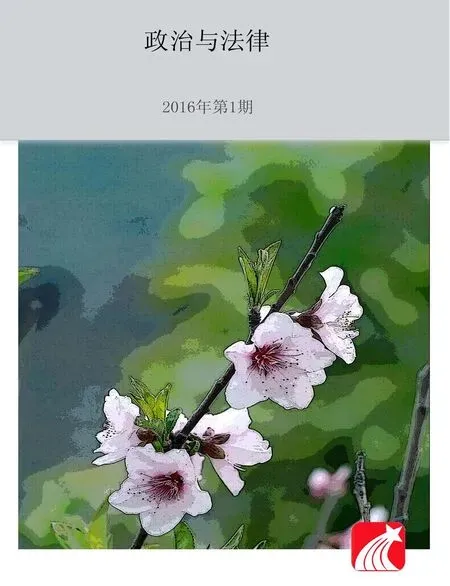论代理中的显名原则及其例外
2016-02-11殷秋实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7
殷秋实(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7)
论代理中的显名原则及其例外
殷秋实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7)
当代,代理法中的显名原则在内容和表示方式上都已缓和。内容上,代理人只需表现出被代理人的存在即可;方式上,尤其是在商事领域中,代理人通过各种形式能够让合理谨慎的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是在为被代理人进行交易即可。综观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其不仅显名原则有所缓和,而且对显名原则都设有例外规定,允许特定情况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为能够对被代理人产生直接效果。这是为了满足商业交易的快捷性和简便性,主要是为了让委托人能够及时获得合同项下的权利,特别是物权。我国《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虽然也是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的规定,但是它们都不是显名原则的例外:第402条只是显名原则的缓和,并不是真正的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的情形;第403条虽然是受托人(代理人)以自己名义的行为,但法律效果是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制度的特别适用,没有直接效果的产生。在我国代理立法中,只有显名原则,而没有该原则的例外,直接效果的发生均需要以被代理人名义的显名为要件。
显名原则;代理;直接效果;自己名义;债权让与;债务承担
代理人在行使代理权时需要表明本人的名义,以被代理人名义对外行为,这称为显名原则,是意定代理行为发生效力的要件。大陆法系国家的代理制度普遍采用显名原则。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句规定,代理人于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所为之意思表示,直接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意大利民法典第1388条规定,由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并为其利益,在授权的范围内缔结的契约,直接对被代理人产生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3条第1款规定,代理人于代理权限内,以本人名义所为之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我国法也继受了显名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然而,原则常有例外。我国《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似乎就是显名原则的例外。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及各自的适用范围一向是解释的难点,在代理制度中则更加困难。我国《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所继受的并非大陆民法传统,而是受到了英美法和相关国际条约、示范法的影响。这些条文的渊源不同,使得我国代理制度呈现表面清晰、内部混乱的状况。另外,我国学者对于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理解并不准确、全面,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代理公约》等国际文件相关条文的理解也有欠缺,这直接导致对《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的解释脱离了法条的文义、所在体系与立法目的。这些原因导致法院在实践中不能很好地把握和适用这两个条文。
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构建和解释代理法中的显名原则。这需要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理解显示被代理人名义的含义,确定显名的功能、内容以及方式;二是解释显名原则之例外情形的存在原因和达到目的的技术手段。正确理解显名原则及其例外后,《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的解释难题以及其与《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的关系就可以迎刃而解。同时,这也有助于分析显名原则在我国可能存在的不足,从而构建更合适的代理法体系。
一、显名的内容与方式:从严格到缓和
意定代理制度可以扩大本人的活动范围,让本人超越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而且,由于公司等商事组织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代理对于公司等组织体的运行不可或缺,扩大代理制度的适用范围,可以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显名原则的缓和是扩大代理适用范围的重要方式,这主要表现在显名内容的变化和显名方式的变化上。
(一)显名内容的变化
就显名的内容而言,缓和表现在代理人并不必须在订立合同时就表明被代理人的具体信息,①一般认为,显名意味着代理人要通过代理行为表示出本人的名义,行为人要表示代本人实施法律行为。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而是可以只表明本人的存在或者自己的代理人身份,本人的具体身份可以暂不公开。
明确显示被代理人身份符合显名制度的传统功能。通常认为,代理人表明本人名义的重要性在于保护交易相对人和本人的利益,完善法律行为制度。首先,显名可以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通常只有在行为相对人能够识别代理人是代理人,并且知道他真正的对方当事人是谁时,才能要求相对人接受代理效果的发生。②参见[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93页。其次,显名原则有利于保护本人利益,显名原则公示了本人的名义,有利于让相对人调查授权的范围,从而防止代理人的越权行为;也可以让被代理人直接取得行为后果,防止代理人截留属于本人的利益。③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3页。再次,显名主义也和法律行为制度衔接。代理中,意思表示的发出和接受由代理人完成,但是法律行为的效果则归属于本人。这种表意人和效果承担人不一致的解决可以通过显名完成。④参见尹飞:《代理:体系整合与概念梳理——以公开原则为中心》,《法学家》2011年第2期。如果代理制度没有显名原则做支撑,法律行为制度就可能瓦解。⑤参见刘宏华:《从外贸代理制看民事代理制度若干问题》,《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综合来看,这些功能强调名义显示对被代理人自身和交易相对人的作用,特别是对相对人的作用。⑥在保护本人利益的方面,防止越权的作用已经被表见代理等制度替代;被代理人直接取得代理效果以及完善法律行为制度的功能则并不需要被代理人身份在订立合同时得以显示,因此,显名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相对人。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显名也有利于保护代理人的利益。对代理人来说,显示被代理人名义可以避免法律行为的效果在自己的法律领域内发生,本质上显名具有拒绝行为效果对自己发生的消极含义。⑦Dei contratti in generale,in Commentario dei codice civile,art 1387-1424,a cura di Emanuela Navarretta,Andrea Orestano, diretto da Enrico Gabrielli,UTET,2012,p.22.即使代理人没有代理权,显名也可以将代理人排除在法律行为之外:在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并不成为合同的当事人,但由于代理人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行为,代理人也被排除在法律行为之外,不会成为代理行为的当事人。⑧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款,代理人可能对相对人承担履行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基础是,如果第三人选择请求履行,会在第三人与代理人之间产生法定之债关系,内容相当于代理人拥有代理权时被代理人所应承担的给付义务(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因此,这是一种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不是来源于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自身。显名原则的这种功能意味着相对人并不需要知道被代理人的具体信息,而只需要知道代理人的身份或者被代理人的存在,显名原则就能实现其功能。
显名内容的缓和并不会影响相对人利益。对于相对人来说,知晓具体的被代理人是谁当然重要,否则就不能有效地主张权利、要求履行义务;然而,在合同订立时,重要的是相对人知道自己的磋商对象并不是合同当事人这一信息。在第三人不知道被代理人身份时,第三人至少清楚代理人并不是法律行为的当事人,此时,第三人仍然愿意缔结合同的意愿表明第三人愿意承受合同相对人暂时不确定的风险。而且,被代理人身份的不确定只是暂时的,第三人最终可以如同在普通代理中一样,确定自己权利义务的相对人。显名内容的缓和只是并非一次性地提供被代理人的全部信息,而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分别提供被代理人的不同信息,这只是显名在时间维度上的拉长而已。
代理人在订立合同时可以只表明被代理人的存在,在比较法上也被普遍认可。在大陆法系中,欧洲民法典共同参考框架草案(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以下称:DCFR)即是范例。依DCFR,要让被代理人承担法律效果,代理人需要以被代理人名义行事,或者以各种方式对第三人表现出欲影响本人法律地位的意图,这只需要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代理人是以本人的代理人身份行事即可,不需要明确指出被代理人的身份。⑨Christian von Bar,Eric Clive,Principles,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DCFR),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2009,p.427.德国法中非纯正的行为归属也是这种情况,行为人公开表示以他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但未向第三人显示该他人具体是谁,此时代理效果依旧发生,并不构成显名原则的例外。⑩参见前注⑧,朱庆育书,第327页。在美国法中,这种情况可以被本人身份不明的代理(unidentified principal)所涵摄。这种情况和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disclosed principal)以及未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undisclosed principal)一起,构成代理的三种类型。无论本人身份不明还是被明示披露,本人都不被认为是隐藏的。①See 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Agency§1.04.在代理法第二次重述的时候,没有表明身份的本人被称之为"partially disclosed principal".See Restatement of the Law,Second,Agency§4(2)。英国法的情况类似,代理人或者表明本人的身份(在英国法中被称作named principal),或者只表明了本人的存在而暂时没有表明身份(在英国法中反而被称作disclosed principal,和美国法不同),两者都能让第三方知晓代理人不是为了自己订立合同,因此被认为可以不做区分,②See Fridman,The Law of Agency,Butterworths,1996,p.215.被代理人都会受到合同约束。
(二)显名方式的变化
就显名方式而言,传统理论比较保守,认为被代理人名义要明确、无疑义地显现,并不接受默示显名的方式。③Commentario del codice civile Scialoja Branca art1372-1405,a cura di Francesco Galgano,Zanichelli bologna,1993,p.210.代理人明确声明自己为被代理人的代理人,或者出示授权证书,或者在签署文件时注明被代理人名称和自己的代理人身份等都构成明示的显名。显名方式的缓和则表现在代理人不仅可以通过明示方式显示被代理人的名义,也可以默示地表达被代理人的身份或存在,甚至通过单纯的沉默来表示。这种情况即如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句规定的,虽未明确显示本人名义,但是根据情境能够知悉该意思表示以被代理人名义做出的,也可认为是显名。如商店的售货员即使没有明言,但是显然是店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某人在公司信笺上发出意思表示,即使仅仅签署自己的姓名,也是在为公司从事行为等。①参见前注②,梅迪库斯书,第699页。在意大利民法中也是如此。意大利民法典第2208条规定,如果经理(institore)疏忽让第三人知道他是为被代理人而实施行为,则由经理承担个人责任;但是,第三人亦得就经理完成的有关被委托的企业经营行为向企业主提起诉讼。此时,替代明示显名的是经理从事的和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行为——一旦经理在经营活动范围外签订合同,或者行为是否是经营活动有疑问时,就仍然需要被代理人名义的显现。②Commentario del codice civile Scialoja Branca,cit.,p.213-214.企业的商业辅助人(commesso)也不需要明示的显名行为,当其在工作场合工作时,很难认为第三人应该怀疑他不是为企业主在工作。③Alessandra Salomoni,La rappresentanza volontaria,CEDAM,1997,p.120.另外,在重复交易的场合,如果代理人一直以代理人身份和相对人进行交易,代理人也不必在每次交易时都表达本人的名义。在我国《民法通则》、我国《合同法》中虽然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但是我国也有学者认可这种通过情景让人知悉被代理人名义的显名。④参见前注⑧,朱庆育书,第326页;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71页。
显名方式的缓和建立在显名行为本质的理解之上。显名是代理人欲使行为效果直接归属于本人的意思,是代理行为意思表示的一部分。⑤参见前注①,梁慧星书,第234页。輥輶訛显名这一要件是否成就,取决于代理人明示、默示的表示或者沉默是否能够让合理谨慎的相对人认识到被代理人的存在;⑥类似的观点,参见C.Massimo Bianca,Diritto civile,II,Il Contratto,Giuffrè,2000,p.94。輥輷訛或者说,代理人是否通过合适的形式让一个具有通常谨慎标准的第三人能够认识到代理权的存在。⑦Ugo Natoli,Rappresentanza(diritto privato),in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XXXVIII,Giuffrè,1987,p.465.简而言之,这是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句规定的情况,其实也是意思表示相对人知晓的,在解释时应该考虑的,足以使他知道意思表示是为被代理人进行的情况。⑧参见[德]卡尔·拉仑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谢怀栻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37页。因此,显名看似是对代理人提出的要求,显名是否完成却需要从相对人的角度来观察。这也就意味着,在代理人提供的信息存在冲突时,需要结合具体情况、交易惯例等因素判断代理人的真意以及合理的第三人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即需要进行意思表示解释的工作,而不能只从代理人行为的角度判断。代理人没有明示提供任何名义,不代表被代理人名义没有显现;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也可能构成真意保留。
从相对人角度看,如果代理人既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名义,也没有明确表示被代理人的名义,结合客观情境同样无法判断被代理人存在时,代理人就是以自己名义行为。这也是解释上的缺省规则:在无法确定相对人是否知晓被代理人存在时,推定代理人是以自己名义行为。对此,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2款可资借鉴,其规定如果代理人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以本人名义,也不考虑为自己行为意愿的缺乏。诚然,该款的意义主要是防止代理人以意思表示错误为由撤销因缺乏公示性而应该由自己承担后果的法律行为,⑨参见前注②,梅迪库斯书,第701页。但其也明确了代理人如果没有以本人名义行为,就视为以自己名义行为的规则。我国法律虽然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解释论上也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代理行为毕竟是法律行为的一种例外,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行为才是原则,这也是为什么代理需要显名的原因。
综上,可以界定对下文讨论非常重要的前提,即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的含义。所谓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是指从代理人明示、默示的表示或者沉默中,结合交易情境和惯例,一个合理谨慎的相对人并不能知晓被代理人的身份或者本人的存在。从代理人的角度看,这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代理人明确以自己名义行为,二是代理人虽然没有明确以自己名义,但也没有以本人名义活动的行为。
二、显名原则的例外和其功能
显名原则的例外,是指代理人虽然以自己名义对外行为,仍能发生直接效果,让被代理人直接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情况。我国立法和理论尚没有关注这种情况,但显名原则的例外在比较法上普遍存在。对比较法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归纳这种例外所欲实现的功能,有益于我国法的解释。
(一)大陆法系:限定的直接效果
大陆法系以显名原则为代理法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相对人无从得知本人姓名,也不能察觉代理人想要影响本人地位的意图时,原则上合同关系只约束代理人和相对人。①DCFR,p.429.意大利民法典第1705条第1款即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行为时,即使第三人知道委托关系的存在,受托人也对第三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过,这种原则也存在例外,例外主要有两种情况,即为事所关涉之人做出行为和间接代理中的动产移转。
为事所关涉之人做出行为的制度基础是德国的学说,指的是第三人并不在乎交易人是何人的情况下——通常是那些生活中即刻就可完成的行为——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的法律效果由被代理人承担。②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页。这时候,相对人被认为无需受到显名原则的特别保护,隐藏的本人可以依据代理规则直接承受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涉及处分行为时,也是由本人直接取得所有权,而不必由行为人移转。③参见前注⑧,朱庆育书,第327页。
此时,替代显名原则功能的是,对第三人来说,代理人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取得无关紧要这一情况。因此,该原则的适用有其限制条件:一般来说,如果相对人还没有获得对待给付,代理人是为谁取得就并非无关紧要——因此,这个原则被认为主要适用于现金交易;④参见[德]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33页。基于同样的理由,该原则也不能延伸到义务行为中,因为法律行为的对方当事人对于因价金或合同上的权利而可以要求由谁来承担责任绝对不会无所谓。⑤同上注,施瓦布书,第534页。从法律效果来说,这时的直接效果是受限的,即使相对人已经获得对待给付,直接效果也限于被代理人权利的取得,⑥这种权利通常是物权,也可以是债权(例如代理人为被代理人从相对人处购买债权),还可能是其他请求权,如物权请求权、瑕疵担保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参见崔建远:《民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页。或者说,在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中,被代理人取得权利,但义务仍然由代理人承担。让被代理人直接取得权利(主要是物权)的目的,在于避免财产仍在代理人处时,代理人的债权人扣押或强制执行财产对本人可能造成的不利。⑦参见前注輦輴訛,施瓦布书,第532页。
间接代理中动产物权的直接移转,指的是在授权范围内,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从相对人处获得动产时,委托人可以直接获得动产的所有权。这和传统间接代理的情况不同:传统间接代理中,委托人获得动产所有权需要一个两步走的移转过程,即需要受托人将所有权移转给委托人,受托人至少在理论上享有一段时间的所有权。较为晚近的意大利民法典、DCFR等都采取了直接移转的模式。不过,在采两步走模式的国家中,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提前构建占有改定约款,这样,受托人取得物权的时候,委托人也随即取得物权。因此,在两步走模式的国家中,也存在让委托人直接取得动产物权的倾向。⑧DCFR,p.4756.不过,这种直接取得只限于普通动产,在需要登记的特殊动产和不动产的场合,所有权的移转需要遵循相应的关于登记的规定。
委托人直接取得动产物权的价值基础是商业实践的简便性和快捷性。就这里所涉及的三方主体而言,委托人直接取得至少没有将任何一方置于比传统模式更糟糕的地位:对相对人来说,这两种模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由于义务总是要履行,由谁获得物品最终的所有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主张权利的对象仍然是受托人(代理人),这维持了相对人订立合同时的信赖;对委托人来说,直接取得的模式显然更加有利,可以避免动产物权还停留在受托人处时被受托人之债权人执行的风险;对受托人来说,直接取得模式可能会导致受托人在还没有取得对价的情况下就丧失物权,受托人可能面临钱财两空的情况,不过,考虑到受托人可以行使留置权,其利益状态并没有实质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在委托人直接取得动产物权的情况下,委托人并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①Giovanni Di Rosa,Rappresentanza e gestione:forma giuridica e realtàeconomica,Giuffrè,1997,p.116.因此,这里仍然是一个限定的直接效果,委托人并没有成为合同的当事人,只是能够直接取得物权,合同项下的义务仍然由代理人承担。
(二)英美法系:受限的构成要件
英美法中,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undisclosed principal)是典型的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但能发生直接效果的情况。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当代理人和第三人缔约时,第三人完全不知道代理人是为被代理人行为;②这是美国法的定义,see 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Agency§1.04.或者说被代理人的存在完全不为第三人所知,第三人不知道代理人的代理人身份,以为代理人就是真正的合同当事人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笔者于本文中并不采纳隐名代理的术语。这是因为隐名代理一词在我国并没有统一的指代,存在颇多争论。有学者认为隐名代理是代理人与第三人磋商时,相对人知道代理人是在为被代理人行为,但不知被代理人具体身份的情况,③参见尹飞:《论隐名代理的构成与效力》,《法律科学》2011年第3期。这对应普通法中本人身份不明的代理;有学者认为隐名代理是代理人有代理权,但是不公开自己的代理人身份,而是以自己名义为民事行为的情况,④参见杜颖:《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中外法学》2007年第6期;吴真:《隐名代理的法律地位研究》,《当代法学》2002年第5期。这对应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有学者认为隐名代理既包括公开自己代理人身份而不披露本人姓名,也包括不公开代理人身份也不披露本人姓名,只是以自己名义行为的情况;⑤参见倪万英:《论隐名代理制度》,《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我国台湾地区的隐名代理则指代理人虽然没有以本人名义为法律行为,实际上有代理意思,且相对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可以发生代理的效果。⑥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页。既然概念如此混乱,为防止混淆或望文生义,不如暂不使用。
我国理论界在讨论和借鉴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时,重视法律效果,忽视对构成要件的研究。其实,从构成要件看,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对授权有严格的要求:本人必须授权代理人将本人带入到代理人与第三人的合同之中,本人想成为合同的当事人。在此前提下,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的适用限于以下两种情况:或者本人希望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是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进入了市场,因此希望隐瞒这一事实;或者是代理人有授权,但是并不想披露本人的存在,因为他不想让第三人在之后的交易中撇开自己而直接和被代理人交易——同时,对于代理人的这种心思,被代理人处于知道或者容忍的状态。⑦F.M.B.Reynolds,Bowstead and Reynolds on Agency,Sweet&Maxwell,2006,p.375.虽然也有观点认为只要被代理人使用了中介人,不管本人是否想要成为合同的当事人,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效果都可以发生,⑧Id,p.376.但是,前者的观点仍然是通说。因此,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需要本人授权代理人和第三人签订合同,且本人有成为合同当事人的意图,只是由于本人或者代理人的原因,本人的存在没有被披露给第三人。⑨See Andrew Burrows,English Private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ara.9.74.这就将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和大陆法系的间接代理区分开来。
不表明本人身份代理中授权的严格性,还表现在如果本人的授权是让代理人进行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代理人却对外以自己名义缔约,可能被认为违反授权而没有代理法律效果的发生。⑩F.M.B.Reynolds,supra note 37,p.377.代理人在行为时,也需要为被代理人的利益行为,如果代理人在缔约过程中不是为被代理人利益而是为自己利益行为,被代理人就不受到代理人行为的约束。①Rolls-Royce Power Engineering plc and Allen Power Engineering plc v.Ricardo Consulting Engineers Ltd[2003]EWHC 2871(TCC).See also 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Agency§6.03,comment c.对授权的严格强调,甚至导致英国法认为在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中,本人不能追认,以防止一个人过于容易地介入到他人的合同之中。②See A rnold Rochvarg,Ratification and Undisclosed Principals,34 M cGill L.J.286(1989).
代理人的行为超出了本人的明确授权,但是仍然处在相对人认为代理人通常应该具有的权限范围之内时,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仍然可以发生法律效果。③在英国法下,这条规则的正确性是有疑问的。参见F.M.B.Reynolds,supra note 37,p.380。美国法的情况,参见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Agency§2.06(2)。没有真实权限的代理人引诱相对人做出了对相对人自己不利的改变,同时本人知道代理人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可能引诱他人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行为,但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通知相对人时,没有被披露出来的本人也需要承担责任。④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Agency§2.06(1).这并不是普通法中表面权限原则的适用,因为表面权限的适用要求代理人具有权限的表象来自本人的表示,而在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中,相对人完全不知道被代理人的存在,也就无法证明表象来自于本人的表示。但是,这种保护相对人信赖的机制仍然扩大了不表明本人身份代理的适用范围。
从法律效果看,不表明本人身份代理的确和大陆法很不相同,这也是我国理论界极关注的地方。在普通法中,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对被代理人发生完全的直接效果,同时代理人也不脱离合同:被代理人是合同的当事人,可以依据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的合同提出诉讼或者被相对人起诉;代理人也是合同的当事人,也可以依据合同提出诉讼或者被相对人起诉。⑤英国法的情况,参见F.M.B.Reynolds,supra note 37,p.507。美国法的情况,参见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Agency§ 6.03(2)。因此,普通法中,代理人在本人授权范围内以自己名义的行为会让被代理人、代理人和相对人都成为当事人,被代理人可以“介入”代理人和相对人的行为,成为合同主体;同时,第三人也可以“选择”一个主体,作为合同的相对人以主张自己的权利。
不表明本人身份代理的这种法律效果,也是出自商业实践便利的考虑。对被代理人来说,由于他是合同当事人,可以直接对相对人提出请求,这可以防止通过代理人主张或者代理人转让诉权的方法可能产生的迟延损失,也可以防止代理人破产对自己可能造成的不利;⑥事实上,这种制度在英国法上最初出现的时候,就是呈上本人在代理人破产的时候能够介入,以要求货物或者价款,后来则是让本人可以依据整个合同起诉。See S.J.Stoljar,The Law of Agency,Sweet&M axwell,1961,pp.203-211.代理人不愿意披露本人,是为了防止可能的本人或者相对人越过自己直接和相对人或者本人进行交易;相对人也获得了优待,某些情况下,相对人的期待可以通过直接对本人主张而得到满足,譬如被代理人(而不是代理人)占有应该交付的财产等。总之,这些法律效果的正当性在于防止诉讼的迂回曲折。⑦P.F.P Higgins,The Equity of the Undisclosed Principal,28 The Modern L.R.167(1965).不过,就被代理人和相对人彼此可以向对方提出的诉讼而言,被代理人对相对人的直接诉权被认为比相对人对被代理人的直接诉权更容易获得解释。⑧被代理人对相对人的直接诉权可以被认为不是建立在合同规则之上,而是建立在财产规则之上。Benjamin Geva,Authority of Sale and Privity of Contract:The Proprietary Basis of the Right to the Proceeds of Sale at Common Law,25 M cGill L.J.32 (1979).在比较法上,也是委托人可以直接对相对人行使的诉权这个方面更受大陆法系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大陆法中可以通过如赋予被代理人直接诉权等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结果。参见Konrad Zweigert,Hein Kotz,Introduction to the Comparative Law, Clarendon Press,1998,p.439。综合来看,不表明本人代理主要试图保护的也是本人的利益。
(三)总结与比较
在大陆法和英美法中,虽然都存在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发生直接法律效果的制度,但构建方式非常不同,两者分别在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上做文章。就构成要件来说,大陆法并没有什么特别要求,通常只要有以取得动产物权为标的的委托关系即可;英美法则需要有本人确定的不愿显名但仍愿意成为合同当事人的授权,这就把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和间接代理区分开来。就法律效果而言,大陆法的直接效果是限定的,委托人可以直接取得权利(通常是物权),受托人仍然要承担义务,委托人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英美法中,在代理人有授权的情况下,委托人可直接成为合同的当事人,产生完全的代理效果。
无论在哪个法系,代理人显示被代理人的存在才能让被代理人成为合同当事人都是原则,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时也能发生直接效果的制度都难以在教义层面上获得合理解释。在大陆法中,虽然被代理人可以取得权利,但被代理人并非负担或者物权行为的当事人,难以解释权利为何能够从相对人直接移转到委托人处。在英美法中,既然代理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行为,代理人成为合同当事人显得理所当然,但是,从合意理论和对价理论来看,未被披露的被代理人成为合同当事人则引发了正当性的争论。⑨See Randy E.Barnett,Squaring Undisclosed Agency Law w ith Contract Theory,75 Cal.L.Rev.1969(1987).现有的解释方法立足于被代理人的意思,认为只要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合理行为,被代理人成为合同当事人的基础就是被代理人的授权,也就是被代理人想要成为合同当事人的意思使其成为当事人。⑩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Agency§6.03,comment b.然而,这只是宏观的价值论证,并没有在逻辑和技术层面解决这个问题。此外,第三人的选择权也颇受攻击和异议:大陆法学者认为选择权意味着受托人破产的风险不再由相对人承担,而是由委托人承担,这是对第三人的过分优待,委托人的授权并不意味着他要对第三人承担责任;①Konrad Zweigert,Hein Kotz,supra note 48,p.440.英美法学者则认为代理人破产时,如果第三人选择代理人会导致本人获得利益而不必承担责任,因此有美国法院认为应该摒弃选择规则,让本人和代理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②参见前注④,杜颖文。这些解释论上的困难至少意味着,如果立法中缺乏显名原则例外情况的明确规定,仅仅依靠法解释学很难创设这种例外。
因此,显名原则的例外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以此为标准,大陆法系不限定构成要件、限定直接效果的模式在实现这个目标时,对原有体系的冲击比较小;而英美法限定构成要件、完全直接效果的模式虽然也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但造成了被代理人当事人的地位难以解释、相对人选择权的合理性等更多的解释论上的难题,有严格要求的授权也缩小了主体保护范围。从这两点来看,大陆法系限定直接效果的模式更值得采纳。
三、我国《合同法》第402条:并非自己名义
从文义上看,我国《合同法》第402条的构成要件是:(1)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对外行为;(2)受托人的行为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3)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4)合同并不是只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在满足以上构成要件时,承受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的是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即委托人和第三人,受托人不是合同的主体。③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因此,该条规定了受托人以自己名义的行为可以直接约束委托人的情况,是显名原则的明确例外。
不过,无论从显名的内容与方式,还是显名原则之例外的通常功能来看,这种解释是非常可疑的。如果将“受托人以自己名义”的规定理解为构成要件,就意味着从受托人明示、默示的表示或者沉默中,结合交易情境,一个合理谨慎的相对人并不认为交易中有被代理人的存在,这会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以及“合同并不只是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这两个要件发生冲突。就“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这一要件来说,第三人知道的途径无非有三种:(1)相对人从代理人明示的表示或者行为得知;(2)虽然没有代理人的明示显名,但结合情境和惯例,相对人可以得知并相信这种代理关系的存在;(3)相对人是从与代理人无关的来源得知,如第三人的告知。第402条既然限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为,这就排除了前两种情况,因为前两种途径都满足了显名的要求。因此,从文义上看,第402条规制的是受托人(代理人)以自己名义,但第三人从并非代理人的途径知晓委托人和受托人代理关系的情况。
然而,这种前提条件不能导致直接效果的发生。受托人并非一旦成为代理人就不能为自己订立合同,而是既可以订立合同约束被代理人,也可以为自己订立合同——为自己订立的合同也完全可以和代理权的范围重合。为了让相对人知晓自己的交易对象,代理人就需要在交易时明确自己的身份,这也是显名重要的原因。相对人虽然可以从其他途径得知受托人的代理人身份,但是,正如意思表示需由本人发出才有效力一样,相对人的知晓也需来自代理人才有意义。④在美国法中,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身份不明的代理以及未表明本人身份代理的判断,取决于本人和代理人的表示,以及第三人在于代理人磋商时收到的信息,这可供参考。参见Restatement of the Law,Third,Agency§1.04,comment b.例如,委托人就行为有利益、第三人知道授权的存在、代理人有为某主体行为的资格等因素,虽有助于解释是否存在显名,但仅凭这些因素不能推定被代理人名义的显现。⑤Alessandra Salomoni,cit.,p.107.仅仅有第三人知道代理或者委托的存在,不足以构成相对人充分信赖的理由,因此也不能让行为效果直接对本人发生,这也是为了区分利他合同与代理。⑥Dei contratti in generale,in Commentario dei codice civile,art 1387-1424,cit.,pp.23,27.例如,甲知道乙是丙房地产经纪公司的代理人,但乙明确以自己名义,或者乙并没有在丙的经营场所和甲洽谈,乙向甲购买房屋的行为并不应该让丙成为合同当事人,合同只约束甲和乙。
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和“合同不是只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也存在冲突。无论是代理人明确表示自己是合同的当事人,还是代理人没有表示,客观情势也没有显示另有被代理人存在,受托人表达的是为自己订立合同的意图,被代理人就被排除在外。受托人以自己名义行为本身就应是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证明。这意味着“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的积极要件直接满足了“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之效果的要件,第402条可能由于构成要件自我满足而失去适用的可能性。另外,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行为可以产生完全直接效果的规定,在目的上也存在问题。依据立法资料,该条是“根据代理制度的原理,适应经济贸易中有关代理的不同要求,兼顾委托人、受托人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⑦参见胡康生:《中华人名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然而,第402条限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行为却能拘束委托人的做法,并没有遵循代理制度的原理,也可能会导致应进入合同的主体没有进入(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却被排除在合同之外)、不应进入合同的主体却进入了合同(合同会约束可能并无此意愿的委托人)的效果。这样,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利益都没有被合理考虑,①有学者从类似的角度批评合同法第402条可能导致代理人既没有以本人名义也没有以自己名义行为时由自己承担行为效果,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时反而可以发生代理的荒谬后果。参见尹飞:《代理:体系整合与概念梳理——以公开原则为中心》,《法学家》2011年第2期。不过,该学者对自己名义的界定并不恰当。反而是相对人可能并不合理的信赖得到了保护。因此,第402条存在严重问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这一要件和其他要件以及本条所欲达到的目的发生了冲突。事实上,从各方面的因素看,“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这一规定不应该出现在第402条之中,至少不应该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理解。
从立法的参照对象来看,第402条的重点是“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第402条所借鉴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代理公约》第12条:“代理人于其权限范围内代理本人实施行为,而且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代理人是以代理身份实施行为时,代理人的行为直接约束本人与第三人。”该条的确没有提及显名,代理人是否明确宣称他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行为或者提到了被代理人的存在并不重要,相对人在合同缔结的时候可以并不知道被代理人的具体身份。②Malcolm Evans,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Agen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Revue de droit uniforme/Uniform Law Review 1984,I.,para.66.但是,由于显名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达到,即使没有受托人的明确表示,相对人能够从交易环境中得知被代理人的存在时,也可以实现显名。因此该公约第12条的规定和显名原则并不矛盾。③M ichael Joachim Bonell,The 1983 Geneva Convention on Agen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32 Am.J.Comp.L. 717(1984).而且,公约第12条虽然没有规定显名,但也未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行为这一要件。我国立法和学说对第三人知道的解释也强调第三人知道的是受托人是委托人的代理人,知道具体的被代理人和授权的内容与期限等。④参见前注⑦,胡康生书,第574页;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2页。这其中暗含的都是代理人已经显名,而非以自己名义行为。
理论学说倾向于将第402条解释为普通法的本人身份不明的代理,是代理人仅公开代理人身份,第三人无需知道被代理人具体身份的情形。⑤参见前注③,尹飞文;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43页;张平华、刘耀东:《间接代理制度研究——以〈合同法〉第402条与第403条为中心》,《北方法学》2009年第4期;江平:《中华人名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左海聪、张川华:《外贸代理的类型化及法律适用——以我国〈合同法〉第402、403条为视角》,《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该条是《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2句的翻版,其实际内容是代理人可以明示,也可以依据情境表示行为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⑥参见前注④,杜颖文。两种解释涉及两种不同的进路,前者是显名内容的缓和,后者是显名方式的缓和,但共同点是都不认同第402条是受托人以自己名义行为。
相比学说倾向于将第402条解释为显名内容的缓和,司法实务更倾向于将第402条解释为显名方式的缓和。在适用第402条的具体案件中,代理人在和相对人签订合同时,被代理人的具体身份都被显现,只是显示的方式不同,有时候更需要细致的意思表示解释工作。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为例,这些显名方式包括:相对人、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就同一标的一起签订多份合同,其中有合同明显指出了本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⑦参见大连羽田钢管有限公司与大连保税区弘丰钢铁工贸有限公司、株式会社羽田钢管制造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龙王塘街道办事处物权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29号。代理人和相对签订人的合同中,代理人明确表示了自己的代理人身份,并表明后果由本人承担;⑧参见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及其厦门分公司与厦门瀛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厦门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国际海上货运代理经营权损害赔偿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213号;名山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诉威格尔国际合作发展公司等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2期。代理人提供的有关合同的其他文件——例如提单——表明被代理人的身份;①参见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与汕头市航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410号。被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有长期的合同往来,在被代理人开始使用代理人后,之后的年份代理人虽然没有明确显示被代理人的存在,但是从交易惯例可以推断代理人仍是为被代理人订立合同,这是通过沉默的行为来显名。②参见四川省鑫福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87号。这些案例基本涵盖了显名的各种方式,被代理人的存在都可通过代理人的行为被相对人获知,并不是真正的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
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看,受托人的自己名义并不是第402条的构成要件,法条的表述应是由于立法时对本人名义、间接代理、隐名代理等比较法上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的理解不清晰和不准确所致。第402条的真正意义在于缓和了显名的内容和方式,并没有超越显名原则。基于这种理解,第402条并不应该置于合同法分则,而应该在消除歧义后置于民法总则关于代理的一般规定之中,构成对《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的补充和明确。未来的民法典总则部分可以如此规定显名规则: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的名义可以明确显示,也可通过相关情事让第三人知悉。
四、《合同法》第403条:并非直接效果
相比第402条,《合同法》第403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规定是典型的受托人以自己名义行为。第403条的问题在于,委托人介入权和受托人选择权这种关于法律效果的独特规定是否构成直接效果。
多数学者肯定直接效果的发生,且认为第403条是普通法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在我国的运用。③参见王艳、王龙海:《关于间接代理制度的立法思考》,《当代法学》2002年第7期;邓旭:《间接代理略论》,《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参见前注輪輰訛,张平华、刘耀东文。在这种观点下,委托人介入权的效果,是使得委托人取得受托人的地位,合同对委托人和第三人具有约束力,受托人将退出合同关系,不再对第三人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第三人选择权的后果,是第三人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第三人选择任何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都表明该当事人是第三人所确定的缔约伙伴。两者加总的结果是委托人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合同的当事人。④参见前注⑦,胡康生书,第575页;同前注輪輰訛,江平书,第346-347页;同前注輪輯訛,王利明书,第829-831页。这种观点在实践中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如认为第三人的选择权意味着合同主体的变更。⑤参见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牡丹江日达化工有限公司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申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668号。也有学者认为第403条的规定是以违约为前提的非常态代理规则,在行为时放弃了公开原则,通过介入权和选择权的形式来补授相关效果意思,最终导致直接代理的效果。⑥参见前注輩輶訛,尹飞文。只有少数学者否定直接效果的发生,认为第403条的规定并没有承认间接代理在任何情况下均得发生直接代理的效果,其功能和目的只是在发生违约的情况下对本人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救济,而不是规定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可以在本人和第三人之间直接发生关系。⑦参见前注輪輰訛,尹田书,第644页。总的来看,现阶段我国学界对第403条的主流解释不仅肯定直接效果的发生,而且认为这种效果是能够让委托人成为合同当事人,由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完全直接效果的。然而,这种解释并不恰当。
《合同法》第403条明显仿照了《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第13条第2款(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303条)的规定。违约情况下委托人介入和相对人选择的权利是国际公约的创新之处,是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做法的折衷。表面上看,委托人介入和相对人选择的权利的确类似普通法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实则,两者在法律效果上的差别不可忽视。普通法中,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形成的是有三方主体的法律关系,被代理人也是合同的当事人,而在有关国际公约中,委托人在两种情况中都不是代理人和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正式当事人。①M ichael Joachim Bonell,supra note 60.《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赋予委托人和相对人对彼此的抗辩权,进一步表明了这种效果上的区分。例如,在普通法中,如果相对人选择委托人作为合同当事人,就意味着委托人要履行合同,即使委托人已经向受托人履行,委托人也不能以此为抗辩对抗相对人。②Guenter Treitel,The Law of Contract,Sweet&Maxwell,2003,.731.国际公约的做法则是相对人选择委托人主张权利时,委托人可以对相对人主张自己对受托人的抗辩。考虑到《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第13条第2款、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303条和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的相似性,以上结论也适用于解释第403条。
除了法律效果的区别,第403条的构成要件也和普通法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存在区别。第403条和普通法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都对构成要件有所限制,不同之处在于,第403条的限制是受托人因委托人或第三人的原因违约,普通法则是对本人的授权有严格要求。这种差别影响了直接效果的正当与否。首先,在普通法中,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对本人授权的要求,虽然难以在教义层面上解释委托人为何能成为合同的当事人,但至少能在价值层面上正当化这种法律效果。虽然第403条提到了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但在我国法下,代理关系是委托人授权受托人以委托人名义订立合同,和普通法的授权内涵并不相同。而且,如果受托人应以委托人名义行为时,受托人以自己名义行为在普通法上也不能约束委托人。其次,第403条以违约为要件,意味着直接效果建立在违约之上,这更像是让委托人和相对人充当对方履行“保险人”的权宜之计。而且,以违约作为直接效果发生的前提,并不能有效实现让委托人直接取得物权,以促进物的流通和交易进行的目的,不符合显名原则的例外通常要实现的功能。因此,如果第403条的效果是使委托人成为合同的当事人,无论在教义上还是价值判断上都不够恰当。
第403条规定的介入权和选择权也不产生类似大陆法的权利层面上的直接效果。虽然介入权和选择权让委托人和相对人有彼此直接主张权利的可能,但这并非直接取得。通过分析介入权和选择权法律效果的性质就可得出这一结论。
就介入权的法律效果,有两个有助于进一步解释的因素。其一,委托人可以行使的是“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③在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代理公约第13条第2款第1项中,这更是被明确为受托人为了委托人而取得的对第三人的权利。参见Convention on Agen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Art 13。并且,委托人行使这种权利时,第三人也可以对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从文义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受托人是为委托人取得权利,但委托人在介入后行使的是受托人而不是委托人的权利。在标的是物权时,委托人的权利也只是针对相对人的对人请求权。④类似的观点,参见前注④,杜颖文。其二,第403条所借鉴的国际条约即《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第13条第3款和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4条,都规定委托人若要行使这种权利,需要对代理人和相对人发出通知,一旦相对人接到这种通知,就不能再向代理人履行。通知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譬如可以和要求受托人披露对方的要求一同做出。⑤Howard Bennett,Agency in th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 and the UNIDROIT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2004),Rev.dr.unif.2006,p.778.从《合同法》的立法资料来看,委托人行使“介入权”时也需要通知代理人和相对人。
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笔者认为,委托人的“介入权”是一种形成权,产生(受托人对相对人的)债权让与(给委托人)的法律效果。事实上,就构成要件而言,第403条的规定替代的只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让与合意,考虑到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委托人本也可以依据委托合同要求受托人让与这种请求权,①行纪中也是如此。例如,依据《德国商法典》第384条第2款,行纪人有义务向委托人交付处理事务所得。法律的这种规定只是程序的简化。通知则本来就是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通常被解释为包含第三人和受托人明确约定禁止他人介入、第三人纯粹基于对受托人个人的信赖订立合同、需要受托人亲自履行的合同、第三人曾经和委托人订约而怀疑委托人的信用和履行能力等情况。②参见前注輪輯訛,王利明书,第829页。这与债权不能让与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③债权让与中,在存在当事人的禁止转让特约时,该特约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69页。由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委托人很难被认为是无过失的善意第三人。更重要的是,介入权的法律效果和债权让与的法律效果完全一致:委托人行使的是受托人的权利,接受相对人对受托人抗辩。介入权和债权让与在抵销规则上也相同:在普通法的不表明本人身份的代理和大陆法的行纪合同中,于委托人可以直接对相对人主张权利的场合,相对人都可以自己对受托人的债权对委托人主张抵销,债权让与的抵销规则没有什么不同。这可以使相对人的地位不因为委托人介入权的行使而恶化。
就选择权而言,解释起来并不如介入权那样清晰。不过,不可忽视的仍然是关于抗辩援用的规定。选择权下的抗辩关系和介入权不同,委托人不仅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还可以主张自己对受托人的抗辩。国际公约作出这种设计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为了保证委托人的地位不会劣于第三人没有选择权的情况;二是虽然委托代理涉及三方关系,但大致上仍可以认为第三人是一方,委托人和受托人是另一方;三是如果委托人对受托人拥有债权,委托人就此债权能够对第三人主张抵销,是参与制定公约的各国能够达成妥协的重点。④Malcolm Evans,supra note 59,para.75.
这种抗辩机制的设计尽可能的维持了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原有的抗辩关系和信赖关系,也有助于对选择权的解释。依据这种法律效果和其设计思想,笔者认为选择权是一种免责的债务承担,具体来说,是债务人(受托人)和第三人(委托人)达成债务承担协议且债权人(相对人)同意的债务承担。就构成要件而言,选择权的法律规定替代的是债务人和承担人之间的债务承担协议。和介入权的情况类似,这种规定是程序的简化和成本的节约。因为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履行债务的最终来源是委托人,在第三人选择权中,基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关系,受托人和委托人不需要达成债务承担协议,法律直接拟制这种协议的存在。在法律效果上,第403条的抗辩关系和债务承担中新旧债务人之间达成免责债务承担协议的抗辩模式相同,新债务人可以对债权人主张旧债务人的抗辩和新债务人对旧债务人的抗辩。⑤参见前注輬輮訛,韩世远书,第490-491页。因此,第三人选择受托人作为相对人可被认为第三人拒绝这种债务承担,债务承担不发生效力;第三人选择委托人作为相对人可被解释为第三人同意这种债务承担,委托人成为义务的承担人。
因此,所谓介入权和选择权是一种精巧的设计,是以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委托合同为立足点,解决受托人和第三人之间债务不履行的问题。委托人介入的后果是委托人主张受托人的权利;第三人选择委托人导致委托人履行受托人的债务。如果受托人和相对人正常履行合同项下义务,并没有介入权和选择权发生的必要。因此,介入权和选择权的目的,是在例外情况下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⑥Malcolm Evans,supra note 59,para.72.而这种例外情况主要是代理人的不履行或者不愿履行的情况。⑦Michael Joachim Bonell,supra note 60.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介入权和选择权的发生需要有代理人违约作为构成要件。①《合同法》第403条规定受托人因为委托人或者第三人的原因违约,事实上,从介入权、选择权的立法目的和相关的国际文件来看,强调的是受托人违约,是否因为委托人或者第三人原因违约并不是重点,因此第403条有构成要件过狭的嫌疑。类似的观点,参见刘芳:《论间接代理委托人介入权的行使——兼谈〈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的完善》,《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无论是介入还是选择,委托人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在受托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之上,本质上是受托人的权利与义务,因而并不是一种直接效果。
介入权和选择权的功能和显名原则之例外所欲实现的保护委托人利益、让委托人尽早取得合同项下物权的功能也并不相同,这进一步证明介入权和选择权并不是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能够发生直接效果的情况。作为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的适用,介入权和选择权确实是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但并没有突破到发生直接代理效果的程度。与其说第403条(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是借鉴普通法不表明本人身份代理,不如说其是建立在大陆法系逻辑和传统上的创新。第403条确实是以受托人的自己名义为构成要件,但并不产生直接效果,因此也不是显名原则的例外。
顺便提及的是,第403条的这种模式脱胎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代理公约》的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主要是商事领域,特别是大陆法的行纪合同。介入权和委托权的设置,也更有利于商事交易中的当事人直接主张权利义务,避免讼累。因此,虽然置于委托合同,但第403条更应该适用于行纪等商事交易,适用于民事委托反而会产生“商化过度”的问题。因此,认为第403条只适用于非行纪的间接代理是不妥当的。②这种观点参见尹田:《民事代理之显名主义及其发展》,《清华法学》2010年第4期。
五、结论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代理制度的需要,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公司等组织体对于代理的需求,显名原则在内容和表示方式上都有缓和。就内容而言,代理人在显名时不再必须确定被代理人的身份,而是表现出被代理人的存在即可。就方式而言,尤其是在商事领域中,代理人不再需要明确地显示被代理人,而是可以通过默示的行为甚至沉默来表示,只要结合客观情境和商业惯例,合理谨慎的相对人可以相信代理人是在为被代理人进行交易即可。
显名原则的缓和扩大了显名制度的涵摄范围,但例外规定仍有必要。显名原则的例外是,虽然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相对人也以为交易的对象是代理人,但是代理人的行为仍然能够对被代理人产生直接效果的情况。虽然英美法和大陆法中都存在这种例外,但彼此的构建并不相同:大陆法对构成要件的要求比较宽泛,但限定法律效果的范围,英美法的做法则相反。这种例外规定是为了满足商业交易的快捷性和简便性,主要是为了让委托人能够及时获得合同项下的权利,特别是物权,从而避免传统的通过受托人行使或者受托人转让权利可能发生的迟延损失,规避标的物仍在受托人处时被受托人债权人执行的风险。
我国《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确立了显名原则。虽然我国《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也有受托人以自己名义行为的规定,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显名原则的例外。第402条只是显名原则缓和的体现,被代理人名义和存在的显示不必以代理人的明确表示为必要条件,并不是真正的代理人以自己名义行为的情形;第403条虽然是受托人(代理人)以自己名义的行为,但法律效果是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制度的特别适用,委托人行使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在实质上是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没有直接效果的产生。因此,在我国代理立法和实践中,只有显名原则,而没有该原则的例外,直接效果的发生均需要以被代理人名义的显示为要件。
(责任编辑:陈历幸)
DF51
A
1005-9512(2016)01-0076-14
殷秋实,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