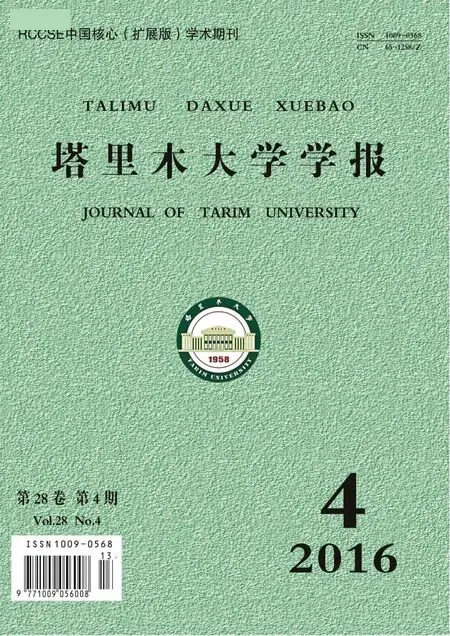丝绸之路上的齐兰古城
2016-02-11孙长龙
孙长龙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丝绸之路上的齐兰古城
孙长龙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文章对新疆柯坪县齐兰古城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研究,认为齐兰在明朝就以聚落出现,而路经齐兰的丝绸之路中道可以上溯到唐代。清代齐兰作为军台在道光八年设置,20世纪20年代废弃,存在约百年之久。柯坪县红砂河上游开垦荒地及齐兰渠得不到有效管理促使水资源短缺是齐兰台废弃的主要原因。
丝绸之路; 齐兰; 军台
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阿恰乡的“齐兰古城”又称“阔纳齐兰遗址”,现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阔纳齐兰遗址”是对清代西路军台天山南路台站体系中“齐兰台”遗存地面建筑群的称呼。台站是我国边远地区所设置的一种类似驿站的机构,是对驿站、军台、营塘等交通、通讯转运机构的总称。台路由台站构成,是连接天山南路绿洲城市的生命通道。
在清代,影响新疆和平与稳定的和卓后裔之乱以及阿古柏之乱等都以毁坏台路为重要目标,意在切断中央王朝与天山南路诸城市的信息往来,对中央王朝在天山南路的控制与管理构成威胁。因此军台及台路的安全与畅通直接关系到天山南路的和谐与稳定,进而影响到清朝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关于齐兰古城的史地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连接丝绸之路中道(一般指经行天山南路,从今吐鲁番到喀什的路程)阿克苏—巴楚段的走向很有帮助。通过齐兰军台的兴衰对于认识塔里木盆地上类似区域绿洲变迁、促进城镇生态可持续发展很有帮助。
1 有关齐兰的历史与考古调查研究
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亦力把里”图幅,“齐兰”标绘在克力宾(柯坪)之东、阿速(阿克苏)之西。[1]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新疆图幅中,齐兰台位于阿克苏回城柯尔坪回庄之东、浑巴什军台西南、叶尔羌回城伊勒都军台西北。[2]
一些地名词典认为齐兰为明代地名,在今其兰。齐(其)兰是维吾尔语‘其兰迪’的转音,有“浸湿”之意。齐兰也是军台及水系、草滩的简称,地近柯坪县其兰村一带。[3]
齐兰台及齐兰烽燧在清朝及民国时期官员的游记及中外探险家、考古学者的考察报告中就已出现(详后)。1949年后,齐兰台及齐兰烽燧的发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国家第二次文物普查。齐兰烽燧“坐落在阿恰乡齐兰村西南,……为唐代遗址。烽燧呈梯形状,……顶部及西南角已坍毁,现残高 18米。烽燧基部为3米厚的夯土层,每层之间夹铺树枝,上部用35×24×8厘米的土坯砌筑,每隔2层夹铺树枝。顶部土坯间夹有“井”字形木骨。”
阔纳齐兰遗址“位于阿恰勒乡齐兰村东6公里,……为清代驿站。遗址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西北方向的平台(亦称炮台)、官邸和较完整的城楼城墙。……城墙仅1道,南北向,长约80米,高约5米,墙头上规则地筑有近30个雉堞。……城墙北端筑长方形角楼,……官邸位于城楼之西约30米处,……地面残留有地砖,……一部分为东南方向的住宅建筑群,……住宅区内有1条西南走向、宽约5米的街道和纵横交错的小巷,城中有1个干涸的大池塘。”[4]
2014年7月笔者也对齐兰烽燧与阔纳齐兰遗址进行实地调查,两处遗址变化不是很大。 关于齐兰台、齐兰烽燧正式刊布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5]、《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研究》[6]、国家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阿克苏地区卷》[7]。
综上,齐兰台距齐兰烽燧约有8千米,学界认为前者在明代就已出现,清代为军台遗址,后者在时间上应属唐代。为了进一步揭示有关齐兰的历史文化信息,下面就丝绸之路中道上的齐兰和齐兰军台的建立、发展、废弃做一定的论述。
2 丝绸之路中道上的齐兰考辩
17世纪初,耶稣会士—葡萄牙人鄂本笃经由叶尔羌汗国(时为马黑麻汗统治时期)前往中原。鄂本笃于明万历三二年(1604)11月中旬起,跟随商团从叶尔羌(今莎车)出发用时近月余到达阿克苏,这段旅程见于冯承钧[8]、何高济[9]、张星烺[10]、刘俊馀和王玉川[11]等先生译著中,译文对其中关涉地名有相应考证。
在文铮关于利玛窦意大利文原著译本中,鄂本笃从叶尔羌用时二十五天到达阿克苏途经有十五座城,分别是“汉齐亚利克斯(Hancialix)、……侯尔玛(Horma)、托杨塔克(Toantac)、明杰达(Mingieda)、卡派塔尔科尔(Capetalcòl)、齐兰(Cilàn)、萨莱·奎贝达尔(Sare Guebedal)、坎巴西(Cambasci)、阿贡台尔泽克(Acon-telzec)、齐亚科尔(Ciacol)”[12]。文后著者引用尼维斯·阿加斯参考玉尔和威塞尔研究成果对上述地名做出了注释。注释中“Toantac即Tewan-Tagh,……Cilàn即Chilyan,……Cambasci即Kubbash”[13]。
上述译著对我们了解鄂本笃行程所经地方很有帮助和启发。虽然途径地名多有不识,但是有一些地名在其后二、三百年间还在使用。“Toantac”(Tewan-Tagh)应是今图木舒克市北的吐木秀克山,位于代热瓦孜塔格东南的第二个山口。1906年10月29日伯希和开始对今代热瓦孜塔格的托库孜萨莱遗址(唐王城遗址)进行调查,遗址所在为“齐干却勒”(今托库孜山)。齐干却勒南部的尖岬山即为“托万塔格”(Towan Tgh),意为下山。[14]
“Cambasci”或“Cambaso”(Kubbash),应是“库木巴什”,即元代的的“浑八升”城,《西域水道记》引《元史·耶律希亮传》中的“浑巴什”城[15],清代的“浑巴什”庄,即今阿克苏地区库木巴什乡之地。
“Cilan”、“Zilan”正如冯承钧先生所疑,应是齐兰。文铮所译“Cilàn”即是如此。这样我们大致知道,阿克苏到莎车,途经齐兰及连接图木舒克的道路在在明朝末年出现在西方耶稣传教士的著作里。如果将齐兰烽燧及其西南的雅依德、都埃、琼梯木等连在一起,则又勾勒出了唐代拔换城(今温宿)到据史德城(今图木舒克唐王城遗址)的驿路。
清朝统一天山南路后,在台路的设置上,阿克苏南行经浑巴什军台等,并未路经齐兰一地。但是我们发现,道光皇帝在平定张格尔之乱后调整台路,齐兰地方又出现在了史籍中。
3 齐兰军台的出现
3.1 乾隆时期西路台站天山南路的设置
天山南路军台是清乾隆时期,定边将军兆惠平定大小和卓之际初创。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兆惠等奏“自巴尔楚克至阿克苏应设台若干,行文舒赫德等办理。”[16]二十五年(1760)三月,参赞大臣舒赫德奏“阿克苏查询应设台站处所。……俱派察哈尔总管敏珠尔、原任副都统杨桑阿办理。”[17]
乾隆官修《西域图志》记载上述协办的阿克苏至叶尔羌台路,从阿克苏南行,依次经过“库木巴什台、英额阿里克台、都齐特台,南接叶尔羌属伊勒都台界。”[18]同一时期的《新疆回部志》[19]、《西域闻见录》[20]收录阿克苏赴叶尔羌路邮驿、军台与《西域图志》大体一致。显而易见,乾隆时期阿克苏到巴尔楚克的台路是不经过齐兰的。
3.2 道光年间阿克苏—叶尔羌台路调整及齐兰台的设立
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之乱后,叶尔羌路台站大多毁于战火,叶尔羌境巴尔楚克台东北台路又多受喀什噶尔河下游水患影响,往往阻塞台路。
道光八年(1828)九月十五日,钦差大臣那彦成等为求长久计,上奏移改阿克苏、叶尔羌二城军台道路。阿克苏境自“雅哈库图克一百里至齐兰设台一处,自齐兰一百二十里至萨伊里克亮噶尔设台一处,自萨伊里克亮噶尔五十里至浑巴什河归并旧路”。[21]同年十月道光帝谕批,“著照所请,所有阿克苏境内移设军台二处。”[22]十一年十一月,又以新改台站路程较远、行旅困难,添设腰站以供打尖及补充车马等。“著照所请沙井子地方分设腰台一处,即令齐兰台笔帖式兼管。色瓦特地方,分设腰台一处,即令雅哈库图克台笔帖式兼管。……以资接递运送。”[23]此处添设腰站、腰台即主要是因原有台路已定,而所设台站间路程又相距较远,补给困难,所以对台路略微调整以方便行旅往来。
随着道光八年台路的调整及十一年沙井子等腰台的添设,阿克苏到叶尔羌台路逐渐稳定。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自阿克苏前往叶尔羌勘定田亩就由新改设的台路前行。途径浑巴什台、萨伊里克台、沙井子腰台、齐兰台、色瓦特腰台、雅哈库图克台等至叶尔羌城。[24]
由此可知,道光八年阿克苏境内移设军台二处,是以齐兰台代替都齐特台、萨依里克台代替英额阿里克台。都齐特、英额阿里克二台自乾隆二十五年设立到道光八年弃用,存在了约七十余年。
4 齐兰台的机构设置和职能
4.1 齐兰军台机构的设置
齐兰军台的管理机构及应差事宜,据舒赫德奏文可知。“请每台派回人十户。兼绿旗兵五名。识字之健锐营前锋或西安兵一名。以六品顶带署笔帖式管理。每台马十五匹,驼四只。……回人等一体给与口粮及盐菜银两。于十户中派出首领一人,以七品顶带管理。台站附近地亩,仍令自行耕种。……得旨、如所请行。”[25]
又据《回疆通志》所载“每二台设委笔帖式一员,每台派绿营兵五名,回子十户,马十四匹至十七八匹不等,牛二只至十七八只不等,车二辆,共骡四头、共驴四头。”[26]
由以上可知,台站以六品顶带笔帖式主守土之责,由台站旁民户派出的首领协助笔帖式维护治安,其本人受七品顶带管理。台站有绿营兵五名防卫台路安全。台站旁的十余户居民除了应差外,闲时种地。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有马、牛、骡、驴等牲畜,所用车辆较少。
4.2 齐兰军台在维护台路安全畅通方面的作用
在新疆南疆,由境外流窜至南疆的贼匪往往以毁坏台站、阻断台路来削弱清王朝对新疆的统治。如道光十年玉素甫之乱,“叶尔羌军台,道路阻断,文报不通。齐兰台当差回子,亦有变乱等语。”[27]道光二十七年七和卓之乱,清军平叛后对“此次伊犁续派在齐兰戈壁防堵之满汉各兵丁,所领赏银,著加恩概免扣缴。”[28]咸丰七年阿克苏属柯尔坪出现匪乱,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朴奏“齐兰军台剿贼获胜,并派兵防守情形。”[29]同治年间阿古柏入犯本境“在齐兰台筑堡驻兵,为进东四城后路,基址犹存。”[30]
一旦台路发生毁坏、台站附近村庄发生匪乱等突发事件,台站将会是“千里眼、顺风耳”,其在维护台路畅通、地方稳定方面有十分重要的应急作用。
齐兰台除了维护台路安全方面作用外,也是这一地区重要的商贸、行旅往来的集散小站。新疆建省后,喀什噶尔为俄商南路重要商埠,阿克苏道温宿府设有三个卡伦沿防绕越,其中南卡便设在齐兰台,“以查通喀什商路,虽按约暂不纳税,无事稽征,然以任保护、司严伪冒之罚、杜绕漏之弊。”[31]
5 齐兰台的废弃
5.1 齐兰水与齐兰渠
光绪十八年(1892),叶城典史王廷襄与齐兰台民人有段对话,对我们了解齐兰台废弃原因很有帮助。“此处,两老渠自北而南,西面一渠虽未废,本年亦未修,居民乏水。东面一渠惟前任江修过一次,以后二任皆未修,东渠遂废。”当问到为何不自修,而坐受其困时,民人对曰:“百姓愚,现在头目老不能做事,必得州大老爷谕知乡约督工兴修始能济事。”[32]齐兰渠在台站分东、西两渠,时至此时,东渠已废、西渠不畅,要知水利乃民生之本。
齐兰东西二渠的渠首在何处?渠水水源又在何处?查阅《新疆图志》卷七十六《沟渠四》,发源于柯坪县西铁克里克山苏巴什沟的泉水东流六十里后,在沟口修筑围堰开南北两干渠,余水潜流经红砂梁后复出东流,又修筑阿碛渠于城东八十里,该渠“导源麻扎而克沙阜”。阿碛渠又分支渠二:一为阿碛新渠;二为齐兰渠,在“城东九十里,……长九十里,广五尺,今灌田三千四百九十余亩”[33]
齐兰渠水引自阿碛渠,阿碛渠水又源自柯坪县西的苏巴什沟泉水,“其源出城西南空潭山峡中”,“经柯尔坪庄南,折而东北流五十里分二枝,一东流五十里入黄草湖,其正枝东流一百六十里入齐兰草滩。”[34]《新疆志》提到齐兰水流经齐兰台“又东流十里伏于沙碛。”[35]
发源于柯坪县西苏巴什沟的泉水即现在的红砂河,因柯坪县及其东阿恰乡用水,河水散失在农田渠道中,已无余水入齐兰草滩与黄草湖。当齐兰渠得不到修浚与有效管理,加之上源开垦荒地、拦坝截水,齐兰绿洲就会遭遇因缺水而带来的生态危机。
5.2 齐兰台的水危机与新齐兰的出现
翻检有关天山南路的中外游记、科考报告,发现在清朝道光八年齐兰台设置到民国初年齐兰台废弃,路径此处的许多官员、文人、外国探险家等大都对此有详略不等的着墨。这些有着一百余年的记述,从时间和空间上向我们展示了齐兰所经历的历史变化。引文叙其精要,详细内容参见所引资料。
前述,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六月间,林则徐奉命勘定田亩,沿着台路来回两次经行齐兰军台。“台馆虽有两所,均极湫隘,且不洁净。”[36]“台馆殊劣,水亦苦咸,来时未住,今夕勉宿于此。”[37]由林公所记,齐兰台馆有两所,比较狭小,水质不是很好。此后叶尔羌帮办大臣倭仁于咸丰元年(1851)[38]、叶尔羌参赞大臣景廉于同治三年(1864)曾路经齐兰台[39],可惜对台馆着墨不多。
1876年12月俄国人库罗帕特金经过的池良庄(齐兰)有二十余户人家。庄上有一个广场,有两个池塘,有一所用烧过的砖建成的大客栈,每面墙长二十五俄丈(1俄丈≈ 2.134 米,计周长约214米)。另外还提到离“建筑物”不远的一个直径约13米的池塘。客栈的水略有咸味。[40]
1906年12月,伯希和从图木舒克到阿克苏途中,停步于齐兰。这里共有40多幢房子。齐兰台作为清朝兵营,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才撤销。该兵营附属于阿克苏,而村庄本身却附属于柯坪。它形成了今天已经坍塌的带枪眼的城堡。[41]
1907年2月据芬兰籍俄国军官探险家马达汉掌握的齐兰资料,齐兰村约有5 000亩土地由40户村民分享。由于缺水和盐碱性土壤影响,每年只有部分土地可以耕种。[42]同年7月日本军人日野强经过齐兰台,这里有约五十户居民,饮用涝坝蓄水,苦咸而且污浊。[43]
1913年6月德国人勒柯克到达齐兰,有一座由几十名士兵守卫的小堡垒,有一口保存得很好的大池塘里汇聚了相当好的水,但是1908年他到此地时,水质还是比较苦咸。[44]
1915年5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描述其兰(齐兰)说这里约有30多户人家,房舍聚集在两座堡垒遗址周围。来自柯坪的水流仅仅能流阿恰新垦的土地上。1931年4月因齐兰已放弃,斯坦因去了央吉-齐兰(新齐兰),也叫库姆-基齐克,这里约有30户人家,水渠里的水汇入了一个涝坝中。[45]
1917年6月谢彬奉民国财政部命赴新疆调查财政路经齐兰台时,车店民居共30余家,涝坝水极苦咸,十里外山泉水味道亦苦。有居民赴西南三十里许库尔地方种田,至秋收后方回开店。希望从浑巴什河开渠引水浇灌齐兰。[46]
1929年因为旧齐兰水味咸苦已无人家,黄文弼到达的是新齐兰,而新齐兰的水也常咸。[47]
综上,通过上述游记的描述,我们可以对齐兰台有个大概的认识,它由兵营与村庄两部分组成,中隔以带角楼的残存城墙,砖修的建筑物就是台站的馆舍。这里的常住居民约有30余户,饮用的水源来自柯坪盆地的齐兰水,齐兰水流经阿恰后,横穿戈壁通过东、西渠到齐兰台后,保存在一个大涝坝中,水的矿化程度较高。流经齐兰戈壁的齐兰水不仅水源短缺,而且水质堪忧,从道光八年(1828)在齐兰戈壁上新设齐兰台,到20世纪20年代最终弃用,齐兰台存在时间约有百年。
斯坦因1915年提到来自阿恰的水仅能到新开垦的土地上,谢彬1916年提到齐兰台的壮年人在西南30里的许库尔地方种田,这个新开垦的种田的地方就是新齐兰也就是斯坦因提到的库姆-基齐克。因此,齐兰水流不到齐兰台应是其废弃的直接原因。
民国7年(1918)4月25日,新疆省主席杨增新指令柯坪县佐李德良呈报称“齐兰台地方,如由阿克苏河及皇工渠接开渠道可垦地十万余亩,究竟该处何地高低如何?能否引水到地,仰即亲往会商金知事,勘察明确再行估工绘图呈候核办。”[48]柯坪县佐李德良上报阿碛修渠堵坝开垦时间与斯坦因、谢彬提到的阿恰新开土地及新齐兰的开发几乎在同一段时间,关于齐兰从阿克苏引水的呈文终未有果,面对极度缺水的窘况,齐兰台及齐兰绿洲渐渐废弃。
齐兰台的废弃和齐兰水上游地区土地的开垦有直接关系,因为齐兰水尾闾的缩短,旧齐兰废弃了,阿恰与新齐兰绿洲却逐渐发展起来。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需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类的能动作用,维持好已有绿洲的生态平衡,毕竟绿洲的转移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综上,文章对丝绸之路上齐兰的历史文化有一定介绍,并对明清时期途径齐兰的驿路(台路)有所辨析。文章对齐兰军台的机构设置、职能作用,齐兰周边的土地垦殖及齐兰军台的废弃也有一定的论述,通过齐兰绿洲的兴衰对于认识塔里木盆地上类似区域绿洲变迁、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有关齐兰古城遗址的属性及断代划分还需要进一步的田野考古调查研究。文章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88-89.
[2]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52-53.
[3] 史为乐.中国历史地面大辞典(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506;钟兴麒编著.西域地名考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718;解玉忠著.地名中的新疆[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186;冯志文、吐尔迪·纳斯尔、李春华等著.西域地名词典[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345-347.
[4] 柯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柯坪县志[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350-351.
[5] 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J].新疆文物,1995(4):57-99.
[6] 张平.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51.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阿克苏地区卷[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57,103.
[8]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101.
[9] 【意】利玛窦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554.
[10]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M].北京:1977:503-504.
[11] 刘俊馀,王玉川译.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M].台湾: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492.
[12] [13]【意】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23,428.
[14] [41]【法】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103,153-154.
[15] 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80.
[16] [17][25]清实录(乾隆).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己酉.卷五九六,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午.卷六百九,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壬寅.卷六百七.
[18] 刘统勋,傅恒等编纂,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卷之三十一·兵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445.
[19] 永贵,固世衡原撰,苏尔德增撰,吴丰培校订.新疆回部志·卷四·邮驿第三十六[M].边疆丛书续编之五,1950年油印本.
[20] 七十一撰.西域闻见录·卷八·军台道里表[M].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21] 容安辑.那文毅公筹划回疆善后奏议·卷七十五·量移军台路,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一辑)[M].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8737.
[22] [23][27][28]清实录(道光).道光八年十月葵未.卷一百四十五,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壬申.卷二百一,道光十年九月乙丑.卷一百七十三,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乙丑.卷四百五十二.
[24] [36][37]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九册)[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4742-4746,4758.
[26] 和宁撰.回疆通志·卷八·叶尔羌,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M].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264.
[29] 清实录(咸丰).咸丰七年六月壬申.卷二百三十.
[30] 马大正等整理.新疆乡土志稿·柯坪分县乡土志·兵事录[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274.
[31] [33]袁大化修,王树枬、王学会等纂.新疆图志·卷五十六·交涉四,新疆图志·卷七十六·沟渠四,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1卷)[M].北京:线装书局,2006.513,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2卷)[M].北京:线装书局,2006:207.
[32] 王廷襄撰.叶柝纪程·卷下[M].清光绪刻本.
[34] 佚名.新疆四道志·温宿州图说·河流[M].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8:306.
[35] 佚名.新疆志·温宿州·齐兰水,国家图书馆编.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21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3:197.
[38] 倭仁著,李正宇点校.莎车行记(西北行记丛萃第一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84.
[39] 景廉撰.行程日记(一卷)[M].国家图书馆藏抄本,3.
[40] 【俄】A.H.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喀什噶尔[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67.
[42] 【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114.
[43] 【日本】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M].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183.
[44] 【德】勒柯克著,齐树仁译,耿世民校.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M].北京:中华书局,2008:28-29.
[45] 王冀青著.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525-526.
[46] 谢晓钟著,薛长年、宋延华点校.新疆游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185.
[47] 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487-488.
[48] 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M].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2143-2144.
Qilan on the Silk Road
Sun Changlong
(Institute of Culture of Western Regions, Tarim University, Alar, Xinjiang 843300)
The paper combed and studied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on the ancient city of Qilan in Keping County of Xinjiang.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city of Qilan had been existed as a settlement since the Ming Dynasty and as part of the Silk Road it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 Qilan was established as a military pos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aoguang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abandoned in the 1920s, existing for more than hundred years. The main reason for abandoning Qilan Post was over-cultivation of upstream of Hongsha River in Keping County and insufficient management of Qilan ditch which led to water shortage.
the Silk Road; Qilan; the military post
1009-0568(2016)04-0023-06
2015-1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XZS017);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QN2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开放课题(XY1402)。
孙长龙(1983-),男,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西域历史地理教学工作。 E-mail:sclldu@163.com
K928.6
A
10.3969/j.issn.1009-0568.2016.0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