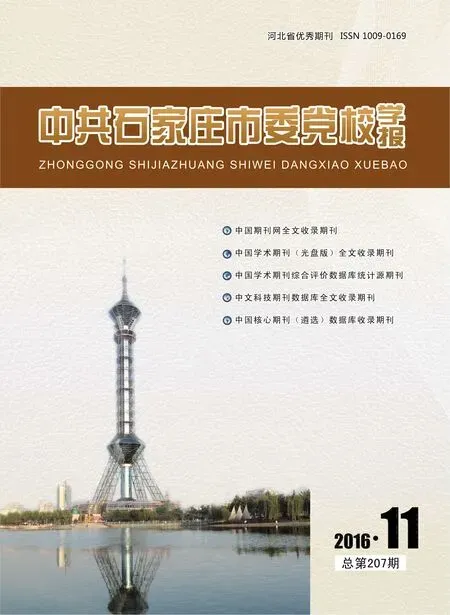中国梦:一种历史视角的解读
2016-02-11何红连
何红连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中国梦:一种历史视角的解读
何红连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的提出是历史传承与时代要求的统一。回顾近代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怀揣梦想不断前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中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中华民族始终在不断地寻梦、追梦和圆梦的过程中得以前进。
中国梦;中国共产党;人民;历史
“中国梦”的生成有一定的历史根基,其背后指向的是中华民族对“梦”不断追逐的历史延续,是最广大人民对中华民族未来的热切期盼和美好展望。回顾近代历史,倘若以“中国梦”为轴心建立一个坐标体系,从纵向坐标看,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梦”的追逐集中在两个层面的目标上:一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从横向坐标来看,人民群众对“中国梦”的追寻横跨三个世纪,集中在“两个百年”的时间坐标上,第一个百年是鸦片战争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个百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本世纪中叶。在整个坐标体系中,起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伴随三个世纪中“中国梦”追逐的是若干个阶段性目标,如邓小平同志曾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16,“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16,以及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四个全面”等等。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中华民族都是在不断地寻梦、追梦和圆梦的过程中得以前进。
一
中华民族在近代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顽强不屈的英勇斗争,尽管国际国内环境异常恶劣,尽管革命任务艰难险阻,尽管革命过程波动曲折,但这些都未能阻挡革命的热情,相反,革命浪潮由小到大不断地迅猛发展,直到1949年震惊世界的胜利。为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会涌现出一股又一股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革命浪潮呢?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原因就是根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个梦想,即尽快摆脱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苦难,尽快实现广大群众的民族解放。这是一场几代人在战争岁月中的“梦想”接力跑,也是几代人在漫长岁月中的精神寄托和行动指南。追溯这场梦的起始人,借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2]563。诚然,近代“中国梦”的启程一定程度上是孙中山先生开启的。但是,“中国梦”的生成并不是某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形势所迫,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英国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开始丧失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走上了半殖民地道路。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这深深地刺激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
亡,一批批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西方工业文化,如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详尽介绍外国情况以期睁眼看世界,又如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标榜“自强”“求富”,学习西方商业模式,建新式陆海军,以增强国力,维护清朝统治等。但是,这些努力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面前显得异常脆弱,一度产生的虚幻安全感在现实面前无力挫败、所剩无几。此后,清政府更是腐朽昏聩,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紧密拴在一起,“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3]。国之不国,广大民众在对清政府表现出极大不满与愤怒的同时,显出更多的是对中国道路的迷茫,甚至分歧。如当时谭嗣同写下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4]其诗悲痛,满怀一颗爱国之心,可以说,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民众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国人渐渐明白“自强”和“求富”并非中国当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救亡”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人们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抵抗外国侵略不能单靠朝廷的力量,而要靠国民的共同奋起。
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人民要奋起,要实现“中国梦”,单单靠一股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和勇气是远远不够的。孙中山先生相较于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态度明朗,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在《民报发刊词》中鲜明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主张用革命手段实现它,这在当时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种新的目标。“在他以前或辛亥革命时其他思想家也许在某些问题的认识深度上超过了孙中山,但从总体上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或代替他。”[5]辛亥革命虽然“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到了,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使中国从此走上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实现人们原先对它的期望。正如董必武所说,革命的结果,建立了民国,但“根本没有打碎封建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更是原封未动”[6]。袁世凯取得政权后,表面上“矢忠共和”,表示尊重议会的“神圣权利”,事实上却完全变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初年这场革命留给中国人的一笔重要精神遗产。面对革命的退潮,国人眼前又出现了黑暗。旧的路已经走不通,可新的出路在哪里?吴玉章回忆当时许多人共有的心情,“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呀!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到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自杀的道路”[7]。
但是,严峻的现实终究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消极、苦闷和彷徨中。在这以后的短时期内,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思想界卷起一股提倡尊孔读经的逆流,这些活剧一幕紧接一幕地在中国社会舞台上演出。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8]1470既然辛亥革命未能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先进的中国人必然要继续探寻解救自己国家于危亡的真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一场启封建之蒙,催促青春中国之诞生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起了。
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林伯渠、朱德等,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接受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而且他们大多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曾经出生入死地投入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从爱国到革命,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走向了共产主义者。
可以说,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到康有为、梁启超推动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前仆后继,英勇奋斗,都是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梦”,但都没有成功。直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了前辈的梦想和精神,承担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9]343。
确实,自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不仅严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更是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为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10]“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技术手段的怀疑和否定;维新运动的发动,意味着开始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价值追求的怀疑和否定。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则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专制集权式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已经无法为正在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指引解救的方向、提供价值上的归属。资产阶级革命者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引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但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许多心系大众的先进分子感到仍然需要寻找理想的方向和道路。新文化运动是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探寻救国的道路和方向。巴黎和会破灭了许多人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幻想,俄国十月革命却在许多人价值迷失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如果说,林则徐、魏源、薛福成、曾纪泽、郑观应、左宗棠、丁汝昌、邓世昌等人反抗侵略是以对民族的深厚情感和对清王朝的忠诚为精神动力的话,那么,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邹容、秋瑾、朱执信、宋教仁、蔡元培等人不但是以对民族的深厚情感,而且是以追求以美、英、法为榜样的新的国家前途为其精神动力。但是,巴黎和会对中国维护主权合理要求的漠视和对列强侵犯中国利益的纵容,使中国许多先进分子对英法式民主制度深感失望,转而向往俄苏式民主制。以俄为师,推动了中国部分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8]1471“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8]1516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道路和提供的价值目标逐渐为许多人接受。
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自觉意识到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从而具有了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不仅要求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而且追求民族振兴和人民解放;不仅要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追求每一个自身全面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谈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1]63
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破除阻滞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适应着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明确地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任务和斗争目标;另一方面也适应着中国人民解放的要求,明确提出了价值追求目标: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统一、富强等。这就使共产党的思想、主张不但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而且具有崇高性、权威性和吸引力;使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党派的斗争和竞争中始终占据着思想文化的制高点和主动性。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12]此后,在抗日根据地,追求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梦想则是抗战时期广大中国共产党人的明确口号和行动指南。1938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又提到:“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2]134“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站在争自由与争平等的人们一起的。”[2]170他充分肯定边区是个好地方,“这里有自由,有平等”[2]170。这就表明了边区虽然经济上贫困,但是边区有着明确的价值追求。事实上,毛泽东还希望以边区的自由、平等来影响全国,边区“要做一个样子出来,给全世界看,给全国看,给华北华中看,给西安看”[2]171。
中共七大前后,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党中央进一步确定了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路线、纲领、政策”[11]431,再次重申了“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8]19的主张。这种占领思想文化高地的策略使共产党赢得政治上的主动优势,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
人民民主共和国”[9]114的主张,不仅从国家性质、政治体制方面,而且开始从价值功能方面勾勒新中国的轮廓。到1952年毛泽东还明确要求:“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13]224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也是共产党人为中国指明的发展方向,是团结、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的旗帜。1954年毛泽东提出新阶段广大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3]329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可以说,“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主要是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它符合长期贫困落后的中国人民希望迫切改变现状的心愿,因而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
但是,“四个现代化”毕竟只能以其蕴含的“富强”的价值含义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一个部分,而不能代替具有丰富内涵和饱满内容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这就导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出现了内容狭窄,价值追求方向迷茫的问题。这种“狭窄”和“迷茫”,实际上就是后来邓小平所深刻指出的,是“我们过去”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结果。[11]63这样,首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上(如“大跃进”运动)出现了失误;接着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宗旨、道路上(如不主张老百姓致富,认为富了就会变修;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估计不足,甚至自我限制、自我封闭或半封闭等)出现了偏差。尽管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制度、体制主要是按照理论原理设计出来的,而不是按照现实的社会情况和现实的人的需要设计出来的,这就使这种制度、体制具有很强的教条性而不能很好地体现人的需要的价值内涵。
与此同时,从1957年开始产生的“左”的错误逐步发展,在社会上形成了对毛泽东崇拜的潮流,“毛主席”(他的语录、指示、思想等)成为衡量一切正确与否的标准,这就意味着社会上形成了“领袖至上”的价值取向。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把这一价值取向作了高度概括:“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会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适应着这种形势,毛泽东倡导的阶级斗争观念逐渐发展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念,“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就是这种价值观的通俗表达。毛泽东向往的“均平社会”也成为人们向往的理想社会,而其中的“平等”则成为当时社会的价值追求。“平等”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种价值,但是,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它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富裕、民主、自由、和谐、文明等价值组成的价值体系单独作为追求的目标。离开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单独去追求平等,结果只能是走向普遍的贫穷的均平主义。这就使得中国社会发展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行的拨乱反正,在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战线的同时,也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三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14[15]。“富强、民主、文明”的梦想价值追求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主要内容,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
进入新世纪,当中国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社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新的利益群体,原有的利益格局逐渐被打破,出现多元的价值追求。面对这种新情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
“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什么”等重大价值原则问题,从价值主体的角度,凸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以人为本”中的人,既是指中国人民,也是指每一个公民,是群体与个体的统一。围绕着以人为本,满足主体——人的各种需要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富裕、公正、正义、自由、民主、文明、和谐等正在逐渐整合到社会价值体系之中。“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的梦想追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竞争力,使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与人民群众个体的价值追求越来越具有一致性。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成为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目标。[16]“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目标,是适应了最广大人民的需要,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幸福,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在得到越来越多人认同的同时,也将越来越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价值——社会主义将是最符合人性、最有利于人生存发展的社会。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及“中国梦”,自此,“中国梦”一词人人知、人人议。“中国梦”的提出,依托的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优秀成果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是党和人民在肯定中国业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对未来的向往和期待。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前进方向和发展目标;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时间路线和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在治国理政中的战略重点。“中国梦”串联出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谱写出中国人寻梦、追梦和圆梦的灵动音符。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论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势[N].新民丛报(第二十号),1902:110.
[4]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488.
[5]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43.
[6]董必武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61-10-10.
[7]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101.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5.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2.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52.
[1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61.
[1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责任编辑:王玮玮
D616
A
1009-0169(2016)11-0019-05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网络媒介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研究”(15YJC71001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网络媒介中的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研究”(15SKS008)、西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4JY008)的阶段性成果。
何红连(1986-),女,重庆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