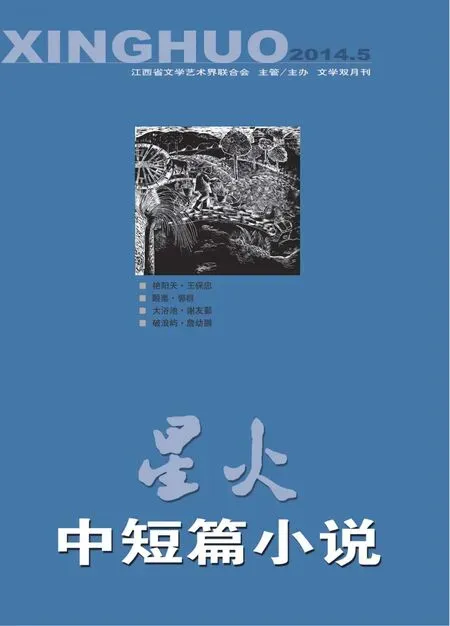三个底层文学青年的命运
2016-02-11吴佳骏
○吴佳骏
三个底层文学青年的命运
○吴佳骏

吴佳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花城》《大家》《天涯》《作家》《芙蓉》《山花》《清明》《长城》《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啄木鸟》等刊,著有散文集 《掌纹》《院墙》《在黄昏眺望黎明》《飘逝的歌谣》《莲花的盛宴》等。曾获首届、第四届“巴蜀青年文学奖”、第五届“重庆市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现为《红岩》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
引子
多年前,因工作关系,我认识了三个底层文学青年。他们分别叫:谢婷,黄谷,刘灿。黄谷写小说,谢婷和刘灿写诗。
那时候,写作是他们活命的方式,也是使他们获得自我拯救和灵魂皈依的方式。他们像一群流浪者,经常聚集在县城一个名叫“滨河”的公园里,追求文学的梦想。他们都来自于农村,学历不高,阅读量少,视野狭窄,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全凭对文学的热爱和青春的激情,以及情感长期被压抑后,需要释放和宣泄的渴望。
那个滨河公园,既是他们的文学营地,也是他们的心灵避难所和灵魂栖居地。似乎只有文学,才能唤醒他们沉睡的灵魂,让他们战胜生活里的一切黑暗和苦痛,并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和自由。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更迭,他们最终又都不得不远离了文学;甚至,刘灿早已不在人世。作为一个同样热爱文学的人,我觉得有必要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以此纪念几个曾与文学擦肩而过人,并借以献给今后那些无论人生遭受怎样的挫折,仍旧顽强地活着的人们。
谢婷
谢婷是这三个人中惟一的女性,在县城一个管件厂里当工人。管件厂坐落在城乡接合部,两根巨型烟囱直指苍穹。孤零零的,冷,硬。两排红砖修筑的厂房,古旧,灰暗。屋顶上落满陈年的煤灰。厂区外面的一条马路,被载重货车碾压得坑坑洼洼。下雨天,货车开过溅起的泥水,落在路两旁的行道树上,像被岁月涂抹了颜料,更像是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疤痕。谢婷每天就在这个像监狱一样的工厂里,面对一堆冷冰冰的钢铁,消耗自己美丽的青春。厂里的工人大多数是来自周边乡镇的农民,年龄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六岁。谢婷是因为逃婚才来到这家工厂的。在这之前,她的父母为她订了一门亲事。小伙子是邻村一个木匠的儿子,人憨厚,老实,在镇上开了家木器店,专门销售桌子、板凳和棺材。谢婷的父母对小伙子是交口称赞,并私下接收了男方的彩礼。而谢婷和那个小伙子却连面都没见过。直到小伙子的父母登门商量儿女结婚的事,谢婷才恍然大悟。她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以泪洗面。谢婷的父母迫于男方的催逼,整天咒骂谢婷,强迫她嫁人。她的父亲甚至以死相逼。谢婷无法承受精神上的重压和心灵上的折磨,终于在一个黑夜打着火把,沿着崎岖的山路,逃离了家,逃脱了父权的控制和命运的枷锁。后来,她还专门写过一首诗,来记录她人生的这次重大转折。
谢婷是在来到管件厂后,才开始写诗的。她说:我做工是为了活着,而写诗则是为了抵抗命运。每天早晨六点钟,谢婷就起床了。她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厂区草坪一个固定的角落看书或写诗。平时,她根本没有时间。八点钟准时进工厂,除了午餐和晚餐各有一个小时外,一直要干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谢婷住的是集体宿舍,统一开关灯,这极大地阻碍了她的求知渴望。有一次,她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被前来查房的主管发现,扣了半个月奖金,还写了保证书。主管告诫她,倘若再违纪,就卷铺盖走人。
工厂的呆板和坚硬,给这个内心柔弱而又耽于幻想的姑娘造成了无形的伤害。面对永不停止转动的机器,不知疲倦的流水作业,以及工友那一张张麻木、冷漠的脸,谢婷掩饰不住内心的悲伤。她感觉自己这个朝气蓬勃的生命,就这样被毫无生命的钢铁给肢解了,连一声喊叫都还来不及发出。
是诗挽救了谢婷。
谢婷所写的每一首诗,都充满了痛感。他们每次聚会,谢婷都会把新写的诗拿来念给大家听。有时念着念着,她便声泪俱下,听者也跟着难受。在他们几个人中,大家都公认谢婷是最有才华的一个。她的诗诚实,有内涵,对生存的体察细腻而深刻。她写过一首诗叫《被囚禁的人》:
钢铁没有生命,我没有睡眠
被囚禁的人,在流水线上歌唱
命运弄疼了我,像一块生铁
横亘在我的喉间。我的歌声
多了一种暴力的美。我的心上
长满了老茧。转动的齿轮
咬住我的青春不放。
疼痛再一次提醒我,我是一个
被囚禁的人,活在人间
抱住一堆冷硬的铁,取暖
我看见铁青色的厂房顶上
幸福丰收在望
这首诗曾在县内一家报纸上发表过,获得不少人的赞扬。大家都鼓励她把这首诗寄给《诗刊》,记得还是黄谷跑去邮局替她寄的稿子,遗憾未被采用。后来,大家觉得这首诗在内部报刊上发表太可惜了。又替她改寄到《重庆晚报》,但还是未见发出来。谢婷投稿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基层文学作者创作道路的艰辛。
即使不能发表,谢婷也照写不误。那两年时间,她总共写了三百多首诗。手稿码起来,有厚厚一沓。她的那些诗,除她自己外,黄谷和刘灿是她仅有的读者。
那时,谢婷最崇拜的诗人是舒婷。她只要一谈起舒婷的诗,就眉飞色舞,激情澎湃。她的枕头下,随时放着一本舒婷的诗集,那是她从一个旧书摊上买来的。书的封面已被她翻得破烂不堪。每晚关灯前,她都要抓紧时间翻上几页。不然,就睡不着觉。
凡遇工厂放假,谢婷就朝书店跑。县新华书店的几名工作人员都把她认熟了。只要进了书店,不到关门时间,她是不会离开的。谢婷的勤奋,以及对写诗的忠诚,深深地感染着黄谷和刘灿。他俩都以她为榜样。
每次聚会,他们都相互勉励。说只要坚持写下去,就能看到希望。
果然,2002年春节刚过,谢婷就收到广州一家杂志社寄来的样刊和五十元稿费。她的那首《被囚禁的人》终于公开发表了。一天,谢婷把黄谷和刘灿召集到滨河公园,她买了一包瓜子和花生,还买了四瓶可乐,说是庆祝一下。谢婷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她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黄谷和刘灿也从来没有如此兴奋。那本印着谢婷诗作的杂志,在他们三人手中传来传去,像在彼此欣赏一件宝物。那天,他们在公园里坐到很晚才各自散去。公园里的几棵垂柳,在夜幕下发出了嫩芽。
谢婷诗作的发表,让他们收获了成功的喜悦,也坚定了他们理想中的信念。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谢婷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首诗,竟成了她一生中发表过的惟一一首诗。
就在谢婷的诗作发表后不到两个月,她的父亲就跑来管件厂强行把她拉回了乡下老家。谢婷离开管件厂的时候,双手死死地抱着她那一沓诗稿。她的父亲一气之下,夺过她手中的稿子,掏出打火机,将之付之一炬。明亮的火光冲天而起,翻飞的纸灰像无数蹁跹的黑蝴蝶,把谢婷的诗魂带走了。
从此,谢婷手中紧握的笔,重新变成了粗硬的锄柄。
谢婷的父亲拉她回乡,是想让她照顾她生病的母亲。自从谢婷逃婚离开家后不久,她的母亲就偏瘫了。她的父亲每天要上坡干活,无暇照料终日卧床的母亲,便四处打听谢婷的下落。最终通过熟人得知谢婷在县管件厂上班,就立即跑来把她拖了回去。
谢婷回到家后,除了照顾母亲,还要出地干活,帮他年迈的父亲缓解生存压力。谢婷原本还有一个哥哥,几年前去广州打工,在工地上被预制板压断了左腿后,就在外面找了一个身体也有残疾的姑娘安家,靠摆地摊过日子,一直没再回来。
为尽孝道,谢婷招了一个丈夫入赘,安心过起了日子。
2004年秋天,黄谷约了刘灿去乡下看她。谢婷明显苍老了,生活已把她打磨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的母亲早已过世。他俩去的那天,没有见到她的父亲和丈夫,他们都去坡上干活去了。谢婷抱着她刚满周岁的儿子,坐在院子里陪他俩聊天。所谈内容已经无关乎文学,不过是地里的庄稼,坡上的羊和圈里的猪。
谢婷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她的儿子将来成为一个文化人,不再遭受她那样的辛酸和痛楚。黄谷和刘灿离开的时候,谢婷从柜子里拿出那本印着她诗作的杂志,用一个塑料袋套着,封皮还像新的一样,光洁,平整。谢婷说:这本杂志,我是为儿子留着的。
听她这么说,刘灿和黄谷都哭了。
黄谷
黄谷一直生活在乡下。白天种地,夜晚写作。在这三个人中,他是惟一没有离开土地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每天都站在大地上,扛着锄头跳舞。
黄谷的家乡离县城二十里路,中间只隔一座山。山下有一条河流,像一根柔软的绳子,将大山死死缠绕。黄谷进出都必须坐船,倘若去一趟县城,至少也要大半天时间。故若无特殊事情,乡民们一般是不外出的。交通的阻塞,使这里的环境更加封闭。贫穷是可想而知的。有的人活了一辈子,还没看到过汽车是啥模样。尤其是这里的男人,打光棍的特别多。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到这个鬼地方来。跑得动的人,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惟留下些老头老太,守着一座座高山。他们的暮年,像山一样孤绝和沉重。
黄谷是留在家乡不多的几个年轻人之一。
曾经,他也跟随那些外出打工的人群,去广州打过两年工。后因他父亲身体不好,而他又没有兄弟姊妹,就重返回老家,一边劳动,一边照顾父亲。黄谷是个有志气的年轻人。他想通过搞养殖业来改变贫困的生活。那几年,他在家里养了十几头猪。猪成了他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黄谷说:无论命运多么不济,人总得活着。他养猪所得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为父亲治病上。好几次,他的父亲流着泪劝他:黄谷,你辛辛苦苦养猪的钱,还是给自己存点吧,别只顾我,留着将来给自己找个老婆。可黄谷总是这样安慰他父亲:爸,你好好养病,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除养猪外,黄谷最大的快乐,就是写小说。
每天晚上,当父母都入睡以后,他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铺开稿子,在精神世界里畅游。他用手中的笔,写出一个个他所熟悉的人物。那些人物,都挣扎在底层,渗透着普通农民的血泪和悲欢。那既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也是底层广大农民的缩影。
他们每次聚会,黄谷都要谈他小说的构思。他常常会为自己的一个想法而激动不已,又常常因他小说里某个人物的命运而忧心伤怀。他的每篇小说都有一种沉郁的基调,字里行间弥漫着感伤。但他所塑造的人物,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从不绝望。他对主人公深怀同情和悲悯,又寄予希望和爱。
黄谷最崇拜的作家是路遥。他说他喜欢路遥作为一个农民作家所持有的平民情怀。他一直梦想着今生能够成为像路遥那样的作家。黄谷最爱读的书即是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他从路遥的作品里,看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和生为底层人的苦难。黄谷不止一次对谢婷和刘灿说过,每当他不堪劳动的疲惫,或因精神落寞而压抑之时,他就会想起《人生》里的高加林。是高加林的顽强和坚韧,以及对生活始终抱有的乐观态度,激励着他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勇敢地活着。
在他们三个人中,黄谷是读书最认真也是读书最多的一个。就拿《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书来说,谢婷和刘灿都只是听说过,并没有买来看。只有黄谷看了。他不但看了,而且至少看了五遍。在黄谷简陋的瓦屋里,还藏着其它一些书,如:《双城记》《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尘埃落定》《白鹿原》等等。这让刘灿和谢婷难以想象,生在乡下的他,是如何弄到这些书的。
黄谷写得最满意的小说,是那篇《乡间夏日》。小说讲述了一个乡村青年与他父亲之间的思想冲突,父亲是个思想守旧,勤劳朴实,对土地怀有深沉的爱的老人,而儿子则是个追求新生活,渴望自由,幻想与土地决裂的青年。父子俩在亦庄亦谐,妙趣横生的情节中,展开情感上的纠缠和观念上的碰撞,并对城乡文明做出了一些思考。这篇小说不长,不到一万字,几经辗转后,被辽宁一家杂志刊发了出来。
当时,在他们居住的县城里,能够在公开刊物上发作品的人并不多。黄谷小说的发表,曾在县城里搞文学的人当中引起过不小的震动。后来,在一次笔会上,县作协主席看到了黄谷的这篇小说,大加赞赏,并把他的事迹介绍给了县电视台。很快,县电视台的记者专门跑去黄谷的老家,为他拍了一集纪录片,片名叫做《大山深处的文学追梦人》。片子播出后,黄谷成了当地的“名人”。大家都以黄谷为骄傲。
但黄谷并不以自己取得的一点小成绩而沾沾自喜,也没把所谓的“荣誉”当回事。白天,他照样下地干活,喂猪。夜晚,就独坐灯下,用文字来编织梦想。冬去春来,黄谷就这样躲在大山的皱褶里,寻找生活的方向。那一座座高山,能够阻挡他的身体,却无法阻挡他的心灵。在那些寂静的深夜,他借助想象的翅膀,在大山上空翱翔,俯瞰着这个让他既爱又恨的山村。山下的河流,是他流淌的血脉,也是他精神的故乡。在黄谷的小说里,经常能看到他对家乡风物的描写——山上的风,黄昏的落日,盘绕的炊烟,孤零零的小船……每一样物事,都寄托着黄谷深厚的爱和深刻的痛。
黄谷最大的心愿,是出版一本自己的小说集。那次电视台的记者到家中采访黄谷,也给他父亲这个庄稼汉争了光。尽管父亲并不懂儿子写的东西叫小说。那次,记者对黄谷的父亲说,你生了个能干的儿子,会写书呢。于是,黄谷的父亲深深地记住了儿子是个会写书的人,并以此为荣。有一次,村委会主任到黄谷家窜门,黄谷偷听到父亲在村主任面前夸耀自己说:我儿子说了,到我死的时候,他要写本书给我垫枕头。
黄谷出书的念头,便是在那时萌生的。
每次到县城,黄谷都要带着他那厚厚的一沓小说稿,四处托人联系出版,可结果总是令他失望。那时,他对出版书籍一窍不通。以为像投稿一样,只要把书稿拿给出版社,就有人给出版。后来才知道,大多数人出书,是要自己掏钱的。就连县作协那些“作家”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是自费的,更何况黄谷这个农民作者。
县作协主席愿意帮黄谷出版书,但至少得花七千元钱。黄谷回到家后,内心经历着痛苦的煎熬。七千元钱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可出书也是为完成他父亲的愿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黄谷还是选择了出书。他把圈里养的那些猪,凡是能够出槽的,统统卖掉了,直到凑足了出书费用。
几个月后,黄谷的小说集顺利出版了。拿到样书那天,黄谷异常高兴。他分别送了刘灿和谢婷一本书,还签了名。可谁也没想到的是,黄谷出书的喜悦很快就被烦恼替代。书总共印了一千册,全部给了作者。面对堆满屋角的书,黄谷不知如何处理。这一包包书,是他用几头大肥猪换来的。痛苦像潮水一样包裹了黄谷。
出书几乎耗尽了他家中的所有积蓄,他不能让这大堆书变成废纸。
无奈之下,他想到一个办法,把书背到集市上去卖。
凡逢赶集之日,黄谷便早早起床,爬坡坐船,用背篓装着他的书去各个乡镇卖。到了镇上,他就找个热闹点的街边,拿一张塑料胶纸铺在地上,把书摆上去。刚开始,他还不好意思,觉得有辱斯文。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甚至,他还扯开嗓子吆喝了起来。来来往往的脚步从他面前走过,带起的灰尘覆盖了书的封面,却没有一个人买他的书。黄谷每天背着书出去,又原封不动地背着书回来。饥饿和疲惫像病痛一样折磨着他。内心的屈辱和隐痛,利剑般将他刺伤。刘灿目睹了黄谷的遭遇,十分痛心,想伸手帮他一把。他建议黄谷去各个中学的文学社团签名售书,可没有一个学校愿意放黄谷进去,不是嫌他身份低微,就是说他不够分量。
就在黄谷专心设法卖书的那段时间,他的父亲因疏于照料,病发从床上滚下来,去世了。灾难的陡然降临,使黄谷深受打击。他觉得父亲的死,应该归咎于他。出书原本是为了让父亲高兴,却不想断送了他的性命。自责和懊悔像两条毒蛇,咬噬着黄谷的肉身,并伤及他的灵魂。
埋葬黄谷父亲那天,下着濛濛细雨。黄谷长跪在父亲的坟前,痛不欲生。他一边哭,一边用蜡烛烧他的书。火光在坟头燃烧,雨珠在草叶上滚动,空寂的山野只剩下黄谷凄清的身影。那在火光中涅槃的每一个汉字,仿佛排着队在替黄谷的父亲送行。
黄谷的父亲死后,黄谷就再没写过小说。
刘灿
刘灿如果还活着,他现在或许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了。
刘灿给黄谷和谢婷的最初印象,是忧郁、孤僻和内向。他个子虽矮,却粗壮结实。一张黝黑的圆脸像是被放进砖窑烧过的陶罐。每次聚会,他都不大开腔,只是支愣着两爿木耳似的耳朵,静静地听。仿佛一个僧人,面对的惟有自己的内心。这跟他的作品气质非常吻合。他写的诗冷峻,安详,充满哲思,还有点宗教的意味。
刘灿原本不是本县的人。在谢婷和黄谷相识的前一年,他才随父亲从邻县的乡下来到这里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
据刘灿自己讲,他还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秋天的一个下午,他的母亲揣着他们家仅有的五千元存款,撇下他和父亲,以及还在读小学的妹妹,偷偷地跑了,至今音讯杳无。
母亲走后的那段时间,他们家陷入了绝境。刘灿每天放学回家,不是看到冷坐在院子里垂头丧气的父亲,就是看到蹲在门槛上哭泣的妹妹。他的父亲也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从来不跟子女谈心,每天只知道拼命地干活,以此来宣泄内心郁积的悲痛。刘灿和妹妹看到父亲如此伤心,一回到家里,就主动帮父亲操持家务。他的妹妹很懂事,煮饭,洗衣,喂猪,割草……样样都做,把家里的日常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他们希望以自己的行动来安慰父亲,共同走出生活的阴影,让他们这个残缺的家庭重新充满阳光。
可命运偏偏不肯放过他们。
刘灿的母亲走后不到半年,他的父亲即在一次锄地时,晕倒在田里。要不是被过路的邻居发现,及时将他送去镇上的诊所抢救,他恐怕早已离开了人世。父亲的病使他们这个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家雪上加霜。那段时间,刘灿和妹妹轮流请假回家照顾父亲。他父亲那次真是病得不轻,整整卧床一个多月,才在刘灿兄妹俩的精心护理下慢慢站立起来。
为给父亲治病,刘灿向左邻右舍借了近二千元钱。眼见自己的家一天天衰败下去,他们三人都忧心忡忡。父亲刚能下地,就又扛着锄头上坡干活去了。刘灿担心父亲的身体再出状况,根本没有心思学习。每天人坐在教室里,心却在父亲和妹妹身上。后来,刘灿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退学,以此来减轻家庭的负担。刘灿的妹妹看到哥哥退学,也哭着要求退学。但最终被刘灿说服了。刘灿说,如果真让妹妹也退了学,他的良心会一辈子不得安宁。
刘灿退学的那天下午,他们家的气氛一直都很沉闷。晚上父亲特意烧了两个菜,让刘灿和妹妹吃。可他们兄妹俩谁都没有动筷,父亲满脸的愧疚。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早早地就上床睡觉了。刘灿说,到后半夜的时候,他听见父亲和妹妹都躲在被窝里在伤心地哭。屋外的秋风撕扯着长夜,悲伤像一条大河,覆盖了他的身体和记忆。
刘灿的辍学使他父亲一直活在忏悔中,他觉得今生对子女有亏欠。因此,他一直在想法改变这个家庭的现状,力图使他们今后的日子过得宽裕一点。就这样,在刘灿一个远房叔父的介绍下,他们父子俩来到黄谷和谢婷生活的县城,开始了辛苦的打工生活。
刘灿和他父亲同住在工棚里,谢婷和黄谷都曾去看过。里面除了一张砖头砌的床和一床旧棉絮外,还杂七杂八地堆满了建筑用的工具。若遇下雨,整个工地上全是泥水。泥水流进工棚内,满棚潮湿。人呆在里面,一股寒气直往身上蹿。可刘灿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那样他就不用出工,可以安心地盘坐床上写诗。他的那些诗,都是忙里偷闲写出来的。刘灿的枕头边,放着几本厚厚的书。书的封皮被翻得残破不堪,其中两本是《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这两本书里大部分的诗,刘灿都能倒背如流。他喜欢古典诗词的意境,这对他的写作影响很深。他写的每一首诗,都精于构思,立意高远,平和冲淡。这是他与谢婷的诗不同的地方。谢婷的作品,更多的是在表达生存的痛楚。而刘灿的诗尽管也是在写现实生活,有疼痛和悲悯,但更多的却透出一种宁静和隐忍。按照刘灿的说法,正因为他在现实中经历过种种挫折和磨难,他才把诗写得清新,乃至唯美。他不想把刻骨的痛带到他的作品里去。他的作品是对未来的展望,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对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安慰。他曾写过一首诗《致妹妹》,很短,也很感人。
即使这个世界上只有苦难
我们也要学会爱,爱世界上
所有的夜晚,所有被苦难放逐的人
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小草依然
在生长,黄昏依旧在眺望黎明
大地是辉煌的,天空是辉煌的
每一条再荒僻的路,都有
先行者走过的脚印
学会爱吧,爱一切恨,爱一切悲
爱世界上所有惊心动魄的美
这首诗朴素,温暖。他们在公园里聚会的时候,大家也喜欢拿他的这首诗来诵读。有一次,谢婷过生日,三个人在公园里为她庆祝。那夜,晚风吹皱河面上的水,月光照着地面,像铺了一层霜。他们并排站在草坪上,齐声朗诵这首《致妹妹》。四周出奇地安静,只有草丛里的蛐蛐为三人伴奏。朗诵完毕,他们都沉默良久。然后,手拉着手,流下了泪滴。月亮似乎更亮了,黑夜并没有淹没他们。
刘灿几乎所有的诗,都是献给他的父亲和妹妹的。他说:父亲是我的脊梁,妹妹是我的灯光。他和父亲有个共同愿望,就是希望妹妹能够出人头地。他们在工地上打工所挣的钱,一半都花在了培养妹妹身上。
每个月,刘灿都要回老家去看望妹妹。自从他和父亲出来打工后,妹妹就一直寄宿在学校。每次回去,他都要给妹妹买点礼物。有时是一支笔,有时是一个笔记本,有时是一件T恤。妹妹一见到刘灿,总是喋喋不休地向他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如果获了奖,就把奖状拿出来在哥哥面前炫耀。这时候,刘灿就会从衣袋里掏出一首诗来念给妹妹听。念完就交给妹妹保存。他希望自己的那些诗,能鼓励妹妹健康快乐地生活。
刘灿从来不向刊物投稿。每次碰面,黄谷都建议他把诗往外寄一寄,可他总是谦虚地说:我写的那些破东西,还够不上发表的水平呢,还是先放放吧。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他写诗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他妹妹。在刘灿心里,只有妹妹才是他最忠实的读者。心情好的时候,刘灿也会把自己写的诗,念一两首给他父亲听。而他父亲总会说:你要是继续读书,该多好。刘灿听父亲如此说,就会笑着回答:难道不读书,就不活了啊。
黄谷说,他是亲眼目睹过刘灿在工地上劳动的情景的。矮小的个子穿着一件宽大的工作服,头上戴一顶沉重的安全帽。每当看到刘灿提着一桶满满的灰浆,在工地上跑来跑去的样子,黄谷就心头难受。刘灿的脸上溅满泥浆,双手都被灰浆腐蚀烂了。手背上到处都是红斑,还起了泡。黄谷不敢想象,一双能写出如此柔软诗句的手,却是那样的粗糙,浸透着鲜血。
刘灿的父亲最大的愿望,是给刘灿说门亲事。他曾多次托人给刘灿物色对象。可人家一听是个建筑工人,就心灰意冷,连见面的心思都没有了。刘灿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为让父亲心安,他也私下努力不少,拜托他认识的所有亲朋好友,为他张罗婚事。后来,仍是他那个远房叔父替刘灿介绍了一个姑娘。姑娘也是农村的,没读过什么书,自幼就被父母抛弃,跟着养父养母长大。由于彼此出生低微,两人互不嫌弃,情投意合,一说事就定下了。也了却了刘灿父亲的心愿。
遗憾的是,刘灿没有这个福分。就在他定亲后不到两个月,在一次送灰浆时,工架上的几根钢管突然间垮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头上。他的父亲哆嗦着身子,还没把他背到医院,刘灿就断了气。
安葬刘灿的时候,黄谷和谢婷都去了他乡下的老家,替他送行。那天,世界静悄悄的,没有锣鼓,没有鲜花,有的是刘灿父亲锥心泣血的呼喊和他妹妹绝望的哀嚎。黄谷和谢婷站在刘灿新垒的坟堆前,上了一炷香,泪水打湿了坟前的泥土。他俩都在心里默默祈祷,愿刘灿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
可就在黄谷和谢婷离开的时候,他们看见刘灿的妹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安放在刘灿的坟头。那个笔记本,是刘灿生前送给她的。笔记本上的每一页,都工整地抄写着刘灿的诗。个别短诗的结尾,还配有他妹妹亲手画的插图。目睹眼前的一幕,黄谷和谢婷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他那首《致妹妹》来。
花落无声,群山无言。
刘灿的灵魂和诗魂,可以安息了。